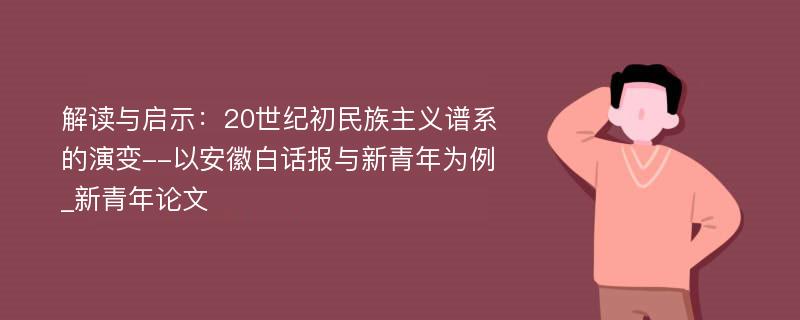
阐释与启示: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谱系的嬗变——以《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初年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安徽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2-0097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思想史上未能解决好的问题,也一直是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譬如有的学者就曾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演绎概括为“步步高涨的50年”[1]。在学术界对这一命题兴趣盎然的当下,如果细究民族主义思想脉络,《安徽俗话报》与《新青年》两种报刊可以为我们提供回环往复、发人深省的历史图景。或许这样的历史文本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对当下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纷争保持必要的冷静。
一、传统民族主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前现代状态
众所周知,就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而言,民族主义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当然,进一步分析还有政治、经济、文化之分,亦有“种族”(race)、“民族”(nation)、“民族国家”的辨析[2](P9)。鉴于我们的分析是两个时段的精神现象,所以笔者将以一个传统与现代直观判定来论述思想先驱从“立国”到“立人”、从“外竞”到“内竞”的转换。
简单地说,传统民族主义,即是基于本民族长期心理积淀的文化认同并力图保持这个文化秩序的稳定、完整和纯正性。当然这个纯正性可以有批判,但这个批判是修正式的、完善意义上的批判。而且即使是大敌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整个系统全方位解体时,文化的完整性还是最为重要,醒悟的思想者更愿意从经济、政治的原因上反思,但对文化的完整性却具有基本的捍卫。在这一意义上,民族主义的“民族”更多地被倾向于是一种“各种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3](P10)。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这个认同还没有完全摆脱原始、种族乃至生理成分,但它的“想象的共同体”特征却较固有的传统添加了很多现代性的因子[4]。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心理背景,出于对“外患”的担忧,陈独秀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个报纸的现代性意义虽然不如日后《新青年》在民主、科学之意念上的启蒙意义含量丰富。但其以“俗”字打头、重在唤醒国民的立意,却以浅文俗字开创了近代民族意识启蒙的先河。1904年3月,在创刊号的开办“缘故”上,主编开宗明义:“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消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5]主编的“第一门论说,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其实这眼前的事体以及“东三省”的事情,无非就是国家存亡、民族独立的“事体”。
创刊号上的《瓜分中国》带有鲜明传统、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他这样解释国情说:“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文章最后用极为浅白的话语告诉读者:“唉!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6]立于文化版图的地域共同体意识,主编的导向从“实业”、“矿产”、“教育”、“恶俗”到说“国家”、“亡国”论,其中关于国家存亡的论述百分之九十的比重,而且无不带有“外竞”的色彩。所谓“外竞”,即是群策群力,以一国或一族的力量一致对外[7]。《说国家》里自述自己生长到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8]。《亡国篇》里则有分明的炎黄子孙、文化中国意识:“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作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个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是可称作‘换朝’,不可称作亡国。”[9]
从陈独秀以及《安徽俗话报》作者着力强调的内容看,虽然它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不乏批判性,但他们的主要倾向还是在保忠报国、救亡图存上。这里的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一个抽象的、集合的概念。在民族立场上,也是一致对外的共同体情感。这一传统民族主义是独立的国家意识的前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在基本范畴上还不能与现代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它更多的处于种族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过渡带上。所谓种族主义,也就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同情的联系和团结的情感不超出群体的内部”[10]。中国人对外国人“洋鬼子”和外国人对中国人“中国佬”的称呼可以印证这样一种种族心理[11]。
二、现代民族主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
时至1915年9月,《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撇开其在创刊号上的开放意识和世界情怀,单就其“名副其实”的《我之爱国主义》等文就足以看出其文化民族主义情怀下沉,世界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情怀上升的趋势。及此,陈独秀的民族思想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主义。他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传统文化,而且走向了现代的政治诉求:民主主义。他和他引领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以开放的世界主义胸怀借鉴着舶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谱系,履行着以法兰西文明为取向的启蒙职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是一场启蒙运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先知先觉以民族独立、国家存亡为立足点,其着眼点从民主、自由、平等诸原则出发。在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民主的民族主义价值趋向,触摸到的是一段个人自觉、自立、自警、自爱的爱国主义历史。
众所周知,“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开创了新文化元典的格局,他们在比较东西文明差异的背后立意打造的是一个现代型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民主共和国排斥的是专制、君主、等级制度,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的新式制度。主撰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就将圭臬落到了法兰西政治文明的模式上:“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12]他在1916年2月15日的《新青年》上,不但将“政治的觉悟”作为起点,而且将“伦理的觉悟”这一被认为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启蒙难题捆绑在一起作为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现代的内因,立下了与传统文化的专制基因和政治毒素决战的誓言:“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度态,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在作了精辟的政治启蒙之后,他替国民做出了选择:“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13]尽管当时对共和制与立宪制的差异还不甚明了,但作者的政治立场却十分明确:义无反顾地将爱祖国、爱民族与追求民主、“共和”、“立宪”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喊出的口号“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声音在东方响起[3](P18-20)。
启蒙运动的最大特点是理性的自觉。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自觉与理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了起色。这同时也说明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自发、自觉并逐步成熟的。
在《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之间,1914年冬,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颇具有“过渡”意义。他在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说:“爱国者何?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在他看来,国家就是能够保障人民权利和幸福的实体,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若中国之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爱之也何居”。他甚至以一副无可奈何的放任态度说出了令李大钊义愤填膺的话语:“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也。”[14]李大钊特以《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回应陈独秀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15]陈独秀是不是断念爱国心呢?他在原文中说:“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还原其本意:“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14]
陈独秀此时的国家、民族理念以及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内涵。这种开放的情怀带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而且不是不要民族、国家的公民意识,他追求的是个人、国家、民族利益之间和谐互动的价值理想。这是现代理性启蒙的协奏,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孟德斯鸠的名言:“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他认定近世国家无不建立在民意之上的信念,为此对国家以及国家的执政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制不是政府的起源,只有人民认可的政府才是政府建立的基础[16]。从他的文字表述中,我们发现他更接近卢梭的“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理论。这个理论将“臣民”升值为“公民”,从而把自由平等、幸福安全上升到个人自由与共和民主的高度,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理论[17]。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要求不是只对国家,同时也向作为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陈独秀的一篇具有导向意义的《我之爱国主义》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现代性)的坐标给予了调整。继《爱国心与自觉心》之后,他站在民族自觉与个人自觉的立场上,以民族大义、国家大局为重,发明了具有独到见解并自诩为“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方针。针对西洋人的种种讥讽,陈独秀对症下药,以“勤、俭、廉、洁、诚、信”等六义为德治本。他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不是旧调重弹:“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假如不能由此入手救国,“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在陈独秀看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救国之道:“之数德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其兴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18]舍此,即使为国捐躯也徒劳无益。注重打造民主共和制国家与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独立意识并行,这已经自觉地将自我纳入到世界秩序的“公民”行列。由前现代的一致对外之“外竞”意识到由民主而民族的“内竞”身份意识[7](P174),五四时期的先哲跳出了传统的窠臼。这种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特征即是以个人本位的民主和自由为原料作为打造新型现代国家的基石。
从《厌世心与自觉心》到《我之爱国主义》,陈独秀的民族主义情怀充满着现代性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陈独秀在对民族性和现代性关系的把握上更为成熟:他一方面没有因为启蒙运动的世界化而忘却自我的身份意识;另一方面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意识而放弃对现代性始终不二的追求。他和他的同仁义无反顾地肩负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使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殉道者角色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前行。毋庸讳言,这时陈独秀们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有着极其浓重的“人道民族主义”色彩,但正是这种色彩对日后走向大同理想、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起到了兴奋剂的激活作用[19]。
“五四”的直接行动是新型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奏。同时代人胡适一直将其看成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20]。“巴黎和会”前后,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盲目乐观到“强权强暴公理”的悲观失望,从以个人主义为依托的世界主义到以人道主义为中介的社会主义,尽管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但“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中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始终守望着启蒙并以开放的胸怀和理性的思考关注事态的发展与未来的走向[21]。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两种杂志为例,即使在“五四”这个以抗议西方列强和北洋政府为主导的运动进至高潮之际,陈独秀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对于“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这样敏感的问题,他笃持自我一贯的爱国立场:“若不加以理性的讨论,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用强力禁止我们爱国,或是下令劝我们爱国,都不能做我们始终坚持有信仰的行为之动机。”而且最后毫不隐讳自己的底牌:“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22]这一表达在应验陈独秀借文化“谈政治”之内在真实的同时,也不难看出:这里所论的现代民族主义在政治哲学上是民主的、开放的乃至“世界的”民族主义,在社会哲学上则是个人的、自治的乃至“自由的”民族主义。“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1919年前后的启蒙表述,尤其是《新青年》前期的思想流布,充分预示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和民族性接榫的成功。
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化解思想史上的吊诡与紧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对自己看重但又觉得没有把握的问题总要保持必要的距离。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近世思想史诸多难题的解决非常重要,以至于它一直是困扰我们描述思想史的壁垒。时至今日,在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倍加关注的当下,化解先贤思想理路的内在紧张与吊诡对我们今天的讨论尤为迫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每每论及近世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笔者首先感到它不单是两个思想谱系的吊诡问题,作为一向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我,脑海里的第一个自觉与紧张还是它们与个人主义话语的纠缠。说到纠缠,还有一个我们无法释怀的近亲:在民族性(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世界主义)接榫、粘连的当口,人道主义在中间的撮合几乎完全取代了个人主义的功能。置身其中,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交叉、排列与组合的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为此,我们的梳理还要从“盘根错节”的“根”落笔。
我们要清盘的“根”,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伴随着鸦片战争与生俱来的。它的年轮甚至超过了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任何一个思潮。无论是我们谈传统的民族主义还是论现代的民族主义,其“现代性”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能否作要么完全狭隘落伍、一无是处,要么“特定时代”、无可非议之非此即彼的判断呢?还有两个司空见惯的学术模式(我这里将其称为“模式”)在这里:一是“一分为二”,二是“此一时彼一时”。就以上论及的四种态度,笔者以为“非此即彼”的简单、化占、轻率做法就是胡适所批评的“懒”,可以不攻自破;“一分为二”其实也可以归结为“差不多先生”一类,那一各有千秋或打一巴掌揉三揉(揉三揉打一巴掌)的做(学问)法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以不变应万变学者的轻车熟路,在似乎无懈可击的形式下其实潜存着很多实质上的不必要;“此一时彼一时”的应景也可以从上面的例子与论述中排除。在很多情况下,“一分为二”与“此一时彼一时”会互换,只是一个“打”和“揉”孰先孰后的滴序问题。不过,倒是这个论史的论式启迪我们进一步反思对待历史上的精神事件譬如说本论论及的民族主义究竟该持何种态度。这种思想史研究态度与方法的矫正不但适用于民族主义思潮,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精神事件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文化史、思想史抑或政治史、学术史都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在承认史实的基础上对其做出回应:既然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想象。而且还是一个有着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存在或想象,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全球化和大同化的乌托邦离我们还有距离,民族主义就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存在并呈现繁杂多变的面相。由此,承认这个存在并给予其必要的空间方是思想史家应有的基本态度。应该看到,中国近世思想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失去了“民族”,我们活动于这个时空中的知识分子就失去了沧桑与坎坷、光荣与梦想的依据,无论是启蒙还是革命,无论是实业还是教育,这些不一而足的手段不都是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性未来而设计的路径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认可“这一个”的前提下,分析并论证民族主义与其他各种“主义”的关系或民族性与其他什么“性”的关系才是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这就是笔者一再强调的思想史研究的“吊诡性”问题[23]。
针对民族主义这一话语,我们要思辨的则是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如同民族主义与近代史与生俱来一样,就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特征而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呈现出一种共生的关系。事实上,它们二者不但是共生,而且是孪生,甚至是连体儿。本然的状态应该是不存在谁压倒谁、谁征服谁的问题。它们同行、变奏甚至变脸,而且需要保持必要的紧张。这个必要的张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度”。过分的世界化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道路会招致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而一意孤行或执意文化本位又会导致故步自封、画地为牢的狭隘民族主义。就近代史上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嬗变过程来看,它与世界主义时刻在争夺地盘,而且民族主义始终有被利用的潜在的危险。固然,民族主义有被利诱并强暴其他思潮的危险,但这不是我们从根本上排斥、否定乃至抹杀民族主义的理由。只是我们有必要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对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引发的行为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知识分子而言,尤其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这也即是笔者一再强调的“批判性”。
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告诉我们,在启蒙者与革命者(救亡者)之间,前者具有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强势成分,而后者则不同程度的披挂着强势的民族性成分。即使是在同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先驱者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当其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时,他就是民族英雄;当他以启蒙者身份立身时,他则是放眼世界的思想家。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民族救亡的呼声一直占据上风,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相对纯正的启蒙思想家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是“救亡压倒启蒙”论断的主要依据[24]。但是不幸的是,《新青年》前期世界主义的占据上风与民族主义的降半旗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与1925年五卅运动接二连三的再次压倒为另一个论断——“启蒙压倒救亡(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空间[25]。不容忽视,先启蒙后革命、从启蒙到革命、启蒙与革命并驾齐驱是近百年来的基本规律和历史真实。无论是启蒙 (思想舆论)还是革命(直接行动),两者颉颃、跌宕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与此同时,在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中国近现代启蒙的终极关怀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款都是跛足的行走。这也是我们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关系应持的基本态度。为了让先觉不再尴尬,租赁鲁迅那句本意并非如此的“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名言反戈一击:“愈是世界的便愈是民族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化解很多与启蒙产生千丝万缕之“主义”瓜葛的紧张,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等。
还应看到,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即是思想者不断思考如何复兴中华、重振雄风的历史。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先知先觉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国难的关注、对民生的焦虑。继“洋务派”以实业救国之踵,“维新派”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则以政治改良的现代性路径演绎着救亡的指归。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派”异军突起,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阵势接橥救亡的大纛。接二连三的颠簸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从传统到现代,从启蒙到革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打通是以一个思想史逻辑为中介的:由“立人”而“立国”。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也正是这个时候插足其间的。如果说辛女革命前的陈独秀“立国”思想占据上风,那么辛亥革命后的理性思考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自由、民主体系的塑造。当然这个塑造又是从“立人”着笔的。陈独秀的“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的“个人本位主义”[26],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周作人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将个人与团体、国家、民族的关系作了根本的调整[27]。更为激烈的是,在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启蒙思想家俨然拿“我”和“世界”直接对话,力求简化并扫除中间的阻隔环节。个人主义和人类主义(世界主义)成了直通车式的伙计。李大钊在《我与世界》中述说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国家、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28]陈独秀也曾在与钱玄同讨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这样说:“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29]撇开新文化元典的缔造者们对“中国文字,迟早必废”的讨论以及对世界语的期待,陈独秀们已经走到了无以复加的乌托邦领地。恰恰在这里,随着五四精神事件的发生,当新文化元典的缔造者们发现了个人“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的吊诡后[30],他们又不得不再度调整个人与民族、国家、社会关系的罗盘针。角色和思想谱系的转化毕竟是在短短几年的“瞬间”。所以为了缓解思想张力和自身的尴尬,他们援引人道主义作为自己思想转换的后盾,在欧战结束后由前期倡导(自治或说无治的)个人化人道主义向为大多数民众谋幸福之(民治或说群治)人道主义陡转。个人主义(自治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和(群治的)人道主义相互联袂,由此出现了“强权”与“公理”、“竞争”与“互助”保持张力并难以自持的思想史困窘。巴黎和会前后,五四思想史由“强权在先公理在后”向“公理升腾强权末日”转变,这正是欧战结束前的基本真实。
综上,回眸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从传统到现代、从世纪之交到五四运动时段的嬗变,再回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领衔人物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我之爱国主义》、《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的思想线索上来,在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林林总总、风云变幻的思想谱系之间,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不应总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也不应总是充当工具性的充气皮囊;民族主义不需要在思想史上躲躲闪闪,它应有自我的位置和尊严,只是当它在动荡岁月和腥风年代也要矜持自尊,以冷静的定位让具有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导向为自己张目。民族性是硬实的后盾,只要它不越位;世界主义是勇猛的先驱,只要它不极端。这也就是我们一再论述的所谓的“张力”和“吊诡”。思想史上的“张力”和“吊诡”并不可怕,而且是必要的存在,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交织的意义正在于此。思想史上《新青年》前期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视角的协调、制衡以及前前后后的跌宕、颉颃为今天民族主义思潮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也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演进昭示了希望。
[收稿日期]2005-11-30
标签:新青年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安徽俗话报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陈独秀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