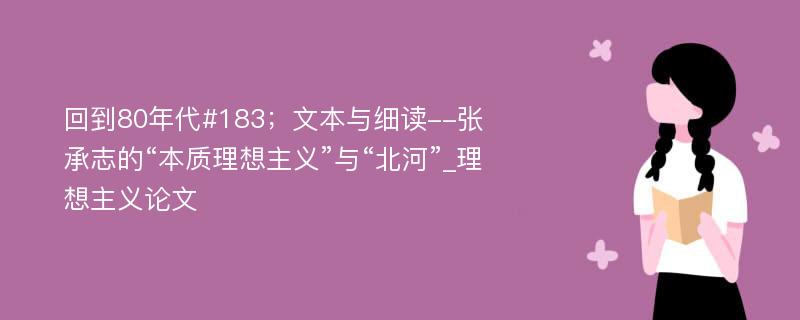
重返八十年代#183;文本和细读——张承志“本质化理想主义”与《北方的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主义论文,本质论文,文本和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讨论显然离不开一个词——“理想主义”。正是由《北方的河》,张承志确立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并在80年代初、中期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得到广泛应和与掌声。但其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好像变得暧昧不清了,从皈依“血脖子教”的“哲合忍耶”到“以笔为旗”倡导“清洁的精神”,让一些人联想到“纯洁运动”而未免不安,吹捧的有,怀疑的有,责骂的也有。这就提出了问题:张承志究竟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时代在变,还是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在变?由此再来切入《北方的河》,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理想主义需要两个支点:一是在精神层面的信仰支撑,二是在实践层面的行为追求。要看张承志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想必须返回到张承志生命及精神的成长之中,探寻其信仰及行为方面的理想主义之路。
张承志生于1948年,父母在建国前是济南的地下党员。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张承志这代人所受到的小学、中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理想教育的熏染使他们具有了强烈的红色接班人的使命感。这种理想教育在信仰树立方面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为依据,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强调理想的实践性。这里,理想既有着美好的未来承诺,又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同时新中国激发出的英雄主义情怀又与理想主义相激荡,激发了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热情与行动。在信仰的行为追求方面,这种理想教育是将个人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奉献与牺牲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些普及到每个人的内心的教导强化了信仰的伟大与神圣、奉献与牺牲的崇高,营造了一种整个时代的集体主义、浪漫主义精神氛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旨向。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精神产儿。很多人都注意并强调张承志的“红卫兵情结”,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他内在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1966年5月到1968年底的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中,张承志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1966年8月14日,张承志离开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漩涡中心,取道甘南,重走长征路;二是1968年8月14日,他写下血书主动要求到内蒙插队,比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了4个月。这两个日期的重合很有意思,它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有意的选择,这让人感觉到某种仪式化的神圣意味。仪式化与理想主义有内在联系,如同血书、宣誓、忠字舞一样,充满仪式化的时代必然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于是,自我成为神圣仪式中对理想的献祭。
张承志这代人的这种强调奉献、牺牲的理想主义属于什么类型呢?海德格尔曾说:“真理设立自身的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1](P42)它把理想(真理)本质化,强调的是理想(真理)对个人肉体、心灵乃至生命的超越,在这一逻辑上自然地导向献身与牺牲。我把这种理想主义称为“本质化理想主义”。这种“本质化的理想主义”也并非抽象,与特定历史条件的结合决定了其路向及结果。有时它可能成为圣徒,有时它可能就很危险,将人导向魔道,比如,海德格尔曾滑入纳粹的重要的思想动因就是这种“本质性的牺牲”。可以说,从精神特征上来看,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也属于“本质化理想主义”。当然,张承志一代人的理想结合的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那个时代激发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精神动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里想要从精神特征方面思考的是,这种“本质化理想主义”是否内蕴了某种危险,当一味强调个人的绝对服从、奉献、乃至牺牲时,它是否易于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它是否易于导致某种狂热性?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催化下,与无限张扬的“奉献、牺牲”相对的是否就是“剥夺”与“消灭”?“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所发生“红八月”等此类惨剧与这种“本质化理想主义”是否存在着关联?应当说,一些人对张承志“理想主义”的不安便是嗅到了这种深层的“本质化理想主义”的危险气味。
所以,就根本而言,张承志是一个“本质化理想主义者”,而且他一以贯之,时代在变,张承志的“本质化理想主义”不变,并且不断地在行动。从红卫兵到知青,从体制内作家、学者到自由职业者,从革命主义的战士到人民的儿子、再到“哲合忍耶”的信仰者,“本质化理想主义”成为张承志未曾衰减的精神源泉和生命动力,这也是我们面对张承志及其创作时应首先而且必须把握的精神核心。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张承志的“本质化理想主义”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合了不同的意识范畴,他寻求(奉献)的对象也有很大不同。在红卫兵运动中,它结合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意识,张承志所献身的对象是领袖和革命。1968年到1972年,内蒙插队时期的张承志对“文革”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在艰苦生活中与草原牧民建立的紧密联系使他逐渐实现了理想主义与“人民”的结合,“人民”成为他文学创作初期的母题,由1978年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张承志一直都在努力践行着“歌颂人民,描写人民”的信念。1984年后,张承志又与“穷人宗教”哲合忍耶结合,高扬宗教主义的献身、牺牲的崇高庄严的旗帜,其“本质化理想主义”更显浓烈和鲜明。
在张承志的“本质化理想主义”不同具体形态的转换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自我精神不断扬弃的过程。张承志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精神的剥离与持存,这使得其转换过程并非平顺甚至充满痛苦。1970年代,从“毛主席的红卫兵”到“人民之子”,是张承志的第一次精神剥离,在痛苦的反思中他告别了自己狂热躁动的“青春期”;80年代,张承志在由“人民”向“哲合忍耶”的精神转换间也存在一个裂隙。张承志是受到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又处于80年代初期“新启蒙”精神高昂的时代,歌颂与启蒙这两个面对人民的不同姿态,成为张承志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1982年的《绿夜》、《黑骏马》均显现出这种矛盾,“那熟悉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在《黑骏马》的悠扬歌声中出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隔膜与距离。这样,1984年1月发表的《北方的河》就具有了一种精神“桥梁”的意义,它是张承志“本质化理想主义”在80年代初期追寻与探求的深化。在这一点上建立对《北方的河》的解读,可能更符合作品的本来面目,更贴近作者的本意。
学界对于《北方的河》阐释主要分为两类:1984-1985年,主要是以“青春、理想、激情、自我”为主题,具有很强的“新启蒙”的时代特征。这样可以看到,当时张承志传达出的“理想”与读者对“理想”的应和,实际上是“同声”而不“同气”的。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实质是发源于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本质化理想主义”,而读者却是立足于当下,为张承志表面的理想主义的激情所感染、激发,他们要在对“文革”的历史否定中,以历史断裂的方式寻求一个新时期的新的自我、新的理想。1985年之后,论者又多以“民族精神、历史文化、父亲原型”等为立足点,对《北方的河》进行“寻根式”解读,关注“河”的象征意蕴,着力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这种方式,又将《北方的河》置于一个广大悠远的历史文化时空中彰显其宏大意义。但这实际上与张承志也发生着某种错位。读者和张承志各自站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言说着“北方的河”的意义:读者指向是外在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张承志指向的则是内在的、更具本质性的生命及其精神的追求,是“本质化理想主义者”最深处的生命冲动。他不想呼应时代、呼应读者,他要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理想主义)存在的方式。所以,“北方的河”具体象征什么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本就是一个“本质化理想主义者”的“在路上”,五条大河只是张承志的精神载体,《北方的河》其实是极具个人化的精神文本。
1986年7月,张承志与冈林信康有一次对谈。冈林认为:“对于自己来说,能不能心情痛快地写好才是唯一的问题。……总是意识着听众,费着心作出的歌,最终还是成不了模样。”张承志说前一种意义上的创作,他仅仅有过两三次,其中即包括《北方的河》,其感受是“那样的作品在完成以后,不如说自己的心情是一片害臊。心里感觉很古怪,简直不愿意有人看到它……”[2]。可见,《北方的河》是张承志一次“痛快”的书写,它面向自己的内心,不以读者为对象刻意地寻求理解,它是张承志的“颂祷与自诉”。这决定了《北方的河》的强烈的主观性,以致它成为很不像小说的小说。一种不能自已的倾诉欲望,一种不加约束的澎湃激情,五条北方的大河就这样“宏大”地承载在一个知青大学生考研的简单的故事框架里。作品真正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研究生”,而是在“引子”中那个既有着坚定的信念、又有着深沉的忧郁,既在感伤、又在奋发,既背负着沉甸甸的过去、又热望着光明的未来的抒情主体。“引子”贯穿的是“我”的强烈的主体精神,它联结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连接着北方的五条大河,最终使它们汇聚而成为一条河—作者的“精神之河”。张承志要抒写的是,这条联结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之河”要贯注什么、拒绝什么、流向何方?《北方的河》是张承志进行的一次自我的历史“清理”和精神的“朝觐”。“我”抒写着自己,更阅读评判着自己,让精神的追寻永不止息。
文本中,在主人公“他”对“北方的河”的寻求中,承担倾诉与自我审视功能的“我”和“你”不断地插入,“他、我、你”在现实与回忆、留恋与反思、否定与肯定之间碰撞,建构着这条“我”的“精神之河”。在黄河之畔,“他”反思了自己的红卫兵时代:“是的,那时我是个地道的红卫兵,但是我没有打过人……”,“没打过人的红卫兵”—张承志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从“红卫兵运动”的罪恶中剥离出去,并在此后一直坚持着“第一代红卫兵”的自我指认并进行着坚决的辩护。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建立一种“历史的同情”,当个人与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心灵乃至生命会产生怎样的激荡?在与“红卫兵运动”的剥离中,张承志实际上将那段历史的沉重甩在了背后,并以“第一代红卫兵”的名义强调并持存了一种“纯粹”的精神。文本中的“他”对黄河有两次横渡,分别代表了两个时代不同的精神指向:“红卫兵时代”的“他”的横渡是“崇拜勇敢自由的生活,渴望获得击水三千里的经历”,“你深信着自己在脱胎换骨,茁壮成长,你热切地期望着将由你担承的革命大任”;而十几年之后的再次横渡,成为“他”对青春的一次回溯,是对自己是否“衰老”、“背叛”的检验,而“我的青春别想背叛”!
既是剥离,又是持存,张承志不“背叛”的“青春”正是“红卫兵时代”纯粹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本质化理想主义”又是什么呢?一旦理想主义被“本质化”,它又怎么能够“衰老”?“他”张开双臂向黄河扑奔,在女记者的镜头中定格:这是《北方的河》呈现的一个“献身”场面。它在文本中反复出现,强化着其仪式化的意味,也强化着“本质化理想主义”的精神姿态。
与黄河一样,无论是额尔齐斯河、湟水,还是永定河、黑龙江,显现的都是这种“在路上”的精神特征。额尔齐斯河是“自由而宽阔”的,而要获得它的“自由”与“宽阔”,需要的是心灵在创伤中的升华,它是创伤中的“坚强”、“忠诚”和对“诺言”的“敬重”。湟水边的彩陶是破碎的,“像生活一样”,即便拼接了,仍然弥补不了那个创口,但湟水是坚韧的,一如高老汉种下的青杨树林生生不息,于是“彩陶片汇成了一条河”。永定河则“不是一道屈辱的驯服的浅流”,它“没有屈服”,“饱含着深沉的艰忍和力量”。这些河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蕴涵着主体“我”对于创伤、困厄的一种超越,一种“苦行”中的“艰苦的浪漫”。在文本中,这种“苦行”既有心灵层面的爱的创伤、青春的幻灭,也有物质层面的贫穷困顿,还有肉体层面的疲劳伤痛,“三角肌”的疼痛成为浓缩这种“苦行”的象征符号。苦行,是“本质化理想主义”的重要的人生实践方式,它在近似“自虐”的苦痛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与满足。张承志曾谈及内蒙四年“艰苦的浪漫”生活:“那段浪漫不是肤浅的浪漫,是非常艰苦的浪漫,零下四十度,皮也冻坏了,耳朵冻坏了,肌肉也冻坏了,吃也吃不上,穿也穿不上……可是我们每月都获得着意义。”[3]在苦行中寻找“意义”,在“意义”中不断超越,这是“本质化理想主义者”的“在路上”的行走方式。最终,这些北方的河流“挟带着热烈的呼啸一拥而至”,汇聚为“精神之河”的下游——黑龙江的壮美的“开冻”。而在对黑龙江的壮丽想象中,“本质化理想主义者”张承志达到了他的理想完满之境。
这使《北方的河》充满了诗情,主人公“他”也正是要抒写一首“北方的河”的诗篇。这首诗成为作品的隐含文本,只在叙事中显现书写过程,而未曾真正地以诗的形式表达。表层的小说文本与隐含的诗歌文本构成关系上的互文性,并且通过这首隐含的诗,“本质化理想主义”得到进一步的“提纯”、升华,更显其崇高与庄严。隐含的诗描写“一个在爱情和友谊、背叛与忠贞、锤炼与思索中站了起来的战士”,所有“理想、失败、追求、幻灭、热情、劳累、感动、鄙夷、快乐、痛苦,都伴和着那些北方大河的滔滔水响……一齐奔流起来,化成一支持久的旋律……”;在对“滋润了我的生命”的“北方的河”的感激与赞美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条永远奔涌着的“精神之河”。值得注意的是,与隐含的诗相对应的,小说中还有一首书写出来的诗:“是呵/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就连你在那儿独自苦斗/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主人公“他”与女记者分手,是因为“他”与“她”的根本不同,“她”属于现实,需要依靠,不免软弱、妥协;而“他”坚信“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于是,冈林信康低沉的吟唱为“他”和“她”作出了区分。两首诗,一隐一显,一首在“颂祷与自诉”中进行自我的认同;一首在“世间皆浊我独清”中让自我佼佼不群,它们共同指向那个在精神殿堂上被“本质化”的永远处于被追求状态的理想。两首诗,一首慷慨澎湃;一首忧郁低徊,同一音乐主题下的变奏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差异。或许,在“本质化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路途中,只能是这样一个孤独寂寞的个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