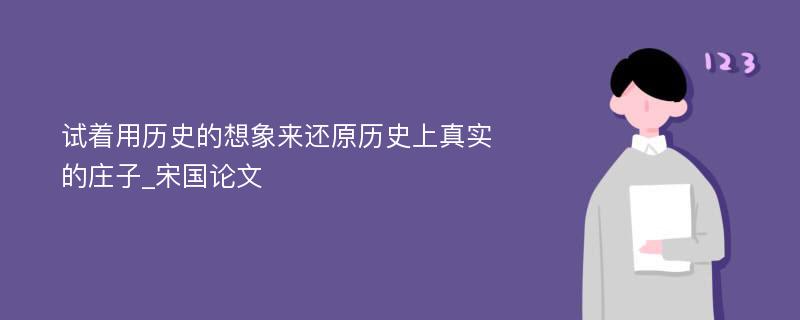
试以历史的想象力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庄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想象力论文,真实论文,历史上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7)01-0074-05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瓠落的文学史》,其中有些论点很值得我们思索,尤其是对先秦典籍的研究。现将其中两段摘录如下:
我的第二点建议是运用历史想象力在多种不同层次上提出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我所谓的历史想像力,指的是自己和自己进行对话,不断询问自己的假设是否犯了违背历史朝代的错误。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常识出发,但是答案则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哪怕只是有关背景材料的证据也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回答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文学史家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提出几种不同的可能性,而避免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让我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开始(假设一个具有一般常识的中学生像屈原发出“天问”一样向教师提出以下这些天真的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屈原在自沉以前写了《怀沙》?他确实把书写在竹简上了吗?他是否用了那些结构复杂的楚国“鸟文字”?他又是从哪儿得到竹简的呢?既然砍竹子、削竹简不是片刻工夫就能做好的,屈原应该一定是随身带了很多竹简来着。那年月一个人出门在外随身带一大堆竹简是常见的现象吗?(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在屈原时代,除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之外,比如说国家档案馆或者需要做笔录的场合,“书写”到底是不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还有,屈原有没有亲自系扎这些竹简,以确保它们的顺序没有被破坏?用当时那些繁复的文字来书写《怀沙》得花多长时间?在文学想象力的展翅翱翔和书写竹简的缓慢速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是谁把这篇作品从屈原流放的荒野带回文明世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这篇作品的呢?
宇文所安以屈原《怀沙》为例,提出要以历史的想像力还原历史的真实,很有启发性。
先秦时期(战国中期)的历史真实是什么?宋国处于怎样的境地?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如何接受教育?《庄子》的文化背景如何?书籍如何书写、流传……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庄子及其著作时首先应考虑到的。
一、关于庄子本人:核心问题是庄子如何接受教育
由于现存先秦文献的阙失,庄子的身世就如谜一般。《史记》里的记载很简单,只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在司马迁看来,庄子博学多才,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庄子是如何接受的教育?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至孔子时方兴办私学,受教育对象扩大,战国时私学之风渐盛。但即便如此,能够接受教育的人还是很有限的。且在当时书籍(竹简)抄写、流传非常不便,私人藏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下文还要论及),庄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博览群书,还能够达到“无所不窥”的程度,一般人肯定是做不到的,而他又没有像老子一样做史官的经历,如此一来,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庄子是贵族的后裔,有着显赫的家世①,小时受过贵族“官学”的严格训练,长大后能够阅读国家的各种藏书(只是后来家世没落)。
我们读《庄子》,可以看到有庖丁、轮扁、梓庆等一批技艺高超的手工世人,书中的描写极尽夸张,而且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赞美、欣赏之情。有一个问题是,相对于百工艺人的繁多,《庄子》书中为什么很少有关于农业以及农民劳作情况的描写(《天地》篇中的伯成子高“耕在野”、汉阴丈人“抱瓮灌圃”,《则阳》篇中长梧封人对“为禾”的描述,《让王》篇中善卷所谓“春耕种”、“夏收敛”,颜回所谓“郭外之田”、“郭内之田”等事例,可以说和农业及农民劳作有些关系,但这些人大都是作为隐者出现的,对战国中期的农业状况并无反映),而在庄子的时代,正是铁制农具开始普及,农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是庄子对农业以及农民劳作厌恶吗?这在《庄子》书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大概的原因就是庄子没有生活在农村而是生活在城市里面,接触不到农民的劳作,而他又曾为漆园吏,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手工艺人,这里也可为庄子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一个证据。
二、关于庄子的交友:核心问题是他如何能够跟惠施成为朋友
惠施,宋人②,大概与庄子同时而年龄可能稍长,战国时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热衷于社会活动,曾任魏惠王相,是魏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从《庄子》中可以看到,惠施和庄子虽常常争论不休,但二人相知很深,相交密切。据《庄子·徐无鬼》载,庄子过惠施墓时曾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言之矣。”二人何以成为朋友呢?
虽然,庄子反对礼,但当时的整个社会是讲究礼的,西周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儒家学派还为之汲汲奔走。礼在很大程度上,其外在形式反映的是等级秩序。那么,惠子贵为魏相,二人又如何交往呢?
这里有两个可能:一是庄子的高贵的身世,惠子也出身为贵族,从小就相知,或者同为“官学”的同学,所以总能够辩论(惠施是宋人,庄子也自然会是宋人),否则的话,二人不可能相知甚深。如果没有小时候的基础,以庄子后来的没落,以惠施的地位与荣光,二人相交往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用说庄子妻子死后,惠子还去吊唁(《至乐》)。二是庄子虽然贫穷(或者只是一段时间),但他有较高的声望,有众多的弟子,他死时弟子还准备将他厚葬。郭沫若在谈及此问题时说:“庄子的声望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他有过一群门人弟子,而且南游楚,北游梁,所游地方相当广,到处和高级的执政者打交道。”[1](P103)虽然或可言过其实,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时庄子的生存状态的。
三、关于《庄子》的文化背景:核心问题是商宋文化和周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宋是殷商的后裔,宋人作为“亡国之余”承袭殷商人的某些特点是自然而然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庄子》以商宋文化为背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庄子》商宋文化背景与周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呢?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灭商后,对商遗民,武力监控与笼络安抚双管齐下,既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旧都,又让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周的一统政策逐渐分化瓦解商的残余势力(包括商文化)。周公摄政后,武庚与管、蔡、霍相互勾结,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处死武庚与管叔,以微子启代替武庚统治殷地,封国于宋。接着,周公为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大兴土木营建雒邑,并将殷之“顽民”强制迁到雒邑,派“八师”军队驻扎。③经过此番战乱,殷遗民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地理位置来说,宋在齐、鲁、楚、越、魏、韩、卫、赵等国包围之中,且在雒邑的直接监控之下,实际完全变为周的一个属国。
周的统治稳定后,周公便制礼作乐,实施所谓的礼乐文化。在周公的强力推行下,礼乐文化大行其道,在整个意识形态占有统治地位。《诗经·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情势下,宋国纵便有一些殷商文化的遗存,也是强弩之末,处于一种日削月蚀的境地。
自西周以降,到平王东迁,经历了近三百年;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春秋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从战国初年到庄子出生的年月,又经历了一百余年;这样总算下来,从殷商灭亡到庄子出生,期间至少经历了六百余年。或许,我们一些现代人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但它是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实实在在地度过的。如果以现在的2006年计算,上推600年,那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我们研究现代某人时,还要考察他明时的文化背景吗?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P23)孔子作为宋国贵族的后裔,重视殷商文化,春秋时作为殷商文化外在形式重要特征的殷礼,已无文献可徵,殷商文化的遗存可想而知,更不用说一百余年后的庄子时代了。社会总是在发展的,中国古代的文化又具有很强的包融性,它总是处于一种不断融合的过程之中。笔者这里只是想指出的是,历史的发展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绝不只是主观想像的那么简单,因而必须要有一种历史的想像力,尽可能地还原一种历史的真实。
当然,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以前,社会发展缓慢,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或许能够长久地保存下来,但是,它的留存必须有一种历史累积的因子,否则就会随时间消亡殆尽。宋国人有一种东西保存的特别长久,而且还总是处于发展的态势,这就是弱国的心理。如前所述,宋人是殷之遗民,西周初武庚想重建殷的辉煌,结果遭到镇压,武庚被杀,部分殷商遗民被迁移。西周时期,虽然社会比较平稳,但雒邑的“八师”总让宋人感到不安,在周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遗存的殷商文化被边缘化、被同化,处于一种被统治的、被压抑的地位。春秋时期,宋国在各诸侯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宋襄公虽欲争霸,但只落得个可笑的下场。其实,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之所以两次送掉作战先机,一直等到楚军渡河列阵之后才战,大概也是这种弱国心理在作祟——我们宋国绝不比你们差,绝不占你们的便宜,谁说我们宋国弱?战国时期,宋国人更是成为齐国、楚国等国家战争的牺牲品,左摇右摆,国势日渐衰弱最后竟至于亡国。因为宋的积弱,宋国人逐渐被其它诸侯国所轻视甚至耻笑,这一点,从先秦诸子作品中一些人物形象可反映出来,《韩非子·五蠹》中的“守株待兔”、《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揠苗助长”等故事嘲笑对象都是宋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用在这里或许不恰当,但事实就是如此),但宋人的反抗却是无奈的甚至是徒劳的,他们仿佛命中注定了要被压迫,因而,在宋人的意识里,一方面酝酿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批判国君的残暴统治,批判战争,批判丑恶的世态人情,另一方面,他们又看淡了主流文化中所谓的功名利禄,看淡了所谓的忠孝仁义,看淡了生与死,在精神世界里开始追求与“有”对立的“无”,于是,就有了伟大的庄子及其作品的诞生。
笔者以为,研究地域文化固然重要,但就中国的历史情况来看,地域文化是从属于主流文化的。地域文化能够提示作家或作品某些方面的特征,但就总体而言,主流文化则更能揭示作家作品的精神实质。笔者这里所指的主流文化,主要是指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所谓中原文化,首先是以周文化为主导,周天子虽然势微,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周文化还有着很大凝聚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又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儒家又为显学,在春秋战国期间影响甚大,这对维系周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宋的地理位置,在楚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包围之中,宋国自身具有的地域文化因子,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同它们相互融合。这样,几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各地域文化共性的东西逐渐凸显,就催生出一种比宋国文化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
或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庄子》并没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周文化)背景。笔者以为,《庄子》诸篇,其主旨是在消解以中原文化(周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它的参照系是以中原文化(周文化)为背景的。换句话说,庄子是立足于中原文化(周文化)的沃土中,不过,他的道家学术思想却使他走向了中原文化(周文化)的另一面,从批判、消解中原文化(周文化)入手,构建起了自己的学术殿堂。
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庄子》文化背景为什么会有商宋文化、楚文化、齐文化等多种学术论点,也可从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为什么会有“庄子盖助孔者”[3]的论断。④
四、关于《庄子》著作:核心问题是《庄子》著作如何流传
这里先看一则消息:《文汇报》2000年8月16日报道,上海从香港市场获得的1200支战国竹简,经整理发现涉及先秦战国古籍81种,其中多为佚文。这批竹简最长的57.1厘米,最短的24.6厘米,约有3.5万字,内容涵盖儒家、道家、杂家、兵家等各个方面。
笔者在这里引用这则消息的目的,首先是想说明战国时期文字基本上是写在竹简上的,《庄子·天下》篇中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惠施的书竟然达到了五车,这当然是写在竹简上的了。怎么在竹简上书写呢?东汉王充描述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4](量知)既然诸子的文章都是写在竹简上,其体例又如何呢?“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诸子尺书,文明实是。”[4](书解)
基于上述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可以确定《庄子》是被书写到竹简上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庄子》书十余万言是怎样书写到竹简上的呢?
从上面知道,《庄子》是写在“尺书”上的,王充所言的“尺”,应该是汉尺。据崔文印说:“古籍上所说简牍的长短,一般皆用汉尺,据研究,一汉尺相当于今天23.3厘米……从出土的实物看,普通的简都长23厘米左右,相当于当时的一尺,宽1厘米,厚0.2或0.3厘米不等。”[5](P60)从上面《文汇报》上的消息看,每支竹简平均约为30字,但竹简的平均长度为40厘米,如若以此文字密度计算的话,一支一汉尺长的竹简,文字量约为20字左右⑤。《庄子》书十余万字,至少需要 5000支竹简。
首先思考的问题是:这些竹简都是庄子自己做的吗?如果是他自己做的,做5000支竹简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他一心用在做竹简上面,他还能著书立说吗?纵使他还能著书立说,还有人会相信一个竹简匠人的话吗?另外做竹简的繁杂工序与庄子飘逸文风之间会不会产生矛盾?如果不是庄子自己做的,他有钱购买竹简吗?如果他有钱买竹简的话,那么他还是一个衣食无着的穷人吗?是别人帮他做的吗?是什么人帮他做的?别人为什么愿意帮他做如此繁琐的工作?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庄子》十余万字,是如何写到竹简上面的?是庄子自己书写在竹简上的吗?如果是庄子自己书写的,他每创作一篇是否都立即记录下来?他创作的动机是什么?他书写的目的又是什么?《列御寇》中为什么还有庄子将死的记载?是否有庄子作为学派宗师宣讲,弟子记录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是由一个弟子记录吗?一个弟子记录的速度如何?能不能全部都能记录下来?是由多个弟子记录的吗?他们记录中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没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取舍?风格能否一致?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庄子》成书后,5000余支竹简是怎样编连的呢?都编连成册了吗?编成了多少册?是否每篇都单独编连?可有错乱的竹简?可有散落的竹简?在战乱频繁的宋国,这么多的竹简是如何保存的呢?是怎样流传的呢?编连成册的竹简可有散失?可有人(弟子)传抄某篇?在传抄过程中可有疏漏或错误?如果有的话,是否有抄本流传而原本轶失的可能?我们还能见到《庄子》的本来面目吗?
第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司马迁在西汉国家档案馆看到的《庄子》是十余万字,班固所言《庄子》为五十二篇,郭象在削删古本《庄子》时,依据的标准是什么?真的如他所说的把那些“妄窜奇说”、“凡诸巧杂”的篇章都去掉了吗?这样的标准是郭象的一己之见呢,还是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认同?郭象有自己的偏见或喜好吗?郭象既有剽窃向秀注的嫌疑(《世说新语·文学》),他为避嫌是否有刻意改动或增删的可能?《庄子》划分内、外、杂篇的标准是什么?内篇的篇名体例为什么和外、杂篇不同?是庄子自拟吗?如果不是庄子本人,是谁加上的?是刘向吗?等等。
上面的问题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非常简单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答案,但却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从中理清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使我们的《庄子》研究不至于走弯路或少走弯路。
关于古代书写于竹木简上的典籍的流传,崔文印说:“……一部著作,甚至一篇文章都需要相当数量的竹木简,因而,简册文献不仅笨重,而且体积必然很大,这就给它的流传带来了一定困难,形成了其独特的流传方式,这种流传方式不是如后世书籍那样,整部整部的流传,而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5](P64)《庄子》书最初也应该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
可以想见的是,《庄子》诸篇并不是在一个集中的时间段内书写到竹简上的。每篇成书之后,以单篇的形式流传。在抄本流传的过程中,有人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处理(或增或删或改动),产生不同的抄本。后来,不同的抄本汇集到国家档案馆,⑥刘安或者刘向⑦最初进行了整理,编辑成五十二篇古本《庄子》。到郭象时又对古本《庄子》进行了削删,遂有了今本的《庄子》。这正如孙钦善所说:“先秦诸子书,比较复杂,有的是自撰,有的为其门徒所记述,有的为本派后学采摘其言行或依傍其学说推演、编写而成。即使是自撰或门徒所记述的,也不是作者或记述者亲自编定,而往往先是单篇单章流传,经后人编辑成书,因此难免没有增窜、补缀的部分。因此,先秦诸子书,撰非一人,成非一时,实际是各个学派的集体创作”。[6](P26)张松辉也指出,对于《庄子》这样的先秦典籍,如果要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地去辨其真伪,“越是这样‘斤斤计较’,越容易出差错,倒不如整体观之,反而不会出现大的失误”。[7](P28)这些论断都是十分中肯、十分客观的。
由上面可知,今本《庄子》三十三篇是庄子及其后学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本无所谓真伪的问题,它们共同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独特品格的重要支撑之一。
收稿日期:2006-09-26
注释:
①有人还就此进行过论证。蔡靖泉《楚人庄周说》中认为庄子“更可能是宋庄公的后人”,见《国际庄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第53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②《吕氏春秋·淫辞》高诱注:“惠施,宋人也”。
③见《史记·周本纪》。
④因中原文化以周文化为主导,又有鲁文化的因子,儒家文化与周文化相通,故苏轼会有此种论断。
⑤此种算法当然不很准确,笔者这里只是粗略估计。
⑥《汉书·艺文志·总序》:“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⑦谢祥皓.庄子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