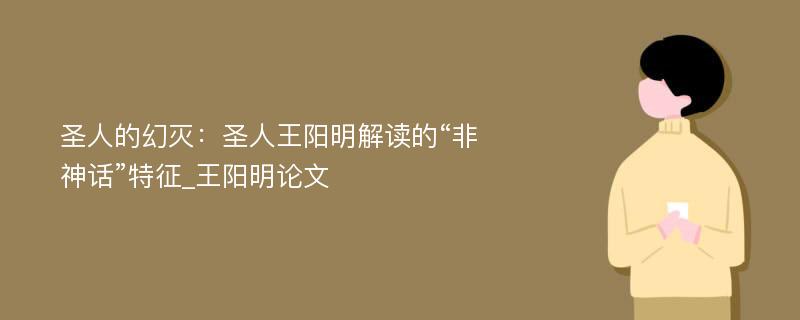
为圣人祛魅——王阳明圣人阐释的“非神话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人论文,特征论文,神话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古代圣人观问题
中国古代儒家学者习惯于认为,他们所讲的是圣人之学,简称圣学。对此可作如下理解:(1)就其所研习的内容来说,是所谓圣贤之书;(2)就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是成圣成贤,在此意义上,也有人把理学称为“希圣之学”(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68年,第47页)。无疑,这种圣学是以他们对圣人的认识为根据的。对圣人的认识,我们称之为圣人观。显然,这里面的“观”字,不是那种概念(concept)的意思,而是指比较宽泛的观念(conception)、观点或看法。举凡有关圣人的讨论,似均可归于这种圣人观题下。从理论上看,有关圣人的讨论又可大致归为以下三类问题:(1)何谓圣人?抑或,圣人的本质是什么?(2)人是否可能成圣?如果可能,又有(3)如何成圣?从逻辑上说,对(2)、(3)的回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1)的认识。但在中国古代,对于(1)“何谓圣人?”这个问题并无多少讨论的余地,因为,一开始圣人就是作为实有其人的具体形象存在的,一谈到圣人,人们想到的不是某个抽象的定义,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如尧、舜、周公、孔子之类。换言之,尧、舜、孔子几乎成了圣人的代名词。因此,如果问:何谓圣人?人们会自然的回答出尧、舜、禹、周公、孔子等一串人名,至于圣人有哪些特征,人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根据这些具体历史人物来说明,且将尽善尽美一类最高级形容词置于其上。严格说来,这种回答不能算真正的回答,它几乎没有触及问题本身。问“何谓圣人?”是希望给出一个有关圣人定义的说明,或至少应当给出一个有关圣人本质的规定。但是中国古代学者在此点上似乎并无多大兴趣,也许在他们看来,圣人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只有追问“成圣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才比较适宜。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关注的重点正是(2)、(3)两个问题。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成圣”?用他们的话说是“作圣之功”、“希圣之方”,用现代语言说是“理想人格的培养”。(注:如冯契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在讨论人能否成为圣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这是一个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冯契文集》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因此,圣人观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成圣何以可能?”的讨论。(注:杨国荣认为,理学(广义上的)是从不同层面对内圣之境何以可能做出理论上的阐释。(参见《心学之思·导论》,三联书店,1997年))
“成圣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康德式的提问。当康德追问:“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形而上学何以可能?”时,他是认为此类知识已实际存在(参见《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9页)。因此,问“成圣何以可能”?就意味着:成圣这件事必然可能。而要使成圣必然可能,除了前面所说的“圣人实际已经存在过”这一事实之外,还要求这样的圣人具有可学而至的特点。“可学而至”实际又包括可学与可及这两层意思。除非已经证明圣人既是可学的,又是可及的这一前提,“成圣何以可能?”才可以讨论。那么儒家学者对此的证明是否成功呢?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都是肯定圣人可学而至。他们论证的方式也相近,都是根据类推原理说明。孟子认为“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荀子认为“凡人之性,尧禹之与桀跖,其性一也”(《荀子·性恶》),“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荀子·荣辱》)。孟、荀之后,儒家学者对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及论证基本予以认同。但是严格说来,类推论证并不具备完全有效性,即便说圣人与人同类,这也只能提供一种原则上的可能,因为同类之间的差异,有时也是一种质的不同而无法逾越,例如道家就持这种看法,所谓“不问远之与近,虽去己一分,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庄子·德充符》向秀、郭象注)。实际上,孟、荀以来对圣人可学而至的“可及”这一层,其论证似乎总是不够令人满意,至多只说明圣人“可学”这一层。这种理论上的缺欠反映到实践上,就是:尽管儒家学者一再讲“圣人可学而至”,但一般人常常“无必为圣人之志”。张载曾指出过这一现象:“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横渠学案上》,《宋元学案》卷十七)其实人“无必为圣人之志”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单强调人“先须立必为圣人之志”,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匡扶不了人心,人们还是自甘为常人为庸人,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正出在长期以来儒家学者对问题(1)“何谓圣人?”的疏略所致。谈论圣人,却对何谓圣人语焉不详,这岂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虽然奇怪,却是事实。似乎只是到王阳明,才开始自觉地反思“圣人之所以谓之圣者安在”这一问题,而此前,学者们对此一直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之中,虽然其间也不乏“圣人是……”式的说明,但对圣人的本质似乎并未触及。学者们满足于笼统不分地谈论尧、舜、周、孔诸圣,却似乎从未想过:这些圣人各自不同而同谓之圣,其根据是什么?学者们习惯于将仁、智、志功诸项最高评价置于圣人之上,却似乎从未想过:如果要在这些特征中寻出一个本质性的规定,那么它应该是什么?以上问题,在王阳明那里都一一得到详细的考察。
二、锲入圣人本质之思
王阳明最初的经历说明了:仅仅归结为“学者无必为圣人之志”这一点,并不能解释成圣实践中出现令人沮丧的结果的原因。王阳明少时即以成圣为第一等事(《年谱》成化十八年条)。弘治二年(1489),拜见理学家娄一斋,后者与之“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年谱》弘治二年条)其后几年,他服膺于朱子格物之学,相信“作圣贤要格天下之物”,曾面竹沉思过七天七夜,却一无所获,人且病倒,不得不感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下引该书,只注《全集》)弘治十一年(1498),他再次按朱子读书之法循序而进,“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年谱》弘治十一年条)这一连串的失败,几使王阳明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以他而论,不可谓“无必为圣人之志”,亦不可谓无“作圣之功”,但成圣之路却是这般艰难,以至令人灰心丧气,其症结何在?正德三年(1508),他谪居龙场,穷乡僻地,始有机会反思这一切。他终于认识到,以往成圣实践挫折的原因就在于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希圣之方”——朱子的格物成圣之说作为指导。龙场大悟的结论是:“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下》,《全集》120页)“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正德三年条)正是这种艰辛的事与思,使他从盲目的成圣实践中摆脱出来,进而思考“圣人之所以谓之圣者何在”的问题。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成圣实践(如何成圣)必然以圣人观(何谓圣人)为先导。在《示弟立志说》中,王阳明正是以这种过来人的口气说道:“人苛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全集》259页)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就是问:圣人区别于众人之处何在?不同个体的圣人同谓之圣者何在?这些问题已成为王阳明关注之点,且提到平时与学生的讨论上来: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先生(案:指王阳明)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有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侧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传习录上》,《全集》27~28页)
单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似乎并非什么新鲜话头,自孟子即言“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而说“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同上),这与程、朱等理学家也并无二致。朱熹亦说过:“是以圣人之教人,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答陈同甫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如此说来,王阳明此说又有何新意?其新意在于:王阳明是有意识地在天理与才力二者之间,选择前者作为圣人本质的规定,所谓“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示弟立志说》中,这种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全集》259页)即明确将德性作为圣人之所以为圣的根据,这种认识却是前人所不及的。(注:杨祖汉也认为:从圣人的内心之纯德上规定圣人之所以为圣,而说圣人是人人可为的,这意思在孟子以下的儒者都曾说到,但是以阳明最能把这意思表达清楚。(参见《儒家的心学传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284页))
孟子以来儒家基本以圣人为“仁且智”(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仁”指德性方面,“智”指知性方面。在圣人品格当中,何者为本质性的?对此,论者并无清楚与统一的认识。从侧重不同而言,孟、荀以来似有两种倾向。(注:陈来说:“理学中程、朱派是比较注重圣的‘智’的性格的,因而比较强调成圣之学中的知识取向……心学只强调‘仁’的性格,突出成圣之学的德性原则。”(《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一种倾向是较为重视德性原则,从孟子到心学即是如此。孟子讲“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曰义曰理)”(《孟子·告子上》),陆九渊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年谱》,《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483页)另一种倾向是较为重视知性原则,从荀子到程、朱理学即是如此。荀子从知能角度将圣人理解为“人之所积而致”(《荀子·性恶》),朱熹相对于陆九渊,侧重“尊德性道问学”中的“道问学”一面,强调作圣贤要格物致知。说两种倾向,只是相对而言,像王阳明这样鲜明地以德性为圣人本质唯一的规定,却属新异。而王阳明对圣人本质的这种认识也是明确地针对他所说的:“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的圣人观而发的,他对朱熹为代表的后世之儒的批评,正是建立在这种区分之上:
后世不知作圣之功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传习录上》,《全集》28页)
“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孤立地看待这些话,难免给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印象(注:如陈来即认为:“心学的伦理中心主义立场毕竟太强烈了,以至常常把德性原则与智性原则对立起来,使知性追求丧失了应有的合理的地位,使儒家传统的圣人人格的丰富性不能不因此受到损害。”(《有无之境》,第292页)),甚至会招致蒙昧主义的批评(注: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该书第四卷下,第890-893页)、朱义禄著《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该书第362页)、冯契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该书下册第896页)等论著都如此认为。)。王阳明将圣人本质系于德性之上,这一作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其合理性呢?
前已述及,中国古代圣人观的一个特点是:其所讨论的圣人是具体的历史人物,而非先有一个抽象的定义,人们是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来认识圣人这一观念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一种具体的特点。它难以摆脱经验成分,没有上升到归纳出普遍性的水平。由此形成的圣人观,就具有以下特点:(1)不稳定性;(2)依赖于外部因素(主要是社会舆论)。总之,是缺乏一种必然性,不可预测与检验。以诸圣中的孔子为例,可以说明之。本来,孔子从未以圣人自居,所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这并非谦词,因为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这些人,其特点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似指内圣一面;博施济众、安百姓,则可认为属外王一面。因此,他理解的圣人兼内圣与外王两面,这种圣人就只能系于尧、舜一类古人,所以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论语·述而》)而后来,子贡将孔子推尊为圣,且美化为“天纵之圣”,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若问子贡、孟子有何先例可援,答案是:否。至于历代君主出于以儒术统治国家有效的缘故,也一再追封孔子,汉平帝追谥孔子为宣尼公;唐玄宗封之为文宣王,并取代周公先圣的地位,宋儒开始,不再是周孔并称而是孔孟并称;元代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以孟子为亚圣。孔子成为圣人,若按尧、舜、汤、武系统的标准衡量,理论上并无必然(注:虽然汉代董仲舒及公羊春秋家,以为孔子受天命为王(素王),孔子作《春秋》是托王于鲁,后来纬书进一步说孔子是黑帝之子,试图将孔子上升为王甚至神,以使之与尧、舜等古圣人相并列,但对大多数儒者来说,孔子还是作为开创儒术的先师形象存在的。),实际取决于人们的需要以及舆认。由于不是根据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推证而产生,因此,在中国古代,圣人事实上并不能再生;孔、孟之后千百年间,再无一人被公推为圣人。何以远古圣人多,而中古以降圣人渐稀竟至于无?这是一个令儒家学者尴尬的问题。(注:当代学者傅伟勋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传统儒家从未针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从来不愿也永远不会做圣人’这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脚踏实地设定并解决与内圣无直接关系的巨模伦理问题。”(《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第33页))如果圣人总是局限于古之人,即使再怎么说“圣人可学而至”,恐怕人们也会渐渐失去信心。对所谓圣人之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此,要把圣人之学讲下去,一个圣人的一般性定义就是必要的,惟有通过这种一般性定义才能使圣人成为一个可检验性的,可操作性的标准。这样,一般的人才有可能被称为圣人。王阳明提醒人们思考“圣人之所以为圣者安在”,且又将圣人的本质系于德性之上,这就冲破朱熹等人为圣人设置的才力限制,使无技能、无勋业、无著述的圣人形象成为可能。这一作法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从思维方式上说,他自觉地探求圣人的本质规定,也已经超出了以往圣人观囿于历史人物的具体思维的水平,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但是,王阳明从圣人本质中剔除了才力、知识技能这些知性因素,又有何理论的必然?
单就本质而言,圣人并不必然就是纯德性方面,也可以兼顾知性一面,因此王阳明这样规定,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考虑,而是有着其实践上的用意。分析他的成色分两说(注:成色分两说是王学有名典故,解者纷纭。冯友兰认为:阳明此说虽是而尚有一间未达,因为才力与境界完全是两回事。(参见《新原道》第十章“新统”)案:此说似乎未识阳明当时说话语境,时弟子所问正为辨明才力与圣人关系,故阳明不能不联系才力来答。另,阳明论众圣分两,如尧万镒,孔子九千镒之说,人多不得其旨。当时弟子德章即有疑于此,以为孔子九千镒之说于心未安,阳明以之为“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传习录上》)其后童克刚复起疑问,阳明不得已再为之分疏,并叹“早知如此起辨生疑,当时便多说这一千也得。”(《传习录拾遗》)据杨祖汉言,牟宗三曾解为:因世运影响,故尧孔分两不同。(参见《儒家的心学传统》,第281页)案:此解似乎亦未达阳明辞旨。)可知,阳明以精金喻圣,(注:据章太炎考证,精金之喻原本孔融,融尝为《圣人优劣论》,曰:金之优者,名曰紫磨,犹人之圣也。(《訄书·王学》)案:章氏对王学原有偏见,乃至讥阳明立义至单。又:章氏非难王学之缘由,详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一书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9~332页))纯乎天理譬金之足色,才力譬金之分两。既然五千镒亦谓金,八千镒亦谓金,那么只要成色足,即便是一两也当谓之金。同理可证,既然才力高者如尧、孔谓之圣,才力次者如夷、尹亦谓之圣,那么只要纯乎天理,即便是才力平平者也可称为圣。这种类推,表面看来非常严密,但细究却疏阔。因为人们可以提出如下反驳、尧、孔,夷、尹才力不同,但毕竟他们的才力都超出常人,其同谓之圣人,由此可知:圣人须具超出常人之才力,从中如何推得出一个才力平常的圣人例子呢?的确,如果将圣人的范围理解为仅限于现有的集合,即仅限于尧、舜、周、孔等十几个人,无论如何也推不出这个范围之外。这与精金不同,它是一个无限的集合,只要满足成色足这一条件的金子不论其分两都可归于其中。对于圣人,除非它被设定为只要满足纯乎天理这一条件的人的集合,并不能这样类比。而事实上,王阳明一开始就确立了他的前提:“圣之所以为圣,只在其心纯乎天理。”这一点本当作为待证明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阳明似乎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因而,王阳明的结论并非从以往圣人观内部演绎出来,而是他自己重新* 设定的命题。他实际上是将原来有限的圣人集合扩大成为一个无限的集合。这一扩大是以牺牲原有圣人的一部分内涵(才力)为代价的。其实,包括才力与德性两重内涵的圣人集合,亦可以说是一个无限的集合,但是这种无限的集合相对于王阳明所设立的新的无限集合而言,是一个外延较小的集合。对于社会中从事成圣实践的人群来说,王阳明的集合比之朱熹的集合显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我们借用集合论,对王阳明的观点可以做如上理解。
综上,关于王阳明对圣人本质的反思,我们可以这样评价:从思维方式上看,他比以前进了一大步,有其历史合理性;就其反思的结论而言,虽然并无理论自身的优越性,但对于实践而言却有开放性的特点。
就王阳明个人而言,经过自身的反思,已确信作圣之功与知识、技能、才力原不相干。但在他看来,同时代还有许多人像他从前一样,为错误的希圣之方所蔽,如在黑暗中摸索,他对这些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答顾东桥书》,《全集》56页)出于这种同情,使他决心将自己思考的收获推广开来,与学者们一起分享,所谓“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答聂文尉》,《全集》80页)于是首先他就从澄清一些长期流行的关于圣人的误解开始。
三、有关圣人观念之澄清
1、关于圣人生知的解释
儒家学者习惯上把人分为三种,即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与困而知之者。(注:此说出自《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一分法无疑带有某种虚构成分,以辩证的眼光来看,人都是学而知之者,所谓生而知之者,只是天赋观念论式的虚构。按照这种理论,圣人正是所谓生知者。生知主要相对于学知而言,前者属先天之知,后者属后天之知。后天之知主要是经验知识,先天之知不能包括后天之知,说圣人生知,就不能说圣人于经验知识也一应俱全。如果要肯定生知、学知之分,比较合理的解释似应如此。王阳明与以往圣人观论者的分歧,不在于他否认圣人生知这一前提,而在于:他们关于生知的范围、内容的看法不同。双方形成争论的焦点在于:圣人谓之生知者,是否也包括礼、乐、名、物、度数之类的经验知识?王阳明对圣人生知的解释,较之以往圣人观论者对圣人不无神化的认识,确有合理之处,他对后者的反驳也是成功的:
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答顾东桥书》,《全集》53页)
他的结论是:“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同上)这段话说得非常有力,足以破学者之蔽,因而他对当时学者的质问就显得不容置辨:
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同上)
与“圣人生知”这一观念相联,时人关于圣人的另一误解是:“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王阳明既澄清了前者,那么后者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2、对圣人无不知无不能的解释
唐宋之后,通常儒者谈到圣人,多指孔子。孔子本人博学多才,确实给人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印象。其实孔子时代,人们关于圣人的观念中并无“多知多能”这一条,观《论语·子罕》“大宰问于子贡”章可见: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联系孔子不以圣人自居的说法以及他关于圣人的认识可知,孔子对大宰的看法表示赞同(注:顺便指出,朱义禄认为:“在《子罕》篇中,太宰以‘多能’为‘圣’,这是沿袭原来的旧观念,但孔子认为‘多能’不足为‘君子’,更何况‘圣人’呢?”(《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第267页)此解有误。),即他也认为:圣人君子无多能,自己多能,确实够不上圣人的标准。至于子贡之说,出于为师维护,不足为证。在后世学者那里,孔子引以为不足的“多能”这一点却成了圣人品格中的应有之义,他们还进而将孔子夸大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与孔子博学多能的真实形象已不相符。孔子明确表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而“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正是他“好古,敏以求之”的例证,但是将孔子夸大为无不知无不能的学者,对此却作了明显的曲解,认为孔子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王阳明则正确地指出:“此说不可通。”(《传习录下》,《全集》97页)
其实王阳明并不一般地反对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是在对“知”的理解上,比一般学者高明。一般学者把“知”仅仅理解为“实有其知”,即一种内容性的知。而王阳明认为在内容性的知之外,还有一种“知如何求其知”的“准知”(Semi-knowledge)。对“知”的如上理解,在孔子那里也似乎可以找到根据。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注:“是知也”的“知”,旧注多解作同“智”字,参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卷二。案:此解并不影响本文对它的引用。)。又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以此而言,孔子于实际“名物度数”未必全知,甚至如他自己所说的“无知”,但孔子的知或智就表现在:他知其无知(苏格拉底也说过最聪明的人自知其无知),并且他也知道:无知就当去求知。故虽或暂时无知,但终当有知。在现实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对某事某物无知,但只要他知道怎样去获得这些知识,也不妨承认他有知(准知)。也许,知道如何去求知,有时反而是最重要的。尤以今天的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而言,掌握学习的方法,往往是最关键的,这种对方法、原理的探讨,其意义远远超过那种根据这些原理、方法来操作的工作。
因此,关于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它是肯定圣人有无不知无不能的潜能,而不是说圣人拥有全知全能的实际内容。何以圣人能够无不知?一般人能否如圣人这样无不知?王阳明对前者的回答是:圣人之所以能无不知,是由于他掌握了一个本原之知(天理),又有求知的能力保证。这一回答显然也有利于对后一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即一般人也能如圣人那样无不知。
王阳明对圣人无不知的解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是认为圣人具备一个明觉的心体。这相当于说,主体有无限可能的认识器官——“心”。王阳明以镜照物为譬,“镜”喻认识器官“心”,“物”喻外部认识对象,“照”喻对外物事变的认识。认识取决于“心”之是否灵敏,所谓“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传习录上》,《全集》12页),“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同上),因此圣人能应变无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这当然不是预先可以讲求的。如果认为圣人预先具备了处理事变的具体知识,这在认识上是不可能的,以王阳明的话说,就是:“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同上)他反问那些以圣人为前知预兆者:“周公制礼作乐以示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同上)以圣人为前知预兆者确实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若是那样,只要一个圣人就够了,何必更多呢?王阳明所强调的这个明觉之心,也就是他常说的良知。良知既是认识的根据,也是认识的动因。所以王阳明又认为:(2)圣人具有本原之知(良知)。而良知的内容就是天理,因此“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白,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传习录下》,《全集》97页)本原有两种意思,一指根本性的原则、方法;一指作为开端、起初的知识。就前一种意思而言,本原之知具有学问“头脑”的意义,识得头脑,则无事不得其宜。具体事变对策,即所谓节目时变,不胜其繁,若要圣人样样预先讲求清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圣人只是抓住了一个根本——良知,即可以一执多,因为“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答顾东桥书》,《全集》50页)。方圆长短不可胜穷,然不出规矩尺度之外;同理,节目时变虽不可预定,但处之莫不以良知为准,故致得良知,“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传习录下》,《全集》97页)其实,“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答顾东桥书》,《全集》49页)以此观之,王阳明并非一般性地拒斥知识,关于他有所谓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之说(注:余英时将王阳明学说的出现视作儒学内部反智识主义倾向的极致,以为“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反智识主义的最明确的表示,参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5~176页。),恐怕也难以成立。如果说圣人无所不知,他这些知识也决非一天获得的,王阳明也注意到知识的积累过程,因此他又将发展的观点引入对圣人无所不知的解释中,他所说的本原的后一种意思,即是作为开端、起源的知识,无所不知须从本原之知开始:
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传习录上》,《全集》14页)
由此,他批评宋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同上)也就并非虚发。
综上所述,王阳明似乎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意味着圣人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圣人之所以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乃是因为一方面他有一个明觉灵敏的心,使他可以随感而应,应变无穷;另一方面他有一个本原之知(天理),他知一个天理,便自能求得节目时变这些具体之知,而他知得再多,也只是从这本原之知上循序渐进,发育养出。
王阳明对圣人生知以及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上解释,从理论上看,相当出色,但在现实中,似乎还不足以使与他同时的学者完全消除疑惑,如顾东桥就和他一再辩论这些问题(参见《答顾东桥书》),甚至最初,得意弟子徐爱也不能完全释然(参见《传习录上》)。因此,王阳明感到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有名的“拔本塞源之论”。
3、拔本塞源之论
王阳明自己对拔本塞源之论非常看重: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答顾东桥书》,《全集》53页)
拔本塞源之论可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从本文关心的主题看,它实际上是为王阳明的圣人观提供了一个历史根据。当然,王阳明所描绘的这幅历史图画,带有很大的虚构性。
按照王阳明的理解,整个历史似乎呈现出一种离开圣人之道越来越远的趋势,根据其描述,整个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原初时代,人人之心同于圣人,天地万物为一体;(2)圣教时代,原初时代后期,人心因物欲我私之蔽,相视若仇,圣人遂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之教施于天下,结果亦达到一种“天下之人相视如一家之亲”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人备安其分,各尽其能,且视人之能若己出,“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3)霸术时代,圣教时代之后,“王道熄而霸术猖”,所谓霸术,是“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霸术既行,圣人之道遂以芜塞。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万径千蹊,莫知所适”,“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发展到王阳明所处之世,“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世人“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历史观上的这种悲观主义,在儒家并不鲜见,但王阳明此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求多知多能的倾向与功利之习联系起来,试图从历史上找出世儒“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思路的根源。王阳明指出,这一思路不过是霸术时代的产物,它根本背离了圣人之道,其实质原在满足个人私欲: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案:皆指古之贤人)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答顾东桥书》,《全集》56页)
对知识的追求,当然不能都认为它是出于满足私欲的动机,而且,即使是出于满足私欲的动机,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也有值得肯定之处。王阳明不能理解:“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当然是囿于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限制所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王阳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如何避免一种负面后果即所谓异化的出现?抑或:人们在知识上的进步是否必然以某种程度上道德的退步为代价?的确,如果没有对把人自始至终作为目的而不作为手段(康德语)的保证,人们对知识技术的追求就很难不发生王阳明所指出的这种情况:“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如现代原子能研究的成就也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而利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现象在今天也屡见不鲜。就此而言,王阳明的话就决非危言耸听。所谓“拔本塞源”,王阳明的意思是指:由于功利之习熏染,人们对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真存在状态久违了,这就好像被拔起根本的树、塞住源头的水。无独有偶,在现代,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社会也有类似的感受:“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305页)当然,海德格尔对现代人之生存境况思索出发点,与王阳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自有很大不同,此不详论。
王阳明对历史与现状的看法都是悲观的,但对未来却充满希望,这一希望的根据来自他对良知的信念,他在“拔本塞源之论”的结尾写道: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同上)
而由良知之学出发,王阳明直截了当地提出“心之良知是谓圣”(《书魏师孟卷》,《全集》280页》)的命题,顺理成章地导出其逻辑的结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传习录下》,《全集》93页)以及“个个人心有仲尼”(《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之一,《全集》790页),一种无知识、无技能、无志功、无神异的圣人形象浮现于思想史的图景之中。正是王阳明,为圣人祛魅,使圣人成为一个内在的观念,从而也开始了它的“非神话化”(demythologize)过程。最后,在王门后学诸如王艮等人那里,“满街都是圣人”的观念把这种趋势推到了极致。
标签:王阳明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为圣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神话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心学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才力论文; 论语·述而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