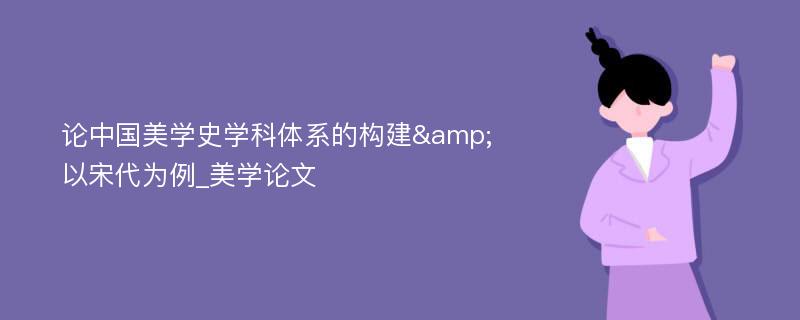
再论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以宋代为案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史论文,宋代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89(2005)01-0013-06
《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注:《南通师范学院学报》于2004年第3期刊发拙文《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姑且称“初谈”),据笔者的涉猎范围,该文已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北京大学学报》等刊转载。所以,本文便是“再论”。)一文主要说的是美学史观、框架理念、方法论,属于宏观性学科体系的范围,然而,这种建构又需进入具体的可体认、可操作层面,这是由前阶段所导入和推进的必然趋势和程序,使之变得可行和具备现实性。史非空言、空谈,应以扎扎实实的实际性的撰述为经验基础。又之所以以宋代为案例,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理论内容和审美形态具有典范性。中国文化经验、审美经验沉淀于宋,出现集大成,是一个寓普遍性意义于其中的美学史时代案例。
一、以人为本位的美学史基点
我们所确立的理论命题是人学—美学,历史命题是心态史—美学史。人是美和审美的主体,是美的创造者,从这一基本的论述支点出发,理所当然地应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美学史基点。以人为本不是履历表似地填写生卒年月、个人简介等等事项,形成人生经历与其美学思想的脱节,因此应打破传统的书写方式。应当把对象的人生经历溶解到所创造的审美现象中,解读对象的人生经历是如何影响自身的审美心态和历程的,这样,人生经历的变化遂与审美风貌的变化糅合于一体。黄庭坚就曾在《与王复观书》中卓越地看到人生经历对审美的影响,他说:“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在宋代则有苏轼为显例:黄州之贬,岭南之谪,时间之长竟达十馀年,处境之厄形同发配充军。政治砺石磨平了他思想的锋芒、棱角,剥落盛气,归于佛气,成为社会环境、经历影响社会心态、审美心态的典型人物。
以人为本就是扣合主体人的心态进行分析,呈现出缤纷多姿的心态色彩。具体而言:发掘独特的心理表现,探入其奥区。李清照在词中以几乎咀咒的口吻说:“种种恼人天气”,实际上包含着女性的春情,体现了她对情感的饥渴、对性的饥渴,这是人性的颤动,心灵的苦闷。李清照在词里实际上以委婉曲折的形式表达了内心隐晦的世界和情感渴望,这才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真正的李清照。《蝶恋花》说:“酒意诗情谁与共”,是一种向往,在酒意中涌发出诗情,也激发出内在的需求。进行这种心理探索,是探求心灵的奥域,是为了在研究中维护一个真实生命的心灵。
把握对象心理特点。秦观的身世慨叹和艳遇之情的结合,典型的南方多情才子的气质,分外缠绵悱恻,而陆游之于唐婉儿,犹然就是一个焦仲卿之于刘兰芝,陆游的豪放之内隐藏着软弱,他如王安石的倔拗、苏东坡的旷逸、黄庭坚的峭拔、辛弃疾奔放中的苦闷,范成大雍容中的舒展……出现了多彩多姿的心态世界。在这个心态世界里,一方面爱国精神、民族情绪高昂,忧患意识深重,另一方面则是禅悦情趣、名士精神盎然;一方面道貌岸然、讲经说法,另一方面则是红巾翠袖、诗酒风流;一方面向往平淡境界,另一方面则充塞富贵气象。这个心态世界充满了矛盾、冲撞和失衡,揭示和描述它们的内涵和色彩将是美学史上很有趣味的事情。而心态是审美的依据,当它们外化为审美形态,就是五光十色的。
重视心态的时代因素。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规范了心态的时代特点。把握具体时代的人的活动、心理、兴趣以致嗜好的背景,才能解读具体个体的心态内容及其特点。宋代鼓励畜养“歌儿舞女”,遂孕育出享乐心态;宋人尚冶游,遂致心态放逸;只有到休闲化的时段才会有休闲的心态,也才会有休闲心态的审美载体——范成大的田园诗;宋人重名节,于是特别重视人格—审美范本,黄庭坚是其代表。他在《再用前韵赠高子勉》中对审美个体的人格规范提出这样的要求:“行要争光日月”,才能在审美中“弦歌”传诵。他在《跋子瞻送二侄归眉诗》中把苏轼、苏辙称之为“成都两石笋”;《跋王荆公禅简》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宋人是崇拜偶像的,王安石是推许杜甫第一人,黄庭坚崇陶尚杜,苏轼崇尚陶潜。宋人又富于怀疑精神,体现了宋人思维的证伪性、存疑性和独异性。这种怀疑精神诚然有具体的形下的对既成结论的否定案例,诸如王安石对《史记·孟尝君传》、苏洵《六国论》对已成定论的否定,然而更有价值和深度的是宇宙本体论的形上质疑。辛弃疾《木兰花慢……因用〈天问〉体赋》,用“九问”,一问到底,蝉联而下,充满着对天地宇宙的兴趣、疑问,包含着极强的探究欲。这是哲学范畴,哲学的思虑是怀疑性思虑;又是美学范畴,体现了对天地宇宙的终极关怀和美的想象。
探求心态的思想根因。黄庭坚诗中常有翻案之语,与众不同,追究其根源,乃是来自禅宗的思维方式。禅宗的机巧和智慧在于逆向思维,例如禅秀以树、镜喻心境,六祖慧能则完全否定,说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以惹尘埃?”作本体性否认。黄庭坚借得此法,在《池口风雨留三日》中以“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颠复了“临渊羡鱼”的成语,在审美上给人以惊异感。
描述心态的演化线索。心态体现了变迁,心路刻划了历程,心态的走向与过程,具备了审美心理史的意义。杨万里的《〈南海集〉序》有一番话很有意思,说道:“予生而好诗,初好之,既而厌之。至绍兴壬午,予诗始变,予乃喜,既而又厌。至乾道庚黄,予诗又变。至淳熙丁酉,予诗又变。”真个是时时新,曲曲变,时喜时厌,喜新厌旧,保持了审美的进取态度和新鲜性质。
二、美学史框架的具体建构
关于美学理论和审美实践相并重的基本学术框架,是“初谈”的论述重点之一,本文则是论说其运用方式。因为我们把感性作品中所自然流露出的美学思想,视为实际上所具有的理论宣言性质,保持了美学的鲜活性质,从而建构起新型的美学史话语系统和结构形式。大体上说,既采撷、解说某一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又解读其作为创作家的审美实践成果。在解读文本中揭示其美学思想,形成二者的互印互证,共同说明一个主题。例如朱熹的美学思想,其“文集”、“语类”中有大量甚至不断重复的论说。既重视这部分的思想资源,看其是怎么说的;又从他所创作的大量诗文作品中去寻觅,看其是怎么做的,总结出他留连山水的自然美学观,从而发现了他纯美学观的成分。这一点对于全面、整体把握朱熹,非常要紧,因为有了它,才纠正了从单纯的理论形态将其定位为理学美学家的偏颇。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从三个方面切入,进而达到三项整合:
——从艺术事实的具体形态切入。其立论依据,已如前述,具体运用的方式则是从艺术事实的切入中描述出并进而逻辑地引申出、概括出某一个体、群体、时段的审美理想、审美趣尚,从而出现艺术事实与美学思想的整合。由此便能以审美特征、思潮、精神为中心,进而划分不同的美学史时段,展现出美学史的发展脉络和历程。例如把北宋的美学史历程划分为唐韵浸染期、宋调形成期、宋调成熟期。据此所形成的美学史阶段学,不仅依据北南宋的自然分期,而且突出了转折期的美学史意义和地位,例如:“南宋初期美学思潮的重大转折”。
——从社会历史的背景切入。既坚持美学的独立畛域,又不脱离美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因素,坚持美学的具体时空性,也就是说运用了社会他律与美学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它虽然具有矛盾性质,但内含着动力和对美学史发展规律的动力的体认,从而出现论述的张力。这种切入又是在分析社会历史势态,寻找出最切当的“点”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不是泛时代,每个时代都采取“一顶帽子通用”的模式。就宋代而言,一是社会变革的状态,一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宋代处于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所谓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相继出现,就是证明。都市繁华走向世俗化,市民文艺亦便得到孕育。人们几乎可以从宋代寻找到所有的通俗性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这方面的考察,还需充分发现其新的成长点及其对文化—美学的作用。北宋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沈括《梦溪笔谈》就有详尽介绍。它是在传统的例如唐代的整版雕刻印刷基础上的一次飞跃和突进。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中曾有记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想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韩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社会历史背景的切入,还需加以细化和深化,不能仅限于经济、社会因素,还应包括政治文化。如果没有北宋末期政治文化的解禁,也就无法形成新的历史语境。对苏轼,宋徽宗仍实行元佑党禁,到靖康元年,宋钦宗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解除元佑党禁包括学术之禁,于是苏轼便风靡一时,成为士人们公开的效法榜样,苏轼词风便大盛于建炎。两宋绵延不断的民族战争,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终宋朝覆没。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荡和消歇,带来了美学思潮的更迭与变化,从而产生社会历史事变与美学思潮的整合。这种整合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寻求美学史发展的动态机制,这是避免把美学史滤化为纯净水。高度评价季宋的美学史地位,其着眼点不是纯美学,而是社会历史美学。宋末因为真正的国破家亡,激荡起又一次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感的浪潮,焕发出又一次绚丽的亮光。在美学史上,它不是以静穆平和的状态体现出来,也不是以圆熟精纯的形式表达出来,在纯审美艺术层面,或有不及。然而审美主体本身在囹圄之内或押解途中,没有此种环境和心境去精雕细琢,便略显粗糙,反倒是审美真实性品格的表征。他们以巨大的人格力量和亮丽的人格精神支撑着审美的世界并照耀着这片天地。他们的审美品格正是在审美的原初和本位意义上取得的。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审美广为人们所接受,得以沿传。
从社会历史背景上解读审美现象,是一种切入方式,而从审美现象上又可以反转过来阐解社会意识,从而构合为双向流程。例如南宋画士纷纷临摹《清明上河图》,以表故国之思,就存在一种社会情绪。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借以焕激宋代的时代精神;他另有《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借唐人精神以激励宋人。从柳词中看到了宋代的汴梁繁华,足可与《宋史》、《东京梦华录》相并列。他著名的《望海潮》写“钱塘自古繁华”,所谓引得金主完颜亮萌发投鞭渡江之志的传说,却足以看出审美中的社会因素。有所谓文史互证,则有词史互证——社会史与审美史的互证。
——从文化学的规律切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颇具时尚性的文化学的美学和美学史研究,而仍然是从历代的具体特征出发所进行的切入性研究。因为宋代是一个比其他时代更具有文化味和书卷气的社会,理所当然地要进行这种文化学与审美学的整合,产生互涵互摄的学术格局。支撑宋代文化学的有两大支柱:一是史学,一是理学,便成为导进美学的切入点。
宋代史学的两种精神:淑世精神、忧患意识便成为与美学沟连的通道。理学与美学,是宋代美学史最需要回答的问题,犹如六朝玄学与美学、唐代佛学与美学一样。这项整合性研究又是从“本体论”、“主体论”、“范畴论”着手的,尤其对“涵泳”这一新的理学—美学范畴进行细致剖析,看其是如何从理学引入美学,它的具体审美涵义、意义及其对后期中国美学史的影响等,这样就深入而非浮泛、具体而不抽象地产生理学—美学在形态学和范畴学上的建构。
三、美学史地位的实际定位
存在于美学史长河中的每一个现象(无论以何种状态和规模出现)都存在着史的地位问题,也就涉及到对其加以定位的问题,事实上每一种类别史都要讲这个问题。不讲或少讲史的地位,对于史著来说是不完全的,使得史著会缺少深度和史感。所以,本文着重谈论这一问题。史的地位定位主要看其提供了哪些新的创获,自身作出了哪些贡献,对后代发挥了哪些影响。史的地位的确定,是高屋建瓴的俯瞰,但却应该在微观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找出其中的精神亮点;对某一现象、现象丛体,或断代史的某一美学门类等等,都应该置身于中国美学史的长程中考察。说到底还是一个“通”字,“通”不是简单的写法问题,更重要的是视域问题,史卷宏通,视域宏放。在通史中看断代,宋代美学史郁然灿丽、彬彬大备,郁郁乎文哉的特征及其与别代所不同的美学史地位便凸现出来。
就某一理论成就而言,宋代山水绘画美学理论虽然博大精深,在总体思路上仍是中国美学理论的传统格局。尽管门类不同,但在深层次的美学底蕴上跟文学美学的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是一致的。这就可以看出,宋代的绘画美学论仍未脱离中国美学论的总体框架。这也就形成了它的定位。在断代与断代之间看本代,互相观照中才会看得更准确、更清楚。我们把唐与宋的差异看成是水系的差异。唐诗是一条河,流至宋代打了个漩涡,宋代诗人在旋转、迂回的水程中寻到了诗的审美积淀,江西诗派所作的基本上是这一工作,黄庭坚则成为其代表。从这个积淀层中他们获得了审美的养分,转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生长点,于是便又改变水道,并且冲刷河道,形成独立的一大水系,留给后代的便有这唐宋两条水系之争。唐与宋的美学差异几乎体现在所有领域,书法美学上唐尚法,宋尚意;唐诗是经验世界的心灵化,宋诗则是对象世界的人文化,等。唐、宋美学差异是文化差异,宋的舞蹈缺少唐的气派,这跟宋的整个文化精神、社会气象相联系。这种差异还取决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两宋均存在着歌妓文化现象,它跟唐有所不同,唐的性质是才子、新科进士与妓女的情爱活动,宋代则是与歌妓的接触、交流中所形成的文化、审美活动。其典型代表是柳永,他为歌妓写曲辞,通过歌妓传播出去。这一现象的出现,极大地规范了宋代乐舞文化的审美性质。
考量所提供的新因素是看原创性的成就。例如宋的素瓷;欧阳修的以文为赋,苏轼的以诗为词,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都是新的审美发展,也是新的生长点。绘画美学上,郭熙的“三远”论,苏轼的身与物化论,董逌的“以牛观牛”论等,都是宋代新论。宋话本通俗化的审美特征,戏曲的讽刺喜剧的审美特质,等等,都是创新性的成就。
根据不同人物在美学史上所提供的资源、所作出的贡献,以确定不同的地位。不是简单地陈述他们做了些什么,而是考量其所发挥的历史(美学史)作用,进而确定不同的人物类别。大致有这样几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刘辰翁的小说评点,尽管没有后来者那样辗转生发、淋漓尽致,但所起的却是先河、先声作用。于是,小说评点便成为中国小说美学的重要形式和方式。欧阳修词开士大夫词风之先。范仲淹开边塞词风,不能因为词的数量少,就不给予足够的估价。范仲淹词还是议论入词的原创者。柳永词开辟通俗化的词审美方向。领军人物,(或曰代表人物)。建炎南渡的事变改变了人们对词的文学审美功能的体认,即由言情转为言志,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这成为全社会的一致意志和愿望。岳飞作为军人,所写的是英雄词,在美学上可称为角色之词,即英雄词人。在这条联系南宋词史的线索中,岳飞是最初的呐喊者、先行者。中介人物。确定中介期、中介人物是对美学史的一种叙述性策略,《唐代美学史》把张说确立为初盛唐美学的中介人物,把杜甫确立为盛中唐美学的中介人物。所谓中介人物,就是经过他们的中介作用,改变了旧有的美学状况,引发出新的美学状貌。过去的美学史不能直接进入新的美学史,需通过这些人物加以中介。在宋代,陈与义是杜甫与陆游之间诗歌审美风格的中介人物;贺铸是英雄主义词的中介人物,他不是开风气之先,也不是领军的,他在苏辛词风中起到过渡性的作用。晏几道词是晏殊、欧阳修词美学的延续,又是变异,是孕育柳永、苏轼词的中介,没有这个中介就不会有新的飞跃。在中介人物中有的起到转折作用,例如词美学中的姜夔,书法美学中的蔡襄。又有传承人物,例如宋“四名臣”。从总体上对某一人物的定位要综合考量、恰当把握,例如对秦观词美学史地位的确认。传承和变异是对美学史演变图式的总确定,而在揭示美学史传承与变异的过程中,又需注意到:避免把朝代更迭与美学史的时代转换混为一谈。朝代更迭是政权转换,属于政治学范畴,美学不会像政权更迭一样变化迅速和直接,它有相对延伸期和惯性运动期。宋初受到晚唐美学很深影响,产生了一个超越朝代更迭的美学史阶段。从本质上说晚唐和宋初属于同一个美学史区间,这是以西昆体、晚唐体、白体诗为标志的。在此基础上,在发现新的时代审美因素之后,考察新旧更替的过程。宋受晚唐影响,只是一段时间而已,新的审美因素在旧的机体上潜生暗长,到一定时期,自身条件孕育成熟,便会起而清算前代美学史的弊端,建立自己时代的美学。于是,便有王禹偁的另立旗帜、柳开对五代的矫正、穆修的反骈、石介痛斥西昆体,可以说是出现了全面清算晚唐五代美学的态势,这段新旧交替的过程内容十分丰富、色彩也十分绚丽,是宋代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看点。它进而为后来的那场声势浩壮的诗文革新运动鸣响了前奏曲。宋代绘画美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摆脱五代绘画传习,走向独立成体,蔚为大观的阶段。熙宁、元丰年间是宋代绘画美学的重要时期,这是改变五代,形成宋风的重要时期,它是以花鸟画家崔白、山水画家郭熙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一描述展示和确定方式,又以某一审美现象为案例,细致地爬梳并呈示出它的演化和兴衰过程。如前述的西昆体,曾在宋初走红;石介的批判,使其受到重创。而黄庭坚的诗美学主张以及瘦硬挺拔、奇峭古朴、沉雄高绝的审美风格的建立,洗尽铅华,剥落香奁,就把西昆体彻底淘汰出局,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说,“唐人之风变矣。”这个过程的展示才是我们所体认的本体性美学史。而美学史地位的确认又是通过某一存在现象加以凝定。为什么会有黄庭坚的风格,是美学史的一种需要。黄庭坚是宋诗的总代表,其论是宋代诗美学的总宣言,他的诗是彻底的宋诗,苏诗还不完全是,尚有唐韵。
美学史不是现象的陈列,而是解读;不是材料的堆码,而是发现。演变轨迹,如“初谈”所说的同化与“异化”,而演变则有线索可寻,可加以描绘和叙述。宋代美学中最具有文体美学标志的是词。诗庄词媚,是最原初定论,但在宋代,它的性质、功能经过了重大变革,由此引发了理论主张和创作形态的重大变化和争议。经过北南宋交替时期的巨变,词演变为英雄词,到南宋,词的审美功能均被赋予为对重大时势事变具有传载作用。李清照《词论》实际上是对这种审美趋向的纠正和反拨。梦窗词和白石词的出现,又体现了词的新变和发展,直接联结了清真词。这样,经过爱国主义精神的激荡后,词又恢复到原有的审美基点上。这可以看出词的审美本体力量的强韧、基核的坚硬,也揭示了词的审美发展历程,从而铺设了词在南宋的美学史轨迹。它提示着人们,婉约始终是宋词美学史的主流派和主流话语,然而在时局变动中豪放、婉约又会时起时落。历史语境规范了审美话语,于是,出现抗战文艺,抗战、图存压倒了一切,在审美上内容压倒了形式、思想压倒了艺术。随着抗战文艺的萎缩,原先的淡淳幽雅话语复又抬头。宋词是一个与时势联系密切的文学审美种类。
美学史是时代存在的美的发现史和诠释史。所谓发现,不仅指资料,而且指审美理想和审美形态。宋代最重要的审美理想是“淡”,审美意识是“韵”。绘画美学上,唐代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但到宋代翻了个儿,逸品居首,而且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莫可楷模”。在审美形态上,宋代出现文人词、文人画、文人园,最能体现宋代美学精神,进而出现三项结合:诗画一体、词园相合、书画同源(进一步延续到元代),也就最能代表宋代美学特点,从而也最具有美学史地位。
四、书写程序和话语系统
美学史书写程序大致是:社会历史背景的描述与勾画,为美学史的形成和发展,寻找依据,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整合→从个体切入,形成个体解读的底色→文体美学→门类美学→群体美学(流派)→思潮→区段、时期美学→时代美学,对时代美学的特征、理想、地位加以定位,对其在美学史影响进行揭示。在这个过程中尤要进行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处理和互构活动。从个体出发到把握住整个的时代审美理想、精神(这是由无数个体所创造和构成的),然后反转来以时代审美理想、精神为屏幕透视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这里又要突出的是个体与思潮的关系。不通过具体而微的分析就无法彰显、凸现出思潮的特征,因为思潮的最终落脚点和体现者是个体。例如对姜夔和姜派词人的美学史地位的分析。美学思潮是一个重大课题。宋代是一个思潮特征特别显著的美学史时代,有的还形成了“运动”,如诗文革新运动。思潮形成有外界因素例如民族战争,内部因素例如变法变革,自身因素例如诗歌变革,江西诗派的出现。对思潮,可以进行具体的共时性研究;而进行思潮更迭的研究,则是历时性研究,更具有史的发展意义和价值。从思潮的视阈考察,是最富于史感深度的。杨万里的文学审美体现了宋代文学审美思潮的又一个重大变化。求“活法”在审美方向和趣味上改变了江西诗法,走向轻松、活泼、机趣,带有自然和生活对象本身的鲜活性质。“诚斋体”的诗审美,影响了此后的江湖派,具备了美学史的思潮演变地位。李清照、陈师道的本色论,均反映了宋代美学思潮的变动特点。特别要注目于思潮的波荡变化,寻绎出变化的线索。江西诗派摆脱晚唐诗派,而到南宋后期以杨万里为代表的诗人则否定之否定,摆脱江西回归晚唐,死灰复燃,很有色彩,也很有史感。
美学史撰述还应当与教科书美学理论知识相沟通,进而实现整合。教科书的美学理论的形成来之于审美的具体创造、审美形态,也来之于美的历程,也就是从美学史林林总总的现象中提炼出来的。它们在原初是整合的。但是,有些美学史著、论,在解读史的现象时恰恰忘记了美学理论知识所曾经提供的东西。教科书的美学理论知识为什么就不能用于美学史研究呢?美学理论知识讲审美感受,但到美学史却不讲,是缺失。美学理论知识中讲审美体验,在解读美学史现象时当然就需要讲。例如苏轼的书法。苏字真力弥满,逸气四射,纵横自如,挟带天风海雨、惊涛骇浪,如怒龙喷水、虎啸山庄,富于生机力量。他的字随物赋形,随意挥洒,可大可小,可收可放,其“意”极丰厚而灵动,或纵横驰骋,或信马由缰,有着极鲜明的审美节奏感和生命律动。就《赤壁赋》帖、《楚颂》帖而言,那种观赏苏字所调动起的情绪感应和生命感受的体验特征,让人们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在对美学史上的审美形态现象解读上,所出现的审美体验论的印证。又例如意象分析是美学理论研究中的常用方法,当然适用于美学史。从意象出现的频率,发现审美主体的意向、意图,进而发掘其意味。柳永词喜用“断”,摒却和颠复对象的完整形态。《曲玉管》:“断雁无凭”,《采莲令》:“断肠争忍回顾”,《少年游》:“断肠声尽”,《夜半乐》:“断鸿声,远长天暮”,《倾杯》:“空目断,远峰凝碧”,等等。尤其是《玉蝴蝶》:“断鸿声里,立尽斜阳”,更形成了孤寂冷落的形象在映衬中的塑造。再例如时空美学。范仲淹《苏幕遮》:“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形成空间的无限延宕。《玉楼春》中:“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延伸,形成时空交错的审美布局。而时空美学中又有着情感意味。欧阳修《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元夜时”的“月与灯依旧”,时空相同,却人事巨变:“不见去年人”,从而逼发出情感巨变:“泪湿春衫袖”。
“初谈”中说到了美学史撰著过程中描述与概括的问题,未及例举,现就宋代建筑园林美学加以实证。无描述则无现象的展示和历史图画的呈现,这是接受者进入史的门槛和世界的必由之路,是美的感性形态的确认,然而,描述后应该有概括,概括所表现的方式是提炼,其着力点则是提升,是形成史的话语判断。于是,进行了这样的概括:由唐入宋,中国园林在审美上格调有变化,审美格调反映了美学精神,而又在物化体的形式上体现出来(这是揭示的史的演化)。宋代园林文化和美学精神的精髓就在于把物质现象的园林视为精神现象,这样就自然超越了物质领域进入精神层次——文化、审美层次。于是,园林便是用于陶冶心志、怡养精神,也因之形成了宋代园林以至于整个中国园林的精神定位——文人园的审美化(这是概括的文化、美学内涵)。以精小为规模、以雅致为风调,宋代士大夫文人以此作为构筑园林的审美依据,又从所构筑的园林中获取了审美的感觉经验(这是揭示的审美特征)。
在“初谈”中还说到撰述过程中的实地考察问题。实地考察是为了亲验历史、置身历史、复活历史——复原原像,获得与历史亲身对话的经验和话语。面对遗址、存物,撰述主体的角色身分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美学史家,所进行的体认和所获得的感受是审美的,是历史的意趣。这种治史方式有着文献资料阅读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保证了美学史撰述的当下语境性质和经验主体性格。
本刊责任编辑注:该文见《美学》2004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