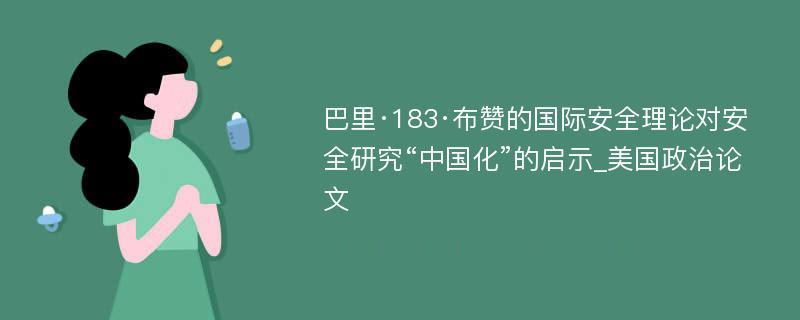
巴里#183;布赞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安全研究“中国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里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教授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琳娜·汉森副教授通力合作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①经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精心翻译已正式在中国出版。该书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并不仅仅多了一本权威的教材,更重要的是,分析和梳理两位教授在该书中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如何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将结合该书的一些理论和思维特点,来探讨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这一著述对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启迪,并进而从他们的视角来寻找国际安全研究“中国化”应该具有的思考。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三大学术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安全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科中最重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之一。本书有三大特色。
首先,该书是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界中“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史。正如该书的标题所阐明的,这是一本总结、梳理“国际安全研究”如何演进的著作。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不仅能了解“国际安全研究”的形成与进展,更重要的是,了解安全研究的演进路程,也是拓展我们安全视角的重要动力。
在此著作出版之前,已出现一系列有关国际安全研究的系谱学总结和介绍性的图书出版。这些书籍中有代表性的包括:爱德华·克沃杰伊(Edward A.Kolodziej)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特里·特里夫(Terry Terriff)等人共同协作的《今天的安全研究》、龙尼·D.利普许茨(Ronnie D.Lipschutz)主编的《论安全》,以及艾尔塞尔·爱登勒(Ersel Aydinli)与詹姆斯·罗西瑙(James.N.Rosenau)合作编辑的《全球化、安全和民族国家》。②这些著作都从国际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日程发展等诸多方面,分析和讨论了国际安全从概念、主体和研究议题等诸多领域内的新变化。然而,这些著作的缺陷要么是偏重于理性主义的安全议程,要么过分强调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兴起的“规范主义”或者说“后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都没有将这两大安全研究的分支——重军事、政治和外交研究的“美国主义”与重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视角的“欧洲主义”进行有效的整合,更没有从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有说服力地概括和介绍“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差异与联系。
其次,布赞和汉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美国主义”的“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国际安全研究起步于冷战阶段。这一阶段安全研究的核心话题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避免世界再度悲剧性地陷入新的大国战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安全研究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命题,那就是如何抵制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扩展、如何防止在经济和军事能力上和西方集团并驾齐驱的苏联集团战胜西方“自由世界”。在此背景下,安全研究绝对就是“国家安全”——以增强西方国家应对苏联威胁的能力建设和战略制定为核心,辅之以有效的政策实施和资源动员。国际安全研究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该研究就是围绕国家在权力竞争中究竟如何能够得以生存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安全研究也具有如何防止内部威胁的讨论,但其焦点都是围绕国家如何防止遭受各种其他国家施加的“外部威胁”的争论。
冷战时代安全研究的支配性范式显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带来各种国家主义安全研究的强有力的理论解释系统,安全研究也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成长和发展最重要的实证来源。其结果,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确定了国家作为主体、武力使用作为关注核心、外在风险作为威胁的基本来源,以及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和危机管理与应对为主要政策措施、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安全学说。
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逐步进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时期”。被冷战阴霾长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国际学术界终于可以开始同“生存”的沉重主题拉开一些距离,转而寻求对冷战教训和各种问题的反思,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多元主义”的趋势。1991年,冷战的结束更是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事件。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多元主义争论,最终汇集成为对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颠覆性批判。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安全研究发起对继续坚持传统主义安全研究议程、继续强调理性主义方法论的“美国主义”安全研究的强大挑战。而美国的安全研究继续保持了传统主义特点,强调安全研究就是“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和安全研究存在着重大关联度的“战略研究”则永远是探讨如何“打赢战争的艺术”。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争论,让国际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期。其学术成就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均势理论”、“霸权稳定”、“理性决策”、“安全合作”、“军控和裁军”和“战略研究”等分支。布赞和汉森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概括了国际安全研究的11个分支,它们分别是:“常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性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和平研究”、“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战略研究”,以及“新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这些安全研究中的不同学派,为我们呈现不是单纯从国家与主权角度而是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剖析和思考。这些分支和学派很多显示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解释功能”,构成了“知识驱动型”的理论而非“政策指导型”的理论。这些色彩斑斓、各有学术依据的安全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认识的全息画卷。正如该书《自序》中所说的,“这样一部思想史记载着不同学术视角如何相互影响、彼此吸纳和不断交锋……一部思想与科学社会学史能帮助国际安全研究者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理论从何而来,为何不同,它们之间的哪些争论事实上将整个安全研究领域链接在一起”。④
与此相对应的是,爱德华·克沃杰伊的《安全与国际关系》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权威性国际安全研究教材。该书的特点是希望以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为主体,来合并和兼容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理念主义等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安全研究。克沃杰伊教授认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安全研究的理论范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都难以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的现实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为此,他强调国际安全研究的未来应该是实现各种范式之间的“融合”,进而形成更具实证意义和经验检验作用的安全范式。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永远是如何理解为什么在国家关系中会“增加或者减少暴力”的问题。⑤克沃杰伊教授的看法依然保持了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而不是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想要竭力倡导的“欧洲主义”。
再次,布赞教授集40年安全研究的知识积累,高屋建瓴地对国际安全问题在进入范式多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进行系统的学科史总结,站在一个全球的视野上透视今天安全研究的演化,并希望在国际安全研究的学术领域,廓清时代特征条件下的未来安全研究议程。显然,对安全研究的学术成长来说,布赞和汉森教授的这一力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们提出的国际安全研究的四类问题——是否应该把国家作为研究的优先指涉对象,是否应该同时将内部、外部的威胁纳入安全的考虑范围,是否应该将安全扩大到军事领域与武力使用之外,以及安全是否必然与威胁、危险和紧急事态相关联,可以说集中和生动地概括了今天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多视角和竞争性的范式。
布赞和汉森教授对安全概念的解释也颇具新意。例如,两位教授认为,为了很好地解释安全的概念,必须引入三组和安全概念相关联的概念。第一,对安全理解的“补充新概念”,即必须将安全引入更加具体和更加具有限定性的问题之中,例如,威慑、战略和遏制等;第二,必须考虑和安全概念具有重叠性的“平行性概念”,例如,权力、主权、认同等;第三,必须参考和安全概念存在着替代性的“竞争性概念”,例如,和平、冲突防止、风险控制与合作等。将安全的定义做这样的分析和解释,显然对于读者理解“安全”究竟是什么,以及掌握安全与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权力、和平及战略研究等——的联系与区别,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当代国际关系学科中,安全与和平似乎在内在逻辑上密不可分,“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却完全是独立的两个领域。“安全研究”在强调以权力为手段、以国家为主体的分析语境中,生存和防止遭受不可承受的暴力是核心问题。但“和平研究”则是一种以世界主义的和平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平研究”的主体常常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它更重视对实现停火、危机控制和冲突预防的技术性操作。⑥
布赞与汉森教授对安全概念所提供的这一分析结构,对于澄清国际关系领域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中其他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作用。
为安全概念的清晰化提供分析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安全研究的努力方向。例如,在分析安全时,学者认为,“谁的安全”是一个中心话题。⑦因为对于不同的安全主体有着不同的安全理解和安全需求。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赞教授就提出安全不仅是“国家的”的、“国际的”,也是“社会的”。因为如果社会结构中的个体——人民不能享有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内在崩溃一定是导致国际不安全的根源。⑧冷战结束之后,“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成为安全概念扩展的重要方向,联合国强调安全的定义“不仅要让人民免于拥有和平,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安全讨论的范围开始延伸到“国内”,安全的主体也由国家延伸到了“人民”。其经典案例是“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如果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崩溃,人民无法得到经济生活领域内的可靠保障,那么,这样的国内混乱就一定会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暴力组织滋生与繁衍的温床。与此同时,这些“失败国家”的国内失序,也必定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将暴力威胁持续散发到国际领域。
与此同时,一系列后冷战时代安全因素的革命性变化为安全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结构,例如,全球金融与经济安全、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安全等。安全不仅是“人的安全”、“国家的安全”,安全同时也是“区域安全”与“全球安全”。这四个层次的安全是一个相互重叠但又各有区分的扁平状的四个独立领域。
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所提供的三个相互关联性安全概念的分析结构,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安全研究而非现实世界的安全议题的分析结构。这一结构不是旨在准确勾勒安全议题的范畴和层次,而是旨在说明国际关系学中的安全研究领域,可以同其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概念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联。
然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国际安全研究演进》一书非常富有学术开放性,但又有挥之不去的学术模糊性的一面。两位教授特别强调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相互重叠,又始终在努力想要清晰地划出这两个领域间的界限。他们认为,区别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因素是国际安全研究开始更加聚焦安全的前提假设和安全概念的争论。这些争论可以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疆域,因为国际关系研究不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唯一学科来源。在冷战时期,政治学理论、经济学中最早使用的博弈论、政治和社会心理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都为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各种分支理论(例如,威慑理论、认知理论等)的创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两位教授所言,国际安全研究没有明确的“边界”,但有“边疆地带”。
学科领域内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学说都有“主流”和“非主流”,国际安全研究当然有其特定的“疆域”,这就构成该研究领域内的“主流阵地”;而“边疆地带”并非是争议最大的地区,而是对争议提出“学术批评”的“非主流阵地”。问题是在今天的国际安全研究中,“欧洲主义”恰恰是“边疆地带”,但该书并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非主流”的领域。和其他否定安全研究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欧洲学派”相比,该书就安全研究的各种观点和学说所做的归类和划分,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折中主义,这也可以说是其又一大特色。
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中,“欧洲学派”又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它综合了三大分支:“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巴黎学派”(Paris School)和“阿伯里斯特威斯学派”(Aberystwyth School)。这三大流派虽然有各自的研究侧重和研究方法,其成员也非简单地侧重在欧洲,但都是建构主义学者、非现实主义和欧洲价值导向的。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安全研究都不同于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安全研究,而是侧重在研究不同的安全主体、社会结构为安全的决定要素,人的安全与“人类解放”、安全与“安全化”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的安全和“非安全管理”的专业建设。⑨在这些学者中走得更远的是完全沉醉于用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来批评和解构传统的安全话语。他们批评的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范式主导下、权力和国家中心主义的安全语境,而是根本否定以国家为安全主体,转向以“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理论”为认识论核心的安全观念。它们的方法论是“福柯式的后现代主义”、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学说和形形色色政治理想的产物。⑩其理论特色是不再承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分支,而是要强调所谓在安全研究中安全“去边界化”(Debordering)。
之所以有安全研究的“欧洲学派”,是因为这些欧洲学者相信,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两者并不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打破“国际”和“国内”的认知差异,是欧洲主义的国际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基础。然而,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坚持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研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学科。国际政治学者坚信,国际系统完全不同于国内系统,因此,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两个虽有一定关联但却互不隶属的两大研究领域。但欧洲主义的学者坚信,人类的政治活动是一个整体,“国内”和“国际”是不能拆分的。这是“欧洲主义”的安全研究竭力颠覆传统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主导的、“美国主义”的安全研究的重要武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旦人类政治生活没有了“国际”和“国内”的区别,那么,安全研究就不能单纯停留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层面,而需要更多地关注人类日常生活更为广泛和频繁的国内政治领域。国际安全研究的“国内威胁”也就自然成为将比国家间竞争和冲突更重要的“学术疆界”。(11)
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显然并不完全接受这种“泛疆域化”的安全研究。布赞教授在1998年曾提出,他并不拘泥于安全研究中的“国际与国内两分法”,因为许多的案例研究所显示的“不安全状况”并不是“国家主导”的。但他认为,国际安全研究还是有其独特的“研究议程”,“构成国际安全议题的通常都是对安全的政治与军事解读”。(12)
在该书中,布赞和汉森教授显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一方面,他们在该书第二章中坚持认为,国际安全研究存在着“经典政治理解”及“规范主义”方法论的“二元论”。国际安全研究就是在这一二元语境中“建构安全选择的倾向”。正是在此观念的支配下,该书保持了布赞教授安全研究的基本立场,即在“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之间争取最大的平衡点。为此,两位教授一方面通过考察中世纪以来经法国大革命一直到今天人类政治生活进步的本质,强调界定国家与公民、人民或社会个体的自由与安全是一切政治理论认识的前提。在突出“国家安全”的同时,必须存在着“个体安全”与“群体或者社会安全”。他们认为,“不安全”有时是国家本身造成的,保障个体安全是减少国际冲突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批评传统主义的安全研究中现实主义范式弊病的同时,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并不否认传统主义安全研究议程的重要性。他们承认,现实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权力政治解释是现实世界中“物质要素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推动国际安全研究演进的五大动力之首,就是人类社会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大国政治”或者“权力政治”。
正因为如此,《国际安全研究的演进》一书强调,不管人类社会和学术界在“规范主义”或者“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展示了多么强大的思辨魅力和人文精神,国际安全研究最显著的驱动力是“世界主要大国间权力配置的变动和不变动”;(13)“9·11”事件后“国家安全的回归”不仅是由于恐怖主义组织的暴力威胁,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安全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直坚持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独享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威胁”。(14)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布赞和汉森教授在该书中承认,尽管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在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有了巨大拓展,但传统的安全议题也在“惊人地延续”。
二、接受安全研究的多元范式和视角,推进国际安全研究的“中国化”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认知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和主观化。例如,究竟如何认识中美关系,如何定位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努力究竟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人的安全?安全利益究竟是国家安全至上还是公共利益的发展、人民的富裕是安全的根本保障?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可以肯定,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历史性的转型时期。安全研究的“中国化”,首先我们必须跳出单一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窠臼,真正从多元视角和范式出发来审视和回答中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在这方面,《国际安全研究的演进》恰恰可以向我们提供多元化的安全理解和安全研究议程。
布赞和汉森教授接受冷战时期国际安全研究被现实主义及后来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范式所主导的事实,但认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安全理论研究范式“建立了对现实的假设,而同时它或许又创造了它所假设的现实”。(15)但这个安全分析的现实主义现实过于“政治化”,它可能延续着安全研究的“国家安全逻辑”或者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安全永远是针对“外来威胁”的假设,然而,这种拘泥于单纯一种范式来探讨安全问题的学术努力和认知方式本身就是片面的。即便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选择”学说将国家视为“理性行为体”,且不说国家的“理性”常常采取表现为“过度的安全反应”,即便“理性选择”的新自由主义的安全假设,也常常更多地注重物质力量的作用,忽视规范、观念、认同等认知(ideational)因素的作用。
为此,布赞和汉森教授强调他们在安全研究的文献梳理中所采用的“后库恩主义的科学社会学”(Post-Kuhanian sociology of science)认识论。“后库恩主义”的认识论,即坚持社会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强调的观点: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并不简单来自对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和发现的积累,而是来自认识人类社会生活的知识系统的创新与发展;而衡量和判断不同知识系统的重要标志是其“核心的假设和逻辑体系”——范式(paradigm)。库恩认为,在单一的“范式”领域内,人类的科学知识永远难以进步。但“范式”创新的根本动力是“科学实证主义”。布赞和汉森教授批评库恩主义中的“实证主义研究至上”的论断,否认安全研究的知识体系只来自于经验和事实。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分析并不能单纯依靠经验和事实,更需要坚持“规范主义”(normative)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许多新的方法论,例如,“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同样可以使学者对安全思考进行“归纳性”研究和“推论性”研究的结合。这一点构成了两位作者所说的他们写作本书时的“认识论立场”(epistemologist footing)。具体来说,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更相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社会学”,而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理性主义”。
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宏观分析架构呈现出“欧洲特色”,但在这些既有联系但又常常对立的安全理解和安全研究议程的背后,不是简单的看法不同或者对现实的“安全世界”的认识不同,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多元化,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对安全问题的不同认知和反应。这些总结对于急切在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来说,提供了难得的分析工具和理性的认知方法。
其次,与19世纪和20世纪相比,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政治”的逻辑虽然根深蒂固,但由于科技、经济和价值等因素的作用,再加上20世界后期以来全球持续的民主化变革,世界政治的运行法则、利益标准及参与主体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基于17-20世纪“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的国际安全理论是否依然能有效地解释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国家间的安全互动,成为一个引入关注的深刻话题。
中国的崛起需要我们从观念更新、政策设计到国际角色转化等许多方面进行智力准备,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中开创“中国经验”。这不仅是为了走出大国争霸和大国冲突的历史主题,同时,也是中国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的国家崛起和人民福祉的基本保证。为此,如何深入理解、把握21世纪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新规律,是对中国政策的巨大考验,也是中国学术界担负的重要使命。
布赞和汉森教授认为,安全的基本认识只有包括三个部分的综合才是全面的。这就是“客观安全”(objective security)、“主观安全”(subjective security)和“话语安全”(incursive security)。“客观安全”是指“缺乏、或者存在以能力为基础的威胁”;“主观安全”是“对威胁的感知或者主体的感觉决定是否存在什么性质威胁和多大程度上威胁”;“话语安全”认为“安全议题”是由政治、历史和社会性因素所决定的,安全说到底是“一种言论行为”,并不能真正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为此,“安全”永远是特定政治议程中自我指涉的“问题”,产生这样的安全事实的本质力量并非“物质性”的,而是各种行为者之间“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观念互动过程。因为“威胁的识别及其意义的赋予最好是通过认同的建构与制度的转型来展开分析”。(16)
今天中国国内的安全问题争论,恰恰是许多人忽视了安全的“三维存在”,要么一味凭借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中国落后挨打时的痛苦历史经验,过多地强调安全的“主观面”;要么过分迷信安全的“物质标准”而急于强化军事力量和缩小与主导国家的差距;要么偏重于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和苛责,相信中国崛起过程难以是一个“共赢的过程”。其实,当深入地从安全的“三维存在”来探讨安全议题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到评判和衡量安全,更需要了解的是“谁的安全”。换句话来说,如何确立安全的主体、区分安全在政治议程上的定位并寻找出建立必要的安全努力在目标和受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才是合理与准确地分析安全问题的关键。否则,竞争性的利益群体、社会声音甚至特定政治议程下的安全看法,很容易上升并成为压制性的安全主张。
再次,安全研究的“中国化”必须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保持平衡。今天,中国安全研究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根据21世纪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战略目标,科学、准确和战略性地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两大安全领域中,确立中国际关系领域内安全研究的议题,这已成为包括中国国内学术界在内的普遍的国际共识。“传统安全”是指用外交、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应对和实现安全问题,例如,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避免受其他强国的军事干预和军事胁迫;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保障国家在各国间力量对比中享有相对稳定的安全感;提高军事能力,确立相应的军事原则,以便预防冲突和保持必要的选择;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在国家战略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有效、合理及战略性地运用国防手段,等等。“非传统安全”主要是指非军事性质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和及时地应对,同样将会实质性地损害一个国家的安全努力,弱化该国在传统领域内的安全努力,并将造成严重的不安全后果。例如,网络安全、经济和金融安全、环境安全、水资源安全、食品安全、打击和严防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生物安全、公共健康安全,等等。与此同时,对一个国家来说,安全威胁的来源不仅是“国际的”,同时也是“国内的”;安全的主体不仅是“国家的”,也是“社会的”和“个人的”。
安全的分类、定义和研究议程,从“传统领域”走向“非传统领域”,这不仅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时代国际局势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安全概念和内涵都扩大和深化的结果;更是在各种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安全的挑战和构成不安全的根源事实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结果。显然,该书将为中国读者打开科学认识安全问题的“新视窗”。
最后,“国际”与“国内”安全研究究竟如何平衡和相互促进,合理地确定它们在安全研究的总体分析架构和政策应对框架中的地位和关系,是中国安全研究需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被关注。近10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对如何定义中国的国家安全、如何审视中国今天崛起进程中面临的安全挑战,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如何发展中国国家安全维护的手段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同时,“中国崛起”已成为今天全球安全研究的热门课题。其原因不仅是中国崛起将改变西方国家的认知,即中国崛起将导致国际体系内利益的再分配,并将导致西方传统的心理优势丧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触动了安全研究领域内一个古老的理论命题,那就是“大国崛起”及由此而出现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从人类历史来看,这常常是造成冲突和战争最重要的根源。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国崛起”更是一个荣誉、威望和满足感等心理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因此,“中国崛起”并不必然带来鲜花、掌声和鼓励;相反,由于中国崛起带来了国际关系中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的再分配,结果是相当部分的国家对中国充满了疑虑、猜忌、怀疑,给予中国更多的是批评、指责,甚至是非难和防范。21世纪世界政治最大的话题之一,可能将是如何在中国赢得更多安全的同时,让世界也变得更加安全。
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或者说远远超出了中国安全的“国际因素”。如果对这一话题感兴趣,如果坚信21世纪中国能够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安全的“国内因素”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国家安全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政策、从主观到客观的诸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进行的体制和观念转型、治理模式的更新和发展、中国人审视世界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进步等等因素,很可能比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与认知的影响更大。例如,笔者一直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更严峻和紧迫的安全挑战来源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内的”。(17)“安全”这一概念如何定义,如何来有效地维护、保障和实现一个国家的安全需求,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如何建立起长期的、可靠的基础上,特别是“安全”如何同“发展”、“治理”、“民主化”和“法治”等概念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这些问题比单纯从政治、军事和传统的战略层面思考的安全议题复杂得多,但很可能又更重要得多。
布赞和汉森并非是20世纪90年代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狂热地追求“去国家化”的“政治社会学者”(political sociologist)。他们强调,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理性主义”与“规范主义”、物质力量和非物质力量都是不可或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他们提出的国际安全研究的五大驱动力中,“理性主义”和“规范主义”妥协性地并存。这五大动力既有“权力政治”、“技术因素”和“制度化”,又有“国际事件”和“学术争论的国内动态”。前三大动力显然都是属于“理性主义”范畴,而“学术争论的国内动态”更多的是强调认知因素、话语因素和规范主义分析因素对安全研究的作用。“国际事件”可以介于这两者之间。因为“国际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常常是“物质主义”的,但对其解读和反应又常常是“观念性”的、“话语性”的。布赞本人的研究显然更倾向于把安全既不解释成“客观的”也不是单纯“主观的”,而是更符合他所提出的“话语安全”的特征。在1998年出版的《安全: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布赞教授提出,总的来说,安全是一种“自我指称的活动”,因为安全的观念和紧迫性,都受到特定的政治日程的左右。(18)
显然,对中国来说,合理与科学地认识安全的“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全球政治中,转型国家的安全挑战都特别复杂和动荡,无论是转型成功还是转型遭遇到挫折甚至失败,都会带来对安全的新思考。今天,我们的思考和目光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国家层面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应对,还需要了解安全研究的“国内议题”,以便更加全面和客观地审视和判断中国正在面临的安全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对安全挑战更为重要的思考和行动,是要回到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的潮流中来。大国兴衰的本质是经济活力、体制效率和价值魅力之争。美欧日西方经济体与中俄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之间围绕着经济成长道路的“模式之争”将是全球战略态势未来走向最重要看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目前,西方对这两种模式的利弊争论方兴未艾。(19)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各有其成就与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兴利除弊、革旧迎新。目前,全球经济比的不仅是谁先走出低迷和窘境,更要看是谁先下决心改革。在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增长竞争,最终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体制修补、调整和革新的能力。大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说到底是经济、金融、工业制造业与科技创新能力间的竞争和较量。在当前全球经济纷纷吹响“改革号角”的同时,经济总体目前表现不错的中国能否顺势而上,加速国家、社会和市场体制的改革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未来的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安全质量。
①[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②Edward A.Kolodziej,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Ersel Aydinli and James.N.Rosenau,eds.,Globalization,Security,and the Nation State:Paradigms in Transiti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Terry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and Patrick M.Morgan,eds.,Security Studies Today,London:Polity,1999; Ronnie D.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③Richard K.Betts,"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Vol.50,No.1,1997,pp.7-33;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0,pp.211-239.
④[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英文版自序”,第1页。
⑤Edward A.Kolodziej,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318.
⑥David P.Barash,ed.,Approaches to Peace:A Reader in Peac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⑦David A.Baldwin,"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Vol.48,No.1,Spring 1995,pp.117-141.
⑧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ghton:Wheatsheaf,1983.
⑨Paul D.Williams,Secur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London:Routledge,2008,p.117.
⑩这方面的典型作品,请参见:Ken Booth,Theory of World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有关这一方面的经典论述,请参见Didier Bigo and R.B.J.Walker,"Political Soci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lennium,Vol.35,No.3,2007,pp.725-739;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London:UCL Press,1997; R.B.J.Walker,Inside/Outsid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2)Barry Buzan,Ole Wa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21.
(13)[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54页。
(14)同上书,第287页。
(15)[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33页。
(16)[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第37页。
(17)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
(18)Barry Buzan,Ole Waver,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p.27.
(19)Adrian Wooldridge,"The Visible Hand:The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 Capitalism Has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a Powerful New Form of State Capitalism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st,January 21,2012.
标签: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