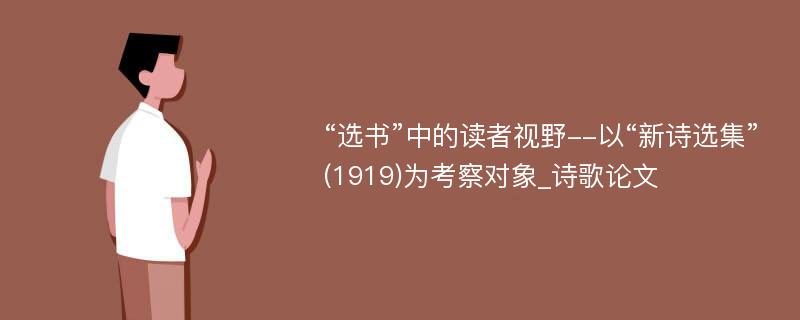
“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以《新诗年选》(1919年)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本论文,新诗论文,眼光论文,对象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诗的历史展开中,诗人写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紧张,无疑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困境,并一次又一次激起批评、辩难的波澜。事实上,这一困境也由来已久,从新诗的发生之日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就作为一种前提性的机制,暗中制约了新诗的历史。在讨论新诗与旧诗在接受方面的差别时,诗人吴兴华的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引述:
(古典诗歌)拥有着数目极广,而程度极齐的读者,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对于怎样解释一首诗的看法大致总是一样的。他们知道什么典故可以入诗,什么典故不可以。他们对于形式上的困难和利弊都是了如指掌的。总而言之,旧诗的读者与作者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他们互相了解,写诗的人不用时时想着别人懂不懂的问题。读诗的人,在另一方面,很容易设想自己是写诗的,而从诗中得到最大量的快感(注:吴兴华:《现在的新诗》,原载《诗论》,夏济安编(台北:文学杂志社,1959年);转载自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唐晓渡译,《学术思想评论》第十辑《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4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与古典诗歌相比,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在新诗的发生过程中却瓦解了。作为一种历史创生物,新诗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产品,所谓不用“陈言套语”,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
“阅读程式”是乔纳森·卡勒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作文学来阅读,在于读者拥有一种“文学能力”,而这种“能力”是落实在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之上的[1]。对于某种新兴的文学体式而言,既有的“阅读程式”往往失效,在读者中建立一种崭新的、有效的“阅读程式”,是其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晚清新小说的浪潮中,一位署名无名氏的论者,就在《读新小说法》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窃以为诸书或可无读法,小说不可无读法;小说或可无读法,新小说不可无读法。既已谓之新矣,不可不换新眼以阅之,不可不换新口以诵之,不可不换新脑筋以绣之,新灵魂以游之(注:原载1907年《新世界小说月报》第6、7期;引自王运熙主编,邬国平、黄霖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14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新小说不可无读法”,这一论断言简意赅,但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样,“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因此,新诗的“正统以立”,也就必然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即: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当然,这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现代“文学常识”的大规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与争论,新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学实践,都有所贡献。本文尝试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讨论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
自古以来,诗文的编撰、成集,一方面有积累、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暗中完成着价值的估定和经典的塑造,“孔子删诗”是这一传统最古老的象征。对于初创的新诗来说,这种自我拣选、自我经典化的努力从一开始便存在,仅在1920~1922年的两年之间,就出现了四种新诗选本: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1920年8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1922年6月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新诗三百首》,以及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年)。其中,《新诗集》不仅是第一部新诗选,其实也是新诗史上最早的出版品,在序言中,编者就这样写道:“我们还记得从前学做老诗的时候,什么《千家诗》、《唐诗三百首》……都要念熟,总能试作。”(注:《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集》,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后来的《新诗年选·弁言》也提到:“自从孔子删诗,为诗选之祖。”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将新诗选本置于这样的历史线索中,无非在暗示,新诗“选本”也会象古老的经典一样,奠定后来人们对“新诗”的想象。
当然,实际的历史功效并不一定与编者的期待吻合,不同的选本之间,也存在精粗、优劣之分。最早出现的《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似乎都力求完备,采用写实、写景、写情、写意的分类,意图全面展示新诗最初的实绩,譬如,由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又名:《新诗五百首》),选诗232首(并非500首),诗人68家,阿英曾言:“此集为初期新诗之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网罗靡遗”[2](P296)。然而,由于作品收集的庞杂,选家的目光反而不够鲜明,朱自清后来就说,这两个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3](P379)。相比之下,由“北社”策划的《新诗年选》,则是一个较为精当的选本,不同于单纯的抄录:一方面在数量上“瘦身”,只选诗90篇,诗人40家;另一方面,在诗作之外,还有编者撰写的评语和按语。阿英说:“中国新诗之有年选,迄今日为止,也可谓始于此,终于此。北社编辑此书,颇是慎重,逐人均有按语。”[2]对前两本诗选颇为轻视的朱自清,对此集也十分看重,认为它“像样多了”:“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3]不难看出,《年选》诗后的评语、按语,引起了阿英、朱自清二人共同的关注,这似乎是《年选》的价值所在。评语、按语,执行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按语的署名都为编者,主要是交待诗歌的编选、删改情况,起到一般性的说明作用;而评语则有具体的署名,四位评者分别是愚庵、溟泠、粟如和飞鸿,作用在于具体诗人、诗作的评价和解读。前者,可以说是编者身份的体现,后者则传达了编者“北社”成员的另一种身份认定。
《新诗年选》的编者,实际上是康白情以及应修人等一批年轻的新诗人,1922年5月2日,应修人在写给潘漠华、冯雪峰信中说:“白情信上说的《新诗年选》,第一期稿已将到上海,一切当予静之说,请勿外扬。”[4]知情人似乎只有湖畔诗人和他们的老师朱自清(注:应修人在5月11~13日的信中说:“年选第一期已到,是1919年的,所选不多,大半后续短评”,并请漠华说给朱先生。(楼适夷编:《修人集》,第21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如此隐秘,不仅体现了选诗者态度的审慎,对于身份的敏感恐怕也包含其中:诗人选诗难免会留下“戏台里叫好”的口实,署名“北社”,与这种顾虑或许也不无关联。据《新诗年选》后附录的《北社的旨趣》一文,所谓的“北社”发起于1920年,主要由喜欢鉴赏文艺的同志组成,成员包括教育家、学生、公司职员、记者等,其宗旨是一个读书的社团,并将读书的结果发表出来:“北社重在读书;而读书是为己的,不是为人的。有时候也把读书的结果,总括的发表点出来。”[5]换言之,四位评者同时又是四位“经验读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阅读”发表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年选》执行的功能,恰好体现在“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读法”的影响和塑造上。编者与读者身份的重叠,“选”与“读”的结合,应是《年选》的特色所在。选家的眼光,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选择上,按语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而体现读者旨趣的评语,则更突出地体现了新诗阅读的某种内在歧义。
《年选》中的评语一共有36条,四位评者各自的份额为愚庵19条、溟泠10条、粟如3条、飞鸿4条。据胡适的说法,愚庵就是康白情[6],从评语数量上看,他在其中所占的绝对主导作用,不言自明,其他三人大概是参与编选的湖畔社诗人。如果仔细分析,四位评者(读者)的声音在《年选》中交替起伏,虽然在相同中又有差异,构成一种微妙的“混响”效果,但某种评价的焦点还是相对集中的。
具体说来,36条评语大致指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是随意写下的阅读感受,或是印象式的风格把握,或是对诗的主题、背景作简要评述,在评价上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目的都在为读者提供“阅读”的门径:如飞鸿评李大钊的《山中落雨》:“此诗音节意境,融成一片,读者可于言外得其佳处。”[5](P64)如作简单归纳,这一类评语大约有14条。另一类侧重于“新诗”特殊品质的解说,推重具体、清新等新的美学可能。如溟泠评傅斯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这首诗的好处在给我们一种实感,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认为其创造力“更有前无古人之概”[5](P187)。评价虽然有点夸张,但显然是为了向读者解说新诗的“新异”所在,这一类评语有六七条左右。
上面两类评语,大都针对作品的本身,没有过多的展开环节,与之相比,第三类评语的思路更令人关注,即:在与古典诗歌或外来资源的比较中,寻求“新诗”的价值定位。许多评语都主动将古典诗词的美学成就,当作新诗评价的主要参照系,予同的《破坏天然的人》让粟如联想起李清照的词调[5](P20),溟泠认为傅斯年的《咱们一伙儿》与屈原的《九歌》异曲同工[5](P190)。这一点在愚庵(康白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19条评语中,除少数几条对诗歌主旨发表感想外,大部分都依照上述思路展开:评玄庐的《想》一诗,他说:“读明白《周南》的《芣苢》,就认得这首诗的好处了”[5](P29);称赞周作人《画家》“具体的描写”时,也作大幅度跳跃:“勿论唐人的好诗,宋人的好词,元人的好曲,日本人的好和歌俳句,西洋人的好自由行子,都尚这种具体的描写。”[5](P86)这种“读法”,目的十分明确,无非是要为“新诗”接受找到合法的参照,将新诗的追求放大成为普遍的价值。这是从美学效果上着眼的,另一种比较则试图发掘新诗中传统的延续,譬如沈尹默“大有和歌风,在中国似得力于唐人绝句”[5](P55),“俞平伯的诗旖旎缠绵,大概得力于词”[5](P109),“康白情的诗温柔敦厚,大概得力于《诗经》”[5](P154)。这些说法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屡屡引用,当作新诗中传统价值的明证。然而,相对于具体的结论,更值关注的是这些评语的功能,在传统的线索中的谈论新诗,在表达某种美学认识外,目的在于以传统为阅读参照,以便帮助读者辨识新诗的价值,换而言之,它指向的主要是诗歌的阅读。
如上文所述,既有阅读程式的失效,造成了新诗接受的某种困境,但《年选》评语所体现出的,则是另一种阅读的逻辑,即借用“传统”的权威,为新诗提供阅读上的参照,对新诗历史合法性的追求也包含在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新的“读法”。无论是“断裂”的鼓吹,还是对“延续”的强调,曾是新诗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其实从总体上看,对于一种反叛性的历史创造,上述两种话语,都是新诗在自身合法性和独立性寻求中,产生的不同的技术方案(注:这种逻辑是有普遍性的,20世纪文学史上的诸多运动(即种种“主义”),均是为了从整体上表现过去与未来的对抗关系而设置的技术纲领。(见斯班特:《现代主义是一个整体观》,袁可嘉主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这样一来,某种历史宿命也随之发生,即:无论是“断裂”还是“延续”,新诗的形象,必须是在传统文类规范的参照中,才能得到辨认,由此带来了矛盾,也折射于《年选》提供的“读法”中。
作为一个评诗的读者,普遍的阅读趣味自然是愚庵的标准,在自评时就说“其在艺术上传统的成分最多,所以最容易成风气”;但作为一个热衷“新诗”实验的诗人,他又不得不对公共习见以外的“尝试”,抱充分的同情和期待。在评价自己“浅淡不及”的胡适时,他说胡适的诗以说理胜,然而说理“不是诗的本色,因为诗元是尚情的。但中国诗人能说理的也忒少了”[5](P130)。“本色”的期待与写作的追求,在句中造成了前后的断裂。说到自己“深刻不及”的周作人时,矛盾语调也暗藏其中:“他的诗意,是非传统的;而其笔墨的谨严,却正不亚于杜甫韩愈。”[5](P80)一为普通读者的代表,一为观念激进的新诗人,两种角色交织一处,身份的歧义形成表达上的悖谬、盘曲,但评者自身的态度还是勉强地表达了出来,在承认“大抵传统的东西比非传统恶毒容易成风气”的同时,愚庵也强调“各发展其特性,无取趋时”的重要性,因为“若干年后,非传统的东西得胜也未可知”[5](P90)。比起另外三位评者,《年选》中愚庵的声音尤其暧昧、丰富,复杂性与其说来自传统/现代之间的对话,毋宁说是“读者”与“作者”两种身份,普遍的“阅读”与新锐的实验之间的碰撞。
这种矛盾状态,在许多新诗人身上都有显现。新诗作为历史的创生物,是对另一种美学可能的追寻,但既有的诗歌“期待”仍是其阅读的前提,这就形成了某种“标准”的错位。胡梦华曾对胡适等人整理旧文学的态度,提出过异议:“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诗词歌曲的价值,以为白话化的程度越高,这作品的价值越大,那就失去了评量艺术的正当的态度了。”(注:胡梦华:《整理旧文学与新文学运动》,《学灯》5卷2册10号。)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古典文学,自然有不正当之嫌,同样,用旧诗的标准前提去衡量新诗,也忽视了二者表意体系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错位”一直贯穿在新诗的历史评价中。
然而,正是在阅读、评价标准的缠绕中,新诗的成立,受到了两种冲动的约束:一是对既有的诗歌想象的冲击,在文类规范外追寻表意的可能;一是某种与传统诗艺竞技的抱负,即:它要在白话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就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基本歧义。这种歧义不仅抽象地存在于构想之中,它还会具体化为诗歌作者与读者间期待的矛盾:当诗人要求特殊的可能性,读者更欢迎熟悉的品质。在一般的论述中,某种妥协(或言融合)似乎是值得鼓励的倾向,有关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相互融合的诉求,也是新诗史上最具势力的一种话语。但写作自身的扩张,与阅读期待的矛盾,又在内部反复发生。这也就是《年选》中评诗者的处境。
作为一个参照,另外一些阅读实践,却体现出不同的逻辑,俞平伯对朱自清《毁灭》一诗的阅读,就是一个代表。在《读〈毁灭〉》一文中,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评价标准:“我们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现代的作家们能在前人已成之业以外,更跨出一步。”而“以这个论点去返观新诗坛,恐不免多少有些惭愧罢,我们所有的,所习见的无非是些古诗的遗脱译诗的变态”,当不起“新诗”这个名称。这种要求,显然已将“新诗”成立的合法性,放在了“新”的审美空间的开拓上。有意味的是,此文也不断将这首长诗《毁灭》与《离骚》、《七发》等古诗比较,但目的不在建立其间连续性的同一,而是说明不同和差异,认为“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7]。在俞平伯的“读法”里,“新诗”是不能由既有的诗歌规范来评判的,相反,他所关注的恰恰是“另标一帜”之处。朱湘在评价郭沫若时,更是将这种标准推进一步,说郭沫若的诗歌贡献“不仅限于新诗,就是旧诗与西诗里面也向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注:朱湘:《郭君沫若的诗》,《中书集》,第19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据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排印。)。这一判断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它却揭示了新诗史上另一种话语,即:无论“新诗”与传统诗歌或西方诗歌的资源间,有多少千丝万缕的影响、渗透关系,其根本的历史合法性以及阅读程式,还是要靠自己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