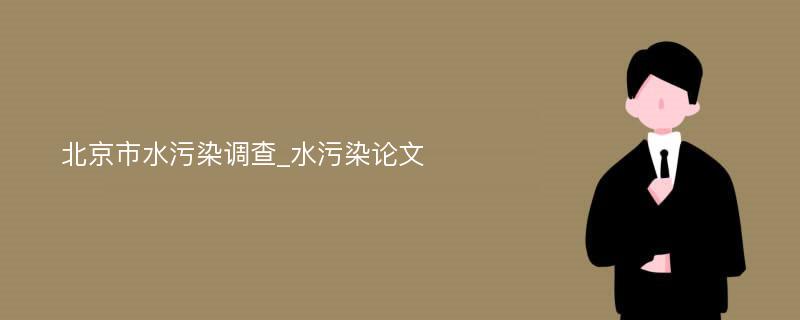
京城水污染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城论文,水污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28届奥运会即将在古城雅典拉开帷幕
在这种火热的奥运激情浸沉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北京这座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在北京已向国际奥委会作出的诸多承诺中,水环境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北京奥运行动规划》中写到,2008年北京污水处理率将达到90%。今年5月19日,在北京市水务局仪式上,首任局长新官上任一把火,就是承诺要用5年时间,实现城市河湖水质还清。
在这5年之限中,围绕河湖治理,北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赶不走的龙须沟
大量的资料数据显示,几十年来,上至中央下到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在改善水质的工作中,的确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北京老市民的口中,记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以前水没有这么清,河边也没有这么多花草”,这是不少人的感受。
记者路过北京城区一些河道和湖泊时,远看绿水荡漾,杨柳依依,确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给夏日的古都增添了几分清凉和诗意。“水岸家园”、“邻水人家”也成为房地产商最有诱惑力的宣传口号,但走近了会发现,很多河湖水体呈深绿色,有风吹来,会闻到一阵阵的腥味。
而在去年开盘的狮城百丽小区,原先邻近小区的凉水河,是宣传的一大亮点。可今天小区居民都在为这条河叫苦不迭,记者离河100米外就可闻见阵阵腥臭,临河的居民有些都不敢开窗。
亮马河是北京城区的一条重要河流,位于东直门外,地处繁华的商住区,下游为外国使馆驻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亮马河水质污染的讨论备受关注,记者也在那里展开了实地调查。据悉,北京市政府已将包括亮马河在内的北环水系改造列为今年的重点市政工程。
胡家园小区位于亮马河畔,曾被北京市命名为优秀管理社区。但由于亮马河水质下降,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居民反响很大。李先生在这个小区已经居住了近20年。他向记者介绍说,上世纪80年代,这里的河水还是很好的,夏天可以在河里游泳,还可以钓鱼。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污水和垃圾往河里倾倒的越来越多,河水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现在不用说游泳,连鱼几乎都没有了。在采访中,记者能够感受到小区居民对水质恶化的深恶痛绝。“这就是一条臭河”、“上面漂的都是大便”、“一直这样,很长时间了”……没有人向上反映吗?记者问。居民们苦笑道,反映好多次了,政府也下了不少工夫,好了没多久,又成这样了。言语间透出几分无奈。
记者观察到,小区旁边河道中的水呈现墨绿色,已经浑浊不清,不时漂来一些粘稠状的物质。居民们说,每到夏天炎热的时候,水中的杂物腐烂变质,臭气熏天,根本不敢开窗户。李先生告诉记者,亮马河的水源地在积水潭。那里的水质现在仍然很好,但是水流到这里就恶化了。李先生分析说,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游沿岸的一些居民区,特别是一些旧平房密集的地方,将生活污水,甚至粪便排到河里造成的。但是似乎并没有人去管。
按照李先生的指引,沿河而上,没过多久记者便看到,大片的生活垃圾已经将河面几乎全部覆盖,水体呈黑色。与此一比,胡家园小区的河水算是好很多了。密集的平房将这里的河道夹在中间,不留意有时很难发现。记者走进河边的一家小吃店,以食客的身份与老板攀谈起来。记者问到,店里是否将污水倒入后面的河道里?老板很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们都有自来水池,污水倒进池子里,而且我们离河还有很远,中间有铁栏杆,不会过去的。记者又问,知道下水管道通到哪里吗?老板表示不知道,为了显示清白,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们刚来时,水就这么脏了。记者看到,像这样的小吃店附近还有很多。
记者再向上游走去,几分钟后,又来到一段河道。这里呈现的景象令记者更加震惊。这里的水质比刚才的河段更加恶化。水体已呈浅茶色,大块的黑色胶状物体漂浮在水面上,令人作呕。河床已经被大量沉淀的秽物托起,依稀可见。路边的居民都对此熟视无睹,好像已经习惯于这种状态。水道在这里进入暗河;不见了踪迹。但记者看到,从暗河口中汩汩流出的水,仍然是夹带着大量杂物的脏水。出口处设有一条很粗的橡胶管,看来是河道管理部门用来拦截杂物的。但周围的居民反映,很少见有人来清理。这条暗河通向哪里?有多深?记者的这些疑问从居民那里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
暗河入口街的对面是一个名为万国城的高档公寓区。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先生告诉记者,暗河就从公寓区的围墙根通过。当初公寓区的设计中有景观河道,开发商想将暗河挖开进行改造。但当得知污染的严重程度后,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暗河上面自造了一条景观河道,这才完成了设计。当记者问及,公寓区的污水是否排入河道中。王先生急忙说,这不可能。他说,虽然他们不是开发商,但当初施工时他在场,公寓区每栋楼下面都有一个标准的污水池,这些池子都和市政的污水管网连接,因此不可能排入河道,并一再表示,河道的脏水绝对和他们没有关系。最后,王先生还向记者透露,这里是朝阳区和东城区的交界处,因此很多事情不好处理。
而在小月河(元大都的护城河)附近采访时一位老人对记者说:“按理说河道两边的污水口已经不让排污了,但有时还是会流出水来。这附近有不少人到这里来捞鱼虫。”而“干净的水会有鱼虫吗”?
功能转换之痛
北京市水务局长焦志忠称,北京城区的河湖水质2/3受到了污染。在北京市2008年奥运规划中,城市河湖水质要达到四类水体的标准,但截至2003年,北京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能达到较高水质标准的河湖非常有限,五类、甚至超五类水体仍然占较大比重。
记者在北京市水务局采访时,听到几个工作人员在低声讨论,某某河段又出现了水华。后经记者查证得知,水华被称为“生态癌”,其危害是使水体严重缺氧,造成鱼类等水生生物窒息死亡,并产生多种有毒气体,形成腥臭,污染环境。2000年7月,北京市曾大面积爆发水华,城区所有景观水系无一幸免。水质状况欠佳,富营养化加重,是导致水华出现的罪魁祸首。而北京市水文站和河道管理处都表示只能提供水务局统一的通报,至于具体每条河道的监测情况不便披露。北京市环保局下属的环保检测中心则表示,北京市河道污染的监测情况属于保密内容。
正如国家水利部门出版的纪念册《北京水利50年》中所说到的,“水环境的治理任重而道远”。
“之所以现在河湖治理有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河道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务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以前河道的主要功能是排污和泄洪。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环境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因此河道又多了景观的功能。但是当初的设计已经定型,污水管都连着河道,河道又连着湖泊,因此改造起来难度也就大了。”
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院水污染所的武江津所长介绍,现在北京城区河湖的污染源中,工业污水已经几乎没有了,主要是生活污水、地表径流和降尘。而目前市政污水管网普及率尚不到50%,所以,有些生活污水排入河道也就在所难免了。
针对河道功能转换的现实,北京市政府曾提出,2010年市区污水管网普及率达到90%,2010年以后普及率达到95%以上;2010年以前完成12个污水处理厂的污水管网系统,2010年以后,再完成3个管网;2010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0%,污水回用率达到每年6.45亿立方米。记者采访中还获悉,北京市正在提高水利用率,提倡办公、居住区建立污水处理设备。规划部门在对新建房屋的审批中,也加入了配备污水处理系统的要求。
但是,河道功能的转换,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历史包袱比较沉重。例如暗河,就有一些市民向记者反映,“很脏,但都和河道、湖泊连着”。记者向水务局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求证此事,那位官员婉转地承认了这种说法,同时也很无奈地辩解,“很多暗河上面都有建筑,治理起来成本太高了”。根据资料显示,北京有暗渠41.5公里。
一龙就能管住水么
5月19日,在原水利局的基础上北京市水务局成立,媒体称之为“‘多龙管水’变成‘一龙管水’”。水务局负责新闻发言的官员向记者介绍,2001年北京市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过一次改革,大体的方案是启来水供应归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归市政,地下水归国土资源局,其它的归水利局。在此以前管水的部门更多。即使这样,在遇到问题时,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颇费周折。具体到污水排放,居民向水利局反映,水利局也只能是暂时截住污水,不能进行根本的处理,等待和市政部门协调,才能再展开进一步的工作,这样就使工作效率打了折扣,老百姓意见就很大。现在水务局成立,除地热,也就是温泉仍归国土资源局管理外,北京市其它所有涉水事务都由水务局集中管理,包括水质改善在内的各项工作可以统一规划,协调进行。“这样好像自己家里人办事,事就好办多了”,这位官员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目前,水务局的设立被当作重大体制性创新似乎受到媒体的较高认可。有文章称,“北京市水务局的成立,将在确保北京城乡水安全,治理水污染、建设生态水环境和节水型社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与这种高调气氛相反,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改善水质的法治环境,公众的看法却并不乐观。记者在中国某水网的一项调查中看到,认为水务局成立将全面解决城市水管理的核心问题的占18.4%;认为对水资源紧张,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适用,但不易推广的占13.1%;认为造成新的政企不分或政府干涉,不利于水业市场化的占18.4%;而认为是部门间权力争夺,管理体制没有实质改变的占到了50%。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王灿发教授分析,导致法律在治理水污染问题中乏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部分条款本身制定得过于严格,超出了实际的国情,使之无法在实际中有效和公正地加以运用。如《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超标要交超标排污费,达标要交达标污染费。但没有底线,只要排水都要交费,有时排的水比河水还干净,也要交费。学术界称之为“立法本身缺乏经济性的分析”;
二是由于我国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法律由中央来制定,由地方去实施,而地方又都有发展经济的内在冲动,其中便会产生冲突;
三是环境执法者在自身缺乏监督的情况下执法不力,而这种执法不力又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部分环保官员与排污人之间存在一些私下交易,滋生腐败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
而更可怕的是形成一种组织性的默契,比如有一些专家将收取排污处罚费形象地比喻成“养鱼吃鱼”,违法排污者存在,才能收取处罚费。目前我国实行的财政体制潜规则中,执法部门收取处罚费的高低与财政返还率相挂钩,因此假如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一龙治水反而会加剧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的趋势,而将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效率极低。
为何偏爱行政手段
“缺水,是根本原因”,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北京有限的水资源首先要保证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然后才能用于水环境的改善。这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王西琴副教授介绍,按照国际标准,须要保证60%的生态用水,才能有效维持河湖的自净能力,但目前北京地区最多只能达到不足20%,远远低于国际标准。
俗语说,流水不腐。如果河湖能够有充沛的流量,即使水中有一些污染物,也可以被冲刷掉。但北京的情况是,河湖的流速由各个闸口控制,据记者观察,很多河道水流很缓慢,甚至没有流动。“我们也想让水流起来,但是哪有那么多水,开闸放水是要市里面同意的,我们都无权决定。”水务局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透露。
南水北调可能是解决北京资源性缺水的根本出路。有关资料显示,到2008年,南水北调工程河南至北京段竣工,北京到时可以用上河南的黄河水,2010年全线贯通,北京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可以基本解决。到时,北京城市河湖“流起来”的愿望有望实现。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段距离。
最近一段时间,在跨区域水资源使用中,“水权”一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北京目前最主要的水资源规划文件《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规划项目》中,也已经提到了上下游共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就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水务局负责新闻发言的官员,但他的回答出乎记者的意料。
“水权分配是一个很好的理论设计但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单说水权如何划分,就难以有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现北京是从河北、河南、山西调水,我们是首都,需要水,人家说是贫困地区,更需要水,不好分。而且,北京处于下游,要是划分水权,就要走市场化,北京要用大笔的资金反哺上游,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对水权北京是不太愿意提的,没有办法,目前只有靠水利部来协调。”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协调”的具体含义,这位官员沉默了一会,说:“就是行政手段吧。”
看来如果把首都水污染治理当成一项形象工程,那么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把目标订在让北京在奥运期间确保河湖水质还清,这并不困难。可以用政治化的全民动员短期内中止排污,甚至可以往河里倒漂白粉,当然也可以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方式大量从外地调水进京,来确保首都用水的充沛。但要彻底改善北京的水环境则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程,相信绝非五年之功那么简单,而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