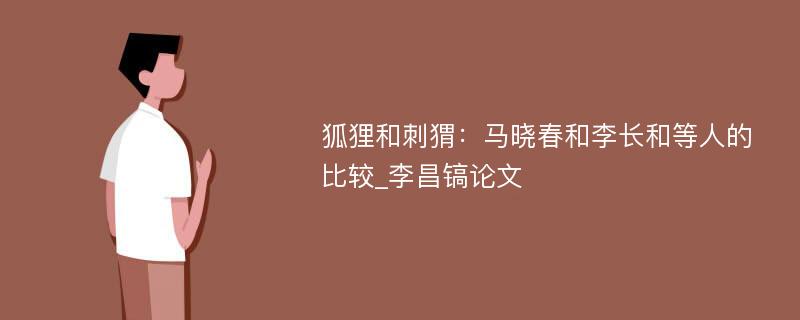
狐狸和刺猬——马晓春和李昌镐之比较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刺猬论文,狐狸论文,及其他论文,马晓春论文,李昌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狐狸能耍十八般武艺,而刺猬精通一门绝技
一位学者曾将历史上的作家和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狐狸型的,一类是刺猬型的。“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前者的特点是:追求许多不同的、彼此无关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其思维是发散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性格是狡诈的;后者的特点则是:有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目标,所有的精力、心思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有着一种不折不挠的、彻底的、近乎顽固的执著和韧性。简言之,狐狸能耍十八般武艺,而刺猬精通一门绝技。
如果我们不作绝对化的理解,这分类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围棋界。活跃在当今棋坛的围棋高手比较典型地属于狐狸型的有:马晓春、武宫正树、大竹英雄、藤泽秀行等,比较典型地属于刺猬型的棋手有:李昌镐、小林光一、曹薰铉、依田纪基、钱宇平等。韩国棋手大都属于后一类,中国棋手则基本上介于两者之间。
行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马晓春颇有“狐仙”气
马晓春的棋以“妖”著称,大竹英雄说马很狡猾,杨晖在讲棋时也称赞马“灵得不得了”。马晓春自己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新编围棋三十六计》。当他在一次中日名人赛中把这本书送给小林光一时,小林光一马上就意识到马真正想送给他的不是书,而是“输”,并称这是马的第三十七计。
马晓春长得并不英俊,但绝对有特点。他并不怎么喜欢说话,也很少讲棋,但只要一开口,那种智慧、灵气、骄傲就会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地流露出来。例如,在东洋证券杯半决赛对曹薰铉的第三局棋中,曹下出了几步极为连贯而又威力无比的好棋,只是后来未能坚持到底才功亏一篑。有记者问马晓春的感想,马说:“我搞不懂他干嘛那么凶狠?不过关键时刻我比他冷静,所以我胜利了。”几年前,在讲解俞斌和石田芳夫的一盘棋时,马说:“石田芳夫有电子计算机的美誉,而俞斌正好是玩计算机的能手。”
马晓春的长相和说话都有些飘,飘得捉摸不住,令人跟不上“趟”,而反映在他的棋上则是轻灵、飘逸、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忽真忽假、忽实忽虚、忽明忽暗、忽逃忽弃、忽攻忽守,真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狐狸本色尽显。刘小光与他下棋时觉得找不到攻击点,曹薰铉与他下棋时觉得使不上劲。轻灵多变,好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是马晓春棋的特点。他的棋没有固定的着法,没有规律可循,也很难学得来。他绝不属于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棋手,相反倒是常常以万变应不变,即使对同样的对手、对同样的下法,他也总是积极求变,冷着、新着、奇着迭出,使对手的如意算盘难以得逞。
年纪轻轻却稳如泰山的李昌镐俨然一位少年姜太公,有着刺猬的执著和韧性
李昌镐呢?相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看不出有“外星人”的任何迹象。他喜怒不形于色,不像别的棋手例如他的老师曹薰铉那样,可以从面部表情判断出一局棋的好坏、局势的优劣。李昌镐自始至终是清一色的冷漠。把他比作少年姜太公是恰如其分的。有人会说:这么小的年龄配上这么老成的心态,生命是不是太沉重?的确,李昌镐似乎未曾经历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很早的时候,父亲就把他交给了曹薰铉,从此,他的命运便与围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并且,他的生活中只有棋,他不仅是以下棋为生,而且是在下棋中生活,棋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时,在局外人看来就不免有些单调甚至为之悲哀,甚至投以莫名其妙的同情。然而,李昌镐根本不需要这种同情。下棋对于他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之所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很适合他,他在下棋中能感受到生活的全部乐趣。
马晓春的性格和棋风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能经常性地赢一个对手,也能经常性地输给一个对手
马晓春和李昌镐都是天才型棋手,尽管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不同。他们都早慧:马晓春在19岁便成为九段棋手,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九段,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李昌镐则在17岁时便夺得了世界职业围棋赛冠军,他当时击败了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林海峰,这个纪录恐怕至少要保持到21世纪。在人们习惯性的看法中,似乎更倾向于把富于灵气、智慧写在脸上的马晓春视作天才,而木讷无声的李昌镐要不是他那么年轻,一定会作为“勤能补拙”的典型了。
藤泽秀行在多年以前就曾预言:马晓春注定会超过聂卫平。但是,马晓春在国际大赛中曾一次次无所建树,一而再、再而三地败在小林光一、徐奉洙甚至依田纪基的手下,那时真让人怀疑把希望寄托在马晓春身上是否是个错误?
马晓春的确是缺乏那么一股冲劲,同时其才气也基本上算不上是纵览全局、心境高远、想象力自由挥洒的大智慧,这就直接造成了他的对局很少那种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给人以兴奋的一击的场面。在这一点上,他不如同样属于狐狸型棋手的武宫正树。武宫常常让人感到天宽地阔、胸襟坦荡、如痴如醉。马晓春的棋虽也灵活多变,但基本上都在小处作文章,因此其结果总是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不出人们所料。每盘棋的胜负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对于比他强的棋手,他准输;对于比他弱的棋手,他准赢。套用足球界的一句时髦话,可以说马晓春是赢了该赢的比赛,也输了该输的比赛。第三届应氏杯四分之一决赛,马出人意料地完败给了赵治勋九段,当问及原因时,马的回答是执黑贴八目负担太重。看来他是一开始就做好了输的准备。在马看来,也许这样的棋本来就是不该赢的,也用不着去放手一搏。马晓春的性格和棋风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能经常性地输给一个对手,也能经常性地赢一个对手。他的棋一旦突破某种限制,便会把这种势头稳定地保持下去。对聂卫平是如此,对小林光一更是如此。
李昌镐像个神秘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企图以各种手段征服他的对手们。但他的平淡和冷静,淹没了围棋的机智、奇想、起伏和创造性
李昌镐最早给世界棋坛造成轰动效应的时间是1991年的第三届富士通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他作为非种子选手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把前两届富士通盟主、正如日中天的武宫正树淘汰出局。那年他才16岁。但那时李昌镐毕竟还显稚嫩,即使是在次年惊险地以3比2击败林海峰夺得东洋证券杯赛冠军后,其布局上的缺点仍是显而易见。
李昌镐在与马晓春的第一盘对局中,被马痛快淋漓地击败,赛后,马晓春不无得意地以长者的口吻评论道:李昌镐果然厉害。如果说马晓春当年的评价还稍带戏谑和自得的话,那么现在他声言李昌镐是其最强对手则是非常认真和发自内心的了。马晓春一定从李昌镐看似笨拙平淡实则意味深长的着法中感受到了无比强大的力量。的确,李昌镐不讲求华丽,也不追求棋形的圆满,他的棋太平淡,淡得没有什么特色可言。他属于那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棋手。平淡和冷静是李昌镐的力量,正是这种处惊不乱、沉着无比的冷静,无声地瓦解着对手的信心和创造力。李昌镐像个神秘的黑洞,无情地吞噬着企图以各种手段征服他的对手们,所有的奇技淫巧在其步步为营、稳健无比的着法面前都变得乱了方寸而失去威力。诚然,李昌镐的棋并非无可挑剔,他也不是什么常胜将军,但是他总能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耐心地、一点一滴地将局势最终翻盘也是一个事实。他的内功已到了使对手在领先的情况下比他更紧张更没信心的地步了。
李昌镐是罕见的奇才,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将在棋坛占据显赫的位置。但我总是有点担心,毕竟李昌镐太顺利了,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磨砺,而且他也不像马晓春可以在优美的钢琴曲中,或者如武宫正树那样在忘情高歌中得到补偿和陶冶。我的另一担心是不愿看到李昌镐长期独霸棋坛的局面。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基于实惠的世界,务实之风几乎吹遍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围棋也未能幸免。围棋说到底只是一种游戏,游戏当然是要追求胜负的,不计胜负的游戏一定是索然寡味的。但胜负并不是游戏的唯一追求,在游戏中表现出的那种机智、奇想、起伏和创造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
然而,现代围棋中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已经越来越少了。曾经风靡一时,以其宏伟的气魄和浪漫的构想充分展现了围棋之美的武宫正树及其“宇宙流”,在更加务实和本分的小林光一和李昌镐面前黯然失色了。浪漫总是脆弱的,诚如赏心悦目、富有激情的荷兰足球每每在严肃理性的德国“装甲车”面前一筹莫展一样。
多年前,藤泽秀行先生说过:“50年后我们这些人的棋都将被后人遗忘,唯有武宫正树是不朽的。”这既是对武宫的激赏,更是对棋界弥漫的因循守旧、不求革新之风的忧虑和批判。但类似赞语大概是不会给李昌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