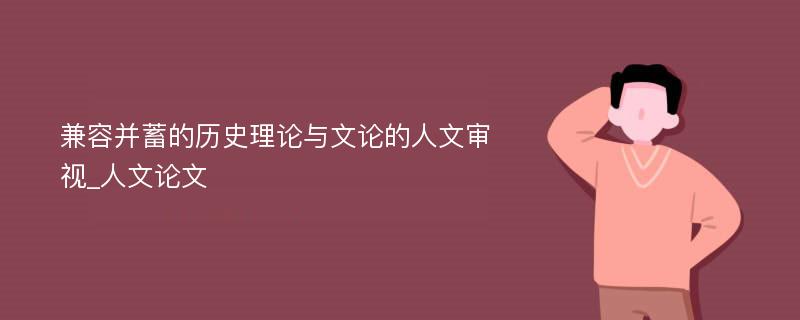
兼容史论与文论的人文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文论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1906-1999),俄罗斯文学史家、文艺学家、版本学家、俄罗斯古文化学家,是苏联科学院(即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著名院士之一。他的著作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文论界,主要是一些关于世界文学史中现实主义问题的论述。他的《古俄罗斯文学诗学》(1967年初版)五十多年来四次修订再版,是俄语文学研究的必读学术经典。20世纪八十年代,他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大家乔·弗里德连杰尔文艺思想的评价也在文论界引起过广泛注意。作为一个人文研究大家,利哈乔夫学术视野极为宽广,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巴赫金对话主义、西方结构主义都有所涉猎。尽管利哈乔夫并非文论家,但他对人文伦理诸多问题,比如知识分子特性问题、“文化性”概念、形式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守护问题等,都有深度的思考。这就是坚守俄罗斯文学的优秀历史传统,面对现代文论方法,守护为人生文学的使命,升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性,提倡在人与自然等量齐观的语境中审视文化问题。这种史论文论兼容的人文伦理审视方法论,值得重视与研究。 知识分子特性与人文伦理 在俄罗斯近代人文思想贡献中,“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т)概念的提出是比较显著的。俄罗斯文化史界公认,库尔勃斯基公爵是第一个知识分子,而作家拉吉舍夫则是第一个贵族革命知识分子。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一次从贵族知识分子的角度,审视了沙俄农奴制对俄罗斯社会正义的戕害,表达了对广大受压迫农奴的同情,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良心。在他的感召下,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及高尔基等续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艰辛而辉煌的华章。 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人文著作中,“知识分子”这个术语与称谓已经广泛使用,但时至20世纪末,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的人格才能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谓,在人文界观点不尽一致。利哈乔夫院士作为学界的名宿与泰斗,对俄罗斯人文界的这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极为关注,希望从其研究领域和人文及人生积累出发,对此问题做出更加严谨而严肃的回答。利哈乔夫在“知识分子特性”和“论俄罗斯知识分子”(或译“论俄罗斯知识界”)等随笔文章中,专门探究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伦理问题,指出知识分子“这首先是俄罗斯的概念”(《解读俄罗斯》468)。他回忆道:“我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看惯了太多令人惊奇的现象,因而能够谈论俄罗斯知识分子,无须对它提供准确的定义,而仅仅沉思它最优秀的代表。在我看来,可以划分知识分子的种类。在某些外国语言和词典中‘知识分子’一词通常不是按本身的意义翻译,而是与形容词‘俄罗斯’一起翻译”(《解读俄罗斯》468)。由此可以看出,利哈乔夫对待人文理论问题秉持一贯的专业习惯特点。他从具体的文史过程看理论问题,从具体地理文化空间来界说“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内涵,他知晓知识分子概念的人文缘起要与具体的民族历史进程相关联。 在此基础上,利哈乔夫进而阐释了“知识分子特性”(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сть)概念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专业人群的称谓。“有关知识分子特性道德基础的问题是如此重要,①以至于我想再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说,学者并不总是知识分子(当然是高级意义上的)。当他们过于封闭于自己的专业,忘记了自己是谁并且怎样利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知识分子”(《解读俄罗斯》71)。所以,在利哈乔夫的心目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与人文伦理紧密相关的。“知识分子特性不仅在于知识里,而且在于理解他人的能力之中,它表现在千百件琐碎的事情中:善于尊重地与人争论,在用餐时举止文明,善于默默地帮助他人(正是默默地),爱护大自然,保持自身环境卫生,不以粗话和恶劣思想污染环境”(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2)。纵观利哈乔夫对知识分子特性的细致入微的理解与详说,很显然,他重视的应该是对称得上知识分子这类人的人文伦理的评价标准问题。而对于从19世纪走过来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它更是与有知识有教养悲天悯人的良心连在一起的。“人应该做一个有知识分子特性的人”(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1),利哈乔夫如是说。他把“知识分子特性”理解为一种人应该具备的理想人文伦理状态。 利哈乔夫特别区分“教养性”和“知识分子特性”两者的概念,批驳这样一种偏见:“许多人认为,一个读书很多,获得良好教育(甚至主要是人文教育),见识很广,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就是知识分子”(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1)。对此,他不以为然:“不能把教养性与知识分子特性混淆起来。教养性依赖旧知识生存,而知识分子特性创造新事物并且把旧事物作为新事物加以理解”(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1)。利哈乔夫把“知识分子特性”理解为一种“善待世界和人们的能力”,一种对世界和人们忍耐的态度。显而易见,利哈乔夫把知识分子与有专业知识的“知道”分子做了严格的区别。有知识并不意味着有人文情怀。他认为,对他者的尊重,甚至忍耐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素质。“礼貌和善良不仅使人变得生理上健康,而且也美丽”(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3)。由此不难看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契诃夫这些作家的人本主义理想观念对利哈乔夫人文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 知识分子特性与精神自由的关系是这位学者着力关注的研究重点。“知识分子特性的基本原则就是智性自由。这是其自由的舵手,他关心自由如何不会变成肆意妄为,而在迷惘的生活状况中,特别是在现代生活中给人指出一条真正的道路”(Лихачев,Избранное 64)。作为接受苏联文化环境熏陶的学者,利哈乔夫关于“自由不是肆意妄为”这种人文理念,十分接近恩格斯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王国认识的观念。 利哈乔夫真诚地追问:“什么是人的智性、文化性?是知识、博学、知识渊博吗?不是!将人从其所有的知识中解脱出来吧,让他失去记忆吧,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情形下还保留了理解其他文化的人们,理解艺术作品广阔的和多种多样的范围、理解他人的广阔范围的能力,如果他还保留‘理性的社会性’的技能,保留其欣赏智力生活的能力,那么这将是一个智性的和有教养的人”(《解读俄罗斯》320)。说到底,在利哈乔夫的人文词典中,“知识分子特性”的核心是人的真善美与人文智力的完美结合。 现代以来,中东欧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新文论思想的策源地,特别是俄罗斯在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路径上成就斐然。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新观念的创立与方法的探索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众所周知,雅克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开启了文学本质特征的文论核心追问。半个多世纪后,文学界又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文化问题核心追问,这就是利哈乔夫提出的“文化性”问题。在他看来,文化性不仅属于人类,而且也属于大自然。这同样是一个独特的有关人文伦理的核心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利哈乔夫的这个概念是从对大自然生态的观察发现中提出来的,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范畴而扩展至天人合一的人文生态理性。 利哈乔夫的人文理念不仅是在书房、研究室及教研室里提出来的,也是在对周围人文与自然环境的考察中摸索而成。“文化性”概念的某些重要内涵的生成,正是他长期在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郊外长期观察植物生长规律的结果。在“俄罗斯人的大自然”一文中,利哈乔夫指出:“大自然有自己的文化,混乱不是正常的大自然的状态”,“大自然有自己的‘社会性’。它的‘社会性’体现在它可以与人一起生存,与人为邻,如果人自身也成了社会的和有教养的,保护它,不给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不把森林砍光,不使河流干涸……”(《解读俄罗斯》381)他得出结论,大自然的“文化性”就是生物总体的社会性。这种人文观念表明,他所理解的“文化性”是一种关联人生、社会与自然的现代大文化概念,也是期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伴共生的一种大人文伦理秩序。利哈乔夫的这些人文理念其实与东方的“天人合一”的人文生态理念已经极其相似了。东西方人文伦理如此近似相通,真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悠同”(钱钟书语)。 现实的艺术与现实主义艺术 俄罗斯文学界素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重,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种深广的创作方法的传统印记也影响到学界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都贯穿一条现实主义的红线。现实主义文化传统对利哈乔夫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是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几乎就是传统优秀文学的代名词。出于专业的习惯,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研究是与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1957年,利哈乔夫在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刊物《文学问题》上发表了“俄罗斯现实主义的起源”②。这是他与某些把现实主义僵化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论战的学术论文。他肯定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但不赞成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定于一尊的那种绝对膜拜的做法。他从文学史考据角度澄清了许多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当时区分了“现实的艺术”与“现实主义的艺术”,力求避免把文学史上复杂多样的文学都定义为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产物。他指出:“在11世纪至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里,描写现实的艺术方法绝不是现实主义的。作为描写现实的特殊艺术方法的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至19世纪才告确立:但是,关于它的历史渊源问题,如果不征引俄罗斯文学自其产生以来的全部材料,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利哈乔夫,“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0)。利哈乔夫注重文学史实的阐释,鲜明地体现俄罗斯学者向来敬重和经常坚持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彰显了他运用实证主义学术研究方法论有利的一面。文论的问题解决也离不开文学史的史实的支持,不可能凭空虚构问题,更不能虚构结论。 利哈乔夫具体指出:“在11世纪至13世纪,人的描写完全服从于这种对世界的态度”(“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3)。现实主义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伊戈尔远征记》、《拔都侵袭里亚桑的故事》、《俄罗斯国土沦亡记》、《达尼尔·扎托契尼克的呼吁》以及其他作品,明显地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对扩大与加深对现实的艺术认识的巨大意义”(利哈乔夫,“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6)。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大量地出现心理描写,而在他的考证中,俄罗斯古代文学里,即西欧中世纪时期的文学中,极少有心理感受的描写,也没有主人公与“环境的冲突”,“不描写心理感受是与这种无意识的‘和谐’密切有关的”(利哈乔夫,“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4)。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他的现实主义问题研究当然也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影响。在分析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缺少人物与环境冲突的现象时,他正确揭示了造成这种描写的原因:“我们看到的是唯一的备极宏伟的文体。无可怀疑的是,这种与现实性相距十万八千里的描写现实的艺术方法,是年青的封建主阶级为要加强封建制度、巩固人们意识中官阶制度的合法性与封建关系的复杂等级的要求所产生的”(“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4)。他认为,古罗斯传道文学缺少心理描写,“并不由于不了解它,而是因为这不是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文学任务所要求的”(“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54)。利哈乔夫就这样揭示了俄罗斯古代文学现实艺术的特点及其成因。他承认,在古代俄罗斯已经有关注现实的艺术,但却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艺术,现实主义艺术形成也非一日之功。他认为17世纪是现实主义艺术开始形成一个重要节点:“在整个17世纪里,艺术认识的发现特别迅速地发生,接踵而来的是新的描写方法的积累。新时代的文学诞生了,现实主义的个别因素迅速地积累起来,这些因素起初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文学各个流派占有自己的位置(在古典主义、感伤主义与浪漫主义里),而最后,它们成为现实主义这个文学流派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161)。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文学界某些人企图“清算”现实主义文学,而利哈乔夫对此却保持了一个正直学者应有的清醒。他以古俄罗斯文学的历史特点证明了现实主义传统自古有之。从俄罗斯文学诞生之初就生长在现实主义创作的丰腴土壤上,很早就确立了宏大的民族史诗深厚传统。众所周知,古罗斯的《往年纪事》(编年史)几乎完全是写实作品。俄罗斯19世纪和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如此发达,是因为现实主义文艺观对俄罗斯文学来说并不是舶来品。他认为,19世纪中期和下半叶,历史科学在俄罗斯的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吻合并非偶然。现实主义与历史感悟性的出现紧密相连,与对世界的变化性意识,自然而然也与对审美原则的意识紧密相连。同时,现实主义有助于理解俄罗斯古代文学。利哈乔夫还把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相提并重,认为两者在艺术内部是相通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本性是艺术的永恒本质。在任何重大的艺术流派中,艺术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面都获得了发展。艺术中所有伟大流派不是重新创造一切,而是发展属于艺术本身个别的或者许多的特点。而这首先就涉及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开始于19世纪的流派,但是,现实主义是艺术固有的一个永恒的特点”(《解读俄罗斯》278)。利哈乔夫的上述论述意在表明,现实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及后来的苏联文艺界占统治地位,是民族文学合乎逻辑的结果;甚至在西欧现实主义衰落的20世纪初,俄罗斯现实主义潮流仍在汹涌奔腾。作者热诚守护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实际上就是守护本民族对世界文艺珍贵的贡献。 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与批评形式主义 现代俄罗斯人文界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思想资源集散地。1921年雅克布森在《现代俄罗斯诗歌》提出了“文学性”的文论核心追问,即“关于文学的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把文学作品变成文学的那个东西”(Лихачев,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мь 124)。在雅克布森确认文艺科学的主攻方向为“文学性”后,形式论宗什克洛夫斯基又提出了“陌生化”或“奇异化”法则。形式主义者认定“文学性”的要义就是文学作品语言结构“陌生化”或“奇异化”,即在阅读中加深感知难度的方法就是文学创作的宗旨。这种文论片面深刻虽然引起了学界一时瞩目,但是,在长于文学史研究的专家看来,“文学性”和“陌生化”的这个定义回答不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复杂现象。利哈乔夫院士尖锐地指出,“陌生化”概念具有构词学的明显学术缺陷。他批评道,“这个术语很不成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词汇中产生的;凭听觉这个术语易与‘отстраннение’一词混淆,甚至即便是正确听到后,也不能立即明白‘陌生化’,而不是‘国家’(可能,更加正确一点写这个术语是通过两个‘н’)”(《解读俄罗斯》312)。在利哈乔夫看来,术语的清晰是避免逻辑混乱的前提之一,而形式文论者却一心标新立异,缺少严谨的构词学的正确理念。利哈乔夫还注意到,形式学派的那一套所谓文论创新只不过是对现代文学思潮,特别是对未来主义文学特点的总结,不过,这些看似新颖的文论对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很不适用。他指出,对中世纪读者而言,主要的审美享受是在“陌生的”现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他在“关于文学研究的思考”中曾经以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为论据,证明了体裁和手法的“世俗化”(即“熟悉化”)创作法则的运用在当时艺术实践中占主导地位(《解读俄罗斯》313)。典型例证是,古代俄罗斯艺术就是“艺术装饰”的现实艺术。“现实艺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俄罗斯世俗大众熟悉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他还注意到,无论是中世纪文学,还有近代文学,都存在着另一个典型现象,这就是俄罗斯作家固有的“形式的羞愧性”,即作者们为了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力求摆脱“过于成型的纯文学的形式”,他们在写作时大多用口语或公文语言,而不用文学语言写作(《解读俄罗斯》313)。利哈乔夫反问到:“而近代艺术总是追求将平常的‘陌生化’吗?如果这是‘陌生化’的话,那么,是从什么观点呢?”(《解读俄罗斯》313)显然,与学术视野相对狭隘的形而上学偏激的形式文论者不同,俄罗斯文学史家是从更加“长远的时间”(巴赫金语)来看待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的。不仅古代俄罗斯和中世纪文学缺少所谓的“陌生化”,近代现实主义的文艺大繁荣也证明“陌生化”写作并不是作家们趋之若鹜的审美取向。的确,普希金的创作也可以作证。诗人常常采用民众熟悉的题材、体裁和语言进行写作。他还经常鼓励果戈理等后辈作家到集贸市场上去学习俄语。他的现实题材和历史创作“驿站长”、《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对俄罗斯人熟悉的生活现象的聚焦和浓缩,其表达手法绝无丝毫奇异陌生可言。这毫不奇怪,普希金语言的第一导师正是描绘民族传统生活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而不是以所谓“陌生化”著称的“纯文学”。当然,即使在传统文学中出现了“陌生化”的转型,也是从熟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中派生而来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典型的著名定义,典型即所谓“熟悉的陌生人”。显而易见,别林斯基的这个典型定义的逻辑重心并不在陌生化上,而是在“熟悉化”上。其实,从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模仿说”来看,人类对艺术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从“熟悉化”起步的。欧洲文论中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复制说”都是从“熟悉化”的文学现象着眼的。因此,利哈乔夫依据俄罗斯自古至近代文学创作的文学经验与史实对形式文论的批评,不仅更加有理有据,而且充满着辩证思维的分寸感与文学史论者的严谨。 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俄罗斯文艺学界具有牢固的地位。利哈乔夫在喜爱的文学史和文论研究中也始终坚守这一传统。在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连杰尔的文论著作时,利哈乔夫高度赞赏了他从历史具体的语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指出弗里德连杰尔超越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和美学的具体言论”,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604)。同样,他主张还原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现实主义”术语的历史语境,并从学科意义上具体分析这个经典术语。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他们所指的不仅仅是19世纪的艺术的优点”(利哈乔夫,“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605-607)。在“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文中,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变化着的价值”(Лихачев,“Принцип историзма в изучениилитературы” 121)。这不禁令人想起别林斯基的名言:文学批评是一种运动中的美学。在评价俄罗斯文本学成就时,利哈乔夫也强调,“文本学中的历史主义也表现在文艺学多种多样的领域里。历史主义早就占据了古罗斯文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光辉成就展现在德米特里耶娃献给古代罗斯的那部专著中”(《解读俄罗斯》315)。他不仅鼓励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而且坚信这种富有成效的方法论会对现代结构主义的弊端加以清除。“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的解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结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Лихачев,“Принцип историзма в изуче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121)。在“文学的结构”一文中,他率先践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指出“近代文学的结构就显著地不同于中世纪文学的结构”(Лихачев,“Стро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54)。所以,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一成不变地抽象谈论文学的作品结构,而忽视文学结构的历史演变性。同样,在探讨文学作为交际和复调的时候,利哈乔夫也没有忘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俄罗斯文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统一:历史的统一和在每个时代的内部既斗争又结盟的统一”(Лихачев,“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общение и полифония”146)。这充分显示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和宽容态度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利哈乔夫既坚守俄罗斯人文学科的优秀传统,同时又不失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能够把历史主义的学科传统和现代人文学科的前沿观念有机融合在一起,以史论与文论兼容的方法推进文艺思想研究的发展。 近代以降,俄罗斯文化成为欧洲启蒙主义文化后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中心主义的人文伦理文化,对世界人文思想的深化多有贡献。而文学中心主义的要义有两个显著的方面;一是向外,倡导“为人生的文学”(鲁迅语)理念,文学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形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二是向内,提倡包括文艺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追求道德完善,刻意人格完美,弘扬真善美。利哈乔夫在20世纪人文思想的探索依然沿着俄罗斯主流思想传统进行,并结合现当代的文化现象加以切近时代精神的丰富与拓展。他的“知识分子特性”观、“文化性”理念、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体论都没有离开俄罗斯“为人生文学”的思想轴心。有关“知识分子特性”的界定摈弃了狭义单纯技能定义,扩展了“知识分子特性”的人文内涵与外延;“文化性”蕴含的新人文伦理打破了传统仅仅以人为中心而忽略人与自然和谐的旧文化观;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克服了厚今薄古忽视传统规律的形而上学的偏执;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体论内化了现实主义的思想与审美两个层面的内在关联。因此,深化利哈乔夫文论思想的解读有助于拓展当代俄语文学及文化的研究。 ①此处黑体部分意在强调,为笔者所加,下同。 ②利哈乔夫的这篇文艺理论文章发表后,很快就被译成中文,收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