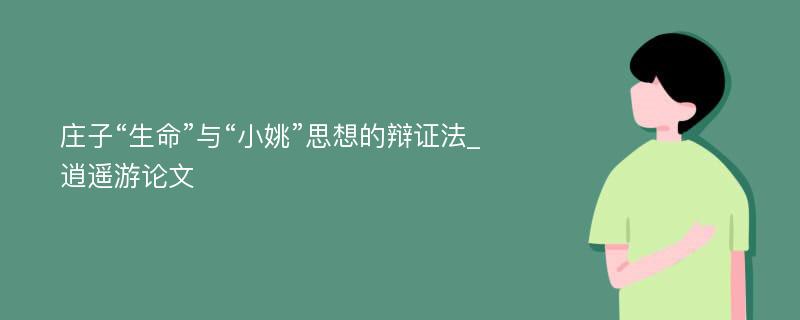
庄子“命”与“逍遥”思想辩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逍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以道解庄”“以儒解庄”和“以佛解庄”,是传统解庄的三个主要进路。自西方哲学引入中国,“以西解庄”,即依借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理论诠解庄子的哲学思想,逐渐成为现代庄学研究的主流倾向。不可否认,“以西解庄”在某些方面确实增进了对于庄子思想的深入理解,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也有比较明显的比附之嫌。比如有人将庄子的“命”与“逍遥”诠解为“必然与自由”:“庄子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因果联系,都要受其它事物的推动影响……这种全宇宙的必然关系,就是他所说的‘命’之意义。他认为人是无法离开或者改变这个必然关系的……而他又是一个渴望追求自由精神的人,于是在这个矛盾中,他产生了幻想主观的逍遥自由思想”(张恒寿,第358-359页),认为,“命”是促使庄子提出“逍遥”思想的主因,而“命”即“必然性”,“逍遥”即“精神自由”,于是,“命”与“逍遥”的关系就被解释为“必然与自由”的关系。然而,如此解说是否妥当呢? 一、“命”并不只具有“必然性” “命”在《庄子》一书中①,凡82见,是一个义涵极其丰富的思想范畴。除却命令、指令、教命、命名等普通用法外,具有哲学意义的含义有四个,分别是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且四个方面的含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如庄子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此处所言之“命”,即是“天命”之“命”。再如:“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至乐》)“司命”是掌管人之生命的神灵,其所司之“命”,乃人的生命之命。又如:“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人间世》)爱父母植根于人之本性,爱亲之“命”,乃性命之命。又如:“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秋水》)此处之“命”,与“时”相联,乃运命之命。 可见,庄子所说的“命”,实包括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四方面的含义。此四者中,“天命”最为重要,它是命,是天之所命,是决定国家、社会、人生之大事大端之最主要的力量,是人所无法抗拒的力量。同时,它又是生命、性命、运命得以成立的基础与关键,生命、性命、运命,其实也是天之所命。《德充符》篇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此处所言之“命”,既是天命,可以决定寒暑之自然变化;同时又决定着人之穷达、贫富,所以又是运命;还决定着人之贤与不肖,所以又是性命;并且还决定着人之死生、存亡,决定着人之生命。可以说,人之生命,由天命所令,有生亦有死,有生必有死,其所以然者,天命所然也;人之性命,由天命所定,贤或不肖,天命使然也;人之运命,由天命所命,穷达贫富之所分别,天命为之也。庄子之“命”,一字而含四义,是一个由天命所统摄,由天命而生命、而性命、而运命,命命相贯通、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然而,庄子“命”之四个方面,虽然有必然性的成分,但亦有偶然性的因素。“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指出了命的必然性。“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德充符》),则揭示了命的偶然性。后羿是古代有名的神射手,几乎是百发百中,在后羿射程之内,并且是在他射程的中间地段,那是一定要被射中的,但是竟然没被射中,这实在是一种侥幸,是一种几率甚微的可能。这种侥幸、可能,无从解释,也许只能用“命”来解释,所谓命该如此。这种命该如此,不具有任何必然性,只是一种偶然。 必然性并不是庄子命论最基本的方面和特色,与其以“必然性”解说庄子之所谓“命”,不如以“自然性”来解说。 庄子“命”之自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命”之所自出的“天”,其根本性质是“自然”的。无论是天命,还是生命、性命、运命,其所发用者,均是“天”。如前所述,天命、生命、性命、运命四者,并非是一并列的关系,生命、性命、运命,从根本上是从属于天命的,就其现实性而言,生命、性命、运命只是天命之所令、所定、所命,而天命之天,在庄子看来,既非最高主宰之皇天上帝,亦非有意志之人格神。 殷周时人们所理解的“天”,一般是指宇宙的最高主宰。如《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周定王使者王孙满在答楚庄王问鼎之事时曰:“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因为周朝之江山社稷是“天所命也”,所以,楚国虽然国大势强,然“天命未改”,楚国并不能改变天所预先决定好的周王朝的运命。孔子亦曾讲:“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里的“天”,亦是有意志的最高的人格神。 庄子并不如此理解“天”。据王叔岷先生辑佚的《庄子佚文》,庄子尝曰:“天即自然”。(《庄学管窥》,第236页)庄子所理解的天,实际上是一自然之天,是一没有人格意志、没有道德属性、无识无知、不预先决定任何人物事物发展趋势的客观力量。 其二,“天命”之如此运行化作,亦是自然的,是事物的自然变化,并不具有目的性、赏罚性,并不具有预先安排的性质。庄子对于“命”有过定义式的表述,其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此句是游水丈人向孔子所述自己为何善于游泳,言其不明个中究竟。若将此意泛化,即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也”②。据王叔岷先生辑佚的《庄子佚文》,庄子又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自然”。(《庄学管窥》,第236页)若将庄子两句所言相参照,即可得出“命即自然”③的结论。“命即自然”,表明在庄子的思想系统中,“命”乃“天道自然之流行变化”。 庄子之所谓“命”,其实是对“天道自然流行变化”的拟称。老子讲:“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又讲:“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十七章),“天地不仁”。(第五章)天道自然,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庄子将老子天道自然与孔子的天命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与老子相同,庄子认为,天道自然,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的流行变化是自然如此的;另一方面,与孔子相同,天命是存在的,并且是强大的,是人所无能为力、无法改变的。同时,庄子又吸收了墨子“非命”论的合理因素,否定有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预先安排好一切。在庄子看来,“天命”实质上是“天道自然之流行变化”。而“天道自然之流行变化”,其力量是无比强大的,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人在天命面前,既不可抗拒,亦不能埋怨,亦非只是消极地接受,而应当以达观的态度,坦然、平静地面对今生今世所遭受的一切。 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矣。”(《人间世》)又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以坦然达观的心态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只有道德修养达到极致的人才可以做到;而能做到如此,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这些才是庄子天命论的理论要旨,而这一理论要旨,与必然性实无多少理论关联。 二、“逍遥”并不等同于“精神自由” 不仅庄子之所谓“命”不应被窄化为“必然性”,庄子之“逍遥”也不应简化为“精神绝对自由”。 逍遥,本是一双声叠韵连绵词,其本义为“游”。屈原《离骚》有言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东汉王逸注曰:“逍遥、相羊,皆游也。”(《楚词补注》,第28页)“游”的本义是“无所事事地漫步行走”,故逍遥作为“游”,本不带有固定的情感色彩。④“逍遥”之“游”,漫步者的心情或有所不同,可能是轻松自在、怡然自得的“游”,也可能是满怀心事、愁忧难解的“游”。虽然,“逍遥”并不带有固定的情感色彩,但它总具有某一情感色彩,并渗透着“游”者不同的精神境界。 《庄子》一书中的逍遥与《离骚》中的逍遥,意义有相似之处,但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屈子之逍遥,乃“聊浮游以逍遥”,总与消极性的情感相关联。而庄子之逍遥,乃悠然自适之逍遥。《逍遥游》中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让王》中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因庄子所言之逍遥,总与悠闲、怡然、自在等情感相关联,故后代注家在解说庄子时,总是赋予逍遥悠闲轻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心意自得等义涵,似乎“逍遥”之本义就是如此。如王穆夜曰:“逍遥者,盖是放狂自得之名也。”(《庄子集释》,第2页)陆德明曰:“逍遥游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然自得。”(同上)成玄英曰:“彷徨是纵放之名,逍遥是任适之称。”(同上,第664页)如此一来,原本不带有固定情感色彩的逍遥,附上了固定的积极意义的情感因素。⑤“逍遥”一词,经过庄学史上注家的不断诠解,它的义涵已经严重“庄子化”。上述注家中,陆德明以“闲放不拘,怡适自得”解说逍遥,义涵丰富,最得庄子逍遥之义旨。若将此义与逍遥之本义“无所事事地漫步行走”结合起来,那么,《庄子》一书之逍遥,可确定为:“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的悠游”。 人们若将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的悠游作为一种处世方式,那么,逍遥也就成为一种自然无为、疏离于名利功业的存在方式。庄子本人即将逍遥作为自然无为的在世方式。如其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天运》)庄子所谓的逍遥,乃是至人将自己从为仁行义等有为的事业中疏离出来,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游于“无为”之墟。以逍遥为自然无为的在世方式,在《庄子》的其他篇章中还有所论及。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大宗师》)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达生》) 庄子认为,“逍遥”即无事无为,茫然悠游于尘世之外。以此方式在世,因其与俗世之事业保持疏离状态,故不为功名利禄所困扰,不为世俗礼法所束缚,更不会计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以观众人之耳目”,所以能够自足自乐、自由自在,能够心意自得。张松辉先生指出:“由于后人把‘逍遥’一词理解为‘自由自在貌’,所以《逍遥游》整篇的主旨就是在讲绝对精神自由。关于这一点,至今没有异议。其实‘逍遥游’的意思,不是在讲精神自由翱翔,而是在讲无为以处世的原则。逍遥者,无为无事也。游者,处世也。”(张松辉,第8页)张松辉先生看到了庄子以“逍遥”为一种疏离于有为事业的在世方式,一定程度上辩正了以往纯以“精神自由”来解说庄子“逍遥”的不当之处。然其以为,“‘逍遥游’的意思,不是在讲精神自由翱翔”,也有所偏颇。 “逍遥”之本义虽为“游”,但由于后人将“逍遥”与“游”结合,组成同义复合词“逍遥游”,且《庄子》首篇以此为题,故后世注家不仅以此解说《庄子》首篇之主旨,更以其概括《庄子》一书之宗旨。然而,理解庄子“逍遥游”之思想,不能仅就《庄子》一书才6见的“逍遥”一词,还应结合全书出现的多达113次的“游”⑥字,来理解“逍遥游”之思想。罗安宪先生通过细审“游”在《庄子》一书中的用法指出:“审查庄子之所谓“游”,约有三意:一为形游;二为神游;三为心游。形游者,身体之闲游也,形之无拘束也;神游者,精神之游驰也,神游万里之外也;心游者,心灵之游乐也,精神之自由也。”(罗安宪,第159-160页)“神游”是“精神之游驰”,而“心游”是“心灵之游乐”,指涉的都是人的“精神”之游。 因此,若从人是形身与精神之统一体的角度而言,人之“游”,实可分为“形身之游”与“精神之游”。故在庄子思想中,“逍遥游”作为一种“游”,不仅指一种“形身”从有为的事业中疏离出来,游离于尘垢般俗世之外的在世方式,也指一种“精神”无所拘碍地悠游于无穷之天地的高超思想境界中。⑦ 由于经庄学史上注家的不断诠解,“逍遥”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等义涵,因此,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者为接引西方的“自由”观念,将庄子的“逍遥”诠解为了“自由”。如章太炎曾说:“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章太炎,第34页)虽然他同时也指出,庄子所谓的“自由”,与西方近代以来“群己权界”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有所不同,但就其“逍遥游”即“自由”而言,实际上是未加辨析地将庄子的“逍遥”直接等同于“自由”。后来张恒寿等先生将庄子的“逍遥”诠解为“精神绝对自由”,因为在他们看来,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无待的逍遥”,而能够无待地逍遥于无穷天地之间的主体,只能是人的精神,故庄子的“逍遥”作为自由只能是一种“精神之自由”。然而在庄子的思想中,“逍遥”不仅仅涉及精神,也涉及身体,将庄子的“逍遥”只理解为“精神绝对自由”,实际上窄化了庄子逍遥思想本身的义涵。 且从根本上说,“逍遥”可否诠解为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也是存疑的。因为庄子所谓的“逍遥”与西方的“自由”,实存有难以融贯的意义上的差别。 首先,“逍遥”本义为“游”,虽经庄学史上注家的不断诠解,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等义涵,但庄子所谓的逍遥依然带有“游”之义;而西方的“自由”,无论是行为层面上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还是思想层面的意志自由、思想自由等,都不包含此义。 其次,庄子所谓的“逍遥”,内蕴有自足自乐、怡然自适等积极情感因素,而西方的“自由”则并不必然地含有这种精神因素。故近代以来,一些学者未加辨析地将庄子的“逍遥”直接等同于“自由”,其做法是值得商榷的。⑧ 三、结论 总之,庄子所谓的“命”,实包含天命、生命、性命和运命等多重义涵,并不简单等同于“必然性”;且“必然性”并不是庄子“命”论之根本性义涵,与其以“必然性”解说“命”,不如以“自然性”来解释。“命”乃是庄子对“天道之自然流行变化”的拟称。庄子认为,天道自然之变化,既有常又无常,故“命”之变化既包括必然,也包括偶然。同时,“逍遥”也无法对等于西方的“自由”概念。因“逍遥”之本义为“游”,虽然它在后来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等涵义,但与西方的“自由”概念还是存在着一些难以融贯的意义差别。故庄子“命”与“逍遥”之思想关系,并不构成“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将庄子“命”与“逍遥”的关系诠解为“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应该是以西释中的一种“不当比附”。 最初学者们在进行这种比附时,其本意可能是为了解释的方便,或者是为了肯定和提升庄子哲学的理论高度,以便确立其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⑨,但这种比附,只不过是将庄子“命”与“逍遥”的思想改造为与斯宾诺莎的“自由即对必然的认识”的理论相似的一种哲学思想,使其“同质化”于西方哲学的“必然与自由”理论,而并未真正提升庄子哲学的思想品质,提高庄子本人的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将庄子原本丰富多义涵的“命”窄化理解为“必然性”,将本有的独具意义的“逍遥”简单理解为“精神自由”,不仅遮蔽了庄子“命”与“逍遥”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而且也抹消了庄子通过“命”与“逍遥”两个范畴对世界与人生所进行的独特思考,故而反使庄子思想变得“干瘪化”,失去了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原创生命力。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冯友兰等学者依照西方哲学的学术范式和理论架构撰写《中国哲学史》以来,依据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理论诠解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方式。受此影响,“以西解庄”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人解庄的主要方式。本来,恰当地“以西解庄”,可以提供一种从新的理论视角诠解传统庄学义理的可能性,拓展庄子思想的解释空间,在将西方哲学与传统庄学进行“视阈融合”的过程中,呈显诸多原先在传统庄学中隐而不显的内在思想意蕴,促使对传统庄学的新理解,但事实上却多有违愿,这是需要我们不断反思的。 总之,在“以西解庄”的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到,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毕竟在概念内涵、思想重点以及思想的时代背景乃至对世界的经验和思考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如果忽略这些差别,只看到二者之间表面的相似性或似是而非的“相通之处”,勉强构造一些不恰当的思想联系,只会将传统哲学思想混同于西方哲学的某个理论,使其变成西方哲学的注脚,丧失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因此,若不想让“以西解庄”变为“以庄附西”,我们就必须在全面把握二者深层义理的基础上,寻求传统庄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真正“会通”,推进庄学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不少人认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所作,外、杂篇则非庄子所作,研究庄子思想应只限于内篇。但也有人认为,《庄子》内、外、杂篇并无实质性差异,不宜先入为主地作此种分别,此分别之证据并非确证,对庄子思想更合理的解释和理解,应将全书视为一个整体。本人持后一种观点。 ②《吕氏春秋·知分》曰:“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者。”此一说法,当本自于《庄子》。 ③鹖冠子尝曰:“命者,自然者也。”(《鹖冠子·环流》) ④张松辉先生曾指出:“‘逍遥’两字都从‘辵’,可见这一语词的本义就是行走,并不带感情色彩。”(张松辉,第4页) ⑤如现在人们常说“逍遥快乐”,将“逍遥”与“快乐”相联系;再如“逍遥自在”,将“逍遥”与“自在”相联系。“逍遥”一词之义涵,由原来的“无所事事地漫步行走”,逐渐变成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怡适快乐”的代名词,词性亦由原来的动词演变为形容词。 ⑥在这113见的“游”字中,除4次用于人名“子游”外,其余皆是“游走、游览、悠游、遨游”之义。 ⑦如邓联合也指出:“庄子的‘逍遥游’既是一种外在的个体生存方式,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邓联合,第82页) ⑧谢扬举先生曾对以西方的“自由”诠解庄子的“逍遥”的做法,进行反思,认为:“‘逍遥’刻画的根本精神与解放自我的西方自由精神虽有交叉,但毕竟是两回事!”(谢扬举,第35页)邓联合则提出:“以伯林的自由观念为基准,‘逍遥游’这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不仅与自由全无干系,甚至背道而驰”;“如果说逍遥精神与西方的自由概念有相通之处的话,那也仅在不受限制和自我决定的意义上,只不过前者仅就内在的心灵世界而言。”(邓联合,第417、418页) ⑨比如任继愈先生说:“庄子是世界哲学史上第一个接触到自由与必然问题的哲学家。关于这一方面的巨大成就,只有斯宾诺莎可以和他相比。”(《庄子哲学讨论集》,第176页)可见,任先生等一些研究者最初将庄子的“命”诠解为“必然性”、将“逍遥”诠解为“精神自由”,确有为中国哲学争取对“自由与必然”“首触权”的努力,以提升庄子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