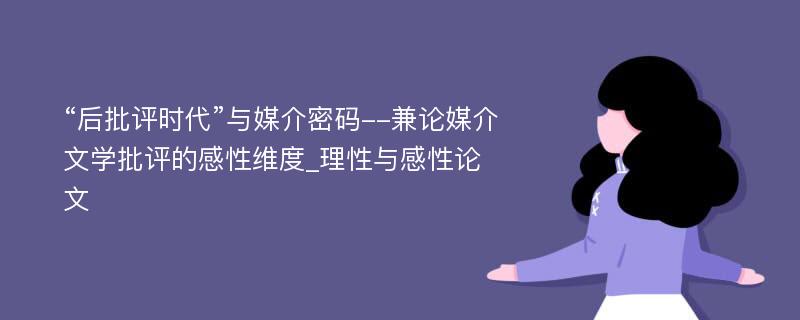
“后批评时代”与传媒符码——兼论传媒文艺批评的感性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传媒论文,感性论文,批评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审美文化的大众化与感性化,循迹而至的是批评话语的大众化与感性化,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汹涌之势和大众狂欢的迷乱。事实上,否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传媒批评的存在,否定传媒批评对学理批评的挤压与鲸吞,否定传媒批评对文化消费主体的诱惑、献媚及对文化消费主体的牵引,这都是不明智的。“存在就是合理的”、“面向事情本身”(海德格尔语),正视传媒批评的存在与张扬,廓清传媒批评的审美品质,厘清传媒批评的生成机制,才是亟待解决的命题。
一 喧哗的质疑:扒开传媒批评的皮相
所谓传媒批评,或者说是媒体批评,一般是指由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是依附于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权力和文化主导地位而渐成气候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传媒批评的突起,拉开了文艺批评话语转型的序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媒批评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探究。
从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2001年,除报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说传媒批评外,一些文艺单位还召开有关传媒批评的专题研讨会,从而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传媒批评更加显豁地展示在文化消费者的面前。在众声喧哗当中,有几篇文章是颇值得关注的。例如,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载于《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载于《文汇报》2000年3月18日)、萧云儒的《质疑“传媒文艺批评”》(载于《文艺报》2000年12月7日)、陈冲的《论“文学批评传媒化”》。特别是萧云儒的“质疑”,对所谓的“传媒文艺批评”进行了刮骨剔肉的剖析。萧文认为,“传媒文艺批评”既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侵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转换批评主体,窃取评论话语权;转换价值标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转换心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并指出,“传媒文艺批评”的张扬,实质上就是西方所谓的“媒介帝国主义”的视域的一种权力延伸与绵延。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第3期的《南方文坛》,在李敬泽主持的“今日热谈”专栏,发表了陈晓明的《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崔红楠的《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三人的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评说了具有当下性的文坛热点——“传媒批评”。尤其是陈晓明的“析骂”,颇有一针见血之犀利。陈文认为,“媒体批评”就是“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并进一步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还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聊的叫骂,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不骂就没有责任感,不骂就不能拯救文学。
在有关“传媒批评”的批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于2001年6月14日至15日在天津举办了“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的研讨会。该研讨会的议题先遣地把网络批评从媒体批评中剥离出来,正式提出了所谓的“三种批评三分天下”(即“网络批评”、“媒体批评”和“主流批评”)的命题。其中陈晓明把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纳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亚文化性和攻击性等;白烨把媒体批评的特点概括为复制性、事件化和“酷评化”,认为当下文艺批评的症结主要在于媒体批评的扩大化与文学批评的媒体化。
上述喧哗的质疑是及时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虚妄。毕竟“批评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批评家连这个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的话(实质上仅有这个承认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泄露批评家的“讳疾忌医”和在引导传媒批评向“健康的批评”渡化的“无能”。也许我们真应该撩开传媒批评的七彩面纱,探究它生存拓展的审美之维。
二 冲动的纠偏:穿越理性的屏障
当主流批评媚态十足地蜇进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狭小胡同,学理批评故作高深地躲进穷经皓首、引经据典的学院阁楼时,感性化的传媒批评却恰恰迎合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依凭着现代传播媒介的文化权力和读者对感性之维、游牧文化的回归,占据评坛中心要津而张扬感性十足的话语霸权。这正如捷克著名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这种精神与小说的精神是水火不容的。”[1]同样,文艺批评也同样“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
从整体上看,“传媒文本”重感性介入与感官刺激,轻理性阐释与诗性价值,同样,传媒批评也在所难免。从价值标准来审视,学理批评强调的是作品的认知价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强调的是公正评断、深刻挖掘、辩证分析。传媒批评强调的是作家、作品的新闻价值,为了抓住时效,抢滩市场,哄抬舆论效应,其表述与言说常常快速而肤浅、片面而极端、大惊小怪和哗众取宠。于是“哥们”、“戏说”、“棒喝”、“枪挑”、直至“灭了他”的语言也在评论界流行了,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轰动一时的“二王之争”、“二余之争”、“二宝贝之骂”以及王朔的“炮轰”、“我看”之类的“无畏之言”……但令人奇怪的是,正是这种受正统的批评家们所鄙视的传媒批评,却得到了受众的广泛认同与欢迎,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割据了很大的地盘。那么,这种悖逆是如何生成的呢?简而言之,都是理性惹的祸。
其一,传统理性主义对欲望、文化和日常生活是熟视无睹的,这中间就隐含着主体被生产和被控制的时空,也就暗示了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蜕化而堕入理性的奴仆。“特别是启蒙运动曾将理性抬高到昔日神灵所处的地位,然而正是这种理性由目的而功利,由功利机制而工具主义,把人的本真存在消蚀殆尽,对人的自然家园犁庭扫穴。”[2]此外,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强权化,人成了异化之物,成了被思想、概念、谱系、逻各斯、意识形态、规范、价值、形而上等宰制的奴隶和愚弄的“大头”。
其二,从理论上来说,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美学”(Aesthetics,音译“埃斯代蒂克”)一词,实际上不仅包含着词源学上的误解,而且也表现了审美文化的偏颇,表现出几千年文明史的片面价值取向。因为无论是从这个词的词根、语源来看,还是从它所派生出来的各种西文变体名词来理解,“埃斯代蒂克”的本意就是为感性立言。鲍姆嘉登在《美学》一书里明确地提出“美学的对象就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突出了美学的感性特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以降的西方美学却沿着知识论、理性化的轨道运行。于是理性在审美的国度挥舞着王权的宝杖,而感性只能萎缩在边缘地带呻吟,恰如学者徐岱所说的,“对肉体快感的由贬低到遗忘、及由此而来的对生命狂欢的意义的忽视,这恐怕是古典形而上美学的最大遗憾。”[3]
其三,作为主流形态的学理批评与学院批评扮演着“牧师”的文化身份,剥夺了接受主体的感性狂欢权与体验享受权,压抑了接受主体的“酒神意识”,从而使接受主体对学理批评与学院批评敬而远之。胡塞尔曾经断言:“体验始终是所有东西的前提”,这无异是给重理性之思的学理批评与重学术建构的学院批评当头棒击。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全过程应当由两个基本环节,即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以及三种要素——作家、作品和接受者——组成。并且说,文艺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作家、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是为了供人阅读、欣赏,文艺唯一的对象是读者和观赏者。姚斯指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4]就文艺批评来说,批评家的批评文本只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要想转换成“现实的存在”,这得依赖读者与观众的接受。事实却不然,学理批评与学院批评过于钟情于形而上的“日神精神”、“政治救赎”和学术建构,高高在上远离“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社会”与消费社会的审美趣味。这样无意识的拒绝、疏远与隔障,却为自己掘下了孤寂的凄凉。
于是,批评话语的位移与转换便在所难免了,这当然包括批评主体的转换、价值标准的转换、评论目的的转换、心理认同的转换、言说方式的转换、语体风格的转换以及话语权力的移交。批评的理性化日暮途穷,批评的感性化蒸蒸日上,传统理性的屏障显得支离破碎,渴望回归“酒神精神”、“乐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文化消费主体轻易地挣脱了理性的樊篱与屏障,在现代传播媒介对感性符号的全力培植下重新塑造着众生狂欢的现世与此岸的风景。
三 清醒的阐释:透视感性的狂欢
在世纪嬗变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只要细细体悟叔本华与基尔凯郭尔“上帝远去”的预言、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告和福柯“人也死了”的哀鸣,就会知道曾几何时处于边缘化的感性主义已到了中心化的时机了。事实上,传媒批评消解学理批评与学院批评的“杀手锏”、诱惑接受主体的“迷魂药”,就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传媒批评话语有着无处不在的感性魅力。
首先,文艺批评的文本意义寄寓于它的感性之维之中。一般而言,包括文艺批评在内的审美活动,首先应是一种“此在”。纵使强调“理念美”如斯的柏拉图也不得不在《大希匹阿斯篇》中承认;“美就是经视觉和听觉感官而产生的愉悦。”康德曾明确地肯定了审美活动本质上属于一种“趣味活动”,他在着手《判断力批判》的写作前就已提出:“在进行理性的批判时,对趣味的批判,亦即美学。”[5]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曾以注解的方式指出“唯有德国人现在用Aesthetik一词来表示其他国家的人称为趣味批判的东西”,明确了审美作为一种趣味活动的特点。并还说:“关于快适,下面这个原则是妥当的,即:每一个人有他独自的自(感官的)鉴赏。”事实证明,为了有效地把握审美活动,美学必须尽力去贴近“现象界”。卡西尔认为:“美学沉湎于感觉现象,而不是想超越现象去研究某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去研究一切现象的根据。因为这样一种超越不能解释现象的审美内容,而只能毁灭它。”[6]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美”的奥秘并不在审美现象的“后面”,而就在现象之中。歌德也在《箴言与沉思》中认为:“在现象背后一无所有,现象本身就是一切。”乌纳穆诺也说:“感觉自己存在,这比知道自己存在具有更大的意义。存在就是感知,存在就是行动……存在就是需要:我需要物,物需要我。”[7]物性与感性,是人类感知存在的立足点。
但遗憾的是,人类以工具理性、科学理性来把握世界的奥秘,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下却忘记了理解的基础是感觉,是与感觉相连的事物的感性的存在。所以,要真正把握文艺批评文本与话语的真正意义,“感性之维”是最初的通道与最终的基石。
其次,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消费化、媒体化和伪治疗化的社会,它所对应的是娱乐文化,所标举的是世俗的天堂。“在娱乐文化中,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快乐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8]于是,世纪转变的文化语境成了一个没有史诗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文艺批评的标准也在此明显了转了个弯——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导。于是,“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成了最切合大众心理的评判尺度。而且随着社会整体上的媒体化,文艺批评的媒体化程度也不断加剧,批评话语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产业的齿轮与螺丝钉,成为消费社会的“休闲品”。所以,精神让位于现实,评论之“思”让位于评论之“闲”,艺术评论成为媒体雇佣的高级保姆:人们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本雅明所谓的“韵味”(Aural)来衡量文艺作品的意义,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畅销性来衡量文艺作品的意义。
再次,现代传播媒介对感性符号的大力培植,也培植了受众对传媒批评的感性符号的认同感。那么什么是现代传播媒介的培植性呢?仅以电视为例,著名传媒理论家乔治·格博纳(George Gerbner)深刻指出:“电视节目是一个讲授故事的集中系统,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将戏剧、商业广告、新闻和其他节目相连贯的公共形象和信息世界带入了每个家庭。从孩提时代起,电视节目就培植了我们的偏爱和爱好,而在以前这些偏好是从其他的第一手来源获得的。电视跨越了文字和地域的屏障,成为社会化和每日信息(多为娱乐形式)的第一手来源,否则我们将还是个异质社会。成批制作电视信息和电视影像的重复帧面图像便成了一个公共象征性环境的主流。”[9]这样“文字符号”让位于“图像符号”,“图像符号”占据主流与中心位置而实施显在的培植功能,受众也乐于在这种培植中张扬着感性的狂欢。换言之,电视被认为是执行一致化作用的文化代理人,这种效应就是培植性;培植性与电视在长时间跨度上所积累传播的全体帧面图像有关,而不是与任何具体的内容或特定的效应有关。实际上,次文化可以保留它们各自的价值,但是电视所描绘的一般主导性影像将横扫个人、社会群体和子文化,进而对它们发生影响。所以,依存于现代传播媒介的传媒批评对感性符号的培植与光大,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接受主体从被动向主动的角色转换,直接导致了受众对批评话语的“选择性接收”(Selective Perception)。我们可以把站在现代批评家族这个“玻璃墙”面前的文化消费大众分为“主动观众”和“被动观众”两类,按照弗兰克·波卡(Frank Biocca)的观点,“主动观众”有五个鲜明的特征,它们分别是选择性、实用性、目的性、参与性和不受干忧性。所以,传媒批评所关注的恒久不变的叙述主题,比如新闻、消息、报道、奇闻轶事、旁门左道、市井言语、炒作、广告、青春、美丽、性爱、金钱、仕途、成功、窥视、揭秘与黑幕等等就成了为“媒介帝国主义”所培植起来的“主动观众”的首选。这样,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话语的传媒批评也就完成了对学理批评与学院批评的蚕食与挤兑,批评家族的分化与此消彼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而言之,传媒批评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有不断拓展的趋势。它穿越了理性的屏障,迎合了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唤醒了受众内心深处的“酒神意识”,以“感性狂欢”的形式释放着摇曳多姿的魅力。但传媒批评在文化权力的庇护下策划炒作的广告技巧与制造卖点的消费行径,思想缺席,利益在场,以及表面的、片面的、个人的、浮躁的印象批评,似乎又暗示了传媒批评离“健康的批评”(伏尔泰曾把“健康的批评”列为第十个缪斯,派她把守趣味的神殿)尚有距离。因此,对传媒批评进行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这正如法国著名批评家蒂博代指出的一样,“没有对批评的批评就没有批评”,“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自由主义的形成永远离不开对自由主义的批评”[10]我们期待更健康的传媒批评在世纪嬗变的文化地平线上拥有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