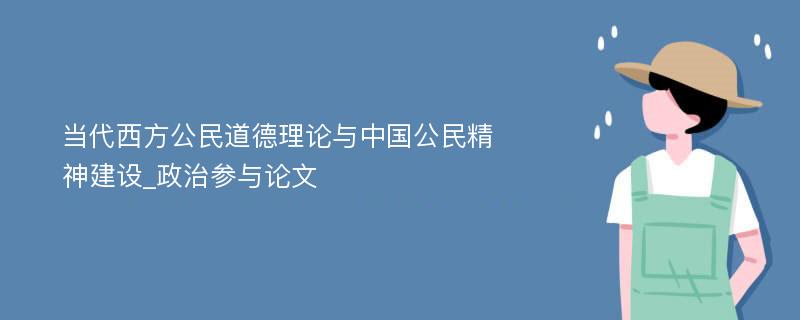
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与我国公民精神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德性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公民与公民德性
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均为我国公民。雅诺斯基认为,“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1](P11) 世界各国对公民的理解大都是如此。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现代的公民概念应包涵着以下价值规定:(1)公民是民族国家的正式成员,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合法的自由权利,同时必须承担对国家的法定义务。(2)公民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平等的社会成员,每个公民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是平等的,这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辩明、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并应以民主、平等的观念和态度对待其他同胞公民。(3)公民身份是主动与被动的统一。当其作为国家主权的参与者时,他是主动的;当其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时,他是被动的。但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主体性则是其基本的价值规定。
公民德性概念被西塞罗称为virtus,后来的意大利理论家称为virtu,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将其译为公民美德(civic virtue)或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当代共和主义理论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认为公民德性这一术语是指称:“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2](P74) 西方不同的政治理论家,对公民德性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但基本上可以把公民德性界定为社会成员基于其公民身份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应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质,可与公民素质、公共精神、公民属性在同等意义上理解和使用。
民主宪政制度与公民德性具有共生性,一方面,民主制度本身能提供有效的公民教育,另一方面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仅仅依赖于结构与程序,而且还依赖于同敏锐地体现民主价值的制度一样重要的东西——公民的民主品性与态度。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成员及公民若缺乏良好的公民德性和政治认同,任何制度都可能遭到扭曲和破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宪政自由制度的价值在于人们对制度的运用”[3]。因此,民主社会中的公民是否具有维持政治制度的意愿和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以及如何培养公民具有这种意愿与能力,是民主社会面对的重要课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在民主社会中现代公民精神应该具有哪些内涵,哪些核心的内涵是维系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些都涉及到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固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培养一代认同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公民则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必要认真研究西方的公民德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德性问题成为西方政治哲学、教育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自由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社群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左派的公民德性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
(一)自由主义的德性理论
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几乎都专注于权利与制度的正当性的证明,以便保障这些权利,但他们没有注意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因而受到指责。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公民德性的论述中,较有影响力的论著却出自自由主义者之手,如,阿密·古特曼(Amy Gutmann)、 斯蒂芬·莫西度(Stephen Macedo)以及威廉·盖尔斯敦(Willim Galston)。盖尔斯敦认为,公民责任所要求的德性可以分为四种:(1)一般公民德性:勇气,遵纪守法,忠诚。(2)社会德性:独立性,开放精神。(3)经济德性:职业伦理,暂缓自我满足的能力,对经济技术变革适应能力。(4)政治德性:辩明并尊重他人权利的能力,愿意只满足于支付得起的东西,评价公职人员的能力,从事公共讨论的意愿[4](P256)。
质疑权威的能力及从事公共讨论的意愿,构成了自由主义德性理论的最显著之点。质疑权威的能力之所以必要,部分原因在于:代议制民主下的公民选举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代表。因此,公民的一个重要权利和责任就是监督这些官员并评判他们的行为,以保持“……普通公民对于领袖人物施行较高程度的控制”[5](P184),这是贯穿于许多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线。参与公共讨论的意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民主政府应该通过自由而开放的讨论作出决策。民主政治的这一特征要求普通公民必须发表他的观点,以便让他的观点广为人知,尤其要让政治精英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这是公民实现其政治影响力的前提。
那么如何获得这些德性呢?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应该从教育系统中习得这些德性。学校必须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教给他们一些道德观点去确定什么是符合公共理性的。古特曼指出:“如果要儿童在成为公民后能实现分享政治主权这一民主理想”,那么在学校时他们就“不仅必须学会依照权威而行为,而且要学会对权威作批判性思考”。“仅仅受习惯与权威支配的人不能组成一个由主权公民所构成的社会”[6](P258) 但这种挑战权威的教育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在私人生活中对传统、家长权威和宗教权威提出质疑,这使得自由主义德性理论家面临着,既要促进学生质疑政治权威而又不削弱他们对父辈生活方式的认同的两难困境。
(二)社群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
社群主义公民理论是一种强调实践社群“公共善”的公民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公民德性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公共善”是社会成员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价值目标。二是公民对其所属政治社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忠臣和认同。三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强调社会成员在社会的共善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群主义的公民德性强调社会、国家优先于个人而存在,强调公民的责任义务以及公共服务的角色,鼓励社群成员选择与社群共善价值相符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是每个公民的必备美德。
社群主义理论家强调文明品质与自我约束对健全民主的必要性,但却认为市场与政治参与都不足以培养这些德性。相反,认为“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的文明品质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团体网络中才能习得。”[7](P253),正是基于公民社会对于培养公民德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民社会理论家认为公民的首要义务之一就是参与公民社团。但把公民社会作为“培养公民德性的苗圃”的主张,可能只是个经验性命题,而不是绝对真理。如,教会、种族团体也可能教会人们对异教和其他人种的偏见和不宽容。因此,公民社团对公民品质究竟有何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左派的公民德性理论
战后左翼理论家一般都从公民权利方面界定公民身份,主张福利国家通过保障公民权利,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享受公共生活。80年代以来遭到新右派的强烈批评,认为福利国家消解了公民的自立。而左派仍坚持认为,虽然公民身份既包括权利也包括责任,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共同体生活的权利必须优先于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参与权得到保障以后,提出履行责任的要求才是恰当的。
左派主张通过政治参与本身(如通过借助于地方的民主制度,地区性集会等方式)来培养公民的自主、责任与公益精神。然而,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左派强调参与,但并没向人们指出如何保证公民负责的去参与,即怀着公益精神而非自私或偏见去参与。
(四)共和主义的公民德性理论
当代共和主义主要受马基雅维里和卢梭的影响,并钟情于古典共和主义的德性传统,强调政治参与对公民个人的内在价值。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生活高于家庭、邻里和职业生活中纯粹私人的乐趣,应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
然而,这种观点与现代世界中大多数人对良好生活的理解方式相抵触。在现代公民看来,政治只是个人生活的手段,政治参与也被看作一种偶尔的活动,大多数主要是在愉快的家庭生活、宗教以及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中而不是在政治中得到最大的幸福。这种观点也为大多数西方政治思想家所赞同。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公民德性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做一个“好公民”应具备的资质,包括自主性,对国家的忠臣和认同,基于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权责意识,对差异人群的宽容与合作能力,对自我需求的节制等。二是如何培养公民德性,主张通过政治参与、加入公民社团、学校教育来培养公民素质。西方对公民属性的要求及其教育方式基本上反映了现代民主制度对人素质的要求,对我国公民教育有借鉴意义。
三、我国公民精神的时代建构
(一)我国公民精神的主要内涵
我国公民精神的培养应在借鉴西方公民德性理论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精神。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积极公民除具备正义、信任、自尊、友善、忠诚等一般德性外,尤其应具有下列民主素质:个体主体性,权责意识,民主法制精神,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质疑权威的能力与参与公共讨论的意愿),对异己人群的宽容与合作的能力。
个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观念是现代公民概念确立的基础。近代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个体主体性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启蒙运动则把自由、平等观念变为西方社会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新右派,左派,公民社会理论家,还是自由主义理论家都把个人自主、自立视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宗法观念的禁锢,使整个社会成员普遍缺乏独立人格意识,表现为无独立性、无主体性、无自我性的萎缩的奴性人格。这些传统观念必然以民族心理的方式沉淀下来,并继续影响今天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公民个体主体性的确立仍是我们时代的艰巨任务。
权责意识。权责意识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公民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有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我国情况与西方不同,长期的封建专制一向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社会成员只知道奉命行事,几乎没有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因此,我国的公民素质教育中仍应把提升公民权利意识放在突出地位。公民权概念在任何一个现代公民国家中都是一个基本概念,它集中体现了“一个广阔而安全的,独立于国家干预的私人领域,一个公民社会的领域。”[8](P178) 因而,意味着公民的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人格尊严的强化和个人自由的增进。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才能在公民中树立起责任意识。
民主法制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是相对于等级或特权意识而言。民主的基本含义是平等,在民主社会里,平等则应该是公民在道德上、政治上以及法律上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民主社会的公民不仅坚信自己应该参与和影响政治决策,而且认为其他公民也和自己一样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法制是维护公民自由、平等权利得以实现的机制,是对人情、特权、等级观念的否定。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对法律权威的普遍服从,是法制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法治社会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柏拉图认为:“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像最野蛮的野兽一样。[9](P27) 柏拉图一直倡导的守法精神之培养,直至今天仍是我们在公民教育中最应重视的问题之一。
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是民主社会对公民素质的必然要求。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民主社会的公民则是社会的主人,是国家的主权者,作为主权者,公民比臣民需要更多的责任和德性,尤其是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现代民主宪政制度要求公民的参与必须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参与至少应包括以下内涵:(1)参与目的的正当性。是为维护本人、他人、或公共合法权益而进行参与;(2)参与程序的合法性。按法定程序参与,反对群众运动式的无序参与;(3)参与的主动性。是基于利益的自主参与,而不是基于动员、说服、纯粹尽义务的被动参与;(4)参与的适度性。阿尔蒙德的研究认为,参与不足和参与过度都会打破政府权力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平衡,不利于社会稳定。只有适度参与,才能保持政府在限制权力与履行职责之间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处在从非理性向理性参与的过度期,更多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动员式的、形式主义的被动参与。因此,如何提高公民理性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公民质疑权威和参与公共讨论的意识和能力,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公民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对异己人群的宽容与合作能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民族、族群以及不同文化集团之间的交往必然扩大,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大规模的移民(主要指西方社会)以及一国之内频繁的人口流动(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改变了城市和国家一度曾经由同宗、同源之人口组成的人口性质。现代公民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与不同民族、宗教及种族的异己人群和睦而又富有建设性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条街道。这需要公民具有尊重差异以及与差异人群联合、合作、协调一致的能力。这种融合与协作有助于在起源不同的公民之间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对于一个多民族民主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公民之间普遍的族裔和政治价值观的对抗的缝隙中生存”[10](P199)。
(二)培养公民精神的现实途径
我们如何获得这些公民责任要求的德性呢?一般来说,教育应是培养公民素质最重要、最可用的手段。阿尔蒙德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五国公民调查中也认为“教育产生了一种主要的公民倾向”。[11](P418) 并认为教育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增进公民的政治认知,情感能力、参与技能和责任感[12](P550)。自由主义德性理论家主张学校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即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的意识和能力。我国的学校教育也应改变过去那种仅仅满足于向青少年直接灌输已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既定的戒律的教育方式,而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选择和评判各种思想观念的独立态度,这是一个自主的、理性的公民的内在规定。同时学校更应在训练和培养学生民主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上更有作为,即学校应成为学生过民主生活的最重要的场所。
但,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不能完全替代公民素质其他成分的创造,如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与多种社会角色相处和协作的能力都需要有相应的实践经历。家庭、工作场所,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参与经历对提高公民实际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阿尔蒙德的研究,以及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家都认为公民参与社团的实践经历对于提高公民的自治和政治参与能力,以及共同义务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俞可平也认为,中国公民社会,在推动政府和公民合作,促进民主公民属性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许多民间组织不仅要求和鼓励其成员积极参与组织内部的事务,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民间组织对社会政治参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公民,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的基层。”[13](P211) 但公民社团在促进公民属性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还需要仔细研究。如,不同类型的公民社团分别产生,承载或传递什么类型的社会价值观念?哪种类型的公民社团更能促进合作、公民参与、宽容、信任和互惠规范?公民社团是否真的是公民的民主训练的学校?公民社团是如何促进公民观念和民主价值观的形成?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家庭、学校教育,工作场所、公民社团和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参与在培育公民的合作、参与的态度和技能方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在创造公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信任和感情信仰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在这方面,政治系统的实际能力——产生满足其系统成员期待的政治输出的能力,也许是最重要的。
标签: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培养理论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