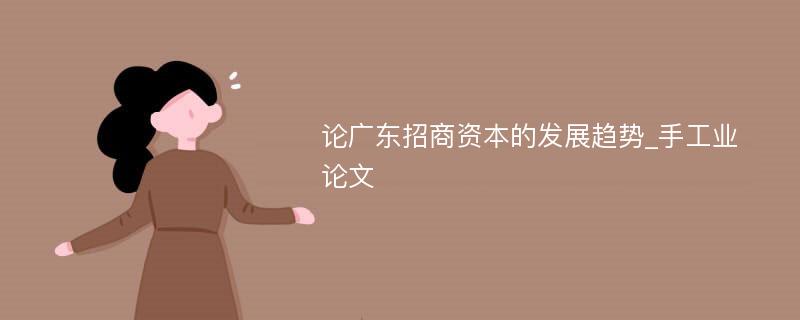
略论广东商帮商人资本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商人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5—0067—05
随着广东商帮的发展,商业资本也不断积累与增殖,并从流通领域流向其他领域,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官僚资本和宗族资产。现分述如下:
一、与手工业生产结合成为产业资本
明中叶以后,广东商帮的商业资本已经开始有一小部分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与手工业生产相结合。在城市和一些城镇中,出现了一些商人直接投资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新现象。例如正统七年(1442)南海商人聂天根把商业资本投资于纺织业中。其家谱记载:“四世祖天根……流贾于厓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注:《聂氏家谱》。)嘉靖年间,佛山冶铁作坊主李壮(号同野)生产出大量产品后,“挟巨资遨游吴楚”,一时成为巨富,“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注:《 李氏族谱》卷5。)商人麦宗泰的父亲曾以经商为业,到他这一代,则经营冶铁业。其家谱说他“性好货殖蕃财,……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注:《麦氏家谱》。)明末清初,新会商人卢从庵、卢鞭人也到佛山从事冶铁生产,“讲求冶生,业钢铁于佛山,善计然求,驯致小康……到崇祯初……赀雄于一方。”(注:卢子骏:《潮连乡志》卷5。)顺治年间,石湾业陶者“陶成则运于四方, 易粟以糊其口。”(注:顺治十六年《三院严革私帛缸瓦饷示约》。)乾隆年间,以“业自鸣钟”起家的潘松轩,也积资颇裕,以至“有贾商积负至数千元无以催,公辄注销记籍不问。”(注:《潘式典堂族谱》卷6。)从顺治到道光年间,“以车模铸冶为业”的黄氏一族,如黄龙文先以经商为业,后到佛山经营冶铁,到其子黄妙科当家时,已是“积有千金”(注:黄先臣:《以寿太祖小谱》(《黄氏族谱》)。)的作坊主了。
众所周知,明清珠江三角洲冶铁业、陶瓷业等较大生产部门能容纳较多的资本,为商人资本转向产业资本提供了可能。但是,能否实现这个转化,取决于产业利润率的高低。清代佛山商人利润率通常为100 %,例如乾隆年间廖介然“高于汉阳,或经年始一归,所获倍利。”(注:《南海廖维则堂家谱》卷3。)道光年间, 陈善性在佛山经营薄荷油生意,获利亦倍蓰。(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志》。)而产业利润则更高,乾隆十五年(1750),佛山炒铁业“盖利与同人,其获三倍”,(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志》。)利润高达300%。追逐高额利润成为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的根本动因。 广东商人把资本投资于本地区(镇)的产业和矿业,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新经济因素。
广东商人资本与手工业结合成为产业资本的途径有二:(1 )直接开办手工业作坊和矿山山场。明清两代,投资冶铁业的佛山商人较多,见于记载的就有隆庆年间投资高书矿山的冼林估,(注:《岭南冼氏宗族谱》卷7。)清初投资本镇冶铁业的麦念居和冯绍裘的祖辈, 康熙年间既从事本镇冶铁又投资外地矿山的黄金发、黄宝阶等人。(注:《江夏黄氏族谱》(咸丰四年手抄本》。)康熙年间投资于纺织业的梁俊伟,其“梁伟号”织机房,“诚实著闻,商业遂振”,(注:《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其机房历康、雍、乾、嘉四代而不衰, 道光九年(1892)仍由其后人继承。(2)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 直接控制某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佛山铁矿业从入清以来就是以商人发炭铁原料给附近乡民(俗称“替铁者”),乡民打制成铁器交给商人的方式生产。(注:《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据口碑材料:乾隆年间有叫住应、住佛两兄弟是著名的机房大户,开铺于佛山安乐里,拥有大量“外机”(即本镇和附近乡村的织产),可见,住氏兄弟也是大包买商。随着佛山商营作坊的不断发展扩大,逐渐出现了手工作坊。《广东新语》对佛山的炒铁业有这样的记载:“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有十余人。”(注:《佛山忠义乡志》卷6, 《实业》。)如果我们把一肆算30砧,一砧算15人,就有450人。 偌大的生产规模,决非作坊式生产所能包容,其生产具有手工场的规模是肯定的。
二、与土地结合成为土地资本
明清时期,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形式中仍占统治地位。当时,广东商帮经商所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正统七年(1442)南海商人聂烟波在经商获利后,就购买土地,“于是田园倍增,手扩租无算。”(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正统年间中山小榄镇大商人何图源致富后,在小榄周围买土地二万余亩,收采成千上万石计的租谷。(注:《聂氏家谱》。)嘉靖十四年(1535),顺德商人龙翠云乘土地兼并日盛之机,“商业因之歇业,仅留自置田产八十余顷。”(注:《小榄何族发家史》。)明末,番禺沙湾商人何叔运捐买族田50余顷。(注:《龙氏族谱》卷7, 《华山堂祠堂记》。)顺治年间香山海商朱殿郎“起家产业十余亩,隆养双亲。”(注:《番禺沙湾农业历史调查报告》(原件藏佛山市档案馆》。)康熙年间中山小榄商人何世宁开酒店、米店经商赚钱购土地17顷和几十亩基塘。(注:《香山翠微韦氏族谱》卷14。)道光年间南海商人潘宽怀“既乃筑广厦,置田园”。(注:何仰镐:《据我所知中山小榄镇何族历代的发家史及其它有关资料》(原件藏佛山档案馆)。)道咸年间中山小榄何品益到64岁时,有土地60余顷。(注:何仰镐:《据我所知中山小榄镇何族历代的发家史及其它有关资料》(原件藏佛山档案馆)。)咸丰年间顺德商人吴敏购田种桑。(注:《潘式典堂族谱》卷6。)同年间顺德商人梁炜买田320亩。(注:《顺德县志》卷30。)宣统二年(1910)中山商人韦必达,买田十多亩。(注:《顺德县志》卷30。)
以上商人资本与土地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的事实说明:
(1)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 商人对求田问舍仍然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的学者曾认为,明嘉靖以后商人对于购买土地的兴趣降低转而热衷于手工业的经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广东商人资本的转化史实看,商人经商赢利后热衷购买土地,是商人资本转移的一个重要方面。
(2)由于商人活动不受地域限制,所以往往出现跨县、 跨省购买土地的情形。例如番禺商人林大楸到广西贵县买地等。这些商人便成为寄庄地主。
(3)商人购地投资主要目的是榨取封建地租, 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经营。从广东商帮的发展史看,商人购买土地后,并没有成为“农场主”,而是商人兼地主。如中山小榄的何图源,广州十三行的伍秉鉴、潘正炜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
什么原因使广东商人购地成风,商人资本与土地相结合转为土地资本呢?
第一,土地财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风险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确实能获得高额利润,迅速致富,但风险较大。万历时刘升认为“富商大贾,算及纤毫;穴金则有窃发之虞,怀璧则有戕身之累,唯有买田广土,无水火盗贼之忧。”(注:《韦氏族谱》卷4。)所以,当时的人积财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置田宅,长子孙,为室家计。”(注:《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第61卷,《田制部艺文二》。)于是商人增加财产,“自当以田地为上”了。
第二,土地能给商人带来高额地租收入。商人购买土地的主要目的是坐收地租,而明清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地租率一般是在50%以上。所谓“佃户就主贷田而耕,岁晚所得之半归之。”(注:《咸陟堂文集》卷9。)根据叶显恩同志的研究,以族田为例, 明初每亩租谷为二石四斗(500斤),沙田每亩30斤。此外,还有预租、押租、 批头租等额外剥削,其中押租一般为租额的20%。清中叶,番禺沙湾何族田的地租率甚至高达70%—80%。(注:丁仁长:《番禺续志》卷112,实业志。)所以,只要占有较多的土地,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地租收入,拥有更多的财富。
第三,明清封建统治者奉行“重农抑末”政策,把主要的手工业收归官府经营,对私人的手工业严加限制。以民营冶铁、铸铁为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广东布政司对民营冶铁规定“每处只许一炉,多不过五十人”。商人开矿冶炼须由官府批准,发给执照才能营业。“若有多聚炉厂及别省人称首者,即便拿获,钉解所在官司,以重治罪。”(注:丁仁长:《番禺续志》卷112,实业志。)此外,还不断增加矿税。嘉靖三十八年(1559)每炉纳银10两,不久增加税银5两,即增税50%。(注:《留耕名沙田总志》(原件藏佛山市档案馆)。)铁课税达到20%—30%,铁炉纷纷倒闭。如乾隆年间,佛山铸铁业有130炉户, 到光绪二年(1876)剩下40家,(注:孔能宽:《雍正归善志》卷2, 《事记》。)光绪九年(1883)剩下33家,(注: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0。)光绪十四年(1888),仅剩下20多家。(注:《光绪二年重修佛镇栅下天后元君古庙官神值事善信芳名喜 记各物签题工金各行工料杂项费用进支数同刊列碑记》(存佛山栅下天后庙内)。)因此,商人不愿扩大手工业生产,便把资本投向土地。
第四,封建宗法势力强大,影响和阻碍商业资本大规模向产业资本转化。虽然广东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但封建宗法势力也十分强大,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乡族集团拥有相当数量的陶瓷、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和铺舍、墟场等;另一方面乡族集团又对族众(包括同宗商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直接干预,用具有族法效力的家规宗法来束缚他们的经济活动。如石湾《霍氏崇本堂旅谱》明确规定:“不可去入窑砌砖,去挑砖入窑,及去樵山抬石,番禺等处入穴挑煤”等等。这些规定是以关心爱护族众为幌子,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官府“重本抑末”政策所起不到的作用。
由于以上原因,加上明清土地自由买卖之风日盛,以及“雇工不如坐吃地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致使广东商人不能摆脱与土地相结合的传统倾向,使得资本积累受到很大的限制,大量的商业资本无法直接转化为产业资本。
三、与高利贷结合成为高利贷资本
广东商帮高利贷资本崛起于清代,较之徽商、晋商,为时稍晚,但发展迅速。嘉庆之后,广东的典税收入已常列榜首,而由广东商人资本所转化的高利贷资本是明清高利贷资本的主要来源。
在封建社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本是三位一体的,地租、商业利润、利息,互相转化,循环不息。他们不仅私放钱债,就是巨大的典当也几乎为他们所把持,并作大宗的信用借贷。嘉庆二十二年(1817),顺德县商人何朝钰在佛山开中泰银店,店伙梁津昌暗中挪用10800两银,查帐时,谎称已经出贷,可见其借贷营运资本之大。(注:《光绪九年佛山清涌碑》(现佛山祖庙)。)有的鱼商设有“鱼栏”垄断鱼的销售,兼营发放钱债。渔民出海所需工钱食用等费“均须向鱼栏息借”。船归,则将鱼交售“鱼栏”。(注:朱檽《粤东成案初稿》(道光刻本)卷22。)有的商人墟头设当押店,墟尾设粮麸、杂货店。农民从其押店得到的押金,用来购买其杂货店的粮麸、杂货。收获后,农民又将农产品压价售给他,得到的现款用来赎回押物,(注:林仲芬、李达才:《旧社会广东的当押业》,《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以此循环剥削农民。有的商店则兼营借贷。南海县西樵黎物明“在本乡设店售沽酒米……遇告贷钱银者,亦必概然与之。”(注:南海《黎氏族谱》(宣统三年刻本),列传。)还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张龚华,“与贷者积至四十万金”,(注:番禺《张氏克慎堂家谱》。)可见其投入高利贷资本之巨。在这里,商人资本与高利贷完全融为一体。
四、与政治势力结合成为官僚资本
广东商帮从事商业活动发迹以后,往往步入仕途成为官僚地主,从而导致商人资本与政治势力结合而成官僚资本。
如冼氏宗族(注:冼氏是荃南独有之姓氏,系出自古代南越首领冼氏之后,南北朝时,著名的高凉太守冯宝之妻,被敕封为信都侯,隋封为宋康郡太夫人的冼夫人即出自这姓氏。)在宋咸淳末由南雄迁居南海县扶南堡(离佛山20里),明初始迁居佛山鹤园里。由于家业渐起,数代之后,政治上发迹起来,成为明清时期控制佛山冶铁业的巨族。霍姓中的一支从邻近的石头迁来,原系寒族,以孵鸭为业,景泰(1450—1459)年间,其先祖“昼则鬻布于市,暇则作扇,市取值以起家”。(注:《石头霍氏族谱》霍韬《又序》。)正德九年(1514),霍韬登殿试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霍氏也因而“气焰煊赫”,佛山经济命脉一度为其所控制。霍韬的儿子与暇也不得不承认,在其父官吏部时,“若佛山铁炭,若苍梧木植,若诸县盐鹾,稍一启口,立致富羡。”(注:《霍勉斋集》卷22,“碑记”:《寿官石屏梁分偕配安人何氏墓碑记》。)霍韬之后,这一家族科举蝉联,成为一方望族。李氏始祖广成,明初从邻近的里水迁居佛山细巷铺,因“得铁冶之法于里水,由是世檩其业。”嘉靖、万历时,这一家族的李同野(李待问的祖父),“因子姓繁夥,合室而爨六十余人。”因享有富名而招妒,幸得某“贤绅怜而身翼之”方免遭害。(注: 李待问:《李氏族谱》卷5,《广成公传》、《祖考同野公传》。)万历十二年(1904),李待问中进士,历官至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从此,这一家族官运亨通,成为佛山之名族。(注:陈炎宗: 《佛山忠义乡志》卷8,《人物志》《李待问传》;又卷6,《乡俗志·氏族》。)清代的佛山梁俊伟, “康熙间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商业遂振……至今子姓繁衍,科甲继起。”(注:同上书卷14,人物六,义行。)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先后操纵佛山经济的冼、霍、李、梁等旺族,都是先致富,后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完成了由商人资本向官僚资本的过渡,由商人转化为官僚地主。
五、与宗法势力结合成为宗族资产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然已相当发达,但肇于汴宋的(注:陈炎宗:《佛山忠义乡志》卷3,《乡事志》。)宗法势力到明中叶亦相当强大,因此商人资本往往与宗法势力相结合转化为宗族资产,其主要形式是购买土地变为族田。
族田被视为“祖垅可保,祠宇可守,达居宗人所由会聚,一脉联固,气魄雄壮,未许外人轻生窥侮”的物质条件。“堂产的厚薄,乎族运的盛衰。”(注:《香山翠微韦氏族谱》卷12。)而族田的相当一部分是由商人、富户捐赠。如明万历朝户部右侍郎李待问致仕归故里佛山后,与族老合资购买族田1顷90亩,“又置书田八十五亩”, 以作子孙之力学者膏火之资。(注:佛山《李氏族谱》卷7,《祀业》(崇祯刻本)。)东莞张祚恒于康熙四十年(1701)将自置田55亩(每年租银21两)捐赠为祠田。(注:《东莞张氏如见堂谱》卷25,《送田引》(民国11年刊本)。)顺德龙锡恩根据其父遗嘱,“送出田一顷六十二亩有奇,以为赡族之田,设立敬宗会名,每年收取租银分送阖族鳏寡孤独恤费。”(注:《龙氏族谱》卷1,《敬宗会缘起》(民国8年刻本)。)番禺县张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创办隆红茶行,贸易致富”之后,便“独立修葺祖祠,并置堂田。”(注:吴道镕《番禺县续志》卷2, 《人物》。)咸丰时顺德商人梁炜在江西、江苏经商致富后,也把商人资本一部分用以“建祠堂产,……为义祠祀费。”(注:郭汝诚、冯奉初:《咸丰顺德县志》卷2。)也有的宗族在族绅的倡议下, 由商人、富户带头认捐,族众各力捐资购买。如东莞员岗何真于明初除“置私田百余顷为义田”外,还“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祠其祖。”(注:〔明〕郭裴《粤大记》卷26。)
在珠江三角洲,各个宗族,除了有数量不等的族田外,还有铺舍、码头、瓦窑、墟肆等族产。所收得的祖堂银均可用来“放债生息”。族产未丰的宗族,则发动族人捐银,用来“生息裕堂”。如顺德《黄氏族谱》记载:乾隆九年甲子岁二月初一吉日,岭芝堂四房子孙等共议,捐得“银三百五十两司码,每年一分二算息,自甲子至癸酉共止十年,共长利息一千零八十七两二分八厘”。(注:顺德《黄氏族谱》(抄本),《建造祖祠乐助捐赀附息总录》。)利息已为本银的三倍。
由于宗法势力不断强大,广东佛山等地的经济日渐蒙上宗法色彩,宗法势力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也日益加剧。从明至清,各名宗巨族及由他们组合的乡族集团,愈来愈加强对主要经济部门各个行业的控制。如佛山的冼、霍、李、陈等巨族都先后长期插足于铁冶业、陶冶业等。这些名族的显贵者,是村宗族的族长、族绅,也是佛山乡族集团的成员,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往往通过宗族产业来干预佛山的经济。如嘉靖八年(1530)成书的《霍谓家训》中写道:“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经岁咨禀家长,以知功最。”(注:《霍谓家训》。)霍氏家族的“家长”通过所拥有的陶冶、炭铁、木植,以及其它“便民同利”的产业来干预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佛山经济的作用。
商人资本与宗法势力结合转化为宗族资产,其经商赚来的利润,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来培养封建宗法势力,加强封建的伦理纲常。其宗族资产愈是膨胀,封建性愈浓,商人阶层在经营商业、手工业中积累的资本,变成了加强自身封建性的手段。其宗族资产(宗族经济势力)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严重阻碍着产业资本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技术的传播,在某些方面对城市经济则起到摧残、破坏作用。尤其是不断增加封建宗族性活动的消费,以及购置祭田、修建宗祠等,加固了城市的封建性,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