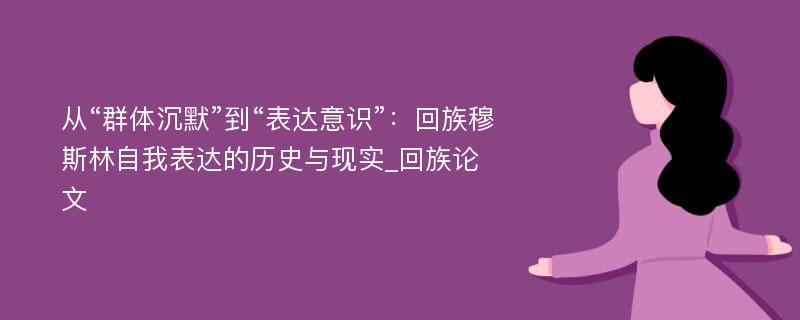
从“群体缄默”到“表述自觉”——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历史与当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回族论文,群体论文,自觉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2)04-0066-08
任何一个族群都生活于非孤立的群体关系网络中,认识我们自己并能被他族群所理解,这是族群间求同存异和谐共存的关键。认识我们自己就是以“内部眼界”审视和理性地把握己群,通过族群主体自觉的内部自我表述和文明对话,呈现给“他者”一个真实的自我。事实上,民族主体自我表述的自觉与否,关涉到一个话语权花落谁家的彼此较量与博弈。因为族群自我表述的非自觉性,以及表述能力的缺失,其后果是族群表述主动权的不自觉地丧失,“他者”外部眼界下强势的“客位”表述,使被表述主体易陷于其所构造的权力话语中。大众缄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憎的,因为大众也由某种宣称能启迪他们的无用的超信息构成,而这种信息所做的一切只是塞满可以表现的空间并让自己消失在无声的相应空间里。[1]26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道:“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他者”的表述作为“一种谋生之道”,如此,萨义德(Edward.W.Said)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著作《东方学》带给东方的不仅是西方话语霸权中危机降临的警醒,更是如何以民族的自我表述来自觉应对话语霸权的时代启蒙。作为学科研究的东方学,实为一种西方构造的具有“权威裁断”的理解东方的思维范式,一种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东方进行表述和表达的话语方式,“将东方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2]4。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始自唐宋以来阿拉伯等穆斯林族群的移居中华本土,族源的外来性和文化的异质性,使回族先民一踏上中国本土化的道路,就必须面对并处理好“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与“主位文化—客位文化”的关系[3],如何在强势的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既“入乎其内”,又能“不拘泥于其中”,在中华本土中坚守本色,在文化层面赢得“主体民族”的认可和谅解,避免误解和不信任招致的文化冲突。回族人选择了以自我表述来沟通彼此实现谅解,这种带有悲情基调的族群表述,在经历了长期的群体缄默后,才成为了回族穆斯林文化精英的“文化自觉”,只是这种以“文化释疑”等为表现形式的精英表述,历史证明其成效并不随人所愿,李普曼所谓西北回族穆斯林“熟悉的陌生人”的尴尬处境,带给回族穆斯林的是对这一历史话题的重新思考与反思。
一、“伊斯兰移植时代”“他者”表述的历史境遇
关于中国回族的历史渊源,史学家一般都追溯到唐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入唐[4]147。自此不断有阿拉伯商人(包括大食军士)来华并“住唐”,与来华留居的波斯人共同组成早期回族先民,拉开了白寿彝先生称之的“伊斯兰移植时代”,历经唐两宋元四朝五百年多年的历史,在族体由小到大的滚雪球过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穆斯林群体移居中国,承担了伊斯兰教移植中国内地的“载体”。作为伊斯兰文化的持有者,给中华本土带来一抹迥异的景致。早期的穆斯林被称为“蕃客”,受到中国统治者的礼遇,被集体安置在专门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称为“蕃坊”,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是未接受儒家文化实现文化涵化的“化外人”。为了谋求在新的异文化空间中穆斯林族群及其文化的持续生存与发展,早期先民开始了自觉的对本土文化适应,这种适应是坚持伊斯兰文化为内核,对本土文化进行有选择性的“借壳”,难以改变其鲜明的异质文化特色,充斥着国人的视野,造成着持久的“文化震荡”,引致的不仅是国人对诸如“夷狄”的想象,其自我本位的文化视镜透视出作为“他者”眼中的穆斯林文化,透过早期中国非穆斯林学人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略窥出两种异质文化接触和碰撞中,“伊斯兰移植时代”“他者”表述的历史境遇。
唐代作为伊斯兰文化东渐的初始,官方和学人都很少对伊斯兰进行记述。唐玄宗年间的杜环是中国文人认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第一人。《经行记》是他在天宝十年怛逻斯战役被俘虏,游历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诸国12年,回国写成的游记。此书作为中国学人关于伊斯兰文化的最早记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透视出早期汉族学人对伊斯兰文化的“他者”认知和表述。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装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止殴击。”
“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5]
陈垣先生认为,杜环《经行记》所记大食王告众语,绝似道教之《太上感应篇》。[4]149后贞元年间的贾耽《四夷述》和后晋张昭远等撰修《旧唐书·西域传》等史料中,其对伊斯兰历史与文化似是而非的主观认知与杜环相较相差甚远。到了两宋时期,穆斯林移居中土百年,成为留居中土“四世”或“五世”的“土生蕃客”。这一时期汉族学人对穆斯林及伊斯兰文化相对较多,与唐朝时期有所不同。
北宋朱彧《萍洲可谈》中记述过广州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他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称为“翟昙氏”[6],而“翟昙氏”实为中国人对佛祖释迦牟尼的另称,并认为先知穆罕默德“受戒勿食猪肉”,确系误解。南宋赵汝适的《诸番志·大食国》中记述:“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7]89其认知既有唐朝学人的特色,又将先知穆罕默德称之为佛,说麦加天房“后有佛墓”,昼夜有霞光,人不能近,近者合眼等,甚为迷离神奇。以后这样的记述就更为多见,如宋人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中有:“回回事佛,创叫佛楼,甚高峻。时有一人发重誓登楼上,大声叫佛不绝……”[8]184方信孺笔下的广州怀圣寺的唤礼塔:“……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9]7-8岳珂《番禺海獠》记述的宋代清真寺中“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10]125-126,却用“尚鬼”来理解穆斯林的信仰,并以“堂内有碑”为拜者皆向之的“像主”。周去非《岭外代答·大食国条》描述:“麻嘉是‘佛’麻妓勿出世之处,有‘佛’所居方丈,以五色玉结瓮成墙屋。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王皆遣人持宝贝金银施舍,以锦绮盖其‘方丈’。”[11]90-100可以看出,宋代汉族学人在表述中从传统汉人宗法性宗教观念出发,是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学语境中,以中国儒释道三教“佛”、“天”等概念为其表述工具,作为衡量伊斯兰教的标尺,如对礼拜寺中的宣礼塔称为“佛楼”,将宣礼声称为“叫佛不绝”,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称为“佛”,麦加是“佛”的出生地、“王与官民皆事天”等。这种“客位”视角的文化关照呈现的不仅是文化隔膜,其误解的表述中充满了自我想象。
蒙元时期,中西亚穆斯林的大量迁移中土,形成了回回人遍天下的分布格局。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蒙古统治者在“远华近夷”的统治策略中,在组成当时二等人色目人的“回回”地位较高。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观念中的歧视性认知根深蒂固。如元人刘郁撰《西使记》中记述了他在报达(巴格达)关于麦加天方的听闻,说麦加天方“内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师名癖颜八儿……”[12]这里胡祖为先祖易卜拉欣,天房为易卜拉欣父子所建,麦加禁寺中有他的立足处,但其并不埋葬于此。其“内有天使神”,纯属误解。元初周密《癸辛杂识》中记述杭州穆斯林葬礼中给亡人的沐浴,就有“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用绢或布等“裸而贮之,始入棺敛”。自口灌水是对穆斯林亡人沐浴的误闻误传,穆斯林对亡人实行土葬,说穆斯林“始入棺敛”,在元初,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显的彻底汉化。又说将洗完之水“聚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这种“客位”认知系道听途说,实为谬传。以后还有诸如此类的记述,及至明朝这样的表述多见于汉族文人士大夫的著述中。金吉堂先生20世纪初的研究中指出“回教入华为不期然而然之结果,而非有所为而来,故回教之真谛与内容,往往不为此邦人士认识;而传其教者每多保持闭关自守态度,如礼拜寺不容外人阑入,又不轻易为人进行进教礼以致外教人对回教每多悬揣,贻误错出。他指出了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的五种误解:有回与佛杂谈;误摩尼即回;误景、回、摩尼为一教;误景、火、回、婆罗门、摩尼为一;误犹太为回教”[13]35-38。“他者”对于异己于自身的客位文化的审视必然是戴着自己的文化镜片,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和带有自己的文化“先见”。[14]他者表述建构的“权力话语”的合法性,使得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从一开始就承担起解魅与解误的两种功能。
相反之下,这一时期,回族先民自我表述极为罕见。他们中虽有彻底“华化”的回族先民,作为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回族先民的代表,他们尽力在中国主流社会中借壳显华,并隐没自己的族群身份和宗教信仰,他们所追求的是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是以放弃本族群的独特文化身份为代价。这在宋及以后的元明时期表现得甚为明显,以至于非穆斯林这样说道:“吾曾目睹耳闻,某某名列子教,读书有成,毫无回教气象。遇酒即饮,遇物则食。使一旦身入科名,鹿鸣琼林,执教固辞,或者不可再如某某。当时名流,行事亦如之,总无拘束。”[15]86“华化”作为一种求生存的文化适应,只是单向的“华化”却忽略了真正意义上的族群适应应该是互为主体间性,而早期回族先民的沉寂却是难以开启互为主体间性的族群适应。马安礼在《清真释疑补集序》中感叹道:“……即本教中亦往往彼此聚讼,又何怪外人之鄙夷而仇怼之焉。”作为掌握汉语言和具备表述能力的回族知识精英,本应承担向他者自我表述的使命,但从他们现今留下的仅有诗作中,实难寻迹穆斯林文化的蛛丝马迹,使得这一时期族群自我表述的使命落到了穆斯林宗教职业者身上。在他们生活的蕃坊中,往往通过内部间的自我表述,体现在宗教人士内部的“瓦尔兹”及其宗教知识的宣讲,是以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为表述工具,却不以非穆斯林的“他者”为表述对象。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有穆斯林中的达失蛮(宗教职业者)无法变通地向他者表达《古兰经》的精神险遭杀身之祸。[16]348自我表述能力的匮乏足以可见,实属几百年里穆斯林群体缄默造成的悲哀。
二、“汉文译著”、“以儒诠经”与“文化释疑”: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开启
回族学界一般都将明朝中后期作为回回民族的形成时期,其分水岭的意义在于结束了一个时代。自唐宋元以来的“蕃客”和“回回人”,在伊斯兰教的维系下形成了一个内部异质多元外部有着共同认同符号的“想象的共同体”。及至明末清初,与回族先民时期截然相反的是,明初王朝的禁胡政策,实现了回族人原有母语的汉语更替,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新的汉语穆斯林族群,却要面对在本土化中自觉与不自觉中的群体文化失忆,回族穆斯林中自此,离经叛教者有之,传译阐扬教门者寥落,教门式微,信仰滑坡,“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17]512。据清初回族经学家马注《清真指南》卷一“援诏”中记述,康熙十八年己末,皇上狩于蠡城(今河北境内),登清真阁,见架置《古兰经》,诏寺人能讲者来,结果竟无人来应诏。由此可见,当时回族穆斯林宗教人才之匮乏,回族伊斯兰文化传承危机的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形态由传统国家的绝对主义帝国转型,程朱理学定为一尊的官方权威话语的形成,自明初以来就被强化的传统“华夷观”持续喧嚣,长期处于群体缄默与他者表述的历史境遇,在对回族穆斯林文化误解中加深着族群间的文化隔膜。早在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贞奏:回夷色目人,不得别造寺宇,崇奉满拉诸祀,以时(事)一统之盛。[18]及至清朝对伊斯兰教的歧视更为加剧,康熙年间,有人密报北京牛街回民夜聚晓散,图谋造反;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陈世绾和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等地方大员向清廷上疏,对回民的服饰、信仰等横加指责、干涉,妄加罪名,说回民“……左道惑众,律有严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为岁年,党羽甚众,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请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戴白帽者以违制律定拟”。大思想家顾炎武对穆斯林不乏有偏见,从“我族中心”立场出发,指责“唯回回守其旧俗,终不肯变。结成党夥,为暴闾阎”[19]。这种以华夏为标尺衡量他者的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传统“华夷观”在特定历史中的极端反映,在对异民族的强制同化中“祛异求同”,非我族类,其族必异,其文化必是异类。“当时士大夫之流不识吾教经典,不究吾教教旨,以为西域圣人非吾族类,不遵中华正朔,异言异服,斋戒沐浴,以为不知奉何鬼神,评话愈多,物议风起”,“而北高(金天柱,笔者加注)犹以世疑为隐憾”。[15]14汉人官员和学者歧视回回人的言论,使处于边缘境地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生存维艰。
赵灿《经学系传谱》中记述:“迄今百有余载,学业相承代不乏人,幸矣。吾清定鼎以来,学者之众,人才之盛,宛如列星。”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经堂教育的产生,它的意义在于与开始终结着一个族群缄默的历史,一个新的彰显着民族觉醒的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实践的即将开启。而表述媒介(汉语与文字)、表述主体(经学人才)和表述能力(博通他教)的具备,使回族穆斯林内部自我表述成为可能,它以“汉文译著”、“以儒诠经”和“文化释疑”为其特定时期的表现形式。
从民族自我表述的主体来看,他们都是有鲜明族群身份的回族穆斯林,有“以执教为己任”的宗教职业者,如马君实、马德新、伍遵契等;有“居庙堂之高”奔于仕途的政府官吏,如金天柱、唐景徽等;也有“处江湖之远”专心治学的“回儒”,如王岱舆、刘智等。他们大都受过经汉两学教育,有深厚的治学功底,他们中有些博览群书,学通四教(儒、释、道、伊),具有驰骋中阿学术,沟通并驾驭中阿文明间对话的能力。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有着“不背乎教,亦不泥乎教”的理融机圆的灵活适应性,作为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渐染的“回儒”,既有着虔诚的伊斯兰信仰,并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使命感,与前经堂教育时期“华化”的“回回”知识分子迥然相异,以学习中华文化来为我所用建设“己族”文化,在“己族”文化面临挑战与危机时,挺身而出,敢于担当,自觉地走在时代前列,“吾将上下而求索”。
从表述的实践来看,发端于金陵穆斯林学人王岱舆等发起的汉文译注活动,后辐射到云南、山东等其他各地。这些译著者其所受教育背景的差异,在汉文译注中译著风格也迥然相异,白寿彝先生研究指出:“王岱舆,张中和伍遵契,在译著上所走的路数,显然不同。岱舆是自有看法,自立间架,而把材料组织起来;张中是就着原书的材料,原来的间架,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遵契在译述以外,不肯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学者认为他们三者代表着明清回族穆斯林汉文译注的三种风格,其中王岱舆为代表的译著风格“自有看法,自立间架”,更具有创造性,作为有较高汉文化素质的一派,以他为代表的译著实践才可以称之为‘以儒诠经’[20],从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以汉文媒介来实现穆斯林文化自我表述,也有两种风格迥异的表述方式。前者是王岱舆、刘智等人援儒释伊建构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性理》,马注的《清真指南》,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等;后者以金天柱和唐景徽等为代表面向中国非穆斯林大众进行文化解误或释疑,如金天柱的《清真释疑》、唐景徽《清真释疑补辑》等。白寿彝先生认为,王岱舆至刘智阶段译著,“内容或转译一经或专述一理论的体系,其兴趣几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21]35,“上穷造化之玄机,中阐人极之妙旨,下究物理之异同。”(刘三杰)以中国主流的宋明理学的思想话语为参照,并以其具有的概念和术语,在本体论、宇宙观、人性论等层面来诠释伊斯兰信仰、教义教法和伦理道德等,其所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体系,义理深奥,文字古奥典雅,晦涩难懂。他们以文化借壳的诠经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向中国主流表述伊斯兰文化,也得到过教外人的认可。然而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是诠释正教,正本清源,给穆斯林大众以信仰和行为指南。这是他们诠经的初衷,其次才是面向教外。清乾隆时的伊斯兰教学者金天柱(1690—1765年)已意识到了这种自我表述的局限性,金天柱认为吾教之宗“然不能释者,非吾教之无人。盖缘吾教之前辈只作大言而不屑白此目前疑案”。因此,金天柱的表述实践,透过《清真释疑》一书中看到的是说理性的“释疑”而不是“诠释”。一书中,他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真主、神灵、礼拜、宰牲、饮食、仪容、沐浴、祭祀、历法、斋戒、天课、修行、丧葬等方面,清源正本,针对外教人对伊斯兰教提出的疑惑进行答解,深入浅出,从伊斯兰信仰、伊斯兰宗教典制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进行“释疑”,阐释清真与儒教“表里如一”、“理同道合”、“不可诬也”。这种释疑性的自我表述,其效果明显于前者。有学者认为以往先贤的著述多是为了“指点教内之人”,不大重视同教外人士的“口舌争辩”,该书则是第一部主动地向教外宣解自己教义的著作。[22]160起到了向教外介绍伊斯兰教,增进相互了解的良好作用。“释疑一篇……其中词旨显豁,大率取儒家道理,以证其说之旁通”[15]2,“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15]9。“无从一览而便知,而疑卒以不释”[15]18。有一汉族“拔贡生”陈大韶阅读《清真释疑》后,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豁然开朗,“余向者尝疑,回教之近于释也,乃言不祀鬼神以邀福;又以近于老也,乃云不求白日以非升。观其教是仍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教也,依然士农工商贾之人也,无以异于儒也”。甚而对伊斯兰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余又羡回之为教,坚定其心志,从未有流而入于释老者。盖以深明其弊,而实知其伪也。”[15]157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践,其共性是在理融机圆中跳出唯我独尊的封闭,是一种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对话”,以附儒并借其话语为表述工具,“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在异教同理的诠释中化解偏见达成谅解,把握中国汉文化语境中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表述主动权。白寿彝先生对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回族宗教学术运动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两种倾向(指“以儒诠经”中内容上的趋向儒家化和文字上的倾向典雅,笔者加注),一方面说,宗教学术运动是逐渐成为专门的研究;在另一方面说,它是逐渐地脱离大众了。”[21]76以后的历史中,各种毁教案的持续不断,中国回族穆斯林依旧遭遇着“熟悉的陌生人”的尴尬境遇。
三、民国以来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自觉与实践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思想革命打开了长期封闭的中国回族社会,回族穆斯林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穆斯林精英走上了时代的前列,在回族穆斯林大众中重新开启思想启蒙,对“己族”及其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检讨,掀起了民国时期的“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在知识界他们积极组织穆斯林社团,创办刊物,宣扬教义,启发民智,改变以往的封闭守旧,探索救国救族救教的真理。1917年,张德明、赵振武、孙绳武等人在北平成立清真学社,并创办《清真月刊》,以“阐明学理,研究学术”为宗旨,以达到“学术研究而愈理,宗教同可藉以昌明,社会国家亦胥获补益”的社会效果。[23]1925年,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发行《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开展“翻译经典,编辑书报,宣传教义,创设学校,设立藏书室”等文化学术活动。[24]1931年,王曾善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回教青年会,该会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为宗旨,在1936年,他们创设了“回民学术研究会”,发行《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1934年,马天英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发行学术研究刊物,编辑出版回族文化丛书,沟通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回族穆斯林中的有志之士创办了诸如《月华》、《清真铎报》等为代表的报刊近150余种,成为民国时期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学术阵地和话语平台,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发扬、宣传和传承了自己的文化,彰显了穆斯林为了寻求自我表述的文化自觉。
民国以来随着梁启超新史学革命的开启,在传统史学研究的“君史”向“民史”转向中,一门关于中国“回教史”的研究发生了。它以《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刊发汉族学者陈汉章先生的《中国回教史》一文为滥觞,1928年,另一位汉族学者陈垣先生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他们首次系统地阐释了中国伊斯兰史,其开山之功,实有抛砖引玉,以启山林之效。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回教史”研究非穆斯林学者的捷足先登,不仅意味着新史学革命的成功,也蕴含着长期文化隔膜造成的历史惨痛唤醒着汉族有识之士,以理解他者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敏锐地指出:“回教文化研究的本身,便是在文化方面沟通回汉的正面工作。因为从文化方面讲,回汉间的隔阂,其问题不在于回人对汉人文化的不了解,而在于汉人对回人的不了解……所以想在文化方面沟通回汉,我唯一的概括的意思是要提倡回教文化本身的研究。”[25]151非穆斯林学人的学术实践和呐喊,似一股清风吹醒了回族穆斯林学人的“文化自觉”。继而有马以愚、金吉堂、傅统先、白寿彝等一批回族穆斯林学人自觉地走上了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的道路。这既是对起始于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运动的继承,也是把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纳入学科研究的起步。1935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统先《中国回教史》,1941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1943年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等。1938年时,白寿彝、杨敬之等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1941年改名伊斯兰文化学会),积极开展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和译著活动,出版回族伊斯兰文化丛书10余种。1939年春,在重庆也成立了中国回教文化研究会,团结当时中国回族穆斯林学人,开展学术研究,形成了民国时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大好局面。
相较于清际的回族穆斯林知识精英的表述活动,民国时期可以视为新的发展阶段。在受到当时国际国内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创办学术研究平台,从事回族伊斯兰文化研究。从研究的队伍来看,既有民间穆斯林精英的自觉参与,也有学院派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在研究内容上,既对回族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也积极对《古兰经》等伊斯兰经典进行翻译,尤其是对中国回族历史渊源等进行澄清。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丰硕,质量较高,成为非穆斯林理解回族伊斯兰的历史与文化的首选读物。这一时期一批非穆斯林学者参与到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行列,与历史上非穆斯林学人对回族穆斯林带有偏见和误解的他者表述相异,他们的研究减少了自我想象的成分,为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提供一种他者意义上的文化参照。
四、新时期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持续不断,知识阶层的学术研究和民间草根的表述自觉较为高涨。随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学术活动等遭受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以来的信仰荒芜,使得穆斯林大众在国家宽松的新环境中,一改沉寂和缄默,从知识界自觉地恢复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到穆斯林民间社会自发地创办刊物,使回族穆斯林的自我表述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80年代初期到21世纪的初十年,我们回溯和梳理这三十年的自我表述历程,不管是在表述的主体,表述的媒介,表述的范围,以及表述的民众自觉上,彰显出了时代新特色。
从回族穆斯林学术研究的表述类型来看,从70年代末的恢复,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发展,回族穆斯林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在研究主体上,形成了穆斯林学者与非穆斯林学者的研究队伍,其中回族穆斯林学者研究队伍壮大。他们既有解放前已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健将,如纳忠、白寿彝、杨志玖等;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长起来的学术骨干,如马通、杨怀中、林松等;也有自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50、60、70、80回族穆斯林学人,他们中有出自于学院派的博士和硕士,他们中也有留学于阿拉伯世界,经汉两通的穆斯林归国人员,分布在中国各地高校和科研单位。新的时期里,穆斯林学人重新肩负其自我表述的使命。自80年代伊始,他们积极倡导并先后创建起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平台,诸如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研究所、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等专门从事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机构建立;也积极创建学术研究的公开刊物,扩大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学术影响,如1991年回族学人杨怀中先生创办的公开学术刊物《回族研究》,还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也先后创办了关于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连续性出版刊物等;也有地方性出版社以打造回族伊斯兰教学术著作为其特色,如宁夏人民出版社等;在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高校的学科建设中,回族伊斯兰教作为重点学科中的特色研究方向,其民族学等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中,都设有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及其文化研究方向。在学术研究成果方面,自80年代以来,回族穆斯林学者潜心研究,成果卓然。出版的一批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和工具书等,具备一定的水平,有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影响。
这一时期,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的时代自觉在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中也呈现出来。在文学领域,萌芽自50年代发展于70年代的回族文学异军突起,一批穆斯林作家在对民族的文化自觉中,自觉地回归到了回族作家回族化创作的轨道,他们在经历了80年代的文化浅描后,将回族文学创作推向了文化深描阶段。在回族文学旗帜高扬中,回族文学创作承担起回族穆斯林自我表述时代任务,2010年以来,随着“穆斯林文学”口号的提出,以文学作为回族穆斯林文化表述的呼声更为强烈。在艺术界,一些回族艺人们,在回族舞蹈、歌曲、影视等领域跃跃欲试,囿于人力、能力等条件的限制,高质量的作品迟迟不发,低水平却又难登主流媒体的大堂,使得这种最具有广泛传播效力的表述方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甚为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的研究自觉地提升到了文明对话的表述高度。它是穆斯林学者走出封闭,向更广阔的空间发出穆斯林呼声的实践,“理解是打开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文明交往的深层次之谜”[26]4。这种行动自觉在2000年来,随着西方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炉,穆斯林学者挺身而出,以中国穆斯林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与中国其他各宗教间展开深入的对话,以求在相互了解中相互尊重和谐共存。2002年8月8—10日由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在南京举办的“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他们以“文明对话的动力与障碍和历史上的回儒对话的意义与研究”为主题,展开了“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对话”,是中国穆斯林学人与时俱进,在与他文化的平等对话中追求和谐共存的时代自觉。随后在银川(2006)、香港(2009)、北京(2010)、南京(2010)等地召开的“回儒”、“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的文明对话,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中国回族的穆斯林学人在“认识对方、承认对方存在这个基本信念,要有了解对方的意愿”[27]的基础上,从开阔心胸中走出自我中心,摆脱强势话语的理念束缚。既以“他文明”为鉴和参照系,又以伊斯兰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进行自我文化表述,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构建文明间的“共同话语”,中国伊斯兰文化越来越多地赢得“他教”的尊重和认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穆斯林报刊在改革开放的沐浴中先后再次出现,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特别是民间刊物的发展尤为迅速,先后在全国各地由清真寺、穆斯林社会团体、中阿学校和有识之士等创办了近百种报刊[28],影响较大的有《穆斯林通讯》《开拓》《甘肃穆斯林》《阿敏》《上海穆斯林》《济南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研究》等。他们以“继承先辈们那种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挖掘和弘扬优秀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倡导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教育素质为己任,为穆斯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鼓与呼,为穆斯林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大造舆论,为传播穆斯林经济文化信息、促进穆斯林经济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穆斯林民间的尔林们和有志之士,在弱势的边缘突然地崛起,强劲的自我表述的言声在民间传播开来。他们呼应着张承志先生“草根表述”的倡导,打破了表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贯专利,呼唤和启醒民众的表述自觉,使作为一种正义和价值的文明内部的发言成为时代共识,文明主体的自我阐释,在“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彰显中,为中国回族穆斯林拓开新的话语空间,形成了民间学术阵地的自我言声的良好势头。
新千年以来,回族穆斯林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在对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中实现着传统交流和表述方式的时代转型。中国穆斯林网站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具有了相当的数量和规模,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回族穆斯林族群开始借助网络发布信息、表达自我、寻求互动、凝聚认同的新方式。如中穆网、伊斯兰之光、伊斯兰之声、穆光文化、东方穆斯林、赛俩目艺术网、三亚伊斯兰在线、圣传真道伊斯兰网、伊斯兰之窗、中国穆斯林等。网站创立者匠心独运,以追求知识和学习交流为目的,在网站内容上,既有古兰圣训和教义、教法知识,伊斯兰教历史等诸多内容。如“中国伊斯兰之窗”网站,就建有动态、经训、伊斯兰与生活、人物、学术、教育、书库、录音课堂、学习阿语、青年生活、图库、影音、留言、杂志、问答、文苑、服务、山牧专栏、资料介绍、宗教信仰、综合下载、教法问答翻译、伊斯兰历史、穆斯林妇女、了解伊斯兰、百科全书、mp3古兰经下载、论坛等几十个版块。这些网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图文并茂,提供视频和音频资料,便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了解和学习伊斯兰宗教知识。网站中论坛版块,便于读者对感兴趣的宗教知识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论坛的发帖频率和参与率较高。同时有些网站还建有英语、汉语、阿拉伯语等几种语言,适应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者浏览和学习。应该说,中国穆斯林网站的出现,向外界打开了一道开放的窗口,便于非穆斯林了解穆斯林文化,将新时期中国穆斯林自我表述带入一个新的境地。
收稿日期:2012-05-25
标签:回族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回族服饰论文; 回族风俗习惯论文; 文化论文; 清真饮食论文; 读书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古兰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