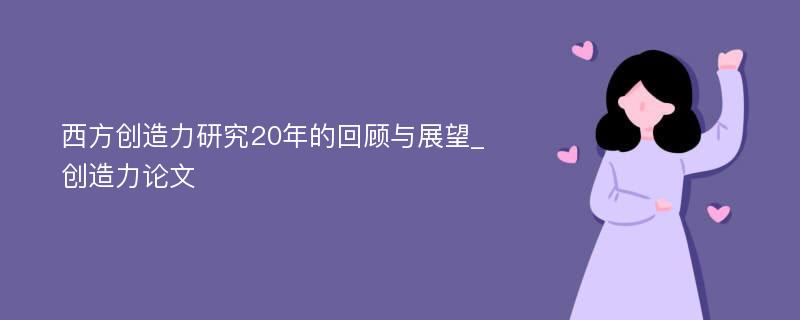
西方创造力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305
创造力研究(creativity research),从广义上理解,应包括“创造心理学”和“创造工程学”;狭义的理解,则指的是侧重于理论研究的创造力心理学。①西方创造力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1950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Guilford)在就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时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力”演说,自此拉开了科学研究创造力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力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进展,并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一、创造力研究的简要回顾:4P框架
究竟什么是创造力?这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分析有关创造力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不同,理论依据不同,研究方法不同,判断标准不同,对创造力的认识也不同。难怪有些心理学家抱怨:“文献中关于创造力的定义如此不一致,以至于给创造力下定义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对创造力的认识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研究框架至少包括4个方面:创造性个人(person)、创造性过程(process,)、创造性产品(product)和创造性环境(environment或place)。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创造性个人
就创造性个人而言,主要探讨高创造力者所具备的人格特质。巴龙(Barron)和哈林顿(Harrington)将其概括为:有较高的审美能力和广泛的兴趣,喜欢复杂的事物,精力旺盛,具有独立判断能力,自主性或独立性较强,有自觉力,自信,有能力处理或适应在自我概念中明显对立或相互冲突的个性特征,以及坚持自己的创造力。②史登堡(Sternberg)在创造力投资理论(investment theory)中提出的人格特质包括:面对障碍时的坚持,愿意冒合理的风险,愿意成长,对暧昧不明的容忍,接受新经验和对自己有信心。③奇凯岑特米哈伊(Csikszentmihalyi)对91位创造性人物进行深入访谈后,发现这些创造性人物有许多共同的人格特质,它们是10组明显正反相互对应的人格特质:精力充沛——沉静自如、聪明——天真、责任心——游戏心、幻想——现实、内向——外向、谦卑——自豪、阳刚——阴柔、叛逆——传统、热情主观——冷静客观、开放——敏锐。④
2.创造性过程
就创造性过程而言,主要探讨创造力产生的过程,即着重于认知心理过程的探讨。这与心理学研究中的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或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是息息相关的。如早期沃拉斯(Wallas)提出的创造过程四阶段模式:准备期(preparation)、酝酿期(incubation)、豁朗期(inspiration)和验证期(elaboration)。奇凯岑特米哈伊从生物进化和文化演化的高度出发,提出了创造力系统理论。⑤该理论认为,创造力的产生是一个系统内部个体(individual)、范围(domain)、领域(field)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鲁巴特(Lubart)指出,一般学者对于“酝酿期”有较多不同的看法,认为“酝酿期”一词过于笼统,事实上“酝酿期”之中还蕴含着许多认知的思考过程。因此,鲁巴特强调,从初期沃拉斯的四阶段模式到近代更深入的“次级历程”(subprocesses)的研究发展历史来看,对于创造力过程研究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⑥
3.创造性产品
就创造性产品而言,主要指创造性过程中产生的高创造性成果或产品。“新颖性”(originality)与“适宜性”(appropriateness)是创造力产品研究中的普遍内涵。艾曼贝尔(Amabile)指出,大部分学者普遍认同施泰因(Stein)在1953年给出创造力定义:创造力是导致了某种新颖的结果,这个新的产品是有用的、立之有据的、或令人满意的。⑦这一定义就强调了产品的“新颖性”与“实用性”。史登堡也认为,创造力是一种创造产品的能力,这种产品既新颖(独创的、预想不到的)又适宜(不超出现有条件的限制,且产品是有用的)。⑧此外,他根据创造力产品的概念提出了创造力的推力模式(the propulsion model of creative contributions),⑨指出在领域(field)之中有8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助力,可将领域从原处推向不同的境界。这8种助力分别为:复制模仿(replication)、重新定义(redefinition)、前向推移(forward incrementation)、加速前向推移(advance forward incrementation)、复位方向(redirection)、重新建构/复位方向(reconstruction/redirection)、另起炉灶(reinitiation)、整合(integration)。根据这些不同创造性产品推动领域的动态历程,史登堡的创造力推力模式为创造力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视角。
4.创造性环境
就创造性环境而言,主要指影响创造力的环境因素。⑩创造性环境最初是指环境对创造者进行创造时产生的压力(press/pressure)。最近,有学者将其更积极地解释为创造者的说服力(persuasive power),也就是说服他人接受或认同产品的重要性。阿瑞提(Arieti)相信,某种文化环境比其他文化环境更能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这种能较好地促进创造性发展的文化环境和这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时代可以被称为“创造基因”。
艾曼贝尔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以创造动机为核心内容研究影响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因素,诸如教育环境、工作环境、家庭影响、社会影响、政治影响、文化影响、以前的活动、玩耍和幻想以及物理环境。
史登堡和鲁巴特提出了创造力投资理论。他们认为,创造力的产生需要6种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资源: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和环境。如果缺乏环境的支持,创造力的前述品质就是空话,创造力也就不可能产生。
奇凯岑特米哈伊从更为广泛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将创造主体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提出了创造力系统理论。他认为,创造性并非是在人的头脑中产生,而是在人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它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现象。近年来,哈林顿认为,支持性的环境对创造力而言,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
伦科(Runco)提出,环境本身就是创造力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促进创造力提高的重要的环境特征是宽容、有节制以及资源丰富。很多研究尤其重视学校教育环境对早期创造力开发的重要意义,认为适宜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儿童创造力的提高,并提出了教师的任务是“播种”,即为儿童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
随着创造力研究的深入,创造性社会心理学成为创造力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取向,已经取得了许多令人颇感兴趣的研究成果,拓宽了创造力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如探讨人际环境、学科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与创造力的关系;构建环境因素影响创造力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包括人类创造性的生态学理论(ecology of human creativity)、创造性的系统观点(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内在训练观点(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进化系统观(evolving system)、创造性行为的交互作用模式(interactionist model of creative behaviour)和创造性的成分模式(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
在早期的创造力研究中,研究者将创造力或者当作一种个性特质,或者当作一种一般能力,他们往往只强调创造力的某一个层面。(11)目前,研究者已认识到,创造力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很难仅依靠某种单一的概念框架获得解释,而应将创造力看作是一种认知、人格和社会层面多因素的整合体。如艾曼贝尔提出一种创造力的三成分模型,认为创造力是工作动机(task motivation)、相关领域的技能(domain-relevant knowledge and abilities)、相关创造力的技能(creativity-relevant skills)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工作动机是人格因素,有关领域的技能是创造力的知识基础,有关创造力的技能是认知风格方面的特征。(12)史登堡在其“智力三元理论”(triarchic theory of intelligence)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intelligence)、智力风格(intelligence styles)、人格(personality)三位一体的“创造力三侧面模型”(three-faced model of creativity)。(13)费尔登豪森(Feldnhusen)提出创造力包括三个方面:知识基础、元认知技能和人格因素,即获得创造力应具备一个广泛的知识基础及特定领域的技能、一套加工新信息和使用原有知识基础的元认知技能,以及一系列态度、禀赋、动机等人格因素。(14)
二、创造力研究的最新进展:多学科视角
创造力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系统化的演进过程。早期的创造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6大取向,即神秘主义取向(mystical approach)、实用主义取向(pragmatic approach)、心理动力取向(psychodynamic approach)、心理测量取向(psychometric approach)、认知主义取向(cognitive approach)和社会人格取向(social-personality approach)。(15)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多采取融合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创造力,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创造力内隐理论、创造力系统理论、创造力投资理论、创造力元理论、创造力培养理论,(16)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也日益纳入创造力的研究视野。
1.创造力生理研究的最新进展
创造力的生理研究是创造力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础。应该说,生物领域的研究并没有明确地关注创造力,而是潜心于与之相关的行为和倾向。斯佩里(Sperry)著名的脑半球实验是创造力生物学研究的典型例证。有关右脑具有创造力的理论,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创造力实际上需要大脑左右半球的相互作用。创造力并不总是或完全是一种直觉,甚至也不完全是独创性。相反,创造力表现为独创性与适宜性、直觉与逻辑性的统一,它需要大脑左右半球的相互协作。霍佩(Hoppe)和凯尔(Kyle)对斯佩里的患者进行研究后指出,这是一种情绪失调症(alexithymia),即患者只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事物进行描述,而不是表达他们对事物的反应;他们的想象力也相对贫乏。这方面的研究多反映在脑电图(EEGs)上。(17)霍佩和凯尔对联合部切开术(commissurotomy)患者进行研究后发现,当个体欣赏音乐或观看电影时,右脑颞叶区(T4)几乎不活动,左脑也相应地不活跃(F3、T3),而左脑顶叶区的P3却异常活跃,右额叶(F4)与P3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受控被试的F4与T3之间存在一致性,这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构:它能够促使右脑的有效理解转化为左脑的口头表达。
马丁代尔(Martindale)和汉森福斯(Hasenfus)指出,在创造性过程的不同阶段,EEGs的活动是变化的。他们检测了位于右脑颞叶区的EEGs,结果发现,至少在杰出创造者身上,豁朗阶段的α波要比验证阶段多。而且,较低水平的脑皮质唤醒允许散焦注意(defocused attention),这有利于提供独创性的联想。戴蒙德(Diamond)等人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研究后指出,左脑39区的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的平均比率显著小于对照组科学家的;而在左脑其他区域或右脑则不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分析认为,爱因斯坦的大脑皮层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新陈代谢需要”(metabolic need),并讨论了大脑皮层在联想思维和理性认识中的作用。梅德尼克(Mednick)等研究者描述了联想过程是如何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18)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额前区(prefrontal lobes)及其在创造力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阿瑞提在其创造力理论中论及了额前区,并首次指出,当整个大脑(而不是大脑某个半球)参与时,不可思议的合成(magic synthesis)发生了。(19)埃利奥特(Elliott)和诺兰德(Norlander)也对额前区进行了研究。随着科学(尤其是脑科学)的发展,有关额前区的研究假设将会很快得到最新方法论的精确证实。
2.创造力认知研究的最新进展
创造力的认知研究肇始于吉尔福德。托兰斯(Torrance)对吉尔福德创造力结构理论进行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著名的“创造性思维测验”,提出了创造能力、创造技巧与创造动机三者兼备才能产生创造行为的创造力结构模式。史登堡在其“智力三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智力风格、人格三位一体的“创造力三侧面模型”。芬克(Finke)等人提出了创造性认知过程的二阶段模型,即“生成—探索”模型(geneplore model)。(20)该模型由生成阶段(generative phase)和探索阶段(exploratory phase)两个不同的加工阶段组成。在生成阶段,人们要建构一种叫作前发明结构(preinventive)的心理表征。这种表征具有许多促进创造性发现的特征,因此前发明结构是最终的创造性产品的雏形。在探索阶段,人们要寻找有意义的方式来解释前发明结构,从而获得创造性的发现。在“生成—探索”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者对“概念扩展”(extending concepts)、“概念联结”(conceptual combination)、“创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ery)等创造力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得到了许多重要发现。此外,罗斯(Rose)基于量子力学理论提出了创造过程的模型,埃伯特(Ebert)提出了创造过程的认知螺旋模型。
注意力分配对创造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尤为重要。沃勒克(Wallach)经过研究指出,广泛的注意力分配有助于发现新颖、独特的观点。注意力分配广泛的人具有以下特点:信息刺激的范围更加广泛,记忆痕迹更加广阔,对偶发线索的利用更加敏感,在信息接受、检索等方面的注意力分配更加广泛。马丁代尔和格里诺(Greenough)也注意到了注意力分配问题,认为这发生在大脑皮质低水平唤醒的时期,并导致大量的联想。史密斯(Smith)等人的研究指出,评价和压力常常直接导致紧张不安,并分散注意力,这对创造性思维极为有害。(21)
知识在创造性认知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认为,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当解决问题时,陈述性知识(事实性知识)为个体提供某些判断,但同时,如果个体仅仅关注这些既定的知识,则会妨碍创造性思维。另一种知识是程序性知识(包括策略),而策略常常用于解决重大问题。史登堡对知识与创造力的关系问题作出了必要而恰当的揭示。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对某方面一无所知,他也不可能提出新见解。……同样,一个人的知识太多也可能是件坏事(尽管不都是这样),他可能画地为牢,一点不敢超出现有的规范和观点。因此,大多数创造是由该领域中相对而言的新手作出的,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得不少,但也不多。”(22)
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有关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研究。佩舒特(Pesut)提出创造性思维模型,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一种自我监控的元认知过程,通过自我监控(自我监督、自我评价和自我强化),个体发展其元认知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更好地监控创造过程中自己的行为。(23)史登堡描述了创造力的三个基本元认知过程——计划、监控和评价认知操作。他还指出了这个过程的三个主要的元成分(metacomponents)——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确定问题、形成策略并对问题结果进行心理表征的选择,以及三个与创造性过程有关的知识获得成分(knowledge-acquisition components)——选择性编码、选择性联结、选择性比较。弗尔登豪森正式将元认知技能作为与知识基础、人格因素相并列的创造力的三方面之一,认为创造性过程中应当有一系列加工新信息和使用原有知识基础的元认知策略。(24)
除此之外,创造力认知研究的其他重要层面还包括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想象(imagination)、酝酿(incubation)、顿悟(insight)、直觉(intuition)、“两面神”思维(janusian processes,即同时考虑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逻辑(logic)、隐喻(metaphors)、警觉(mindfulness)、误判(misjudgement)、感知(perceptive)、联觉(synaesthesia)等。近来,量子论(quantum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非线性动力学(nonlinear dynamics)也常被用于创造力研究,如罗斯基于量子力学理论提出的创造过程模型、戈斯瓦米(Goswami)受量子力学理论的启发提出的创造力统一理论。(25)
3.创造力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
儿童和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研究是创造力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托兰斯发现,在创造性思维领域存在着“四年级下降”(fourthgrade slump)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大约只占50%的比例,不具有普遍性。在创造力发展研究中,个体创造力的发展阶段日益受到重视。莱什纳(Lesner)和希尔曼(Hillman)提出,个体的创造力发展经历了创造性的内部丰富阶段(creative internal enrichment)、创造性的外部丰富阶段(creative external enrichment)和创造性的自我评估阶段(creative selfevaluation)。(26)
多数研究表明,创造潜能可能与家庭背景(family background)、出生顺序(birth order)、家庭规模(family size)、兄弟姐妹数量(number of siblings)、年龄间隔(age gap)等相关,家庭倾向(tendencies)和价值观(values)也可能发挥作用。(27)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要数出生顺序研究,以及居于兄弟姐妹中间位置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保持反叛精神的频数研究。反叛(不墨守成规)的孩子并不一定能进行创造性工作,但是,多数创造性个体具有反叛和抵制传统的精神。
创造力也存在着性别差异。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具有“男女双性化”(androgynous)气质的个体比只具有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的个体更具创造力。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男女双性化”气质的个体具有更强的选择性和灵活性。(28)早期的家庭经历能够帮助我们解释创造力的性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明显地反映在男女的生命全程之中。赖斯(Reis)研究了生命全程和职业生涯中男女创造力的差异,认为人际关系对女性取得创造性成就中的作用要大于男性。(29)在她看来,女性需要有意识地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投身于创造之中。
4.创造力教育研究的最新进展
教育对创造力的影响得到研究者较多的关注,因而也就成为创造力研究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在课堂里,期望年幼的学生顺从一致(安静整齐地坐在座位上,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导致了“四年级下降”。这可以从个体的生理变化来解释:学生的神经系统似乎对规范变得敏感起来,独创性的减弱也反映了压力下的顺从(这是许多教育环境的特点)。学校里的多数测验主要是聚合思维(仅有一个正确答案),发散思维则被忽视。
在教育中,个人和团体往往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传统的教育技能上(如识字),而不是创造性技能上。鲁本松(Rubenson)和伦科对此进行了解释:相对于识字和其他传统教育的技能而言,创造力是一项风险投资,回报相对较少。同样,雇主更喜欢雇用取得公认的教育机构学历的求职者,而不会选择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具有创造性的应聘者,原因之一就是前者对组织机构的贡献更为明显。因此,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将创造性技能整合到学校课程中。(30)
杜德克(Dudek)等人对1445名小学生的发散思维进行研究后指出,不同学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tnomic status,SES)的高低紧密相关。他们还发现,学校内部的课堂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中间课堂”(intermediate classroom)对发散思维有影响。(31)这项研究再次证实了沃勒克和科根(Kogan)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经典研究。他们也非常强调“中间课堂”,认为只有在宽容、自由的氛围下,创造力才能激发出来。教师自己就是学生的潜在榜样,他们的期望对学生的创造力具有很大的影响。(32)有趣的是,创造力也有助于教师提高自我效能感。
三、创造力研究的未来展望:多元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力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很多研究主题逐渐被重视并证实;新技术、新主题和新应用日益出现,创造力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
1.创造力研究日益多样化和综合化
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发展与深入,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不同领域的创造力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创造力的差异仅仅表现在思维方式和认知风格的不同上。早期对创造力的研究多是对艺术家、建筑学家等杰出人物创造力的关注,多元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33)的提出,使创造力研究日益由特殊领域(杰出人物)走向日常生活领域(普通人),逐渐关注普通人的创造潜能。在最近的研究中,创造力研究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如生物学中对脑电波(EEG)与创造力的研究、临床学中对精神病与创造力的研究、经济学中对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创造力的研究。行为、生物、临床、认知、发展、经济、教育、历史与历史文献、组织、心理测量和社会等众多学科领域纷纷对创造力进行整合研究。(34)
可以看出,多样化和综合化是未来创造力研究的趋势。这一趋势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潜在优势:(1)克服了以前单一的学术性研究所固有的弊病,同时,其多元化的特性必将在创造力研究中具有更强的解释力;(2)提供了看待创造力“两难问题”的新视角,即创造力是一种普通的过程还是一种非凡的过程;(3)有助于对不同的创造力研究方法进行融合,从而把创造力与心理学诸多领域的研究联系起来。(35)这一趋势为创造力研究提供了更加崭新、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一方面,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创造力的本质及其机制,提出了众多的理论;另一方面,利用各学科的原理,综合考虑影响创造力的各种因素,整合以往的研究结论。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还应注意不同领域中创造力的特殊性(因为不同学科能力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性),大力开展特殊领域创造力的研究,提出不同学科领域的创造力理论;同时,还应注意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创造力的差异。这样,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指导学科教学中创造力的培养,而且能够加深我们对创造力本质的理解,以便更好地进行综合。
2.创造力研究从个体走向团体
有关创造力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条研究路线:一是将人的创造视为某种特殊的心智历程,而侧重于创造性思维一般规律性的探索;二是视创造为个体的某种特殊能力倾向,侧重于对创造个体的人格品质或特征的研究。(36)无论是认知途径还是人格途径,对创造力的研究都是从个体角度进行的,遵循的是客观化、量化和因素分析的研究方法,但专注于个体自身因素对创造力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如对个体认知机理的探索,一方面越来越深入到揭示微观的脑神经生理机制层面,另一方面则进入了对人工智能或机器发明的研究;而对创造性人格的研究,目前也并不能完全确认某种个性特征一定就是某种创造性品质的体现。所以,传统的个体层面的创造力研究虽然为理解创造力作出了贡献,但还是越来越失去这一领域的中心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力研究必然从个体走向团体。
团体创造力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目前已成为创造力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新热点。(37)近20年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文献日益增多。总体来看,其中侧重于测评的实证研究居多,如较早期埃克瓦尔(Ekvall)设计的创造氛围问卷(CCQ),其后伊萨克森等人发展的情境态势调查表(SOQ),艾曼贝尔等人的KEYS表等;而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相对较弱,相当多的文献是对“头脑风暴法”研究案例的分析,对其他理论问题的探讨仅见于库尔茨伯格(Kurtzberg)和艾曼贝尔的研究之中。无论如何,团体创造力研究的日益兴盛,开辟了创造力研究史上的新时期,开阔了揭示创造力本质研究的新视野。
3.创造力研究从科学主义走向人本主义
由于西方心理学发展史的渊源,以为只要基于科学手段就能解决有关创造力研究中一切问题的思想,在创造力研究中十分明显。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中存在的“科学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有关创造力本质的问题上,由于片面注重因素分析与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而导致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偏颇;(2)在有关创造力的具体问题研究上过于“原子论化”,因而导致忽视人的整体性特征与人的巨大潜能作用的偏颇;(3)在对创造性思维(如直觉)问题的研究上,过分强调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因而导致以机械论观点来看待人的创造现象的偏颇。(38)可以说,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这种学科内部的科学主义倾向是造成其理论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的整体论创造观对于创造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具有启示性意义。简而言之,以人为本的创造观就是视创造力为人的一种内在本性,是人的本性充分展开时所必然会达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创造观主要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得以体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重视人的尊严、价值、主体性,从人性的角度、从健康人的人格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创造力。人本主义创造观具体研究以下方面:(1)创造力本质观,即创造力是人的内在本质或本性的体现,也就是“人人具有创造力”,这实际上是创造力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meta-problem);(2)创造力发展观,即创造力是健康人格的副产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本主义创造力发展观是一种人格发展观;(3)创造力教育观,即以人为中心,培养人格健全的、人性充分展开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具有创造性的人;(4)创造方法论,亦即一种整体动力论(holistic-dynamics)的观点。也就是说,从整体人的人格发展来看创造力,并视创造力为整体性人格的一种副产品。(39)
4.对创造力本质和机制的研究仍需加强
“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创造力是应用的最不严格的术语之一,因而也是含义最模糊不清的术语之一”。普遍认为,创造力是一种人类才能(capacity),但作为对人类才能的一种描述,创造力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尚存在“能力”(ability)、“专长”(expertise)、“胜任力”(competency)等描述个体才能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研究者对上述诸概念的区分不甚了解,对它们的使用也相当混乱,这进一步模糊了创造力的含义,因此,只有明晰创造力与这些概念的区别,才能在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内理解创造力,弄清到底什么是创造力。有学者对“创造力是否是一种能力”,“创造力是否需要专长”,“创造力是否以胜任力为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创造力不能简单归结为一种能力;创造力也不可简单归结为一种习得的专长;创造力以胜任力为基础,是一种比胜任力更复杂的现象。(40)在这种背景下,不直接探讨“创造力是什么”,而集中分析“创造力不是什么”或“创造力不像什么”,这种对创造力外延的缩小对于创造力本质的认识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尽管创造力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新颖性是创造力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创造力与某种形式的精神病理学有联系,但创造力不是一种精神病理学;创造力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但并非所有创造力都蕴涵着问题的解决,也不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创造力。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如创造性过程是目标导向的还是探索性的;创造性技能是与具体领域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通用的;创造性过程是结构化的还是非结构化的。(41)大量的研究多是与创造力相关的研究,而不是对创造力本身的研究,如斯佩里的研究关心的是脑半球的专门化,创造性行为研究关心的是新颖性和顿悟,创造性产品的研究关心的是产品的生产力与生产率。因此,在未来的创造力研究中,对创造力本质和机制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注释:
①傅世侠:《创造学究竟是什么?》,《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455~460页。
②F.Barron and D.Harrington,Creativity,Intelligence,and Personal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32,1981,pp.439~476.
③[美]R.J.史登堡、T.I.鲁巴特:《不同凡响的创造力》,洪兰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第250~278页。
④[美]奇凯岑特米哈伊:《创造性:发现和发明的心理学》,吴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149~231页。
⑤田友谊:《国外创造力理论研究新进展》,《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1期,第14~17页。
⑥T.I.Lubart,Model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Past,Present and Future,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13,2000/2001.
⑦[美]特丽萨·艾曼贝尔:《创造性社会心理学》,方展画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⑧R.J.Sternberg and T.I.Lubart,Investing in Creativity,American Psychologist,51(7),1996.
⑨R.J.Sternberg,J.C.Kaufman and J.E.Pretz,The Propulsion Model of Creative Contributions Applied to the Arts and Letters,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2001.
⑩田友谊:《中小学班级环境与学生创造力培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第8~10页。
(11)武欣、张厚璨:《创造力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第13~18页。
(12)[美]特丽萨·艾曼贝尔,1987年,第80~92页。
(13)R.J.Sternberg,A Three-facet Model of Creativity,in R.J.Sternberg(ed.),The Nature of Creativity: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25~147.
(14)J.F.Feldnhusen,Creativity:A Knowledge Base,Metacognitive Skills,and Personality Factors,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9(4),1995,pp.255~268.
(15)R.J.Sternberg and T.I.Lubart,1996,pp.677~688.
(16)田友谊,2004年,第14~17页。
(17)K.Hoppe and N.Kyle,Dual Brain,Creativity,and Health,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3,1991,pp.150~157.
(18)M.A.Runco,Creativ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55,2004,pp.657~687.
(19)[美]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钱岗南译,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502~507页。
(20)R.J.Sternberg,et al.,1999,pp.189~211.
(21)M.A.Runco,2004,pp.657~687.
(22)傅世侠、罗玲玲:《科学创造方法论——关于科学创造与创造力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526页。
(23)田友谊,2004年,第14~17页。
(24)J.F.Feldnhusen,1995,pp.255~268.
(25)胡卫平:《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与培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
(26)胡卫平,2003年,第20页。
(27)R.S.Albert and M.A.Runco,Independence and Cognitive Ability in Gifted and Exceptionally Gifted Boys,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18,1989,pp.221~230.
(28)傅世侠、罗玲玲,2000年,第58~61页。
(29)M.A.Runco,2004,pp.657~687.
(30)D.L.Rubenson and M.A.Runco,The Psychoeconomic Approach to Creativity,New Ideas in Psychology,10,1992,pp.131~147.
(31)M.A.Runco,2004,pp.657~687.
(32)田友谊:《国外课堂环境研究新进展》,《上海教育科研》2003年第12期,第13~17页。
(33)田友谊:《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中的特殊教育》,《中国特殊教育》2004年第1期;《多元智能理论及其对教育的意义》,《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多元智能理论:我们应当如何借鉴?》,《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多元智能热的‘冷’思考》,《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3期;《多元智能理论视野下的创造力培养》,《现代教育科学》2006年第6期。
(34)M.A.Runco,2004,pp.657~687.
(35)田友谊,2004年,第14~17页。
(36)傅世侠、罗玲玲,2000年,第2页。
(37)邓雪梅:《试论团体创造力研究与创造心理学的理论转向》,《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第1277~1278页。
(38)赵春音:《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考察》,《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62~366页。
(39)傅世侠、罗玲玲,2000年,第203~251页;赵春音:《关于创造力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第8~14页。
(40)郝宁、吴庆麟:《创造力与能力、专长及胜任力关系述评》,《心理科学》2005年第2期,第501~504页。
(41)R.J.Sternberg,et al.,1999,pp.189~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