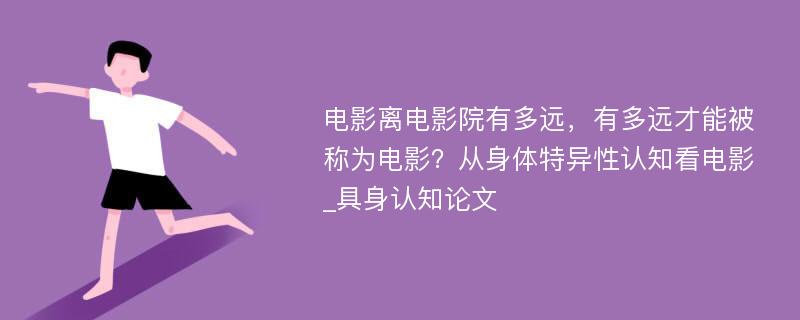
电影离开影院多远还能叫电影?——论具身认知视域中的电影与观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视域论文,多远论文,还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随着电视电影、手机电影、微电影、网络视频、游戏电影(过场动画和预告片)等新概念纷至沓来,“电影与电视等视听文本之间的区隔已被打破”①的观念在国内学界开始流行,“电影化的电视和电视化的电影”②,“电影与交互媒体整合的后电影”③等观念已经在模糊、泛化、改写电影概念。同时,更加激进的“大电影”概念也浮出水面。“‘大电影’概括的基本叙述对象和艺术形态,包括了传统电影本身,但又不断变化、改写,趋向空间化和更广的涵盖面。除了电影这样的主题类型,电视剧、动漫、电视电影、电视专题片、新媒体网络电视剧、手机剧、微电影、纪录片、MTV、广告MV、游戏、进口影视剧、预告片、宣传片……构成不尽相同的媒介形式、文本体裁和观影载体及平台,视频影像形式丰富而复杂。电脑技术、互联网助推一个虚拟世界和视觉艺术生态群落出现”④。应当看到,这些观念显露出一种将视听文本纳入总体性研究视域的学术雄心,但同时,这些观念也把视听文本抽象还原为简单的先验实体,侧重于讨论它们的共性,而对其在现象学层面存在的显著差异视而不见。 “电影”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必然会走向消亡,但眼下将电影和其他视听文本混为一谈还为时尚早,用“电影”标注其他视听文本则更不合时宜。这样做不仅忽视了电影仍然保有的无法替代的独特性,也无益于指导当下的电影实践。从尧斯的接受美学观点来看,电影在被观众观看之前还只是个半成品,只有在影院中被观众所感知,电影才能成为其所是的成品。即便是最贴近电影概念的电视电影,显然在半成品转化为成品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非电影的东西。在具身认知的视域下,电影的独特性与影院不可分隔,离开影院的电影不能称其为“电影”。观影不是一个抽象的图景,而是一个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影院的具身认知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从电影与“离身心智”的互动转向影院与“具身心智”的互动时,电影相对于其他视听文本的本质差异性才会显现出来。本文将首先论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身体转向”,然后对柏拉图“洞穴喻”进行具身化重读,并揭示在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重要细节,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洞穴观影的有限理性和享乐特质。 一、从离身认知到具身认知 认知科学已从第一代的离身认知发展到第二代的具身认知,而这种“时代精神”似乎还没有受到电影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心智的具身性”被美国学者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与“认知无意识”、“抽象概念的隐喻性”并列,称之为20世纪认知科学的三个重要成果⑤,而后两者其实都与认知的具身性有关。 早期认知主义电影理论家将观众的大脑看作是一个像计算机一样的信息加工装置,电影认知过程就是对电影信息进行输入、转换、存储、计算的过程。观众的心智是离身性的,更是脱离具体情境的。这种离身化、还原论式的思维,直接受影响于第一代认知科学。沿着他们的思路和理论来审视电影与其他视听媒介的区别,自然很容易只看到“大脑+影片”的认知关系。在电影院里,是大脑对影片;在电视上,是大脑对影片;在手机上还是大脑对影片等等。那么,提出“电影与电视及其他视听媒体的界限已经打通”,并试图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就不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了。其实,有迹象显示像大卫·波德维尔这样的认知主义电影理论家也曾留意过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观念,他曾提及:“我们对形象的理解,几乎不能不与我们在三维环境中的活动和认识同类的能力联系起来。根据当前流行的最强有力的理论,个体的语言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生物能力,一如人有长手臂而不是长翅膀的倾向那样。”⑥在这段波德维尔的论述中,前一句涉及具身认知的情境观,后一句涉及具身认知的发展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观念之外,具身认知还包括认知的具身观和动力系统观⑦。“具身认知的具身观”指的是认知能力是有机体身体的生物神经系统整体活动的显现,而不是离身心智的独立功能。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基本立场是要理解心智,必须回归大脑。大脑的生物神经学特征将其与身体整体相连,大脑绝不是孤立地对世界做出反应。影院中的大脑,不是“瓮中之脑”,而是整体肉身的一部分。大脑不可能完全脱离肉体的其他部分而独立做出认知甚至思考,其时肉体的其他部分的活动常常影响大脑的思维和判断。“具身认知的情境观”指的是具身心智嵌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约束中,必须相适应于环境的状况和变化,环境对于有机体认知的影响是内在的、本质的。因此,观影必然是观众的具身心智嵌入影院的物理环境和观众群的社会环境中,这些环境对观众的观影体验有着巨大影响。“具身认知的动力系统观”指的是人与环境的认知互动中存在认知的动机机制问题,动机的产生绝对不是大脑中的孤立事件,而是脑、身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婴儿发展出用手抓球的能力,而小狗则发展出用鼻子拱球的能力。“具身认知的发展观”指的是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处于高级(言语思维)的认知水平,而是从皮亚杰所说的“感知—运动阶段”发展起来的。就观众而言,对电影的理解和认知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比如,现在的观众不会再像1895年目睹《火车进站》的巴黎市民那样被吓得四散奔逃了,库里肖夫实验也很难在现代观众身上获得相应的效果检验。无论总体的观众还是个体的观众,他们的电影认知都处于发展状态。具身认知包含的这四种主要观念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都统一于认知的具身性。 具身认知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大量的实证支持。 一方面,具身认知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第二代以具身认知为核心观念的认知科学是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全面反思。第一代认知科学,无论是狭义的认知心理学(信息加工心理学),还是早期的认知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亦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人工智能等,都在追求一种普遍的理性形式。这些理论最根本的立场或假设是人类的认知是独立于身体、与身体无关的,是离身性的。这种普遍的理性观念究其哲学根源,可上溯到柏拉图“去身取智”的理念论,随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则更加强化了这种离身性,到当代则直接受到英美分析哲学的客观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有了人类心智与身体无关的假设,才有了信息加工心理学将人与计算机类比的构想,即认知即计算。而具有现象学基因的第二代认知科学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离身认知”这一核心观念,以“具身认知”取而代之。认知不再是第一代认知科学认为的那样,只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一个符号加工过程,而是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的认知。 认知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观点的兴起,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思想。梅洛-庞蒂指出身体对主体而言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他的身体是指现象的身体而非客观的身体。客观的身体是物质意义上可分解的生理实体,而现象的身体是“主体我”所经验的身体,“是身体地在世存在”。这一观点也是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阐述,就主体体验而言,“在世之中”的存在感不是“我思故我在”的存在判断,而是与身体经验(即体验)无法割裂的一种存在体验。另外,杜威的身体经验观、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理论也影响或直接启发了具身认知理论。杜威曾说:“在思维的操作和生物的、生理的操作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连续上的断裂……这意味着理性操作源于身体器官的活动。”⑧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则强调认知是嵌入社会和文化之中的,凸显了文化和社会环境对认知的重要性⑨。皮亚杰从自己童年研究水螅身体形态对不同流水环境的适应性中获得启发,提出了人类后期认知能力发端于早期的“感知—运动阶段”,从而将认知打上了身体经验的烙印⑩。总之,上述思想汇集起来可以推论出这样的观点:人类认知是在具体环境(无论是自然物理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环境)中具体的人与认知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么,对影院观影的研究也能从这个观点中获得诸多启发。 另一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已显示认知和思维受到身体的物理属性制约(具身观),而且身体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决定了认知(动力系统观)。已有实验表明身体经验影响到被试的认知判断,如琼斯曼(Nils B.Jostmann)的轻、重写字板实验和威廉(Lawrence E.William)的冷、热咖啡杯实验,以及伊泽曼(IJzerman)和肖明(Semin)的系列实验等。这些实验显示:拿重写字板的被试者在判断外币的价值时,比拿轻写字板的被试者认为其价值更高。手捧热咖啡的被试者与手捧冷咖啡的被试相比,更容易将一个中性的人物判断为是友好的。在温暖房间里的被试者比寒冷房间的被试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与实验者比较亲近。这些实验都充分说明了“身体的温热体验、皮肤的触觉等物理属性的刺激给认知和判断加以了重要影响”,且存在一种因果关系(11)。试想观众不是坐在温度宜人、座椅舒适的影院看电影,而是坐在电脑前或是拿着手机站在地铁里看“同一部影片”,他们对影片的感知会一样吗?又或者是观众坐在冷气过足的影院内看一部恐怖片,同时手捧冰咖啡,难道不会比通常观影条件下更容易产生恐惧感吗?我想基于具身认知的实验证据已经能给出具有启发意义的答案。 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实证研究来看,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观念已成为“认知实验室”内漂浮的幽灵,而这一幽灵还未出现在影院观影的系统研究之中。 二、洞穴观影的具身化重读 鉴于柏拉图的“洞穴喻”被普遍地挪用作影院观影的一个经典比喻,而该比喻的关键所在又往往被挪用者所忽视。同时,鉴于影院观影是观众之脑、身体与影院观影情境和银幕叙事情境的一个复杂互动过程,那么,就有必要对该比喻做一次具身化的重读,以便进一步分析电影的特殊性以及观众为何会“重返洞穴”观影。 首先,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挪用。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比喻能比“洞穴喻”更能如此贴切地描绘影院观影的情境。“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对应影院,“一些头颈和脚腿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的人对应坐在椅子上的观众,“洞穴后壁”对应银幕,“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发出的火光”对应电影放映机,“一带矮墙”对应放映室,“傀儡戏演员”对应放映员,“木偶”对应胶片拷贝或数字拷贝,“过路人发出声音在对面洞壁的回音”对应电影音响等等(12),但是这种形式上的一一对应就是理论研究上反复引用洞穴喻的全部价值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对大多数人而言,只看到了这种挪用的表面,而未能明白其实质。 柏拉图的本意是借此比喻来达到“去身取智”的目的。为了阐述身体感官经验的不可靠,柏拉图细致地描述这个洞穴观影的场景,其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相信那些“一生身体被囚禁的人”在怎样的一种条件下更容易甚至是必然会把“洞壁上的阴影”当作“真物本身”。让观众把影像当作真物本身,让观众沉浸其间,这难道不是电影最想实现的效果吗?电影想要令观众产生“错觉”或“幻觉”的感知效果,首先必须具备基本的视听条件。虽然电视、网络视频、手机视频等被统摄到“大电影”中的视听媒介都要求具有相应的视听条件,但它们对视听条件的要求远不如电影高。比如,手机视频仅需要方寸之幅、立体声耳机即可观看;而电影则需要大银幕和高保真、多通道立体音响的支持方能保持其在视听体验方面的优势和魅力。如果说在视听方面,过去的挪用者没有忽视这种观影者和视听文本展示界面之间的物理—生理差异(实际上鲜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柏拉图强调的另外几个因素,如“黑暗的洞穴”、“被束缚的身体”、“一群人”等,则几乎从未出现在挪用者的话语分析中。 在分析这些要素之前,先分享我的一个亲身体验,它或许可以作为个案予以考察。在《泰坦尼克号》上映时,我先后三次看过该片,时间在两个星期之内。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在家里的电脑上,最后一次是在电影院,其中唯一让我感动到眼眶湿润的观影体验是在电影院。我坚信这种经历绝不是一个特例。这一经历时常让我反思,是什么让观影者在电影院里而不是在家里如此沉浸呢?家里电脑上那部《泰坦尼克号》和影院这部《泰坦尼克号》还是同一个东西吗? “黑暗的洞穴”是影院观影的必要空间条件,其中又可以分别从“黑暗”和“洞穴”两个层面予以讨论。首先,“黑暗”确保在影院内没有其他的杂散光线分散观众观影的注意力,银幕成为在亮度上具有绝对优势的部分,周围的观影者甚至包括观众自己的手脚都湮没在黑暗中,一种“观众和银幕”的互动关系逐渐被牢牢地锁定。按照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经典说法,黑暗的剧场和“传统电影中关于演员绝不应当看观众(=摄影机)”共同为观众设置了一个“窥淫”的位置(13);从具身认知的角度看,“黑暗”的功能只不过是让观众忽视所在的物理空间而已,演员目视观众则会提醒观众对所在物理空间位置的知觉,从而在影院物理空间和电影叙事空间之间做出划分和判断,影响深度沉浸。其次,“洞穴”是确保能隔绝影院外的一切声光干扰、创造种与现实暂时隔绝的封闭空间。这些条件是看电视、看手机视频、看网络视频、看车载电视等所不具备的。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为了在这些媒体上欣赏一部“电影”,刻意熄灭周围的灯光,拉上窗帘,也仍然时常受到环境和他人的干扰,而难以享受到一场深度的“沉浸”。排除干扰是影院的重要功能,而在影院外,观众面临频繁的不可知干扰,其注意力很难长时间保持,从而让那种强调视觉化、叙事环环相扣、情节紧凑的电影在这些视听媒体上无法大展拳脚。“洞穴”的另外一层功能则是创造一个封闭空间,允许观众与现实暂时隔绝,从而电影能在封闭空间中建立新的价值秩序。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所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早已证明了这点,被试者在封闭空间中模拟“狱警”和“囚犯”,最终形成了“路西法效应”,即好人变成了恶魔(14)。津巴多的实验场地就是一个“封闭空间”,这个封闭空间给人的感觉是在社会规则和法律监督之外,因而人在新秩序中重新分化。影院也是一个封闭空间,它的秩序系统也可能被电影所重建,观众也将在新的秩序中体验到新的感受。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的观点是有启发意义的,即封闭空间中的人可以脱离现实象征秩序的“凝视”,并在空间中建立一套新秩序,接受新秩序的询唤。 “被束缚的身体”同样也是影院观影的必要条件。与柏拉图“洞穴喻”中的描述不同,影院观众不是被捆绑了头颈和手脚,而是被影院舒适的座椅“温柔地束缚”住了。无论是捆绑头颈和手脚,还是温柔的束缚,都会造成眼睛和耳朵之外的其他感官失感。乍看起来,柏拉图在叙述中仅仅强调了视、听觉被欺诈而让囚徒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而实质上“被束缚的身体”才是更为关键的部分。人类对于外部刺激信息的感知主要通过眼、耳、鼻、舌、身以及本体感受器(proprioceptors,主要负责身体位置感和平衡感的部位)等感官来完成,但洞穴内囚徒除了视觉和听觉之外的其他感官能力都被削弱或被剥夺了。目前,削弱部分感官对主体所带来的影响较少见诸实验报告,但极端的“感觉剥夺”实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研究表明,“倘不能使(人类感觉的)多样性维持一个关键的水平,就会出现心理上的混乱,其中包括思维过程的障碍和出现幻觉”(15)。感觉剥夺实验导致被试者出现的病理现象不会在“洞穴囚徒”(即影院观众)身上全部表现出来,但对触觉、嗅觉、平衡觉的感觉剥夺难道不会更容易让观众沉浸于电影、更容易出现“幻觉”吗?另外,人的正常思维和感知能力不仅需要感觉有一种多样性,同时需要多感官整合才能达成。所谓“多感官整合,是指在环境背景、时空一致性等多种作用因素的基础上,一种感觉模态的输入可影响另一种模态信息的处理,以克服刺激强度低、环境干扰大等困难,弥补单一模态信息的匮乏,最终导致对事物的感知增强或减弱”(16)。多感官整合的研究对于理解电影的沉浸机制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观影实际上是选择某些感官参与感知过程同时抑制另外一些感官,也就是说,它既要增强观众对电影叙事空间的感知,又要削弱观众对影院物理环境的感知。对于目前绝大多数电影(4D电影等例外)而言,观影实际上仅需要视觉和听觉的参与,而这两种感觉为人类感知外部世界提供了94%以上的感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触觉、嗅觉、平衡觉对物理环境和自身状况(如身体不适)的感觉会削弱视、听觉对银幕事物的感知,这就是多感官整合相互削弱的情形,于是它们就成了影院需要努力去削弱的感觉器官。可见,正是观众不用坐在针毡上或硬板凳上看电影,他们才能避免身体触觉对视听觉整合效果的削弱,从而更容易沉浸于电影。这正是影院设置舒适座椅来“束缚”观众身体的科学依据。 “一群人”强调的是影院观影具有的群体性和社会性,它对观影效果影响巨大。观影动机是一个多维度、多因素的问题,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和他人一起看电影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共在感。人处于群体中,他的认知和情绪会受到群体环境的影响。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并非起始于具身认知研究,其他领域的人早就谈论过。莫泊桑对此深有感受,他说:“我不能进电影院,或者观看公共集会。它们让我有一种奇怪的无法忍受的不安全感、一种可怕的痛苦,似乎我在尽全力搏击一种不可抵挡的神秘力量。其实我是在抵挡群体的灵魂,它正在试图进入我的头脑。我多次注意到,当一个人独处时,智慧就会增长,就会上升。而当一个人与其他人混杂在一起时,智慧就减少并衰落。”(17)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莫泊桑这种焦虑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相信自己的理智正在失去用处;另一个是他感到他的情感反应是过分的、极端的”(18)。这种过分的情感反应难道不是影院观影的人们常常表现出来的吗?在电影院里难道不是比一个人看电影时笑得更多或者哭得更厉害吗?勒庞也发现,“融入一个群体的个体所发生的心理调整,各方面都与那些由催眠术带来的心理改变相似。集体状态与催眠术状态相似”(19)。观影本身既是一种群体状态,也是一种催眠状态。莫斯科维奇指出:“每一场催眠活动都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与某种情感关系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生理的控制有关。前者包括被催眠者对催眠师的绝对信任以及对治疗专家的顺服。后者的实质是被催眠者环境视野的局限性以及被感知的刺激数量的极其有限性。”(20)“后者的实质”印证了我对前两个因素的相关论述,影院的局限性和对视听觉之外其他感觉的剥夺,让观众处于一种极易催眠的状态。在勒庞早就论述过的“剧院的方法”中,也指出剧院必须能施行催眠术,他说:“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与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象出来的离奇故事。”(21)这种情感的共鸣和共在的体验实则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群体认同机制,它或许仍存在无意识的成分,但也存在社会认知的因素,即观众感受到自己仍是某个群体的一员,仍然保持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情感和趣味,从而避免自己被排除在群体之外而产生的焦虑。利用观众在群体中去个性化的这种心理特征,影院轻易地让观众处于“低智慧、高情感”状态。 心理学家还注意到,情境对认识和情绪具有启动效应。“我们所处情境中的微小特征都会启动我们的目标、信念、情感以及行为”(22)。封闭黑暗的影院、充斥整个视野的银幕、高保真多通道环绕立体声、舒适的座椅等物理条件,任何条件的变动都启动了观众的认识和情绪。影院这一空间格局更多启动的是观众的消费娱乐需求,而不是认知发展需求。影院与观众之间的物理—生理关系,是其他视听媒介所不具备的,因而决定了电影独特的美学形态和创作观念。毕竟,直到艺术作品展示在嵌入情境的受众面前并与之发生互动的时候,其创作才能宣告真正的结束。否则,马塞尔·杜尚的男用小便器,何以能在展览馆产生了那么大的艺术效果呢? 三、洞穴观影的有限理性和享乐特质 尽管认知主义电影理论认为观影也只不过是一个具身的有限理性的认知过程,但是对此缺乏细致的观察和思考。或许它需要从“曾经的对手”精神分析电影理论那里获得更多启发,对观影现象做更细致地观察与测量。 从具身认知的角度看,与其探讨观众为何去看一部电影,不如首先探讨观众为何去影院。影院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远比回答“电影是什么”要简单得多。从“镍币影院”到“教堂式”的“电影宫”(23),再到现代多厅影院,它都是一个旨在通过价值交换让观众获得心理满足的生产性空间。与部分学者关注观众在数字科技支持背景下“走出电影院”的趋势不同(24),我更关注在同一背景下观众更多地“走进电影院”这一心理动因。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视野下,心理满足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众所周知的娱乐消费心理满足,即便它不是观众去影院观影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首要原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西奥迪尼认为:“当不同的情境提供不同的机会时,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的愿望、目标相匹配的机会”,因此想从压抑的现实心境中解脱一下的现代人会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院能够提供消遣放松以转移焦虑”(25)。英卓·德·施尔瓦(Indra De Silva)通过电话调查366例有效样本后发现,95%以上的观众基于以下四大原因而选择去影院观影,即逃避(43.8%)、技术设备优越(31.7%)、时效性(10.3%)和影院氛围(9.1%)(26)。可见,观众去影院观影有着一个复杂而多维的动机结构。结合前面对柏拉图“洞穴喻”的具身化解读,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原因中除去“时效性”之外都与观影的具身性有关,且也与观影的享乐特质相联系。“逃避”有着消遣、放松、逃避现实的含义,“技术设备优越”则有利于视、听刺激和感官沉浸,“影院氛围”侧重于到人群中去的意味,这三点分别于对应于享乐的空间封闭性、享乐的感官性和享乐的社会性,而封闭空间、感官享乐、社会群氓正是理性的障碍。 理性的坚执和享乐的意图常常是矛盾的。意欲进入影院的观众,常常下意识地期望从阿波罗的理性秩序中暂时性地解放出来,融入狄奥尼索斯式的情绪宣泄中。享乐的前提就需要对理性进行抑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确常常通过饮酒等形式来达到对理性暂时抑制的目的,饮酒后也的确能实现享乐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影院首先应该是对理性具有抑制性的空间,在这里不难看出“洞穴喻”能再次起到阐释作用,封闭洞穴里的人不都是“非理性的”吗?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实证研究可以证明或证伪,在影院观影过程中的观众与在现实中的自己相比较,在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前文提及的莫泊桑的个人体验和勒庞等人的观察与思考足以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影院观影过程中的观众仅具有现实中的部分理性,即有限理性,这是享受电影的前提。在分析有限理性和享乐特质时,认知主义电影理论或许会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得不再次面对一直回避的概念“潜意识”。所以,求助于“老对手”精神分析的阐释也未尝不是一种打开思路的方式,毕竟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与认知主义电影理论之间从哲学源头到研究方法都存在不同,二者并不需要拼个你死我活。 精神分析在对观影的阐释时遇到了挑战,出现了一些备受争议的观点(尤其是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并不妨碍我们从拉康晚期思想的转向中(从“象征界”、“想象界”转向“实在界”)获得关于主体享乐的精神动力学启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更准确地说是精神动力学,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动力机制促使人们去做某些事情”。而在电影研究中,这个问题变为“是什么动力机制促使人们去影院观影”。观众去影院观影,具有自愿将自己暂时设定为“有限理性和高度感性状态”的精神动机。在柏拉图的“洞穴喻”中,那个被释放的囚徒,如果他走出洞穴看到的是世间的单调平淡、孤独寂寞、空洞虚无、残酷凶险,而与之前在洞内体验到的精彩纷呈大为不同,难道他的返回不可以解读为一种放弃启蒙理性的含义吗?去影院观影难道不是和《美国往事》中“面条”去中国影院借助鸦片享受短暂的幻觉具有同样的精神动机吗?《黑客帝国》中反派人物塞佛尔不是后悔吞下了红色药丸而必须走出“虚拟的数字洞穴”,不得不面对“现实的荒漠”吗?那么他为了享受“比现实更真实的虚拟世界”的精彩,试图和“Matrix”重新连接,而放弃启蒙的自由,不正和影院观影具有同样的放弃理性的意味吗(即便影院观影只是暂时放弃理性)?观众手中的电影票不正是那颗“蓝色药丸”吗? 观众购买电影票,其目的是想获得相应的娱乐价值。施尔瓦的调查同时显示,阻碍观众去影院观影的前三大理由分别是价格(45.1%)、噪声(18.9%)和舒适度(10.3%)(27)。可见,观众付费观影的重要前提是对电影进行一种价值判断,即是否值得花钱去影院换取相应的娱乐。影院不是教室。如果说影院观影是为了获得某种认知发展价值,这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说不通的。观众到影院去是为了感受而不是为了认知,是去相信而不是去质疑,是将自控转化为一种他控,是一种自愿放弃批判理性和独立反思而让“缺席的导演”给自己带来一场类似催眠或醉酒的“自愉”设定。当然,这种享乐过程并非全然地失去理性,暂时放弃理性并不意味着理性能力完全丧失,观众需要保留基本理性能力(诸如前后镜头的因果逻辑和简单相关的推理判断等),以便能理解剧情,并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化解释。 既然洞穴观影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暂时放弃理性,以便可以从电影中获得现实生活之外的享乐,那它对电影创作的启发和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奇异的景致、恐怖的角色、惊悚的剧情、可笑的动作、激烈的战争、凶残的搏杀、温馨的画面、甜美的微笑、精致的叙事等等,都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通过暴力、情色、僭越(集体僭越)、叛逆、挑战等内心压抑力量的银幕展示,让观众在内心进行“意象性实践”(28),几乎可获得接近真实水平的心理满足。叙事电影的大团圆、收编、回归等结局处理又能在电影将尽之时,让观众重回现实的怀抱,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心理冲突。例如,《蓝丝绒》就通过大量的暴力和情色展示满足了观众的相应欲求,而在结尾处却以主角的回归将观众同步带回现实世界。《搏击俱乐部》通过大段的近身肉搏与破坏场面,释放了观众在工作中和生活中积累的对象征秩序的愤懑,最后同样通过醒悟和回归重返现实。观众对暴力、情色、僭越、挑战现实等存在着潜意识的需求,观影则提供一个心灵释放或精神治愈的暂时性过程,它俨然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保健方式”。它不是通过拉康派精神治疗技术中主张的“说出你的欲望”,而是通过“观看你的欲望”,来达成心理调适的目的。当然,这也是其娱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愿返回“洞穴式”影院,还可解读出艾瑞克·弗洛姆论及现代人“逃避自由”的意味。倘若那个启蒙的人回到洞穴,选择重新囚禁自己,他或许慢慢地也会把洞外的经历当作是一场不真实的幻梦吧!由于囚徒之间互不可见,互不了解,那有谁能确定邻座的人不是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心境呢?也就是说,或许洞穴内每个人都单独出过洞,他们在之前和之后都不知道还有别人出去过,最后他们都选择重回洞穴。他们出去时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回来却可以和大家在一起,哪怕是一种表面的共在体验。施尔瓦的实证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有53%的人因为“想外出”或“到人群中去”而去影院看电影,观影也意味着成为“未知”群体的一部分(29)。怕被群体抛弃是人在进化论意义上的生存本能,人会为了融入群体而放弃自由。现实世界越让人感觉孤独冷漠,现代人生活越原子化,电影院的生意就会越红火。 比“大电影”概念更早的是尹鸿等人翻译的《大电影产业》(The Motion Picture Mega-Industry),不过该著作强调的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大产业”,而不是试图包摄所有视、听媒介的“大电影”。“大电影产业”已然成为客观事实,无须争论。然而,对试图包揽一切视、听媒介的电影概念以及模糊电影与其他视听文本界限的主张,我们或许应趋向于采取一种保守的立场,否则一个极其庞杂且难以统一认知的研究现象将会令研究者手足无措。 从具身认知出发,影院之外的视听文本都难以套上“电影”的标签,甚至手机上的《阿凡达》和影院里的《阿凡达》都不是同一个东西,这并非只是尺寸上的差异或量上的差异,而是质的不同。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要说:“影院之外无电影”。电影的本质应该是由观影主体、银幕、音响、座椅、影院物理空间(黑暗与封闭)、观影社会环境、电影自身等一切关涉物共同决定的,它们不仅决定电影从半成品走向成品的全过程,甚至决定电影成为半成品时导演的创作思路和艺术策略,由此,影院的空间生产成为电影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注释: ①虞吉:《像与像化叙述知识体系中的动画基本理论表述》,载《艺术百家》2010年第4期。 ②尹鸿:《电视化的电影与电影化的电视》,载《电影艺术》2001年第5期。 ③陈犀禾:《虚拟现实主义和后电影理论——数字时代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观念》,载《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 ④丁亚平:《新语境下“大电影”的建构与发展》,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11期。 ⑤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 ⑥大卫·波德维尔、诺埃尔·卡罗尔:《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⑦李恒威、黄新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 ⑧John Dewey,Logic:The Theory of Inquiry.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1,p.26. ⑨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载《外国教育资料》1999年第4期。 ⑩施良方:《学习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190页。 (11)叶浩生:《西方心理学中的具身认知研究思潮》,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7期. (12)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2—311页。 (13)克里斯蒂安·麦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王志敏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4)参见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姣、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7页。 (15)托马斯L.贝纳特:《感觉世界:感觉和知觉导论》,旦明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16)韩磊、刘宇等:《多感官整合的研究进展》,载《生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5期。 (17)(18)(19)(20)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第21页,第106页,第109页。 (21)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22)(25)道格拉斯·肯里克、史蒂文·纽伯格、罗伯特·西奥迪尼:《自我·群体·社会——进入西奥迪尼的社会心理学课堂》,谢晓菲、刘慧敏、胡天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第49页。 (23)顾铮:《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5页。从日本摄影师杉本博司的《影院》系列照片,大家会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电影若脱离了“洞穴式”或“教堂式”的影院,就难以是其所是。 (24)数字化时代观众“走出电影院”是否是一个趋势还难以断定,已有研究证实影院观众和录像带观众之间没有明显的重叠(巴里·利特曼:《大电影产业》,尹鸿、刘宏宇、肖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那么可以假设影院观众与网络观众或许也不存在明显的重叠。进一步还可以假设,影院观众和电玩玩家也不存在明显的重叠,那么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影院观众会越来越少,观众也不会像电玩玩家一样对电影剧情要求更高的自控权和选择权。 (26)(27)(29)巴里·利特曼:《大电影产业》,第155页,第155页,第154页。 (28)心理学研究发现,实际的抓握动作与想象的抓握动作具有相同的神经机制,在大脑中枢中的兴奋点是一致的(参阅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5期)。从这个结论推断,影院观众观影时的动作想象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我称之为“意象性实践”。标签:具身认知论文; 认知科学论文; 影院观影论文; 电影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泰坦尼克号论文; 武打片论文; 恐怖电影论文; 欧美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