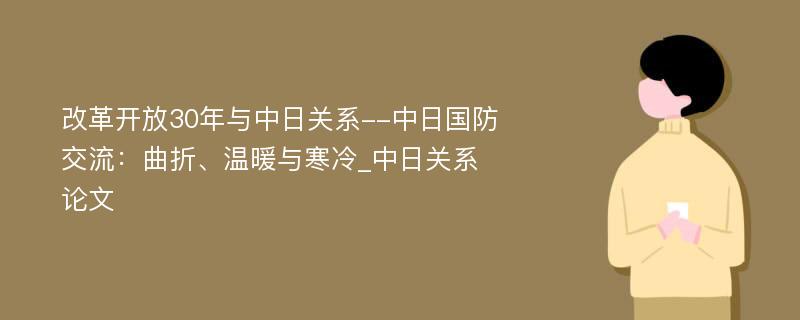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与中日关系——中日防务交流:一波三折,乍暖还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乍暖还寒论文,防务论文,中日关系论文,一波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11-0029-04
2008年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双边贸易额由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的1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 360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两国人员往来达到544万人次,[1]并呈继续发展的趋势。
相对于经济、文化和人员交往领域的快速发展,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日防务交流却在长时间内一波三折,步履维艰,长期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直到2007年和2008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大力促进下,筹划多年的中日舰艇互访才最终成行,两国的防务交流有了较为明显的起色。但无论是与中日关系的其他领域还是日本、中国与其他重要国家的防务交流水平相比,中日防务交流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亟待进一步加以拓展。
一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4年,双方互设武官处,开始了防务领域的最初接触。197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在访美途中顺访日本,开启了两国高层军事往来的大门。[2]1984年7月,前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过境日本,在会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祐幸时表示赞同进行更多的防务交流。[3](P195)1987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祐幸正式访华,并邀请中国国防部长回访。这是日本防卫厅长官第一次正式访华,中日防务交流出现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但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两国防务交流遂告中断。
1991年,海部首相访华,中日政治交往得以恢复。1993年5月,日本外相武藤嘉文访问中国。在与钱其琛外长的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双边安全磋商机制,以提高两国防务政策的透明度,实施关于地区安全问题的对话,并决定磋商将在两国首都轮流举行。1993年12月20日,在北京举行了中日外交当局首次安全对话(以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司局级官员为首)。对话的议题包括:通过提高透明度建立信任、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核试验、地区安全合作,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1994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由中国国防部和日本防卫厅、自卫队局级官员参加的首次防务安全对话,主要议题是双方的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以及日美同盟问题、台湾问题等。自那时起,双边安全对话成为两国了解彼此安全政策和传达彼此安全关注的重要渠道。
1995年1月,第二次中日安全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首次将外交安全对话和防务安全对话合并,以外交当局司局级官员为首,并正式命名为“中日外交防务当局安全磋商”。1995年2月,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这也是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参联会主席首次访华,标志着中日防务领域的高层交往正式恢复。
1997年11月,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访问日本,与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秋山昌广举行了中日第一次副部长级防务安全磋商,标志着两国防务当局副部长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磋商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热点问题、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情况及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对当年的防务交流进行总结和评估,同时对下一年度的防务交流做出安排。
1998年2月,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国防部长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在迟浩田访日期间,双方防务部门领导人一致同意加强各个领域、不同级别的交流,包括舰艇互访。200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傅全有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军队总长首次访问日本。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期间,同森喜朗首相就“增加两国军方之间的交往,实现军舰互访”达成共识。在当月举行的中日防务当局副部长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时,双方同意中国军舰访日,并开始着手落实舰艇互访事宜。
这一时期双方在1998年两国防务部门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还开展了中日防卫医学研讨会(1999年1月)等医学领域的交流和军事学术交流等。同时,中国军队的研究人员还从1997年起应邀出席由日本防卫当局主办的各种多边防务研讨会。
2001年,由于小泉首相上台后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一个“冰冻期”,防务交流由此也进入了长达五年的低潮期。中国方面为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主动提出暂停中日防务领域的高层交流,原定的中国海军军舰于2002年5月访日等重要交往项目搁浅。到2006年安倍政府上台之前,除2003年9月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访华外,两国只保持了副部长级防务安全磋商、外交防务当局工作层次磋商和低级别团组互访。
在官方防务交流受阻的情况下,通过第二轨道进行的防务交流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典型的例子是由日本往川和平财团资助的中日中级军官互访项目。该项目自2001年开始以来,已连续实施了8年,迄今已有100多名现役中国军官通过第二渠道的方式访问了日本,近100名现役日本自卫官访问了中国,[4]此项军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对于增进两国年轻军官之间的友谊和互信,对于了解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走马上任选择中国作为他的第一个出访国。在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中,双方就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相互信任达成共识,并提出努力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在中日防务部门首次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阐明了以下共识: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将于11月或12月访日,中方并邀请日本自卫队舰艇随后访问中国;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尽早就此进行专家组磋商;开展双方防务部门在军兵种、军事医学、军事学术、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加强人员培训合作,扩大包括青年军官和自卫官在内的人员交流;中方邀请日方于2007年派员赴华观摩步兵师进攻战斗实兵实弹演习;逐步探讨在抵御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等。这些共识涉及多个方面,且颇为具体,预示着中日军事交流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5]2007年9月,中国首次邀请两名陆上自卫官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在中国沈阳军区举行的军事演习“勇士—2007”。
在中日政治关系明显趋暖的背景下,中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应日本海上自卫队之邀,于2007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历史上首次访问日本。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与福田康夫首相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落实该声明,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其中涉及防务交流的内容有: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将于2008年6月访华;双方将继续为早日建立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作出努力;双方将就扩大军兵种、防务相关教育机构、研究机构间的交流进行探讨;双方将探讨在联合国维和行动(PKO)、灾害救援等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年内将相互邀请约15名尉官级干部访问对方国家一周左右;双方将就当前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主要问题保持磋商等。[6]
作为对“深圳”号2007年访日的回访,日本海上自卫队“涟”号驱逐舰于2008年6月24-28日对广东省湛江港进行了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这也是日本自卫队舰只在二战之后首次访华。
这次延宕多年方最终实现的舰艇互访,标志着两国防务交流有所深化,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对两国在防务领域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防务交流是国家间最为敏感、最具实质性的交往领域,它主要包括人员互访、多边与双边安全对话、互派军事留学生、军舰和航空器互访、军事援助、军控谈判与核查、军事技术合作、专业技术交流、国际冲突和危机的处理、国际维和、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开始防务交流以来,双方主要在高层互访、事务级官员的定期磋商、团组互访、学术交流等领域开展了以人员相互交往为主要方式的交流活动,以增进双方在防务安全领域的互信。过去两年中所实现的舰艇互访,虽然与此前的中日防务交流成果相比算是一个突破,但就总体而言,目前的中日防务交流水平基本上还处于国家间防务交流的初级阶段,即建立互信阶段,而没有达到采取实质性行动,如联合训练、联合军演和防卫技术合作等层面。中日间的防务交流水平甚至还比不上双边关系素来不睦的日俄之间的防务交流水平①,遑论日美、日韩和日澳之间的水平。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中日两国在国家层次上目前仍然缺乏战略互信。中国担心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插手台湾问题,担心日本逐渐放弃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政策;日本则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对日本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将给本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日本在中日防务交流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中国军事透明度的问题,尤其关注中国国防费的增长以及武器装备高技术化的问题。这种潜在的战略角逐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而进一步放大,使得中日两国防务交流比一般国家之间的防务交流要更为复杂、敏感、微妙和脆弱。就上文概述的过去30多年间中日防务交流的历程而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国之间的防务交流深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防务交流主要是基于总体政治关系的改善,而不是相反。两国关系顺利时,防务交流也顺利发展;两国关系紧张和恶化时,无论关系的紧张与恶化是源于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东海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美日同盟强化问题,还是中日两国国内的政治发展,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影响的必定是防务交流。这是中日防务交流历经30余年却仍发展缓慢,缺乏实质性交往的主要原因。可以预计,今后中日防务交流的发展仍将受到中日政治关系氛围,尤其是两国间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影响和制约。
其次,在两国普通国民的层次上,缺乏互信的情绪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情绪必然会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和决策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当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据日本内阁府于2007年10月发布的舆论调查,认为当前中日关系总体良好的仅占26.4%,而不认为好的却占63.5%。虽然认为良好的受访者比例比去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但应该说仍然是相当低的。[7]这样的比例自然而然地使人担心中日未来防务交流的走向。
所幸当前在中日两国领导层中对中日关系大多抱有建设性的态度,都认识到中日防务交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积极致力于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通过近两年高层互访发表的共同文件为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勾画出路线图。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官民合作来实施这些路线图。
三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应该说,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和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新安全观”,以及当前两国所致力于构筑的战略互惠关系,均体现了两国安全观的变化,显示出两国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共同利益,问题是怎么把这种共同利益在防务交流的层面上变得可操作化。
第二,强化防务交流机制,不仅是在中日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多边防务交流的场合以及本国防务机构之间的协作。当前中日防务交流虽然初步建立起高层互访、事务层次的定期磋商、部队之间的交流、交换留学生和军事学术交流的多层次的交流体制,但目前的中日防务交流机制仍不够健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省已经于2007年颁布了一份题为《防卫交流的基本方针》的文件,对日本的对外防卫交流进行了详细的规范。[8]中国的对外防务交流可能也需要这样一部东西,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第三,中日应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两国间防务合作的空间。当前,环境问题、自然灾害救援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打击海盗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各国的安全关切中日益占据显要的位置。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在应对这些新的无国界的安全挑战方面,理应携手共进。应对非传统威胁将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日防务合作的新的突破口。
第四,中日应该加强在多边场合的防务交流。当前,在联合国维和、“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多边安全框架下,中日之间也可以相互协调配合,以进一步深化彼此的信任。
中国和日本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逐步扩大和深化安全对话与防务交流,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30多年来中日防务合作的历程虽一波三折,而且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基础也难称巩固,但作为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在保持中日政治关系稳定的大前提下构筑具有韧性的中日防务关系,以加强两国之间的互信关系,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关注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8-10-06
注释:
①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俄之间便开始了两国军舰的定期互访。1998年7月以来,日俄海军舰艇已发展到在日本海北部联合救灾演习的层次。参见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00,The National-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Japan,pp.254-255.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中日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