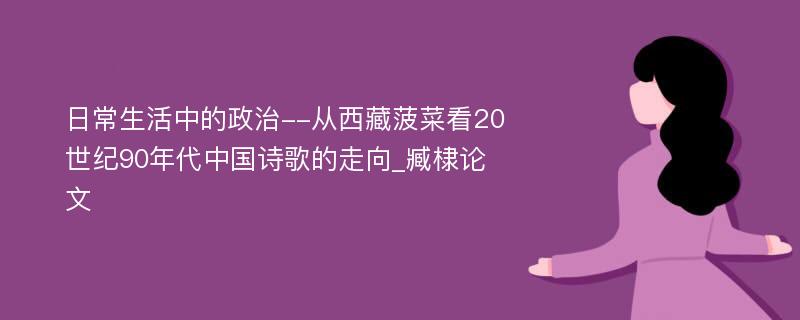
日常生活的政治——从臧棣的《菠菜》看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菠菜论文,日常生活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5)06-0022-05 臧棣的《菠菜》写于1997年,是一首看起来简单平淡的短诗。因为,这首诗写了生活中一种极为普通的事物——菠菜: 美丽的菠菜不曾把你 藏在它们的绿衬衣里。 你甚至没有穿过 任何一种绿颜色的衬衣, 你回避了这样的形象; 而我能更清楚地记得 你沉默的肉体就像 一粒极端的种子。 为什么菠菜看起来 是美丽的?为什么 我知道你会想到 但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冲洗菠菜时感到 它们碧绿的质量摸上去 就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 如此,菠菜回答了 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 看见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天使的问题。 菠菜的美丽是脆弱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只有50平方米的 标准的空间时,鲜明的菠菜 是最脆弱的政治。表面上, 它们有些零乱,不易清理; 它们的美丽也可以说 是由烦琐的力量来维持的; 而它们的营养纠正了 它们的价格,不左也不右。 为什么选择菠菜这样一种十分常见的事物作为书写的对象?这也许是首先引起的疑问。当然,菠菜之类普通事物进入诗写的范围并非始自此诗,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里也不是孤立的个案。不过,这类写寻常之物的诗歌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较为密集地出现,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某种变化,表明诗歌开始放弃关于超拔、伟岸和庄严事物的宏大叙事,转向对身边的切近的琐屑事物的书写。这是一种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的转变,虽然其中不乏为写俗物而写俗物以至干泛滥无边的伪劣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菠菜》虽然可算作一首写物的诗,却不同于以往(古典时期和新诗早期)的“咏物诗”,它对菠菜这一“物”的书写没有采取歌咏或称颂的态度,而是以一种非抒情的方式进行了书写,其间甚至包含了强烈的论辩的成分。如果要考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非抒情趋向,《菠菜》也许是个较好的切入点。 与臧棣的其他许多诗一样,《菠菜》采用了不分节的样式,全诗27行①浑然一体,非常紧凑。这是它在外形上的一个特点。不过,尽管没有分节,但随着平缓节奏的推进和语风的转换,整首诗还是显得颇有层次感的。如果一定要划分层节,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三节:从开头到“一粒极端的种子”为一节,从“为什么……”到“……天使的问题”为另一节,从“菠菜的美丽……”到末尾为最后一节。 “美丽的菠菜不曾把你/藏在它们的绿衬衣里。”诗的开头两行用否定的句式(“不曾”)给出了菠菜和“你”(这个“你”是谁呢?下文将有分析)的关系。一个“藏”字道出了菠菜形象的特点之一:宽大;加上前句中的修饰语“美丽”和本句中的“绿衬衣”,令菠菜的形象得到了初步敞露。有必要指出,作为全诗的起首,“美丽”(一个抽象的词)显得波澜不惊,似乎毫无独异之处,但在诗中多次出现,几乎成了专门形容菠菜状貌的语词。这两行诗有两点格外值得留意:其一,此诗一开始就用复数人称“它们”来指代菠菜,较符合菠菜有着鲜明群体性的宽大形象;其二,在描述菠菜与“你”的关系时,菠菜占据主导位置,是动作的发出者,而“你”是受动者,仿佛菠菜是能够荫庇“你”的强大之物。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出:开头这两行所突出的菠菜的“绿”,实际上是呈现菠菜形象和理解全诗意旨的关键之一。紧接着的三行诗陈述“你”对“绿颜色的衬衣”的态度,在语感上显然是顺承第二句而来。这三行也用了否定的表述(“没有穿过”),显示“你”对“绿衬衣”形象的回避,并且将菠菜与“你”的主动—受动位置进行了颠倒。从属性和外观来说,菠菜所具有的“绿”是一种相当单纯的颜色。一方面,绿色赋予菠菜“碧绿的质量”(第14行),其纯粹、柔和的色泽和质感让人不免生出怜爱之情(“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而“绿衬衣”这一喻象也给人某种温暖的感觉;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绿色的过于单纯,却让“你”对之产生了怀疑乃至抵制的意绪,故而“回避了这样的形象”,第6—8行中“我”所记得的“你沉默的肉体”,并将之比喻为“一粒极端的种子”的说法,无不可视为对这种“回避”态度的强调,尽管此处的“种子”与后面的“我和植物的孩子”之间可能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毋宁说,这折射的是由菠菜的单纯之“绿”引发的“你”和“我”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心态。 那么,菠菜的“绿”为何会引起“你”的抵制和“回避”呢?这一点后面将会有所揭示。 如果说诗的前8行(作为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是基于“你”的角度或立场看待菠菜,那么从“为什么……”到“……天使的问题”这部分,则是以“我”的眼光和感受来评价菠菜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对,的确是一种评判。“为什么菠菜看起来/是美丽的?为什么/我知道你会想到/但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两个缠绕在一起、具有相互抵消意味的连续发问,体现了臧棣式诗思和句法的狡黠。但不能说这样的发问毫无价值。前一个“为什么”既可以是充满疑惑的提问,也可以是设问(无须回答),关键是谁发出来的;从后一个“为什么”的字面来看,该问题应由“你”发出,但根据后一个发问暗含的意思,“你”只是“想到”,实际却并未(“不会”)提出该问题。这让前一个“为什么”的设问成分占了上风,由此菠菜的“美丽”变得不容置疑。“想到/但不会提出”——这一通过发问而展现的微妙心理,再次确认和强调了菠菜的“美丽”。 在随后的三行诗里,“我”因与菠菜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请注意其中的两个动词:“冲洗”和“摸”。它们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动作,“冲洗”似可见出“我”对菠菜的细心与珍惜,“摸”更显“我”与菠菜关系的亲密。这样的喜悦之情在一个关于菠菜的新奇譬喻中达到极致“像是我和植物的孩子”。无疑,这个譬喻会带来令人愉悦的奇幻效果,它勾联着诸如米歇尔·图尔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②之类的现代寓言文学传统。 不过,此处在用“孩子”这一譬喻表达怜爱之意的同时,字里行间也掠过一丝须细细体察的隐忧。这种隐忧与菠菜引出的话题有关“菠菜回答了/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天使的问题”。在此,菠菜无疑为“我们”洞察(“看见”)生活的奥秘提供了一次契机,“看见”犹如经过生活化语汇转化的浪漫主义的“灵视”,体现了一种先知般的对于生活的领悟与处理能力。这里出现了仅此一次、显然与“我们”相对的复数人称“他们”,应该指有别于“我们”、处在全然隔绝状态的人们;借用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术语来说,“我们”和“他们”是被“区隔”(Distiction)的两类人。而这三行中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天使”一词,这是理解全诗意旨的另一关键语词。正是经由菠菜,“天使的问题”才得以彰显出来,而“天使的问题”早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是诗中直接提及“生活”)。那么,何为“天使的问题”?怎样理解此处所说的“天使”? 根据上下文推断可知,这里所说的“天使”并不具有其在宗教中的原初含义及引申义,也不同于赖内·马利亚·里尔克诗歌里的“可怕的天使”[1],而只是被还原为一种非人间的、高踞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飞翔物。联系诗中前面所述的菠菜之“绿”,可以说那种如“天使”一般的生活“形象”与生活方式的单纯性、抽象性,正是菠菜之“绿”的单纯性的极致,这种过于单纯的生活“形象”和生活方式,势必会引起警惕和“回避”。臧棣后来写过一首《天使政治学丛书》(2011),其中写到:“没有一座天堂能经得起我们的怀疑。”而另一首《必要的天使丛书》(2013),虽然借用了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文集的标题,但呈现的是十分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包含了痛彻心扉的个体性体验。臧棣还有一篇题为《绝不站在天使一边》的短文,是讨论诗歌中的所谓边缘与中心问题的,他赞成南非诗人布雷腾巴赫提出的“要保持批评的态度,绝不能站在天使一边”,认为“边缘离天使太近,离历史太远”,因而“必须取消边缘”,回到对历史现实的关注[2]。 自这三行以下,《菠菜》的主题逐渐显露。接下来的一行诗非常重要,是一个判断句“菠菜的美丽是脆弱的”。何以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显然,这种“脆弱”性部分地来自菠菜之“绿”的单纯性,它虽然“美丽”,但却是“脆弱”的;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当我们面对一个只有50平方米的/标准的空间时,鲜明的菠菜/是最脆弱的政治。”这三行诗是全诗用力的着眼点,也是彰显全诗主旨的最核心的句子。如果说在“菠菜的美丽是脆弱的”这句之前,都还是对菠菜及“你”“我”与菠菜关系的直观描述,那么从该句起,诗人将目光聚集在切近的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存处境,深入其内在进行思索和剖析。可以看到,相对于生存处境的窘迫和严峻而言,有着单纯绿色外表的菠菜的“美丽”无疑是“脆弱”的,其“脆弱”性与生存处境的巨大压力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从而成为一种“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是一种泛化的政治,指盘踞在人们观念里、支配其言语行为的某种意识形态或心理机制。“50平方米的/标准的空间”对于某一个体而言是具体而微的生活境遇,它直陈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状况和社会生态——包括那种“标准”化指令对人们思维与生活的制约。按照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看法,“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s)。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3]。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文化潮流的冲击下,“50平方米的/标准的空间”已不再具有私密性和稳固性,而是因挤压、剥蚀而暴露无遗且无处躲藏,“脆弱”得不堪一击。这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政治。 对“空间”的观察和书写是一项重要的诗学命题。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其著名的《空间的诗学》一书中认为:“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4]这正是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这首以反思“空间”为主题的诗的价值。 究竟应该怎样应对那种“脆弱的政治”导致的后果呢?在诗的结尾部分,诗人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菠菜:“表面上,/它们有些零乱,不易清理;/它们的美丽也可以说/是由烦琐的力量来维持的”。也就是,返回到如“零乱”“不易清理”的菠菜一样的日常生活当中,担负起它的无尽的“烦琐”、枯燥和平淡。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甜蜜与幸福如同菠菜的“美丽”,“是由琐碎的力量来维持的”,这无疑是一种富于辩证意味的生活哲学。在此,“烦琐”不只是风格意义的,而更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形态及其美学特征。显然,对菠菜的重新审视引起了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深层反思,这一反思在诗的最后两行戛然而止: 而它们的营养纠正了 它们的价格,不左也不右。 “营养”与“价格”巧妙地指向了一种内与外的关系,“纠正”以及“不左也不右”中的“左”和“右”这对往往与特定历史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范畴,在此显然被讽喻性地借用了,恰切地回应了上述“政治”题旨。 现在,可以对《菠菜》中的几种人称略作探究了。这首诗的人称转换十分频繁,除明确指代菠菜的“它们”外,还有“你”“我”“我们”三类人称在交错使用。那么,这几种人称分别指代什么?其在诗中的关系如何?“我”的指代可能好理解,应当指言述者或观察菠菜的诗人本身;而“你”所指的对象却要模糊许多,既可以指诗人的一个亲密的对话者,甚至可以明确为他生活中的伴侣——即与“我”组成“我们”、共同居于“50平方米的标准的空间”的那个人,要是这样解释行得通的话,那么全诗的语气就是一种倾诉的语气,但这种倾诉并不是单向的,还须有一个倾听者或对话者,双方能够构成一种言述—倾听的关系。同时,“你”也可指“我”的替身即另一个“我”,这个“你”可被看作是从“我”中分裂出去的,倘若如此的话,这首诗就成了一种充满自审、反思的独白或絮语,所有与“你”展开的对话、问询最终都指向了“我”自身:“为什么菠菜看起来/是美丽的?为什么/我知道你会想到/但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提问便成了一种无对象的自我提问。当然,还可以极端地认为“你”一无所指,或者只是一个缀词或语气词,如此阅读起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 《菠菜》是一首典型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它的主题和表达方式显示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某些新的趋势。由于普通之物的进入和对日常性的关注,这首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人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人那样,拘泥于一种所谓的“不及物”写作,而是将诗歌的笔触指向了平凡、琐屑的现实生活。“不及物”写作由于过分强调诗歌的纯粹性与自我指涉而放弃了直面现实、介入现实的责任,因而丧失了应有的向现实生活发言的能力。 在《菠菜》一诗中,菠菜其实仅是一扇窗口或一个媒介。它朴素得只给人留下纯然绿色的印象,它是“美丽的”,同时这种“美丽”又是“脆弱的”,正是它单纯的绿色把诗人引向了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菠菜是人们每天遭遇的食物(蔬菜)中的一种,据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即“营养”),人们从市场上购买它,与商贩讨价还价,然后把它带回家中。在这样的过程中,菠菜充当了一个中介,使人们所居留的相对独立的“空间”与外界广阔的现实生活发生了关联。不仅如此,菠菜被带回家后,在成为桌上的一道菜、一种食品之前,它还要经过精心的清洗、烹饪,但“它们有些零乱,不易清理”,因此“它们的美丽也可以说/是由烦琐的力量来维持的”。也就是在“冲洗”菠菜等一系列“烦琐”行为中,居家之内的所有成员在已有的关系之外,平添了一种新的关联。由于菠菜是人们每天都面对的现实,所以每天人们都要在“冲洗”菠菜之类的行为中,进行这种新的关联的情绪操练。因而在诗中,菠菜既是把个人(比如说书斋里的某个人)与现实生活连接起来的通道,又是诗人观察和思索这种生活哲学的窗口。 从隐喻的意义来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们希望发明一种方式,像连接个人与现实生活的菠菜一样,重新构筑诗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为此诗人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应该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新诗史上持续困扰诗人写作的关键议题之一,曾得到反复的不同层面的讨论。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学情境中,诗人们一度试图对这一关系作出新的诠释:“先锋诗一直在‘疏离’那种既在、了然、自明的‘现实’,这不是什么秘密;某种程度上尚属秘密的是它所‘追寻’的现实。进入90年代以来,先锋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动向,就是致力强化文本现实与文本外或‘泛文本’意义上的现实的相互指涉性”[5]。“文本意义上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事态的自然进程,而是写作者所理解的现实,包含了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6]。这被认为是诗歌处理这一问题的最理想状态。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代表性诗人王家新提出:“把我们的写作从一个‘纯诗的闺房’中引出,恢复社会生活和语言活动的‘循环往复性’,并在诗歌与社会总体的话语实践之间重新建立一种‘能动的震荡’的审美维度。”[7]他期待的正是将诗歌重新带入现实生活场域的“菠菜”。 在谈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时,臧棣曾作出过一个著名的表述:“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与语言的欢乐。”[8]他本人在90年代的颇具创造性的诗学理想和写作实践恰好充任了这番表述的例证,能够体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在语言探索方面可能达到的深度及面临的困境。 关于“语言的欢乐”,臧棣早在90年代初完成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一文中,就主张语言特别是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技艺在诗歌中的优先地位:“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的肌体上使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技巧永远就是主体和语言之间相互剧烈摩擦而后趋向和谐的一种针对存在的完整的观念及其表达。技巧也可以视为语言约束个性、写作纯洁自身的一种权力机制”[9]。在较晚近的一次访谈中,他还提出“诗歌就是不祛魅”的观点,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总想着要重新发明语言”,“诗歌的特性也是由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所触及到的某种特殊的行为来完成的”,“每一个真正的诗人身上都寓居着一位贵族……这个贵族的生存空间是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多重关系”[10]。这种强调诗歌“特殊性”“贵族化”的观念,承接着中外现代诗歌中的“为诗一辩”的传统。当然,在当前变幻多端的诗学语境里,这种源自语言的“可能性”和“为诗一辩”的勇气而衍生的写作信念,其诗学效力和限度几乎同时显现。如何延伸和拓展为语言的“可能性”所激活的诗学空间,或许并非臧棣一个人需要面对的难题。 臧棣的“重新发明语言”的意图,使得他的不少诗作表现出一种综合的对诗歌写作本身进行反思的意识和能力,成为某种意义的“元诗”: 每个松塔都有自己的来历, 不过,其中也有一小部分 属于来历不明。诗,也是如此。 并且,诗,不会窒息于这样的悖论。 而我正写着的诗,暗恋上 松塔那层次分明的结构—— 它要求带它去看我拣拾松塔的地方, 它要求回到红松的树巅。 ——《咏物诗》 不难发现,在臧棣的诗歌中,“写作的可能性”伴随写作进程的展开被探讨着,或者说,其诗歌写作就是有意识地对“写作的可能性”、写作行为本身乃至写作的终极目的进行勘察和追问的过程。这种反思意识在写作中的渗入,赋予了臧棣诗歌以变动不居、而又相对稳定的样态,其中蕴藉着多股相互冲突却并非相互抵消的力量:它既瓦解着过往的囿限又确立着新鲜的可能,既消除着预设的韵律又构筑着内在的节奏和旋律,在不断的超越与回溯、毁灭与复苏的共生中,完成着经验和语词的重组,由此体现出一种“语言的欢乐”。 而“历史的个人化”的确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总体趋向之一。除去那些极端的遭受诟病的“私人化”写作,中国20世纪90年代涌现了众多真正的“个人化”诗歌,它们如陈超所描述的那样,“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判断力去处理生存和生命中的问题”[11]。臧棣当然不会赞同“私人化”写作,却也极力反对诗歌对历史、现实的直接书写。出于对诗歌与现实之间过于简单的关系的反拨,臧棣的不少诗歌显出“即兴”色彩和“喜剧”精神,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充满智性的语词“嬉戏”,并因此发展出一种富于启发性的观念——将诗歌比喻为“风箱”。在臧棣那里,“风箱”既“散发着日常生活的气息”,又具有“往复不已”的劳作的特性,“风箱”的结构之空与不断更新的特点,使这一寻常而奇特的事物中,几乎隐喻着关于诗歌写作的全部秘密:“咫尺之远,新的事物被创造着,并和人类对生命的体验以及对历史的探索融为一体”;借助于“风箱”这一譬喻,臧棣想呈现诗歌与现实之间的良性关系及诗歌抵达历史深处的暗道:“如果我拉动风箱的把手,我也许会给诗歌的‘空’带去一股强劲而清新的现实之风,我也不会忘记在把手上镂刻一句铭文:向最高的虚构致敬。”[12]这或许是让诗歌保持活力和有效性的通途。 不管在诗歌中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臧棣都毫不掩饰对日常生活特别是生活细节的迷恋。他的诗集《新鲜的荆棘》的开篇之作,就是一首《日常生活》:“每天清晨,我的邻居/会向路边的花草弯下身去,/样子就像一个厨师/捡掉在地板上的大蒜。”采用的是一种基于细节的白描。而在《新鲜的荆棘》一诗中,更是不厌其烦地叙写了烹饪荆棘的过程:“他用香油拌料酒/泡软了去过皮的荆棘,/决心将它们的生硬和锐利/征服在不粘锅内——把姜丝切成胡须,/把花椒和辣椒放在一起,/把枸杞撒入啤酒,/把狗肉换成兔子肉,/把油烧开,把抽油烟机打开,/把锅盖盖好,把火苗调小,/把专注挪开十五分钟,/把回味提前两分钟,/把它们再焖一会儿。”这种孜孜于日常生活细节的经营,正是对日常生活政治的抵制。 ①有的版本是28行,即“看见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天使的问题”被分成了两行:“看见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天使的问题”。 ②这部小说颠覆性地改写了名著《鲁滨逊漂流记》,讲述鲁滨逊未能驯服野人礼拜五、反遭其同化的故事,其中有人与神秘植物做爱的情景。关于《菠菜》中这一诗句与图尔尼埃小说关联的论述,参阅胡续冬《诗歌让“不存在的天使”显现》,见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