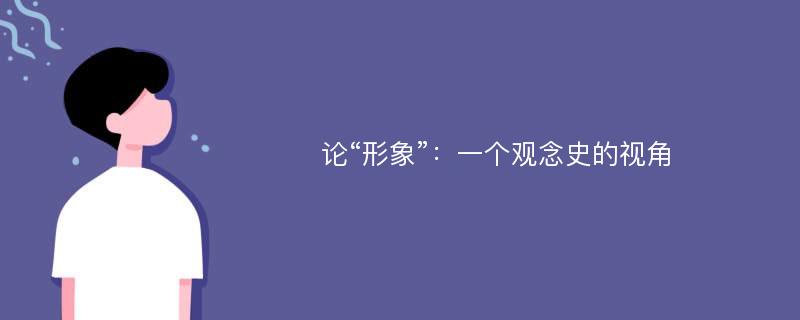
摘 要:“形象”是一个视觉用语,指人们描绘或记录视觉感知的产物,人们却在各自不同的知识领域(例如,图像解释学、象征论、位相学)的意味上使用该词。“形象”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衍变史:从古希腊时期到16世纪, “模仿”“譬喻”等观念是文艺批评的主流词汇,而“形象”本身只是隐含的观念。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和黑格尔进而把形象作为诗学、美学的理想观念,甚至是文学艺术中无所不包的精神存在。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论述了形象的观念。20世纪理论家从原本的、引申的、比喻的意义上分析了形象的本质,尤其是对精神形象、词语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形象;观念史;视觉形象;想象;幻想
“形象”(Image, 拉丁语词源imago)首先是一个视觉用语,指人们描绘或记录视觉感知的产物,I.A.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Ivor Armstrong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指出,文学总是过分重视形象的感觉性。形象往往强调诉诸感官的各别性,而且形象的符号化处理(signal processing)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却在各自不同的知识领域(例如,图像解释学、象征论、位相学、神学/宗教哲学)的意味上使用该词。形象是对认知对象(例如,自然物体或者人为创造物)的感官印象、感知或想法,以及语言层面的概念、判断和结论,甚至理论。古典哲学总是强调,形象是认识世界或用以再现并理解现实的、完美的、透明的媒介,尤其是形象与现实事物的相互关系,但是超验哲学(例如,胡塞尔)却否定了形象关系的可能性。人们需要阐释形象,因为形象是一种符号,它存在于一个不透明的、扭曲的和任意的再现机制,和意识形态化神秘化的过程中。
J.M.默瑞《心灵的各疆界》(John Middleton Murry, Countries of the Mind, 1931)之“隐喻”(Metaphor)指出,形象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形象,也可以是听觉的、或者完全是心理上的。[注]J. Middleton Murry, Countries of the Mind, second serie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1-1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写道:“视觉的形象是一种感觉或者说知觉,但它代表了、暗示了某种不可见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它同时既可以是某种事物的呈现和再现。”[注]203.在20世纪,语言与图像(Image)是最重要的描述世界的方式,苏珊·桑塔格《论摄影》(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1977)之“形象的世界”写道:“现实总是通过图像所给予的报道来加以解说(Reality has always been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reports given by images);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一直试图通过建立非图像认识世界方式的标准来松弛我们对图像的依赖性。”[注][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二是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流域统一管理和水务一体化管理。一方面,成立了省属四大江河流域管理局,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配力度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强化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着力推进市、县一级水务一体化管理体制。
一 “形象”的观念史
“形象”(image)观念在欧洲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衍变史:从古希腊时期到16世纪,模仿论强调表现与现实事物的相似性,“模仿”(μíμησιç, mīmēsis)“譬喻”(figure, figure of speech)等观念是文艺批评的主流词汇,然而,“形象”本身只是隐含的观念,虽然中世纪出现了“幻想”(fancy)一词,但直到17世纪该词才成为精神形象的一种。在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和黑格尔进而把形象作为诗学、美学的理想观念,甚至是文学艺术中无所不包的精神存在。黑格尔把“形象”部分等同于逻辑学中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形象”(image)观念被视为文学艺术中超越性的、绝对的精神形象,与抽象的观念相对应。
在古希腊文学中,修辞学对于语言表达来说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修辞性譬喻(rhetorical figure or figure of speech)是文学形象最显著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古希腊文学的表达是比喻的、具象的(figurative)。形象是一种基于视觉感官的人为技巧(artifact),是现实事物的语言表现或者以音乐、舞蹈、美术等的意义传达方式。《伊利亚特》极其普遍地采用“譬喻”(figure),包括品质形容词、史诗式明喻、隐喻等,例如,“一番话掀腾起澎湃的心浪,在全体兵勇的胸腔”“长了翅膀的话语”“酒色的的大海”“沉雷远播的宙斯”等。[注]荷马:《伊利亚特》,陈中梅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萨福《暮色》写道:“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注]《古希腊抒情诗选》,水建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14页。
在欧洲浪漫主义晚期,与以科学/学科的方式追问形象的意义不同,联觉(作为一个新的、神秘的、综合性的观念)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感官与各种感觉形象的稳固关系,对于现实事物的记忆与再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形象自身的意义。歌德《论色彩》(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ZurFarbenlehre, 1810)较早论述了色彩的联觉(Synesthesia)。波德莱尔《应和》(Correspondances)一诗最显著的特征是表现了产生于原初的天主教思想的联觉,“自然是一个圣殿,在那里,有生命的列柱,常发出隐约的话语;人经过那里,行游在象征的森林,它们用熟稔的眼光注视他。像悠长的回声遥迢地溶合在一个深邃而幽暗的一体中,浩渺的,像黑暗也像光明,芳香、颜色和声音相互呼应。新鲜的芳香,像儿童的肌肤,柔和,如双簧管,绿的,如草茵,——还有别的,腐朽、富丽,征服人的,这些无限的事物,弥漫着,像龙涎香、麝香、安息香、乳香,它们唱颂精神与感官的沟通。”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较早完成了模仿论的理论化。柏拉图《理想国》对比了模仿(mimesis)与叙事(diegesis),认为“模仿”是形象创造的基础,“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真相了,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或任何其他媒介中显示出来的影像看它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因此,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者真实隔着两层。……因此,模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而这似乎也正是它之所以在只把握了事物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表像的一小部分)时就能制造任何事物的原因。”[注][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4, 393页。而后,亚里士多德《诗学》再次强调了“模仿”与相似性,“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Dithurambos)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Aulos)和竖琴(Kitharis)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领。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人们乐于观看艺术形象,因为通过对作品的观察,他们可以学到东西,并可就每个具体形象进行推论,比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某人。倘若观赏者从未见过作品的原型,他就不会从作为摹仿品的形象中获取快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引发快感的便是作品的技术处理、色彩或诸如此类的原因。”[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7,47页。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九章集》(Plotinus,The Six Enneads)认为艺术产品没有完全表达出美的理念,因为物质材料阻碍着美的印入。外部世界是无生命客体的幻影,只有诗人的知性才能赋予外部世界以活力。[注]参见[英]R.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中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神学)对“圣经”的阐释往往强调字面意义、道德意义、象征意义和神秘意义(参见但丁《飨宴》)。形象的观念在中世纪逐渐转向象征和神秘意义,寓意故事(allegory)、梦幻与宗教性象征是中世纪文学最显著的特征,文学批评由此区分了“形象”(image)与“譬喻”(figure)。此外,寓言(fable)是欧洲传统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类型,整个中世纪寓言文学尤其繁荣,从伊索寓言、(基督教)圣经寓言、勒那传奇(Roman de Renard)、拉伯雷的寓言故事,到拉封丹寓言,寓言总是具有鲜明的形象(包括动物、幻想的动植物形象),并强调类比或者各种不同的事物/观念的联合。T. S. 艾略特《但丁》(Thomas Stearns Eliot, Dante, 1932)强调了但丁用形象表达思想,用寓言表达心灵的方式,“寓言意味着清晰的视觉形象。如果清晰的视觉形象再被赋予某种含义,那么它的强度就会大大加强,……但丁的想象是一种视觉性想象(visual imagery)。它不同于现代静物画家的视觉性想象;但丁生活在一个人们还能够看到幻像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想象力是视觉性的。它是当时的一种心理习惯,我们已经不记得它的诀窍了。”[注][英]T·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 77页。但丁《喜剧·地狱》(Durante degli Alighieri, La Commedia: Inferno)写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因为我在离弃真理之路的时刻,充满了强烈的睡意。但是,走到使我胆战心惊的山谷的尽头,一座小山脚下之后,我向上一望,瞥见山肩已经披上了指导世人走各条正路的行星的光辉。这时,在那样悲惨可怜地度过的夜里,我的心湖中一直存在的恐怖情绪,才稍微平静下来。犹如从海里逃到岸上的人,喘息未定,回过头来凝望惊涛骇浪一样,我的仍然在奔逃的心灵,回过头来重新注视那道从来不让人生还的关口。”[注][意]但丁:《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ymage(法语imagene,普罗旺斯语image,拉丁语imago)原本指绘画或者雕塑作品的相似性(artificial resemblance)。13世纪英语中,该词指任何艺术上的摹仿或表现形式,1225年《圣徒凯瑟琳》(The Martyrdom of SancteKaterine,1476)写到了黄金的雕像:Ichulleletemakiete of gold an ymage as cwenicrunetantswa me schalamitte burh setten hit on heh up. 手抄本《世界诅咒》(Cursor mundi M. 2298,?1300)写到了雕像:For freinddedtattam was dere did make ymage o metal sere. 雷·弗兰兹《“形象”一词的起源》指出,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既已区分“形象”(image)与“譬喻”(figure),但是这个时期的批评词汇是来自修辞学、逻辑学的术语,专有词汇Icon(画像)意味着某物的图像,修辞学的一般词汇Enargia(vivid, lively description,生动的描绘)意味着让读者像看见与实际事物一样的过程;虽然他们的诗作具有极其丰富的形象特征(imagery),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在使用任何“形象”,而是“譬喻”这一修辞表现手法。[注]Ray Frazer.The Origin of the Term Image,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27,No.2 (Jun.,1960),pp.149-161页。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1949)之“想象”(imagination)认为,想象(imaging)不应当被描述为以一种特殊的状态看见图画(seeing of pictures),心灵(mind)也不是一个看到心灵图画(mental pictures),听见再现的声音和乐曲的“场所”。赖尔认为把心灵的(mental)等同于想象的(imaginary)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人们称之为视觉心像(visual images)、心理图像(mental pictures)、听觉心像(auditory images)以及观念(按某一种用法)的东西,通常被认作这样一些实体:它们真实存在着并且存在于外部世界之外的其他某个地方。因此,心灵被指定为它们的剧场。但是我将试图证明,尽管人们不断地在他们的心中看到各种事物并且在他们的头脑中听到各种事物,可是这个为人熟悉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他们如此看见和听到的事物存在着,也不能证明人们事实上正在看见或听到这些事物。”“我们通常可以正确的称之为想象性(imaginative)的行为,种类繁多而且大不相同。……并不存在任何专门的想象官能,一心一意的从事各种幻想出来的视觉活动和听觉活动。相反,看到一些东西是想象的一种运用,像一头熊那样吼叫则是想象的另一种运用;用心灵的鼻子闻到一些东西是一种不常见的幻想动作,装病则是一种常见的幻想动作,如此等等。”“认识论者长期以来一直鼓励我们去假定,一幅心理图画或一种视觉心像与一种视感觉的关系有点像一种回声与一种声音、一块伤痕与一次打击、或镜中的一个映像与它所反映的脸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些,人们曾经假定,我的看到或听见或闻到活动与知觉活动中的那种纯粹为感觉认知的要素相符合,而不与构成了认出活动或看出活动的那种要素相符合,亦即作像是一种近似于感官知觉的东西,而不属于智力的一种功能,因为它的确不在于具有真正的感觉,而在于具有影子感觉(shadow-sensation)。但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注][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70, 283, 294页。
一是从人员构成角度探讨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华黎明等(2008)认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主要由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志愿者组成。余熠(2009)则将非营利组织人员分为比较笼统的三大类:董事会成员、公职付薪职员和志愿者。
在古代罗马,普鲁塔克提出了“诗如画”(utpicturapoesiserit),本·琼生重申了模仿论和诗画同类,“诗如画”在18世纪重新被人们广泛关注。[注]参看彭建华:《当代比较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369—373页。18世纪的批评家、思想家更多强调词语形象(word-images, verbal images),印象/记忆形象(impression, memory images)。大卫·休谟认为,(视觉)形象是自然事物(即外在客体)通过感官或者幻想(fancy)投向心灵的精神幻景(mental vision)或观念(ideas),《人类理解研究》(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之“观念的起源”把知觉分为思想/观念、印象,“记忆和想象这两种官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与活力。这两种官能即在最大的力量活动时,我们至多也只能说,它们把它们的对象表象得很活跃,……诗中的描写纵然很辉煌,它们也不能把自然的物象描绘得使我们把这种描写当真实的景致。最活跃的思想比最钝暗的感觉也是较为微弱的。”[注][英]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页。
在特定的认知维度上,形象与想象是十分近似的、现实事物在精神上的表现形态,再现与想象都与“观看”(observing, viewing)密切相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ikel Dufrenne, 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esthétique, 1953)首先区分了想象的真正先验方面和想象的经验方面,并把先验的想象与经验的想象结合起来,强调主体性在现实事物与形象之间的介入作用,呈现出现实事物与形象二者的分离状态,模仿论所赋予形象的意义不再是稳定的、可依赖的,杜夫海纳进而指出人们需要阐释形象,“在先验方面,想象应该是一种观看的可能性,这种观看以‘景象’为其关联物。”“先验应该是由想象即作为自然光的‘我’承担的观看能力。形象——自身是使对象被人们感受的原始呈现和使对象变成观念的思维这二者之间的一个中项——使对象得以显现,亦即使对象作为再现物呈现,而想象则可以说是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纽带。因为尽管想象是使人们观看或使人们想到什么的能力,它也是植根于肉体的,就像对模式的探讨向我们所提出的那样。”“想象为了扩大外观和给外观以活力给知觉带来的东西实际上不是无中生有,它是以实际经验中已经构成的知识来滋养再现的。更确切地说,它起双重作用:它调动知识,并把通过经验获得的东西转变成可见的东西。关于第一种作用,我们认为应该把只是算作想象,因为知识确实是形象的一种潜在状态,形象的意象关联物就是可能事物。”“最后,形象进入知觉以构成对象。形象不是存在于意识中的一种材料,而是意识把自身向对象开放并根据自己之所知从自身深处预示对象的某种方式。”[注][法]米盖尔·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82, 385, 387页。从心理现象学的符号出发,萨特《想象论:想象的心理现象学》(Jean-Paul Sartre, L'Imaginaire: Psychologiephénoménologique de l'imagination, 1940)把心灵形象(image mentale)与想象二者看作类同的观念,并把肖像、漫画、梦、象征列入形象的家族(La Famille de L’image)。萨特认为,形象具有鲜明的意向性结构(Structure Intentionnelle)。自发性(spontanéité)的形象是一种意识(L’imageestune conscience),是近似观察的现象(Le phénomène de quasi-observation),想象性意识假定其对象类似虚无(La conscience imageante pose son objet comme un néant)。形象是显现在人们的反思性描述中的超验性意识,“形象的对象只要是被想象的,……被想象的对象的这种实际上的不在场,这种本质上的虚无便足以使之与知觉的对象区分开来。”“想象的活动,同时也是构成性的,孤立的和幻灭性的。”[注][法]萨特:《想象心理学》,褚朔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在现实事物与形象的关系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 1921)深刻批判了精神形象观念,强调了形象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本身,进而把形象称为逻辑形象,形象即是它自身所表现的意义,“我们为自己创造事实的形象(das Bild)。形象在逻辑空间中描述情况(die Sachlage),即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形象是现实的模型。这种形象的要素,在形象中与客体相对应。形象的要素,在形象中代替客体。形象是这样构成的:它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互相结合着。形象就是事实。形象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这件事情表明各物也是这样互相结合起来的。形象的要素的这种结合称之为它的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可能性则称之为这种形象的描画形式(Form der Abbildung)。表现形式是一种可能性:物也像形象的要素一样是互相结合起来的。形象就是这样与现实联系起来;它达到现实。……使它成为形象的所描画的那种关系,也属于形象。所描画的关系是由形象的要素和事物同格(Zuordnung)而构成的。这些同格好像是形象要素的触角,形象就是用这些触角同现实接触的。要成为形象,一件事实必须与它所描画的东西有某种共同处。在形象和被描画的东西之中,必须有某种统一的东西,使得前者一般地能成为后者的形象。形象能依照自己的方式——正确的或错误的——来描写现实,所以必须与现实具有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其描画形式。形象能反映任何现实,它具有现实的形式。空间形象是一切空间之物,颜色形象是一切颜色之物等等。可是形象不能反映自己的描画形式;它把这种形式表明出来。形象从外面来描写自己的客体(它的观点就是它的描画形式),因此形象描写自己的客体有正确的或错误的。但是形象不能使自己置于其描画形式之外。每一种形象,不管具有何种形式,要一般地描画——正确的或错误的——现实,必须与现实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形式就是逻辑形式,即现实的形式。如果描画的形式就是逻辑形式,则形象称之为逻辑形象(das logischeBild)。每一种形象也是一种逻辑形象。(反之,比如,不是每一种形象都是空间形象。)逻辑形象能描画世界。形象与所描画的东西共同具有的是描画的逻辑形式。形象用描画原子事实的存在与不存在的可能性来描画现实。形象在逻辑空间中表现可能的情况(Sachlage)。形象包含着它所表现的那种情况的可能性。形象符合或不符合现实;它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真的或是假的。形象通过表现形式表现它所描写的东西,不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形象所表现的是它的意思。”[注][英]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28页。
源自基督教神学的转喻,自然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其存在状态是有缺陷的;在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 1079—1142)之后,雨果式的辩证法(参见《巴黎圣母院》)却促使人们对怪异丑陋事物的兴趣。在整个19世纪,形象作为诗学、美学的理想观念,甚至是文学艺术中无所不包的精神存在。随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传统的模仿理论所假定的形象与现实事物(即自然)的关系在遭到了强有力的、普遍的质疑,甚至极端性的否定,由此二者之间简单的、澄明的、直接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介入,更高的心灵想象的介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心灵/精神的形象独立于自然(现实事物),超越了自然;人们进而否定了由单一的感官所形成的感觉/知觉,多种感官联合形成的联觉形象逐渐被心理学、美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所接受。“词语形象”的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趋向于“词语即形象”的文学乌托邦,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eyer Howard Abrams,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1953)可以部分证实这一观点。
与柏拉图神秘的、终极真实的“理念”近似,黑格尔《美学》(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über die sthetik, 1829)之“题材的划分”认为艺术即绝对理念的表现,“我们既已把艺术看成是由绝对理念本身生发出来的,并且把艺术的目的看成是绝对本身的感性表现,……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想象,天才和灵感”认为艺术创造的最杰出的本领是想象,而现实的外在形象是创造的材料,“不要把想象和纯然被动的幻想混为一谈。想象是创造性的。⑴属于这种创造活动的首先是掌握现实及其形象的资禀和敏感,这种资禀和敏感通过常在注意的听觉和视觉,把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的图形引入心灵里。此外,这种创造活动还要靠牢固的记忆力,能把这种多样图形的大千世界记住。……⑵其次,想象还不能停留在对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的单纯吸收,因为理想的艺术作品不仅要求内在心灵显现于外在形象的现实界,而且还要求达到外在显现的是现实事物的自在自为的真实性和理性。……⑶通过渗透到作品全体而且灌注生气于作品全体的情感,艺术家才能使他的材料及其形状的构成体现他的自我,体现他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特性。”[注][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7,357—358页。概言之,黑格尔倾向于把形象归属于“精神事实”或“概念总体”,把词语形象(或者绝对理念的赋形)等同于创造性的想象,即一种心灵/精神上的存在状况。由于具有对现实事物(自然)的超越品质,心灵/精神的形象总是超越人类的感官本身。从现实事物对(精神的)理念的追求出发,黑格尔从哲学和文学行为上否定了词语形象对自然的模仿,由此与传统的模仿论决裂。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十分重视文学“想象”,柯勒律治《文学传记》响应了黑格尔《美学》的想象理论,区分了第一位的想象、第二位的幻想”[注]Samuel Taylor Coleridge.BiographiaLiteraria;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vol 1,1817:202. 柯勒律治《老水手谣》重新燃起了对基督教寓意与象征的热情,表现了形象的神秘意义,“人声喧嚷,海船离港,兴冲冲,我们出发;经过教堂,经过山岗,经过高高的灯塔。……冰海上空,一只信天翁穿云破雾飞过来;我们像见了基督的使徒,喜滋滋向它喝彩。我们喂的食物它从未吃过,它绕船飞去飞回。一声霹雳,冰山解体,我们冲出了重围!”[注]杨德豫译:《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94页。
在古希腊,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表现与现实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却并不直接强调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像本身。赫拉克利特(, Hērákleitos)最早提出了词语/表述(Logos)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把现实世界看作是语言、艺术的模型。模仿(, mīmēsis)与“譬喻”(figure)这一表现技巧密切相关,模仿理论假定语言形象与现实事物存在着直接的、澄明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奥尔巴赫《摹仿论》(Erich Auerbach, Mimesis: Dargestellte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ndischenLiteratur, 1946)认为,荷马“所描述的事件的每一部分都摸得着,看得见,可以具体的想象出各种情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内心的活动也是如此:没有可以隐瞒的、不可表述的事情。”[注][德]埃利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值得指出的是,模仿论将持续到16世纪,甚至是古典主义时期,模仿被认为是艺术的基础。
第四,“自我造血”支撑可持续发展。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是要回答养老资源来源问题、资源提供者与资源需求者相结合的问题,而在智慧养老服务模式中,通过嵌入市场营利机制的方式,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功能优势与政府行政干预的功能优势,实现“两架马车”并驾齐驱促进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正是对核心问题的最佳回答。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主体在明确界定智慧养老服务范围的基础上,还能通过提供服务范围之外的一系列配套收费服务;另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链接养老服务资源,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自我造血”与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19世纪后期,心理学成为一门前沿性的人文学科,人们(例如,Francis Galton, Edwin Garrigues Boring, June Downey, Charles Baudouin, Hart)对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动觉等感官产生的不同形象做过无数次心理学实验。沃伦、韦勒克《文学理论》认为意象(Image)、隐喻、象征和神话属于同一个范畴,进而区分了静态形象(static imagery)、动态形象(kinetic or dynamic imagery)、移情(empathic)、联觉形象(synaesthetic imagery)等,并认为意象是诉诸感官的和审美的连续统一体,“意象(Imagery)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主题。在心理学中,意象(Image)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 形象的功能在于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的神奇结合,尤其是想象与重现。[注][美]沃伦、韦勒克:《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01页。
直到17世纪,随着现代科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形象(image, imagery)的观念开始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主导性词语。严格地说,奥古斯丁《忏悔录》并未提出语言具有图画性的观点,由于修辞学的传统逐渐走向没落,自然(nature)的观念替代了现实事物,由此也取消了(主体)外在与内在的二元结构,语言本身开始被认为是具象的(figurative),词语形象被认为是语言的内在品质。福柯《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之“相似性的想象”指出,16世纪后出现了“认知型”的转变,即新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新的“物的秩序”:想象是普遍观念,存在于心灵与肉体的结合体(人)之中,并生发出四种相似性(适合convenientia、仿效aemulatio、类推analogie、交感sympathies),“相似性位于想象一方(la resemblancese situe du cté de l’imagination),或者更为精确地说,只有救助于想象,相似性才能得到体现;反过来,想象也只有依靠相似性,才能得到实施。……如果没有想象,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就将不存在。人们能清楚地看到双重的必要条件:在被表现的事物中,必定存在着相似性的明显的呓喃;在表现中,必定存在着想象的始终是深刻的可能性。”[注][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2—93页。W. J. T. 米歇尔《图像学》认为,17世纪以来文学转变为朴素、明晰的风格,而形象的观念取代了“譬喻”(figure)。[注][美]W. J. T. 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25页。自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PeriPsychēs)到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 1689)以来,哲学家们往往强调精神形象(mental image)。此外,“形象”(Image)与“想象”(Imagination)在17—19世纪欧洲文学批评中总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在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1949)中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谢林《对人类自由本质及与之相关连联的对象的哲学研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都强调了知性的、精神的想象。
二 “形象”观念的实质与祛魅
什么是形象?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十分容易。这个问题曾经在某些时代被看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宗教、政治或者社会文化问题。对于一些知识学科,形象(imagery)往往是处于中心的位置。W. J. T. 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William John Thomas Mitchell,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1986)写到了形象的族类:图像与视觉形象、别的感知形象与表象、词语形象、幻影与精神形象,即严格的直接意义上的、引申意义上的、隐喻意义上的形象,在此,形象的分类是基于多重相似性(likeness, resemblance, similitude),“形象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符号,而颇像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被赋予传奇地位的一个在场或人物,参与我们所讲的进化故事并与之相并行的一种历史。”“对试图概览被置于‘形象’名下的所有现象的人来说,有两件事必定即刻引起其注意。第一件不过是此名所涵盖的广大事物。我们说图画、雕像、视觉幻象、地图、树状图、梦、幻象、景象、投射、诗歌、图案、记忆,甚至作为想象的思想,而这个名单的纯粹多样性似乎不可能导致系统的、统一的理解。第二件惊人的是,用‘形象’这个名称称呼所有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具有共性。最好是把形象看作一个跨越时空来自远方的家族,在迁徙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形。”[注][美]W.J.T.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陈永国译,第5—6页。米歇尔有意突出了词语的(Verbal)形象、精神的(Mental)形象,有利于澄清20世纪文学批评对形象观念理解的歧误;词语的形象包括隐喻(metaphors)和描写(descriptions),而精神的形象包括梦(dreams)、记忆(memories)、观念(ideas)和幻影(fantasmata)。
11月7日至9日,三天两夜,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中外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知名专家学者等约1500名嘉宾齐聚乌镇,纵论全球互联的历史,共话数字世界的未来。“物联网”“数字经济”“5G”“人工智能”成为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最耀眼的名词,它们让人类与未来连接,并由此畅想未来。
20世纪前期,精神形象的诸多歧义普遍引发了人们在分析哲学、现象学、心灵哲学上反思形象与描写对象的关系。形象既然是运用语言、音符、几何形状与色彩、形体与姿态等遵循特定的艺术的游戏规则或者图式化(schematic)原则创造出来的产物,人为的意图或者指涉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事实对象本身。作为象征的符号,形象本身是各要素的互相结合,并成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精神(mental)现实,不再依赖对事实对象的回指或者现象学式的还原。E. 庞德《规整和划分》(Ezra Pound, Pavannes and Divisions, 1918)强调了事物的心灵形象(mental image),形象(Image)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再现,是多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智力与情感的复合体(complex),……正是这种‘复合体’瞬间的呈现给人一种突然的解脱感。”[注]Ezra Pound,Pavannes and Divisions,New York:Knopf,1918:96.
当天夜里秦川将她占有,或者说当天夜里她将秦川占有,她认为后者或许更恰当一些。她不是随便的女人,她无比保守,可是见到秦川,她就想将自己交付出去。她不是淫荡的女人,她无比清纯,可是见到赤裸的秦川,她甚至想跪下去亲吻秦川的脚趾。那几天里,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合格的充气娃娃。
在《想象的愉悦》系列散文中,约瑟夫·爱迪生表达了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热情和赞美,较早区分了幻想(fancy)与想象(imagination),意义(Sense)和理解(Understanding),并认为语言形象是词语自身的属性,语言形象比真实事物本身更有力更生动。《想象的愉悦》(6月21日)写道:“在英语中,几乎没有什么词语就意义表达而言比幻想和想象的意义显得更宽松,更不受限制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严格定义并确定这两个词的概念,……通过想象的愉悦,我的意思是,即是原初从视觉中产生的愉悦,以我的预想,我将这些愉悦分为两种:首先谈论的是这些想象的第一位的愉悦,它们完全从我们眼前的事物生发而出;其次谈论这些想象的第二位的愉悦,它们是从可见事物的观念中流出的,当这些物体实际上并不在眼前,而是在我们的记忆中被唤起的,或者是对不在场或虚构的事物形成的十分近似幻像(Visions)。……那些想象的愉悦和另一个(Fancy)是一样强大,并具有良好的传播性。一个美丽的景象使得灵魂激动,像是一个(卓越的)展示;荷马的描述比亚里士多德的章节更能取悦读者。此外,想象的愉悦具有超越理解(Understanding)的优势,它们更加明显,更容易获取。只要睁开眼睛,场景即可进入。色彩在幻想(Fancy)中描绘自己,对于观看者来说,只需要少许的思想(Thought)注意力或者心灵(Mind)的应用。”[注]Joseph Addison.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Spectator.No.411,June 21,1712.《想象的愉悦》(6月27日)写道:“精心选择的词语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它的描述常常会给我们提供比事物本身更生动的观念。读者发现一个用十分强烈的色彩绘制的场景,并通过词语的帮助更多地在他的想象中描绘生活,甚于通过对他们描述的场景的实际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似乎描绘了更好的自然(Nature);确实,他接受了自然的景象,但却给它更有力的触动,增强了它的美感,使整个作品更加活跃,以至于从物体本身流出的形像与来自表现的形像相比显得微弱暗淡些。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对任何事物的调查中,我们只是把眼睛看见的描画在想象中,然而在诗人的描述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取悦过他的自由视角,并向我们揭示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部分,或者当我们第一次看到它时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当我们观看任何物体时,我们对它的整体观念可能由两三个简单的观念组成;但是当诗人再现它时,他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复杂的观念,或者只是使得我们生发出那些想象所最易感染人的观念。”[注]Joseph Addison.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Spectator.No.416,June 27,1712.值得指出的是,Fancy(即fantasy, phantasy的缩略形式,意为“幻想”)是一个1360—1400年前后出现的英语新词,表示“感官的幻像,幽灵”。约瑟夫·爱迪生、黑格尔、柯勒律治把“幻想”看作是一种显著的精神形象。
D.-H. 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进而突出了形象在心理学、文化交往行为中的符号意味,“形象”是一种思想,或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有时是一个纯粹的“信号”。“形象不是在类比意义上(它或多或少像……),而是在参考系意义上的形象(按照光存于描述的一种思想,—个模式、一个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形象)。”“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或还可这样表示: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或赞成了,宣传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形象是描述,它是感情和思想的混合物,必须抓住其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反响。……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在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注视者文化的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形象是语言(关于他者的语言);在此意义上,形象显然反射出了它所指称的、表示的现实。然而真正的问题在形象的逻辑性,在于其‘真实性’,而非其‘错误性’。因而研究形象,就是要弄清楚构成它、认证它的因素;如有必要,还应弄清使其相像于其他人或原始形态的原因。”
关于形象的意义,符号学认为形象(image)是一个特殊的、用以描述心灵/精神领域的符号(signal),它蕴涵一种或多种指向性的意义,甚至直接或间接指示某个主题及相关信息(information)与信息传达功能(function)。作为象征的符号,形象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出某些意味的心灵图像(mental picture),伊瑟尔《阅读行为》写道:“意象突出了某种东西,如被指示的那样。这种东西既不能等同于特定的经验对象,也不等同于被指示的对象的意义,因为它超出了感觉,但又尚未完全概念化。”“意象是观念化的基础。它与非确定或空缺相关联,赋予观念化以存在。它同样创造可以想象的革新,这些革新来源于对现有知识的拒绝或者产生于符号的不同寻常的组合。”[注][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74, 176页。
构什么?几何图形是由点与线构成,对于线基于尺规可以构造直线与弧线.因为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所以构直线其实就是构造两点;因为弧线取决于圆心与半径,圆心与弧上任一点确定,其弧线也就确定,所以构造弧线也是构造两点.总而言之,可以明确构什么?就是构造点.
胡塞尔《精神现象学》认为,形象是意义的完成(Erfüllung)。萨特《想象论》论述到了符号与形象的关系,即形象的形成是通过对知觉上的缺陷作出补充的意向达到的,形象近似于速写的简略图画(les dessins schématiques)。在艺术史上,艺术创作的形象作为记忆的代码往往是图式化(schematic)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之“通过艺术的视觉发现”在区分了回想(recall)和辨认(recognition)之后指出,人们可以选择性地记起视野里的景象/事物,图式化的图像是人们在一定范围内对其记起(remembering)的任何东西进行编码的结果,“我们的博物馆向观众展示了种种令人炫目而惘然的图像,这些图像的范围之广,足以和大千世界的自然造物相匹敌,……它们都出诸不同文化和不同气候中的人们的梦想与梦魇。”“凡是能用符号编码的东西,相对来说也就更容易追溯和回忆。怎样画这个或那个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简单的编码方法。对图式的需要其实是对代码的需要。艺术史上有许多风格仅仅是用这些现成易记的代码进行创作。”[注][英]贡布里希:《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范景中、杨思梁等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第1页。
HS-SPME萃取及进样过程由Gerstel公司多功能自动进样系统(MPS 2)完成,萃取头为2 cm 50/30 μm DVB/CAR/PDMS三相萃取头。
三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象
黑格尔的形象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提供了最初的基础和启发,然而唯物论的立场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新回到现实事物与词语形象的关系上,而且关于未来的“自由世界”的人类理想和社会进化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坚信词语形象应该高于现实事物。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中最初提出了反映理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道:“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第4版第15页。1905年日内瓦俄译本第12—13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Spiegelbild译作‘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十分无力地’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是译‘反映’,而不是译‘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作Abbild(反映、模写、映象)来使用的。”[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页。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形象”是一个核心观念,即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根本特征,文学创作即是形象创造的活动。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再现,形象是反映过程的理想结果,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如科学、意识形态、道德、艺术、宗教,在精神上获得客观现实。形象出现在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中,并将材料再现为理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ZurKritik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 1859)论述了“精神事实”或“概念总体”与想象/形象的关系,“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39页。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观念主要发扬了“艺术精神的掌握世界”这一核心思想,尤其是文艺批评对“形象思维”的论述。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之“文学的形象与典型”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典文论、现代文艺批评的结合,把文学形象简化为语言所描写的自然/现实事物或者叙述中的人物形象,把形象思维看作是形象的生命力之源泉,“从生活素材到文学形象的创造,需要经过作家创造性的劳动。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从选取生活素材,进行分析、概括、加工、提炼,到完成文学形象的塑造)所进行的艺术的思维活动,就叫形象思维。”“在形象思维中,想象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可以补充实际经验和感受之不足,而且可以使作家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更加丰富多彩,光辉动人,乃至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想象——联想和幻想是形象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只有充分而恰当地运用了想象,然后才可能产生反映生活真实的虚构。”“这些优美的抒情诗主要都不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但却生动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具体形象,使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并通过生动的形象描绘,有力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至于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不论叙事诗或小说)的形象性,最主要的就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自然,它们也要写景物——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注]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90, 196, 198, 203页。赵炎秋《原型与文学形象》则把文学形象简化为形式化了的生活,把生活看作为形象的原型,“感性具体的生活经过语言形式化后,就成为文学形象。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形象就是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的生活,或者说,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感性表现形态。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感性表现形态虽然千变万化,具体表现各不相同,但是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的模式。我们把这种共同的模式称为原型。原型是文学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象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注]赵炎秋:《原型与文学形象》,《湖南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第127—130页。
一般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形象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意识形态和列宁的反映理论则是形象的基础,由此在根本上区别于欧洲传统的模仿论。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形象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实上,苏联的形象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多地表现出一些认识上的差异。Л. И. 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1948)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形象是虚构的(即作者创造的),是社会生活(即描述的现实对象)的具体的反映,“形象是具体的,同时也是综合的人生图画,藉助虚构而创造出来,并且具有美学的意义。”“形象是有更广义的解释的。我们把艺术家用以反映生活的类型称为形象,以别于别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形象不但包括我们以上所说的语言,也包括文学作品一系列的各方面。……广义的形象指出整个艺术和文学的普遍的性质。文学的形象——和别种艺术的形象不同——是文字的形象,是在文字中形成的形象。我们可以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形象是艺术的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但这个说法稍嫌空泛,因为它并没有说所谓特殊是什么意思。可是,清楚地说明形象的反映生活的基本性质是完全必要的。”[注][苏]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上海: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第68页。维·波·柯尔尊《文艺学概论》沿用了季莫菲耶夫对形象的定义[注][苏]维·波·柯尔尊:《文艺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原理》反对把形象思维和逻辑认知看作是形象的源泉,再次回到了人对现实事物的感知以及感受和行动的再现(即模仿论),尤其是区分了美学与形象理论,“形象既不是来自逻辑认知过程,也不是来自思维工作,而是产生于感觉活动,产生于情绪体验和思维联想过程。形象创作的产生得益于情绪波动固有的感染力,从一个机体传导给另一个机体的过程。……记忆和想象在激发好感体验和模仿激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记忆和想象,感受和行动的再现——即所谓的模仿——就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回忆或想象某种感受,就意味着与记忆再现或想象创造的感受主体进行交流。”“形象是会思考、有情感、有体验、能激发情感回应的有生命的创造物;而描摹只是实物的复制,提供关于认知对象的视觉印象和直观认识,从而简化思维的认知工作。描绘是思维的产物,而形象是情绪感染的产物,模仿的产物。”“艺术家和批评家不是在美学中,而是在形象的理论——形象学中思考创作活动塑造形象的艺术家无需忧虑形象的审美效果,因为如果他塑造的形象真正是情感的体现,那么无需关注它就能引起审美感觉。形象使我们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审美感觉,并不源于艺术家的意愿。对艺术家创造的形象的反应——或笑、或愤怒、或赞赏,不是因为形象的创作者在创造过程中希望我们赞赏、发笑、发怒,而是由于他在所创造的形象中模仿了能够引起上述反应的性格的情感和行为,因为表现在形象中的性格具备激发这些审美感情的特性。……我们区分形象的形式和内容,是因为形象是其所表现性格的心灵感受的物质表现,他具有心灵和肉体、心理组成和物质组成。在审美的和美的概念中没有这个区别,于是也应该没有形象天生具备的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美学可以研究美的形式,但是这种研究与形象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制造混乱外,不会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注][俄]瓦·费·佩列韦尔泽夫:《形象诗学原理》,宁琦、何和、王嘎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2—3, 4, 32页。
结 语
人们更容易想起“诗如画”(utpicturapoesiserit)这个“形象”的比喻用法,然而,“图画”的观念是十分局限的,经验主义的“形象”(image, imagery)观念获得了极为普遍的接受:形象是外在事物在意识/心灵上的印记,由于外在事物被理解而言,形象就是观念,在引申、比喻的意义上,一切在心灵或思考中没有汇集之处的那些现象被称为形象。在20世纪,吉尔伯特·赖尔、杜夫海纳认为经验主义的“形象”观念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但他们所致力于对形象的解释活动,或多或少是有成效的。
1348 Correlation between first-phase insulin secretion and diabetic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移用柏拉图《克拉蒂勒对话录》(Dialogue of Cratylus)论语言的话也许是合理的,形象有晓示也有隐瞒的力量,形象可以定义一切事物,但又可以这样那样地改变事物。人们对词语/心灵形象的意义的追问,使得形象再次回到人类话语与表达的领域,形象再次作为交往行为的要素或符号,形象在现实事物与心灵/精神之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词语形象、精神形象的再现上的不确定性,召唤着人们对形象及其意义的阐释。
On Image:A Perspective of History
PENG Jian-hua
Abstract: “Image” is a visual term, referring to the product of visual perception that people describe or record, but people use it in different fields of knowledge (for example, image hermeneutics, symbolism, phase studies). The concept of “image” has experienced a long history in Europ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16th century, “imitation” and “analogy” are the main words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le “image” itself is only an implicit concep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omantic Movement and Hegel took it as an ideal concept of poetry, aesthetics and even an all-embracing spiritual existence in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arxism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imag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orists analyzed the essence of image from the original, extended and metaphorical meaning, especially the spiritual image and word image.
Key words: image; view of history; visual image; imagination; fantasy
作者简介:彭建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欧洲文学、翻译(E-mail:fennuyulin@sina.com;福建 福州 350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莎士比亚戏剧的早期版本研究”(18BWW082)。
收稿日期:2018-12-25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2-0013-13
【责任编辑 龚桂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