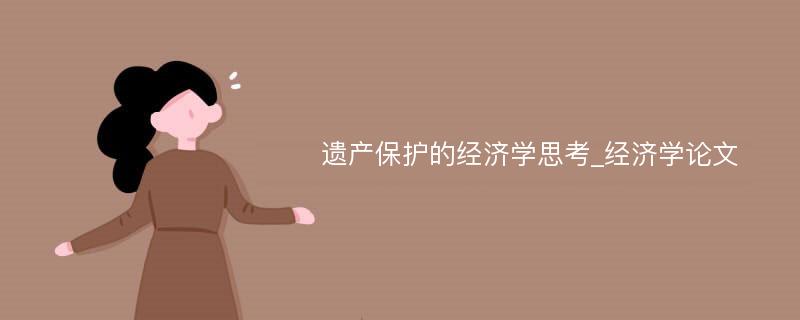
遗产保护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什么是遗产保护而不是遗产开发利用呢?我想这体现了保护第一,开发利用第二的观点和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社会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也不是旅游的开发利用或者其他形式的开发利用,而是全面的社会发展,这不单单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要使全社会的成员都能分享到通过遗产保护的益处,在这全社会的成员里既有当代人、也包括下一代人。
一、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前在文物部门开会,听到过一些比较极端观点,认为对于遗产资源(包括文物)只能提保护,不能谈开发利用,许多文物被少数专家以研究和保护的名义“垄断”在个人手里,一面对公众开放就是破坏,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我把它称作遗产保护的“原教旨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恐怕也很难认同这种极端的观点。《中华遗产》第十四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申遗”,作者夏骏也不认同这种极端的只保护不利用的观点。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保护是要花费高额成本的,一讲保护就是要国家拿钱、政府拿钱,也就是全体纳税人拿钱。从体制和机制上讲,一味依靠政府财政不是可持续的方法,因为政府要做的事太多了,你说遗产保护重要,但是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就业、扶贫、社会治安、国防等部门哪个不重要,都需要财政支持。而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遗产和文物异常丰富,而我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能投入在遗产保护上的资金相对于需求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二是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具有公益和教育等社会功能,如果连本国公民都无缘见识,那其公益和教育等社会功能如何体现?
此外,不利用,不发展旅游业是否就一定能保护好?在实践中,既有遗产资源开发利用过度的案例,如曾遭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的张家界,也有开发得太少,利用不上,最后也造成资源破坏的案例,但后者可能大家关注得不多。第一批的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周口店遗址,就是苦于开发不起来,没办法变成旅游吸引物,游人寥寥,入不敷出,仅靠财政拨款无法全面保护遗址,地层剖面自然风化很严重,管理方也曾想过开发旅游业,前几年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风靡全球,掀起一阵恐龙热,他们就利用科研单位的优势,在遗址博物馆里搞了个恐龙展,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讲科学了,因为恐龙是生活在中生代,而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是出现在新生代第四系的地层中,两者相差1.4亿年以上。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就是因为保护经费严重短缺。这是搞旅游搞不起来,也造成破坏的例子,所以正反两方面都有这样的例子。
二、在保护的前提下怎么样开发利用?也就是如何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首先我觉得不要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过去我们有个误区,以为发达国家的遗产保护做得都很成功。一讲国家公园就言必称美国,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许多专家学者拿来作为遗产保护典范来讲的,但殊不知它前几年才从世界遗产濒危名录上除名,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财力那么雄厚,公民对于遗产保护观念那么强,尚且都出现在濒危名录上。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认为只有我们国家才特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做的都很好,都是经验,都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有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1.认识我国遗产的保护问题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目前我们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认识还有待于不断深化,对于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改革也正处于探索的过程中。所以,遗产保护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再加上遗产事业对我们国家来讲也是一个新生事物,解决这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有创新性思维,有全局和大局观念,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死抱住一些理想化的教条,不切实际地就保护谈保护。
2.如果我们把遗产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话,是否一定由政府来独家经营?公共产品能不能外包给市场,这个事例在国外是屡见不鲜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个“诺斯悖论”,即在公共产品领域里没有政府不行,但是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因为政府的介入就意味着缺乏效率。如果实行外包,用市场的手段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政府就可以裁判员的身份来监管市场,现在呢,政府来经营,政府提供服务,政府制定标准,政府来监管,自己查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还当裁判,其结果可想而知。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公共产品外包给市场就改变了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的产权性质了,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产权是一个多种权利的集合体,不止是所有权,除了所有权以外还有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对于外包的公共产品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你可以有使用权、收益权,但没有处置权,我可以收回。这四种权利是可以分离的,现在连军工企业、航天企业、能源企业、国有大型银行都上市了,但仍然是在国家的控制下,社会股东并不掌握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权,利用资本市场并非是有些专家学者想象的“洪水猛兽”。
这里也有四个认识上的误区,其一是政府就是国家利益的当然代表者,而事实上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也是多方利益博弈的集合,中央各部委都说自己代表政府,到了地方都说代表中央,所以我们讲政府主导,实际上就是部门主导,其实都是代表部门利益;地方讲政府主导,比如省政府讲政府主导,就是省政府主导。地县政府讲政府主导,就是地县政府主导。这些以政府的名义出现的利益体本身都在博弈,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个体(部门或地方)的理性选择并不能导致达成集体的理性(中央、国家或全社会)的一致目标,这已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所证明,即所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其二,传统的文物管理体制有没有弊端,要不要改革?万能政府是不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从1949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文物和遗产都是政府一管到底的,没有市场的介入,但是否都保护得很好,如果行政管理体制非常有效,那就不需要研究文物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了,只要简单地回归旧体制就行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在旧体制下,文物遭到的破坏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仅十年“文革”期间毁坏的文物就不计其数。目前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现在遗产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出现的法制不完善、政策不配套等动态不一致的问题,只能用进一步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来解决。也就是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要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解决。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同样是世遗,北京周口店就没人抢着要,因为那是包袱(如果不能发展旅游业的话),带不来经济利益。至于像遗产类的公共资源在利用过程中出现正的或负的外部性问题(如搭便车问题),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干预(如应用行政的或司法的手段),“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现在遗产保护问题上,许多专家学者都很忌讳谈如何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似乎在个问题上一讲市场经济就有“原罪”。一开发利用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其三,在利益驱动下,在现行制度不完善的情形下,任何部门都有可能过度利用遗产资源,从而造成对遗产资源的破坏,这类事例旅游部门存在,文物部门也同样存在(如武当山遇真宫失火案)。因此文物部门并不占据保护文物天然的道德优势,这不是一个部门或某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制度的缺失。作为学者应该从学术的角度,站在一个更超然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就事论事,不做部门利益的代言人。
其四,有的学者认为,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遗产保护也是由国家拿钱,市场经济和民间资本不得染指。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专门关注过这个问题,英国的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基金协会,在一百周年的时候(1995)出过一本纪念册,看了以后我才知道,所谓的国家信托基金其实它完全是个民间基金,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该组织成立于1895年的英国北部湖区,发起人有一位英国湖区的牧师卡农·伦兹利、著名英国儿童女作家波特以及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等,他们出于对长期居住的这片湖区环境的珍爱和免遭后人的破坏,自发设立了这个基金,现已发展成为英国的全国性组织,该协会作为私人机构拥有和管理着英国最广大的土地、古堡和私人领地。协会不依赖国家援助,完全自筹资金运行。一直守护着数百年的历史遗产。协会会员超过200万人(包括国外会员)。会员缴纳会费后,可以免费或以优惠票价参观游览协会所属的景点,也向度假者出租古城堡以获取保护资金。目前这一组织已成为英国自然资源保护、绿色及环保方面最大的会员制组织。因此,事实与国内某些专家学者的说法正相反,至少是在英国最大的遗产保护组织不是政府,而是私人的,而私人组织的保护经费也不是来源于国家,而是取之于民间。
不要将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人为地、先验地对立起来,两者关系处理得当的话是可以达到互相促进的。英国的国家信托基金的运作模式便是一个例子。再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较好地处理了文物研究、收藏保护与参观游览之间的关系,其收藏保护条件、向公众开放的程度和游览环境都要胜过北京故宫博物院。
遗产保护涉及到各相关利益方,这些利益相关方是政府(或各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投资方、经营方、游客、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尤其是非物质遗产)、当地居民 (社区),还有不直接相关的,像在座的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 (NPO)以及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等,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关键是制度,各相关利益方获取利益的边界取决于他们在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处于什么地位,掌握多大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参与谈判的能力。
三、关于文化遗产原真性的问题。旅游业经常受到一些文化学者诟病的是,旅游开发使许多原生态文化沦为“表演文化”,失去了其原真性。所谓原真性就是指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根据徐嵩龄教授的研究,原真性分三个层次:历史上的真实、演变中的真实和妥协下的真实。旅游一般都是妥协下的真实。对于非物质遗产,有文化传承的问题,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文化传承者承担了我们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就是必须把这个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但问题是文化传承者与我们一样有追求现代文明和享受现代物质生活的权利。我们有些专家到了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要求当地人自发地穿戴当地传统的服饰,生活在当地传统的(往往是居住条件非常差的)民居环境里,以取悦和满足他们的猎奇心和提供人类学的研究素材,但如果让这些专家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他们会愿意吗?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你自己都不愿意,就不能强加于人,尤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希望过上比他们父辈更加美好的生活,改变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选择。躬身自问,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专家学者自己不也早已脱下我们的传统服装(长袍马褂),穿上了西装革履或夹克衫、休闲装等舶来品吗?为什么一定不许他们进化(或者说西化呢?),对于非物质遗产原真性的苛求,实际上是一种将原住民生活区建成“人类动物园”的思维,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文化传承人不是一件物品,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人,平等地用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来看待,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权,激发他们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豪,而不是强迫他们恪守某些专家学者喜欢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是平的,我们很难筑起与西方现代文明绝缘的“防火墙”。
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像美国的“艾美什人”,原来是非常恪守宗教戒律的,主动拒绝使用一切现代工业文明的产品(如电、电器、汽车等),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但现在越来越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的挑战了,物质文明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许多艾美什年轻人纷纷离开边远社区,进入城市生活,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艾美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在历史上出现的事物,必然会在历史上消亡。文化的演化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传统文化中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如妇女缠小脚、太监制度等反人性、反人道的文化糟粕)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记录,但不能传承。
美国著名旅游人类学教授贾法利认为,旅游为拯救具有旅游价值的一切文化价值做出了贡献:“许多宗教或考古建筑之所以从被毁坏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更多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居民看来所具有的价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如此。所以妥协下的真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总比这种文化快速消亡要好。由于发展旅游,给了当地保护和保存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上的动力,尽管不喜欢。为了赚钱所以才保留下来(或作出其他方面的妥协和让步),但如果把房子建成跟大多数城市一样,游客就不来了。当然当地居民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取悦于旅游者,如果存在其他更好的赚钱机会的话。但对于一些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来讲,发展旅游使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多了一种选择,甚至可以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后工业社会,而不一定要经过环境污染代价很高的工业化阶段,这方面的案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
总之,对于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原真性的问题,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是没有的。应用经济学的法则就是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妥协下的真实尽管在一些专家学者眼里毫无真实性可言,甚至没有研究价值,尽管它带有很强的经济上的功利性,但却不失为是一种拯救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
在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诺斯悖论”:没有旅游者不行,旅游者太多了也不行,关键是我们如何适度地发展旅游,合理地把握好这个度,需要各相关利益方的共识和利益平衡机制,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