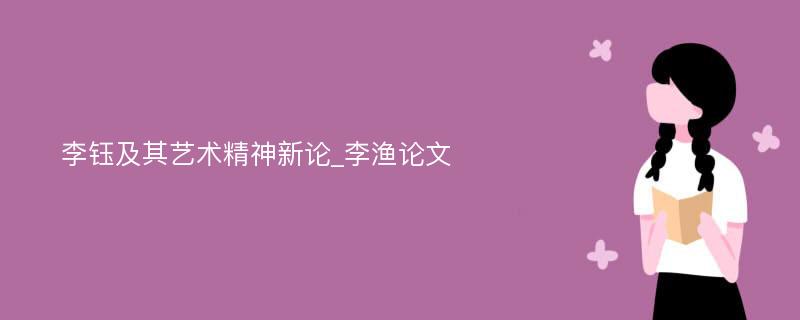
李渔及其拟话本艺术精神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话本论文,新解论文,精神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李渔,很难一言以蔽之。面对他仿佛面对西方印象派的画。先是以华丽的色彩和鲜明的阳光感觉夺人眼目,而要仔细辨别画中的物象却又模糊不清。那种耀眼来自于他全新的多色调的触击,而那种模糊则来自于他难以归属的文化品格。
但难以归属不是不能归属,近似归属还是能够做到的。只不过李渔所归属的范畴,是历来为正统价值哲学所轻视、忽略的边缘哲学范畴,虽然生活实践中代不乏人,但评者较少堂而皇之地论及于此,即使论及也多含鄙视和不屑。李渔的出现,他的大模大样,他的不可抹杀的影响不容人不正视他,并对他所代表的哲学做进一步的思考。笔者认为李渔其人及其小说所反映的总体精神应是鉴赏主义生活哲学,更具体来说即“家居有事之学”(注:《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节色欲第四》,第33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的愉快鉴赏。
一
研究界对李渔其人及其小说总体精神的概括大致有以下几种:享乐主义(注:德国汉学家马汉茂先生曾在1966年写就《李笠翁论戏剧》(Helmut Martin,"LiLi-weng Uberdes Theater,Heidelberg University,Heidelberg,1966),评价李渔时用了“追求现实的享乐主义”和“行乐观”字样。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华裔学者毛国权和柳存仁,他们曾合著《李渔》(Twayne Publishers,A Division of G.K.Hall & Company,Boston,Massachusetts,1977),认为李渔的思想“比较接近于西方的昔勒尼学派、伊壁鸠鲁快乐主义哲学以及近代的功利主义哲学”,“公认标榜享乐主义哲学,舍弃正统的生存之道”。美国汉学家Henry Eric P.的《中国娱乐:李渔的喜剧》也持同一主张(《Chinese Amusement:The Li Vely Plays of Li Yu》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0.)。)、喜剧主义(注:参见张晓军《李渔创作论稿——艺术的商业化与商业化的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5月版。)、劝惩主义(注:参见崔予恩《李渔小说论稿》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学末流的代表者(注:马汉茂认为李渔“是传统文学末流的代表者;在袁枚之后,这种传统文学末流的浪漫作风即在文坛上消失”。这里所指的末流当指起于晚明,终于清代中期的讲求“韵”、“趣”、“苦心孤诣”的文风。见马汉茂《李笠翁与“无声戏”》,台湾《大陆》杂志,第三八卷第二期,1969年。)。这几种提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感觉还有再商榷的余地。
关于“享乐主义”。这个概念源起于古希腊的昔勒尼学派,主要内涵是指:“即便享乐来自于最丑陋的事物,它也是善……”(注:A·古谢伊诺言夫等著,刘献州等译,《西方伦理学简史》第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他们认为肉体的快乐远远胜于灵魂的快乐。后来发展为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伦理学,认为“快乐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注:《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虽然后来伊壁鸠鲁又补充道:“当我们说快乐是最终目的时,我们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而是指身体上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强调了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理性的调适。但后人多注意他前面所说的话。如就前面的话来评价,把“快乐”说成是唯一的伦理原则,并把它抽象化,那就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得出结论说伊壁鸠鲁的伦理学说是享乐主义的,甚至是非道德的。可见享乐主义与快乐主义在后世人的心中是两个概念,享乐主义多强调感官的满足,而快乐主义兼顾到了精神。特别是经过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极端提倡,享乐主义已有其区别于快乐主义的特别含义。享乐主义的根本追求及其对人的片面理解使这一主义的信徒们必然陷入失落、悲哀、沮丧、紧张、焦虑等不良的心态之中。这是今天被实践证明了的。因此,虽然马汉茂等本着西方学者如实评判的原则,认识到李渔短篇小说的成绩,但用了“享乐主义”这种中国人感觉总有点贬义的词,似与他肯定的优点相牴牾。加之,李渔及李渔作品中反映的思想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所能概括的,这一点后面详谈。
关于“喜剧主义”(注:如萧小红《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短篇小说的喜剧性》,载《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它也不能很恰切地概括李渔短篇小说的独特性。且不说中国古代戏曲普遍来说从不能真正地板起面孔,所有的作品都带点谐谑味(包括《牡丹亭》),而且“喜剧”,这一用滥了的舶来品即便套用在李渔热闹的戏曲作品身上也缺乏一种个性色彩,并有一种故作高深之嫌,更何况相对来说更厚实更复杂的小说了。如此论定,只能令人注意一些李渔搞笑的小技巧而已。有的学者更深入地接近了李渔小说的精髓,但可惜的是太沉迷于悲剧的锐利、深沉、阔大等诸般审美享受,而对李渔小说自身价值缺乏认同,因此抱怨的多,缺乏平心静气的挖掘工夫。而由此引出的“商业化艺术”的提法又很容易产生李渔文学理念虚无的误读,有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之嫌。
关于“劝惩主义”。中国文人惯常分为入仕与避世两类,分别依归于儒家与道家思想。人们毫不勉强地肯定和欣赏这看似不同的两类文人,原因是他们都具有严肃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贵族气派,都力图摆脱世俗的羁绊而获得一种自由。小说,在它刚刚问世时被称作小道,本是来自于平民,愉悦于平民的文学样式,要提升它的地位,必须向以上诸种“崇高”靠拢。晚明一批有影响的文人就是这样做的。像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他们拉升小说的共同法宝即是小说的教育功能。李贽评《水浒传》,认为是“发愤之所作也”(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叙》。)。冯梦龙认为小说乃“六经国史”以外的一个辅助教材,将他的作品之所以命名为“三言”,是因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注:《醒世恒言》序。)。他又将小说的价值建立在“忠孝节义”之上,要“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注:《醒世恒言》序。)。诚然,强调小说的教育功能并没有错,但当教育内容只限于忠孝节义、有助风化的道德论,就不免狭隘。冯梦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李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评的。而李渔虽也说过文学作品“无益于劝惩……亦终不传”(注:《李渔全集》第一卷《〈香草亭传奇〉序》。),甚至说过他的创作“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注:《李渔全集》第一卷《曲部誓词》。)。但他并没以此作为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唯一标准。他也强调小说的教育功能,但其目的并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为世人能立足于现实人生,最大限度地摆脱精神上的痛苦而提供经验。加之他那种崭新的谋生方式、非正统的生存之道,更证明他不会以此为首要。可能有人会说,像李贽那样反伪道学的斗士,还一味坚持小说的劝惩,怎么能肯定李渔就不会?正如鲁迅在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那篇演讲中,提及嵇康、阮籍,说他们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而李渔不同,胸中无横此念,因此能更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人生,更能挖掘小说的其他重要功能。别忘了,关于文艺作品如何葆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问题,李渔也曾道出真言,即“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注:《香草亭传奇序》。),把“有裨风教”仅放在第三位。
关于“讲求韵、趣的传统文学末流的浪漫之风”(注:参见崔予恩《李渔小说论稿》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虽然李渔身上自由派的成分稍多于正统派,但他及他的作品是否体现出的是晚明陈眉公、清中期袁枚所代表的韵和趣?亦如在早期研究界对李渔的评价中常说的,“反映了封建时代有闲阶级文人的消极避世的一面”(注:膺戎《评李渔散文》,《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12月第4期。)?其实不全是这样。其一、李渔并不像袁枚、陈眉公乃有闲阶级,他乃自由职业者,没有袁枚的大笔家产。他要谋生,而且谋生手段亦不复是陈眉公的书画雅业,却是人所轻视的俳优小道;其二、李渔的不出仕为官并不说明他消极避世,他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完成他的用世之志,他是心平气和地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他写的大量的戏剧、小说,包括编写的通俗读物《资治新书》、《古今史略》、《千古奇闻》等等,内容涉及之广、其反映的人间性,都不是袁枚、陈眉公辈诗文小品书画所能及;其三,人们评其为讲求韵、趣,多以《闲情偶寄》为据。其实,他的《闲情偶寄》并不是贵族文人“点缀山林,附庸风雅”之作,而是满怀热情地面向平常大众应对日常生活的指导书。看它所涉及的题目:辞曲部、演习部,虽说是戏曲理论之作,但面向的还是不入流的俳优们;居室部、饮馔部等则关涉民生的衣食住行,下分的小题目分别为“房舍”、“向背”、“途径”,“蔬食”中又细分为“笋”、“蕈”、“瓜”、“匣”、“瓠”、“芋”、“山药”等。其琐细、其平实似近于《齐民要术》、《梦溪笔谈》之类的前代科技书。而且在写作过程中反复强调崇俭勿奢,如“羹以下饭,乃图省俭之法,非尚奢靡之法也”(注:《闲情偶寄·饮馔部·谷食第二·汤》。)。说鉴赏骨董之道时云:“予辑是编,事事皆崇俭朴,不敢侈谈珍玩,以为末俗扬波”(注:《闲情偶寄·器玩部·制度第一·骨董》。)等。“美指称实际审美生活样态,其中,政治、居室、饮食这三种生活样态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积淀着最为深厚的审美意味,渗透着中国式的对美的体验。”(注:林岗《深圳大学学报》2002年1期。)这里所指的中国式,其构成群无疑是占大比例的中国大众,而不是曲高和寡者。所以李渔绝不是以韵、趣为主,出于闲暇遣兴为目的而创作曲高和寡的文学作品的。
总之,以上诸种提法似乎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李渔的某些价值。
笔者遂试着用“鉴赏主义”来诠释李渔。何谓“鉴赏主义”?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一段话颇给人以启发:“在人类可以营为的艺术生活上,有两面。第一是对着自然人生一切的现象,先想用了真挚的态度,来理解它。但是如果更进一步说,则第二,也就成为将已经理解了东西更加味识,而且鉴赏它的态度。使自己的官能锐利,感性灵敏,生命力丰饶,将一切都收纳到自己的生活内容里去。溶和在称为‘我’者之中,使这些成为血肉的态度,这姑且称为享乐主义吧。”(注:鲁迅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第14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厨川为什么强调“姑且”二字?因为他一时间没有找到更准确的表述字眼。后来,他在谈到与一位先辈就dilettantism是翻成“享乐主义”还是“鉴赏主义”一事时,后悔当初只从语源方面考虑而翻成“享乐主义”,但从内容看似不如“鉴赏主义”更准确。因为享乐主义中“享乐”这两个字常被误解,以为就是浅薄的不诚恳的快乐主义。厨川白村进一步解释说:“真爱人生,要味其全圆而加以鉴赏的享乐主义,并非像那飘浮在春天的花野上的胡蝶一样,单是寻欢逐乐,一味从这里到那里似的浅薄的态度。”“所谓观照享乐的生活这一个意义的根柢里,是有着对于人生的燃烧着似的热爱,和肯定生活现象一切的勇猛心的。”这才是“鉴赏的享乐主义”的确切含义,我姑且简称为鉴赏主义。概括来说,鉴赏主义具有一种乐观主义性质,但其轻松和明朗必是切实地与现实人生联系在一起,必是来自于现实人生,必是有着对现实人生的热爱及敢于迎接人生风雨的坚强。
李渔的鉴赏主义有别于呆板的劝惩主义,也有别于浅薄盲目的享乐主义,甚至也不同于中国闲雅文人袭来讲求的韵、趣。正如他对自己的定位:“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注:《李渔全集》第三卷《闲情偶寄·节色欲第四》,第33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渔的鉴赏主体是平常人,鉴赏对象是平常生活,映现其鉴赏观的载体是作品,赏鉴的基调是审美的、乐观的,赏鉴的目的是令人生活得快乐、轻松。其实,杜书瀛的《李渔美学思想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已将李渔的戏剧美学、园林美学、仪容美学做了系统、细密的理论阐释,注意到李渔丰富的审美思想和卓越的审美能力,亦理应提醒我们注意李渔那活跃的鉴赏细胞必然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现。所以,以此来概括他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下面即从李渔拟话本创作方面对其“家居有事之学”的“鉴赏”加以说明。
二
李渔拟话本的独特性即是以赏鉴为基调:赏鉴生命,赏鉴美好,赏鉴琐细,赏鉴卑贱,甚至赏鉴苦难。有着古代文人笔下难见的既实在、实用,又通脱、潇洒之气。
赏鉴琐细生活。李渔小说重视实实在在的琐细生活,对平常生活、平常日用细心体味,在平实生活中去发现美和价值,展现出其精到的生活哲学,即“家居有事之学”。
李渔小说多关注普通人。首先我们看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李渔小说集《无声戏》系统(含《连城璧》)共18篇,《十二楼》共12篇,总共30篇作品。如果将贫寒书生及仅有经济基础而无社会地位的富人都算作普通人的话,那么,李渔的短篇小说普通人的比例是73%,而社会上层官吏与处于中上层的文人则占27%。如下表:
无声戏
十二楼
总集
官吏
1
2 3
比例
6% 17%10%
书生
6(贫寒
5(中
11
书生)
上层)
比例
33%42%
37%
普通
17 5 22(包括贫寒书生
百姓
及无地位的富人)
比例 94%42%73%
上层 1
7
8(指既有社会地位
又有经济基础。
比例22%
58%27%
富人3
2 5(富人因无社会
地位故属普通人)
比例17%
17%17%
再看李渔小说的主题。大体上是说命、相、财,说子嗣、妻妾,说戒赌、戒嫖,说为人之道、修身之理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李渔尽可能地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从人的本体,从实际生活出发,挖掘生命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因而道出很多新鲜的生活哲学,非出于正统教义。仅举几例。如《夺锦楼》,写得很热闹,写了夫妻相斗,胡乱为女儿许亲,最后告上公堂,刑尊设锦标,张告招亲,才子佳人,各归其所。看似才子佳人小说,但主要目的是告诉人们一种齐家之法。他要奉劝身为父母的该如何正确地许配女儿。李渔不依从陈言,说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套话,而是切实地告诫做父母的要“慎之于始,不变之于终”,以防空惹“讼端”。且公然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本篇“单为乱许婚姻,不顾儿女终身者作”。又借讼官这一形象道出齐家之妙法,如“论起理来,还该由丈夫做主。只是家庭之事尽有出于常理之外者,不可执一而论”。再如《合影楼》中所发的议论:“从来的家法,只能痼形,不能痼影。”“不痴不聋,难做家翁”等,真是很实在,也很新鲜。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是他唯一一篇写戒嫖,而且是以妓女作为反角的小说。这一主题从另一侧面看出李渔真是从生活出发,不是现实生活的逃避者。自古赞妓女多情,叹妓女光辉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而李渔却颇实在地告诉你“世上青楼女子,薄幸者多”。讲述了一个骗情骗财的妓妇,以警诫对妓女抱有幻想的多情少年。
更多的是像《移妻换妾鬼神奇》、《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等写阃内风烟的作品,把家长里短道了个罄尽。
李渔小说所关心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津津于对这一世界的认识与看法,用理性的目光探究一些原来不为人们所重视和关注的细琐层面,尽量理解平常生活中的平常之情、平常之人、平常之事。这种“理解”,要求一种清醒、理性和承担,更需要有足够的热情、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意志、足够的通脱,从常情、常理、常人出发,并实用于常人。
赏鉴生命。李渔小说显示出对鲜活生命的珍重之情,凡事予以生命的诠释,既顺应生命的欲求,又弹性掌握束缚生命的成规戒律,展现出其认同人本体的实用理性精神。
李渔不赞成对生活的无谓苛酷。《三与楼》写了对悭吝者的讥刺。唐玉川乃“骤发的富翁。此人素有田土之癖,得了钱财,只喜买田置地,再不起造楼房,连动用的家伙,也不肯轻置一件。至于衣服饮食,一发与他无缘了”。作者称之为愚人。而与之相映衬的人物乃是一个“达者”,“他说人生一世,只有三件器皿,是实在受用的东西,不可不求精美。那三件?日间所住之屋。夜间所睡之床。死后所贮之棺。”但如此对生活达观的人并不是讲求奢华靡费,而是“晓得舍少务多,反不如弃名就实”。这种见解易使人联想到比李渔稍前王艮的思想,即“安身立本”和“明哲保身”说,即“身与道原是一体,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注:《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答问补遗》;《明哲保身论》、《语录》。)。从“安身立本”和“尊身”即“尊道”出发,就必然要求“明哲保身”。王艮认为:“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注:《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答问补遗》;《明哲保身论》、《语录》。)不同意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壮烈得没边的行为。“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而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注:《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答问补遗》;《明哲保身论》、《语录》。)强调人的主体性。
由此李渔自然提倡对生命的珍重。《女陈平计生七出》、《奉先楼》与其说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同情,不如说表达了他浓重的生命意识。
《女陈平计生七出》入话虽在倡导忠孝节义,但对以生命去换“名色”颇感遗憾:
话说忠孝节义四个字,是世上人的美称,个个都喜欢这个名色。只是奸臣口里也说忠,逆子对人也说孝;奸夫何曾不道义,淫妇未尝不讲节。所以真假极是难辨。古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要辨真假,除非把患难来试他一试。只是这件东西,是试不得的。比如金银铜锡,下炉一试,假的坏了,真的依旧剩还你。这忠孝节义将来一试,假的倒剩还你;真的一试,就试杀了。
进而感叹:岂不可惜!李渔并不像一般道学先生,谈女人守节,唯恐她不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吝笔墨,大力彰显了一个被流贼掳去却安然而归,既未拼掉性命,又未失节的女英雄。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但这涉及到对守节的重新界定。
守节,一弱女子面对强徒若不付出生命该怎么守?要么是誓死不屈,要么是忍辱报仇,而后者毕竟受辱失身,还要费道学先生们的许多犹豫。李渔的功夫往往表现于此,他另辟蹊径,一方面夸大智谋的效用,一方面偷换“节”这一概念,目的就是要向人们献出一“活宝”,还私下以为“却比那忍辱报仇的还高一等”。女陈平的守节,与夫子们心中所横的标准相差太远了。二娘共七出计谋,其中前四出皆为护卫“名器”;后三出则为逃身并护卫名声。在护卫“名器”的过程中,采取的是螯虫噬手,智士断腕之法:“二娘千方百计只保全这件名器,不肯假人。其余的朱唇绛舌,嫩乳酥胸,金莲玉指,都视为土木形骸,任他含咂摩捏,只当不知,这是救根本不救枝叶的权宜之术。”话是如此说,可孰不知古人对守节的范畴可不仅于此,不是大倡“男女授受不亲”吗?不是有宁可溺死而不接小叔相救之手的吗?即使老如敬姜(注:季康子从祖叔母,季康子尝如敬姜往候,敬姜开阃而与之言,皆不逾阈。仲尼谓敬姜别于男女之礼矣。《诗》云:女也不爽,此之谓也。),亦要别嫌明微。五代不就有引斧断臂之事吗?王凝妻李氏一臂被牵,即以为失节,引斧自断其臂。相形之下,女陈平已大大失节了,若如李氏法炮之,女陈平应周身尽断,唯剩一“名器”耳。其实,真正“名器”乃是生命,李渔在这里巧妙地设了一个最后防线,一个障眼法,实际上他已走得很远。
《女陈平》是以迂回的方式道出生命的重要性,无视贞节的愚见,而《奉先楼》则直言对生命的珍重。写一秀才夫妇好不容易得了一子,却逢贼寇兴兵,人人自危。面临着是保妻子的贞节还是保儿子的性命以不断后这个问题,不仅二人,全族的人都展开了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守节事小,存孤事大”。舒秀才道:“如今遇了变局,又当别论。处舜之地位,自然该从揖让;际汤武之局面,一定要用征诛。尧舜汤武,易地皆然。只要抚得孤儿长大,保全我百世宗祧,这种功劳也非同小可,与那匹夫匹妇自经十沟渎者,奚啻霄壤之分哉!”这种乱世论人足见其忠厚之道,与夫子们的节烈观又是相违拗的。而且结局又突破了节妇必死的窠臼。
李渔对生命的认识在当时如此的不同凡响,自然对发自于生命之源的情、欲亦予以认同。在《闲情偶寄》中他即告诫人们:情、色不可戒,戒情色即犹如“人为饥死,而仍戒令勿食”(注:李渔《闲情偶寄·一心钟爱之药》。)般无道理,将情、色、食等而同之,都视之为生命之源。
《合影楼》,从家长角度告诫儿女之间的情与欲要力导而不是禁锢。认为“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以消除,独有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
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拚了一死,定要去遂心了愿。
因此才有我们熟悉的《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彰显出情所具含的令人瞠目的冲决力;因此才有《鹤归楼》中的郁子昌(谐音为欲自昌)明确信奉“得美妻才是名教中最乐之事”。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李渔的鉴赏还具含客观、理智、明智等质素,正因为这些质素,鉴赏的结果绝不是激烈的、迷狂的、偏执的,它是站在圈外的仔细玩味,它是旁观者清的弹性调适,它是不屈意、不累身的最佳距离。因此他在张扬情、欲时,有时又表现出一种保守,不像我们熟知的作品那样走极端,而是掌握在适宜的度数里,即便像《谭楚玉》,在展现情的无比冲击力时,也不忘给男女主人公戴上“贞夫节妇”的花环。再如《夏宜楼》前面写吉人费尽周折,为实现与小姐情的交好,可最后却加以抵销,安排了“古人既占花王,又收尽了群芳众艳”这样有些杀风景的结局。《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反却劝说那些追求正常情、欲的女子:心性高者薄命,要该忍则忍。评者因此进而认为:“此书一出,可使天下无反目之夫妻,四海绝窥墙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岂可作小说观。”等等。
赏鉴卑微。李渔小说能在卑微现象中开掘出崇高与价值,具审视人与事物的独特视角,不武断,不高傲,不剑拔弩张,不先入为主,以平和、客观、赏鉴的心态去深自体味,展现出其超乎寻常的涵容与理解力。
惯常被认为丑的卑微的或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在李渔小说中出现,并以英雄、主人公、正面形象堂而皇之地出现。写爱情,却是戏子之间的爱情、同性恋的爱情。写英雄,却是“穿窬草窃之内尽有英雄,鸡鸣狗盗之中不无义士”(注:李渔《十二楼·归正楼》。)。写清官与士大夫,他要开掘出那可理解可宽容的“一团私意”(注:见《夺锦楼》中的刑尊。),等等。在对这一系列卑微的人或事物进行展现的过程中,让你一点点品咂出其中的味道——卑微中的崇高与价值。
在李渔笔下,小官地位提高了。以往同性恋题材中的小官形象或从反面写起,写他们如何利欲熏心、无品无行;或从正面入手,如《弁而钗》,写他们情感坚贞(注:《弁而钗》中《情烈记》、《情奇记》即是代表。)。但可能正因为不能真正理解同性恋的实质,只能将封建社会晚期对女性贞节的严酷要求原封不动地搬到这种同性恋关系中,因此他们处于一种“准女性”状态。他们在性关系位置上的倒错的、难以确认的状况,使他们似乎成了被关闭在以两性为主体的社会之外的第三者——一个无依的游魂,往往比女人更不幸。李渔《萃雅楼》塑造了一个出身于小官的英雄,而这个英雄并不是像以往标榜同性恋的作品中所有意树立的忠贞于情的楷模,而是被卷入忠奸斗争这种社会大舞台中的真正的英雄。权汝修,品格坚贞不屈,不畏强暴,甘于贫贱,在惨绝人寰的侮辱和迫害下却没有被压垮,镇定从容地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个不屈服的同性恋者可以说是明清同性恋文学中最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正义的英雄来颂扬而不是以蔑视猎奇的眼光来看待他。当然李渔毕竟带有那一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更深入地认识同性恋这一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尚存在许多矛盾和疑虑之处,所以在承认的同时还有些畏首畏尾,如:《男孟母》最后却道:“如今的人,看到这回小说,个个都掩口而笑,就像鄙薄他的一般。这是甚么原故?只因这桩事不是天造地设的道理,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凿出来的,所以做到极至的所在,也无当于人伦。”——满怀热情地写完后,又加以否定。这样做既使读者反而接受了这些原本不大好接受的内容,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有了一个绝佳的掩饰。但不管怎么说,李渔能从同性恋这一现象中发现一种价值、理解一种价值,显现出李渔超乎常人的通脱。不武断、高傲地放弃一种东西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涵容。
李渔为“拐子”铺写正传。《归正楼》以一“恶人”为主人公,写恶人回头,有对偶然失足者的劝诫。如“一善可以盖百恶”,“一恶也可以掩百善”,李渔在此有一种常被人忽视的审视“恶人”的独特视角。
小说不像“浪子回头”类故事惯常那样,先列数恶人或浪子的劣迹,好为后面“回头”做铺垫,而是一开始便似贬实褒,介绍他的“无穷恶迹”,却以“美谈”之规模推出。贝去戎相比乃父贝戎,上了一个层次,颇多丈夫气及智能含量。作者对其拐骗智谋不禁由衷叹其“奇也不奇,巧也不巧”。作者又为他添加了许多个人魅力:豪爽、仗义、不贪婪、潇洒、聪明,正所谓“风月场中要数他第一个大老(撒漫)”。看他所拐骗之人,不是大户宴饮之家,就是当铺老板,再就是官衙老爷,其中一笔客似乎穷一点,但他“利心大动”,也咎由自取。他作拐子亦做得自负、仗义,大有舍我其谁之概,认为“若使辇毂之下没有一位神出鬼没的拐子,也不成个京师地面,毕竟要去走走,替朝廷长些气概”。他不认为自己是个贼,却像一个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者,甚至在他的世界里他还自认为是一个英雄。当骗得钱物竟以万计时,则见好就收,其实此处才是他回头之始,而想回头,想做好事又完全出于一片私心:心上思量道:“财物到盈千满万之后,若不散些出去,就要作祸生灾。不若寻些好事做做,一来免他作祟,二来借此盖愆,三来也等世上的人受我些拐骗之福。”随即善良、慷慨又尽现,令妓妇们感恩戴德。即使后来所做最大的两起骗人自愿捐钱建佛殿塑法像之事,也是拐骗那些“还拐骗得起,叫他做的又都是作福之事,还不十分罪过”。说是歹事,其实是成全人之好事,最后令捐钱的那两个仕客富商,儿孙满堂,终其天年。
作者如此不吝辞费地夸说一个拐子,在后面道出原由:“可见国家用人,不可拘限资格,穿窬草窃之内尽有英雄,鸡鸣狗盗之中不无义士。恶人回头,不但是恶人之福,也是朝廷当世之福也。”其间反映出较浓的江湖文化和平民意向。在老百姓看来,神偷神拐,不管怎么说,他有神技,乃世上之能人,如若再仗义、扶弱锄强,真强似官府中的贪官污吏,朝廷如能发现人才、很好地运用人才,他们会为老百姓谋利益,为国为家皆有用。所以李渔在品咂拐子时,恰切地品出了百姓的心声。
李渔对乞丐也别有寄托。与拐子正传异曲同工,李渔对乞丐形象也给予自己的认同。他认为:
不知讨饭吃的这条道路虽然可耻,也还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比别的歹事不同。
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的这条路数,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
睡乡祭酒评此段为:“大经济,大见识,大学问,从来圣贤口中未经道破,岂特稗官野史之流乎?真异书也,竟该作经史读。”(注:《李渔全集》,第八卷,第282页。)虽未免夸张,但确认此见之新还是准确的。
《乞儿行好事》塑造了一个传奇型的乞儿形象。他竟能将“叫化”做成“教化”,将乞讨做得“何等清高”、“何等廉介”,可谓“从来叫化之中第一个异人”。
李渔如此推重一个乞儿自有深意。一方面冠乞丐为明末乱世忠臣,另一方面亦为自己张目。前者不难理解,有诗为证:“三百余年养士朝,一闻国难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后者则较为复杂。因为李渔曾到处打秋风,靠与官僚权贵们周旋酬酢,来维持一数十口之家的生存,这时李渔要特意保持某种卑下柔媚的态度,或以自己贫寒的家境来打动对方,如此表现又与乞丐何异!所以变相为乞的经历令他更感兴趣于这个题目。有人因此而指责他人品卑下,没有民族气节。其实,在鼎革之际,中国的“士”阶层仍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特权和优越感,而他立即做了摒弃的选择。有所不为即是有所为。如仅从狭隘的民族气节方面看,相比于所“巴结”的新贵们,他不知要强多少倍。李渔在抛弃了旧的传统的精神秩序之后,同时也在追求着某种新的人生意识,一种自由的和平等的人生观。但是作为新人不被理解的郁闷和不平使之诉诸自己的笔端。
总之,当李渔注目于市井之中卑微的奇人怪事,不是以偏狭的成见武断地论定,而是以一平常心、平常情去深自体味,因而能道他人之所未能言,品他人之所未能感。
赏鉴苦难。李渔小说在对人间苦难正视与咀嚼的同时能融进快乐因子,既有理性的面对、勇敢的担承,又有调适的聪慧,展现出其足够的坚强和通脱之气。
李渔小说多涉苦难。并不像评者常认为的都是些热闹的喜剧,他特别强调生活多有变迁、世界多有苦难,他的小说常以这些变迁和苦难作背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他的笔下:婚姻错配者多,如《丑郎君》,感慨“天公局法乱如麻,十对夫妻九配差”,那害“哑子愁、终身病”的苦才是真苦,再如《十卺楼》,感叹好事多磨,“无端地天予波澜”;有情人难成眷属者多,要么像《谭楚玉戏里传情》中青年男女因旧观念恶势力横加阻挠,不得不化鱼转生,要么像《寡夫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因心性不同,为爱而生纷扰;家庭纷争者多,如《移妻换妾鬼神奇》、《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儿孙弃骸骨童仆奔丧》,上演的是若无贤妻孝儿,亦不啻灭顶之灾的家庭悲剧;贵贱穷通不由人者多,如《改八字苦尽甘来》篇首诗近乎呼天抢地,喊出“多少英雄哭阮途,叫呼不转天心硬”的英雄失志之悲。除此之外,还有本无甚事却人为善意制造祸事的,如《闻过楼》中顾呆叟的遭遇。还有堪称人世间最大苦难的战乱:如《女陈平计生七出》、《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鹤归楼》、《奉先楼》;冤狱,如《美男子避祸反生疑》、《人宿妓穷鬼诉嫖冤》、《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谑致奇冤》、《萃雅楼》、《男孟母》等。
统观这些苦难,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非人力可避免的,如来自于战争、天灾或相差悬殊的某种权力等;二是来自人事的纷争,可以通过人力与智谋巧妙越过的。针对不同类型的苦难,李渔提供了弹性原则。对于后者,李渔主张积极地去努力,强调的是进取后的快乐;针对前者,李渔主要从心理调适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减轻苦难给人带来的痛苦,不主张鱼死网破式的无效抗争,其最终目的还是让读者获得精神上的愉悦。通常采用三大法宝:一、惜福,即要有预防苦难的心理准备。李渔强调预防的重要性,特别是心理上的预防。这就要求一种清醒和理性为前提,像《鹤归楼》所提倡的“惜福”即是最好的调适方法。何谓“惜福”,用小说中段玉初的解释,“处富贵而不淫是谓惜福”,段生也更像是李渔在现身说法。面对天降绝色佳人,段生刻刻担忧,不敢肆意行乐。心下想的是“在太平之日,尚且该有无妄之灾,何况生当乱世,还有侥幸之理?”遂与妻子早做死别之准备。面对突降御旨,入金国赍金赍帛,段决意死别,冷面冷心,且题所住楼房匾额曰“鹤归楼”,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以见他决不生还。临行时“任妻子痛哭嚎啕,绝无半点凄然之色”。致使段妻在以后漫长的等待中因先断了与那个“从古及今第一个寡情的男子”的情分,倒安心乐意做了个守节之人,以纺织为生,尽着受用,倒比段在家之日肥胖了许多。方能忧患过后,夫妻相聚。李渔通过段生此举强调了“惜福”的颇具效果性。段看似无情、薄幸,其实是惜福,而且全是为妻子着想,正所谓“那番光景,正是小弟多情之处,从来做丈夫的没有这般疼热。”
二、“安穷”,即当苦难降临之际的应对法宝。
何谓“安穷”?即“遇颠危而不怨,是谓安穷”(《鹤归楼》)。有人认为“安穷”哲学乃一种奴隶哲学,就是劝诱人们,特别是社会底层大众安于现状,不要有犯上之想、不做犯上之事,主要为统治者维持正常秩序而言。其实,“惜福安穷”在本义上确有此义,更何况李渔《鹤归楼》人话末尾还加了这么一句:“总合着一句《四书》,要人‘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意思。”不由人不想李渔是要以《四书》教化人。孰不知,李渔惯会旧瓶装新酒,是的,孔教《中庸》是提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朱子解曰:“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注:《朱子集注》。)强调的是“所居之位”,后人多看重的也是前两句“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教化人安于富贵贫贱之等级差别。而李渔在这里越过富贵贫贱,单挑出“素患难行乎患难”,并且置于快乐人生的前提之下。《鹤归楼》人话中说“若还世上的苦人都用了这个法子,把地狱认做天堂,逆旅翻为顺境,黄连树下也好弹琴,陋巷之中尽堪行乐,不但容颜不老,须鬓难皤,连那祸患休嘉,也会潜消暗长。”可见其目的主要是出于一种面对苦难来临之际心理上的调适和有效的应对方策。
三、“退一步法”。
指的是凡遇见令你痛苦不过的难事,若退一步深一层想想更糟糕的事情,作一比较,心情就会好过些。亦即使安穷能得以继续下去的心理调适之法。《鹤归楼》“牛女相会”的篇首诗与入话中“仲夏夜打蚊子”的故事即是例证,段玉初入金国,受尽金人的折磨,如何抗过来的?也是靠的此法:
到了五分苦处,就把七分来相比,到了七分苦处,又把十分来相衡。觉得阳世的磨折究竟好似阴间,任你鞭笞夹打,痛楚难熬,还有“死”字做了后门,阴间是个退步。
这可谓退到极处了。这样一来,段玉初“全不觉有拘挛桎梏之苦”。
“退一步法”虽然有时显得很好笑、很肤浅,但一直发挥着效用,至今老百姓不是还在用吗?小品中“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想想人家克林顿”。知足常乐、知足守分一直是历经劫难的中国老百姓苦中作乐的法宝。西方快乐主义哲学家也信奉知足。“只有当我们痛苦而无快乐时,我们才需要快乐;当我们不痛苦时,我们就不需要快乐了。”可见痛苦中的快乐该有多么必要!
李渔除了提供给读者面对苦难的三大法宝外,在具体描写苦难时亦采取了举重若轻的态度,并化苦为乐。方法有二:其一,以轻快的笔调写灾厄。如《女陈平》、《奉先楼》、《生我楼》、《萃雅楼》。前三篇皆以战争做背景,《萃雅楼》则以忠奸斗争为主题。战争与忠奸斗争题材通常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笔下该是何等庄严与郑重。战争的血腥与沉重,忠奸的善恶较量都应该是全力推出的。然而我们读了李渔的这类小说却完全没有这些感觉,而是多了一些轻松,多了一些侥幸。前三篇虽未明说,其实都是以明末“东反西乱”,即李自成起义与清兵入关做背景。《女陈平》先也交待“忽然流贼反来,东蹂西躏,男要杀戮,女要奸淫。”但故事讲下来,我们被他设计的热闹的“二娘斗贼头”所吸引,二娘如此聪明、有手段,“竟把贼头当了傀儡猢狲,肆意挈弄”。流贼之乱淡化了。《奉先楼》写得略有战争感,写出了形势的险恶:“彼时流寇猖獗,大江南北没有一寸安土。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甚至有熬取孕妇之油为点灯搜物之具,缚婴儿于旗竿之首为射箭打弹之标的者。”写出了战乱令人如草芥,特别是令女人毫无尊严及丧失自我意志的辛酸,令人更感心寒与滑稽的是平日惯以督促家中女子守节的族人与家庙,竟然那么正式那么残忍地逼迫一个弱女子去失节,目的是为了存孤。而战乱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李渔又乐观了一把,让舒娘子碰上“鼎革以来第一件可传之事”,即遇到鼎革以来第一个可传之将军,既完了舒娘子忍辱存孤的节妇之名,又使夫妻二人与那三尺之童同归一处,皆大欢喜。《生我楼》更是如此,“从来鼎革之世,有一番乱离,就有一番会合。乱离是桩苦事,反有因此得福,不是逢所未逢,就是遇所欲遇者”。写盗寇横行,列举其罪状之一是将掳来的妇女论斤称两,卖与百姓。卖又不是好卖,“把这些妇女当做腌鱼臭鲞一般,打在包捆之中,随人提取,不知那一包是腌鱼,那一包是臭鲞,各人自撞造化。”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演出的却是父子团圆,夫妻会合的喜剧。其二,巧解灾厄。在《失千金福因祸致》、《三与楼》中解释英雄失志却换了另一个调调,认为英雄被埋没之苦本不为苦,不是造化弄人而是造化护人。《三与楼》,从解释卖楼进而解释江山更替。卖楼本是桩苦事,正该嗟叹不已,他却要形诸歌咏。显得潇洒和通脱,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解释为:“要晓得世间的产业都是此传舍蘧庐,没有千年不变的江山,没有百年不卖的楼屋。”不卖,使儿孙贱卖,导致的结果是:不孝不仁不智。卖的结果:对己博得个慷慨之名,对儿孙得个“不阶尺土”的美号。这也像江山更替,“从古及今,最著名的达者,只有两位。一个叫做唐尧,一个叫做虞舜。他见儿子生得不肖,将来这分大产业少不得要白送与人,不如送在自家手里,还合着古语二句,叫做:宝剑赠与烈士,红粉送与佳人。若叫儿孙代送,决寻不出这两个受主,少不得你争我夺,构起干戈。莫说儿子媳妇没有住场,连自己两座坟山,也保不得不来侵扰。”——天下,何其大也,朝代更替,往往要伴随无数的人头落地和鲜血淋漓,李渔亲身经历过那种血雨腥风,而用这几句话就开解了。
总之,李渔在对苦难的正视与咀嚼的同时融进了快乐因子。因为李渔的哲学是生活哲学,是为了活着的人奉行的有益哲学,李渔的哲学也是中国老百姓不自觉信奉的哲学。李渔,由于他的经历与阶层决定了他不会从哲学与宗教的终极意义上去评判人与社会,而是以一个普通百姓、普通文人的视角映现这个民族所依循的精神。因此他才会有笑对人生、笑对苦难的从容和潇洒。
三
要之,李渔及他的小说绝不像人们常评说的那样“浅薄”和庸俗。他,既有对自然人生的深切体味,又有对自然人生的热爱、参与和鉴赏;他的小说,洋溢着独到的对生活积极乐观的情思,只是所体味的有些别样而已。非从概念出发,亦非从教义出发,不那么崇高,不那么执着,亦不那么纯粹,但能用鉴赏的目光、积极的态度去发掘本不完美的生活那些稀有的美,从而给读者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他笔下的人物你可以轻蔑他们,可以指责他们,但你从不会看过之后而忽略他们。只要你敢承认你也是个俗人。
其实,要探求李渔鉴赏主义哲学的渊源,并不必要只从西方文化中找,中国人骨子里早巳蕴涵着这种质素。李泽厚针对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与民族性格曾提出“乐感文化”这一概念,他说:
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中国文化)不如用“乐感文化”为更恰当。《论语》首章首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还反复说,“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
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认为“乐感文化”即来源于孔子。孔子思想不是去建立某种外在的玄想信仰体系,而是去建立这样一种现实的伦理—心理模式。正因为孔子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它也就避免了、抵制了舍弃或轻视现实人生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观念。这种观念日益渗透在广大人们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即实用理性,具体表现为: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善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这种乐感文化所蕴含的乐生思想、饱满的乐生精神,是一种风雅的、细腻的和高度艺术化的东西,即艺术人生。
但后世儒学渐渐走向极端,遂改变原有的仁慈近人而为苛酷板滞。像鉴赏主义中味识人生这一部分内容,即乐生精神,常面临着被轻视和曲解的命运。好在明代中期兴起了重人伦日用的新型理欲观,其实李渔也由此汲取了营养,但很短暂,到李渔那一时代,又基本上恢复了对人性的苛酷,李渔及其作品也因此不被人所理解。在他给礼部尚书龚鼎孳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赍志以没,俾造化虚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故不得已而著为《闲情偶寄》一书,托之空言,稍舒蓄积。”(注:李渔《一家言》。)道出了世人只以“庙堂智虑”等大题目、大志向为高,而对立足于人生、鉴识享用人生的艺术多有忽略甚至轻视的现象,而这对李渔只知泉石经纶,无意于庙堂智虑的人来说,不能不引为憾恨。同时代的为《闲情偶寄》作序的余怀无怀氏亦为李渔抱不平,指责“世之腐儒,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者”(注:《李渔全集》第三卷第2页。)。此种价值的被忽略至今还存在,否则我们不会在此为李渔正名而大费气力。
正如李渔所说:“世间万物,皆为人设。观感一理,备人观者,即备人感。天之生此,岂仅供耳目之玩,情性之适而已哉?”(注:李渔《闲情偶寄·种植部·草本第三》。)在他心中,世间万物,无论巨细,皆为人而设。人是本,既为人而设,就有其抹煞不掉的价值。我们也理应重新解读素来被人忽略的甚至误解的李渔及李渔拟话本的独特价值。那么正视并肯定李渔的这种价值不仅能相对公允、相对客观准确地揭示一个作家的艺术世界,同时亦具有一定的小说史意义:李渔的拟话本完全是文人化的拟话本,它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共同将中短篇小说完成了文人化的过渡,只不过二者走的路途是那么不同。李渔求新求异之个性决定了他不会跟着“才子佳人小说”的风潮走,他要另辟蹊径,他也果真另辟蹊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