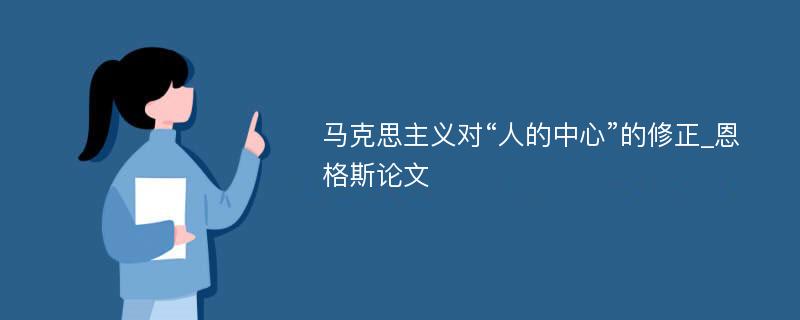
关于“人类中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人类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新世纪到来的,是事关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慎重思考,尽管保护环境已 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但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有 关“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论便是一例。人们在开发、利用和改善环境活动中究竟处在什么位 置?是人类,还是某个群体之作为“环境”的“中心”?而所谓“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泛道德 主张是否可行?马克思主义理应作出自己的回答。
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本来就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劳动使自然成 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也在人的身上延续其 存 在,成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使环境“人化” ,在环境中实现自己;不断印证人的本质力量,并赋予这种力量以历史的性质。“人创造环 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因此,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 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人作为人的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自然的发展(自然史)是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 ,与人类的发展(人类史)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当然要涉及它们的原始对立,“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 、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 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 与没有脱离自然的动物不同,人类不满足于对自然的消极适应,通过利用、改造环境的行动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人类的出现,人与环境的对立、矛盾和较量就一天也没有停歇过, 如果人在自然力面前无所作为,便谈不上什么文化、文明,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了。
事实上,人从周围“环绕”(envion)的自然条件中脱颖而出,分手脚,开智慧,作为一个 有智力的物种,他从一开始就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压力,并且必须不断克服这些压力才能生存 和发展。
火和劳动工具的利用,使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大大增强了,他“通过自己的 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改变完全被动受制于环境的生存方 式,营造一个更大程度上是由人创造的环境。远古时代的人们从事模仿自然生长的生产,出 现了最早的农业和牧业,他们对提供生命之需的自然满怀敬畏之情,又诞生出各种自然崇拜 ,这就是“文化”(culture<拉丁文cultura,即耕作、培育,衍义教育、修养和文化;而c ul t又是崇拜、景仰)的起源。人的活动日益改变了自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 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文化(耕作)的意义就在 于:没有对自然的适应就没有人的生存之地;没有对自然的改造就没有人的发展空间,人类 社会即由此开拓出来。
比起原始的采集、狩猎和捕捞活动来,哪怕是刀耕火种的农业(agriculture=agri[<拉丁 文 agre,土地]+culture)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人类对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发轫。由于农 业,丰衣足食成为可能,人口也稳定增长了;而农业主要是靠天(自然)吃饭,“顺应自然” (拉丁文secum dum naturam vivere)便成了古人信奉的基本信条。
“(农业)使人类与现实自然界保持联系,在自然界中,人是而且始终是十分脆弱的部分; 使人类较广阔的居住地成为具有人情味的高尚场所;提供正当生活所需要的食物与其它原料 ”(注:[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页。)。当然,农业规模必须与自然环境的生长(再生)和净化(自净)能力相适应才能做到这一 点(注:考古人类学表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衰落就与当地森林消失和耕地退化有关。北非曾 是罗马帝国的粮仓,但土壤风化使那里的农田变成了沙漠,南美玛雅文明的瓦解也大抵如此 。马克思认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 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饶有意味的是,世界各地的古老神话中都有一个归根结蒂者(即“帝”、“上帝”)开天辟 地,而“环境”概念的起源与这个创造行为有关,古人“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 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当人们意识到应该把自己与环境区别开来时 ,就把环境拟人化为具有无限生长能力的“自然”(希腊文physis,本义生长),众所周知的 “自然(大地)母亲”隐喻应运而生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列举了“自然”的几种含义,他所研究的“物理学”(拉丁文physica)实 际上是关于自然之所以然的自然之学:由生长,到本性,再到自然物的集合(自然界)。更早 些时候,中国的老子则提出更精辟的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老子·二十五》。)法 ,就是根据、效法的意思。
古代的西方有“大宇宙小宇宙”(macrocosm and microcosm)说,如肌肉对应于土,血液对 应于水,气息对应于空气,体温对应于火等等。类似地,中国人认为“天有日月,人有两目 ;地有九州,人有九窍”;(人的)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形体 骨肉,偶地之厚;耳目聪明象日月,体窍理脉似川谷,喜怒哀乐类神气;内有五脏副五行, 外有四肢副四时;乍视乍瞑副昼夜,乍刚乍柔副冬夏;乍乐乍哀副阴阳之类的比附(注:见《黄帝内经·灵枢》、《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等等。)。可见 ,基于古代农耕文明的人与环境观念是无所谓什么中心不中心的。
二
在对日后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自然(界)是上帝的作品(造物),《 圣经·创世记》说,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使他们对海里游的、空中飞的、地上走的 爬的,乃至整个大地拥有支配权(have dominion),因此人在上帝创造的“环境”中处在一 个特别优越的位置。人所居住的地球被置于中心的宇宙模型更强化了这种信念。中世纪哲学 家用natura naturata(natured nature)来表示“被创造的自然”(相当于形而下的Being), 而用natura naturans(naturing nature)来表示“创造的自然”(相当于形而上的Letting b e),已经寓示了自然概念的分化。
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性”(humanus,人文、人道都是这个词)的旗帜,反对由来已久的禁 欲主义,世俗功利合理性又在新教伦理那里得到了证明。近代科学兴起,动摇了对上帝的迷 信,并把自然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由人来扮演这个世界舞台“中心”的角色(在这个意义 上,说人文主义即“人类中心主义”亦大抵不差)。
培根提出,人类不仅要自然服务于自己,而且还要用技艺制造新的自然;因此首先要了解 自 然,使知识变为控制自然的能力(“知识就是力量”)。伽利略认为自然物均具有机械运动的 性质(“第一性质”,以区别于人所感知的“第二性质”),人的因素开始从自然中分离出来 。笛卡尔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二分,并构成典型的机械自然观:人是自然的旁观者;上帝创造 了自然,并使之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运行,就像一部大机器。牛顿打破“天上物理学”与“地 上物理学”的界限,将支配自然运动的统一数学原理明白地作为科学透彻研究的对象。后来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并以“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揭橥理性,而黑格尔的(合)理性既 意味着人类的合目的性,也包括了自然的本性和规律,但在“绝对理念”的笼罩下,自然不 过是一个中介或扬弃物罢了。
大地母亲的自然图景被取代了,近代的自然变成了“物”,而且“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 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父权的征服和统治的关系(注:见C.Merchant,The Death of Nature: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Harva rd Univ.Press,1980.)。自然 不再具有生命,而是一架可以通过力学(machanica,即机械)方式推动的大机器。机器的时 代“不仅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人不仅在手上而且也在 大脑里和心里机器化了”(注:见[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9页。)。自然作为可操纵和被控制的对象,变成了一个“物理学的世界 ”、一个“祛魅的世界”(Disenchanted world)。
欧洲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实现了产业方式的伟 大变革。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工业是自然 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之间的现实的历史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工业形成的自然界,以异化的 形式集中体现了近代人的创造力和所掌握的物质力量。如果说,农业文明是同土生土长的“ 自然”打交道;那么,工业文明就是同它制造出来的物理世界打交道。工业革命仿佛用魔法 呼唤出来的财富,使人陶醉于征服的喜悦,以为只要熟练如仪就能对自然为所欲为。“由于 这些变化,人类确实一下子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知识和力量。可是,人类陶醉于这种成就,认 为这正是自己是万物的中心的证明。……人们还过多地滥用和浪费这种力量和智慧。整个环 境 因此而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注:见[日]池田大作、[意]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 988年版,第158页。)
重要的是,工业造就的物质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掠夺、殖民和利用先进技术 开采欧洲以外的资源的基础上的。从地理上看,它并不是自给的,而是依赖于开采全世界的 资源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的。”这种繁荣也是建立在开采非再生性资源和可耗尽资源的 基 础上的,它在时间上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些资源现在使用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就再也不能 得到了。这种繁荣又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不断的和不可逆的转变的基础上的。土地被用来生产 而完全不管原有的植被和动物群落,农业和工业废料被排放而不考虑(常常是不知道)它们对 生态的影响。因此,它在生态上也是不能自立的(注:[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商 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7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业“一方面聚集 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 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页。)这就进 一步破坏了城乡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生活,而“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 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张,它在给近代人带来以往无法想象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面貌同时,又 “必须通过提取、加工和消耗自然资源才能存在,所以世界经济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无法 摆脱的联系。同时,这些资源又必然遵从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并最终成为废物而排出”(注:[英]戴维·皮尔思、杰瑞米·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人们不仅争先恐后开发现在的自然,还肆无忌惮地预支未来的自然,而“不能预见的作用占 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页。)。这种剧烈“透支”的积累效果终 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率超过了它们的再生能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率 超过了发现其替代品的速度;环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不可逆的环境退化程 度超过了新环境建设的速度。
20世纪两次大战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几乎被等同于现代化)成为各国发展的 优先目标,但与之相伴的是:温室效应引起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城市大气污染和酸 雨频频,日益广泛的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森林锐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全球环境状况愈来愈向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向演变,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遏制,用不 了多久地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
……
人们追溯工业社会的思想根源,环境危机被归咎于启蒙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与人 类 沙文主义、人类征服主义相提并论,并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 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注:一般说来,非人类中心主义旨在扩大价值共同体的范围,认为自然物种和生态系统本身 具有某种内在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能还原为人的兴趣和偏好。)。
三
所谓“环境”(environment),本义是环绕的周围,引申为环绕人的自然环境,或人类一切 活动所依赖的“场所”eco-(拉丁文oeco)(注:就此而言,经济学(economy=eco+nomy)和生态学ecology(eco+logy)都是关于eco-(场所 、环境)的学问。);而所谓“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 anthropo+centrism)(注:“人类中心主义”这个概念大抵可以在三个意义上使用:一是人作为宇宙的中心;二是 人作为一切事物的尺度;三是根据人类的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识世界(见Webster's Third N 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4th Merriam Co.,1976。)第一种意义其实早已为哥白尼的 日心说所否定,第二种意义出自古希腊智者派领袖普罗塔哥拉的名言,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实 用 主义的表述;第三种意义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宣扬的一个普遍观念:人是自然的 主人、支配者和统治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动者,是主体,而一切自然(物)都是 人改造和征服的对象;也有人直接把这种主体人居于中心位置的世界观叫做“人道主义”, 如海德格尔。)则意味着人类居于有周边(环境)的中心,这个周边,其实就是“自然 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事实上,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不断展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实现“超自然”的 生命价值,建立起(属人的)价值关系,就此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 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人在环境中的事实判断(当然更不是人类处在宇宙中心的判断)(注:有人也把以个体(不一定是个人)感性偏好(felt preference)为价值取向的称之为“强人 类中心主义”,而把经过审慎思考的理性偏好(considered preference)作为价值取向的称 之为“弱人类中心主义”(Bryan G.Norton,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 rism,Environmental Ethics,Vol.6,No.2)。这种划分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前者实际上是 个体,而不是人类的中心主义。)。 人是价值的主体,而一切非人的东西只能属于对人来说有价值的对象(客体);但是,人的活 动又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制约,超过了某种限制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人,既是环境的消费者,又是环境的生产者。人力既是自然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最具有破 坏性的力量,它可以提高自然的质量,促进环境的良性循环,也可以破坏自然的平衡,引起 环境的严重退化。而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人自己。只有人具有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创造的能 力,承担得起对自然的责任,也只有人能自觉意识到环境恶化终将有损于人类利益和价值的 实现;并通过反思自己的行为,借助文明手段和道德观念改变这种状况;人又是唯一有所预 期,能通过实践活动逐步实现希望、想象和未来之梦的物种,人类对未来的投入,决定了人 类摆脱生态困境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注:见W.H.Murdy,? Anthropocentrism:A Modern Version,Science,187(1975).)。
维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维护人类的利益,人类的需要 和利益(应该是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人类要求保护 的是更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恢复相对于人类来说的生态平衡。但具体的“人”( 可 以放大到群体、利益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总是有目标偏好和时间偏好的,他们所追求的 往往是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着眼于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 义是不可能超越的,而要超越的是恰恰基于狭隘的(局部的)、短视的(眼前的)个体利益的什 么中心主义。
在“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条件下,个体的人“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 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尽管人们也在“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 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 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 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 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 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但是,正如离开 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无法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离开人与人的关系也无法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所不 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 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1页。)。要消灭现代工业不断产生的矛盾,就必须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 性质。
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人类所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 道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3页。)。马克思寄以希望的“社会化的人”,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 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这个论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而共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 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尽管这个“真正解决”还有待时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环境所包容的是全人类, 而不是某个群体、某个利益集团或国家;无论哪一个群体、利益集团都不能把自己的环境利 益看得比人类的环境利益更重要,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能我行我素,置全人类的环境诉求于 不顾,更不能转嫁环境危机,推行损人利己的生态殖民主义,不管这种转嫁是以什么名堂表 现出来的。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 害。这就要求当代人改变征服者的姿态,“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引者按:可广义地理解 为 自然)改良后传给后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5页。);要求人们遏制唯利是图的扩张主义、享乐主义蔓延,补救已经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建立与环境相协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要求对人的行为 有所限制,避免向环境的过度索取和过度排放,防止自然满足能力的下降,同时努力开发自 然的潜力、改善自然的状况,促进自然满足能力的提高。人们不仅在对待自然的手段和行为 方式上,而且在预见可能产生的结果上都应采取明智的选择,将有限资源的单纯经济利用转 变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利用,这也意味着个体不得不放弃一些局部的、短期的利益,调 整其与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正确处理有关环境的适应与改造、利用 与保护、索取与补偿等许多关系上。
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对自然做了什么,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注:J.Passmore,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New York,Scribner's,1974.)。人类的这个 中心位置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由于民族冲突、阶级压迫和不公正利益分配的客观存在, 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尚有许多艰难和变数;但无论如何,人类视野中的环境问题,不能仅仅 诉诸于道德愿望,而更有赖于科学的解决,有赖于人类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而如果“要 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2页。)。
克服环境危机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只有站在人类的,而不是生态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基 于人类的,而不是环境利己主义的利益来思考和行事,才能有助于真正实现“人同自然的和 解”和“人同自身的和解”。“它将更有力地表明我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 部 自然,月球,和外层空间,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现成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的能力( 这种能力广泛地分散在社会中每一个人身上),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注:[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 调整、规范人们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促进人类健康的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人的实 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的生动体现,当然这种愿望的实现,任重 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