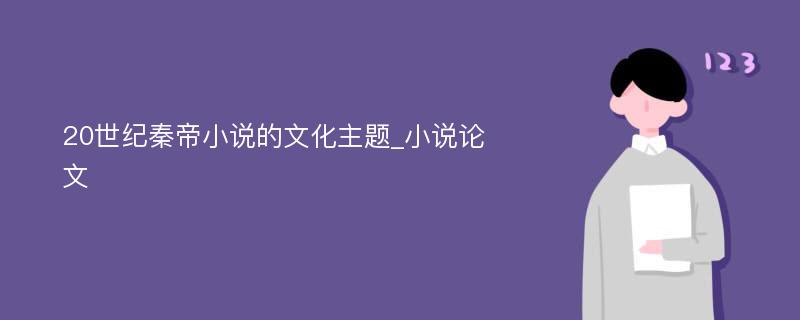
20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秦地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倘从地域文化角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深入考察,便会看到,由于三秦文化的制约和影响,20世纪秦地小说主要呈现出四大文化主题: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性恋·爱情主题,解脱·信仰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文化主题在滋生于本土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复合、转化为地域文化的精神传统,对后续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 秦地小说 文化主题 地域文化
从历史上看,秦地诚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20世纪的三秦文化与秦地小说相偕而行的“文化苦旅”,则让人们尤其能领略到秦地作为“厚土”的特有风貌。[①a]如果说“文化涵括着小说,小说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②a],而小说的“文化主题”既指主要的文化题材,又指主要的文化思想的话,那么,秦地小说家必然得益于作为地域文化而存在的三秦文化的滋养,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也必然和三秦文化有着血肉相关的密切关系。仅就秦地古迹胜地所显示的地域文化景观而言,它们便形象地向人们打开了一本丰富的巨型教科书,给那些明慧的秦地作家带来了许多灵感与启示。比如从蓝田遗址、半坡纪念馆、轩辕黄帝陵、秦皇兵马俑、汉唐丝绸路、临潼贵妃池、马嵬贵妃墓、大雁塔、法门寺、楼观台以及李自成故地、延安宝塔和窑洞等古迹胜地所展呈的文化视象中,20世纪秦地小说家亦不难感悟到那隐现于历史烟云中的文化主题,并将其充分地展示在一系列作品之中。概而言之,20世纪秦地小说主要呈示出了深受三秦文化影响的四大文化主题,即“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性恋·爱情”主题,“解脱·信仰”主题。以往我们较少地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秦地小说及其文化主题,这里且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对加深认识和理解秦地小说或许不无裨益。
1
是生存还是毁灭?黄土地上的绿色生命似乎总要面临着这一严酷的问题。与绿色生命同在的秦地农人也是如此。在自然条件极其严酷的大西北,深重的苦难及其如影随形的天灾人祸,使这里的人们拥有着异常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创业冲动。苦难既消解着生命,又激励着生命。柳青在《创业史》开篇的《题叙》里,用不少笔墨来写秦地1929年发生的那次可怕至极的旱灾,[③a]写梁三怎样在逃难的人群中找到了快要饿死的一对母子,从而有了家,并一起顽强地挣扎着生存下来,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这种回溯“旱灾”的笔墨,确如日本学者冈田英树所说,“已经为小说准备好了1953年春的背景”。[①b]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也写了这次持续数年、死人达数百万的特大旱灾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民生民俗的事象,诸如赈灾、祈雨、暴乱等等,都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切的印象。
干旱,意味着生命之泉的枯竭,人性得不到生命泉水的滋润,即使没有泯灭,也极易变得愚鲁和火爆。尽管秦地除干旱之外,还有霜冻、冰雹、水涝等其他灾害,而且陕北、关中和陕南的灾情也不尽相同,但最数旱灾为害尤烈,对秦地人的生活和风俗影响也最大。
当然,天灾与人祸常常联袂而至,灾害的发生每与人间种种罪恶的统治、掠夺行为密切相关。《陕西省志·农牧志》在介绍近现代陕西农村“灾难深重”的根源时,便列述了这样几个原因:1.分摊赔款,加重农民负担;2.天主教案,干扰农民生产;3.镇压农民起义,破坏农业生产;4.鸦片入侵,大量侵占农田;5.旱灾频繁,民不聊生。[②b]由此可见“人祸”为害之烈远甚于天灾,并且,“人祸”还常常是“天灾”事象的深层原因。《白鹿原》第4章照引了斯诺《西行漫记》中的话说:“……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注重对人间苦难的“人祸”根源的揭示,本是中国20世纪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优良传统。作为“左联”作家的冯润璋,早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便以当时的中国社会为背景,状写秦地农人所承受的深重苦难,揭示了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等“祸陕”祸民的社会根源。如他的小说《逃兵》、《丰年》、《劈开来》等,就相当深切而又生动地展现了秦地农民的苦难生活,对地主逼租、官家逼税、军阀抓兵等社会怪现状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天灾人祸的理性分析态度,在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等新时期秦地小说中,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露,对人间“左祸”或极左之弊害给予了深沉的反思和批判。
秦地作家对苦难人生的集中关注,使他们既不淡化对天灾人祸的冷峻审视,又不忽视对秦地人承受苦难的坚忍品格的热烈称扬。有学者指出,苦难既能消磨生命热情,也能激励出英雄豪气,既能谱写出生存的种种悲剧哀曲,也能唱出豪迈激越的喜剧壮歌;有时坚忍会显示为一种刚强,有时坚韧升华为一种豁达,有时坚忍还养育了美。[③b]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一系列作品中,就在道德层面弘扬了黄土地上的男女老幼或父老乡亲从苦难中历练出来的高尚品格和刚强豁达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极写了秦地人创业的艰难、人生的曲折和求学的不易,远离鄙俗而归趋于崇高,展示了既古老而又现代的审美理想。贾平凹前期的《满月儿》、《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以及《浮躁》等,大抵都可视为志在改变穷困面貌的“创业记”,其创作主旨也应合着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当然,秦地作家中在营构“创业”史诗方面最突出的作家是柳青。他的《创业史》第一、二部,在集中揭示农民的生存经验和合作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与曲折性方面,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要想彻底摆脱贫困,仅靠数千年习惯的个体自然经济和带有严重局限的个体现代经济,充其量只能缓解贫困,在现实中或可视为权宜之计。随着人们觉悟的真正提高和其他条件的完善,现代合作化道路(可以超越阶级乃至民族的界限)终必超越尝试与失败的层面,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要创大业以摆脱贫困并走上共同富裕和幸福的道路,秦地人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文兰在《丝路摇滚》中即写了现实改革中以狼娃为代表的西北汉子的艰难而又勇猛的探索。“创业难”的旋律再次响起。既善于写战争风云又善于写和平建设的杜鹏程就曾认为,和平年代的建设,并不亚于昔日战场上的拼杀。这在韩起的《水焚》、莫伸的《蜀道吟》等作品中也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2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挣扎生存的老百姓,常不免由于饥饿难当、逼上梁山而踏上造反的道路。在20世纪,传统的造反形式(主要是起义暴动和绿林为匪)在马列主义引导下发生了现代转型,这就是革命。这种世纪性的重大主题在秦地小说中得到了很突出的表现。从历史上看,秦地民间确实拥有着让人惊叹的造反传统。尤其是陕北,县志所载的内容,用高建群带点夸张的话说,“其实是一部饥饿史和暴动史而已”。所以他在《最后一个匈奴》中非常专注地发掘着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野性之力和造反的传统,并将之与中国现代的革命联系了起来。陕北古时有安塞的高迎祥、米脂的李自成、肤施(今延安)的张献忠,现代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他们都从黄土高原卷起了狂飙,投入并延续着该地域强大的民间造反传统。事实上,中国革命正是依赖这一传统并促其向现代转型,才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由失败走向胜利。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长期生活在延安的李建彤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刘志丹》,相当生动地再现了刘志丹走上造反之路、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艰苦历程。
秦地作家涉写革命的小说相当可观,仅延安时期就有许多。这类小说的革命主旨大体从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地体现出来。一是针对旧世界即革命对象的揭露和批判;二是显示革命战争威力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描写;三是对革命的主体(工农兵)及其事业的正面歌颂。这些意向在柳青的小说世界中便得到较为生动的表现。检视柳青早期的《牺牲者》、《地雷》、《一天的伙伴》、《王老婆山上的英雄》、《喜事》、《土地的儿子》等小说,浓郁的革命气息就会扑鼻而来。他后来的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以及《创业史》,在深化革命主题方面也明显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在杜鹏程的笔下,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是作家倾心描写的重心,字里行间充溢着战斗的豪情和颂扬的格调。如其名著《保卫延安》在最后仍用激越而又含蓄的抒情诗般的笔墨写道:
周大勇,王成德、卫刚,像无敌的旗帜一样,率领着战士们,从沟里的梢林中钻过去,向延安的大门——高耸在天空的劳山进攻了。……
……北方,万里长城的上空,突然冲起了强大的风暴,掣起闪电,发出轰响。风暴夹着雷霆,以猛不可挡的气势,卷过森林,卷过延安周围的山岗,卷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征战过的黄河流域,向远方奔腾而去。这种出诸革命激情与理想的颂体文本,曾长期在秦地小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新时期以来的秦地小说中也还是多样化中相当突出的一类,如任士增的《不平静的河流》、杨岩的《西府游击队》等,都归结到对革命者人格的称扬。无可否认,在20世纪的中国及秦地,“革命”确曾长期是最激动人心的话语,也是文学中最醒目最有意味的文化主题之一。从当年延安窑洞中诞生的开辟新时代的革命文化,成了秦地小说作家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里也不必讳言秦地之“匪”与小说中“造反·革命”主题的密切关系。在习惯性的思维中,官/匪或成者/败者的二元对立模式,无疑使“匪”或“败者”(寇)成为草莽文化的创造者,也使“匪”具有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性。“匪”通常疏离家族意识或宗法观念,离经叛道,与民间源远流长的造反精神相通,表现上既有凶残、贪婪、暴躁、昏乱的破坏性一面,又时有打家劫舍、扶弱济贫以及讲义气、重承诺的另一面。秦地小说对这种复杂的匪性显然有着相当充分的描写,比如《最后一个匈奴》对陕北匪(黑大头及“后九天”一带的土匪)的描写,《白鹿原》对关中匪(如黑娃)的描写,都对来自民间的造反精神以及可为革命利用的社会基础有着大胆而又深切的揭示,都透入了民族秘史和革命史的底蕴。相比较,贾平凹所写的陕南匪(即“逛山”)虽也充分顾及到匪的复杂性,但较少强调匪的造反精神,而着意于描写匪的情感世界及地域文化风貌。
3
大致说来,80年代及此前的秦地作家,都是慎于写性写爱的。“五四”时期的郑伯奇受关中文化的影响,没有像创造社的伙伴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那样勇敢地揭开性爱的面纱;“延安”时期的丁玲、欧阳山等作家受延安革命文化的影响,甚至还抛开了自己原来长于描写性心理的笔墨,在写爱情时也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到了柳青、王汶石等五六十年代的秦地作家笔下,“延安”时期叙描性恋爱情的一般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写性意在暴露、写爱旨在衬托的倾向更加鲜明(如《创业史》写姚士杰奸占素芳、梁生宝与改霞恋爱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但到了新时期,开放搞活也使性恋爱情翻出无数花样,相应的描写也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主要是80年代后期以来的事情,尤以“陕军东征”的作品(《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热爱命运》、《八里情仇》、《骚土》)为突出代表。这些作品都逼视着人间复杂的性爱婚恋世界,都写出了曲曲折折的性爱婚恋情节及相应的性爱体味或性爱象征。这些描写表现出了对秦地性文化进行叩询的浓厚兴趣。
简略地分析秦地性文化,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三个层面。一是原始本能层面,主要是源于性本能的生殖文化。在新的人文视野中,秦地作家显然更真切地看到了秦地人生命的一种本相:贫瘠的土地上强化着更为旺盛的生殖文化。《白鹿原》开篇便切入这一性文化层面,着意描写白嘉轩为了生殖目的而“豪壮”地连娶了七个婆姨。这种描写极富文化人类学的意味,既很古老,也很时髦。《最后一个匈奴》在展示黄土高原上强盛的生殖文化景观时还明确指出:“在这荒凉的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生命的崇拜高于一切,人种灭绝,香火不续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东西……”。诚然,透视生殖文化可以破译民族的生存之谜,对禁欲主义或某些宗教信条也可给予质疑。但生殖文化也往往打上了性别歧视和“实用理性”的烙印,有其明显的局限性。[①c]
二是性的审美文化层面。在20世纪的秦地,文化娱乐的条件仍普遍匮乏,尤其像陕北的穷乡僻壤,“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夜晚,在这闭塞的一村一户被远远隔开的荒山野坳上,夫妻间的温柔,成了他们夜晚主要的文化活动”(《最后一个匈奴》)。在这种情形下,性爱活动涉入了精神领域,在追寻生命自由的渴望里,秦地人将性恋爱情的体验与想象,谱写成了一曲曲动人的信天游。这也是民间普遍存在的对性爱的美化与诗化。来自陕南山地的贾平凹,曾倾心于赛若山歌的“远山野情”;关中作家文兰也曾将“北方狼”(关中愣娃)的性爱能力给予了诗意的提升。此外,程海的《热爱命运》,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莫伸的《尘缘》等许多小说,也都在挖掘和表现秦地的性的审美文化方面,留下了一些优美动人的篇章。
三是性爱的社会理性层面。应在性爱描写中去观照社会人生,这是将性爱置入社会系统中进行考察势必会引出的结论。从现实社会出发去把握性际关系,必然更为关注婚恋中的社会因素,而非性本体。延安根据地小说已将爱情与革命、与生产牢牢地结合了起来,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白杨树派”[①d],则进一步弘扬了这种社会化亦即纯洁化的爱情描写方式,除了《创业史》堪为典范之外,王汶石的《大木匠》、《黑凤》,杜鹏程的《延安人》以及王宗元的《惠嫂》等,也都成功地将爱情婚姻与革命事业(包括生产建设)结合了起来。这种努力顾及性爱婚恋的社会理性的写法,在80年代秦地小说中仍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蓝袍先生》、《四妹子》,李天芳的《爱的未知数》等,都是以社会人生为透视焦点的,但不脱离对人物婚恋体验及历程的传神描写。90年代的秦地小说涉性描写增多,言情说爱司空见惯,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均能进入性爱的社会理性层面(如京夫的《八里情仇》、王蓬的《水葬》、李康美的《情恨》、韩起的《冻日》等)。即使像《废都》那样的恣意写性又寄意遥深的文本,也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中展示性魅力和性腐蚀力的,并由此显现出社会人生的莫可名状的沉重。
4
艰难的人生对秦地人来说,显然有些过于沉重。于是他们不断地寻求着解脱与超越的途径。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只要世间还有苦难还有困境还有绝望中的企想,就很难消除信仰、理想乃至宗教迷信等文化现象,与此相关,也很难抛弃文学艺术构拟的亦真亦幻的符号世界。对文学艺术神圣性的信仰,至今仍是秦地优秀作家心底珍藏的一个永恒之梦。
在秦地,既有久远的历史遗存的丰厚的宗教文化,也有从圣地延安崛起的旨在改天换地济世救人的革命文化。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革命文化,尽管有性质上的区别,但都与民间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最后一个匈奴》在生动地转述“割肤施鹰”这一民间故事时,不仅是在交待延安本名“肤施”的由来,也是为了说明一种地域文化精神,亦即奉献牺牲、惠及苍生的精神。当年的革命队伍正是受到这一方水土的滋养和民众的“肤施”而不断壮大,同时又将歌颂救星和解放的民众心声谱成时代的强音。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伟力”确乎不能忽视。贾平凹的“商州小说”,亦多有对民间信仰及神秘文化的描写,即使在近年来的“古都三部曲”(《废都》、《白夜》和《土门》)中,也注入了道家文化的精髓,将“老牛”请进了“废都”,将“民俗馆”搬进了“白夜”,将“生命之根”(众妙之门)栽进了“土门”。倘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贾平凹,应该承认其文化心理中更多一些中国本土的道家、道教文化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秦地亦是道家、道教文化的沃土。陕南有东汉末年创立的五斗米道,信奉老子《道德经》;关中有名播遐迩的楼观台,有全真道创立者王重阳及其著名弟子“北七真”的布教……。所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②d],此言确有深意。草芥之民的生存经验似乎天然地倾向于道家——道教的文化信仰,并借此在精神上有所解脱和超越。赵熙在《狼坝》中,就相当充分地写出了道家、道教文化对狼坝山民和官仔的深切影响。作品中的苏静远从仕途退归田园山林,曾热衷于在名利场上明争暗斗的周五爷也在困境中归于修道,金田厌弃了人之争斗而重做割漆人……作家在这里表达的,不仅有对社会现实种种丑恶的批判,而且也有对着意于解脱苦难、寻觅家园的民间文化精神的称扬。
在沉重的生活苦难中坚韧顽强地执著于生命,浑浑沌沌却又豪迈苍凉,其间总让人感到有一种类似宗教精神的民间信仰,支撑着那周而复始的过于沉重和黯淡的岁月。曾是陕北知青的史铁生,在《插队的故事》中写出了对民歌的深切感受:“不过像全力挣扎中的呼喊,不过像疲劳寂寞时的长叹。……歌声在天地间飘荡,沉重得像要把人间捧入天堂。其中有顽强也有祈望,顽强唱给自己,祈望是对着苍天。”难怪秦地小说中会有那么多对民歌民曲(信天游、秧歌、道情、秦腔、山歌等等)的借用与化用。此外,秦地作家也注意对民间宗教或准型宗教文化活动的描写,从中探觅民众面对苦难寻求解脱的文化心态。比如蒋金彦的《最后那个父亲》,就对民间的信仰民俗(如跳端公、魁星送灯等)进行了相当细致的描写,从而揭示了“平民百姓如何得渡苦海,走向现代的心灵史。”[①e]为了守护经常陷入危机中的生命和家园,秦地乡民代代传承着一些信仰习俗和相应的祈祷仪式,其中的文化意味也显然引起了秦地作家的浓厚兴趣。陈忠实在《白鹿原》中曾以浓墨重彩描写白嘉轩率村民在关帝庙祈雨,在传达那种极为紧张、神秘而又悲壮的气氛的同时,将白嘉轩的那种虔诚与牺牲精神以及不甘屈服而欲感天地泣鬼神的民性,也相当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作家写此显然并非要宣扬迷信,甚至其中也隐含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和批判之意。应该说,20世纪的秦地作家毕竟经过了科学主义的洗礼,像郑伯奇《忙人》对桃花坞村民崇拜偶像的讽刺、柳青《创业史》对梁大老汉迷信行为的描绘,与其说十分真实,毋宁说相当浪漫。耐人寻味的是,社会历史与人之命运很难被人们预先设定,就像《八里情仇》中的荷花从苦难中走向教堂复又从教堂中走出那样,很难说悲剧已经终结。
通过以上对20世纪秦地小说文化主题的简略考察,我们大体可以认识到这样几点。其一,20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的生成莫不有着本土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无论是秦地小说较早引人注目的生存·创业主题,造反·革命主题,还是近些年才格外醒目的性恋·爱情主题,解脱·信仰主题,就都与三秦文化的渗透、制约和影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三秦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在逐渐开放的20世纪也会持续地同化一些外来文化,从而不断建构着新型的地域文化及相应的人文环境,并由此对秦地作家的小说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二,20世纪秦地小说的各个文化主题在作家笔下并非是被孤立地表达着的,而是以复合主题的形态显现于同一作品之中的。尤其是秦地那些优秀的小说,都有着相当丰富的主题意蕴。同时也应注意,尽管同受三秦文化的影响,作家也会因创作个性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地表达某一文化主题。因此,不必要也不可能要求同一位作家对所有的文化主题都有充分的表达。其三,20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在滋生于本土文化土壤的同时,也在文学传播及接受过程中,复合、转化为地域文化的精神传统,从而对后续创作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文学界内部的传承和发展,不仅可以发生于上下代作家之间,而且在同时代作家之间也可以互相产生影响。其四,20世纪秦地小说的文化主题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就其复合性的文化主题的两个层面而言,常常是前一层面(生存、造反、性恋和解脱)尤其可以引人逼近历史与现实,后一层面(创业、革命、爱情和信仰)则尤其可以引人亲近未来和理想,尽管20世纪秦地小说在表达其文化主题时并不尽是完美无缺的,但无疑在总体上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少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的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a 详参拙文《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片论》,《小说评论》1996年第6期。
②a 白海珍、汪帆:《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a 《陕西省志·农牧志》载:“民国18年,88县大旱,受灾人口650余万,旱灾持续3年,死250余万,外逃40余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①b 冈田英树:《长篇小说〈创业史〉——生动的农民群像》,《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第223页。
②b 见《陕西省志·农牧志》,第143页。
③b 参见樊星:《北方文化的复兴》,《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
①c 参见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①d “白杨树派”是笔者对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秦地作家为代表的小说流派的命名。参见拙文《大师茅公与秦地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②d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①e 赵德利:《命运悲剧的探寻与超越》,《小说评论》1996年第2期。
标签: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最后一个匈奴论文; 平凡的世界论文; 创业史论文; 白鹿原论文; 创业论文; 废都论文; 八里情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