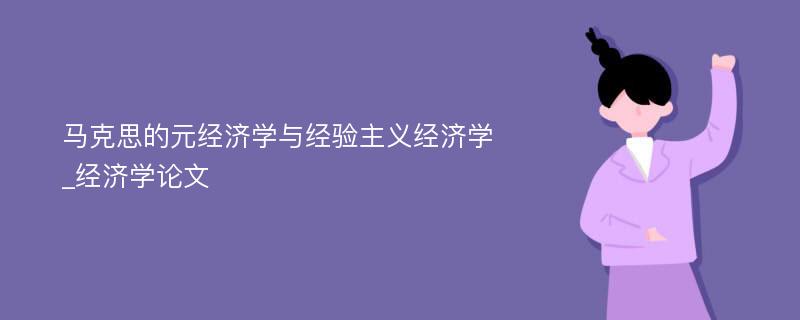
应该区分马克思的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马克思论文,实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转轨,给经济学家们,特别是新生代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建立各种过渡时期(或称转轨时期)经济学理论的机遇。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从总体制度到具体制度的急剧变迁和不断创新,为经济学家从事现实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素材。中国的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抓住了机遇,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经济学论著,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并没有系统的本乡本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这一点不同于文、史、哲领域。在文、史、哲领域,传统的中国文化得以在现代土壤中生根,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扬光大,影响波及海外。在经济学领域,我们一律是拿来主义。当代经济学家们运用的理论工具无非是两个方面:作为正统老派(但并非都是老人)的马克思经济学和日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新派(也并非只是年轻人)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目前,后者在纯经济学理论界已经占据大半壁河山,并试图将整个经济学理论研究彻底规范到运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张军1997年)——以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的范畴、术语、方法和工具去交流。马克思经济学日渐萎缩到只能占据大学公共政治课的讲坛。
一种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这种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马克思经济学地位之所以日趋下降,就其客观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套理论、概念和方法,无法准确有力地解释现实经济;二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很多具体结论和预测被证明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和现实的。尽管很多马克思经济学家们仍试图放松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约束条件,使理论对现实具有更广泛的说服力,但修修补补并无助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此相反,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的范畴、方法和工具,特别是与新制度经济学结合起来后,为新生代经济学家提供了新鲜有力的分析工具。许多新制度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似乎是专门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创立的,就是在西方,它们也很难像在中国这样得到充分的运用。时代对一种理论体系的选择,同样有一个效绩比较问题,只有那种真正具有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才能为时代所选择。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时代创立的经济学理论,究竟是否仍有生命力,是否仍能对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严格讲,两者同属西方式经济学)是否水火不容,或能否将两大理论体系融成一个整块。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
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必须区分成两个层面:作为元经济学的纯理论经济学,或称之为作为“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张军1997),它提供了从事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工具和方法;作为对现实经济进行具体研究的实证经济学(注:西方经济学也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但它的实证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元经济学范围;就是它的规范经济学(如福利经济学),主要也是提供了分析经济效率的一种方法。如一定的财产分配结构,总是对应着一种帕累托最优。但对财产分配结构本身已经被排斥在研究之外。笔者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实证经济学的概念。),它是运用元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对某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发展阶段、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研究。经济学中作为共性的、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是前者,而后者的内容都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什么是马克思元经济学?长期以来,理论界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元经济学,或者不加区别地把《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理论经济学,这是一种误解。《资本论》基本属于实证经济学,是马克思运用其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特定的以英国为代表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证研究。其研究的是确定的对象,并具有明确的时间界线,至于对资本主义以后发展趋势的研究,则属于经济预测。预测无论怎样科学,终究是预测,与对现实经济的实证分析必须区别开来。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在于它是否科学地分析了、解释了特定的研究对象,而不在于它是否适用于将来。如同今天新生代经济学家们对中国过渡经济学研究,也只能适用于过渡时代的经济现实,而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未来经济。因此《资本论》中很多具体的观点和结论不能用来解释当代西方经济,这是完全合理的。
那么作为分析方法的马克思元经济学在哪里呢?马克思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包罗在被划归到哲学范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去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属于马克思的一般哲学理论,哲学界早已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实际上被后人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属于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马克思元经济学的内容。关于马克思哲学体系应该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仍无定论。但现在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很多范畴和原理,不属于哲学范畴,而属于经济学范畴,这是十分明显的,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社会经济制度、阶级等,这些范畴与研究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为主题的哲学理论(高清海1988年),显然不属于同一层次。由于长期以来把这些范畴看成是哲学范畴,使马克思元经济学研究窒息在哲学框架中,而把马克思的实证经济学,又当成是元经济学,这就很难科学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了。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从建立学科体系的角度,去有意识地建立一门元经济学,也并没有明确地把元经济学研究和实证经济学研究划分开。因此在他的实证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作《资本论》中,大量包含着元经济学的内容,而他的元经济学又同他的一般社会历史观、哲学观交织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但是作为后人去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必须把两者区别开来。他的作为方法的元经济学,是有长久生命力的;而对他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只能放在历史的坐标上去评价。
混淆马克思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界线,导致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解上的种种误区。第一,由于马克思实证经济学研究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就把马克思整个经济学都看成是有阶级性的,包括他的元经济学。实际上元经济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其本身是不存在阶级性的,它是人类社会互通共享的一种知识产物(樊纲1996年)。运用这种工具和方法,可以解释现实的经济运行并进行有效的预测。阶级性只能体现在对这种分析结果的价值判断、政策取向和政治导向上。而这些已经不属于元经济学范围内的事情了。第二,由于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制度的实证研究中,许多具体结论和预测的历史局限性,往往会认为整个马克思经济学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不适应现代经济现实。经济学家总是运用其创立的或被其接受的元经济学去研究特定的经济制度、发展阶段、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这种实证研究都具有历史性,随着客观条件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和发展,其研究的成果也将逐渐被淘汰。这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经济现象。马克思所研究的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很多区别于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特点。例如在生产要素占有上极度的两极分化。工人一方只占有自身的劳动,而资本家一方则占有全部物质性的生产要素。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界线分明,物质利益矛盾异常尖锐。分配机制就不是由市场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由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分配机制,而是资本在分配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分配机制。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必然是劳动收益的最小化。而劳动收益最小化有个限度,必须保证劳动力能再生产,否则资本主义经济将因劳动力的再生产得不到保证而呈萎缩式发展。因此,马克思得出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的结论。这一结论,既是对当时现实经济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又是根据当时分配机制的自然的逻辑推论。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素占有的广泛社会化,劳动要素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使得现代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与古典资本主义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对古典资本主义分配的实证研究结论自然不适合当代,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如果仍试图通过放松一些约束条件(如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是可变的,含有某些伦理道德因素等),强硬地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过去的实证结论来解释现实,那就显得可笑了。实证经济学的很多结论和预测的历史局限性,不能证明元经济学也已经过时了。元经济学虽然也不可能是亘古不变的东西,但其生命力比实证经
济学要长久得多。第三,不加区别地将马克思实证经济学与西方元经济学加以横向比较,相互否实或批判。元经济学只能与元经济学比较。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主要是提供了一套分析现代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过程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其核心内容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只能体现在对分析结果的评价和政策取向上。我们不能一方面广泛地运用西方经济学这套工具和方法去分析和解释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基本理论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除了这套范畴、工具和方法外,还存在什么基本理论呢?现在,在大学经济系的经济理论教学中,一方面不加区别地把马克思实证经济学当作元经济学进行灌输,另一方面又系统地学习西方经济学。两者由于属于不同层次的理论,形式上矛盾很多,观点截然对立,学生无所适从。所以必须分清马克思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能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横向比较的是马克思的元经济学,《资本论》只能被看作是马克思运用元经济学进行实证研究的一个制度案例,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第四,由于没有区分马克思实证经济学和元经济学,使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偏离了正常轨道。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主要体现在其元经济学中,经济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变化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逻辑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视角由古典经济学时代的总体制度的研究,转向到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将制度和技术等变动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暂时搁起,使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可以在封闭的、抽象的系统下进行;于是,最优、均衡、边际、替代成了新的基本范畴,数学分析法、边际替代法、均衡分析法等新方法得到了充分运用。新视角、新方法,使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形成了完美的结构、精巧的形式和逻辑演绎化的理论体系。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又逐渐将技术和制度等外生变动因素,内化到核心理论中,形成了宏观动态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使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研究的视野也在不断拓展。而后期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们,始终把马克思对古典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证研究,当作马克思经济学的灵魂,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为马克思实证研究结论正确性的辩护上,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元经济学的发展,使其始终停留在古典时代,这样就大大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现实的分析解释力和研究领域的扩展。这是造成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存在落差的主要根源。因此发展马克
思经济学主要应发展其元经济学。
马克思元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和体系是什么,这还要依靠当代经济学家们去发掘和整理。笔者认为,其核心内容主要应包括这些方面:社会系统观(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社会经济结构观(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范畴)、经济发展观和增长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及其演化观、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理论、阶级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分析法等。充实和发展这些马克思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元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恢复马克思经济学在当代的生命力。必须明确,元经济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本身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实证研究内容,也不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这里必须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法和阶级性两者分开。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元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阶级首先属于纯粹经济学范畴。阶级分析法无非是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相同地位者具有相同行为的经济行为分析法,是一种物质利益矛盾分析法,是经济人在经济行为中的内在动机分析法。其本身不能直接为哪个阶级服务。阶级分析法也不可能使一种元经济学就带有了阶级性。
马克思元经济学与现代西方元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基本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作为方法学科的西方主流派经济学,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上的:一是对人是有理性的,追求行为最大化的假设;二是“均衡”概念。其实,以这两个如此抽象的前提或假设能否成为特定学科的前提,值得怀疑。人是有理性的,追求行为最大化,撇开特定时代、特定经济制度下的具体内容,它可以成为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提,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至于“均衡”这一概念,无非是系统观的另一表达方法,而均衡也好,系统也好,可以说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共同具有的属性。作为一门特定学科的基本前提假设,应该是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定假设,过于宽泛的假设,等于是一种无条件的假设。正因为其前提假设过于宽泛,才使得很多新生代经济学家们企图将理论推演到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领域的分析,大有取代各门社会科学之势。
即使是作为一门元经济学,也有其实用的特定领域和历史界限。元经济学比实证经济研究具有更长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普通性,但不能无限制地滥用元经济学去分析任何对象。元经济学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元经济学往往只能适用特定领域的分析,不同元经济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马克思元经济学主要适用于对总体经济结构,总体经济制度变革的动因和过程,经济增长过程,特定经济制度下的阶级关系及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析。西方元经济学则侧重于在特定经济制度下,一系列约束条件下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和过程,各种具体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过程的分析。因此,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是十分明显的。在西方,挂牌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并不多见,但羞羞答答地运用马克思元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学家比比皆是。在特定领域,他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元经济学是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如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国新生代经济学家们,在他们对传统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进行精辟分析的一部部论著中,大多宣称运用的是“纯”西方经济学方法,但不知不觉中都在不断渗透和运用着马克思元经济学的方法(这也许得益于面壁苦读阶段对他们的被动灌输);而且也正是马克思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使他们作品的理论和逻辑分量大大增强,那么何必不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元经济学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经济分析工具呢?“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应该包括马克思元经济学语言!
标签:经济学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实证分析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