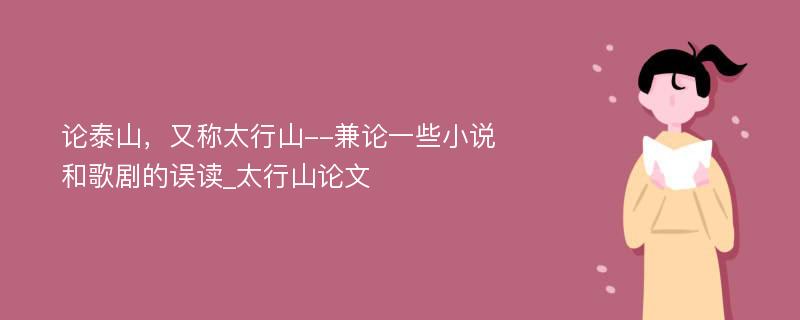
试说泰山别称“太行山”——兼及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行山论文,泰山论文,别称论文,戏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山之称始见于《诗经·鲁颂》,同时及其以后,又多别称。《尚书》曰“岱”(《禹贡》)、“岱宗”(《舜典》),《周礼》称“岱山”(《职方》),《尔雅》称“东岳”(《释山》)、“岱岳”(《释地》),《汉书·地理志》:“海、岱惟青州。”颜师古注曰:“岱,即太山也。”故又称“太山”等等。各有所据,为学者所熟知。但自唐代至明末千余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泰山又别称“太行”或“太行山”等,虽然流行未广,影响不大,但时有见于各类杂著与小说戏曲等文本,至今似不为人指出,造成百余年来对相关作品的阅读上的错误,应予辨证与澄清。
一 泰山别称“太行山”
众所周知,我国泰山与太行山隔华北平原千里相望,绝无联属。但太行山纵贯南北,古人号为“天下之脊”①,进而与黄河一起成为我国北方分区的两大界标。以太行山为界,北方自古及今都有“山左”、“山右”与“山东”、“山西”之称。而从来界划,泰山都在山东,距太行山远甚;又无论如何界划,泰山却又在太行山的界标系内。所以,古人言地理者,《上党记》仍有曰:“太行坂东头,即泰山也。”②“太行坂”即著名的太行坂道:一壶关、二阳曲、三晋城,均东西向。按今天的理解,此言应是说自太行坂出山东向,就可以到达东岳泰山,绝无说泰山与太行山相连或为后者之余脉的意思。但这句话毕竟把相隔千里的两座名山并在一起说了。是否因此导致后世诗歌有“太山”、“太行”似相混淆的做法③,还很难断定。但在小说中,自唐代即有径称“太山”为“太行”者,如《浮梁张令》写卸任贪官张令遇巧勾魂吏云:
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呼?”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行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④
“太山召人魂”本晋张华《博物志》卷一:“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魄。”可知其中持牒鬼使曰“太山召人魂”之“太山”,确指泰山。而牒之首云“太行主者牒金天府”之“金天府”,指西岳华山神金天王府第③,而“太行主者”无疑即“太山”主者。由此可知,本篇所称“太行”即“太山”,为东岳泰山之别称。
《浮梁张令》出《纂异记》,唐李玫撰。此篇别称泰山为“太行”,虽无旁证,但也不会是李玫个人杜撰,而应有先例可循,或与诗歌中“太山”与“太行”混淆之例为同一传统,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由此可知唐宋有以“太行”即“太行山”为“太山”即泰山之别称者,是一个事实。但从唐代文献中除此以外别无考见看,当时此称行之未广,知者不多。遂使后世学人,或为了从众,或由于少见多怪等原因,易“太行”为“太山”,以致有关作品版本出现作“太行”或“太山”的异文现象,也是一个事实。由此两方面事实的启发可知,唐宋及其以后文献中以“太行”为“太山”即泰山之别称的现象固然不会是大量的,但也不应仅此一二例,当仍有待揭蔽者。
元人文献中以泰山为“太行山”须揭示才见者,如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载元世祖与人问答云:
帝问相士山水。士奏云:“善恶由山水所主。”帝问:“太行山如何?”相士奏云:“出奸盗。”帝云:“何以夫子在彼生?”帝召僧圆证问云:“此人山水说得是么?”证回奏云:“善政治天下,天下人皆善。山水之说,臣僧未晓。”帝大悦。④
以上引文中“夫子”无疑指孔子。孔子为泰山之阳鲁都曲阜人。《诗经·鲁颂》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朱熹注:“赋也。泰山,鲁之望也。”故《论衡》称引:“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⑦而明查志隆《岱巅修建孔庙议》云:“圣哲中之有孔子,犹山阜中之有泰岳也。岂惟诞育降自岳神,乃其里居尤为密迩。”⑥这就是说,孔子诞生是“(东)岳神”降瑞人间,并且使之“里居”也离泰山不远。从上引帝问“何以夫子在彼生”可知,帝问“太行山如何”之“太行山”,和相士答以“多奸盗”之“太行山”所指为一山,但肯定不会是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而应当是指与孔子“里居尤为密迩”之泰山,只是用了它的别称“太行山”而已。
明代泰山别称“太行山”见于佚名《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以下简称《二郎宝卷》)。《二郎宝卷》上、下卷,卷末各署“大明嘉靖岁次壬戍(戌)三十四年九月朔旦吉日敬造”⑦。卷中叙確州杨天佑与云花夫妻本是天上金童玉女,生子二郎后双双参禅,《圣水浸润品第五》云:
参禅不受明人点,都作朦胧走心猿。猿猴顿断无情锁,见害当来主人公。念佛若不拴意马,走了心猿闹天宫。行者碓州来赴会,压了云花在山中。斗牛宫里西王母,来取二郎上天宫。二郎到了天宫景,蟠桃会上看群仙。走了行者见元人,压在太山根。行者回到花果山中,今朝压住几时翻身?母子相会,还行整五春。⑩
如上引文中“元人”即“主人公”是二郎的母亲云花,而正如卷中别处所叙,“心猿就是孙悟空”(11)。引文说孙悟空把云花“压在太山根”之后,就回花果山去了。而接下叙二郎劈山救母,又把孙悟空压在了“太山”之下:
移山倒海拿行者,翻江搅海捉悟空……撒下天罗合地网……拿住孙行者,压在太山根。总(纵)然神通大,还得老唐僧。(12)
又曰:“因为二郎来救母,太山压住孙悟空。”(13)直到唐僧取经路过,悟空求救,“唐僧一见忙念咒,太山崩裂在两边”(14),悟空才从太山底下出来。总之,这个二郎救母与孙悟空斗法的故事,始终围绕“太山”和以“太山”为背景。
还值得注意的是《二郎宝卷》中写泰山除多作“太山”之外,还一称“崑山”(15),又称“太行山”。后者出西王母教告二郎:“开言叫二郎,你娘压在太行山。子母若得重相见,山要不崩难见娘。”(16)从卷二中称泰山多作“太山”而偶作“崑山”看,这里的“太行山”应即“太山”,是说唱中随缘发生之泰山的别称。但这偶然一见是否造卷人“字演差错多”(17)的一例呢?这个疑问从《二郎宝卷》稍后成书的《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以下简称《泰山宝卷》)和应是明末清初人西周生所作的《醒世姻缘传》中似可以得到解释。
《泰山宝卷》是一部宣扬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灵应的说唱本子。车锡伦先生在其即将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中专节介绍此卷说:“这部宝卷是明万历末年黄天教教徒悟空所编。卷中泰山女神被称作‘圣母娘娘’或‘泰山娘娘’,它反复说唱泰山娘娘的神威和灵应,却没有统一的故事。”(18)因为“反复说唱泰山娘娘”之故,卷中“泰山”之称名络绎不绝。却与《二郎宝卷》不同,此卷中“泰山”除直写之外,均不作“太山”,而多作“泰行山”。如“泰山娘娘,道号天仙,镇守泰行山……眼观十万里,独镇泰行山”(19);“娘娘接旨仔细观,敕封永镇泰行山”(20);“泰行山,天仙母,神通广大”(21);“处心发的正,感动泰行山”(22);“施财虔心有感应,虔心感动泰行山”(23);“造卷的福无边,感动了泰行山顶上娘娘可怜见”(24)等。凡此七例,足证《泰山宝卷》中泰山又称“泰行山”,决非笔误。这种情况又必然是在与受众约定俗成时才可以发生,所以也不会是写卷人随意杜撰,而应该是明万历前后至少在宝卷之类民间说唱文学中较为通行的做法。由此上溯,可知明嘉靖年间《二郎宝卷》的泰山一作“太行山”也非写卷人之误,而是与此“泰行山”一致是泰山的别称,乃民间说唱随缘改称的产物。
《二郎宝卷》中“太山”即泰山别称“太行山”,还可以从《醒世姻缘传》第八回写青梅说自己“真如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一般”(25)的话中得到证明。虽然“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与上引《二郎宝卷》中说“你娘压在太行山”和“太山压住孙悟空”不一,但是参以卷中既称悟空把二郎的母亲云花“压在太山根”,却在西王母口中是“你娘压在太行山”,便可以知道《醒世姻缘传》所引“孙行者压在太行山底下”,其实也就是压在了“太山”即泰山底下,而《醒世姻缘传》的引述很可能是从《二郎宝卷》之类唱本来的;只是那个唱本“拿住孙行者”以下,不作“压在太山根”,而是作“压在太行山”,并衍为《醒世姻缘传》中的比喻罢了。由此可知,明朝中晚期流行的如宝卷一类说唱本子中“太山”即泰山与“太行山”时或混用的现象确曾存在,并且已经影响到如《醒世姻缘传》之类文人创作的小说,使“太行山”在文人所撰写的通俗小说中,有时是泰山的一个别称,乃隐指泰山。
二 泰山别称“太行山”的原因
唐宋金元明诸代泰山别称“太行”或“太行山”可能的原因,除上所论及“太行坂东头,即泰山也”等等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太行山之“太行”很早就被训读为“泰行”,从而太行山时或称“泰行山”,易致与“泰山”之称混淆。按杨伯峻先生撰《列子集释》卷五《汤问篇》“太形、王屋二山”句下集释云:“[注]形当作行……○王重民曰:《御览》四十引‘形’作‘行’,当为引者所改。○《释文》‘太形’作‘大形’,云:‘音泰行。’”(26)《御览》即《太平御览》为宋籍;《释文》为唐殷敬顺纂,宋陈景元补,亦唐宋间成书。因此可知唐宋间即已以“太形”为“太行山”之“太行”并训读为“泰行”。这显然有可能导致社会与文学中“太行山”被称为“泰行山”,乃至因此有笑话出来。宋李之彦《东谷所见·太行山》载:
有一主一仆久行役,忽登一山,遇丰碑大书“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随后揶揄官人不识字:“只是‘太行(如字)’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笑不已。主有怒色。仆反谓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钱一贯与官人。若是太行(如字)山,主人当赏某钱一贯。”主笑而肯之。行至前,闻市学读书声,主曰:“只就读书家问。”遂登其门,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公当赏仆矣。此只是太行(如字)山。”仆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仆请钱,即往沽饮。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复求见老儒诘之:“将谓公是土居,又读书可证是否,何亦如仆之言‘太行(如字)’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琐末耳。教此等辈永不识太行山。”老儒之言颇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辩。(27)
上所引例虽为笑话,但事或有本,显示宋代人于“太行山”读音进而认知上确实存在歧异。这一则笑话到了明朝为赵南星《笑赞》所改编,仍题为《太行山》云:
一儒生以“太行山”作“代形山”。一儒生曰:“乃‘泰杭’耳。”其人曰:“我亲到山下见其碑也。”相争不决,曰:“我二人赌一东道,某学究识字多,试往问之。”及见学究问之,学究曰:“是‘代形’也。”输东道者怨之。学究曰:“你虽输一东道,却教他念一生别字。”赞曰:学究之存心忍矣哉,使人终身不知“太行山”,又谓天下人皆不识字。虽然,与之言必不信也,盖彼已见其碑矣。(28)
这里赵南星根据于《列子》“太形、王屋二山”句的旧注,把李之彦《太行山》之“太行”的正读音训为“泰行”,讹音“如字”著明为“代形”,不仅意思更显豁了,而且其故事被改编本身,表明了赵南星认可“太行山”自宋至明有读音与认知上的歧异。若不然,则前后都不成其为笑话。所以《太行山》虽然相承实为同一则笑话,但仍由此可知,自唐宋至明代普通民众和一般读书人中,有以太行山为“代形山”者,也有以为“泰杭”山者。“杭”音“行(háng)”,从而“太行山”很容易就成为了“泰行山”,与民间也称“泰行山”的泰山发生混淆。这一现象在元代所可考见者,如无名氏[越调]柳营曲《风月担》即有句云:“可怜苏卿,不识双生,把泰行山错认做豫章城。”(29)其所称“泰行山”当即太行山,但也不免使人想到别称“太行”或“泰行山”的泰山。总之,如上自唐至明,因泰山别称“太行”与太行山之“太行”音读为“泰杭”,使在实际生活进而文艺中有发生太山——泰山——泰行山——太行山诸称一定范围与程度的混淆,并主要是以别称“太行山”隐指泰山的可能。
其次,是自晚唐五代以降讲唱文学中泰山往往被随缘改称之传统的影响。泰山不仅自上古多异名,更在晚唐五代出现在讲唱文学中时又往往随缘改称。如今存末署写卷年代为后梁“贞明七年辛巳岁”(921)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下简称《目连变文》),叙目连之母青提夫人生前造孽,死被“太山定罪”,在“太山都尉”管下“阿鼻地狱受苦”,目连救母,恨不“举身自扑太山崩,七孔之中皆洒血”,后来“遂乃举身自扑,犹如五太山崩”(30)。句中显然是为了讲唱的节律凑字数,把“太山”改称为“五太山”了。而《二郎宝卷》中有云:“二郎救母,访(仿)目连尊者……游狱救母。”(31)说明《二郎宝卷》写二郎救母拟定与“太山”的关系非作者自创,而是追摹《目连变文》救母故事以“太山”为背景的描写而来。那么既然《目连变文》中“太山”可随缘改称“五太山”,后世如《二郎宝卷》、《泰山宝卷》等因说唱节律的需要,而有“太山”即泰山为“太行山”或“泰行山”的改称,就是有例可循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论,自唐宋以迄金元明诸代,中国社会与文学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中长时期存在“太山”即泰山别称“太行”即“太行山”,和太行山别称“泰行山”的习俗。其成因除两山称名本身即易于混淆之外,还有宝卷之类民间说唱随缘改称的创作特点。二者的结合导致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而时过境迁,其在传世文本中的表现遂致后人的读误,试分说之。
三 黄巢题材小说戏曲中的“太行山”
旧、新《唐书》等旧史载黄巢为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僖宗乾符二年(875)从王仙芝起义,并于仙芝死后自称帝。其事历经十年,踪迹涉于大江南北,但有关文献未曾一称太行山,反而一致记载黄巢于僖宗中和四年(884)兵败“走保泰山”,并最后战死于泰山之狼虎谷(32)。另据周郢先生考证,黄巢除最后战死泰山并留下多处遗迹之外(33),还早曾一度占有并经营泰山以西地区,“从中足窥黄巢在泰山一带深收黎庶之心(后黄巢失利率残部“退保泰山”,欲借斯地以再起,当与此有关)”(34)。
今存宋元或至晚明初成书写及黄巢起义的小说,一是佚名《五代史平话》,二是署名罗贯中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以下简称《残唐》);另有陈以仁《雁门关存孝打虎杂剧》(以下简称《存孝打虎》)。这三种作品均据史演义,传统的写法应是大关节处不悖史实,但诸书不然。
《五代史平话》中涉及黄巢的为《梁史平话》、《唐史平话》,均未直接写到太行山;其写黄巢甚至不及其兵败自杀,而结于“黄巢收千余人奔兖州,克用追至冤句,不及”云云,也完全未及于泰山;《残唐》六十回,写黄巢起义始末在第三回至第二十回。其中第五回写黄巢杀人起事,“就反上金顶太行山,杀到宋州”;第二十回除虚构了黄巢兵败途中自刎于“灭巢山鸦儿谷”之外,还写他死前曾遇到“金顶太行山大将韩忠”,死后又有周德威追述前情说“巢即作了反词,反上金顶太行山”(35)。这两回书中共三次提及“金顶太行山”,而未及泰山。《存孝打虎》第三折写有黄巢上云“某在太行山落草为寇”(36),除不同于《残唐》的称“金顶”而仅及“太行山”之外,还与《五代史平话》同样地都没有写及黄巢结局是战死于泰山。
笔者以为,旧、新《唐书》等史著关于黄巢始末的记载,特别是黄巢起事与太行山无关和最后战死于泰山等重大历史关目,是包括出于“长攻历代史书”(37)之手的《五代史平话》在内的三种黄巢题材小说戏曲作者绝不会不知道的。但在三书之中,泰山除被用作比喻之外,完全不曾被实际写到,而是或如《五代史平话》与《存孝打虎》的宁肯不写黄巢之死,也绝不如实写他自杀于泰山;或如《残唐》虚构黄巢事始于“反上金顶太行山”,终于“灭巢山鸦儿谷”,而避不言泰山。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而只能认为是作者有意避写泰山与黄巢起义的关系。唯是《残唐》与《存孝打虎》的作者不甘或觉得不便于完全抹杀历史的痕迹,于是用了“金顶太行山”或“太行山”以隐指泰山。
关于《残唐》等之“金顶太行山”或“太行山”隐指泰山,除从其叙事与史实的明显不合可以推知之外,还可以举出以下理由:
一是从《残唐》叙事的矛盾可以推知。《残唐》写黄巢“就反上金顶太行山,杀到宋州”,但唐之宋州即今之河南商丘,在河南开封以东,与开封西北的太行山相去甚远。倘“金顶太行山”指太行山,则完全不合于地理的常识。这在古代小说虽是能够允许或可以被谅解的,但在作者明知历史上黄巢死于泰山而无关太行山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理解为其心目中的“太行山”实非太行山,而是另有所指,即距宋州为近之当时别称“太行山”的泰山。
二是泰山有“金顶”之称,“金顶太行山”即指泰山。笔者检索文献未见太行山有“金顶”之称,而清唐仲冕辑《岱览》收有末署“万历甲寅年七月吉日造”的《御制泰山金顶御香宝殿铜钟赞文》,除题目中已称“泰山金顶”之外,文中也有“差官修理泰山工程金顶大工:玉皇宝殿、天仙宝殿……”(38)云云。因知明代泰山之巅一称“金顶”,有“泰山金顶”之说。参以唐以降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则可信“金顶太行山”实指泰山。虽然这里似不便以万历年间的资料论前此成书之《残唐》中的“金顶太行山”,但可信上引赞文作为“御制”之作,称泰山之巅为“金顶”必于古有据,可以上作《残唐》中“金顶太行山”为实指泰山之注脚。总之,在太行山并无“金顶”之说,而泰山有“太行山”之别称又有“金顶”之称的情况下,《残唐》中之“金顶太行山”就不会是太行山,而应是别称“太行山”的“金顶”泰山。
还应该说到的是,三种小说戏曲写黄巢事避不及泰山乃至别称“金顶太行山”或“太行山”的现象强烈显示了一个历史的信息,即当是由于泰山自上古即为神山与帝王之山,又在宋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之后,泰山更加神圣(39),遂多忌讳,使包括宋元说话人在内的相关作者们觉得不便把诸如“盗贼”等负面的形象与泰山联系在一起,于是除书写中简单地完全规避之外,还与上论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相应,小说戏曲中早就有为避讳泰山而别称“太行山”的笔法被发明出来了。这一认识对于理解同时同类作品类似情况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四 《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太行”
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所录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以下简称《赞》)(40),是今存最早记载宋江三十六人姓名、绰号及主要特征的文献。《赞》中涉及宋江等人活动区域的地名不多,除赞阮小二有“灌口少年……清源庙食”和赞雷横有“生入玉关”等语,提及“灌口”、“清源”、“玉关”三处其实无关大体的地名之外,其他称“大行”即“太行”亦即“太行山”者,共有五处,分别是:赞卢俊义云:“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赞燕青云:“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赞张横云:“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伙儿,其数不足。”赞戴宗云:“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大行。”赞穆横云:“出没太行,茫无涯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诸赞中五称“太行”,除严敦易先生认为“这里面当是龚氏有意的用太行来影射,隐寓寄希望于中原俊杰草莽英雄的说法”,而非实指太行山(41),与本文将要得出的认识有一定契合之外,其他论者无不以为就是指太行山,唯是进一步的推论有所不同。如何心先生还止于说:“可见当时认为宋江等三十六人聚集在太行山。”(42)孙述宇先生就不仅以“这卅六人的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还把《赞》中“太行好汉”故事作为“水浒”故事的一个“分枝”,“标作‘山林故事’,以别于讲梁山泊的‘水浒故事”(43);王利器先生则更明确说《水浒传》成书的基础之一是讲宋江等人故事的“太行山系统本”(44)。现在看来,这很可能都是错误的,溯源即在对《赞》中“太行”为太行山的误判。笔者这样认为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综观史载宋江等活动的大范围,实际是以京东梁山泊为中心包括泰山在内的广大地域,倘以《赞》文五称之“太行”为太行山,则于史不合,所以当有别解。按宋人记宋江事,或称“淮南盗”(《宋史·徽宗本纪》),或称“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东都事略》。“河朔”,《宋史·侯蒙传》作“齐、魏”),或称“河北剧贼宋江……转掠京东,径趋沭阳”(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或称“宋江……剽掠山东一路”(张守《毗陵集》卷一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或说“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宋江扰京东”(方勺《泊宅编》),或曰“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或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宋史·张叔夜传》),或曰“山东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等等(45),今见除《赞》之外所有宋人关于宋江活动区域的记载,涉及不过“淮南”即“淮阳”、“京西”、“京东”即“山东”、“河北”即“河朔”、“齐、魏”、“青、齐、单、濮”、海州等地。这些称说中虽然都不直接涉及泰山或太行山,但综合其所构成之宋江活动的大范围,明显是汴京(今河南开封)周围偏重京东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实际的中心是京东的梁山泊,正是远不及太行山,而与泰山为紧邻。
这尤其可以从《东都事略》与《宋史》同是记“(侯)蒙上书言”称宋江等,一作“横行河朔、京东”,一作“横行齐、魏”的不同而相通处看得出来。其中“河朔”与“京东”并列,可以认为是指河北路。“齐”即齐州,今山东济南,宋属京东路;“魏”即“安史之乱”前的魏州,后改置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入宋称大名府,后改北京,即今河北大名,宋属河北路。由此可知,“横行河朔、京东”,一作“横行齐、魏”的不同,实是前者以路一级范围称,后者以府一级范围称,其相通处在其所指具体都为宋河北路毗连京东路之今河北大名与济南东西相望间梁山泊与泰山毗连一带地区。这一地区的重镇为郓州(治须城即今东平),而郓州于宣和元年(1119)升为东平府,所以才会有《宋史·侯蒙传》载蒙因上书言“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而被“命知东平府”之事(46)。否则,若以宋江“横行河朔”为在河北近太行山一带活动的话,朝廷还会命侯蒙“知东平府”吗?徽宗虽昏,亦不至如此。
第二,史载宋江事虽涉及“京西”与“河北”即“河朔”两路,因此不排除宋江等偶尔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但并不能得出宋江“这卅六人的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的结论。按宋之“京西”、“河北”两路各地域甚广,不便一说到“京西”、“河北”就一定是到了太行山。按《宋史·地理志》载:“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东暨汝、颍,西被陕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又载:“河北路,盖《(禹贡》兖、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兖为多……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岱,西压上党。”这两路属今河南、河北、山西的部分地方如上党(今山西长治)近太行山或在太行山,但这些地方分别为宋京西之北界、河北之西界,而上引“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人海州界”等涉及京西、河北的记载中,其征战运动的路向,一致是京东、沭阳、楚海州界等偏于汴京东南之京东东路、淮南东路一带去处。这一路向,倘非有意作大宽转至京西路北界和河北路西界的太行山,然后折回以去京东等地,那么其绕行京西、河北两路的取道,一般说应是京西、河北两路近汴京之地,便于去京东以至沭阳、楚海州的地方。这条以汴京为向心点绕行的路线,在京西、河北境内,总体上为背太行山而趋向于京东梁山泊,而后归于淮南东路的海州。这一条路线,如果说其上半段自淮阳绕京西以至河北的部分言,尚不排除偶尔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但也绝不会到可以称“太行好汉,三十有六”的地步,那么其下半段自河北走京东入淮南的部分,不仅与太行山为渐行渐远,而且中经八百里梁山泊,主要是水道,即如余嘉锡先生所说:“江所以能驰骋十郡,纵横于京东、河北、淮南之间者,以梁山泊水路可通故也。”(47)更是完全没有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从而《赞》中五称之“太行”,必非太行山。又自古举事者,胜则攻城入据,败则退保山林,宋江这支队伍的流动性与战斗力极强,其且战且行,既“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所向无敌,也就没有在京西、河北遁入无可“掠”之太行山的必要,从而以《赞》之“太行”为太行山,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第三,《赞》中所透露地理特色亦与太行山不合,而更合于别称“太行山”的泰山。按《赞》中既称“太行好汉,三十有六”,则诸赞中涉及地域的用语,除如上引“清源”、“玉关”等仅关乎个别人物来历始末者之外,其他都应该与“太行”有关。倘以“太行”为太行山,而太行山虽临黄河,却在河之中上游并无水域广大的湖泊,那么《赞》中如“出没太行,茫无涯岸”所凭之湖山相倚之态,和相应写有“伙儿”、“火伴”等水上英雄的内容便无所着落。而京东“八百里梁山泊”东与泰山毗连一带,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水陆两栖作战的大舞台。孙述宇先生因于余嘉锡等人的考证,仅执于“靖康”之后“太行忠义”活动的史实对水浒故事的影响,而不顾《赞》辞隐写有水上英雄与广大水域的事实,所做《赞》中所说是一个“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的“山林故事”(48)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四,从元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对《赞》辞的理解看,此“太行”也不会是太行山,而是泰山。陆诗一面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论云:“友仁诗作于有元中叶,去宋亡未远,典籍具在,故老犹存,故所言与史传正合。”(49)确有诗史的价值;另一面陆诗就《赞》而作,也是理解《赞》之内容的可靠参考。而正是这首诗称“京东宋江”,而无一言及于《赞》中五出之“太行”,反而若为《赞》中写有水域和“出没太行,茫无涯岸”之说作注似的,明确写出了“宋江三十六”活动过的地域有“梁山泊”、“石碣村”(50)。这使我们一面不能不认为,陆友仁是以《赞》所五称之“太行”并非太行山,宋江等活动的中心是“京东”毗邻泰山的梁山泊;另一面推测他也许还知道此“太行”为泰山避讳之不甚流行的别称,不便承《赞》之五称以“太行”言宋江事,遂舍“太行”而仅言“梁山泊”、“石碣村”。
第五,从《水浒传》的描写看,其作者或写定者也以《赞》之“太行”为隐指泰山。《水浒传》虽作年颇有争议,但其写宋江三十六人与《赞》中所记多相一致,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后者的承衍。从而《水浒传》对宋江三十六人形象的处理,可以看作对《赞》辞记叙的理解。以此而论,《赞》称戴宗云:“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但《水浒传》写戴宗并未著明为山东人进而泰安人,却最后到泰山归神。倘若《水浒传》的作者以为《赞》之“太行”为太行山,则不难写他去彼终老,却一定把《赞》中戴宗所不“敢离”之“太行”写作泰山,这在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的情况之下,应是表明《水浒传》作者知道而且认可此“太行”实为泰山之别称,从而在写及戴宗归神这一不同于《赞》之写“群盗之靡”的褒扬性情节时,能断然不用《赞》中容易引起误会的别称“太行”,而直书揭明为泰山了。
综上所论,我们宁肯相信《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完全不及“太行山”的记载,相信陆友仁诗与《水浒传》以不同形式所表达对《赞》之内容的诠释,而决不应该只据诗体的《赞》辞字面所显示内容上亦不无自相矛盾的说法,相信其所谓“太行”是太行山并进而想入非非;反而是从乱中有序的历史记载和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以及《赞》之并写山水的特点中深窥其所写“太行”,绝不会是“天下之脊”的太行山,而应当是毗邻梁山泊之别称“太行山”的东岳泰山。对《赞》中“太行”称名的这一揭蔽,将有利于澄清宋元如《宣和遗事》等小说戏曲中称“太行山梁山泊”等的读误。
五 《宣和遗事》等小说戏曲中的“太行山”
除上引陆友仁诗之外,宋元明文献中把宋江三十六人与梁山泊联系起来的小说戏曲,有宋或元佚名《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写晁盖、宋江等“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51);元末明初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杂剧中有云:“你怎不察知就里?这总是你家门贼。怎将蓼儿洼强猜做蓝桥驿?梁山泊权当做武陵溪?太行山错认做桃源内?”(52)把蓼儿洼、梁山泊与太行山并举;又晚明冯梦龙编著《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有“明日是济宁府界,过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与“前途太行梁山等处”(53)等语。此外,《水浒传》中虽无“太行山梁山泊”的称说,但百回本第十六回写黄泥冈的赋赞中仍有“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54)的句子,明确提及“太行山”。
以往有关如上表述的研究中,学者对“太行”、“太行山”与“梁山”、“梁山泊”之关系,或避而不谈,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马幼垣《〈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55);或以为“太行”为虚拟,如严敦易先生认为:“我们不必要去想象明万历以后,太行梁山连在一处,还有其特殊的解释,或济宁一带,真有另外一个太行的山名。太行和梁山并称,是传说故事中对于草莽英雄,特别是抗金义军的一种概括,太行梁山混用,是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弄不清空间与地理上的距离间隔的艺术现实,太行梁山,都是一种象征。”(56)或认为是叙事中的地理错误,如何心说:“太行山在东京之西,梁山泊在东京之东,把两处地方牵扯在一起,这是《宣和遗事》编者的粗疏”(57);或以为虽非地理错误,但当别解,如王利器把“太行山梁山泊”断句作“太行山、梁山泊”,进而认为《遗事》中“同往”、“前往”云云的两句话,表明“《水浒》故事有太行山、梁山泊两个系统的本子”,这两个本子“一经传开,后人便以太行山、梁山泊相提并论”(58)。
如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太行山梁山泊”之称,其“太行山”、“梁山泊”在宋一属京西,一属京东,绝不可能连属称同一区域。对此,除余嘉锡先生等持阙疑的态度可以不论之外,严敦易先生的解释虽在小说美学上是说得通的,但出发点却是“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第二回)。至于王利器先生由此生出“太行山系统本”的推想,当是由于不敢相信“太行山梁山泊”间为连属关系而不可以点断,又在点断作两处地方以后,还忽略小说中“明日是济宁府界上,过了府去”,不当先到“太行山”而后到“梁山泊”,从而失去了发现自己读误的可能。又何心先生以为“编者的粗疏”,虽常识常情,但也应该知道《遗事》虽为野史,其有关晁盖、宋江故事一节叙事,却并无多明显地理错误。所以,这个问题并不能至诸先生之说而了断,还有必要寻求“特殊的解释”。
于是上论泰山别称“太行”即“太行山”成为释此百年疑惑的关键。因为除了常识可知的比较太行山,别称“太行山”之泰山才真正与八百里梁山水泊为山水相连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上实已论及,宋人文献载宋江活动区域中,已包括了泰山一带。余嘉锡论《泊宅编》言“京东盗宋江出青、齐、单、濮间”说:
青、齐、单、濮皆京东路滨梁山泊之地也。元陆友仁诗云:“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不曰河北,不曰淮南,并不曰郓城(小说言江为郓州郓城县人),而曰京东者,因梁山泊弥漫京东诸州郡,故举其根据地之所在以称之也。(59)
虽然余说也未及于泰山,但北宋泰山为齐州(后称济南府)南界,而地连梁山水泊,宋江等当年活动区域包括泰山,实可以意会得之。进而以泰山之别名称“太行山梁山泊”,实在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恰是小说家叙事可取之境。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遗事》作者等必是犯了东拉西扯的低级的地理知识错误,就应该相信“太行山梁山泊”之称“太行山”,实是用了泰山的一个不够广为人知的别名,所指乃泰山与梁山泊相连一大片地域。
至于《遗事》作者别称泰山为“太行山”而不直称泰山之故,除上论泰山避讳的原因之外,一方面还当由于其既写宋江等“落草为寇”,就不能不说他们有山寨凭依,就只好用了泰山的别称“太行山”并时或简称“太行”;另一方面太行山不仅与泰山一样自古“多盗”(60),还如泰山与梁山泊相连地域一样,是靖康之后抗金忠义军活动的两大主要区域之一,使二者确有严敦易先生所说“很悠久的精神联络”(61),实也有便于作者作此以“太行山”隐指泰山的安排。
关于《遗事》之“太行山”不是太行山,而是隐指泰山,从其叙事中也可窥见一斑。按《遗事》写“太行山”或与“梁山泊”缀为一体,故应与后者联系起来一并考察。而相关文字,除写杨志卖刀杀人被捕发配卫州的途中,李进义等“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和“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之外,其他有四处都作“梁山泊”。由此可见者有三:
一是杨志等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的“太行山”,也就是“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前往落草的“太行山梁山泊”的“太行山”,同是与“梁山泊”山水相倚的一座山。而由于“梁山泊”只在山东,所以此“太行山”不会是太行山;
二是《遗事》写得清楚:杨志卖刀杀人是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获罪刺配卫州(今河南汲县),途经汴京(今河南开封)。卫州虽近太行山,但杨志尚未至卫州,到了“黄河岸上”,就被孙立等杀公差救了。当时黄河流经汴京城北,这救了杨志的“黄河岸上”在汴京的郊区,北距卫州尚有约三百里。所以,孙述宇先生说“他的义兄弟孙立等在卫州黄河边上,把防送公差杀了……从卫州上太行山”(62),又注说“杨志等人上太行,是从太行山区边上的卫州去的”(63)云云是错误的。杨志等人是从流经汴京城北的黄河舟行而下,去了京东梁山泊毗邻的“太行山”,所以才有下文“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之说。由此也可见上列“太行山落草”与“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的一致性,在于其所谓“太行山”都不是太行山,而是近“梁山泊”的同一座山,为别称“太行山”的泰山;
三是进一步联系《遗事》此节写晁盖、宋江诸事,凡涉及地理,除郓州等之外,如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的地方是“南洛县”“五花营”也实有其地,即今河南濮阳南乐县五花村,南距郓城、梁山都在二百华里以内。倘以“太行山”为太行山,那么一位叙事在“五花营”这种小地名都准确(合理)无误的作者,会同时发生“太行山梁山泊”的所谓“粗疏”吗?此外,还如严敦易先生所论:“《宣和遗事》记宋江攻夺的州县,作‘淮扬、京西、河北三路’,独无京东,当因梁山泊本在京东之故;否则既在太行山,又何必再特提河北呢?”(64)种种迹象,可见其“太行山”必非太行山;而且从《遗事》中极少虚拟地名看,这“太行山”也不便遽以为仅是“一个象征”,而与八百里水泊相倚的泰山别称“太行山”,正可以备为“特殊的解释”。
《遗事》写晁、宋故事以“太行山”隐指泰山的秘密,从其写“太行山”、“太行山梁山泊”等同时写及泰山也可见端倪。按《遗事》写及泰山的文字,除九天玄女实为泰山神之外,还写了吴加亮向宋江说及晁盖“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又写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并“择日起行……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65)。如此等等,“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的“宋江三十六”受到的是“东岳保护之恩”,晁、宋曾先后率众朝拜的是泰山。倘以此“太行山梁山泊”之“太行山”为太行山,那么太行有北岳恒山,“东岳保护”岂非越俎代庖了吗?而且晁、宋等既在此“太行山梁山泊”,则太行山才是其最大保障,怎么可以不感恩太行山或北岳的保护,而“往朝东岳”呢?这些矛盾的唯一解释,就是以其“太行山”只是东岳泰山的一个别称,从而感恩“东岳”也就是感恩“太行山”。唯是《遗事》作者在他视为是正面描写涉及泰山时直写称“东岳”,视为是负面描写时则曲笔作“太行山”。后世刘景贤、冯梦龙等当因深悉此义,故能以不同方式袭用之。而今人一切有关“太行山梁山泊”为“编者的粗疏”或奇特解会,皆是因不明此“太行山”为泰山别称之故,而误入了歧途。
至于《水浒传》中只说梁山泊,仅一见“太行山”,当是由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订者虽知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但也知其流行未广,故从众之常识而有意避免牵合太行山以言梁山泊,并不见得就是为补《遗事》“粗疏”。否则,尽管其笔下要略加斟酌,但并不难“只说梁山泊,绝不提太行山”(66)的。
综上所考论,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自古就有“泰山”别称“太山”之说,而唐宋元明诸代又有“太行山”、“泰行山”之俗;另一方面“太行山”之“太行”又自古音训“泰行”或“泰杭”,后世或称“泰行山”。两山各称名多歧与交叉共名的现象,导致唐宋金元明长时期中主要是泰山别称“太行山”的混淆,并时或进入某些文献的应用。
二、泰山别称“太行山”在官书与正统诗文中较少,各类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中时见。一般说来,泰山被作为褒扬的对象或与这类对象相联系时,往往直写为“泰山”、“东岳”或“太山”等,而在说唱有修辞上的需要如《二郎宝卷》、《泰山宝卷》及《水浒传》之例中,和涉及“盗贼”等负面因素时如在《赞》、《遗事》、《残唐》等有关黄巢、宋江故事的作品中,往往因讳言泰山而代之以别称“太行”、“太行山”等。这时的“太行”、“太行山”等,不是太行山,而是东岳泰山。明乎此,则知以往学者于“太行”、“太行山梁山泊”等的判读及其推测中的所谓“太行好汉”的“山林故事”与“太行山系统本”,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三、泰山别称“太行山”只是一定范围的小传统。其始偶见于唐代小说,宋代及其以后文献中迤逦有较突出的表现,并形成一个演变的过程,即宋人史籍涉“盗”记载的讳言泰山——宋元杂著及小说戏曲涉“盗”描写的泰山别称“太行山”——元明《水浒传》的有意避言“太行山”。这同时是“梁山泊”在水浒故事中从无到有被突出为中心的过程。但至明代,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及其对说唱文学与小说的影响,仍不绝如缕。
本文以上就泰山别称“太行山”与若干小说戏曲之读误进行的讨论,虽已尽力搜罗辨析,但由于涉及面广,资料浩瀚,识浅力薄,诚不免管窥锥指,是非有所不公,诚盼专家学者赐教匡正。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索隐》曰:“常山于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常山即恒山,为太行山支脉。庄绰撰《鸡肋编》卷中录李邦直《韩太保墓表》云:“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国,号为天下脊。”
②《太平御览》卷三九《地部四·泰山》引《上党记》。《上党记》久佚,但裴骃《史记集解》等屡引此书,可知此书至晚出刘宋以前,而以泰山为“太行坂东头”说出更早。
③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五《白马篇》诗“手接太行猱”句,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三《杂曲歌辞三》录作“手接太山猱”;苏辙《栾城后集》卷三《颍川城东野老姓刘氏名正》诗“东朝太行款真君”句,蜀藩刻本作“东朝太山款真君”。两例异文均为“太行”与“太山”,疑似改易者认为“太行”即“太山”,所指均为泰山。
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七册,第2774页。
⑤《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玄宗……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天王。”
⑥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大正藏》本卷二二,清宣统元年江北刻经处本卷三六。
⑦王充《论衡》卷四《书虚篇》,《四部备要》本。
⑧查志隆《岱巅修建孔庙议》,见查志隆著,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⑨佚名撰《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张希舜、濮文起、高可、宋军主编《宝卷》初集(以下注简称《宝卷》初集)(1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588页。又,嘉靖壬戌为四十一年(1562),三十四年(1555)为乙卯,未知孰是。
⑩(12)(15)(16)(17)《宝卷》初集(13),第507—509页;第567—568页;第529页;第515页;第535页。
(11)(13)(14)佚名撰《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开山宝卷》,《宝卷》初集(14),第37页;第30页;第33页。
(18)据车锡伦先生赐寄电子文本,谨此致谢。
(19)(20)(21)(22)(23)(24)佚名撰《灵应泰山娘娘宝卷》,《宝卷》初集(13),第22页;第28页;第89页;第140页;第356页;第380页。
(25)西周生撰、黄肃秋校注《醒世姻缘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114页。
(26)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
(27)李之彦撰《东谷所见》,《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页。
(28)赵南星《笑赞》,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29)徐征、张月中、张圣洁、奚海主编《全元曲》第十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889页。
(30)《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4—755页。
(31)《宝卷》初集14,第171页。
(32)《旧唐书·僖宗本纪》,旧、新《唐书·黄巢传》。
(33)周郢《泰山通鉴》,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63页。
(34)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书稿,承作者寄示,特此致谢。
(35)罗贯中著、王述校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宝文堂书店1983年版,第11、74、75页。
(36)陈以仁《雁门关存孝打虎杂剧》,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2—563页。
(37)罗烨《新编醉翁谈录》,《新世纪万有文库》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8)唐仲冕编著、严承飞点校《岱览点校》,泰山学院编印,下册,第421—422页。
(39)《宋史》卷一○二《礼志》:“真宗封禅毕,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遣职方郎中沈维宗致告。又……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
(40)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150页。
(41)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42)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页。
(43)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95页。
(44)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45)本段以上引文皆转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46)参见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第4—5页。
(47)(49)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第33页。
(48)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第195页。
(50)顾嗣立《元诗选》三《庚集》陆友仁《杞菊轩稿·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
(51)《宣和遗事》,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03页。
(52)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四册,第1333页。
(53)冯梦龙编、许政扬校注《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66、668页。
(54)施耐庵、罗贯中著,李永祜点校《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55)马幼垣《〈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水浒二论》,三联书店2007年版。
(56)(61)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第44页;第45页。
(57)参见何心《水浒研究》,第386—387页。
(58)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耐雪堂集》,第67页。又,笔者虽然不同意王利器先生关于《水浒传》有一个“太行山系统本”之说,但赞同余嘉锡等先生关于《水浒传》可能吸纳化用了太行山抗金义军人物与故事的考论。
(59)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第91页。
(60)关于太行山多盗,参见《后汉书·鲍永子昱传》、《宋史·王仲宝传》;关于泰山多盗,除上引史载黄巢事之外,另参见《庄子·盗跖》,《三国志·魏书·凉茂传》,《金史》卷八○《斜卯阿里传》、卷八二《乌延胡里传》、卷一○一《承晖传》。
(62)(63)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第195页;第207页。
(64)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第44页。
(65)《宣和遗事》,第305—306页。
(66)何心《水浒研究》,第386—3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