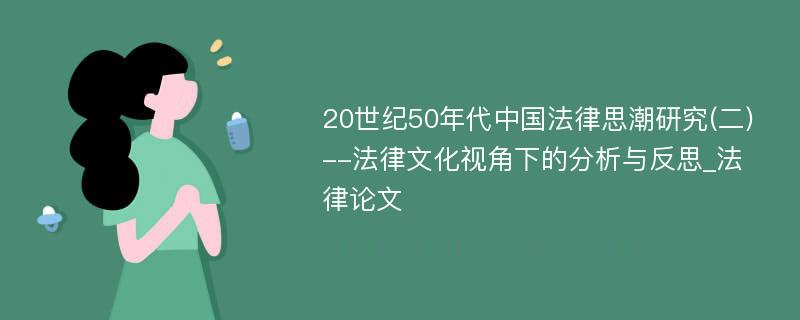
中国五十年代法律思潮研究(下)——法文化视角的剖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文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五十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50年代法律思潮的法文化透视
50年代的法律思潮固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但是,社会意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从这种意义上来看,50年代的法律思潮只是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片断,它必然带有传统法律文化所固有的某些特点。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在类似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法律思潮?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50年代之后,尽管社会现实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这股法律思潮却依然挥之不去?由此可见,对50年代的法律思潮必须追根溯源,从法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和思考。
(一)蔑视旧法的法文化根源
建国前的废除旧法活动和后来的司法改革运动,是对旧法制的最彻底的摧毁。为什么新生的人民政权能轻而易举地把旧法彻底摧毁?为什么民众会对旧法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从法文化视角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从来就缺乏对法律的信仰。
从传统上说,法律并非中国社会的主导性秩序模式。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是制定法,这种法律在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观念中只占相当次要的地位。按照儒家的看法,礼是治国的根本。孔子曾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注:《礼记·哀公问》。)法律是在“礼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制定的,是维护伦常秩序的消极的、最后的防线。“化民之道,礼教为先;礼教所不能化者,则施刑罚以济其穷,此法律所由设也。”(注:《浙江巡抚增韫奏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6页。)因此,在礼法关系上,礼是根本,法是手段。正如《唐律疏议》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注:《唐律疏议·名例》。)重礼轻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法律从根本上丧失权威。50年代彻底摧毁旧法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即在于此。当时,被摧毁的不仅仅是旧法体系,还包括法律的权威本身。不难想象,在一个有优良法制传统的国度,法律的权威是决不可能以行政手段毁于一旦的。
重礼轻法的文化传统反映在立法上就是引礼人法,礼法结合。这在《唐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唐律的制定与修撰,始终以儒家的纲常之礼作为指导。例如,《唐律》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皆“于礼以为出入”。以斗殴为例,一般“斗殴人者笞四十”。但“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诸殴祖父母父母者,斩。”(注:《唐律·斗讼律》。)由于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据亲等处以不同刑罚,这是礼所要求的。在引礼入法的过程中,礼不断被法律化,法也不断被道德化。由于礼和道德是用以别贵贱、序尊卑的,所以,引礼入法的结果是导致立法差等和司法特权的出现,这就使法律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品位,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正是受这种法文化传统的影响,在50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类最基本的法治原则才会受到批判。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法治应有的基本精神,并非《六法全书》所独有的“旧法观点”。相反地,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才是真正的“旧法观点”,因为它是封建法律制度所奉行的观点。
重礼轻法的文化传统还表现为法律领域的泛刑主义。按照儒家学说,礼和法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很明显,在孔子看来,较之与法,礼是一种更优越的统治方法。西汉的贾谊则提出:“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注:《汉书·贾谊传》。)就是说,礼侧重于教化,以防患于未然;而法侧重于罚恶,以惩戒于后。因此,“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注:《后汉书·陈宠传》。)对一切违反礼义的行为,都要运用刑罚方法来进行惩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法律广泛运用刑罚手段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泛刑主义。泛刑主义使民众长期生活于恶法高压之下,不可能奢望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久而久之,民众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并对法律产生了一种冷漠、对抗甚至仇视的心理。50年代盛行的蔑视旧法心理,无疑受到了“法即恶法”这种传统心态的影响。
(二)党法不分的法文化根源
建国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绝对领导权。因此,党法关系实际上就是权与法的关系。党法不分、以党代法的实质是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党的领导权为什么能够轻易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此,绝不能简单地从党自身的成长历史和5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来解释,而必须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剖析。
众所周知,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法律依附于国家权力,是维护权力的手杖。首先,法自君出,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在夏商周三代,法律皆由国王制定。《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注:《左传·昭公六年》。)这说明,当时的刑(也即法)被看作是国王针对乱政而制定的。在封建社会,皇帝总揽国家的立法权,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一切成文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除都必须由皇帝命令或允许,由皇帝钦定,并以皇帝名义公布。特别是在各朝各代的基本法律之外,皇帝还可以发布诏敕,作为追加法,这种立法不仅灵活性强,而且更能充分体现皇帝的意志。通过诏令,皇帝可以左右法律,也可以创制和取消法律。这就使得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的限制。历代的法典从来没有约束皇权的条款,直到晚清立宪,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其次,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在夏商周、国王掌握着司法的最后决定权。甲骨文记载的“贞,王闻惟辟”和“贞,王闻不为辟”,就证明了这一点。从秦至清,皇帝则成了最高的审判官,皇帝常常“廷殿决罚,朝堂杀人”,亲自审决案件而不受法律的约束。例如,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经常躬操文墨、亲断刑狱;宋太宗“常躬听断”;宋徽宗也经常以“御笔断罪”;明朝则流行廷杖制度,即在皇帝的决定和监督之下,于殿廷上对大臣直接执行杖刑。此外,各朝还流行“奏裁”制度,即对重大案件、贵族官僚犯罪案件或疑难案件,一般司法官均无权擅断,须先奏报皇帝裁决。对于特别重大案件,则由皇帝召集王公大臣或交朝廷命官讨论,最后由皇帝决断。
最后,贵族官僚阶层享有法定特权。不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或皇帝,其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各级官僚贵族也都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特权。这种情况,早在西周就已出现。据《周礼》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注:《周礼·秋官·小司寇》。)而由其子弟或下属代理。封建社会的法律更是公开维护等级特权,实行良贱异制,同罪不同罚。各级贵族官僚不仅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而且享有免纳赋税、免服徭役、传袭官爵、荫及亲属等法定特权。如若犯罪,则可以通过议、请、减、赎、官当等各种措施而减免刑罚。因此,封建法就是等级法、特权法。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法律只是权力的奴婢,始终受权力的支配。建国后,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种权力同古代王权、皇权及贵族特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党法关系问题上,权大于法的文化传统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50年代,在立法上往往照搬党的政策,有时,党的政策甚至未经正当立法程序就获得了法律效力。尽管这种“法自党出”和古代的“法自君出”本质不同,但二者都是“法自权出”。在司法上,党的政策甚至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指示取代法律而成为司法的依据,党政领导有权直接干预司法活动。这实际上是“无法司法”、“非法司法”,和古代司法专横、司法特权的文化传统显然有关。
(三)民主非法制化的法文化根源
50年代,在对待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是有惨痛的教训值得汲取的。当时,党和政府的初衷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但是,由于对民主本身及其运行规律缺乏认识,以致结果适得其反,公民的民主权利反而屡屡遭到严重践踏。产生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无疑和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密切相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2页。)从法文化角度看,50年代,党和政府从理智上对人民民主的重视是对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反叛;而实际上发生的人民民主权利备受践踏的事实,则又反映了专制传统对现实的顽固影响。
中国的专制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三代,便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国王垄断国家的一切最高权力,集最高的经济权、行政权、军事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小雅·北山》。),便是写照。而且,国王的权力还经天命神权的渲染而被神秘化。例如,《尚书》鼓吹王权天授,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注:《尚书·大禹谟》。)
到封建社会,则实行极端专制的皇帝集权,借助各种立法,皇权专制还逐渐被制度化、法律化。首先,以法律的形式,划分君臣名分,维护君尊臣卑的关系,严密防范非法逾制。以唐代为例,唐律明确规定,臣下的衣食住行必须遵照礼典政令,违者处以刑罚。臣下处理军、政、司法要务,凡依法应奏报者必须奏报,不得非分擅权。唐律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其次,严厉制裁侵犯皇权统治、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行为。犯者一律科以重罪,处以严刑。在“十恶”大罪中,直接涉及皇帝的就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四种。再次,法律明确确认皇帝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监察权等。
由于皇权至高无上,因而,民主的呼声微乎其微。在封建社会,虽然也有约束皇权的祖宗成法和宰相制度,但其实际作用却相当有限。所谓祖宗成法,就是前代君主立下一些规矩,要求后代皇帝不得违背。不过,这种祖宗成法只是开国皇帝自定的家规,并不能真正约束后来的皇帝。这不仅是因为没有承担约束皇帝任务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皇帝可以对祖宗成法进行补充、解释乃至部分否定。宰相制度,也是一种制约皇权的制度,自秦至明初,一直实行。汉、唐、宋各朝,皇权与相权是有划分的,宰相对皇权起着一定的制肘作用。例如,在唐代,皇帝颁发的政令须由宰相副署,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正式生效。然而,宰相的权力毕竟是皇帝给予的,宰相的人选又是由皇帝决定的,因此,宰相制度同样不能对皇权发挥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皇权越来越走向专制,宰相的权力不断被分割和削弱。至明代,朱元璋最终废除了宰相制度。
儒家是君主专制制度坚定的拥护者,他们竭力鼓吹人治,排斥法治,为皇帝集权提供理论依据。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名正言顺地制礼作乐,征战诛伐,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问题时,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注:《礼记·中庸》。)孔子虽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但他在论述君主与法制的关系时,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这一理论,经过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为了强调人治,宣扬君权神授理论,提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注:《孟子·梁惠王下》。),认为君主是天定的,其个人品质是维系天下存亡的纽带。荀子也认为,在治国过程中,决定治乱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他指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注:《荀子·君道》。)因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董仲舒为了论证“君主至上”的合理性,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鼓吹“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可见,无论是从法制层面来看,还是从观念层面来看,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都在于用法律维护专制集权,而与民主无缘。这是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症结所在。长期的专制传统,致使中国社会对民主和法治怀有一种本能的陌生感、排斥感。这种心态在50年代的法制建设中流露得相当明显。一方面,党的某些领导人在观念上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专制集权,不习惯按照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定处理问题,喜欢将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这种现象,尚未发育成熟的民主机制显然无力予以抵制。另一方面,长期生活于专制集权之下的社会民众,对于如何行使民主权利更是缺乏起码的认识,以致在实际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极容易走向极端,把民主演变成无政府主义。这不仅是对民主的破坏,而且进一步助长了人们不尊重民主的心理。
(四)司法非程序化的法文化根源
50年代的司法活动,不是由专门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诉讼程序来进行的。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司法组织极不健全;第二,处理案件不以法律为依据;第三,缺乏明确的诉讼程序。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法制发展水平有关,但同时也有其深刻的法文化根源。
首先,从传统上来说,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在奴隶制社会,国王掌握着最高的司法权,朝廷中设大理和司寇,辅佐国王处理案件;地方上则实行行政、司法不分。从秦至清,皇帝独揽司法大权,重要案件都得“取自上裁”。在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受行政机关控制。如秦汉时,廷尉的判决要由皇帝和丞相最后决断;唐朝的刑部对死刑案件须会同中书、门下二省更议;明清两朝,对重大案件实行九卿会审。在地方,则实行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北宋以前,地方行政长官掌管审判的决定权,通常由辅佐官代理折狱;从宋朝开始,地方行政长官亲自审理案件,行政和司法合而为一。可见,在司法体制上,行政干预司法由来已久。50年代,只有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司法机构。其他时期,司法组织都不健全,而且党政机关干预司法活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和行政干预司法的历史传统显然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传统的诉讼活动中,法律并非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主要标准。受儒家思想影响,封建社会的司法活动盛行“依礼决讼”。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十义”成为处理案件的首要标准,即所谓“分争辨讼,非礼不决”(注:《礼记·曲记》。)依礼决讼的突出表现,就是原心论罪,即审理案件时,注重作案人的动机,以动机作为判决其有罪与否及罪刑轻重的依据,“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盐铁论·刑德》。)依礼决讼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这实际上是公开抛弃法律而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准绳。不仅如此,儒家甚至还主张以众人的情绪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注:《论语·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引申道:“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侯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注:《孟子·梁惠王下》。)在50年代的司法活动中,往往牺牲法律以顾全政策,这和传统的“依礼决讼”、“屈法原礼”何其相似。同时,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时,往往以“民愤极大”作为定罪的理由,这和孟子所主张的“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简直如出一辙。
再次,传统的司法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立法一直极不发达,一些最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如司法独立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辩护制、陪审制、公开审判制、合议制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实行极端专横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可以依据或不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刑讯逼供,使用各种酷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凭个人的主观臆断定罪量刑。这种诉讼传统同样影响到50年代的司法活动,当时,非法逮捕、非法拘禁、非法拷问、非法审判、随意出入人罪等违背司法程序的做法在历次群众运动中都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