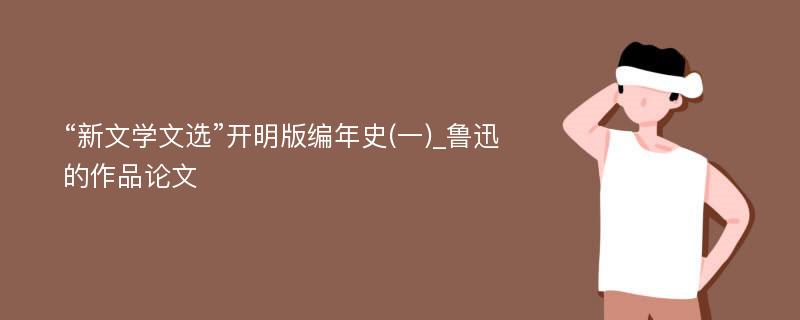
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新文学论文,选集论文,纪程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注:“新文学选集”出版广告,《进步青年》(原名《中学生》)1951年8月1日。)的“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套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由茅盾主编,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1951—1952年开明书店出版。“新文学选集”分为两辑,已故作家的选集为第一辑:原定出十二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王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计划也出十二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赵树理选集》。遗憾的是《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丛书除初版本外,还印有乙种本(即普及本)。
“新文学选集”设计考究: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健在作家的书名多由作家本人亲手题写,已故作家的书名均由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的郭沫若题写;扉页和封底衬页上的正中都印着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比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画像、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有的还附有小传。编选“新文学选集”时,编委会曾有一套长远的计划,准备在推出二十四位重要作家之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注:《〈新文学选集〉编辑凡例》。)1952年12月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任务有所更改。“新文学选集”出版了两辑二十二本后不得不告一个段落。
一、传播“新文学史知识”
开国伊始,读者热爱解放区作品,开明书店面临稿荒,经营颇为困难。此时,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开明书店股东胡愈之,萌发了编选“新文学选集”的念头。当时市面上正在热销“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开明书店要想寻找卖点,就得另辟蹊径,结合开明书店悠久的出版新文学作品的历史,胡愈之把目光转向了1942年以前的新文学作品,提议出版“新文学选集”,得到茅盾、叶圣陶、丁玲等人的呼应,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委会。
“新文学选集”的《编辑凡例》中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显而易见,“新文学选集”的拟想读者首先是青年,其编选目的是使青年读者可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新文学的发展,获得基本的认识。编委会又是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发展的过程”的呢?《编辑凡例》中有这样的描述:
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会被称为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会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编委会把“现实主义”命名为新文学主流,这是左翼文学界长期以来强化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结果。第一次文代会开幕那天,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讲话,他说:“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有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倾向,但是它的主流,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始终是同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相联系的。”这种把新文学主流与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相联系的思路在三十年代左翼理论家的文章中就有所凸显。但是,作为新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又是如何同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建立内在的联系呢?评价“新文学选集”的《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注:冷火:《新文学光辉的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1951年9月20日《文汇报》第4版。)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新文学选集”的意义,指出“新文学选集的本身,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纪程碑。而这纪程碑所昭示的大道,便是从旧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一条大道。我们今天得以明辨这条路向,就必须感谢死去的先烈和继续在努力工作的文艺作家。”至于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是否对应于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新的现实主义)有何区别,这正是当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新文学选集”既然是以丛书形式来确立新文学权威、排列作家队伍、形成新文学史的看法的,丛书的人选也就至关重要。从入选作家来看,“新文学选集”基本上兼顾到了1942年以前不同代际的作家群体。其中,鲁迅、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郭沫若、朱自清、许地山、王鲁彦、闻一多、洪深、田汉等人均在第一个十年登上文坛,除瞿秋白外,他们的作品均被选入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剩下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茅盾、丁玲、巴金、老舍、曹禺、蒋光慈、柔石、胡也频、殷夫、洪灵菲、艾青、张天翼等人,都在第二个十年开始展现创作才华的。用当年流行的观念来看,除叶圣陶、朱自清、许地山、闻一多、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外,其余的占入选人数近四分之三的都是左翼作家,“新文学选集”把众多的自由主义作家排斥在外,这昭示出编委会意图建构以左翼文学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史的设想。为了突出鲁迅与郭沫若高于其他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鲁迅与郭沫若入选作品的数量多于其他作家,《鲁迅选集》有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为上下两册,其他作家均各一册。
这套选集分为“健在者”与“已故者”两辑。健在作家中茅盾身份特殊(注: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1981年4月11日胡耀邦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人都是党员作家,占人选者的二分之一。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都比较亲近,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注:茅盾在《关于目前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中称十年来国统区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与“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注:冷火:《新文学光辉的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健在者”建国后都担任了领导职务,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而把“已故者”列为“第一辑”,这寄寓了编委会在享受建国的“大欢乐”时,对牺牲者的深切缅怀和纪念,意识形态的色彩浓重。
在已故作家中,鲁迅与瞿秋白为“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人都是革命作家。虽说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是,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号召“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注:《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新文学选集”编委会在《编辑凡例》中特别强调了要出版烈士作家的作品,并说这次只是初步编选了十二种,“二十余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收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新文学选集”突出已故作家的革命烈士身份,再次彰显了新文学史与革命史重叠的文学史观念。
二、编选方式的“组织化”
“新文学选集”编委会对于人选和选目都极为慎重。叶圣陶1950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说:
上午治杂事。午后两点半至文化部,雁冰邀开新文学选集之编辑会议。编委缺席者多,仅余与雁冰、杨晦、丁玲四人会谈而已。此选集选五四以来作者二十余人,老解放区(注:建国初期,把延安等地称为“老解放区”。)之作家不在其内,各选其文为一集,印行传世。余之一集,原定自选,余以不愿重览己文,请灿然代定之。今各册目录已大致交到,故开会商讨。即按诸目逐一检览,或略表意见,或无异议。决定再由编委分册重看一过,以示郑重。此书将交开明出版也。(注:《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
从叶圣陶日记来看,丛书最初的数目大致为“二十余本”,很有可能并不一定全是最终选定的二十四本。
“新文学选集”中,健在作家的作品一般由作家自己编选,也有请人代选的,如《叶圣陶选集》就由出版总署秘书长金灿然编选。已故作家的选集,编委会约请他人代为编选。编选者多为作者同时代人,与作者有过直接往来或更亲密的关系,对作者的创作和为人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比如,编选《洪灵菲选集》的孟超与洪灵菲同为太阳社成员,编选《胡也频选集》的是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对于编选者提交的作品选目,编委会反复讨论,认真把关。《鲁迅选集》的编选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拿它与四十年代由文协总会组织作家编选的“现代作家文丛”(注:1947年,为打击盗版书,捍卫作家利益,文协总会出面组织作家自选文集,1948年9月开始出版,这就是“现代作家文丛”,由梅林主编,上海春明书店出版,共12种。依次为《鲁迅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郁达夫文集》、《叶圣陶文集》、《巴金文集》、《老舍文集》、《丁玲文集》、《张天翼文集》、《雪峰文集》、《胡风文集》、《梅林文集》。)中的《鲁迅文集》作比较。《鲁迅文集》,选录了37篇小说和杂文。书局排好清样后请许广平撰写后记,许广平对选目颇为不满,在《后记》中说:
这本集子共收三十七篇,分四类:小说有《药》、《故乡》、《阿Q正传》,取自《呐喊》、《祝福》、《在酒楼上》则采自《彷徨》,而《奔月》、《非攻》、《老子》乃从《故事新编》所选。随感录有十篇,除末篇《文学和出汗》,原在《而已集》内,其余九篇都取自《热风》,演讲仅二篇,都是一九二七年的,也是从《而已集》选出来。杂文共十七篇,在这文集内占的分量比较多,那是无足为奇的,因为鲁迅先生写杂文实在不少,拿他的全部杂文比起来,反而觉得并不算多了。这里前六篇选自《南腔北调》集,后九篇取于《准风月谈》,末两篇则由《全集补遗》中选出。
文集取材的标准,我不大明白,因为是从书局排好清样之后才看到的。照时代说,从一九一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而对于鲁迅先生末年身临抗战前夜的暴风雨前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文章如《花边文学》及《且介亭杂文》所载,这里却一篇都没有。据我的推测:或者因为要力求平稳,周到,适合一般人的胃口,所以小说方面没有《狂人日记》及《伤逝》一类的透入骨髓的文章;而《故事新编》为鲁迅先生最卖力的得意之作《铸剑》宁可割爱,却选中了描写两位思想者墨子和老子的《非攻》与《出关》。虽然如此,就这薄薄一本中,从早期《热风》的随感录起,以及本书各篇的内容,还是不少针砭时俗的。那些杂文,更是丰富的罢了。所以还是不容易求其平稳,周到。这是什么缘故?我以为因为他毕生那分明的是非,包含在鲁迅整个的文章上,风格上,无法遮掩得住的。
“选集”的“选”字是有学问的。作家的自选集其实就是作家的自叙传,他人选编的选集往往就是他人为作家汇编的传记;而不同的选本,往往体现了选家对作家的不同理解,也为读者塑造了不同的作家形象。鲁迅本人是很注重选者“眼光”的,他在《“题未定”草(六)》里严厉地批判了那些破坏作者真相的选本,他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注:鲁迅:《“题未定”草(六)》,《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在许广平看来,鲁迅毕生都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作家,但“现代作家文丛”中的《鲁迅文集》想要给读者一个“周到、平稳”的鲁迅形象。1935—1936年的鲁迅把其杂文“针砭时俗”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可这样的杂文,《鲁迅文集》一篇也没有选,也没有选录小说《狂人日记》、《伤逝》和《铸剑》等“透入骨髓的文章”,这就“遮掩”了鲁迅的真相。
与“现代作家文丛”打出清样后,送请许广平过目的做法不同,“新文学选集”中的《鲁迅选集》的编选工作由许广平担任,选目由编委会与许广平反复协商确定,《鲁迅选集》(上)的《后记》附录的“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志”云:
关于鲁迅先生遗著的选本,编委会最初建议:在《鲁迅自选集》及秋白选辑的《鲁迅杂文选》而外,再加选鲁迅先生的后期杂文,并请许广平先生担任。编委会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广平先生的同意。后来,再有一次编委会会上,大家觉得《狂人日记》等四篇小说,有口皆碑,《鲁迅自选集》中虽未收入,而此次编选,似不应割爱。此议又征得许广平先生同意。现在就把这四篇排在《自选集》的最后,特此申明。
作为鲁迅的伴侣和同志,许广平对鲁迅有深刻的理解。鲁迅去世后,她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鲁迅遗稿,赢得了进步文艺界的钦佩。建国后,随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广为传播,鲁迅的声誉越来越高。1950年新中国专门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由冯雪峰主持,整理出版《鲁迅全集》,许广平也参与其中。“新文学选集”编委会要编选《鲁迅选集》,许广平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选本,茅盾、胡绳等人在四十年代末批判胡风等人“歪曲”鲁迅形象,理论依据之一就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编委会建议编选的《狂人日记》、《药》、《社戏》和《祝福》等四篇小说,也是“有口皆碑”的杰作。从“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志”中可以得知,编委会与许广平通力合作,对选目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推敲。
三、《田汉选集》和《瞿秋白选集》的缺席
1951年7月,“新文学选集”开始出版。最早的出版广告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进步青年》(第238期)上。随着出版的进度,《进步青年》、《语文学习》,甚至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封四上都有“新文学选集”的出版广告。所刊载的广告中,《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都标有“在排印中”的字样,这样的标示给人的感觉是选集已经编定了,正在“排印”。其实,《田汉选集》就没有编,或者说没有编成。1955年田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
当一九五○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以往的作品难以查寻,并不是“延搁”的理由。在“新文学选集”中,烈士遗作在收集方面最为困难,丁玲曾感叹收集到的殷夫作品仅限于二十六篇(注:丁玲:《序——读了殷夫同志的诗》,《殷夫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黄药眠也恳请蒋光慈的友好提供蒋光慈的材料(注:黄药眠:《蒋光慈小传》,《蒋光慈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可最终编选者经过多方努力,即便材料不那么齐全也还是出版了烈士选集。田汉的选集没能编出来,主要的还是他心怀“惶恐”,觉得以往的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拿不出去。以新的人民文艺为标准来衡量以往的作品,对旧作极度不满,这种心态在入选这套丛书的其他老作家那里也很普遍,他们也都在选集序言中表达了这种心情。
《瞿秋白选集》没能出版,也是有原因的。建国后《瞿秋白全集》纳入国家出版计划。1950年2月26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到他与杨之华见面的事, 杨之华说正在收集整理《瞿秋白全集》的材料,不久可以付排(注: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6页。),可见瞿秋白的材料收集是比较齐全的。为何没有出《瞿秋白选集》,有可能是在编选中遇到了困难。瞿秋白是文学家,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中,有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的话语。“新文学选集”的主编茅盾,以及其他编委在瞿秋白评价问题上当然是敏感的。1949年纪念瞿秋白逝世十四周年,茅盾撰写了《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一文,谈到瞿秋白对文艺批评上的贡献时,茅盾说:
他首先提出了“大众语”问题,发表了卓越的主张;他又不遗余力地抨击那非驴非马的“五四文腔”,给写一个嘉名:骡子文学。他对于“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的成就评价过低,当时朋友们中颇有几位不赞同他这意见。记得《学阀万岁》的初稿,有几个朋友就认为不能发表,退还了秋白;后来经过他自己稍稍修改,这才发表了出来(这些事发生在“左联”还存在的时期)。有一天,在某处遇到他,我就问他:难道你真正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的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的多了。
茅盾就瞿秋白对新文学的评价过低的观点作了解释,认为那是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接着又说:
二十年前,文艺理论上若干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结论,——那时候,一般的理论水平都不见得太高,所以,秋白在那时候的文艺评论在若干论点上有时不免有点偏向,我们正不必为他讳;但是,值得我们钦佩,而且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是他的决不固执己见的态度。(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五十年代为了确立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凸显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领导,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基本上都采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五四”新文化是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取得的,对“五四”以后的文学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文艺界领导者之一的茅盾怎能不郑重指出瞿秋白的“文艺评论在若干论点上”有“偏向”呢!1953—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瞿秋白文集》,冯雪峰在《序》中申述了同样的观点:“作者在个别论点上有偏向”(注:冯雪峰:《〈瞿秋白文集〉序》,《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因为《瞿秋白选集》涉及的问题太敏感了,即便茅盾、叶圣陶这些瞿秋白的挚友也不敢大意。八十年代出版《瞿秋白全集》时,出版署有明文规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过中央审批。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瞿秋白的作品也要经过相当层次的审批。或许是这些原因,使得《瞿秋白选集》没能及时编选出来。
四、赵树理的“越界”
“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作家才能入选“新文学选集”,而赵树理居然入选了。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他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写于1943年,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写于1945年,这两个作品在1949年就已经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了,1950年又重印了校阅本。除了《李有才板话》外,《赵树理选集》中的《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地板》、《打倒汉奸》等作品,也都发表在1943年之后。近年来,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洪子诚从经典化的角度给予解释,他在谈到编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编选“新文学选集”时说:“这反映了当时一种矛盾态度:即想将解放区文艺作为榜样加以标举,又对其思想艺术水准缺乏充足的信心。”(注:洪子诚:《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贺桂梅在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联系在1956年作协理事(扩大)大会上周扬把赵树理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称为“语言大师”一事,也认为新政权意图把赵树理经典化(注:贺桂梅著:《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这种阐释并不全面。
建国前后,赵树理的作品相当畅销。上海新知书店于1947年1 月出版《李家庄的变迁》时,把茅盾的《序〈李家庄的变迁〉》一文的手迹影印发表,以示隆重。当时解放区报纸报道了赵树理的作品在上海受欢迎的情况:“农村作家赵树理的名著《李家庄的变迁》最近将要在上海出版……赵氏另一名著《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寻找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在“新文学选集”中,只有《鲁迅选集》和《赵树理选集》印了10000册,其他选集的印刷从2000册到5000册不等。可见,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有满足读者市场的需求。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体现了编委会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的关系的解读。
建国初期,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出自感激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阅读解放区文学成了时尚,而冷落甚至误解了“五四”新文学作品。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等多种职务的丁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时代青年排斥“五四”新文学的错误观念,她在《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一文中说:
“五四”时代以及稍后一时的作家和作品,在我们还很熟悉,但对于很多青年就不大十分清楚了。有很多年轻的朋友知道高尔基、托尔斯泰、爱伦堡、西蒙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却不十分知道、甚至完全不知道中国除了鲁迅、郭沫若以外,还曾有过什么作家。也有许多年轻朋友觉得应学习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也有可以学习的东西。也有少数人有这种偏见,以为凡是由“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生长出来的作家,是要不得的,甚至拿这种话当作一种讽刺。(注:丁玲:《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
丁玲这样说,是有感而发的。当时,她还是专门培养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主任。1951年1月至4月中央文学研究所为学员开设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课程,由李何林、蔡仪等人讲授,课程分为:“五四前后”、“左联时期”、“江西革命根据地文艺”、“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五个部分。为配合讲“史”,要求学员阅读“五四”以来的主要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丁玲等人的代表作。开始时学员对“五四”新文学充满“误解”,甚至把“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对立起来,《文艺报》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说:
个别同志,对“五四”文学采取否定的态度,以为这一阶段文学运动是错误的。也有个别同志,盲目地认为“五四”新文学是胡适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有的则错误地认为“五四”前后一些作家与作品,大多没有什么内容,不过多少有点技巧罢了。有人还认为连技巧也没有。这些同志自己不仅从来不学这些东西,甚至一见别人看“五四”新文学作品,就武断地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感情”。有的则以为“五四”新文学,只出了个鲁迅。另外,还有人认为:“我不是搞理论的,学文学史干什么!”或者认为要学,可以只要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作品就行了,而真正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较有正确认识、较重视学习这段文学史的,只是少数。因此,很多同志开始不怎么重视这一段学习。(注:记者:《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学期学习情况与问题》,《文艺报》4卷7号,1951年7月25日。)
丁玲在《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一文中,也谈到了学员对学习“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不理解:
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学习新文学史中选了一些作品,作为对历史了解的材料,研究员(即学员——引者注)中就有个别的人提出问题:“这些作品能有思想性吗?有什么艺术性吗?对我们现在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可见这些作品是极不为人知道,也不被人喜欢知道。(注:丁玲:《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
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1月2日,学员来自各大行政区、各野战军,是一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写作潜力的青年(有的还是作家)。这些学员对“五四”新文学尚如此误解,社会上一般读者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针对以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为代表的年轻人对“五四”新文学的误解,丁玲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评,认为青年人对“五四”新文学的误解,“是由于不懂历史也不懂得怎样去学习历史”所造成的。指出:“那种否定‘五四’,否定‘五四’文学影响的看法,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偏见”,是一种“割断历史”的错误态度。她说:“少数人以为可以割断历史,可以不受历史影响而忽然跳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这就更纯洁更伟大。”在批评了从整体上否定“五四”新文学的错误倾向之后,她又对“五四”新文学进行辨析,告诉读者,“五四”文学中“一般所指的欧化太过,形式累赘、内容空虚的文体大体是后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文学作为消遣品时,才往那种趣味上发展的。”鲁迅作品中的“彻底的革命精神”,“反映了那时的革命思想,其深刻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至今也还没有为我们所达到。”意在提醒青年人在批判“五四”新文学中某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时,应该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传统”。
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丁玲批评青年读者对“五四”新文学的错误态度代表了文艺界的意向。茅盾、叶圣陶等其他文艺界领导人,对社会上一般年轻人对“五四”新文学的错误看法,也必然会有所警觉。“新文学选集”的编选本身,就是以政府行为来引导青年读者对“五四”新文学的重视和学习的。在编委会看来,1942年以后的解放区的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内在的联系,解放区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用丁玲的话来说:“后来的文学,是在‘五四’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注:丁玲:《怎样对待“五四”时代作品》,《中国青年报》1951年5月4日。)而“新文学选集”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成果。
也许有人会问:茅盾、叶圣陶和编委会其他成员在本时期为什么没能像丁玲那样对青年人轻视“五四”新文学的错误倾向进行尖锐批评呢?建国初期,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文艺界领导人各有各的重任,比如身为文化部部长的茅盾,要统筹安排全国的文艺工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忙于教科书编审工作,尤其是语文、政治课本刻不容缓。而丁玲对她管辖下的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进行批评,这正好是她的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更为重要的是“新文学选集”是用出版方式来确立文学史秩序,是靠作家作品说话的,编委会文学史意图的实现,人选极为重要,而且,通过人选的调整也更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的代表,他入选“新文学选集”,就体现了茅盾等人在文学史观念上的努力态势,旨在建立“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的内在联系,对建国前后那种把“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割裂开来的流行观点予以纠偏。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被界定为“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的情形下,“新文学选集”从另一个侧面作了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越界”意味深广。
五、序言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按照“新文学选集”的体例要求,选集前面有一篇导读性的序言。健在的作家均由自己撰写,叶圣陶虽请金灿然代选作品,序言仍是他自己写的。已故作家选集的序言,大多由选者撰写。健在作家在序言中回顾创作道路评价旧作时,大都对旧作进行不同程度的否定。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家认为“旧作”只具有“史料”价值,茅盾借编选工作来诚恳地“检查”以往创作的“失败的经验”,老舍很干脆地说:“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
“检讨”即认错,借用福柯的理论,就是对权力的“驯服”和“归顺”。“自我检讨”在当时是与“自我批评”联系在一起的。与“自我批评”相对应的另一个名词是“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建国后,为防止共产党人产生骄傲情绪,“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经常地有系统地监督我们的工作”,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50年4月19日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4月21日,各报纸刊载了这个决定,并按照要求检查各自的工作。《文艺报》在2卷5号(1950年5月25日出版)开设了“批评与检讨”专栏,据统计,从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赵树理、阿垅、张松声、张梦庚等30多位作家在《文艺报》上发表自我批评和检讨的文章。文艺界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从文学创作扩大到秧歌舞、年画、连环画以及电影的推广,戏剧、美术、音乐运动的展开和旧剧的改革等诸多方面。1951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思想改造运动,更进一步地加剧了文艺界自我检讨的风气。“新文学选集”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编辑出版的。选集的序言自然浸润并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时代风气,这在作家选集序言中就相应地表现为健在作家的“自我批评”和编者对已故作家的“批评”。
健在作家的“自我检讨”既是对“旧我”的告别,也是对“新我”的塑造。作为思想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通过自我检讨来表明文学观念的转换。到过解放区,并以《大堰河》、《吹号者》等作品闻名的诗人艾青,对他笔下的农民和士兵形象都很不满意,觉得他们“有些知识分子气质”、“意念化了”。而老舍则以他创作符合《讲话》精神而自豪。老舍强调自己“苦寒出身”,熟悉城市平民,他的选集中选录的《黑白李》、《上任》、《断魂枪》、《月牙儿》、《骆驼祥子》五个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城市平民。在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五十年代,老舍的这些表述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文艺新方向对作家的巨大的规范力量,非左翼作家只有竭力证明其作品中具有左翼文学和新中国文学所需要的品格,才能获得在新文学史上和新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除了在题材上的自我观照外,不同身份的作家还从“怎么写”上反省旧作,检讨旧作没有写出人物的“出路”。左翼作家中,茅盾对《蚀》的重新评价就是一个显证。1928年7月茅盾撰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注: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19卷10号,1928年10月18日。),对于钱杏邨在《幻灭》(注:钱杏邨:《幻灭》,《太阳月刊》第3号,1928年3月1日。) 和《动摇》(注:钱杏邨:《动摇》,《太阳月刊》第7号,1928年7月1日。)中对他没有表达“慷慨激昂”的调子、给人物一条“出路”的指责予以回应。茅盾反复强调《蚀》是自己情绪的真实流露,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他承认“《追求》的基调极端的悲观”,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并说这是他的性情所致,“我素来不善于痛哭流涕剑拔弩张的那一套志士气概。”同时,茅盾又认为产生这种“极端悲观的基调”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那个社会现实。而他在作品中之所以没有给人物一条“出路”,是由于“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已被证明这出路之差不多称为‘绝路’”,在此基础上,茅盾不赞成革命小说就必须要“积极的引导一些什么——姑且说是出路罢”的主张,也坚决反对那种以为他在小说中不写“出路”就表明了他在革命中“落伍”的说法。《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以后,招来了许多尖锐的批评,茅盾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撰写了《读〈倪焕之〉》(注: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8卷20号,1929年5月12日。)一文,再次重申小说中人物的“落伍”不等于著者“落伍”的观点。他说:“即使是无例外地只描写了些‘落伍’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品,也有它反面的积极性。这一类的黑暗的描写,在感人——或是指导,这一点上,恐怕要比那些超过真实的空想的乐观描写,要深刻得多罢!”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茅盾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化特点,强调作家的个性和对现实的忠实,在他看来真实地描写黑暗要比空想的乐观描写深刻得多。
1952年,茅盾在开明版《〈茅盾选集〉序言》中再次谈到《蚀》的情绪基调以及“出路”等问题时,以往那带有反讽的辩解却转换为彻底的检讨。他说:“《幻灭》等三部小说(一九二七年九月一十二月写作)是有若干生活经验作为基础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联系,因此,按理说,我应当有可能了解全面,有可能作比较深刻地分析。”但是由于没有看清“正确的方向”,故而悲观失望,“这是三部小说中没有出现肯定的正面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茅盾还说:“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面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摇,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可见茅盾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真实”,而是以“正确”来评价作品。要“正确”,不要“真实”,这也是后来许多作家阐释旧作和修改旧作的特点。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茅盾接受了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可以把福轲的“重要的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套用为“重要的是阐释旧作的年代”。五十年代,在文学中表现“出路”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二三十年代,“出路”成为革命文学的一个标准,后来又衍化为左翼文学批评对文学改造社会、组织革命的一个内在要求,人物是否有“出路”,暗含着对革命能否胜利以及人物要不要革命的判断。如果说,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对写出革命“出路”的提倡,出于鼓舞士气召唤人们投身革命的目的,其不切实际之处,被茅盾称为属于“空想的乐观描写”,带有幼稚盲动的弊病;那么,与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相对应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则标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追求的“出路”是正确的。因此,建国初期,坚信“出路”不仅意味着对共产党人准确把握历史走向的信服,还可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伟大、英明和正确,具有巩固新政权的意义。1951年底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要求作家具备抓住社会发展本质的敏锐,以带有理想性的写实,展示社会“图景”,引导和激励读者。在这种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部长,必须要率先调整文学观念,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阐释旧作中带头示范。
茅盾检查旧作没有写出“革命者”的胜利,老舍则检讨没有让人物参加“革命”。老舍特别强调其创作“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只是在写法上没有给人物找到“出路”。他说我“没给《月牙儿》中的女人,或《上任》中的英雄们,找到出路。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他表达了对《骆驼祥子》的不满意:“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
与老舍一样,曹禺也为没有写革命而检讨。《雷雨》在1933年发表后,曾被左翼文艺界误读为“社会问题剧”,序幕和尾声在排演中往往被删削,曹禺多次提出抗议。但是,在开明版序言中,曹禺却把他的剧作敲定为真正的社会问题剧。他说在创作时“确实要提出一些问题,说明一些道理。”与理想的社会问题剧相比,曹禺认为旧作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他们向敌人作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旧作存在着“片面”、“不深刻”以及“浅薄和过失”。健在的作家以“出路”来衡量旧作,并重新给以往的创作定位时,不仅表明不同文学样态不同文学力量向被文学史确立为主流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文学样态靠拢,而且说明到了新中国那些没有写出“革命”的文学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如果说健在作家的序言显示了作家的“自我批评”,已故作家的序言则充分发挥了“批评”的功能。已故作家中,除鲁迅和王鲁彦外,其余各位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序言作者看来,已故作家抛弃非现实主义因素的过程与作家成为战士(烈士)的道路是重合的。李广田在《〈闻一多选集〉序》中首先谈到闻一多早期思想的复杂性,认为闻一多既是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这一论断本身并不新鲜,李广田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唯美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思想在闻一多一生中的交会作了辩证分析,他把爱国主义思想放大到极致,把它作为贯穿闻一多一生主宰其行为方式的积极因素,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使闻一多从“诗境”转向“尘境”;与他走向现实相对应的是,其诗歌中关注和反映现实的内容日益增多,唯美主义成分在逐步消遁。写作《死水》时期的闻一多,由于对现实的反抗态度,比《红烛》时期向现实突进了一步,“诗的内容也就更充实了”。而走向现实,不仅使他了解到社会真相,心也和民众贴近到一起。“在两个多月的徒步迁昆长征中,他已经看到了人民的困苦,在朝夕与青年相处中,他又恢复了童心,由期待抗战胜利而等来了节节败退,更使人痛心的是等来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闻一多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整风文献》等书更帮助他懂得了,而且给了他思想以领导,他懂得了‘国家’的意义,他知道政治乃是阶级斗争。而且他认识了人民,认识了群众,知道了真理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认识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李广田高扬闻一多身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强调他对人民大众的依归,实际上是把闻一多塑造为追随共产党,参与革命进程,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的斗士形象。“艺术的忠臣”,终于成了人民的忠臣,李广田对闻一多爱国主义的赞扬,也就是对他追随共产党的赞扬。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鲁迅文集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论文; 李家庄的变迁论文; 许广平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茅盾论文; 文艺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丁玲论文; 赵树理论文; 叶圣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