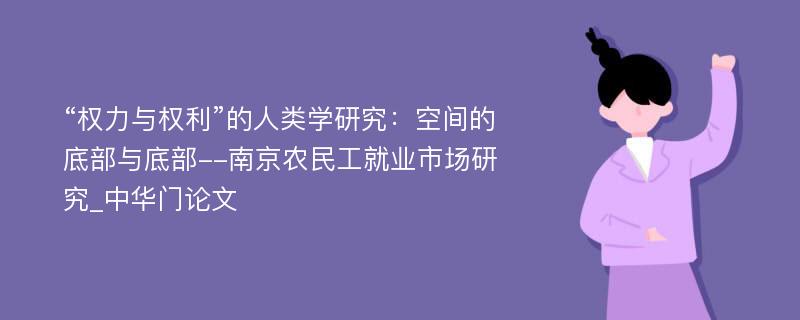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人类学笔谈——空间的底边与底边的空间——对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边论文,笔谈论文,人类学论文,空间论文,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空间关系关注农民工群体
时至20世纪末,空间关系在学术界对现代性的讨论中,逐渐变得同文化、政治和经济活动一样重要。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尤其在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考察中,我们也看到了空间的重要性。在对北京的浙江村的研究中,张鹂揭示了浙江移民里的精英如何将非正式的空间私有化,并逐渐产生权力的过程。[1]而Laurence J.C.Ma等学者则指出,地方认同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坐标,也是我们把握流动人口之地方身份认同的关键。[2]通过双方有意识地对工厂宿舍场所的控制与利用,任焰、潘毅展示了资本与劳动者双方强化各自的权力。对于住在工厂宿舍的工人来说,宿舍这种集体性的资源有助于工人向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3]一些学者把社会空间看作是规训农民工言语行为举止的场所的同时,也揭示出农民工如何巧妙地利用社会空间产生、强化、巩固获得的权利。[4](PP103-124)[5]
南京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简称“劳务市场”),属于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管辖。它是在政府部门的规划安置下,于2002年的6月在原来有色金属交易市场基础上改建而成。2004年初改制,成为一家实行市场化运作模式的私人企业。该劳务市场主要为来自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常年为工矿企业和城市居民提供熟练劳动力。截至2009年底,劳务市场驻场职介机构多达72家。这里的农民工来自五湖四海,最远的有来自云南、广西、内蒙、黑龙江等边远省份。他们长年在外面四处漂泊流浪、风餐露宿,饱经风霜的面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都要大10岁左右。2011年春节其间,仍然有大约三四百人待在劳务市场没有回老家过年。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他们无家可归,只能漂泊在外勉强度日。这里有小商人、酒鬼、小偷、性工作者、嫖客、乞丐、精神病患者以及同性恋者各色人等。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处在社会的底层,却同样受到来自主流社会权力的宰制与压迫,绝非“法礼之外”。[6](PP36-46)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从“底边”与“边缘”[7]的角度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中被家庭抛弃、社会排斥的最“底边”的部分。从空间维度对这一最边缘的群体的生存与劳作进行分析,能够展现他们那种处在城市边缘角落和社会空间底层的场景。以安德门民工就业市场为例,笔者认为劳务市场作为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第一站,不但自身遭受到了整治、搬迁等坎坷经历,而且直接充当了隔离性户籍制度的工具,锤炼、型塑、淘汰外来的农民工。然而,处于农民工群体中最“底边”的他们并不甘心一味屈从,在挑战这个空间秩序的同时,又将此挪用为生活、消费、娱乐的栖身空间。这是对权力宰制下的空间秩序的抗争,也是对城市公民权的排他性的挑战。
被驱赶的公民权
提起公民权,特纳(Bryan S.Turner)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在高度异质性的社会里成员的身份归属,二是在此基础上关注的资源之效率与平等之分配。他将公民权定义为,“各种实践的集合(司法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通过这些实践人们获得了成为社会成员的能力,并相应形塑了资源在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8](PP2-3)因此,公民权具有一定范围的排他性,“只有那些‘合法地’生活在一定界域之内者,才享有公民的权利。当然,在实际的操作中,一个国家之内的合法居住者未必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9]。正如本文即将展开讨论的农民工群体一样,居住在同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的中国农民,来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却因户口在农村而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等同的公民权。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粉墨登场,进城的农民出卖劳动力,身体成为可以流通的生产要素之一。然而中国的经济有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它借助户籍制度,将本国的人口分成城市和农村两大类,置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于不能之境,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围墙。城市的管理者利用户籍制度所授予的特权,将进城的外来者定义为农民工,使其排外的行为和逻辑获得合法性,农民工事实上成为了一种身份。因此这一主体的出现,可视为市场的力量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共谋的结果。[10](PP1-35;PP31-59)同样,与农民工进城务工关系紧密的劳务市场,同农民工群体类似,也遭受到了整治、搬迁等坎坷经历。当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时,自由农贸市场在城乡普遍复苏。一些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纷纷进城,并渐渐进入城市劳动服务市场,以满足城市居民建房、保姆、环卫的劳动力之缺。到80年代中后期,大批外来农民从城南的扫帚巷一带延伸至中华门东人行道,形成了曾名扬南京城的中华门劳务市场。中华门城堡,这样一个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爱国教育基地,为什么会衍生出所谓的劳务“黑市”呢?当地居民介绍,中华门处在南京内城的最南面,毗邻江宁县,临近安徽的马鞍山、芜湖等地。城南曾经是南京最贫穷的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比农村好不了多少,农村人觉得此处有点乡土的味道,就在那里待下了。
说它是“黑市”,是因为该市场完全是自发形成,并没有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的批准,而且劳资双方交易没有任何法律形式加以约束,以口头承诺约定为主。这为日后被取缔埋下了制度隐患。一些游手好闲者拉帮结派,混迹在中华门劳务市场内惹是生非。虽然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浙江村”,如同张鹂认为的那样,流动人口之帮派的出现是在一个缺乏政府保护的地方建立秩序和实施控制的一个可选途径。[1](P190)但牢骚满腹的附近居民与媒体一道,给城市的管理者施加舆论压力,为城市管理者整治并最终取缔劳务“黑市”提供了合理的说辞。从90年代末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黑市”进行集中整治。政府通过在城墙上贴通告、在城门附近用大喇叭播放等方式,每天不间断地宣传禁令。后来,当地政府发现仅靠宣传,效果甚微,反而越禁越火。于是成立了取缔领导小组,针对中华门劳务“黑市”采取行动。
从地方政府的取缔决心之坚定,我们体会到了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的:中国流动人口在城市争取公民权(citizenship)。她认为,当代中国管理者所牢牢控制的户籍制度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影响力,中国经济的转轨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样,促进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融入和对同等公民权的获得。因此,苏黛瑞对中国流动人口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的前景并不乐观。[11]在中国,由于城乡的分割管理,城市的管理者没有义务和责任为外来者提供就业服务和生活保障。当面对来自市民和媒体的舆论压力时,城市管理者动用户籍制度所赋予的特权,将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界定为不合法的“黑市”,并将外来者区分为暂住人员和“三无人员”,予以区别对待和处理。城市管理和公民权抗争的辩证关系在此被充分展示出来。从表面来看,当地政府对中华门劳务市场的整治和取缔,是对城市容貌的维护、对居民生活的保障、对社会治安的维稳,实质上却也伴随着对外来流动人口的驱赶、对农业户籍人口的清理、对非城市居民的公民权践踏。然而农民工并非一味屈从,而是借助这个空间来增强自身的权利。当整治的风暴袭来时,农民工们纷纷从内城分散到更远的郊区;当风声渐次消退时,便悄悄地又返回劳务市场。这种“潮汐”式的规律活动反映了他们对城市公民权的排外性提出了挑战。
经过几轮的整治和清理,城市管理者无奈地意识到,粗暴的驱赶和遣送并不能彻底有效地处理好中华门劳务“黑市”。况且,如此一味驱赶劳动力无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于是将“堵”的方式改为“疏导”的方式。2002年6月28日,经政府认可的劳务市场开市了。然而,该市场已经从南京“内城”的中华门,被边缘化至南京“外廓”的安德门。从中华门到安德门的迁移,不仅仅是为了内城开发拓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存在着一种空间权力——在权力宰制下的空间,存在着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的宰制。正如赛义德(Edward W.Said)在《东方学》中论证的那样,人们的各种身份是他人赋予的各种标签,进而被塑造、消解或操纵的意义和联想。[12]农民工的身份便是这一话语的最好诠释,它传达了农民工公民权被侵占、剥夺的社会信息。
对空间秩序的反抗
空间描述出了机制权力和支配力量实际的运动状态,正如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所言“空间是场所(地点)的实践”[10]。因此,空间性的存在便成了日常生活实践的特征。与德塞都相比,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列斐伏尔则更为大胆。他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13](P46)如果我们认可列斐伏尔所说的,那么对空间的型塑、改造和控制便弥漫着政治的和策略性的硝烟。空间的秩序实质上是社会秩序的实践和暴露,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等级差异。
当来到劳务市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旁边的治安值班室:醒目的警徽、白色蓝底的墙面,房顶带着一个昼夜闪烁的红蓝警灯。往里紧挨着的分别是保安值班室和民警办公室,门口站着头戴白色钢盔,身着“水泥灰”色服装的彪悍保安。城市景象本身就给他们造成一种惊恐不安和挣扎求生的压力。当面对这些带有符号象征性的警示建筑时,他们想到了什么呢?与新来者表现出一片茫然的反应不同,“老油条”认为,他们和中介是一伙儿的。安徽和县老王的经历或许会让我们明白个中奥秘。初来乍到的他,按照中介人员的介绍去了工地,但现场的工作情形与中介人员描述的大相径庭,而且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老王便放弃工作回到市场,并要求中介人员退还中介费。按照市场的规定,若是就业人员对所介绍的工作不满意,可以在24小时内无条件被退还中介费用。然而,中介人员却一反昨日热情的态度,责怪老王不会听话、理解有问题。隔壁的中介也来帮腔对付他。无奈之下,王先生要求见领导。市场办公室的人听了双方的陈述后,说农民工来到城市是打工的,而不是来城里享受,城里人需要像他一样的人提供服务的,而非相反;并教育他,好吃懒做的人不该来城市打工,应趁早回家……王先生觉得冤屈,与他们争吵了起来,却被随后赶来的保安和警察带进保安办公室“写检查”了。
在此,笔者无意讨论警察和保安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着重关注在GDP作为衡量地方领导最重要的政绩指标的背景下,权力、市场资本是如何联合起来一致压制农民工的抗争情绪。建立劳务市场,游散的民工集中起来,不仅被提供给外来资本挑选,还要受到劳务市场自身的挑选。虽然中国的农民工与早年欧洲的无地游民不同。早年欧洲的那些流浪者们被圈地运动制造出来,在饥饿的惩罚下,成群结队地进入工厂,被迫通过出卖劳动力而维持生活。而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经济状况难以满足农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他们只有主动出来打工才能实现人生中最伟大的两项事业——建房和结婚。进城打工,农民工与来源地分离,他们的劳动受到市场规律的调控——年轻力壮很受青睐,暂留城市。而对于一些“捣蛋分子”,劳务市场以扰乱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为名出面“摆平”,以确保劳动力在用工企业遵纪守法、卖力工作。上文提到经过“规训”之后的老王就是如此。
再往里走,便可以看到类似仓库的几处大开间,分别是职业介绍厅、招聘信息厅、验证发证厅等。大厅里的塑料质地的椅子早已被损坏,留下了一根根钢铁支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偶尔有几个民工支在上面酷似杂技演员似的小憩。水泥地面和四周的墙体上布满了燥痰留下的斑斑痕迹。整个大厅屋面使用蓝色彩涂钢板,安装简易且成本低廉。此种空间场景与坐落在闹市繁华区南京市人才市场相比天壤悬殊,呈现出城乡二元体制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自觉的排斥,强化了忽视农民工公民权的政治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市管理者提供了特定的场所供农民工应聘之用,但农民工却并不领情。他们认为,在外面直接与雇主商谈,可以保证用工要求与待遇信息的准确可靠,而且不用交纳中介费用。而在市场内,中介人员为了收取中介费,极力撮合劳资双方达成合作意向,给双方提供的信息不对称,致使民工有受骗的感觉,从而影响农民工对市场与中介的信任。因此,农民工纷纷从内部位移到外面的马路边等待雇佣。表面上看,这是对劳务市场及其中介人员的不信任,实际上却蕴涵着民工对城市管理者的权力逻辑与行为的藐视,也是对市场空间秩序的公然反抗。与其说国家权力将他们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摆在某个社会等级秩序的位置上,为的是能够更有效率地管理、控制、使用这些劳动力,毋宁说隐藏更深的目的在于干预农民工劳动力的供求法则,迫使其在资本的挑选下价值贬值。“里面骗人的,光要钱,没好活儿”。这种藐视和抗争并非天然存在,它是在陌生的城市中经历了种种挤压遭遇之后产生的。农民工并不甘心被安顿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愤而反击,从身体和空间上挑战这种安排。劳务市场空间秩序的内外颠倒,使得民工们在一定的权力空间中开辟了一片自主的天地,自行把握应聘行为的规则和节奏,掌控自己的打工命运。
抗争的空间
然而空间并非是社会互动的决定者,而仅仅是作为权宜的场景,并且空间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按照城市管理者的规划思路,劳务市场被定位成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应聘场所。然而笔者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劳务市场不仅仅是一家大型的民工就业市场,而且也作为农民工就餐、娱乐、睡觉的场所而被加以挪用,成为一个栖身之处。随着大门每天早晨的开启,劳务市场内外很快便充斥着找工作的农民工。白天,农民工主要在市场内外活动。每到吃饭时间,农民工们可以从那些来回穿梭的小贩儿那儿购买食品,既便宜又实惠。一位卖大饼的老板告诉笔者,他们就是农民工的烧饭师傅,这里的农民工不会为了吃饭而伤脑筋。一些农民工出来时间久了,头发胡子也长了,便直接在路边的移动剃头摊点上理发刮胡子,而且屡次提醒理发师傅要给他剃短一点。吃完喝饱,脸面也修理干净了,一些年老农民工便拉着二胡,唱着凄怨哀婉的《小寡妇上坟》,这是一种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小调,引起了很多来自淮河两岸农民工的共鸣。
农民工的住宿则在马路两边或在附近的高架桥底下。晚饭后,他们赶紧去高架桥下占“窝儿”,去晚了就没有地儿了。之所以许多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是因为高架桥的路面可以作为屋顶,旁边有砖墙围成的护栏,能避一些寒风和细雨。笔者曾问一位农民工为什么不住旅店,哪怕是便宜的。他说出来打工,也没赚到什么钱,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下。到了年终岁末,很多农民工全年下来挣不到几个工钱,更谈不上存钱,觉得回家没面子,还有一些农民工家庭矛盾剧烈或夫妻早已离异,无家可回,便将此处当成了家。除夕之夜,这些民工也跟城里人一样,兴高采烈地去澡堂洗澡,置办一点酒菜、燃放一些鞭炮,“来年图个吉利吧”。
显然,劳务市场不仅仅是个就业市场,它是一个属于苏贾(Edward W.Soja)的“第三空间”,是一个充满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空间。[14](PP67-104)蓓尔(Hooks Bell)运用第三空间的概念,着重分析了在反抗白人和男性霸权秩序行动中的黑人女性主体性建构过程。[15]与此相似的是,农民工作为户籍制度和资本共谋下出现、并在两者宰制下生存的群体,在反抗宏观权力体制和城市社会霸权的过程中,努力争取打破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二元对立,并试图抛弃压制与屈服、剥夺与失去、排斥与被排斥的空间,努力进入一个拒绝被摆弄成“他者”的抗争空间。农民工们不断地反思自身所处的空间:“除了市场,这里还是什么?”他们不断地拷问自己:“除了农民工,我们还是什么?”这样的转变导致的结果是,这里并非仅是一个远离市民、容纳农民工应聘的场所,而且实际上成为了农民工生活、娱乐、消费的空间,一个由他们决定自我和掌控自我的空间。这是对权力宰制下的空间秩序的抗争,也是对城市公民权的排他性的挑战。
结论与反思
波兰尼(Karl Polanyi)在谈及“市场与人”的时候指出,当英国的工业革命传到欧洲大陆时,工人阶级并非是由于失去土地,而是受到更高的工资和城市生活的诱惑才主动离开农庄移民城市,并与城市低层的中产阶级一道,取得了发展城市品位的机会。虽然他们的住房条件是恶劣的,酗酒和淫乱在下层劳动力中十分猖獗,但他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的地位下降,反而认为新的社会环境提升了自己的地位。[16](PP148-149)在当代中国,受到收入因素刺激的农民工如同欧洲大陆的移民一般,主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他们在城市受到的对待却与当年欧洲大陆的农村移民截然不同。作为非市民的农民工无论在就业权方面,还是在住房、医疗等日常生活方面均面临着种种困境。因为现行的户籍制度不只是一项针对农民工的隔离与控制制度,它还是一种面向城市居民的福利制度。[11]尽管如此,农民工还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不利的社会空间改造成有利于自己的生活、娱乐的栖息之地。
从劳务市场的诞生、演进到后来的搬迁,从对劳务市场空间秩序的反抗到对社会空间的挪用,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进城艰辛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为了生存而发挥能动性的一面。农民工以争取城市空间的控制权来争取公民权的行动,“虽然这种斗争还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它却表明:对社会空间的支配性的界定,永远都会遭遇挑战,总是会不断地改变”[17](P8)。“他们这样做,并相应地构建了没有正式公民权的生活意义时,也就改变了城市公民权的排他性。”[11](P264)难怪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声喊道空间是政治性的,是意识形态性的。[13](P46)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仅是在空间中将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组织起来生产剩余价值,而且也是对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个生产是一项政治安排、规划设计的过程,权力利用空间以保证对社会、人员、环境的隔离与控制。在国家权力、户籍制度和市场资本联合建构的空间里,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空间被挤压遏制,形成了既被置于合适的空间,又不在合适的空间的“在位与错位”[18](PP89-120)[5]。
当国人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沾沾自喜时,当今年的“民工荒”再度严峻地在各地出现时,当农民工离乡背井以艰辛劳动换来经济的繁荣却无法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时,我们不得不怀疑T.H.马歇尔(T·H·Marshall)所言的市场经济的兴起与一个国家国民的公民权的诞生有着线性的正相关关系。[19](PP3-60)正如苏黛瑞所言:“不论向上转向结构层面,还是向下求助于能动主体角度来看农民工作为市民融入城市的前景,实质上都是很悲观的。”[11](PP316-317)笔者希望,随着“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出台,农民工群体公正平等的公民权的春天能真正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