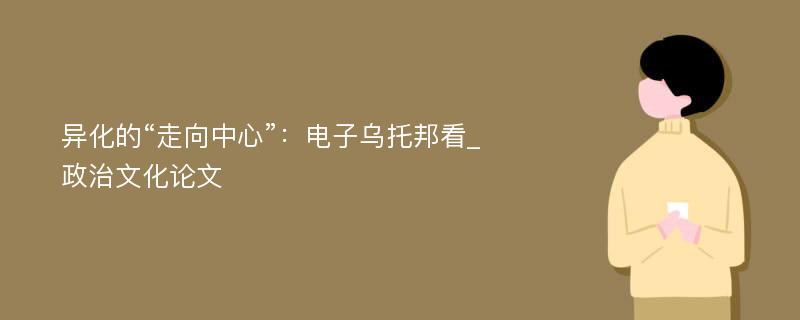
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电子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10-0120-07
一、电子乌托邦: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问题
网络已成为社会文化表征的一个重要场域。网络媒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去中心”的文化和政治、话语范式的遐想。在这种想象中,传统的话语霸权和集权似乎经受着平民化、平等、开放、强互动的话语力量的颠覆,网络媒介被赋予了强大的去中心、反权威和开放、平等的解放性文化力量。研究者们纷纷对新兴的网络文化进行欢呼,例如:“网络世界里是没有中心的,可以说在网络空间里人人都是中心,人人又都不是中心……”;①“网络所体现的开放性、非中心化、反权力以及反意识形态的特性是应当予以关注的。”②网络媒介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结构使得对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以及话语“狂欢”的憧憬愈加显明,而对文化霸权和中心化的社会文化控制则作出了乐观的判断,认为“在真实世界里,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威、经典、秩序、制度等,都在网络世界里被无限地淡化,在网络世界里,文化又一次地被昭示着辉煌,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成为广大网民盛大的狂欢。”③“网络文化具有无中心、无权威的文化精神,人们在网络中充分感受到了自由和平等。”④
从理论渊源来说,“游牧”、“碎片化”、形而上主体的消解等后现代主义图式,“主动的受众”等受众中心模式对传统的传播中心的冲击与瓦解,文化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思潮对话语权的下放诉求和对草根文化书写的抬升,以及对新兴媒介容易寄托的过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理想,都为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文化假设注入了充足的驱动。在此,需要对这种去中心化的“电子乌托邦”提出质疑。赛博文化并非一种去中心化的话语狂欢、文化撒播,也并非德勒兹、瓜塔里所谓的后现代“根茎”(Rhizome)式表征。有必要对这种媒介技术形式的神话进行祛魅,还原网络文化深层所潜藏的中心性和集中式符号话语权威。所谓网络文化对平等、开放、自由的“公民社会”和对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促生,所谓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权力中心的冲击,是面对新的媒介文化所容易产生的乐观误识。
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对网络文化的霸权性、负面性影响进行了审慎的评断,认为去中心化的网络也会带来和滋生种种中心化、专制和不平等。他们不无忧虑地指出,“毫无疑问,网络技术具有很高的民主、开放特质,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网络技术专制主义的一面……”⑤这类反思经常性的欠缺在于,对“去中心化”网络所带来的非去中心化后果的思考,尽管严肃地触及了种种集中和霸权后果,但并非在根本上质疑网络的“去中心化”这个前提。也即,认为网络本身是开放、民主、平等、去中心的,尽管它可能受到一系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依然产生集中化与非平等的景观。这也是对网络文化的负面性的外部思考而不是深入到内部反思的层面。具体研究中,常表现为对网络政治、网络社会有着充分的谨慎,而对网络文化本身则常局限于后现代主义式去中心化框架的乐观之中。对网络中文化政治霸权的负面反思,可以从以下角度梳理并审视它们的不足:
1.从网络技术本身来说,需要跳出“好的技术+坏的使用”之类的公式化辩证法,也即,在文化和话语权力问题上,网络本身也不一定是去中心的“好的技术”。研究者们貌似辩证地指出,网络信息过滤、网络数据库、电子监控、网站封锁等技术手段可能强化中心性的控制力量,加强马克·波斯特等人所谓的电子“全景监狱”等权力专制和霸权文化。例如,娄成武等说道,“互联网络的出现的确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使公民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络同时也为专制主义者提供了最好的技术实现方式……甚至成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者最有力的技术工具。”⑥然而,这种技术反思指向的仅仅是网络技术的负面因素以及对网络技术的负面使用——换言之,它通过把网络分为“双刃剑”的双重后果,从而以方法论层面回避和代替了网络本体论层面的质疑。
2.从网络主体和受众来说,不能只强调网络受众和文化主体、社会政治现实对去中心化和平等开放的网络的扭曲,而忽视网络自身对去中心性的“异化”。例如,研究者们看似忧虑地强调,平等的网民具有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和个体差异,自由民主的网络参与也可能带来网络暴力、网络暴政和“情绪型民主”、“群体极化”等种种非理性现象。然而,这是对网络文化政治后果的主体审思,依然不是指向网络技术本身的后果。当从网络民众之间的差异和特征来归置这种现实不平等性时,也要注意平等的网络构架自身所蕴含的理论不平等性。
3.从网络文化信息的监管和传播、操纵来说,网络的中心性和文化权力、非平等之类话语特征,不仅是种种负面操控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些负面操控得以实现的原因。研究者们看似深刻地意识到,网络中存在着信息霸权和技术帝国主义等话语权力,具有技术和文化优势的集团和阶层依然在网络中享有着中心霸权,居于信息传播和控制的中心位置的话语主导方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轰炸”、“信息伪造”、“信息规避”、议程设置、网络警察等手段来引控分散的民意,走向“意见气候”和监管的集中。这种视角尽管强调网络可能被各种政治、技术、社会、资本的力量和机制所操控,但是,它把网络操纵等反平等和反民主的后果看作是和社会体制等因素的缺失或不完善的网络发展程度有关,而不是深入到网络完善性表面之下的非完善性本真。当我们指责网络中的文化操纵、技术官僚统治、信息霸权、资本推手等所造成的社会文化“扭曲”时,应注意到:并非仅是前者造成网络的异化,而且网络本身是这些异化现象得以现实化的内部动因。
二、“去中心性”的异化:网络狂欢的文化权力集中
需要指出,网络文化在表层的去中心性下潜藏着深层的话语中心性,在表层的话语自由和狂欢下潜藏着深层的话语的不自由和不平衡,在其自身作为“公共领域”的属性中恰恰蕴藏着种种文化符号霸权。本文在此讨论的不是政治、社会、技术的外部不平等在网络中的映射和操控,而是网络自身如何在去中心性的表象基础上,导向中心化的异化后果。这里强调的是:网络文化并非像去中心性范式所表述的那样具有过于乌托邦式的平民化、反权威性质,它并不比马克·波斯特所谓的“第一媒介时代”的集中化、单向化媒介或其他各种宰制性的意识形态机器和话语霸权工具拥有更多的平等、开放、民主特质;相反,网络依然是一种中心化的媒介,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理想图景只是一种缺乏实际意义的理论承诺。网络文化中的中心与权威采取了不同于传统媒介文化与社会中的形式,然而这无损于它作为一种集中化媒介文化的社会政治本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话语的中心化表征恰恰是在其去中心化特征基础上的自我异化后果。
(一)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化与话语传播上的中心化
网络媒介所表征的“第二媒介时代”被认为具有不同于报纸、广播、电视等第一媒介时代的强互动性以及平民化的普遍性。正如马克·波斯特所阐述的,“当大众传播转换为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时,发送者变成接受者,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用来理解第一媒介时代的逻辑就被颠覆了。”⑦由此,有研究者指出,网络表达具有大众化的平等便利以及民主化和开放性的文化权力效果:“在网上,一切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什么权威,什么领导,或者是什么小人物,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网络使大众前所未有地走进了神圣不可进入的殿堂,曾经受到某种权威和清规戒律所压抑的声音得到了释放,过去的一种声音,在网络上成为了‘众生喧哗’……”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具有话语的表达权不等于具有话语的传播权,言说的权利不等于被听到的权利。话语权在本质上不是能否说话的生理、物理问题,而是话语之间关系的社会问题。所谓“只要有电脑,能上网,就能有发言权,进行参政议政,使网民在作为政治参与者时变得前所未有的积极与主动”⑨,这类乐观的观点虽然注意到了网络时代民众的表达权和表达能力的极大提升,却忽视了发言机会的平等不等于被倾听到的权利平等,因而也不等于事实上的话语平等。一方面,一种表达必须是在与其他表达的关系以及社会性的表达场域整体中,才能确立自身的话语效果与话语间性构型;另一方面,网络表达的便捷、讯息“把关”(Gatekeeping)门槛的降低所带来的信息爆炸与泛滥使得信息的被倾听与取得效果更加困难,使得网络表达的草根化带来反草根化的“异化”后果;此外,如拉斯洛·巴拉巴西所强调的,万维网的连接具有有向性或“适航性”的分隔结构,并不是每个页面都能平等地被链接和阅读到,即使是搜索引擎能覆盖的页面,也只是网络中很有限的一部分⑩,而大量页面仍只能隔绝在网络丛林的黑洞之中。如果说,传统媒介文化的中心话语权问题在于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具有话语表达的能力,话语权力的体现在于对电台、报纸等话语表达源的享有,那么,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是否具有表达权不再能成为衡量话语权的直接标杆。虽然网络中不再只有少数权力阶层或精英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大众并不藉此就获得了使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的能力。如果仅用大众发表网络言论的能力作为判断网络文化相对于此前的媒介文化的去中心性的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谓的“后视镜”视角:看到的只是过去。
大众的表达固然可以由“撒播”的非中心节点产生,但是终究要通过中心节点的放大效应,比如重点网站、重要意见领袖以及主流和权威媒体的转载和链接、评论等,才能取得话语上的聚焦与“承认”。正如喻国明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很多议题的首发论坛是市级及其以下论坛,但这些信息只有经过网络搬运工向主流论坛搬运后,被主流化才成为热点事件。”(11)2009年的多数网络热点事件都是经著名的论坛、版面如天涯社区、百度贴吧、twitter等渠道,甚至进一步得到主流纸媒或电媒的关注才得以聚焦。如王帅发帖举报政府违法征地、温州市官员低价购拆迁安置房等是通过天涯社区,贾君鹏事件、浙江杭州飙车者胡斌“替身”案是经由百度贴吧。罗彩霞维权事件开始在“邵阳红网”上并未引起足够大的关注,到天涯论坛发帖后才逐步引起重视,最后经由主流纸媒的介入而广为人知。而此事所折射的问题,正如网友评说的:“要说冤屈,要说苦大仇深,要说不公,比罗彩霞悲惨的多了去,为什么单单罗彩霞脱颖而出?”实际上,在罗彩霞维权案的背后,尚有千千万万的罗彩霞,他们并没有因为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就可以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与诉求,而是湮没在网络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由于信息爆炸与有限聚焦力之间的矛盾及其所带来的愈趋重要的信息权问题,网络的大众化和草根化表达,其异化后果之一,是大众的表达反而更趋艰微。
(二)信息渠道上的去中心化与信息传播上的中心化
毫无疑问,网络在分布的拓扑结构和信息渠道上具有鲜明的去中心性,由此人们对这种网络结构容易产生“脱控制化”的乐观。例如尼葛洛庞帝描绘道:“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12)因此,在网络信息的传播问题上,有一种乐观的论调是:每一个节点都可以与其他节点连通,“人们在网上皆可通过个人电脑自主发布各种信息,真正享受着过去难以实现的传播权”(13),因而传统的话语中心似乎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冲击,促进着平民社会兴起的曙光。然而,这种论调忽视了:信息传播物理结构上的去中心并不等于信息传播中的去中心;互联网在物理结构上固然是去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局部节点的效果固然难以真正影响网络的信息和数据传输,但不能因此而认为网络在信息传播上是去中心的。相反,这种去中心的信息渠道结构恰恰隐藏着中心节点的内在机理。
诚如巴拉巴西对无标度网络的研究中所指出,网络的中心性分布特征并非符合正态分布而是符合幂律分布,万维网的结构“被一些高度链接的节点(或称作中心节点)所主导。这类中心节点,如雅虎或亚马逊网站,都具有极高的可见性——不论我们到哪儿,都能见到指向这些节点的链接。”(14)正是这类中心节点使得整个网络呈现集聚而非平面化发散的“小世界”特征,为系统中任意两个页面或节点创造了链接的捷径。“和此类中心节点相比,万维网的其余部分是不可见的。实际上,只有一两个链接指向的文档几乎就等于不存在。他人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的网页,即便是搜索引擎对这样的网页也心存偏见。”(15)中心节点影响着整个网络的信息传输结构,对整个网络系统的联通性和稳健度具有重要作用,邓肯·加莱维、马克·纽曼等人的分析显示,少数中心节点的删除到达一个临界值后就会导致网络的瘫痪。这种高连接度和整合性的中心节点为“宏大叙事”的存在提供了技术意义上的网络模型基础,使得各种“小叙事”、“小传统”或分散的表达成为被分隔的话语沉寂和文化冗余,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网络文化中心节点的集聚性与拓扑稳态。此外,受注意力经济逻辑的影响,中心节点通过自我移制和链接以及“马太效应”,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对非中心具有强大的挤兑和屏蔽力量。节点信息内容对受众的呈显,尤其是大范围、长距、持久的呈显,更需要经由有效的中心节点的链接和文本间性的指向。通过对2009年重要网络事件与网络舆论的回顾,可以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经过了高点击量、覆盖面与阅读面的重点网站、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平台的信息集聚、中转与链接。(16)次中心、非中心节点与言说信息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到达大多数受众终端,但如果它不经由中心节点的再呈现,在实际上则会影响微弱并迅速湮灭。
网络文化中的去中心只是一种拓扑模型上的去中心,它甚至不能等于理论上的去中心,更不能等于实际网络中的去中心。在霸权构型未改变的情况下,谈论这种拓扑模型的文化解放力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四通八达的超文本、超链接和受众终端不仅并不改变着中心和非中心节点的区分,而且恰恰由这种散布式和开放性而生成并凸显着中心节点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也在反方面昭示着,通过对重点网站、服务器等集聚中心的监督、过滤和管理,对漫无中心乃至匿名化、草根化网络话语的强监管存在着的理论根基。它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到技术官僚、技术统治的“器”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涉及到文化霸权与符号权力的“道”的本体论问题。
(三)传统威权中心的弱化与中心方式的转变
不少人在当前依然不假思索地套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宣称:“所谓‘去中心化’指的是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它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指挥机构,……‘去中心化’导致现实中的等级制度瓦解……”(17);“因特网赋予了人们平等地传播与表达思想的权利,使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特网为全球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受外在的霸权政治、经济利益控制的交互式讨论的公共领域。……这对社会主流文化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18)然而,这类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网络文化及其公共领域并非不受传统的居于话语和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文化霸权力量的宰制。网络表达的“草根化”虽然改变了传统媒介文化中少数权力阶层控制表达媒介的状况,对先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工业”和话语霸权构成了一定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心权力的消褪以及民众话语的狂欢。
近年来,“躲猫猫”、“跨省追捕”、周久耕案等诸多网络事件与网络舆论中,普通网民与草根个体言论似乎取得了比以往更大的主动权与影响力。但是,它们所表现的,与其说是民间话语缘于网络的东风而取得对传统官方权威的挑战和颠覆能力,不如说是传统中心权威借助网络的东风而对自身的调整以及对民众权更多的尊重和承认。主体媒体的积极介入而不是消声态度对这些网言网情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跨省追捕”事件中,王帅得到了人民网的多次在线访谈,最终促使地方政府改变强硬态度而向王帅作出道歉和赔偿;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介入,它们大大提升了当事人的网帖的社会反响,促进了地方政府对错误的及时承认和修正。从反面说,主流权威同样也可以对这些民众话语采取拒绝和消声等传统媒体体制中的强控制,这种强大的治网能力在新近对网络不文明内容的有效整治、对谷歌的清理等都得到了较好表现。即使在官方未直接介入的公共场域中,草根也并未就此取得话语的狂欢,一方面他们需要经过种种具有广覆盖性与高点击量的具有强大文化资本的网络平台,以免自身迅速归于网络黑洞中的湮寂;另一方面,连结传统现实世界与网络意见市场的各种精英言论、意见领袖也在表面平等的网络话语体系中生成着不平等的话语权。据曾俊对2009年初新浪博客的统计,点击排名前100的博客中,演艺明星有31个,包括记者、主持人、体育解说员等在内的媒体人有20个,专家学者和作家有25个,企业家有8个,体现了传统精英在网络中发表的观点同样具有强舆论影响力,而排行前100的草根博客只有12个,并且在前20的只有2个,处于明显的话语弱势。(19)此外,“网络推手”、“网络黑社会”、网络公关的兴起也表现了网络的自由走向了不自由和话语权力的异化:在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平等网络世界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的威权构型。这正如资本的平等交换的逻辑,生成的却是不平等剥削的异化逻辑。
因此,大众能平等地发言并不意味着削弱权威的力量。网络中的传统威权方式并非消失而只是发生了转变与新的构型,从直接的政治权力逻辑转变到信息权力逻辑,从路易·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逻辑到“注意力经济”逻辑,从信息控制的“把关人”(Gatekeeper)过滤模式到信息中心节点的集聚模式。不能把信息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简单地等同于其地位的平等与去中心性。各种中心节点、重点网站、意见领袖平台依然是网络中信息传播和集聚、接收的信息聚焦,网络中的集中形式会发生变化,但这种集中本身并不会削弱。对于传统媒体的独语控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失效,但它们依然可以通过适应网络中新的话语中心的载体而重新实现其话语宰制。毋宁说,网络时代如果表现出某些话语权力的式微,那只是因为它从传统威权转移到新的威权方式和话语间性构成;如果表现出某种集中度的削减,那只是因为它的集中方式发生了型变。
三、结语:网络时代的文化权力悖论
本文认为,对网络时代文化权力的反思,在观照网络文化的特征时,放弃对后现代主义的轻率套用,而正视网络本身的集中与权力型构;避免停留于“主动的受众”、受众本位论等表层乐观,而切入这种平等背后的话语权差别;打破对网络文化政治的平等、开放与草根化的乌托邦幻想,而正视其自我异化走向的权威与中心化;尤其是,超越对于网络文化的外部反思而深入到其内部反思的层面,认识到网络本身的集权与中心化诉求,而不是仅把它归之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操纵。这些错误思潮在当前对网络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而通过对网络文化去中心性的再审视,有助于我们对此加强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必须更彻底地认识到,网络媒介生态在根本上并没有比其他媒介更为去中心化的文化和政治属性,政治和权力并非机械地对应于技术形式,而是会根据技术作出自我调适,更为根本的始终是政治和权力形式问题而不是技术形式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文化的去中心性在很多情境下恰恰成为向集中性的自我异化。这种异化指的是网络本身的开放、平等逻辑中所生成的非平等与集中霸权,它意指的,与其说是权力的网络化不如说是网络的权力性。话语表达上的去中心性并未改变话语传播上的中心性,讯息“把关”门槛的降低与大众化的表达时代使得脱离了中心节点、话语中心的表达在使得自身被倾听到、取得传播效果上更加艰难,使草根化的表达带来反草根化的自我异化。网络分布和传输渠道结构的去中心性并未改变信息传播的中心化,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散布式的信息网络结构内生成着中心节点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传统话语中心权威的弱化并不意味着话语中心的消解,而只是意味着它的转移和方式转变。因此,所谓网络文化权力的去中心性是一种表面的虚像,是通过传统媒体的“后视镜”视角所看到的片面浅征。对网络文化权力应有新的审视方式,而不是仅立足于它与传统媒介话语的简单比较,就轻率地得出其后现代特征的结论。
辨析网络文化权力的意义之一,是使得对网络中强监管、强控制性等负面的政治、文化后果的批判,具有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本体论基础;更多地深入自由、平等、去中心化导致中心化的内在悖论,而非仅停留于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揭批。所谓网络舆论不可控、不可堵的自由民主政治遐想只是一种电子乌托邦,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可以不再是直接控制其生成与表达,而是通过中心节点、话语权场域来控制其传播与流转。这也要求反对对媒介技术形式的文化解放力量的过分演绎,诚如卡伦所批评的:“文人的世界总是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论调,渴望用技术手段来把那些棘手的问题统统解决。”(20)斯皮瓦克曾提问道:“底层(Subaltern)能说话吗?”(21)对于网络中的“底层”而言,由于表达不等于传播,传播不等于效果,话语不等于话语间性,因此他能说话并不真正意味着能说话。网络场域不断生成着表层的“碎片化”、“狂欢化”向深层的话语和霸权集中的异化,以及两者之间的文化权力悖论。
注释:
①田科瑞:《网络时代的民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②袁峰、顾铮铮、孙钰:《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③王文宏:《网络文化对权威意识的挑战》,《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④邵思源:《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网络文化》,《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⑤⑥娄成武、张雷:《质疑网络民主的现实性》,《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⑦【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⑧王文宏:《网络文化对权威意识的挑战》,《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⑨毛旻铮、李海涛:《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网络话语权》,《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⑩Steve Lawrence and C.Lee Giles,"Searching the World Wide Web",Science,Vol.280,1998,pp.98 - 100; Steve Lawrence and C.Lee Giles,"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on the Web",Nature,Vol.400,1999,pp.107 - 109.
(11)喻国明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1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
(13)秦志希、葛丰、吴洪霞:《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性》,《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4)(15)【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69页。
(16)参见喻国明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0)》,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杜骏飞主编《沸腾的冰点: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7)刘燕:《媒介认同论: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互动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18)袁峰、顾铮铮、孙钰:《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网络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效应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9)曾俊:《精英与草根之辩:博客世界中话语权的严重失衡——对新浪博客的分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20)【英】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21)【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