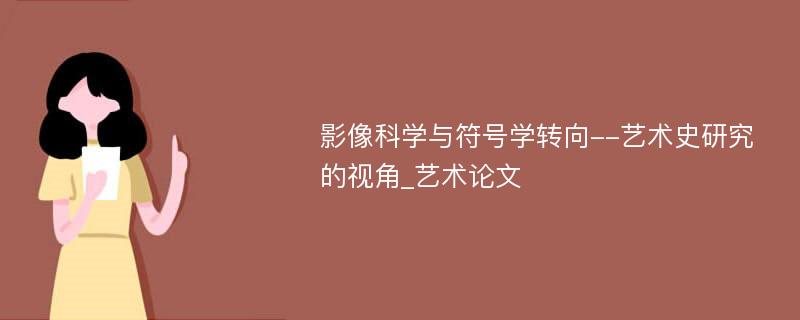
图像学与符号学转向——基于艺术史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视角论文,史研究论文,图像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3)11-0132-04
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名的《文化研究及理论遗产》中指出:“我希望为理论研究提出一种不同的隐喻,即与天使搏斗的隐喻。唯一值得拥有的理论是你必须将之打败的理论,而不是你轻松谈论的理论。”[1]艺术史理论是一个激烈又充满激情的论坛,其中出现的诸多观念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近二三十年,艺术史学科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方法,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例如符号学、现象学、心理学、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等。从视觉认知和感受的角度,人类文化可以分为文本文化和图像文化,文本系统是哲学、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图像则是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相对于传统艺术史的文本理论,艺术理论史的图像学转向使之出现了不少新的质素。
一、艺术史中的形式主义
图像学和符号学都致力于艺术品的意义问题,即艺术品意味着什么,如何产生意义。在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形式主义理论,这是一种研究艺术的方式之一,它并不强调对语境分析和意义的探寻,而是强调观者与其视觉特性的联系。
形式主义者认为应将语境与意义的问题放置一边,而纯粹、直接地与艺术品打交道。虽然这并不符合当代艺术史的趋势,但形式主义的这种认为艺术品是独特的存在的观念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德(Kant)在论述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时说:“诗人试图超越经验的边界,并将一种完满性呈现给感觉,这种完满性在自然界中是没有的,因为作为他们的天职,艺术在心灵中通过将这种景象扩展为一个各种相似表象的无限领域,使心灵感到愉悦。”[2]瑞士学者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在20世纪初提出形式与风格理论,在那样一个科学家都在揭示自然与人类行为规律的时代,沃尔夫林也认为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在主导艺术风格,由于他主要关注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因此他认为这一原则就是早期阶段、古典阶段与巴洛克阶段的循环。随着现代艺术的兴起,英国画家、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成为形式主义新的支持者,他认为艺术品是无法还原回语境中的,艺术并不需要图像志或艺术家传记去做“解释”,艺术品与其作者或文化并无实际联系。艺术史家亨利·福西雍(Henri Focillon)的形式主义理论则广受争议,他将艺术形式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并根据自身材料的自然属性与空间位置而在时间中发展变化。福西雍还研究了罗马式与哥特式风格在建筑与雕塑中的发展,指出了技术在决定艺术形式中的重要性。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拥护抽象表现主义,是现代艺术的形式主义的捍卫者。他的批评文章《前卫与庸俗》(1939)、《走向更新的拉奥孔》(1940)和《现代主义绘画》(1961)都声称艺术的主体即艺术自身,是艺术制作的形式与过程,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与这种看法合拍,关注抽象、画面的平面性和笔触等。美国艺术理论家与批评家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关于现代主义的独特见解,《以毕加索之名》(In the Name of Picasso)一文可以为例,认为拼贴画通过其形式与材料声称“再现根本上关于真实存在的不在场”,并批评了通过传记来阐释艺术作品的实践。
对形式主义理论的回顾可以说是图像学和符号学观念的导论,这是一种研究艺术的方式,与图像学、符号学致力于多语境、意义的探寻不同。
二、图像志与图像学
图像志,即图像研究,简单来讲,图像志的工作意味着鉴定艺术品中的母题与图像。通常,图像志与图像学二个词可以互换使用,但是二者实际指二个判然有别的阐释程序,图像学通过图像志的分析完成了鉴定工作,并从图像的更广的文化背景来阐释形象何以被选用,以及我们何以将这些图像视为一个特定文化的“象征”。
图像志与图像学起初是由艺术史学者专门为了艺术分析而产生。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很早就关注了图像的主题,意大利艺术鉴赏家乔万尼·贝洛里(Giovanni Bellori)将传记方式与图像志分析相结合,解释图像的文献来源。德国学者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对古代艺术主题的研究,为图像志现代体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澳大利亚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发展了现代图像志理论,拒绝了艺术的纯形式研究,认为特定时代的艺术是以诸多方式与宗教、哲学、文学、科学、政治及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他的学生、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on Iconology,1939)界定了图像志分析的三个阶段,认为图像志是一种方法,能让学者重新找到埋藏于艺术品中的内容。他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中写道:“在一件艺术品中,形式不能与内容分离:色与彩、光与影、体积与块面的安排,尽管有如一出视觉盛宴般怡人,也必须将之理解为一种不仅是承载着视觉意义之物。”[3]
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志分析的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即前图像志分析(pre-iconographic analysis),观者分辨出能以视觉识别的东西,而不考虑外来因素,是基本的形式分析;第二阶段即图像志分析(iconographic analysis),观者分辨出图像是一个已知故事或人物;第三阶段即图像学分析(iconological analysis),观者解读图像意义,同时考虑图像制作的时间、地点、文化风格、艺术家风格及赞助人意图等诸多因素。例如,对于一个塑料小人,首先可以将其认定为女性形象,进而认出她是一个芭比娃娃,再考察其所表达的社会中的妇女角色或女性身体的某些观念。当然,我们研究艺术品时,依次进入这三个阶段并不那么简单,例如第一阶段前图像志分析所需的“纯真之眼”(innocent eyes)就受到了很多质疑,一个基督徒在观看《基督诞生》图时,就会立即跳至图像志分析阶段,即第二阶段。此外,如果眼睛过于“纯真”,也很难对艺术品进行任何层面的阐释。例如,如果不熟悉植物,那么对于莲花的母题就不易分辨;如果不熟悉非洲艺术,那么就难以识别一个约鲁巴人的gelede面具上的不同形象。
图像志的任务是找出包含在艺术品中的象征与寓意的意义的工作,图像学则是紧跟在图像志之后的阐释阶段,考察母题、象征、寓意等在其文化中的意义。潘诺夫斯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符号形式理论的影响。卡西尔认为有意义的形式是为文化的意义所承载的,这大大区别于形式主义者对文化意义的剥夺。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许多学者仍认为他是此学科的领军人物。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方法与其对文艺复兴艺术的研究相关,但后来此方法也被运用于研究其他时期与文化,例如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等人的研究。美国艺术史家利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的有争议的《基督的性征》(Sexuality of Christ)就是一部富有想象力的运用图像志与图像学分析的著作。
20世纪兴起的“新艺术史”使图像学批评得到了发展,那是一个具有强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运动的时代,新艺术史学者对异军突起的批评理论尤为关注,例如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艺术史的历史等,并质疑艺术史的预设、方法和目标。由于潘诺夫斯基的方法是因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而产生的,因此特维特拉娜·阿尔伯斯(Svetlana Alpers)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最适于分析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而不应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一方法,否则将错误地暗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普世的制像(image-making)模式。这场争论在研究17世纪尼德兰风俗画时变得更为激烈。尼德兰艺术史家埃迪·琼(Eddy Jongh)运用了图像学方法研究这样一种对日常生活及事物的描绘,认为这在象征意义是寓意着富有,这遭到了阿尔伯斯的反对,她在《描述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1983)一文中认为荷兰艺术与意大利艺术不同,不是象征性和叙事性的,荷兰艺术家处于一个特殊的视觉文化中,这种文化将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描绘看做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独特的荷兰视觉文化的表现。
三、符号学阐释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黑骨头:少女时代回忆录》(Bone Black:Memories of Girlhood)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她们说,她不能穿红色衣服,因为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这太成熟了……她知道红色是代表激情的颜色,知道一个女人穿红色衣服就是放荡、性感,知道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最好警惕。红色代表她们所说的荡妇和妓女。她已经在试穿另一件粉色的衣服了,她们说她穿粉红色衣服看起来那么单纯、甜蜜。她私下喜欢黑色,这是一种夜晚的、内在激情的颜色,当她们盛装去夜总会时就穿黑色连衣裙……她等不及要穿一件。”[4]这是胡克斯描述的女人衣着的符号学,是基于文化的知识。黑色是夜晚的符号,因为它像夜晚的天空,也因是女人去夜总会时的穿着。黑色也是内在激情的符号,这对胡克斯有更具个人化的意义,因身边的成年女人夜晚外出穿黑色连衣裙而形成的。对其他人而言,如果没有与胡克斯相同的经验和想象,黑色并不一定代表内在的激情。因此,符号要被识别才起到符号的作用,并且也像黑色一样,符号可以有多重含义。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理论,是以某物代表某物。对于许多艺术史家而言,符号学更像跨学科版本的图像学,一种细致的提问方式,追问作品的意义及如何创造或表达意义。有学者认为,符号学提供了另一种“语言与模式”,来阐释图像及其与社会、观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艺术家、观者和文化是如何创造这些意义的。
说到符号学,最值得一提的学者自然是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索绪尔认为符号由二个部分组成,即能指(符合所采用的形式)和所指(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二者的关系就是意指的过程。皮尔斯则将符号分为三个部分,即代表项(符号所采用的形式)、解释项(符号得以理解的常识)、对象(符号指涉的事物)。以红色交通灯为例,在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中,十字路口的红灯是代表项,停下的车辆是对象,红灯意味着车辆必须停下的观念是解释项。此外,皮尔斯的三种基本的符号分类对艺术史家是最有帮助的,即符号(symbol)、图像(icon)和表征(index),符号这种能指完全是任意或约定俗成的,和所指并无相似,例如字母、数字、交通信号等;图像这种能指感觉上或性质上与所指相似,或模仿了所指,例如一幅肖像、一架飞机模型等;表征这种能指则不是任意的,在某种程度上与所指直接相关,例如临床症状、脚印、照片、电影等。当然,符号通常不仅属于一个类目,有许多交叉,肖像照可以为例,它既是一个表征,也是一个图像。重要的不是为一个图像贴上标签,而是思考不同的意指过程,以及能指与所指的不同关系,进而提出各种问题。
索绪尔学派和皮尔斯学派都承认符号学对艺术的阐释是一种颇有成效的方法,捷克语言学家简·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rovsky)用索绪尔的方法分析视觉艺术;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也将索绪尔模式用于知觉现象学研究,并于1960年出版了著名的《符号》一书;巴特著名的《符号学元素》一书也将索绪尔模式用于研究卡通、广告等流行图像。在艺术史学科之内,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在视觉艺术研究中探索了符号学分析的观念,将艺术品形式分析与其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相结合。新艺术史家也对符号学进行了不懈的研究,美国学者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在《语词与图像:古代政体中的法国绘画》(Word and Image:French Painting of the Ancient Regime,1981)一文中,探讨了艺术与书写语言的关系,提倡对艺术品的开放性考察,认为一个图像并非一个封闭的符号,而是开放的,有着多层重叠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在图像与文化环境中发生作用。
此外,荷兰学者米克·巴尔(Mieke Bal)对艺术符号学有着重大贡献,强调艺术品是一个事件,一个每一次图像被观者审视时都会发生的事件,符号学的艺术史的任务就是分析图像与对图像的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图像志研究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这一方法强调的是图像的共同性,而不是对一个特定图像与特定观者的研究,从而忽略图像的特殊性。
四、文本与图像
图像志、图像学和符号学理论在近些年来被限定为“文本与图像”的问题,而文本与图像是什么关系?视觉在说明文本,还是文本在控制图像?将文字用于阐释图像,这对艺术史家意味着什么?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从发生学上理解图像志、图像学和符号学理论的当代形态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文本与图像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有着漫长的历史:亚里斯多德讨论过诗与画的关系,贺拉斯的名言“诗如画”(Ut picture poesis)至今仍有很多学者引用。美国当代艺术史家W·J·T·米歇尔(W.J.T.Mitchell)在其著作《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1986)和《图画理论:语言与视觉的再现》(Picture Theory: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1994)中认为,视觉与语言的再现都具有一种必然的形式上的独特性,尽管是通过先于它们存在的艺术活动与社会、政治语境相联系。进而,米歇尔提出了著名的“图画转向”,他在《图画转向》(Pictorial Turn)一文的开篇这样表述:“知识和学术话语中的这些转变必定是相互关联的,而非那样紧密地相关于日常生活和普通语言,这并非特别显见。但看起来的确清楚的是,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另一次转变正在发生,又一次关系复杂的转变正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里、在公共文化的领域里发生,我想要把这次转变称作‘图画转向’。”[5]米歇尔认为对潘诺夫斯基的研究的复兴是“图画转向”的一个征候,潘诺夫斯基在1926年的经典文章《作为象征形式的视角》(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中,讲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图像空间和文艺复兴时期发明视角的故事,涉及图像的西方宗教、科学和哲学思想。米歇尔极为称赞这篇文章,认为是对“图像再现进行任何宏大批判的重要范式”[5],它包容了空间、视觉感知和图像建构的综合性历史,在广度和深度上是无与伦比的。未解决的问题只是观者的问题,对谁是其历史主体模糊不清,他使用了“划时代的感知”这样的词,似乎一个历史时期是在视觉上可见的东西或本身就是一个感知主体。
米歇尔明确地使用“转向”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变迁,更多地是指一种哲学方法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方法论转向。米歇尔认为“图画转向”可以从哲学和文化理论中对视觉再现的焦虑和对形象的恐惧得到证明。图像或视觉转向并非我们时代所特有,它是呈现出具体形式的重复的叙述,似乎在许多环境下都可以获得其简要的形式。他的这种说法可以用于批评一个新的媒体、技术发明或有关视觉的文化实践,摄影、动画、人造景观、雕刻、网络、写作以及模仿本身的发明都是显著的事件,新的生产视觉形象的方式似乎标志着历史的转折。
米歇尔指出“图画转向”出现的原因是由于音像时代和控制技术以及电子复制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仿像形式和幻觉主义,对形象的恐惧和对形象会摧毁其创造者的焦虑由来已久,正如形象生产本身一样古老。并且图画转向的幻觉,即完全由形象所统治的文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种对图画转向原因的看法与大多数学者相一致,都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和消费时代的产生,也有不少学者将“图画转向”作为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的响亮口号,或提出“视觉转向”等相似的概念,这种转向构成了视觉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图画转向”并不意味着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的到来,米歇尔用了“似乎”一词来表示,并非肯定这一结论。他认为原因在于一个“悖论”,即发达的图像技术和对图像的恐惧。对于把读写时代和图像时代对立并且把读写能力下降归于图画转向的观点,米歇尔称其为“图画转向的谬误”,他说:“这种错误建筑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的二元对立模式上,仅仅以这些转折点的其中之一为中心,并断言一个读写时代和视觉性时代之间单一的巨大分割。”[6]可见,米歇尔提出图画转向首先是针对人文学科而非大众文化而言的,在这种转向中图画获得了类似语言在语言学转向中的主体地位。图画在图画转向中摆脱了被社会编码、被符号学解读的被动地位,与语言平等,并可以影响创造、思想、社会。因此,米歇尔认为“一个比较有趣的选择正是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视觉经验或视觉素养不能完全用文本性的模式来解释。”[5]这也就是所谓的“后语言学”和“后符号学”。因此,图画转向并不是对语言学转向的取代,其另立中心是对语言霸权的颠覆,但最终目标是让图画与语言平等相处,共同构建世界,这也是对文本与形象关系的一个发展。
从形式主义到图像志到符号学,有分歧性的理论流派最多,每个流派都有热情的实践者。每一种研究艺术的方法都与阐释相关,在哪里可以找到意义或如何找到意义成为了争论的热点——意义是否如形式主义声称的那样存在于作品之内,或者如图像志和符号学声称的那样存在于作品之中,而作品是更大语境的一部分并与语境相互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