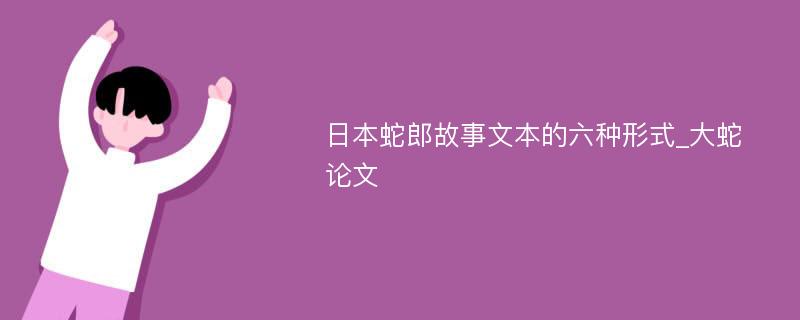
日本蛇郎故事文本的六种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六种论文,形态论文,文本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3)02-0080-05
蛇郎故事文本是典型的具世界性的文本,目前关于这一文本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 在文本的流布区域上,有学者指出中国、印度、缅甸、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非洲 、北美和拉美都有蛇郎故事[1];在故事的源流问题上,有学者认为蛇郎故事在西欧、 东欧(如俄国)、印度等国都存在,很可能这一情节是从印度传到西方与东方[2];在民 俗学研究领域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地理历史学派运用“AT分类法”,对此文本做了大 量的收集活动[3,4]。以上各种研究都说明了众多研究者对这一文本的高度关注。本文 作为一种尝试,只就所收集到的日本国的文本,将其分为“神婚与祖先之神”、“英雄 的蛇子”、“人神之间的池中之物”、“农夫的女婿”、“原生态的淫者”、“殉情之 蛇”六种形态加以梳理阐释。
一、神婚与祖先之神 日本最早的古典文献《古事记》里记载有一则哑皇子与肥长比 卖的人蛇神婚故事;与后来流传的蛇郎故事相关的记载有两则,一则为“八歧大蛇”的 故事,一则为三轮山神的故事[5]。这三则故事具有以下特点:(1)蛇的神异性与夸张的 艺术想象力的结合;(2)由图腾崇拜演化出的以蛇为祖先的神话故事演绎;(3)初露日本 文学在描写爱情、恋情上的悲情传统。之后的日本文学里,以蛇为主要描述对象的作品 都与这三则故事包括其所确立的艺术基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八歧大蛇的故事描述了天照大神之弟建速须佐之男命,设计杀死了每年一度到出云国 吃掉一个女子的大蛇。建速须佐之男命即素盏鸣尊。日本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的 人们以为这条大蛇就是伟大的魔王——水神,因此“人们每年用一名处女向这条作为水 神的蛇神献祭,想用这种办法略为摆脱一下水田农业所带来的不安。素盏鸣尊用人的智 慧和勇敢,终于斩了这条可怕的大蛇。因此,这个故事显然是为了保存并纪念英勇的人 们反对自然界、对野蛮而残忍的风习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记忆,有意编造出来并加以 流传的。”[6]这一阐释与马克思主义的神话观不谋而合。中国民间流传的河伯故事和 李寄斩蛇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斗争胜利的记忆。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及其文学的 源头,这则故事中的蛇神的神异性远大于它的可怖性。不仅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观念还 深深铭刻其中,从现实的生存处境上看,古代遭遇到干旱的人们经常为了求雨而举行仪 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往水里投美女以博取水神的欢心,这种行为通常会贯之 以嫁娶的名义。在这则最早的神话故事里,蛇神吃女子(同样也具备神的身份)可视为嫁 娶的前在形态,或者是象征、隐喻或变形。三轮山神的故事描述美貌的神女活玉依比卖 与夜访的神人相恋,后来发现神人是美和山神社里的神。“蛇郎夜访”这一核心情节最 早的版本即从此出。这一故事后又演化为“大和箸墓”的故事,山轮山神是祖先之神, 但只是一条三十厘米长的美丽小蛇[7]。这是最早将三轮山神的神体确认为蛇的文本, 与八歧大蛇的故事一样带有强烈的神异色彩。
以上两则神婚故事,还有学者做出了别具新意的解释。梅原猛直接把蛇与山联系在一 起,从八歧大蛇的外形入手,得出了“八歧大蛇是圣地三轮山的象征”的结论[8]。就 蛇与山轮山神的关系,民俗学者吉野裕子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 日本,当蛇作为神被造型化塑造或被描述时,往往取盘身的姿态,这也是蛇的正统的姿 态。这一姿态联系着日本人对圆锥形山的信仰。描画着秀丽弧线的圆锥形的山之形容, 会唤起人的心灵里的一种虔敬的信仰之心,催促着人们去归依并非人世的神圣东西。因 此在被浓郁的蛇信仰所遮蔽的日本人的眼里,作为祖先神的蛇是以稳稳地盘身坐在大地 上的姿势而映现的。三轮山神之所以以蛇体得以流传,首先是其优美而典型的圆锥形容 易让人联想起盘身的巨大的蛇。其次,从三轮山的名称看来,已经意味了神蛇的盘身之 轮,嵌入了“神轮山”的意思[9]。尽管学术界能否接受他们的观点还有待证明,但这 些观点也的确鲜明地突出了圣地三轮山的蛇之神体及其所含的信仰之一端。
在冲绳的古典文献《宫古史传》里,“神灵大蛇与住屋的姑娘”就是一则典型的以蛇 郎为祖先神的故事。因目前尚未见有译文,现将这一具代表性故事梗概大体译出如下: 从前,宫古岛下里南宗根的住屋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十四五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她的 父母责问她为什么没有丈夫却怀孕了。姑娘羞红着脸说,有一个不知名的美男子每晚偷 偷来相会。一想起他的来临,自己就有了梦幻便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怀孕了。她的父母 想知道男子是谁,就教女儿把穿有麻绳的针插在男子的头发上。第二天一早,只见麻绳 从门上的钥匙孔中穿出。他们顺着麻绳找到了涨水御岳(译注:神社的名称)的一个岩洞 ,一条二三丈长的大蛇躺在里面,头上插着那根针。姑娘的父母惊慌失措。晚上,姑娘 梦见大蛇来到枕边,对她说:我是宫古岛的创建之神,为了生这个岛的守护之神而偷偷 地与你相会,你将生三个孩子,等他们三岁时,请把他们带到涨水御岳。姑娘将此告诉 了父母。不久姑娘即将临盆,三月初巳日,姑娘采花沐浴,果然生下了三个孩子。三年 后,女子带着三个孩子来到涨水御岳,当上父亲的蛇两眼发光如日月,牙如剑,吐着红 舌头,以岩石为枕,发着鸣声。女子放开孩子昏厥过去。三个孩子并不惊恐,一人抱住 蛇首,一人抱住蛇身,一人抱住蛇尾纠成一团。大蛇流着泪亲吻孩子后升天而去。三个 孩子进入御岳,消失了身影,成了这个岛的守护之神。[9](P279~281)
冲绳是日本岛内非常典型的以蛇为图腾的地区,这则故事就是对奉蛇为祖先神的图腾 信仰的演绎。与三轮山神的故事相比而言,故事于男子夜访、蛇神为始祖神的情节演变 上有相似性,出现变更的是,与蛇神联姻的女子已演化为人,并且后者在对蛇父蛇子的 相见场面的渲染上,悲情与悲壮共存于中,父子分离的场景犹如人间的悲欢离合,让人 不禁怀疑这是人类创建初始艰辛备至的集体无意识的凝聚与镌刻的投射。
二、英雄的蛇子 这一种形态的蛇郎故事的基本情节依然是英俊男子夜访美女子,女 子的父母(或女子本人、仆人)通过穿在针上的线发现了男子的原体——蛇。将死的蛇此 时已被针的毒气重创,但有后代留存于人世。蛇的后代有如下几种结局:(1)成为著名 的僧人;(2)成为伟大的人;(3)为蛇子建祠堂;(4)蛇子成为有名的勇士、当地的豪杰 五十岚小文次;(5)蛇在临死之前告诉女子,她将生下三个蛇卵,要把蛇卵放在一个箱 子里,沉在水里六十天才能打开。可到了第五十七天时,由于箱子里有骚动,女子忍不 住打开来看,结果三个孩子都成了有名的勇士,因为提前三天打开,所以不能成为天下 霸主[10]。这类故事的特点是以蛇子的非凡业绩弥补了蛇父的死亡。这是蛇郎身份转变 的一个信号,同时也是蛇郎故事由神婚转变为兽婚的过渡形式,这一转变意味着图腾观 念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认识进程中抹去神秘色彩而逼近理性的进程。当然,借助蛇形象 使某一显耀家族的身份或权力神话化也是其潜在原因之一。《源平盛衰记》里也说古时 的显赫门族旺族、绪形氏一家的祖先也都是蛇子勇士的后代,这与《史记·汉高祖》所 载刘邦在起义之前斩蛇,并由此将刘邦比附为天帝之子有着实质上的相似。
这一种形态的故事中还有两个特例,它们将蛇郎的身份改变为蛇女,分别流传于日本 小■郡的西■村和武石村,是同一个故事的异文。故事梗概为:一个女子每夜都来拜访 年轻僧人(某寺庙住持),被针毒所伤,临死前生下的孩子被小泉村的一个老太婆所救, 蛇子就是成为大力士的小泉小太郎。后一个异文顺带解释了当地一条叫“产川”的河流 即为女子生蛇子的地方[10]。这两个特例极有可能是在故事传讲的过程中,因口头流传 的不确定因素,故将蛇郎的性别改换为蛇女,再加上日本原本就有蛇女故事流传,所以 听众也就不以为怪,直至此类故事在当地成为固定的文本。
三、人神之间的池中之物 这一种形态的蛇郎故事的共同主题是妻子被池中之物所魅 ,但对结局的处理却有两种。一种为某女子被水中之物(大蛇)所魅,其父或其夫携名刀 潜入水里欲救女子,在水里与变成年轻武士的蛇郎相会之后,看到女子在水中的生活状 况不错,就接受了布匹回到陆地上。另一种为女子——锅子到水池边洗东西时,池里的 主人——大蛇被她迷住了。有一天锅子去了水池边之后再没回来。她的丈夫太郎兵卫只 在池边找到她摆得整整齐齐的湿鞋子。太郎兵卫在那里痛哭不止,这时水里出来一个美 丽的男人,对他说:“死心吧,牧山的太郎兵卫,死了的锅子不回去了。”另一个异文 说,每当干旱之年,到水池的深处可以听到大蛇在唱着“死心吧,牧山的太郎兵卫,死 了的锅子不回去了”这样的歌。还有一个异文说锅子入水之后,她的家人去找她,在池 边大叫:让我再看看你吧。锅子从水池里冒出来,下半身是蛇,之后笑嘻嘻地又潜入水 里[11]。
同样是妻子被池中之物所魅的题材,却做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前者带有对水底世界的 美好想象,后者当是对悲惨现实的一定程度的反映,大蛇唱的那首短歌“死心吧,牧山 的太郎兵卫,死了的锅子不回去了”看似简单,却有着无穷的韵味,短歌以最简洁的词 语组合和谐地传达了淳朴的无可奈何的悲伤以及言无尽意无穷的意境。这种短歌的加入 往往给此类故事增添了抒情的色彩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注: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是日本 民间故事的一个特点。在这种故事里,如果出现与此类似的短歌,故事的整体氛围就会 有很大的变化,由简单转而意味无穷。例如《日本传说大系》第九卷有一则故事写美丽 女子——辰子,每晚有一年轻僧人来与她相会,后来才知道僧人是蛇精。辰子生下蛇子 后死去,人们在前往她的故乡的途中,在路旁叠了两块石头为她做了墓碑。这个地方因 此有短歌流传:“去看看,荒神的辰子的墓,起雾了”,看似简单,但依然是言有尽而 意无穷。)。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会产生并流传开来,与上文曾谈到的“往水里投美女以博取水神的 欢心”有着实质上的相近。这种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是——在类似祭神求雨的古老仪式 中,女子的牺牲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的生离死别。这样的生活真相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就 有可能出现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如前者,一种如后者。前一种是虚幻的浪漫主义式的, 当痛苦的现实无以排遣时,人们只能以美好的想象来替代以求心灵的慰籍;后一种是现 实主义式的,将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惨痛经验如实传达。以喜剧的方式包容现实悲剧,往 往是底层民间用以对付现实困境的大乐观,这无疑也是人类用以对付天灾人祸的苦涩的 大智慧。也正为此,这一形态的故事才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四、农夫的女婿 这一形态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田间地头或渔村,农夫出于某种原因(蛇 郎以帮忙干农活等作为迎娶农夫女儿的条件),不得不将女儿嫁给蛇。但故事的重心主 要放在农夫女儿如何在出嫁的途中与蛇郎(这里的蛇郎还可是猿猴等)斗智斗勇。就如柳 田国男所描述的,蛇郎带领女子来到池边,眼看就要进入池底时,女子把一千个葫芦都 扔到池里,说这些东西我都要带去。蛇郎在水里游来游去,想把葫芦牵到水里,但葫芦 一个都沉不下去。蛇郎游得筋疲力尽,女子又向它投了一千根针,每根针都刺到它的鳞 片之下,蛇郎终于死了[12]。中国的蛇郎故事里于姐妹之间展开的善与恶、智慧与愚蠢 的斗争,在这里则是人与蛇之间的对抗。日本民俗学者认为这里的蛇是邪神的象征,女 嫁蛇的故事的现实形态往往是女子作为牺牲品在祭祀时献给蛇。这是留存于民间的一种 惨痛记忆,人们因此希望女子在故事中能击败蛇。如果把这种故事形态与“人神之间的 池中之物”这两者拼接在一起,就是对过去的历史年代里人类上演的一幕悲喜剧的完整 的隐曲记录。
不仅如此,人类在塑造这样的邪神时还不忘运用充分的想象力来对邪蛇加以揶揄。日 本一种叫“夜叉池”的故事说蛇从农夫那里娶到了一个女儿,带回家后,蛇的原妻很妒 忌,无可奈何的蛇郎就想请人间有勇气的人为它杀了原来的妻子,后来终于有一个勇士 为它解除了烦恼。另一种说法是原来的蛇妻把女子推下山崖,自己也就在山崖之下住了 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蛇妻杀了女子之后,就伏在一块岩石上,据说那块岩石里被烙上 了怨念。这种因情而生的怨念几乎也可以称之为“蛇怨”,并且也有一系列故事存在。 [13]
五、原生态的淫者 这一形态的故事的特点在于:文本形式以佛教说话的面目出现, 内容上则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赤裸裸地写人与蛇之间的交合。这就是《日本灵异记》中卷 第四十一记载的“女人与蛇交,依靠药力保全性命的故事”,和《今昔物语集》里记载 的“蛇看见女阴情欲激发,爬出洞穴被刀砍死的故事”(注:故事的主要内容参看拙作 《中日两国的蛇精传说》,《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第102—103页。)。尽管民 俗学研究未将此类说话列入“蛇郎”的条目,但本文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形态来看待。因 为恰恰是这一种形态的故事突出了蛇郎故事文本一直被忽视的性爱因素。中外学者都曾 论及蛇形象所负载的性象征内涵。而在本论文所列举的这几种故事形态里,蛇郎形象所 蕴涵的从生殖崇拜意义上的生育繁衍,到宗教话语体系下被贬义化的淫欲观念的发展过 程,也正是人类通过这一形象及其故事而展示的,在对性的不断探视中所发生的快乐与 死亡、神秘与阴影、渴望与惧怕、引诱与抗拒相互搏斗的心灵历程。
因为这种故事是以佛教说话的形态出现的,所以并不排除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印 度文化乃至其中的佛教文化里,蛇形象负载有多重象征内涵,生殖信仰、祖先崇拜、恶 欲、贪色等等均包含其中。但在日本本土出现的“原生态的淫者”的故事形态依然很独 特,蛇所代表的性是直露激烈的,与死亡、阴影、恐怖等负面因素紧密相连。表面上看 这是人类借助这一形象来传达对自身的性的恐惧,但于潜在的层面,恐惧与渴望又是二 而一的。日本民族及其文化充满着矛盾性,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日本既可爱又可怕 ,蓝蓝的天空,漆黑的深渊”,日本文化则“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1 4]。在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纵欲与禁欲对立而又统一地交织在其文化中。蛇郎故事文 本的多种表现形态的出现与该民族这一文化特色不无关系。
六、殉情之蛇 在日本有关道成寺的故事里,爱恋僧人未果的寡妇死后化为大蛇追赶 僧人。年轻的僧人被藏在钟楼的大钟里,大蛇破门进入钟楼,尾巴缠着大钟,两眼淌着 血泪死去。蛇的毒气烧灼着大钟,躲在里面的僧人也被烧成了骨灰。这里的蛇女既是一 个因恶魔般的情欲不仅毁人同时也自毁的异类形象,也是重重的压制之下弱者借以传达 心声的艺术载体。因这一形象的存在,日本的蛇女故事颇具典型性,并且也与中国的“ 白娘子”形象区别开来。
但并不是说这样的异类形象只是用以塑造女性形象的专利。日本胜田郡流传有一则故 事,现试译如下:城山里住着一家姓诚的豪族,他们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一个大雪的夜 晚,一个受伤的武士来到她家,在照顾武士时,女子和他相恋了。武士病愈后起程离开 。女子从此消瘦下去,吃什么药都不见效。请法师来看,说是被怪物缠住了。于是,他 们晚上偷偷地窥视女子的房间,发现先前的武士来了,就认为那一定是怪物,于是把女 子关到别的房间。但武士又来了,因此只好盖了一间石头房子,把女子藏在里面。第二 天早上,一条大蛇盘住了房子。把蛇赶走后,发现里面的女子已经融化了。从此,蛇盘 住房子时枕在头上的那块石头,就叫“石之枕”。[15]
这则故事显然还是延续了蛇郎夜访女子的情节,与后来出现的女子母亲根据中毒的蛇 郎与蛇母的对话,让女子吃了三月三的桃酒、五月五的菖蒲酒和九月九的菊酒,打掉女 子腹中的胎儿不同。这里的蛇郎几乎就是道成寺故事里的蛇女的翻版。这一异文的出现 也有可能是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的口误。但既已作为一种文本存在,也说明了在日本 本土,蛇形象所蕴涵的恶魔般的情欲,其指向并没有完全地倾向于女性,在这一意义上 它笼统地指人类的一种两性都可能存在的可怕的非理性情欲。
以上只是对日本蛇郎故事文本的粗线条划分。就以蛇这一动物形象为主要描述对象的 作品而言,日本文学中还存在一系列的蛇女故事,并且也呈现出多种故事形态,这里略 而不谈。在日本文化中,蛇形象喻示的性内涵是最突出也是最主要的象征。而蛇与性之 间的隐喻关系也一直贯串在本文所归结的这六种故事形态之中。日本有关蛇文化、蛇信 仰研究的集大成者吉野裕子在追溯蛇信仰于该国形成的两大基本原因时指出:首要原因 在于蛇这一形象所意味的强大的性暗示与性联想的力量,再者是毒蛇、蝮蛇等的旺盛生 命力(繁殖力)与毒素对敌人的致命打击。绳文时代文化遗留物里具典型性的蛇型器物, 正是绳文人对跃动的粗野生命力与性的情念的象征,所以绳文土偶中的女性神的头上盘 着蝮蛇,石制蛇神体则为棒形,前头亦有蛇盘于其上[9]。也就是说,蛇郎故事在日本 的诞生及其广泛分布有其久远的历史文化根源。之后,由于文明体制的确立及其文化的 发展,这种带有原始文化特色的信仰崇拜文化渐次被儒家文化等外来文化所改变,蛇郎 故事文本也就渐渐具备了新的评判标准。因此,其文本的多种形态既包含有“农夫的女 婿”这种具世界性的形态,同时也存在独具日本特色的“原生态的淫者”、“殉情之蛇 ”的形态。前者可能是与不同文化交融的产物,农耕社会形态是文化得以交融的现实社 会基础;后者则主要源于该国由来已久的蛇与性的紧密联想观念的文化积淀。尽管把蛇 作为性的象征物这一文化现象在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圈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通过上述 多种形态加以表现,日本蛇郎故事文本的确独具特色,这也就是日本文化对这一世界性 文化现象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收稿日期:2002-09-11
标签:大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