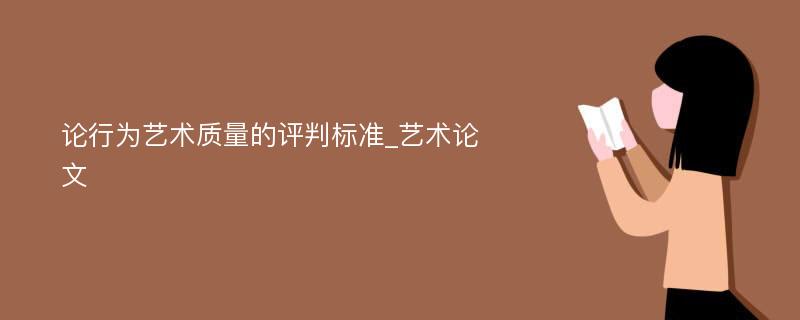
试论评判行为艺术好坏的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为艺术论文,好坏论文,试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产生自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西方占据重要地位,形成浩浩荡荡的“行为大军”,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其一度不振,到90年代在亚洲却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艺术的发展。
然而,行为艺术作为当今中国最前卫的艺术遭到了各界的批评,争议蜂起。在批评中,我们深深感到缺乏一个合理有效的界定和评判的标准,对种种概念的混淆使许多批评陷入了没有意义的境地。在此,我就针对这一问题,尝试性地讨论一下行为艺术的界定以及评判行为艺术好坏的标准。
一、界定——行为艺术和“行为”:
行为是伴随每种动物终生的活动,它是一种生之本能和生之必须。比如我们吃饭睡觉是行为,甚至可以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吃,可以关在家里睡一年,但没人认为这是在做艺术,顶多说你是神经病。然而同样是吃饭,美国的波尼·舍克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吃饭就被认为是行为艺术;同样是睡觉,中国的谢德庆在隔离室里睡一年就是行为艺术。原因就在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考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它始终在一种无意识的牵引下活动,它只起到一个满足生理欲求的作用,而行为艺术则不同。波尼·舍克的吃饭强调了笼子里肮脏环境和昂贵食物的对比,意在唤起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及浪费现象的关注:谢德庆的睡觉引发了我们对生存问题的思考。因此,行为艺术首先是一种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的行为,也就是说,它首先要有意义。
那么,所有具有指向性和针对性的行为都是行为艺术吗?这里存在三种误区。
首先,附会的指向性行为不是艺术。在这里,“附会的指向性行为”是指以一种行为为范本,生拉硬拽地把意义附着其上,即先行为后指向,从而把“不成熟的作品利用误读而变成解释的借口”(注:黄笃:《形象的焦虑》。《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2页。)。“附会”主要会引起两种“症候”(注:参岛子:《行为艺术论》。同上,第79-80页。其中提到行为艺术的两种“附会癖”:一、“泛行为主义”;二、“极‘左’主义政治美学”。)。第一种就是行为艺术的“泛含义化”,比如有人将行为艺术等同于商纣的酒池肉林、二十四孝的割肉挖心,甚至说二战是最大的行为艺术,这就是一种当前很流行的附会症状。第二种症侯就是对各种艺术的“泛标准化”。各个时期的各种艺术存在不同的评判标准,以传统美学的眼光看待行为艺术是愚昧的,以古典艺术的标准来评判行为艺术也是毫无意义的。同样,不同艺术的标准也是与不同的地域相关的,不能因为行为艺术在当今美国艺坛不再占据主流地位,就草率地认为中国的行为艺术是过时的、杜撰的、拙劣可笑的。另外,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许多所谓艺术家也犯了这种附会的病症,把当代艺术定义为“乱搞”,把西方的形式不加甄别的挪用,正是这种种打着“艺术”旗号的行为破坏了行为艺术的思想性,造成了行为艺术的生存危机。
其次,不具有公共性的行为不是艺术。不具有公共性的行为没有形成一个共同关切,不能在艺术的层面上打动人,或者说根本不构成艺术的题材。还是以吃饭睡觉为例,上文中已经说过,我们吃饭睡觉只是一种没有指向性和针对性的生理行为,还不构成艺术,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吃饭睡觉只是自己关心的事,还没有上升到公共层面,而艺术家的“吃饭睡觉艺术”是用来展示的,他们的行为所具有的指向性是人类所共同关心的,比如环境问题、生存问题。另一方面,有些行为虽然是展示给公众的公共行为,但只表达了作者的一己之愿,在本质上是私人的。这样的行为跨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陷入了自言自语的话语体系。更有甚者以艺术的名义而公开跳楼、排泄甚至卖淫(注:“1967年古恩特·布鲁斯的《希思行动》,是当众大便并拍成电影。1969年奥图·弥勒在一个电影院的舞台上当众往他的一位朋友嘴里小便……德国杰出的女艺术家芭芭拉专门从柏林到巴塞罗那去当妓女,以卖淫作为艺术行为冲击传统腐朽的社会准则……克莱因曾两次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从二楼跳下,体验‘升空’的感觉,承受了严重的伤痛之后,又跳了第三次,不过这次下面放了垫子,完成了他的《虚无的舞台》。”马尚:《生存互联:欧美当代行为艺术》,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31-32页。),这种种行为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泄愤的个人体验或者一种哗众取宠,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发泄或者怎么样去赢得大众的“眼球”,而且这样的行为往往是和“附会”及下文的“自相矛盾”相连的。行为艺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问题的紧密追踪和致力于建构的解构,它应当是积极的而不是封闭、消极、没有任何公共意义的。
最后,自相矛盾的行为也不是艺术。行为艺术之所以争议颇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猛”、“陈尸”等“暴力化”行为混淆了人们的视线。以“生猛”著称的朱昱为例,他的所谓“行为艺术”先是把一死婴煮熟当晚饭吃,接着又把自己的孩子喂狗,而他实际上所要表现的正是人吃人的社会现实。“就人吃人的主题而言,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任何食人场景,而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这一主题的历史的根源和本质。那么,今天的艺术是否一定要用人吃人的行为作出简单的形式复制?”(注:黄笃:《形象的焦虑》。《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19页。)事实上,这些行为在主题和实际操作上是自相矛盾的,根本上就是不合逻辑的,这和行为艺术深刻的思想性根本不可相提并论。可以说,“行为艺术‘暴力化’倾向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假问题,…这种‘追查元凶’式的论证,更是落入了这个假问题编织的圈套”(注:管郁达:《回答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九个问题》。同上,第37页。)。当然,这些“暴力化”的所谓艺术家也许是怀着英雄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来完成他们的“作品”的,然而,正是这种“大无畏”使得行为艺术的生存成了问题,导致很多人以偏概全地对行为艺术一概否定。因此,要使行为艺术生存下去,就必须将这些“暴力化”的行为从“艺术”的讨论范畴之中删除出去。
二、疑惑——行为艺术和“艺术”:
传统艺术更多是将人引入一个“意境”,自给自足地形成一个灵魂得以依托的艺术世界,而行为艺术恰恰相反,在它身上,我们很难找到审美的影子,它所作的更多是把我们引向现实的生活,它的着眼点在实事,在人文的层面上进行运作,使艺术关注哲学、政治,走上了“反艺术”的道路。其实“反艺术”并非行为艺术的肇始,早在杜尚的《泉》问世时,现成物的艺术已开始了“反艺术”的探索(注:[美]乔治·迪基:《什么是反艺术》(周金环译)。《世界美术》,1988年第3期,第77页。),只不过行为艺术把这种“反艺术”带入了一个动态的新境地,使这种反叛成为一种潮流。
海德格尔的学生博德尔说,“亚现代的艺术——在繁荣的亚现代艺术——只是继续分享我们历史中已经形成的艺术之名,而且将它置于艺术的连续统一体中就会不公正,很愚蠢,类似到处试图建立一种无基础的联系一样。”(注:[德]H·博德尔:《如何判断当代艺术》(何卫平译)。同上,2002年第4期,第64页。)也就是说,行为艺术不过是在艺术的名义下的一种与“艺术”截断了血缘关系的“反艺术”,这种“反艺术”除了还利用了“艺术”的名号以外,它的实质已与传统的艺术大相径庭了。
然而,行为艺术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反艺术”,在严格意义上说,它只是一种“反传统”,它从来没有也很难放弃艺术甚至去反对艺术。波依斯解释道,他所谓的“反”是反对因袭至今的艺术概念,其实,他所作的恰恰是拓展了艺术的概念,杜尚也说过,“反艺术和为艺术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注:《禅宗、杜尚与美国现代艺术》。[法]卡巴内:《杜尚访谈录》(王瑞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换个角度说,行为艺术作为艺术大家庭的一份子,在这个家族的发展史上起到了积极的拓展性作用,任何现当代艺术史都不会忘记叙述“行为艺术”这一辞条,经时间检验的历史并没有剥夺行为艺术的生存权。
当然,行为艺术作为一种先锋艺术,自身还很不完善,滥竽充数的所谓“艺术”还在混淆大众的视线,它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和自身的完善,最终取得时代的认可。但是,这种被认可并不等同于依附体制,它所要做的恰恰是不断向体制“进言”,最终和体制达到一种互帮互助的共生局面。这样(让我们畅想一下),行为艺术就从艺术的圈子里跳了出来,致力于关注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现代科学的发展,把落脚点放在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之上;同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领域又不会无视艺术领域的这种代表大众的呼声。在这样一种良性发展之中,行为艺术可以起到其真正实在的作用,从而实现其价值。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行为艺术的这种实用功能就把它划出艺术的界限,反而可以说,这正是行为艺术向早期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一种回归。正是这种回归使行为艺术摆脱了“精英艺术”的束缚,并提供了一块坚实的土地,助其摆脱了纯粹追求精神性的极端状态,从而最终可以切实地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和我们的时代发展是步调一致的。虽然在现代社会,行为艺术仍占有“先锋”的地位,但从其发展的总趋势来说,这种“先锋”地位终将大众化为一种把上层建筑和大众相连的普及工具,这也是由其实用功能所决定的。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艺术批评的诸坐标”中提到,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即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其中“作品”是这四者的核心(注:[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虽然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仍由“作品”这一概念生发而来,但是,在评判行为艺术时,我们所关注更多的已不再是作品本身了,我们要看艺术家的是否有想法,看它是否反映了世界,看它是否能够明晰地将观念传达给欣赏者。可见,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最核心的部分已很少具有“艺术性”了,而是将这种“艺术性”转让给其外围部分来表现。这由内而外转换的关系也许就是在哲学意义上对“行为艺术是不是艺术”争执不下的一大原因——有人认为,“行为艺术不是艺术”,因为它已不再是以“作品”为关注点了,而“艺术家的伟大……像一片春风,所经之处,冰融花放,自己却消逝于无形”(注:陈嘉映:《感人、关切、艺术》。《思远道》,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行为艺术却恰恰凸现了艺术家及作品以外的东西而忽视了“作品”;另外的人认为,“行为艺术是艺术”,因为它毕竟只削弱了“艺术品”概念中的“作品”一项,只不过是另一种艺术的变体。
三、主题——评判行为艺术好坏的“标准”:
勿庸置疑,在评判一件艺术品之前,首先要甄别它是否属于艺术。但是,这恰恰是对行为艺术的评判所常常缺少的,这种不加甄别的评判,不仅使行为艺术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而且还会把批评引向误区,陷入假问题编织的圈套而不自知。
当一个行为具备了行为艺术所应有的针对性、指向性、公共性,并且不附会、不自相矛盾时,我们就可以对它在行为艺术的层面上进行评判了。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以什么为标准?其实,在解答了行为艺术的界限之后,它的标准也随之显现了。可以笼统地说,行为艺术好坏的标准就是它所具有的行为艺术的特性的强弱。
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标准——新颖。好的行为艺术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关注生活,还会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贡布里希曾说过,“…精通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极其灵活、极其机敏的,这两点既表现在技术性解决办法的发展上,也表现在通过其他方向的新颖而意外的活动对技术缺陷的补偿上。”(注:[英]贡布里希:《艺术史与社会科学》。《理想与偶像》(范景中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然而在当今,行为艺术已经很少考虑技术因素了,因此,“精通”的另一方面——新颖——自然成了判断作品好坏的主要标准。其实以新颖作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艺术的首创,甚至并非现代艺术的首创,只不过到了现代,艺术已越来越少和技术发生关系,而走上了一条求新的道路,杜尚说:“关键的因素是差异”(注:[美]卡文·托姆金斯:《达达怪才:马塞尔·杜尚传》(张朝晖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其所谓差异也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新颖”。这么说也许会招致某些人的反感,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谓的新颖是建立在此行为已属于行为艺术的基础之上的,即这里的新颖是有意义的新颖,全然不同于单纯的“为新而新”。收藏家施特勒厄在解释他购买波依斯作品的原因时说:“我深信,波依斯几乎是唯一表达出这个时代特殊之处的人。”(注:[德]海纳尔·施塔赫豪斯:《艺术狂人—波依斯》(赵登荣等译),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波依斯作品的内容是新颖的——这个时代特殊之处;二、波依斯作品的形式是新颖的——这种形式充分地表达出了内容的特殊。可见,好的行为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新颖是全面的新颖,是内容和形式良好结合的新颖。
以1997年的行为艺术《为鱼塘增高水位》为例,它和1989年的《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在形式和意义上基本相同,从时间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为鱼塘增高水位》明显有借鉴《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嫌疑,于是我们可以说,《为鱼塘增高水位》并不是一件新颖的行为艺术。
在界定行为和行为艺术时,我提到一种对各种艺术“泛标准化”的附会症候,其中就存在以别国的所谓“原创性”来攻击中国当前行为艺术的现象。有人说,行为艺术是西方早就搞剩了不要的垃圾,有人说中国的行为艺术完全是西方的翻版,毫无价值可言。虽然我也提到了一个“新颖”的问题,但我并不同意诸如此类的观点。我们知道,西方艺术首先是以写实风格出现并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而当中国专心致志地发展写实主义时,西方早已抛弃了写实风格而进入了现代艺术阶段,如果延上述思路说下去,中国沿袭西方的写实风格也是没有价值的,然而恰恰相反,西方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艺术风格。其实中国的行为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这样的道路。“当原创和挪用并列为艺术手段时,原创即降格为自我挪用。批评对价值的寻求不再是原创不原创的问题,而是所谓原创和所谓挪用有什么意义。”(注:王林:《追问当代艺术》。《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8页。)比如乌克兰行为艺术家奥雷戈·库里克在1997年做的行为艺术《我咬美国,美国咬我》,就是对波依斯1974年作品《我爱美国,美国爱我》的很好挪用,二者相似的形式和题目表现的却是讽刺和召唤两个不同主题,库里克巧妙地挪用更加强了其政治讽喻性,这种挪用构成了其作品不可缺少的一个意向。(这个例子可以和《为鱼塘增高水位》的例子相比较)
另外需要重复强调的是,行为艺术的针对性、指向性既是行为得以成为艺术的重要标志,也是判定行为艺术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美国当代艺术家布鲁斯·瑙曼说:“真的艺术家藉着揭露神秘的真相来帮助这个世界”(注:[英]修·昂纳.约翰·弗莱明:《世界艺术史》(范迪安中文版主编),海南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865页。),他和波依斯开创了将重点从表现形式转移到意义上的新作法,而这种对意义的强调也就是我所说的“针对性”和“指向性”,这是作为当代先锋艺术的行为艺术与传统强调审美态度的纯艺术的一个很大区别。正如本雅明所说:“……当衡量艺术产品的本真标准失效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艺术的根基不再是礼仪,而是另一种实践:政治。”(注:[德]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在行为艺术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传统意义上的美感了,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揭示现实和唤起关注,好的行为艺术能以新颖的手法唤起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四、结语——行为艺术的“明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零派艺术”(Zero Art)、“贫乏艺术”(Art Povera)。“事件”(Event)艺术等一系列极简主义的艺术形式把艺术的发展导向了极端,于是有人认为,作为这些艺术的共同因素——行为艺术也同样无路可走了。然而事实却是这样:极简艺术没落了,行为艺术却在世纪末重新崛起。这和行为艺术自身的不断更新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充分表明,行为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然而,行为艺术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先锋”艺术,它无法避免地同任何艺术的童年时期一样,“和创作个体的牺牲与眼泪、绞杀与飨宴、抗争与内讧、信心与诽谤紧紧纠缠、连结在一起。”(注:岛子:《行为艺术论》。《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79页。)但是,前文已经说过,行为艺术将发展成为一种普及化的艺术,它终将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从而实现其“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理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许多问题,比如规范和界定“行为艺术”这一名称,防止其无限制的乱用而混淆了人们的视线;拓展行为艺术的领域,引导其走向社会和大众;同时也要避免行为艺术落入不健全体制的“权威”控制之下,从深层挖掘,力求内容与形式的新颖。
总之,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行为艺术真正表明了这种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的趋势,同时也在不断改进以适应这种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艺术是一种真正具有“远大前程”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