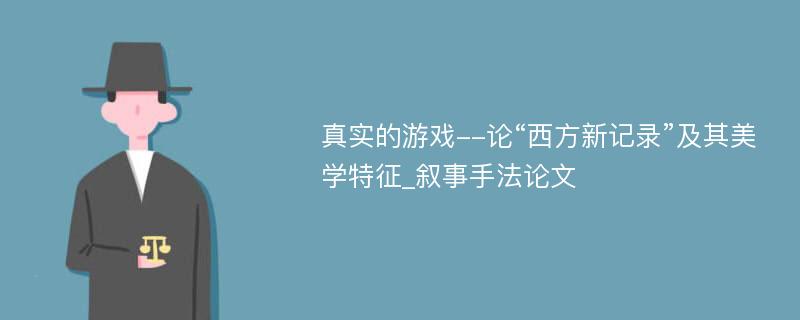
真实的游戏——论西方新纪录及其美学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新纪录论文,特征论文,真实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纪录电影中,“新纪录”(New Documentary)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熟悉是因为它经常与“新的纪录片”(The New Documentary)相混淆,每一时期近期出品的纪录片常被称为“新纪录片”,而把“新纪录”作为纪录电影创作中正在进行的一次革新运动的理解却显得较为陌生。与纪录电影史上的其他艺术运动相比,“新纪录”的发生显得迟缓而拖泥带水,以至于长期以来只有很少的几位理论家关注这次纪录电影的革新。本文试图从纪录电影美学的角度论述新纪录现象。
一、新纪录诞生的语境
新纪录的产生是纪录片制作者在非技术革新的条件下,从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吸纳其他艺术的成果,积极适应社会对纪录电影的特殊要求,从而对纪录片的表达形式和社会功能进行的一种自觉的探索。这种探索与当时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艺术潮流和时代需求紧密相关。同时,电视的作用和先锋电影的启示也不容忽视。最终,它是以反叛和对抗直接电影暧昧的涵义和追求表象真实为旨归而实现。
1、社会文化语境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济极度繁荣但社会文化却激烈动荡的时期:校园骚乱、犹太人暴乱、政治暗杀、黑人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摇滚狂潮等,构成了一连串的文化危机事件,而打破一切偶像的反传统文化成为当时最盛行的文化思潮。“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几乎成了一个单单发生在美国的事件。”① 后现代主义主要被用来描述二战后“美国性格的变化”、② 后工业社会的一种状况、美国社会各种反文化和存在主义的智力反叛力量,它标志着现代主义神话的解体,预示着各种被“现代主义”废除了的艺术风格的“复活”。正如德国科勒所总结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特定的风格,而是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尝试”。它同时从激进的实验和指向通俗的两个极致来对抗现代主义的成规,力图填平现代主义精英意识人为造成的那个鸿沟,以到达人类统一精神的彼岸。由此衍生了以反对主流、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生活观念。
艺术上,美国60年代的先锋派比前辈们更接近自由的主题。他们打破代表了社会束缚的艺术常规,部分摒弃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手法并引入具体的政治内容。他们把艺术当作游戏,也反对主流文化认为高雅艺术是严肃事业的价值观,提倡艺术的娱乐性,并进一步提高了对艺术形式解放的强调。特别在对抗苏联极权主义艺术形式的宣传下,繁荣的先锋派艺术成为美国民主和自由的象征。他们关注文化和价值问题,承认差异,确立边缘权利,坚持激进的多元主义艺术立场,主张取消差别、允许普通事物成为艺术的表现内容,推崇基本结构的并置、平等,取消差别的方式,挑战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反技术倾向,模糊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同时采用拼贴或多种艺术手法。正如电影理论家保罗·亚瑟说的,“这些分享了其他文化现象的纪录电影可能达到了空前杂交的程度,它们对资料的使用和表达技巧与模式,不但借鉴早期的纪录片风格,而且借鉴美国的先锋电影,乃至借鉴好莱坞”。③正是对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热情在艺术规则的开放姿态中孕育了新纪录。
2、电视受众的培养
越战时期也是美国电视新闻的大发展时期。在这段时间中,电视技术的发展为电视新闻的制作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另外,自50年代爱德华·R·默罗时代以来,电视新闻一改以前由播音员“客观”“权威”的报道,始终围绕个性鲜明的记者而结构。如罗杰·马德、麦克·华莱士、沃尔特·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蒂斯等,这些记者有着观众熟悉的嗓音和面孔,他们在观众与报道对象之间制作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调和关系。电视对新纪录最重要的积极影响体现在:首先,新纪录继承了电视新闻的采访形式,并使其核心化。因此,新纪录从形式上亲和了自爱德华·默罗以来培养的大批电视观众群,尽管新纪录的采访与电视新闻的采访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次,新纪录处理现实题材的敏感、棘手和争议的启发来自于电视新闻的实效性,使其更加符合人们对纪录电影的社会责任的期待。还有,电视促进了观众对新纪录开放的素材观念的接受。新纪录对构成影片的资料呈完全的开放态度,电视录影、家庭录像、旧电影资料等,都可能成为新纪录的素材。这些非电影标准的素材杂交混合在新纪录中,使新纪录形式上具有一种家庭私人电影的亲切感。
3、直接电影的遗产
众所周知,真理电影和直接电影运动的原初动力是电影技术的革命。50年代晚期,面对手持摄影机和便携式录音机的发明和应用,大西洋两岸的纪录片人热烈赞扬这个新的易接近“真实”的手段,实际上是表象的视听现实生活的真实。以让·鲁什为代表的真理电影制作者带着他们的“电影自来水笔”冲上大街积极干预现实。紧步法国同仁之后尘,美国的理查德·李考克等人紧密团结在德鲁小组周围,他们仿佛第一次发现纪录片“无中介”存在的生命力,他们谈论忠诚、隐私以及纪录片的首要问题——客观性。直接电影“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利用同步声、无画外解说和无操纵剪辑尽可能忠实地呈现不加控制之事件的一种尝试”。④ 因此,直接电影的制作者努力否认和隐藏制作者个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通过客观冷静的观察方法就能够获得其他任何纪录片制作形式所不能达到的真实。于是,直接电影表达的结果经常是含糊和暧昧不清。从本质上说,“直接电影最严重的缺点不是它的主观性本身,而是它固执的不偏不倚的借口”。⑤ 而且,当时不加选择地使用直接电影的这种“客观”的观察方法感染了许多影片,不仅使作品在评判价值上混淆,还蔓延到主题的混乱、自我中心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缺乏冷静说理和制作者暧昧态度的直接电影在面对美国的重重危机,尤其是越战时显得极为保守。可以说,越战对美国直接电影的考验也几乎是致命的。本质上,直接电影与越战没有直接关系。然而,随着战争的升级再升级,直接电影人却全神贯注于摇滚音乐会和悠闲的对象,如李考克的《局长们》(Chiefs,1968)、怀斯曼的《基础训练》(Basic Training,1971)、梅斯莱斯兄弟的《编戏的人》(Showman,1963)、《遇见马龙·白兰度》(Meet Marlon Brando,1966)、《给我庇护》(Gimme Shelter,1970),唐·艾伦·潘尼贝克的《别往后看》(Don't Look Back,1967)、《蒙特利流行歌曲》(Monterey Pop,1968)、《继续摇滚》(Keepon' Rockin,1969)等,还有一些则粗俗地转向商业舞台。尽管直接电影也时常提供一些意义深远而动人的艺术作品,但显然这时的直接电影已不能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对纷繁的社会政治进行清楚直率分析的需求。由此,一些投身政治的电影工作者深感需要超越直接电影,发展一种新的更具有论战性的纪录电影风格。而直接电影则在好莱坞已经被发展成为一科以手持式摄影机造成画面动荡不安的纪实风格的陈套。
二、应运而生的新纪录
从直接电影到新纪录转变的最终根源在于埃米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等纪录片人对60年代美国的政治文化气候做出的反应。像当时持不同政见的电视新闻记者一样,安东尼奥也积极吸纳了这十年占主导地位的直接电影的优势,但他又使直接电影严肃和谦虚的形式与他民主启蒙主义的目的相适应,探索了纪录片作为一种诚实的政治调查媒介的潜能,使60年代含糊暧昧的直接电影最终被这种公开承诺、调查和分析的新纪录电影推向边缘。新纪录电影从一开始就坦率承认,摄影机在服务于有意识的政治倾向性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及受到一定的约束。这种谦虚和承诺使得新纪录能够经受商业的出卖和政治凝结作用的双重陷阱。
理论界对新出现的电影现象能够做出恰当而正确的评价往往比较滞后。即便是新锐的电影杂志也对20世纪70年代纪录片创作的这种新趋势显得狼狈不堪,更不用说较为保守的评论家了。安东尼奥的第一部影片《议事程序问题》(Point of Order, 1964)在参评1964年的纽约电影节时,被纽约电影节的评委们驱逐出门,原因是“那是电视而不是电影”。⑥ 讽刺的是,时隔三个月之后,最初拒绝该片在纽约上映的评委之一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议事程序问题》是电影,而且还力邀该片参加伦敦电影节”。⑦ 相比之下,好莱坞则要慷慨得多,1969年,安东尼奥的越战史诗影片《猪年》(In the Year of the Pig,1968)获奥斯卡提名。1974年好莱坞又颁予彼德·戴维斯的《心灵与智慧》(Hearts & Minds,1974)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由此,新纪录的创作手法得到好莱坞的正式认可。而直到1976年美国现代艺术馆才以回顾展的形式承认了安东尼奥作为新纪录敏感的先锋和最初实践者的成就,也才迟迟地回应了观众对新纪录的需求。《滚石》杂志把德·安东尼奥的价值提升到激进的圣徒的地位。这时期,对安东尼奥的关注更多地倾向于从激进主义电影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如《电影季刊》1971年秋季号上伯纳德·维纳的《激进主义的净化:与埃米尔·德·安东尼奥的一次访谈》,《跳切》1978年春季号《德·安东尼奥就他的马克思主义电影〈猪年〉与比尔·尼克尔斯的问答》等。
随着德·安东尼奥日增的声誉促进了电影理论家真正开始关注新纪录现象。1976年,电影评论家托马斯·吴沃在电影杂志《跳切》第10—11号上发表了《超越真理:埃米尔·德·安东尼奥与70年代的新纪录》,文章一开始就说:“过去的几年中,一连串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片的出现——最知名的有《画家的绘画》(Painters Painting,1973)、《I·F·斯通周刊》(I.F.Stone's Weekly,1973)、《阿提卡》(Attica,1974)、《安东尼娅》(Antonia,1974)及《心灵与智慧》——是一个暗示,在这十年的中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美国纪录片不仅展示着显著的生命力迹象,而且还在自觉地前进,以它自己独特的方向贯穿70年代。正是这个方向明显地区别于统治了60年代的真理电影,它存在多样性。尽管怀斯曼延续了真理电影的声音,梅素斯兄弟及其他人还在奉行着十年前的风格,但是毫无疑问,70年代美国纪录片已经增添了新的篇章。”⑧吴沃肯定了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新纪录的发生,他从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以及纪录片理论方面分析了新纪录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比尔·尼克尔斯1983年在《电影季刊》春季号上发表的《纪录片的声音》一文中认为埃米尔·德·安东尼奥是一种纪录片策略变化的“先锋”,他“树立了一个清晰的路标”。⑨ 由此,新纪录才正式进入电影理论家研究的视野。
1991年,《乡村之声》的评论家艾米·托宾认为“1991年出现的四五部纪录片使纪录电影走上了一条多样化的航线”。⑩ 1993年,保罗·亚瑟在《行话的真实性》中认为《心灵与智慧》等70年代几部纪录片试图通过与后现代时期的文化论相适应而复兴了以前的资料加采访的纪录片实践方法。(11) 他还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影片《细蓝线》、《罗杰和我》等影片达到了空前的杂交程度,是新纪录的典型作品,并论述了新纪录的美学品质。同年,琳达·威廉姆斯在《电影季刊》春季号第3期上发表了《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中认为《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1988)、《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内战》(the Civil War,1990)、《浩劫》(Shoah,1985)、《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1990)等影片已经使纪录电影走上了一条新道路。(12) 她并以《浩劫》、《细蓝线》为典型文本阐述了新纪录的某些特征。
进入21世纪,新纪录的发展更加迅猛,2004年被电影界称为“纪录片的回归年”。(13) 从获戛纳金棕榈奖的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Fahrenheit 911)到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埃罗尔·莫里斯的《战争迷雾》(the Fog of the War,2003),还有沃纳·赫尔措格的《白钻石》(The White Diamond,20041)、泽娜·布里斯基的《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2004)、尤金·杰瑞肯的《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2005)、摩根·斯伯利克的《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2004)、乔纳森·考特的《诅咒》(Tarnation,2003)、詹赫恩·纽翟姆的《控制室》(the Control Room,2005)、休伯特·苏佩的《达尔文的噩梦》(Darwin's Nightmare,2004)、尼克·布鲁菲尔德的《艾琳: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Aileen:Life and Death of a Serial Killer,2003)等都是优秀的新纪录影片。以至于电影理论家保罗·亚瑟发出了“刚刚过去的90年代,每年年终著名影片的调查中能够发现提到一部纪录片的几乎没有。去年(指2004年),人们惊奇地发现每一份报刊或杂志的批评家在其十佳影片排名中至少不包括一部纪录片的非常罕见”。(14)
三、新纪录的“新”论
对于美国70年代产生并持续至今的这种纪录片创作新的变化现象,创作者和理论家使用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名称——“新纪录”(New Documentary)。新纪录不像苏联的电影眼睛、英国纪录片运动或真理电影和直接电影那样有较为统一的创作纲领、鲜明的艺术主张或宣言,它既没有具体的导演名单、一致明确的美学主张、统一的创作方法,也没有具体的社会范围或明确效忠的意识形态,甚至在产生时间和名称上都有争议。这是因为新纪录不是在短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纪录片的创作或技术上发生的一次激变,而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由一些先锋导演的创作开始,逐渐使得纪录片创作发生渐变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优秀的影片毋庸置疑地奠定了新纪录在纪录电影史上的位置。新纪录的美学主张和创新价值的分析则散布于新纪录导演的访谈以及少数纪录片理论家的评价中。
理论家和一些创作者把这种区别于直接电影的纪录片的革新现象称之为“新纪录”,也有根据这种新的创作现象的文化特征称其为“后现代纪录”(Postmodern documentary)。从纪录电影发展史来看,“新纪录”这样一个中庸的称呼显然是一个权宜之策。理论家更愿意从新纪录的杂交形式特征来谈“界限的模糊”、“跨类型的啮合”、“交互式纪录片”(15) 等,而不大愿冒险从新纪录创作群体的历史语境和整体的美学价值上给予评价。新纪录的创作群体因为没有一个共同明确的美学纲领和领导者,加之新纪录影片形式上的千差万别以及与传统纪录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很难对这种创新现象达成共识。因此,一些理论家和新纪录导演仅仅为了区别于直接电影而对其采用了“新纪录”这个称呼。至于以“后现代纪录”称呼这次创新运动的则更为罕见,从一些导演的访谈中看出,主要是基于后现代语境中纪录片与观众的关系考虑的,即便是新纪录最有影响力的导演埃罗尔·莫里斯也不甘心服膺于“后现代”的名号,而矛盾地称自己是“反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16) 克劳德·朗兹曼直言“我对属于哪个流派并不感兴趣,我的影片(指《浩劫》)是由观众评判的”。(17) 实际上,“新纪录”这个名称与新纪录导演在创作上表现的锐利和讽刺,与新纪录影片的丰富多彩、张扬凌厉的特征相比,纪录电影史上的这次革新运动的术语选择在后现代文化的喧嚣声中显得空前贫乏和苍白。
四、“空前杂交”的美学特征
出生于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新纪录所呈现的美学特质不可避免地沾染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如多元化、拼贴、碎片化、杂糅化、反讽等。与后现代社会这个没有恒定主题、反英雄的时代相适应,新纪录电影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杂交。“剧院上映的(纪录)电影的最近的文体——《谢尔曼的进行曲》(Sherman's March,1987)、《布莱德克上空的闪电》(Lighting Over Braddock,1988)、《令我疯狂》(Driving Me Crazy,1988)、《罗杰和我》以及《细蓝线》——与其他文化现象所分享的是一个空前程度的杂交。”(18) 新纪录有意打破各种电影文体的壁垒:画外叙述、拾得的片断、访谈、搬演、字幕、特技等交织一起,模糊了传统所划分的剧情片、纪录片乃至MTV的界限,突出特征是纪录电影像拼贴画样被人为地铸造。拼贴画的结构策略成为新纪录的思维方式。它对待现实不再是“挑、等、抢”而是不同质感素材的杂糅“拼贴”,间离效果成为该思维方式的必然审美效果。反讽则是新纪录文体特征和结构策略中渗溢出的气味。
1、个人化的叙事方式
“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9) 纪录片的叙事方式,透露了摄制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及不同的纪录片风格的特质。后现代语境中的新纪录崇尚不确定性、开放性、多元性以及非中心化,因此,它的叙事方式是含混多义的,往往是游戏式、个人化的。注重直觉和体验的个人化叙事方式的新纪录完全区别于“客观叙事”方式,它是一种精巧、更易令观众接受的方法。它增加了叙事的亲历性,并从有限的叙述带来丰富的联想,满足了观众理所当然的好奇心,或者至少具有令人感觉亲切的外表,还能巧妙地表达叙述者的主观情感和评论。如《灰熊人》(Grizzly Man,2005),沃纳·赫尔措格巧妙地用崔德威自己拍摄的录影,以他的解说和采访就像给观众引见一位他的好朋友一样,重塑了“恋于熊而死于熊”的提摩西·崔德威这个传奇式人物复杂的人格。个人化叙事方式的纪录片以个人体验和个体情感作为对现实记录的一个主要参照。在后现代的多元的、破碎的语境中,那种重大而统一的主题被多种非中心化的多元主题并存所取代,个人化叙事成为一种对于公共叙事不由自主地回避或反叛的策略。
2、采访元素化
采访是“经由微妙及其他的方法,访问者引导受访者,提供受访者需要的方向和阻力,以使受访者的底层灵魂浮现”。(20) 新纪录承认纪录片对现实的反映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真实是一种关系,是在策略性的调查中逐渐浮现出来的,而采访则是潜入心灵底层进行调查的一种强有力的策略。因此,采访在新纪录影片中被元素化,其作用大致有:1.采访增加了电影制作者和他的拍摄对象或被调查的人之间的积极互动,并且避免出现没有来由的画外解说,因此使影片更加清楚地表明了特定的时期和独特的观点。如《罗杰和我》中摩尔为采访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罗杰·史密斯进行的每一次努力和失败都是对摩尔所要表达的观点的证明。2.采访中独具气质的个人表达丰富了解说的内涵。《灰熊人》中接送崔德威去灰熊营地生活的飞行员、清理现场人员、崔德威的前女友、灰熊保护基地的主任等不同的观点与赫尔措格的解释相互补充丰富,使观众逐渐理解了影片中那位狂热而执著的爱熊者。3.通过访谈把对事件的各种叙述充分融入一个单一的题材当中。这种表达方式往往是把个人谈话的声音和支持谈话内容的影像材料剪辑在一起,一方面为观众提供了大量史实的影像,另一方面谈话的声音是对这些影像的说明或分析,如《猪年》、《浩劫》等都是这类优秀的影片。这种模式的纪录片往往将两种或以上题材相融合,从而创造出以那种随意发表但又负责的个人观点来表述现实社会的影片。
3、自我反射的引力
自我反射方式的纪录片是指在影片中展示出来涉及制作过程本身的各个方面,它使影片具有了人为操纵的性质。直接电影极力掩饰摄制者的在场和导演的建构,让观众进入一种“目前看到的就是现实所发生的事实”的假定之中。而新纪录则是要打破这种假定,提醒观众纪录片表达的真实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并激发观众就影片表达的内容进行多元认知和思考。从自我反射的表达方式所带来的美学效果来看,它与新纪录的艺术主张在精神上是契合的。因此,它对新纪录是一股巨大的引力。
新纪录对自我反射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为:1.拍摄影片的过程直接出现于影片中,标注影片对所拍摄现实世界的建构过程,如迈克尔·摩尔、尼克·布鲁菲尔德的大部分影片都采用了这种自我反射的方式。2.导演通过自己画外解说对所表达现实的影像进行说明和评论,如赫尔措格的《灰熊人》、《白钻石》、《时间之轮》(the Wheel of Time,1999)都是以非常个人化的解说引导观众多层面地深入认识一个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简单的正反两方面的评价。3.在影片引用的资料上标注来源和日期以及对它的利用来实现。《抓捕弗雷德曼父子》中,导演安德鲁·贾瑞凯以弗雷德曼的家庭录影作为另一个叙述时空。这些旧家庭录影成为理解弗雷德曼家庭关系和人物性格,促使观众从家庭亲情的角度思考该案件。4.以采访者提问或回应的声音来标明电影制作者的存在并对拍摄对象的干扰。《兄弟的监护人》(Brother's Keeper,1992)当采访一位紧张不安回避镜头的老头时,老头一再咕哝说自己天生就紧张,导演则问“为什么我不紧张?”时,老头边走边说“你当了农民你就紧张了”。这段小采访直接反映了摄制者与拍摄对象地位的不平等,提醒观众拍摄者和电视新闻的报道都是处于另一个阶层地位上对弱势的拍摄对象发出的调查和得出结论,其实这完全是不对等的。
4、剧情片的叙事策略
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新纪录影片的叙事策略从传统纪录片及直接电影的“规范”和“自律”走向了游戏化。它的最大特征是兼容一切电影叙事手段,尤其是打破剧情片与纪录片的壁垒而积极吸纳剧情片的叙事策略,如叙述追求戏剧化,有目的地搬演、影片有适当的配乐、剪辑自由使用各种特技等等。
新纪录戏剧化的叙事策略往往令观众大吃一惊,甚至怀疑是在看好莱坞影片。《艾琳: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警察一年内在一片森林中发现七具被同一型号手枪射杀的男尸,而这位凶手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连环杀手;《灰熊人》中,庞大的具有攻击性的野灰熊零距离地在摄影机前信步、嬉戏和捕食,野狐狸舔崔德威的手指等场景是剧情片也不会出现的。可以说,戏剧化叙事是新纪录叙事的一个重要特性,它是新纪录打破传统纪录片的平铺直叙的有力武器。“我是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才尝试突破冷静、不干预的传统纪录片拍摄原则”,尼克·布鲁菲尔德回忆道,“当时我正在拍一部关于女演员莉莉·汤姆林的纪录片,我非常不走运,所有有趣的事都发生在我关机的时候。因此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重现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并将它们和采访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唯一的弥补方式,否则影片将非常平淡——一种不真实的平淡”。(21)
纪录片的搬演是从剧情片中借鉴的一种叙事技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纪录片的视觉力量。大量的新纪录影片使用了搬演的方法,但是搬演手法却不是新纪录影片的构成要素。搬演以埃罗尔·莫里斯的《细蓝线》中关于高速公路上射杀警察伍德的案发场景的搬演最为出色和意蕴丰富。莫里斯的这场搬演粉碎了传统纪录片把搬演手法称为“真实再现”的观点,他却提醒观众看到的往往是不可信的。除《细蓝线》外,莫里斯还在《死亡先生》(Mr.Death:The Rise and Fall of Fred A.Leuchter,Jr.,1999)和《战争迷雾》中采用了搬演手法,他都以写意的风格,采用精美的广告拍摄手法,并结合电影特技制作,给观众一种纯粹的视觉美的享受,而不是告诉观众“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新纪录对搬演手法的滥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歌曲与音乐是剧情片的一个重要的表达元素,它在表现电影的主题、渲染和烘托气氛、表达情感上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甚至在电影的叙述上也充满魅力,但是剧情片的这个富有表现力的手法一向被纪录片视为忌禁,认为有悖于纪录片的纪实宗旨,仅有少量的音乐尽量不露痕迹地为环境或人物做点渲染。新纪录在创作上主张模糊所有的电影界限,电影歌曲和音乐无疑是新纪录创作的一个有效手段,如《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华氏·911》、《抓捕弗雷德曼父子》(Capturing the Friedmans,2004)、《四个小女孩》(4 Little Girls,1997)等影片都使用了大量的歌曲,或者参与叙事或者表达情绪,都是用语言难于企及的表达效果。
5、间离效果
从新纪录电影的形式来看,它的自我反射手段和拼贴画的结构策略都造成了间离的美学效果。间离效果的意义在于使观众对所描绘的事件,有一个分析和批判该事件的立场,调动观众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
新纪录电影间离效果的实现大体分为:1.新纪录的拼贴画特质使得异质的影像和声音与影片实际拍摄的影像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直接导致了叙述上的间离,使观众在不同肌质的画面和声音间转换,这个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的拼合和建立的过程,是观众的思考和批判的过程,如《抓捕弗雷德曼父子》声画主要在弗雷德曼家庭录像和导演的调查拍摄之间转换,二者交替剪辑构成了影片强烈的间离效果。2.拍摄对象直接面对摄影机的采访,使影片的叙述不断被打断,不断转换视角,观众的观看过程也是一个碎片的整合过程。新纪录“众声喧哗”的采访,不同于传统纪录片中作为导演意志附庸的“众声一词”的采访,后者只是导演观点的图例而不是间离的思考。3.新纪录中导演的采访声音、导演作为角色、影片的摄制过程出现在完成片中的自我反射手法,提醒观众反思纪录片的真实是有假定性的,还满足了观众揭开电影的神秘面纱的心理期待。不过,通过自我反射手法达到的间离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作为影片角色的导演,导演过分地炫耀和煽动也会诱使观众失去批判意识。
6、强烈的反讽意味
保罗·亚瑟在总结新纪录的特征时说,“新纪录电影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杂交……但是,新纪录最显著的品质是把影片的摄制过程和制作者浓厚的反讽意味明显地中心化,表现出一种失败的美学”。(22)正如埃罗尔·莫里斯所说:“它们(他的影片)只能说明一种状态,它们都具有反讽意味。”(23) 新纪录的反讽意味是宏观的文体特征而不是局部文本的修辞手法,它不只是表现一种单纯的滑稽讽刺,而带着浓重的荒诞、阴暗、绝望甚至残忍的色彩,又使得观众以轻松,甚至娱乐的态度接受它,并达到认识层面上的新视角和多元理解。
当然,新纪录不同导演和不同作品的反讽意味则显得丰富多彩、强弱不一。埃米尔·德·安东尼奥的政治讽刺影片就不同于迈克尔·摩尔的政治讽刺片,前者是靠表现对象自身的表演和演讲以及严肃事件戏谑化处理,而导演不加任何解说,只是通过剪辑控制叙述,使影片中的叙述和人物形象与公共媒介或大众惯性视野中的叙述和人物形象产生强烈的反差和对照,通过两个不同语境的互文释义而产生强烈的反讽意味,如影片《米尔豪斯:一部白人的讽刺剧》(Millhouse:A White Comedy,1971)中那个自作聪明、好炫耀、卖弄学问、哗众取宠的尼克松完全对立于公共媒介塑造的美国尼克松总统形象。在这个冲突中德·安东尼奥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反讽。迈克尔·摩尔的政治讽刺纪录片无疑是新纪录影片中讽刺的最强音,但却不是最有力的反讽。摩尔的讽刺是以导演的叙述、自我反射式的表演、夸张的剪辑达到近乎于“直面斥责”的强讽刺。相对而言,埃罗尔·莫里斯影片的反讽显得深沉内敛、蕴涵丰厚、富于哲思,有苏格拉底对话式反讽的机智和妙悟。克劳德·朗兹曼的反讽则具有深刻的历史底蕴。“成熟的反讽只是陈述,让受众自己加上讽刺的调子。”(24)
五、余论
新纪录从70年代产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纪录片创作的主潮,改变着人们对纪录片的认识。新纪录在西方各国的稳定发展与它们有着相似的政治文化语境、深厚的纪录电影传统、开放的电影表达空间和完善的发行体系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30年的时间来拥抱西方两百多年积累的文化思潮和社会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相当不充分,它不能给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提供现实的思想武库。然而,随着纪录片国际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以及一批重要的世界纪录电影史与电影理论著作的引进和译介,新纪录对中国纪录片人的创作手法和纪录片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在世纪之交,准确地说是1999年初,中国纪录片理论界也逐渐提出了“中国新纪录运动”的理论,其声音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力图勾勒出一个中国新纪录运动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25) 的概念与本文所论述的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新纪录现象只是称谓上的巧合而无实质的联系。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新纪录运动”其实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开始,中国的纪录片有意识地从专题片中分离出来,开始寻找自己的方向,追寻独立的美学品格的一种状态,而不是一场意识形态上或者美学意义上的革新运动。
注释:
① 王宁,《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综述》,《文艺研究》1991年第6期。
② [美]杜威·佛克马、汉斯·伯顿斯,《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③ Paul Arthur.“Jargons of Authenticity (Three America Moments)” .Michael Renov edited, Theorizing Documentary,R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1993.p.127.
④ 罗伯特·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⑤ Thomas Waugh,“Beyond verité:Emile de Antonio and the new documentary of the 70s”,Jump Cut, no. 10-11, 1976, p.33-39.
⑥ Bernard Weiner,“Radical Scavenging: An Interview with Emile de Antonio.” Film Quarterly,No.25,Fall 71,p.3.
⑦ 同⑥,p.8.
⑧ 同⑤。
⑨ 该文也可以参见 Alan Rosenthal edited,New Challenges for Document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Los Angoles/ London,1988.p.56.
⑩ 转引自[美]琳达·成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580页。
(11) Paul Arthur.“Jargons of Authenticity (Three America Moments)”.Michael Renov edited,Theorizing Documentary,Rutledge,New York and London,t993.p.126-127.
(12) [美]琳达·威廉姆斯,《没有记忆的镜子》,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80页。
(13)(14) 保罗·亚瑟,《纪录片变脸》,《电影人》,孙红云译,《世界电影》2006年第6期。
(15) Bill Nichols,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2001,50.
(16) 参见埃罗尔·莫里斯网站(www.errolmoriss.com)的同名讲座。
(17) 2004年“中国国际纪录片节”北京导演见面会上的谈话,此段为笔者当时的记录。
(18) 同(11),p.127.
(19) 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20) Michael Rabiger,《制作纪录片》,王亚维译,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5页。
(21) Allison Pearson.Nick Nroomfield:The Fly in the Omintment.Michael Renov.Theorizing Documentary.R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1993.p.344.
(22) 同(18) 。
(23) John Conomos.Errol Morris and the New Documentary.The 47th Sydney Film Festival Writings.
(24)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5) 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