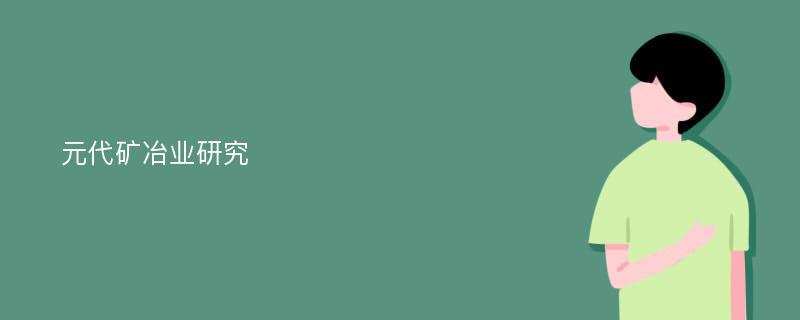
刘莉亚[1]2001年在《元代矿冶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政府重视矿冶业的发展,在其内部施以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其中矿冶业中曾同时并行过劳役制生产、个体小生产、雇佣劳动生产等多种生产方式,它们对矿冶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与此同时,元政府还设立了多级机构,制定出一系列管理政策、制度,体现了封建国家管理、调控经济的职能。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角度,力求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拟分四章加以阐述。 第一章介绍了元代矿冶业生产发展的概况,重点论述了作为元代矿冶业生产发展重要体现的边疆地区矿产开发与冶炼。第二章探讨了元代矿冶业内部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并简要分析了诸生产分配方式对矿冶业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第叁章介绍了元代矿冶管理的各级机构,分析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分工、权限及特色。第四章通过国家矿冶业管理政策的研究,探讨元政府管理经济的成败得失。
张毅[2]2011年在《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矿冶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矿冶业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时期矿冶业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直接推动着当时山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山东冶矿的开采在宋元时期颇具优势,尤以金、铁生产最为有名,这一时期的山东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但受地区因素及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又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本文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矿冶史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来探讨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第一章主要概括分析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主要矿产的分布、产量和相应的政府管理。古代山东地区的矿产分布相对集中,矿产特色明显,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由于宋元时期政治动荡相应制约了山东地区矿冶业经济的发展。第二章分别就金矿和铁矿展开探讨,对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业开采冶炼生产技术进行了研究。重点介绍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在开矿、采煤、冶炉、鼓风等方面的进步,最后还对农具制作的改进作了介绍。第叁章探讨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矿冶业内部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并简要分析了诸生产分配方式对矿冶业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第四章重点结合现存山东文物讲述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冶铸业。文章通过一些冶铸遗址介绍了该时期山东地区铁器制造业发展状况。第五章围绕山东地区流行的矿冶业行业神分析了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信仰文化。重点介绍了一些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碑,以及说明了行业神崇拜的影响。第六章主要论述了矿产品的流通及对山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探讨了宋元时期存在着金、银和铁的禁榷与通商政策。其次说明了矿产品开采流通对山东区域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影响。总之,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产以金矿和铁矿为主,主要的两大矿产分布相对集中。金矿基本分布在山东的鲁西和胶东地区,而铁矿则以当时的兖州莱芜监为主。山东地区的矿冶业发展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具有断续性。尽管山东地区的矿产开采冶炼一度在宋朝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限于当时政治情况,特别是北宋末年开始山东地区所在的华北平原成为宋、金、蒙等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角逐争夺的主要战场,经济受到极大破坏,矿冶业也一度中断。直到元朝中期稳定下来后,随着相应政策的出台,山东的矿产开采才取得了恢复。山东东矿冶业的研究不仅为全面了解宋元时期山东的经济增加一个视角而且对于今天矿冶业的管理也会起到以史为鉴、趋利避害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山东矿冶业的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刘明罡[3]2015年在《元代金银研究》文中认为同前代相比,学术界元代的金银研究十分薄弱,虽有单篇论文就元代的金银开采、金银赏赐、金银消费有所研究,但大都处于简单的点的研究,对元代金银的整体、全面的研究几乎没有。但金银作为元代重要的课税收入,对元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对元代金银进行深入挖掘既有助于对元代经济政策同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同样也有助于元代的政治制度以及国际关系的研究。元朝的金银作为重要的国家财富,既支撑着元朝的正常运转,又与元朝社会每个人的生活命运息息相关,尤其影响着周边国家的经济生活以及贸易往来。客观上金银成为元朝国家的财政手段,既能平准物价,又可开支军费、赏赉大臣,和买和籴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质如粮食、马匹等,是元朝钞法破败后的有力补充。同时,金银又是元朝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对象,也是元朝商业资本的重要来源,并在元朝与海外国家的香料、丝绸、珠宝等商品交易的环节内充当了世界货币。金银在元朝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它的身上可以投射出这一强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元朝以及蒙元时期的金银开采与冶炼,先后经历了蒙古灭金前、蒙古灭金至元朝建立、元朝统一全国前后这叁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金银产地以及金银产量都照前代有所恢复与发展。但由于金银矿产勘探与开采技术的停滞不前以及对金银冶户无偿劳役剥削的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加之生产开采的无序与混乱所导致的金银生产能力下降以及对自然环境破坏,都导致元朝的金银开采与冶炼虽处于一个旺盛期,但是却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元朝政府建立起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善的金银矿冶管理机构,为金银矿冶的正常开采与冶炼提供了保障。各地金银场提领所直接管理,各提领所由提举司或总管府提领管理;在较大的产区,提举司上设都提举司、总管府上设都总管府进行管理;这些专职机构又都直接受中书省监督与管理。其特点是对继承金、宋的矿冶管理机构,同时也有蒙古草原因素在内。而在元中后期金银生产数量却呈下降趋势,金银冶户也大量逃亡,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元朝矿冶制度自身特点有很大联系。元朝金银矿冶生产、管理与产品分配、收储等方面的规章与制度仍具有一定残酷性与掠夺性,是金银冶户生产积极性与金银产量下降的直接原因之一。元朝的金银流通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在元廷收紧货币政策,严禁民间金银流通时,金银作为钞法的组成部分与纸钞相权对换;在元廷放松货币政策,解禁金银流通时,金银又可作为国家财政手段进行运转和流通,但并未直接成为货币形式进入到流通领域。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金银在民间的使用逐渐合法化,并进入到商业领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元朝的金银流通仍然以国家的财政流通为主。此外,元朝与境外的金银流通大致经由两条路线,路上是由元朝经中亚各国至叙利亚同欧洲各国进行金银流通与贸易,海上则是由广州、泉州、庆元等港口出发同日本、高丽以及东南亚诸国进行金银流通与贸易。而元朝的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为以中国为起点的国际丝绸贸易,同时也为以中国为转运站的国际香料贸易提供资金保障,并成为茶叶、香料、丝绸之外中世纪贸易的重要商品。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元朝的金银开采使用与流通尽管经历了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政策的改变、文化的交融,但金银作为自然物的金银物质的根本属性不变。而作为“特殊商品”,金银货币的五种基本职能即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储藏手段与世界货币在元朝也有局部的丰富与发展。
沈卡祥[4]2017年在《明清时期滇东地区族群分布与地名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滇东地区地处川滇黔桂四省交界地带,长期以来就是各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理想的定居之地。元代以前,滇东地区虽时有汉人移民迁入,但因移民数量较少、分布地域分散,加之中央王朝对滇东地区的控制力不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汉人丧失民族特征逐步被“夷化”。元代滇东地区重新统一于中原王朝,蒙古人、色目人、僰人等族群纷纷以任官、驻屯、经商等形式进入滇东地区。元代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滇东地区民族构成和地名分布格局。元朝国祚短促,移民规模也有限,但是,元代滇东地区族群分布的变迁为明清时期族群和相关地名的变迁拉开了序幕。明清以来,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移民大规模的涌入,滇东地区族群和地名分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迁。首先,以内地移民为主体的各族移民的进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滇东地区的民族种类和民族人口比重。此外,内地移民大规模的迁入使滇东地区族群及其相关地名在地理空间分布格局上发生了剧变。明代内地移民主要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坝区及战略地位较高、交通较为便利的的交通沿线地区,同时,明代汉语地名也集中分布在这些地区。而在自然条件较差,土司势力较强大,未设置卫所的会泽、师宗、罗平等地区内地移民分布数量很少,这些地区汉语地名数量也较少。清代随着汉人向山区和会泽等移民新区的扩散、迁移,到清代中前期,滇东地区汉族无论在人口总数上还是在地域分布的范围上都超过了任何少数民族。随着汉族向山区和移民新区渗透,各类汉语地名也开始遍布滇东各州县山区和“移民新区”。明清时期,除汉族大规模迁入滇东地区外,也还有回族、蒙古族、彝族、布依族、壮族、水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进入滇东地区,滇东地区也随之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少数民族语或与之相关的地名。明清时期,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进入和中原王朝的行政设置,滇东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与内地市场逐渐一体化。汉人大规模的迁入也使得滇东地区汉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经济、文化内地化的助力下,滇东地区呈现出了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汉族融入少数民族和各少数民族间相互融合的民族融合趋势。
吴伟, 姜茂发[5]2008年在《元代矿冶业生产赋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代的冶炼生产方式较之唐、宋时期有很大区别,综观历元一代,在矿冶业中主要实行了劳役制、课额制和抽分制叁种生产赋课制度。不同的生产赋课制度对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对矿冶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大相径庭,从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来看,元代官营矿冶业中的劳役制生产赋课制度实行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劳役制生产制度与唐、宋时期相比是生产制度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性比前代大大加强,奴役程度加深。但是随着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课额制和抽分制生产制度得到恢复发展,最终出现官私矿冶并存的局面。
刘莉亚[6]2004年在《元代手工业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正文共分叁章。第一章官府手工业。本章论述了官府手工业的整体情况,包括官府手工业的叁种类型、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以及官府局院劳动者——系官匠户身份地位叁节内容。其中第一节划分了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元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营着规模庞大的手工业,按类型划分可分为中央政府在大都经营的手工业、中央政府在地方经营的手工业、地方政府经营的手工业叁类。这叁种类型的手工业,因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它们在经营的内容与各自的职能上有很大差别。第二节论述了官府手工业的内部管理情况。元政府为了保障官手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实施了一系列的管理举措,首先设立了工部、内府、武备寺等管理机构,对手工业进行管理;其次制定了一套包括对劳动人手以及生产各环节管理的措施。第叁节探讨了系官匠户的身份地位。元代,在官府局院劳动的主要是系官匠户,位列匠籍。虽然他们与其他人户一样,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享有与其他人户一样的法律地位,但在应役的具体环节上,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 第二章民间手工业。第一节对民间手工业的类型作了划分,元代民间手工业就其本身的专门性以及从业者的身份讲,可细分为家庭手工业与私营手工业两种类型。前者多为家内副业,是农业的附属;后者则不同,它的生产以盈利为目的,生产的商品化程度较高,其生产者往往是具备专门技能的手工业劳动者。第二节讨论民间手工业的商品化问题。民间手工业与商品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突出表现在,由于分工程度的不同,民间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出现了高、中、低叁个不同的发展形态。另外,随着手工业地区分工的发展,元代某些日用手工业品,还实现了跨区域的商品流通。第叁节论述了元政府的手工业、矿业政策。元政府的纺织业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家庭纺织业,制定了奖励农桑、提倡小农发展丝、麻、棉多种纺织业的措施;二针对民间私营手工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内容涉及对织造式样、规格、质量的详细要求。元政府的矿业政策则突出表现在:鼓励开发边疆地区矿产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允许私人采炼、交纳矿课的举措上。 第叁章寺观手工业与投下主贵族手工业。第一节初步探讨了元代寺观手工业的大体生产状况。寺观经营的手工业,就其类型讲,属寺观内部成员集体所有制性质,较为特殊。经营的内容,大部分是与日常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诸如粮食加工业、榨油业、制茶业、药品加工业等等;此外,由于元代寺观经济力量强大,一些重要的、资金投入大的行业,如矿冶业、酿酒业等,寺观也多有经营,这是元代寺观手工业经济的一个突出特色。第二节介绍了元代颇具特色的政治群体——投下主贵族手工业经营的情况。元代投下主贵族经营的手工业规模大、范围广,其中有些行业,如军器制造业是官府特许经营的。另外,在它内部不但有专门的手工业机构(比照官府机构设立),还有隶属自己的工匠——怯怜口,因此就它的性质讲,具有公私两重性,也是较为特殊的手工业类型。
綦保国[7]2011年在《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具特色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经济管理理念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本质的差异和冲突。今天,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虽然其政治经济学基础与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完全不同,是建立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但借古鉴今,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有制经济在富国强兵,集中力量办大事,增强国际竞争力,节制私人资本,限制贫富分化,促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等具多领域可以发挥与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类似的作用,但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百般弊病,尤其是权贵经济的祸患、贪官污吏的肆虐,足以引起世人的警惕。这也是笔者选择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进行探索研究的主要目的。根据笔者的研究目的和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论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共五章: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建立的政治经济背景、思想文化冲突、产权基础以及立法过程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实体分析部分,共叁章,即第二章元代官营造作手工业的法律规制,第叁章元代官营课程手工业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元代官营商业的法律规制。本部分在充分占有翔实的法律史料基础上,首先,从静态的角度,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地文献分析,考证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具体法律制度、经营模式、管理规范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法律措施;其次,从历史的纵向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元代主要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产生、形成及其嬗变的历史过程;再次,通过典型案例的补充研究,揭示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运行情况和法律规制效果。第叁部分是总结评析部分,即第五章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评析。主要是在分析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及功利价值、主要流弊的基础上,总结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历史个性,反思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利弊得失,以期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就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而言,本文具有开拓性。除此之外,本文可能的特色和创新之处还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就研究的意义来说,本文将研究的目的置于西方经济私有制与中国传统经济公有制、西方自由经济与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文化冲突背景之下,不仅凸显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而且为笔者研究本文提供了原初的动力和勇气。而就研究的对象而言,本文选题定位具体,十分务实,且直指要害。中国传统封建经济是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主导、管理国家经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手段和制度就是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因此,本文选题以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其“以小搏大”“知微见着”意蕴十分明显。其次,本文十分注重对“社会生活中的法律”、“社会运行中的法律”进行研究。笔者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关注有关元代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立法及体现于一定文本的法律制度,而且把法律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更关注社会中的法律,即法律在社会中应用与运作过程及社会效果,法律与政治、法律与经济等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更为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活法”的研究。其具体体现如下:一是本文不仅注重对元代法史文本如《元典章》、《大元条格通制》的研究,而且注重搜集和分析元人留下的大量奏章、笔记、戏曲、诗歌等文献资料,挖掘元朝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事实”。二是本文不仅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法律文本和法律条文,而且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运作状况及法律效果,也即法律的具体运作情况。叁是本文极为重视对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本身进行研究。过去,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中,往往总是就法制谈法制,而对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漠不关心,结果是法律条文罗列了不少,但人们对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仍然知之不多。本文十分关注元代官营工商业经济的运行过程,从生产资料的产权属性到劳动力的来源与法律地位,从官营工商业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到产品、收益的分配制度都纳入了本文的研究视野。四是本文不仅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产生、形成、演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而且还注重研究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和影响,试图对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社会效果、利弊得失给出合理的评价。再次,本文将元代官营手工业分为造作手工业和课程手工业,将其作为两种不同手工业类型分别进行研究,分类更合理,逻辑更清晰。以往的官营工商业研究成果中,要么将官营课程手工业与官营造作手工业统称为官营手工业进行研究,由于两者的职能、目的及具体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它们混为一谈,很不合理;要么将官营课程手工业法律制度与专卖制度合并在一起进行讨论,但结果往往只关注官营课程手工业产品的流通制度即专卖制度,而对官营课程手工业的宏观调控制度、生产管理制度、产品分配制度不作重点研究,甚至留下空白,这是很不完整的。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起源于西周的“工商食官”之制,经秦汉,历唐宋,制度历备,内容代丰,可谓一脉相承。然而,其历史功过、价值利弊,自古也是人们争议的焦点。言利而害义,富国而伤民,溢上而损下,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因此累遭世人诟病。本文以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标本,对其立法背景、规制内容、运行状况、社会效果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考析和论述。通过这些考析和论述,可以看出: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唐、宋旧制。官府直接经营管理大量工商业经济,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为皇室贵族和各级政府提供各种消费品和奢侈品,为国家财政节约货币开支并获得大量利税收入。然而,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民族文化背景,就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价值意义而言,元代的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挫长扬短,将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百般弊病暴露无遗。究其具体原因,既有法律运行的政治、法治环境的原因,也有其制度本身缺陷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蒙古少数民族的权贵政治重利轻义。元代是一个蒙古少数民族强势统治中原汉地的朝代。由于元政权在政治上过度依赖蒙古权贵,在经济上处处维护蒙古权贵的经济特权,在文化上重利轻义,因而他们经常将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作为榨取人民超经济利益的实用工具,只知取之于民,不知用之于民,急敛暴征,岁司羽鸠。其二、产权基础家族性导致的分配不公。元代官营工商业,只是在经营管理法律制度上继承了前代的管理模式和方法,而事实上因产权基础不同,其代表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完全与唐宋不同的生产关系,其分配制度是“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原则的具体化。这必然导致元政府泛赐滥赉,财政入不敷出,疯狂地榨取汉地民众。第叁、“各依本俗”的法治差异。基于“各依本俗”的法治原则,元代蒙古权贵仍然适用大汗国时期的自由工商业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兴办投下工商业,甚至部分禁榷工商业。这种不一致的法治制度,使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打击地方豪强势要及节制富商大贾的政治、经济作用大打了折扣。第四、直接劳役制经营模式的落后。元代官营工商业手工业劳动者最初就是来源于“唯匠屠免”的战争俘虏,其使主将他们称为“驱口”。入元之后,直接劳役制一直是元代官营工商业的主要生产经营形式。元代官营工商业劳动者虽然不是奴隶,但在国家强制下几与奴隶无异。相较于宋代的召募制、承买制,元代的劳役制无庸置疑是历史的倒退。第五、经营管理的监督机制不完善。从纯粹经济学分析来看,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控制问题,因而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监督机制肯定是既昂贵而又不完善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元代更是如此。贪污成风、非法盘剥严重、生产成本高昂、经营效率低下,诸如此类的制度弊端,都在元代官营工商业经营过程中暴露无遗。元代的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在恢复和促进元初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官营工商业发展成果被少数蒙古权贵攫取,广大中原民众沦为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的受害者,被无情地剥削和压榨,最终导致官贪民穷,民穷则国也不富,国民经济陷入民不聊生,经济崩坏的境地。这种历史教训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和反思。总之,本文集法学、史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一体。本文研究的是过去,思考的却是现在,因为笔者一直有一种信念: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背负着过去走向未来的,过去与现在不仅不可割裂,还能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
胡小鹏, 狄艳红[8]2006年在《略论元代的矿冶制度》文中研究表明元代各种矿藏的开采和冶炼最初均由政府控制,官府拥有大量的矿冶户计,采用劳役制生产方式,对矿产品实行禁榷制度,企图独享其利。但在现实情况冲击下,宋金时代曾普遍实行的课额制和抽分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矿冶业逐渐向民间开放,最终出现官私矿冶并存的局面。
刘莉亚[9]2003年在《元代国家各级机构的矿冶业管理权》文中研究说明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矿冶业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其中 ,在中央机构中以中书省、制国用使司、尚书省的作用最为突出 ,它们对矿冶业的管理全面而宏观。中政院、徽政院管理矿冶业是元代矿冶业的一大特色 ,其职责范围仅限于对其所属矿产的经营与管理。地方机构中以行省的职权最重 ,作用最为重要 ,体现了它作为中央派出机构的特色。路、州、县叁级行政机构则以兼管矿课为其主要职能 ,而这一职能与它们作为国家财赋征集者的身份相吻合。
靳阳春[10]2011年在《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文中提出客家学的研究多以客家界定、客家源流、客家精神、客家文化等等为主要对象,对客家经济发展则关注较少,尤其是对宋元时期闽粤赣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客家民系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尚无专门研究。本文选择“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作为题目,以解读史籍文献为基础,辅之方志及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重点研究汀州交通、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具体内容。本文认为,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原与福建的交通路线对历代南迁入闽移民活动的基本方向与走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南迁入闽的北方汉人基本从闽北进入福建。闽西始终处于国家权力扩展的边缘。直到唐宋以降,闽西山区才逐步得到开发,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是汀州第一次接受大批北方移民的时期,两宋之际是汀州第二次接受大批北方移民的时期。交通也随之发展。九龙溪航道在唐代就已经开发利用,在唐宋时期其重要性要高于汀江。南宋绍定以前,汀江出于自然开发状态。南宋后期,汀江航道得到改善,为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奠定基础。元代隆兴至潮州驿道的开通使汀州成为赣闽粤边区的重镇和交通枢纽,促进了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汀州经济发展。北宋时期,矿冶业是汀州的支柱产业,南宋时汀州矿冶业处于没落阶段,元代则处于停罢状态。南宋时期,私盐贩卖成为汀州经济生活中大部分人赖以谋生的重要产业,是后代汀赣间进行钱粮贸易的滥觞。以汀州为中心的私盐贩卖参与者成分复杂,而且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一直延续到元代。宋代汀州的集市层次非常完整,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表明宋代汀州的对外交通需求因为政治原因,依然以闽北为主。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大范围的活动中,生活在以汀州为中心的闽粤赣地区的各个族群相互之间增进了交流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新族群。汀州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不断。北宋时期,汀州的社会冲突危害轻微。南宋汀州动乱由百姓与政府争利的经济冲突,演变为以推翻地方政府为目的。宋末元初,汀州抗击元军的军队多为购募,中后期义军以“复宋”为口号,汀州的动乱已经演变成为带有强烈民族反抗意识的斗争。宋元时期汀州的文教有了较大发展。汀州的教育机构完备,理学有所发展,并以汀州为中心形成了定光佛信仰圈。文教的发展促进了汀州社会风气的变化。南宋时,汀州形成了一种融贯土客的新风习,促进了客家文化形成,最终以汀州为中心形成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后,与相邻而居的畲族携手合作,经历了宋末元初直至元朝末期的长期畲汉联合抗元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畲汉族群互相融合,主流是畲民汉化,壮大了客家民系。经过这场波澜壮阔的联合斗争的洗礼,客家人的族群性格得到很大的磨练和提升,客家民系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的高潮。
参考文献:
[1]. 元代矿冶业研究[D]. 刘莉亚. 河北大学. 2001
[2]. 宋元时期山东地区的矿冶业研究[D]. 张毅.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3]. 元代金银研究[D]. 刘明罡. 河北大学. 2015
[4]. 明清时期滇东地区族群分布与地名变迁研究[D]. 沈卡祥. 云南民族大学. 2017
[5]. 元代矿冶业生产赋课制度研究[C]. 吴伟, 姜茂发. 山西大学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 2008
[6]. 元代手工业研究[D]. 刘莉亚. 河北大学. 2004
[7]. 元代官营工商业法律制度研究[D]. 綦保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1
[8]. 略论元代的矿冶制度[J]. 胡小鹏, 狄艳红.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9]. 元代国家各级机构的矿冶业管理权[J]. 刘莉亚.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3
[10]. 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D]. 靳阳春.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工业经济论文; 手工业论文; 移民欧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法律论文; 移民论文; 工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