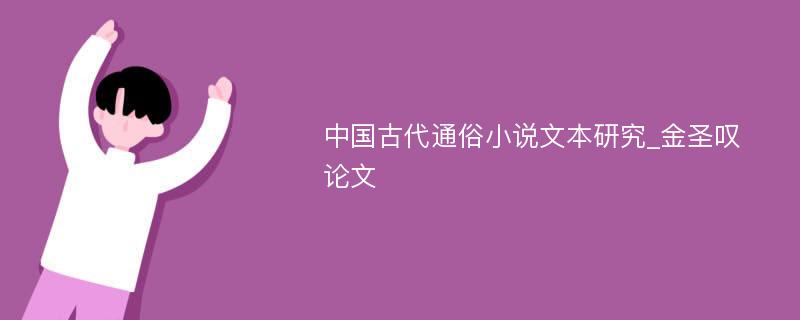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通俗论文,版本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成为一门显学,至今仍然盛行不衰。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文献相比较,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从而为版本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亟须深思、有待解决的课题,如“一书各本”的现象、文本“原貌”的追寻、不同版本的价值等等。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水浒传》的版本最为纷繁复杂。本文即拟以《水浒传》作为例证,针对上述问题,谈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敬请学界同仁指教。本文以《水浒传》版本作为例证,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而不拟对《水浒传》版本本身进行深入研究,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一 “一书各本”的现象
版本指一部图书经由抄写、刊刻等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实物形态。一部图书问世以后,在流传过程中,由其著述背景、制作背景与流传背景所决定,往往产生文字内容或外观形式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这就是“一书各本”的现象。在“一书各本”之中,根据各本的书名、卷数、次要作者、文字内容、版式行款等方面是否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往往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版本系统。
问题在于,一部图书在问世以后,或经主要作者(即一部图书问世之前的原作者)修改增饰,或经次要作者(即一部图书问世之后的整理者、增删者、修改者、注释者、校点者、批评者、翻译者等)增删改易,从而导致“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互有出入或多寡不同的现象,这在中国古代书籍出版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作品,从来就没有关于“著作权”或“版权”的政策法规,也没有约定俗成、行业共遵的出版惯例,“谁都可以任意修改,不仅抄时可以改,就是刻时也可改”(注: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第70页。)。因此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一部通俗小说作品往往经过次要作者或多或少的增删改易,甚至于“一书各本”的内容面貌相去甚远,造成不同版本正文文字内容歧异纷呈的复杂状况。
以繁本《水浒传》为例,从“文繁事简”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百回本和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杭州容与堂刊百回本,到“繁简综合”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安徽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在情节内容上增加了征田虎、王庆二十回,全书正文文字内容也作了许多修润改写;再到“腰斩断刻”的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刊金圣叹(1608-1661)七十回本,则既有情节内容的减少,如将百回本七十一回以后的部分尽数砍掉,也有情节内容的改易,如将百回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另外杜撰一个“惊噩梦”的结局,此外在文字内容上也作了大量的删削改动。
如果说上述三种类型的《水浒传》版本的区别,主要还是正文中大段情节内容的增删改易,那么,“文繁事简本”与“文简事繁本”两种类型的版本之间,在情节内容、语言文字、写作风格、审美效果等方面则存在着全方位的巨大差异,两相对读,不能不给人以“面目全非”、“判若两人”的感觉(注:关于“文繁事简本”与“文简事繁本”的差异,参见何心《水浒研究》“四、简本与繁本的不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73页。)。早在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汪道昆,1525-1593)就说:
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指《水浒传》),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去,既已可恨。自此版者渐多,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浑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赭豹之文,而画蛇之足,岂非此书之再厄乎!(注:天都外臣《水浒传序》,《忠义水浒传》卷首,明万历十七年新安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转引自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页。)
稍后胡应麟(1551-1602)也说:
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庄岳委谈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那么,这种正文文字内容相去甚远的“一书各本”,是否仍然同属一书呢?易言之,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的差异是否应该确定一定的限度?如果说“量变终将导致质变”的话,那么,“一书各本”正文文字内容差异的限度,能否以一定的量化标准加以确定,在这个限度之内“各本”仍属一书,越过这个限度“各本”即各属一书呢?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版本研究中,这的确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
其实在古今中外各种类型图书的版本研究中,这都是一个有待思考和解决的难题。姚伯岳说:“所谓正文的文字内容基本相同,意思是各本正文的文字内容可以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不能超过某种程度范围,就是说不会使人看后以为是看了几部不同的书。至于这个限度具体应怎样掌握,是很难一概而论的,只好因书而宜了。”(注: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不会使人看后以为是看了几部不同的书”,这未免主观性太强,而缺乏客观性标准;而“只好因书而宜”,其中的分寸也实在难以拿捏。
我认为,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所谓“一书各本”的正文文字内容基本相同这一原则,大致可以非常宽泛地容纳次要作者对小说原作的下列著述行为:(一)发凡起例的整理,(二)添枝加叶的附益,(三)删繁就简的删略,(四)修饰润色的修订,(五)逐字逐句的校勘,(六)分句识读的标点,(七)注音释字的注释,(八)条分缕析的批评,(九)不同语种的翻译。所有经由这些著述行为而产生的版本,包括整理本、增订本、删节本、改写本、校勘本、标点本、音注本、注释本、批评本、翻译本等等,仅仅构成一部图书不同的版本系统,而不是另起炉灶,构成一部性质不同的图书(注:至于一部图书“狗尾续貂”的续写本、“依样葫芦”的抄袭本、“改弦易辙”的改编本(改编成不同体裁的作品)等,则不属于“一书各本”的范围,而另成为一部图书的续书、仿书、改编之书。)。
持此标准,在马蹄疾《水浒书录》“上编”著录的《水浒传》众多版本中,无论是中文的“文简事繁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还是“其他文种翻译本”(注:马蹄疾《水浒书录》上编“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0页。),它们都同属一书,仅仅构成一书的不同版本系统而已。它们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显著,如何巨大,都仅仅属于《水浒传》不同版本系统之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说,一书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具有显著的、甚至巨大的差异,这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难点。在阐释学的意义上,我们固然可以说“文简事繁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等是不同的《水浒传》;但是,在版本学的意义上,我们却应该认定它们都属于一部《水浒传》,只不过分别构成不同的版本系统而已(注:因此,所谓“两种《水浒传》”、“两种《红楼梦》”的说法,在阐释学的意义上是合理的,在版本学的意义上则是讹误的。“两种《水浒传》”说,见张国光《〈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两种《红楼梦》”说,见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二 文本“原貌”的追寻
文本是指书面的或口头的、具有一定形式结构和意义的、具有交流功能的作品本身。正因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不同版本系统之间往往具有显著的、甚至是巨大的差异,因此,能否恢复一部作品的文本“原貌”,或者说恢复一部作品什么样的文本“原貌”,便成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一部图书在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中,其文本“原貌”往往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从创作过程来看,作者一生可以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著作,从绝对意义上说,只有到作者去世之时,他的著作才能最后“固化”为所谓“定本”。因此,有可能在作家在世时就出现一部图书有多个文本的现象(注:如白居易在世时,即先后由元稹编成五十卷的《白氏长庆集》,自编六十卷、六十五卷、六十七卷、七十五卷的《白氏文集》。这些各自不同的文集,不仅篇章、卷数逐次递增,而且因为辗转抄录,正文文字也当互有异同。参见万曼《唐集叙录》“白氏文集”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9-240页。),那么,在没有作者本人作为最后仲裁者的情况下,哪一个文本可以被认定为该图书的“原貌”呢?从流传过程来看,一部图书同时或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由于传抄、刻板等的原因,这些不同的版本往往会出现正文文字的各种变异(如误字、脱文、衍文、错位等,包括抄刻者的无意致误和编撰者的有意致误),那么,在没有作者手稿本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哪一个版本或版本系统可以被认定为一部图书的文本“原貌”呢?因此从极端的意义上说,一部图书的文本“原貌”无疑是永远无法完全恢复的。
但是,一般地说,古代诗文作品大都还是会有作者定本的,经由作者写作改定之后,文本的文字内容即已固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也主要是传抄刊刻过程中亥豕鲁鱼之类的错讹,而不至于影响定本文本的“原貌”。因此,相对而言,要恢复古代诗文的文本“原貌”是可以有一定的客观依据的。我们可以综合一部图书的流传情况以及作者个人的语体特征、文体风格、创作心理等因素,尽可能近似地恢复古代诗文作品的文本“原貌”。
但是古代通俗小说作品则不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难以确定现存的哪一个版本是经由主要作者最终订定的文本,而且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次要作者往往随心所欲地对原作品加以改动,从而造成“世无定本”的状况。尤其是像《水浒传》这种“历代累积型”的通俗小说作品,各种版本歧异纷呈,在版本研究实践中,人们要判定其定本的文本“原貌”往往众说纷纭,要恢复其定本的文本“原貌”更是难以措手。
例如,即使可以推定现在所读到的《水浒传》小说最终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我们至今仍然无法确定成书时的《水浒传》是“文简事繁”的本子还是“文繁事简”的本子,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无法证据确凿地判定究竟是先有“文简事繁本”还是先有“文繁事简本”(注:关于是先有“文简事繁本”还是先有“文繁事简本”的争论,参见邓绍基、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41页。)。因此我们便无法论定,这两个版本系统的祖本,哪一个更接近于成书之初的《水浒传》“原貌”。
再退一步讲,假使我们可以认定“文简事繁”的本子接近于《水浒传》的“原貌”,但是在众多“文简事繁”的版本中,我们也无法确定哪一个版本是其他版本源出所自的祖本。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氏双峰堂刻《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卷首《题水浒传叙》端首眉批《水浒辨》云:
《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注:转引自马蹄疾《水浒书录》第1页。)
据此,在属于“文简事繁”系统的余氏双峰堂刻本问世之前,福建已有十余种“文简事繁”的《水浒传》版本行世,但却早已无从觅见,我们无法考定它们所依据的是一个祖本还是几个祖本。而且,由于经过书坊主的改正、删削和挪移,我们想要依据现存的余氏双峰堂刊于万历初(1573-1588)的《新刊京本全像增插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与刊于万历二十二年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去恢复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底本的文本“原貌”,也是困难重重的。
其实,除了有确凿无疑的手稿本或初刻本可资考证,对于许多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来说,其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易言之,如果没有确凿无疑的手稿本或初刻本作为凭证,任何对通俗小说文本“原貌”的追寻,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假设或猜想。假设或猜想固然是推动科学研究的动力之一,但是按照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的理论,如果假设或猜想是“不可证伪”的,那么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注:参见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34页。)。
然而,如果不能悬定一书的文本“原貌”加以追寻、考证与复原的话,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将会沦为漫无目标的琐碎工作。因此就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恢复一部图书的文本“原貌”,而在于恢复的是一部图书的哪一种文本“原貌”。
我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一方面,一书同一版本的各个复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外观形式与文字内容方面的差异,从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一书同一版本各个复本的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比勘和归纳,尽可能地恢复一书同一版本的文本“原貌”,尤其是恢复一书同一版本正文文字内容的“原貌”。另一方面,一书同一版本系统的各种版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也会产生外观形式与文字内容方面的差异,从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价值。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对同一版本系统各种版本的相同或相似特征的比勘和归纳,尽可能地恢复一书同一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尤其是同一版本系统正文文字内容的“原貌”。
例如,我们可以用芥子园翻刻大涤余人序本为底本,对校袁无涯本(除去田虎王庆故事的二十回),恢复“文繁事简”的《水浒传》郭勋删改本的文本“原貌”。我们也可以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容与堂本为底本,对校日本内阁文库藏容与堂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容与堂残本以及石渠阁补修本、四知馆本等版本,恢复“文繁事简”的《水浒传》百回本的文本“原貌”。我们还可以用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原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为底本,对校其后刊刻的各种七十回本,恢复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的“原貌”。至于那些“文简事繁”的各种版本《水浒传》,由于各本正文文字删改情况不同,前后源流关系也颇为复杂,因此几乎不可能恢复这一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甚至可以说这一版本系统原本就没有一个单一的祖本。因此对“文简事繁”的各种版本《水浒传》,我们只能通过同一版本的各个复本的比勘,恢复每一种版本的文本“原貌”。
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力图恢复一书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其本质乃在于求真,即求一书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之“真”。段玉裁(1735-1815)谈到经典校勘时提出:
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注: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一二《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清光绪十年秋树根斋刻本。)
他所说的“底本”,盖指历代经典注疏者如贾公彦〔唐永徽间(650-655)人〕、孔颖达(574-648)、陆德明(约550-630)、杜预(222-284)、郑玄(127-200)等人所依据的经典原本。可见,校勘经典应该首先求一书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之“真”,与此相同,要坚持古籍版本学存真复原的科学性,也只能以求版本之真为原则。焦循(1763-1820)也说:
校雠者:《六经》传注,各有师授,传写有讹,义蕴乃晦,鸠集众本,互相纠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误,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阅者参考之也。(注: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清道光四年扬州阮氏岭南节署刻本。)
“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阅者参考之也”,这不仅是古籍文字校勘的基本原则,也是古籍版本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一部图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各自有其一贯性,我们不应强行将它们混合为一。严格区分一部图书的不同版本,不使它们各自的文本混合为一,这既是版本之学的定则,也是文本批评的基点。混杂“一书各本”,为了恢复所谓一书的文本“原貌”,人为地制造一种“四不像”的版本,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之大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和1953年整理出版的两部排印本《水浒》(注:此二本均以金圣叹七十回本为底本,依照百二十回本加以校订。),1954年郑振铎与王利器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注:该本以明万历十七年原刻清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天都外臣序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为底本,中间插入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的田虎、王庆故事,合成百二十回,并作了详细的校勘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校订出版的《水浒全传》(注:该本以原商务印书馆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为底本(该书据袁无涯本标点排印),用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本中的校文加以校订。),为了提供“一个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的较为完善的本子”(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水浒全传》卷首《出版者的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都在不同程度上杂取不同版本系统的《水浒传》文本,拼凑为一个新的版本,这实际上违背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求版本之真的基本原则。以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水浒》为例,该社编辑部《关于本书的版本》说:
我们是完全根据金本的,但和金本也稍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本子是经过慎重校订的,要比金圣叹的本子完善。我们不仅除去了金圣叹的那些荒诞和反动的批语,而且把那些被他改坏了的地方,也依照百二十回本,改回原来的样子。(注: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本《水浒》卷首《水浒出版说明》,亦有类似的说法。见朱一玄《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89页。)
既然“不仅除去了金圣叹的那些荒诞和反动的批语,而且把那些被他改坏了的地方,也依照百二十回本,改回原来的样子”,还怎么称得上是“完全根据金本”呢?既然做了如此明显的改动,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要比金圣叹的本子完善”呢?
吴师道(1283-1344)《战国策校注序》说:“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注: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也应坚持这种“存古”、“阙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态度,这既是对历史、对古人负责,也是对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负责。
三 不同版本的价值
从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的实际展开状况来看,一部通俗小说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往往传本各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也往往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我认为,既然几乎不可能恢复一部通俗小说的文本“原貌”,而只能尽可能地恢复一部通俗小说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原貌”,那么,我们在进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时,就既没有必要对一部通俗小说面貌各异的版本或版本系统进行高低优劣的轩轾,也没有必要对一部通俗小说纷杂歧异的版本或版本系统进行整齐划一的规范。因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部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其各自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其各自的价值。研究通俗小说的版本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比较清晰地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而且更有助于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动态地考察通俗小说的历史存在方式和历史发展进程。
首先,在同一历史时期里,一部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正文文字内容的差异,适足以表现出不同的次要作者在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从而赋予这部通俗小说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以特定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内涵。
在明代中后期,社会上同时流传着《水浒传》的“文简事繁本”和“文繁事简本”。一般而言,“文简事繁本”大抵是“俗本”,作为水浒故事说话的辅助性的通俗读物,广泛流传于平民阶层中间;而“文繁事简本”则大抵是“雅本”,作为一种供案头欣赏的文学读物,则主要流传于文人阶层中间。《水浒传》这两种不同版本系统正文文字内容的异同,实际上映现出平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与文人阶层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之间的异同。李开先(1502-1568)《词谑》说: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侯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86页。)
崔后渠(铣,1478-1541)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而李开先、熊南沙(过)、唐荆川(顺之,1507-1560)、王遵岩(慎中,1509-1559)、陈侯冈(束)等人,同为嘉靖朝进士,被时人推为“嘉靖八才子”(注:《明史》卷二八七《陈束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371页。)。这批仕宦文人阅读的“一事而二十册”的《水浒传》,应属于“文繁事简本”系统。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不是梁山好汉“奸盗诈伪”的故事,而是《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的“序事之法、史学之妙”。其后李贽(1527-1602)称《水浒传》为“古今至文”(注: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中华书局1975年版。),将它与《史记》、杜诗等并列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注:周晖《金陵琐事》卷上,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袁宏道(1568-1610)推崇《水浒传》“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司马迁)失组练”(注: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九《听朱生说〈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也大都着眼于此。因此,《水浒传》“文简事繁本”和“文繁事简本”两种版本系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共存并在,无疑为我们研究明代中后期平民文化与文人文化、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通俗话语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关联、渗透和差异,提供了绝好的文本资料(注:关于民间叙事与文人叙事异同的理论辨析,可参见王丽娟《论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以“连环计”故事为例》,《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第108-118页。)。我们不应仅仅看到“文简事繁本”的文字过于简陋粗糙,便断言它们“最没有价值”(注:郑振铎《水浒全传序》说:“最没有价值的是那些‘文简事繁’的闽本。它们求‘文简’的结果,把百回本的原文,刮去了肌肉,榨出了血液,只留下一副枯骨架子,作品便完全被损坏了。”郑振铎、王利器校点《水浒全传》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其次,一部古代通俗小说往往在不同时期里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或不同的版本系统,我们可以从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正文文字内容的差异,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外在缘由,从而描述各个时期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迁,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水浒传》自从崇祯年间金圣叹删节、改易、批评之后,七十回本成为社会上最为通行的本子(注:关于金圣叹对《水浒传》所做的修改,参见何心《水浒研究》第94-114页。)。在这期间,《水浒传》的主要面貌几乎是通过七十回本得以反映的,人们阅读、评论的大都是七十回本。曾在明中后期盛行一时的各种“文简事繁”、“文繁事简”或“繁简综合”的《水浒传》版本,均成为过眼烟云,早巳退出传播领域了。直到1922年胡适写作《水浒传后考》时,还坦然地承认:在一年前“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本的《水浒》,其余的版本我都不曾见着”(注:《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94页。)。小说发展史不仅是作家创作史,而且更是社会传播史和读者接受史,因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只有进入传播领域的文本才真正具有意义再生的价值。因此,七十回本《水浒传》固然是“断尾巴蜻蜓”,固然是金圣叹“腰斩”经典的恶果,但是我们要追问:它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取代各种《水浒传》版本而独擅风骚?它具有何种独特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这种独特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满足了明清之际的读者什么样的“期待视野”,体现出明清之际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什么样的变迁?这种变迁又隐逗出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样的特征?深入地研究、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便可以借助一个生动的事例,从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的角度描述明清之际通俗小说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因此,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不仅仅是要通过对一部通俗小说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差异、优劣高下的考证鉴别,为现代读者介绍和推荐其最可靠的或最合适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应该综合运用异同比较法、源流梳理法、内涵阐释法、文化寻因法等版本研究方法,探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现象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探究版本现象变迁的方式与规律,探究版本现象产生及其变迁的文化因缘。
邹自振评议:
古代通俗小说研究难度不在于阐述思想主题与艺术成就,而在于理清各种版本之间的来龙去脉。版本研究是与文本专题休戚相关的,这也是数十年来诸多学者热衷于小说版本研究的原因之一。郭英德先生在明清传奇研究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又以难度较大的《水浒传》为例,强调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重要性及其方法,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论文提出“一书各本”的现象,认为研究版本的目的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不同版本系统均有其自身价值,不可简单地加以否定。论文针对古代通俗小说的特点而提出,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小说的阅读对象不同于诗文,除知识层外,更多是文化不高的市民层;小说除精神产品的属性外,其商品性更强烈。市民层不讲求文字的典雅而更多追求故事的有趣与热闹,也造成其版本的多样性。论文提出“一书各本”的概念,解决了阐释学与版本学叙述的不同,避免了类似“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等提法上的混乱。论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为了恢复所谓一书文本之“原貌”而人为地制造“四不像”的版本,认为这是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之大忌。论文认为可以通过不同版本的研究去探讨各个时期社会思想、审美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迁,为古代小说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值得商榷的是,可否将“一书各本”的现象改称为“同一题材,多种版本”?这样可能更符合古代通俗小说的实际情况。另外,小说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虽然探究十分困难但仍应探究,因为它还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