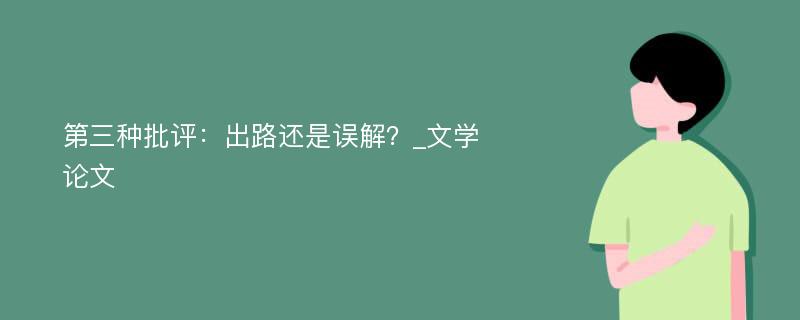
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种论文,出路论文,误区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种批评”试图改变文学批评的萎糜状况,为当代批评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应该说这种努力是难能可贵的。但其理论出发点存在诸多的矛盾与含混,又不能不令人置疑其自身的理论逻辑与实际的可行性。
就具体的论点而言,第三种批评也能自圆其说,倡导者当能在相对性的意义上来展开理论逻辑。正如任何理论设计都会有一种“理论的保护带”一样(拉卡托斯语),第三种批评也必然有其理论的保护带。关键在于理论的内核与前提设定。我试图从具体论述中找到他们的理论前提。我关心的或许是已经被认定为“真理”的那部分前提——而这一前提已经形成普遍的意识形态,它正在成为我们构建新理论的基础。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第三种批评倡导者的过错,这是隐含在我们意识中的天经地义的“真理”。
吴炫兄新近发表在《文论报》上的文章《知识转变的方法》,无疑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症结性的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路径却引起我的思考,吴炫解释说,“第三种批评”要发现中西方各自理论的长处,相对于当下现实的局限性——“从而建立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来统摄和超越这种局限”。吴炫认为:“出路就只能是提出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命题。不仅哲学是这样,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可能都只能是这‘第三条道路’”。【(1)】吴炫数年前曾出版《否定本体论》一书,这是一本非常精采并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其中可以看到作者具有非常丰富广博的西方现代理论知识。但我不清楚吴炫为什么要“超越中西方现有理论”。它的前提和结果隐含了某种不可能的本体论的梦想。
吴炫及其同道朋友提出第三种批评,强调要“提出新的知识命题和理论命题”无疑是正确的,但什么是“新的思维命题、思维方式”就值得考究了。而“统摄和超越这种局限”就更值得推敲。就“第三种批评”提出的理论动机来看(在这里并不仅仅限于吴炫的观点),显然是要超越现有的“中西方文艺理论”,从而创建新的批评体系。第三种批评这种提法表明,它的前提设想已经存在两种批评,一种是“西方的”批评,第二种是“传统中国的”批评,在这两种之外(或之上)可以建构第三种批评,即面对“中国现实的”的第三种批评。这显然是一种“元批评”的观念。这种观念以中西方的二元对立来派定文学批评的性质,给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超越西方理论,回到中国文化本位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则是第三种批评存在的实践依据。
我们可以说西方批评包罗各种流派方法,但要设想一个与东方中国对立的整体性的西方文学批评却有相当的难度。所谓“西方的”批评,是一个极其笼统而宽泛的指称,西方的文学批评存在着非常具体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区分。从历史时间来说,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主义时期,以及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相径庭;从地理学的意义来说,欧洲与美国的文学批评就不尽相同,而法国大陆学派与英美学派经常是南辕北辙。这里面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与东方(中国)截然对立。并不仅仅是说在差异性的意义上,不存在一个相对对立的西方文化,更重要的是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整合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的”——这种说法也值得考究。这个“传统中国”是限定在先秦后汉的“天人合一”,还是魏晋以降的儒道释三位一体的诗学传统?或是以宋明理学为底蕴的诗话词话?更不用说近现代以来的深受西学影响的文学批评理论。一个已经存在的或者说发生过的文学传统,它是历史对话,谈判(negotiation)、交流或流通(circulation)的结果。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始终存在某个地方的西方的或中国的批评。“元批评”并不存在。人们设想一种相对差异的中西方文化或文学的区分是可能的,但以此来构造一个宿命论式的、封闭的西方或中国的“元批评”模式,显然难以成立,而在此前提下,设想一个超越其上的“第三种批评”,更显得不切实际。一个很简单的实践问题,第三种批评难道不要涉猎西方/中国既定的知识体系?如果涉猎,如果与之对话,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于西方/中国的第三种知识体系或批评方法?如何区分,如何界定?
这种在中西对立的二元模式中来思考文学批评的历史,并且给理论创造打上民族—国家认同的印记的致思趋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内在冲动,它支配着现代以来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超越西方文化,重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建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图式——这一直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那些试图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保持中国传统价值的知识分子,也并非站立在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之外,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实践,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内部的持续张力。只要看一看中国现代以来的那些国学大师,他们中没有一人不与西学结下不解之缘。例如。辜鸿铭之于阿诺德、克莱尔以及一些19世纪浪漫派诗人,后者经常是辜氏论据的来源。梁启超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对现代化的质疑,与一次大战西方知识界的悲观论调不无关联。梁漱冥早年热衷于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某种意义上还是全盘西化派。当然转变后的梁漱冥是另一回事,但梁熟知西方文化,而且对西方给予泰戈尔的礼遇津津乐道,这也是事实。张君劢确认西方世界陷入危机,得益于艾柯、柏格森,特别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影响。张君劢早年对西化及现代化的怀疑,呼吁中国人停止模仿西方,理由主要是因为西方人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文明产生怀疑,张君劢对科学及现代化的抨击,这与他称道柏格森哲学如出一辙。强调中国文化本位,其实隐含着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内在情结,这与全盘西化的主张者,试图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达到同一层次的交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内心深处都隐含着对西方文化的恐惧。现代化一直被理解为西化,而西化显然是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失去自身存在合法性地位的最根本的威胁。设想超越西方,又不简单回到陈旧的传统,这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谈论了近百年的老话题,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化和知识的意识形态情结。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恐惧有增无减。第三种批评针砭的对象,主要是当前受到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影响的批评群落。称其为“群落”可能都有些夸大之嫌,实际不过寥寥数人,在尝试运用一些西方新近的理论知识来阐释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实。有一种观点是令人惊异的:运用西方新近的理论知识就是“照搬西方”,就是舶来品洋泾滨,而谈论西方古典时代或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知识,以及俄苏经典现实主义传统就不是“西方的”,就变成“中国的”?就文学批评这门学科而言,什么是“中国的”是值得推敲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主要接受西方的影响,建国以来的正统文学批评则承袭苏联的传统,尽管也会用到中国传统诗学的部分知识,但其主体结构,系统,术语概念,论证方式,都很难说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文学批评和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一样,是西方创立的学科,更准确地说,它是现代知识大转型的一部分。在这里,有必要区分“西学”与“现代知识转型”两个概念。过去,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一直用“西学”来指称西方的知识体系,这种指称在逻辑学和语义学的意义上当然无可置疑,但这种指称包含着与“东方(中国)”知识体系对立的意识倾向。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就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化的过程,更不用说西方的人文知识体系,更是包蕴着西方价值准则的“西学”。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东方的简单对立,而是从近现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问题,“现代知识转型”乃是人类文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标志。这种转变并不是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主义式的压迫和同化,而是自西方向东方运行的文明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西方也同样面临现代化转变的压力。并不是说西方世界就轻而易举兴高采烈地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西方社会同样付出各种代价(当然“落后的”东方代价要大得多)。只要看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就可以理解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是如何对现代文明转型持不信任态度。从浪漫派到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某种意义上就是抵抗现代工业文明的运动。抵抗现代文明转型的(相当一部分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构成了现代西方知识的一个主导部分。这种思想趋向直到八九十年代依然在起有力的支配作用。
就文学批评而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进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在某种意义上,英语文学是“骑在战时民族主义的背上才走向兴盛的”(特里·依格尔顿语),文学批评则是在寻求抵抗现代精神危机的灵丹妙药而在大学占据一席之地。新批评如此,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也不例外。现代知识转型在西方同样经历着传统向现代位移的阵痛,以至于八九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重审帝国主义文化,再次对现代的“知识构型”发出责问。但这种责问也依然是“现代知识”综合发展的产物。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欧美大学占据显要的讲坛,也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的综合运用,才发展出“后殖民”理论。现代知识就是一个悖论的复合体,一方面是人类知识的普遍性的大转型,另一方面又是各种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创立特殊性的价值准则。正如反抗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学艺术构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民族—国家”认同在现代性创立之初,其普遍性意义远大于其特殊性价值,或者说特殊性不过是普遍性的表达形式而已。如果说在政治上还有其特定的本土化的实践方式,而在文化上则是与普遍性对话、谈判的不同形式。就文学而言,其现代性的普遍性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特殊性。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本土化的“文化身份”认同并不强烈就足以明证。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艺术家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考虑“文学艺术”的本质,构成了其艺术创新的根本冲动。而在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展开的“拯救国民灵魂”的种种构想,同样是在现代性的普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生存状况与境遇。就艺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言,“启蒙”或“救亡”的宗旨实则是把中国提升到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水准;就纯粹的艺术审美价值而言,就更少民族或传统本位的构想,更多的是在现代文化的水准上寻求艺术的普遍性意义。
文学批评这门学科不过是现代知识转型的产物,这并不是所谓“西方的”,也不太可能是“东方(中国)的”,不存在什么第一种文学批评,第二种文学批评,因之也就无所谓第三种文学批评。只不过人们在运用不同的知识,探讨的都是“文学”这一普遍性的对象。既设想着东西方对立,又设想对这种对立的超越,这是一种本体论神学的自我虚构。植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策略,而由此派生出来的文化霸权看不出来对思想的自由表达有多大益处。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不过是在运用不同的知识,或不同的文化资源。文学批评更是如此。文学批评或许可以严格分为各种具体方法,但并没有哪种方法特别适合于西方,哪种方法更适合于东方(中国)人。在现代知识的流通领域中,很难设想哪些方法可以被界定为西方的,另一些方法可以被界定下为东方(中国)的。更难设想还有超越其上的第三种方法(或道路)。
事实上,警惕西学,标举学术和文化立场的民族本位,这在90年代正是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这与8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立。所谓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回到国学,重建中国本位文化……等等,都标示着回到本土的思想意向。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什么样的“本土”,拥有什么样的“民族本位”,我也看不出新近的西学到底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危害。如果说与当下的文化实践有相冲突的地方,那也主要是与既定的制度化的权威话语构成对立,我也看不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权威话语起绝对支配作用的结构中,能够获取多大的表达空间。人们已经忘却了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前提,却对西方新近的理论知识表示出莫名其妙的恐慌和仇视。我当然不是说新近的西方理论知识就无可挑剔,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实践中有许多的变易,这都是有必要重新清理的地方,但如果表示出本能的拒绝,并且固守住民族本位或想当然的第三种立场,很可能是为一种偏见所束缚。
文学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批评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实践,它的自觉存在方式应是它的知识品格。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知识的实践,只是社会历史的结构运动,将其编码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就知识的理想形态而言,事实上,各种知识总是不自觉卷入特定的意识形态。正因如此,在近四十年来意识形态危机的年代里【(2)】,由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始流行,并且与其他批评流派融合不断构筑新的知识体系。但现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与理论)致力于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并努力降低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至于它终究也无法逃脱被历史重新编码的境遇,又当别论。当代知识分子总是努力于摆脱意识形态的直接束缚,将知识的自由、宽容的运用视为自身理论建构的基地,这也是当代多元化知识形势得以形成的前提。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的任务,并不是要急于建构一种排他性的元批评模式,或是某种“个人话语”【(3)】——学术话语怎么可能是个人性的呢?个人性又如何交流呢?学术话语总是在多方争论、商谈、流通过程中才得以展布传播。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不是没有“个人话语”,而是过于个人化和随意性,同行之间没有认真、真诚、严肃的对话,同行之间很少引用各自的学术成果,甚至在批评对方时都很少引用对方的原文,有些干脆连名字都不愿提,生怕批评对方还让对方占了出名的便宜,这是对同行极为不尊重的做法,也可说是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例如在对“后现代”进行各种批评的文字中,我就很少看到有引述原文的文章,不着边际随意调侃,根本不顾及个体差异性。捕风捉影,攻讦成风,这是当前文学批评存在的严重问题。
归根结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急待完成知识转型。当代文学批评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苏俄模式上,术语、概念和独断论式的论证方式,唯我独尊的权威意识,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特征……等等,思想意识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体系的转换,事实上,相当多的同代人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例如,前面提到的吴炫的文章的题目就是关于知识的转变。但知识的转变没有必要设定一个中西对立的二元模式。在目前的历史发展阶段,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我们就认真向人学习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急着走第三条道路?急着说“自己的话”什么叫做“自己的话”?“自己的话”就那么重要么?独断论式的以自我为真理核心的话就真的是“自己的话”么?这就像中国足球一样,还没有学会踢球,就急着要踢中国特色。中国很多事情就是被自欺欺人的“中国特色”给弄得不伦不类。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意识到新的知识体系显然不可能在“个人的”自言自语的写作中产生。我认为大量吸取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优秀成果依然是一个建设性的基础工作,这需要文学共同体保持平静和务实的态度,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现代理论所达到的水平,了解现代理论已经走过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这可能更有助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文学批评没有种族,没有国界,正是使人类全体关注自身的普遍命运这一基本准则,才使得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永久存留下来。
注释:
(1)参见吴炫:《知识转变的方法》,《文论报》1997年5月1日。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引证吴炫的观点展开我的质疑,事实上,就我的有限阅读而言,吴炫关于“第三种批评”构想最具理论色彩。由于本文并非单纯与吴炫兄商榷,我的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并不是针对吴炫的观点。我想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点。
(2)意识形态的危机在美国可以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失败为表现形式,在欧洲可以60年代的法国左派激进主义运动(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失败为表征。50年代后期欧美学界对此问题曾有过讨论。可参见丹尼尔·贝尔著《意识形态的终结》,格伦科,1960年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的《政治家》一书,纽约,1960年。
(3)可参阅邵建:《作为“个人话语”的第三种批评》,《文论报》1997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