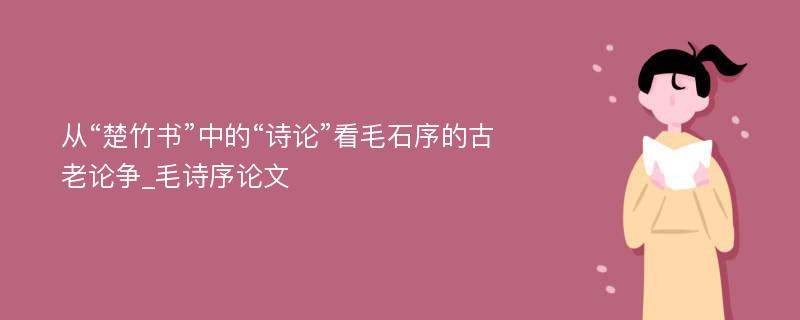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说论文,好色论文,诗论论文,毛诗论文,楚竹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1-0064-04
关于《毛诗序》的作者的争议,由来已久。东汉以后,长期在民间传授的《毛诗》日渐盛行。汉人重师门,毛诗之所出,在班固只是说“自谓子夏所传”,至郑玄作笺,则认定不疑,进而有陆玑、徐整排出的传授世系,遂成定论。而疑问也就由此而起。刘宋范晔有《诗序》作于卫宏之说,北朝沈重提出序有大、小,大序作于子夏,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唐朝钦定《五经正义》以颁发天下,争议稍歇。至宋,对子夏作《诗序》的质疑最为强烈,争议也最激烈,论争并延及清代。其实,论《诗》是否遵《序》,应以《序》是否合于《诗》为议题,本不在作者是谁。而古人之所以在《序》是否作于子夏的问题上聚讼纷纭,是因为,若《序》作于子夏,子夏亲聆孔子的言教,则《序》就是孔子的亲传,圣人教诲,自然不可有异议;若非子夏作,则非孔子旨,也就可以批评反对,阐述己见了。问题在于:即使《毛诗序》传自子夏,是否就能完全代表孔子的《诗》说呢?古人的争论,由于思维方式与材料的局限难以就《诗序》本身得出结论,而战国楚竹书《诗论》的问世,则给我们提供了重新探讨这一问题的机会。
战国楚竹书中的《诗论》(以下简称《诗论》),据测定,抄成于战国中晚期,它使今天的学者能够跨越二千多年的时空去亲近历史,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虽然《诗论》的作者也有争议,但多数人认为它传自孔子,作于子夏的可能性最大(如载于简帛研究网的李学勤的《诗论的体裁和作者》及江林昌的《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均持此见)。那么,《诗论》的内容就可以成为讨论今传本《毛诗序》是出于子夏还是有后人加入的一个参照。本文拟以关于《关雎》的评说来探讨楚竹书《诗论》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
《诗论》的二十九支简中谈及《关雎》者有四简,兹引录如下,以便讨论(为书写方便,本文所引《诗论》释文,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1]外,兼采李学勤《诗论分章释文》[2]。因为学者熟知,以下只标明“李说”以为区别。):
第10简:关雎之改,……何?曰:童而皆贤於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於豊。(李说)
第11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
第12简:……反纳於豊,不亦能改乎?
第14简:其四章则俞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李说)
虽是断简残文,仍可见出“以色喻礼”是《诗论》说《关雎》之诗的主旨。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故“以色喻礼”至少包含两层涵义,一是承认人的“好色之愿”,二是指出诗之借喻在说礼。虽是“以色喻礼”,却唯有承认好色是人之本性,才有设譬借喻之可能。而关于礼乐教化与人之情性本然的关系是先秦儒学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
儒家讲《诗》,重在教化,譬喻是常用的手法。《论语》中两次记录“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礼记·坊记》则称“子云好德如好色”。可以推想,以“好色”为喻是孔子比较常用的话头,这也许正是《诗论》以“好色”说《关雎》之所出。虽然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但是,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也有对人性问题的关心。孔子推崇君子的德行,提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由于德行在于后天的修习砥砺,于是从人性之自然好色而有德行修习之难的叹息。对于人性之本然,《孟子》则说得直截了当:“好色,人之所欲。”(《万章上》)在孟子看来,人皆有好色之心,圣人也不例外,他甚至举《诗》为证:“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梁惠王下》)孟子说,君主之“好色”若能与天下共之则无伤,而人之“知好色则慕少艾”,则可加以引导。故孟子之言“好色”,是从人之有所好的本性加以发挥而言人之修习向善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简单的设喻之言。荀子对情性问题最为关注,在《礼论》《正论》《正名》等章中都有专节论述,系统地阐明礼乐教化与情性本然的关系。荀子认为,情性之欲为人性之常,只有承认情欲为人之常性,才有奖惩引导的教化基础;但情性之欲,求而无得,得而不足,则天下乱,故“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故曰“礼者,养也”(《礼论》)。他驳子宋子之“寡欲”说,斥墨子之“去欲”说,以为是“小家珍说之所愿”,不明白“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的根本。因此,情性出于天然,虽不能为,然而可化。礼、乐、《诗》、《书》,教化之具,可以养生,可以养财,可以养安,可以养情,“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礼论》)。承认情性而以礼义养之,导之,与夫行“瘠则不足欲”,“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富国》),乃“是儒墨之分也”(《礼论》)。自孔、孟而至荀子,都曾以“好色”为题而说“好德”,并不否认“好色”为人性之常。荀子又对孔、孟之“好色”说作了理论性的发展,提出礼乐教化之所以可行是由于人有情性之欲,所谓“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强调的是礼义对情性的引导,并未将两者对立起来而视作互不相容。荀子将人之情性欲望视作礼乐制度的基础以莫定儒家的教化理论,使之成为儒家学说之区别于其他诸子的重要特色。
荀子生活在战国晚期,是《诗经》传授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强调人情有所同欲,乃礼义教化之可行,其说《诗》有同样的表述。《大略》云:“《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从表述形式上看,“传曰”以下是对“国风之好色”的阐释,则“国风之好色”应是儒家学说的一个肯定性的命题,相对于通常观念中对“好色”的否定,所以才在传授的过程中需要老师作出解说。而以“好色”来说《国风》,可见说《诗》者注意到十五国风中颇多情诗的实际,这与后来的经学家对此现象或视而不见或曲解辩护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这里的“传曰”,是指荀子的解释还是荀子所引的解释,无法认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代表了荀子的看法,则可以无疑问。“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愆,过也;止,犹“相鼠有皮,人而无止”之“止”,指合于礼的行为。这是说,既要满足人的内在欲望,但其行为又不可以没有节制,是在承认人之好色乃本性的基础上来讲礼义对行为的规范。“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指欲望出于本性,行为合于礼义,故其诗发于诚心,其乐可用于宗庙。这样说《诗》,注重的不仅仅是《诗》之文辞,更有诗人借文辞所表达的“思无邪”的情性,不仅在表达方式上追原于孔、孟的“好色”之喻,而且表现出了荀子承认情欲而规范情欲的教化思想。《毛诗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教也”,即与此同。《关雎》是十五国风的第一篇,这里的“国风之好色”也可理解成“《关雎》之好色”。那么,荀子之以“好色”说《国风》与楚竹书《诗论》之以“好色”说《关雎》,都是承认“好色”为人性之常而借以喻说礼义的教化,可以视为一脉相承。据此也可以解释《诗论》中存有异议的文字。
“《关雎》之改”的“改”,马承源释作喜悦之“怡”,廖名春释作改正之“改”,并引《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谓即改易风俗之意。[3]《诗论》中的四支竹简所论《关雎》在内容上显然是相互联接的,一曰“《关雎》之改,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二曰“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三曰“《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都围绕着“《关雎》之改”而言。其中,“关雎以色喻于礼”,即以“求女”喻“求德”,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故有“反纳于礼”之说;“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即以求女愿望的满足喻德行修习所达到的精神愉悦的境界,因而“其思益矣”。说《诗》者以“好色”喻“好德”,从人性之好的本然而进于君子追求的道德,从情欲的满足上升为精神的自足,故曰“贤于其初者也”。这里所谈教化,为人之情性教化,相比于尊卑上下的政治教化,是更为根本的心性之事,故立足于“君子”而言个人,虽与风俗相关,到底所指不同。马承源释“改”为“怡”,以为从“巳”。其实,“改”字从“己”,与“怡”同在古韵“之”部,本也相通,可以通作“怡”。故“《关雎》之改”的“改”,当从马承源之说,作“愉悦”讲。
总上可见,《诗论》以“好色”说《关雎》,是基于儒学“以礼养欲”的理论。这与《诗论》引孔子有“民性固然”之言,论《诗》则有“其用心如何”之问,应为同一思路。但是,比较一下《毛诗》之说《关雎》,却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好色”这一问题本是基于男性而提出的问题。孔子以“好色”喻“好德”,孟子说“好色”则有向善之心,荀子所谓“盈其欲而不愆其止”,都是以君子为要求,是针对男性而言。但在《毛诗》,“关雎,后妃之德也”,却是将“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好德”视作对女性的要求,其所谓淑女,即没有忌妒之心的女性。郑玄笺“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就说:“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东晋时,谢安欲纳妾而畏夫人,故使侄儿去做工作,侄儿遂在夫人面前称颂《关雎》“有不忌之德”,希望刘夫人以为仿效(《艺文类聚》卷35引《妒记》)。魏晋以后,《鲁诗》《齐诗》俱已亡佚,《韩诗》虽存而习者少,《毛诗》独盛,谢氏子弟因之引以为讽劝。讲《毛诗》者以“后妃之德”说《关雎》,用诗者自然以《关雎》为针对女性的讽谏之诗,这与《诗论》的“好色”说相去甚远。
第二,《诗论》曰“《关雎》以色喻于礼”,是以人的情性为喻而讲修礼好德,是以整篇诗所言的求女之事为喻。但在《毛诗》却说:“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则将关雎这一水鸟作为了喻体,既言其“慎固幽深”,又称其“夫妇有别”,以作为对女性的行为要求,并置于社会政治秩序之中来彰显其意义。这种譬喻的载体与意义都完全不同于《诗论》。后人由此而有对关雎习性的种种社会化的猜测,其牵强附会之荒唐,追究起来,《毛诗》是发其端者。
第三,《关雎》之末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联系孔子曾赞叹“《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可以体会诗末一改“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忧伤而呈现的欣悦之情。故《诗论》曰“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正是以音乐的娱悦比喻情欲的满足,进而比喻道德完满之时的精神欣悦。这是“养欲”之说的形象描写。但在《毛诗》却说:“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以不忌妒为后妃之德,有德乃可以事宗庙,则以道德来否定人的情感欲望,将礼义与情欲对立起来,因此郑玄就以“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的宗庙祭祀来解释诗中的琴瑟钟鼓,将欢欣之情变成了肃穆之事。
注重情性的教化而不是片面的行为规范,是先秦儒学的一个特点。卢文弨评说《荀子·正名》曰:“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旨推广之,极言人不能无欲,必贵乎导欲以合道,而不贵乎绝欲,此荀子之小家珍说而与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旨相合。后儒专言遏制净尽者,几何不以雍而溃矣!”[4](P228)孔子有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是从情性教化这一点上为儒学说《诗》者定下了基调。楚竹书《诗论》有此特点,上引荀子论《诗》有此特点,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毛诗》没有完整地保持这一特点。《毛诗·关雎序》通常称之为“大序”,在“《关雎》后妃之德”的篇旨之外,广论诗之特性及风雅颂之体,应是一篇集成之说,情性教化的问题是其论述的主旨之一,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论点就表达了自孔子、孟子而至荀子对于情性与礼义关系的一贯看法,与楚竹书之说“好色”也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关雎》之诗的具体解说中,《毛诗》的说法却与《诗论》以及荀子颇有区别。《毛诗》的特点在“以史说诗”,在解说一篇诗之主旨的“小序”中,几乎将每一篇诗都与具体的史事联系起来阐明其美刺之所在。郑玄为《毛诗》作笺,就据此而作《诗谱》,将三百○五篇诗与西周王朝的政治兴衰作对应。通观小序,《毛诗》之说在规范人的行为,情性问题不再是论说的主旨,并且一律视作“淫僻”加以斥责,而与礼义相对立。在这里,《关雎》之“好色”被扭转为对女性的情感强制,《桧风·隰有苌楚》曰“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陈风·月出》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孔颖达疏曰:“人于德、色,不得并时好之。”正是卢文弨所说的“专言遏制净尽者”。既然以《诗》为史,自可资史取鉴,故“以三百○五篇为谏书”在汉人就是顺理成章之言。但是,这样解说《诗》旨与孔、孟、荀的以《诗》为“讽咏情性”者已不在同一层面。
汉代传《诗》者四家。《鲁诗》的传授者申培是浮丘伯的学生,浮丘伯是荀子的弟子,故《鲁诗》出于荀子(《汉书》卷88)。《新唐书·艺文志》录“《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魏源《古诗微》引以为《韩诗》出于子夏之说。陆玑《毛诗鸟兽虫鱼疏》谓《毛诗》出于子夏,五传而至荀子,荀子传鲁人毛亨。似此,则荀子是由战国末至秦汉间传授《诗经》的关键人物。在《荀子》书中,引《诗》为议论依据的事例多,说《诗》之例少,要研究荀子《诗》论与汉代《诗》论的关系,尚缺少必要的参照。楚竹书《诗论》的问世,就在荀子说《诗》与孔孟说《诗》之间补上了重要的一环。虽然《荀子》一书尤重政治制度的论述,与孔孟论述之重思想修养有所不同,但重视人性问题则是一贯的。在《荀子》,不仅强调了人的情性之常,而且以之作为整个礼乐制度的建立依据,可以说,这是荀子的情性论对孔孟“好色”之说的继承与发展。楚竹书《诗论》之以“好色”说《关雎》,与荀子之言“《国风》之好色”,既为相承之说,而《毛诗》中“小序”往往是注重史事而否定情性,由此也就见出荀子说《诗》与汉人说《诗》的区别所在。
汉代的传《诗》者虽说出于荀子,但其中一定有继传者的增补与扩充。如,同出于浮丘公者,《鲁诗》之外,还有《元王诗》;辕固《齐诗》之后,又分出《后氏诗》与《孙氏诗》(见《汉书·艺文志》及《楚元王传》),这些《诗》既自立门户,也必有其师法家数以与其它传《诗》者相区别。这些汉代的《诗》学,在魏晋以后只有《毛诗》流传不衰,保留完整,因此由荀子而上溯子夏的传授渊源也就成为《毛诗》的一道光环,屏蔽了学者的质疑。现在由楚竹书《诗论》之说“《关雎》好色”可以见出荀子之说“国风好色”是孔孟以来以情性说《诗》的继续,那么,《毛诗》的变情性教化为政治讽谏,则似有后人学说的渗入。如果《毛诗序》的解说诗旨与荀子尚有差距,那么《毛诗序》出于子夏的说法就不可视作绝对,至少要在其内容上加以具体的分析。而《毛诗序》中哪些是源于先秦的儒家《诗》说,哪些是出于秦汉时期的传授者说,楚竹书《诗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参照。
[收稿日期]2003-04-03
标签:毛诗序论文; 儒家论文; 荀子论文; 诗论论文; 孔子论文; 国风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国学论文; 礼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