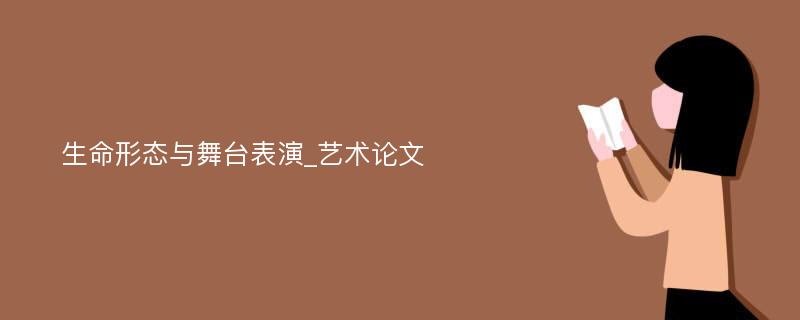
生活形式与舞台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台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剧作家和导演来说,积累生活都是一项基本功。而所谓积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积累生活形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在这五个“一切”中,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的特点,都要通过独特的生活形式表现出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年龄、性别,不同的教养、习惯,不同的个性的人们,都有不同的生活形式。生活形式与生活内容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生活形式也就无法把握生活内容。恩格斯说:“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怎么样做。”(《给拉萨尔的信——论革命悲剧》)这怎样做就是生活形式。因此可以说,把握生活形式是作家、艺术家认识生活、把握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和方法。
人们常说,文艺创作要从生活出发,实际上应是从生活感受出发,即是说客观的生活触动了作家艺术家,然后引起了他们感情的激动和理性的思索,这才引发创作的欲望。这触动作家、艺术家的首先是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戏曲表演不能照搬生活,戏曲舞台表现形式与自然状态的生活形式有根本不同,那么把握生动的生活形式对于戏曲作家、艺术家是不是重要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生活形式蕴涵的艺术魅力
在电影、电视、话剧乃至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中,生活形式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新时期以来,《黄土地》、《秋菊打官司》、《二嫫》等影片受到人们的重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影片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一些偏僻农村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作用,引起人们的联想。
近日看黑龙江省大庆话剧团演出的《地质师》。全剧只有一个场景,离北京火车站不远处的卢静一家,戏里没有正面表现石油会战的宏伟场面,也没有正面表现“文革”之类的激烈的斗争,仅凭人们的行为、交往、语言、装束等生活形式,却能够把观众带回几十年的历史生活的回忆中,使人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一曲《勘探队员之歌》使人们不仅回忆起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学生时代。卢静的妈妈给去东北的“骆驼”做的一条棉裤,既富有时代特征,又体现了多么深的母爱。刘仁、“骆驼”在大庆艰苦环境中弄得病残的身体及治愈又是这一代人坎坷命运的形象的缩影。
音乐、舞蹈中有不少作品也是重视生活的真实的。舞蹈《黄河儿女情》、《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等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广泛流传,也在于它们表现了人们质朴的生活形式。民族文化园的兴办,民族服饰的表演等等,也都是新颖的生活形式吸引人。
对于戏曲也是这样。我们说传统剧目丰富多彩,首先在于它所揭示的生活内容的丰富多彩。从宫廷的龙争虎斗到老百姓的拜年、借米、小放牛、打猪草,从人间的男婚女嫁,到天上的神仙聚会以及地狱里的鬼域世界,林林总总。有些戏表现了坎坷的人生际遇,如《秦琼卖马》、《平贵别窑》、《桑园寄子》、《伍子胥过昭关》等,武将卖掉心爱的坐骑、贫贱夫妻的生离死别等等,这都是何等动人心魄的生活形式!再如表现人际关系的,如《甘露寺》、《打金枝》、《金水桥》等,巧妙地把家国利害的考虑通过脉脉亲情和朋友关系等表现出来,人们正是看刘备怎样得到吴国太的喜爱而避免了一场灾祸,唐王如何对待打了自己女儿的女婿、秦英的母亲如何设法救下自己闯祸的儿子等这些生动的生活形式而饶有兴味。
传统戏里有许多表现男女爱情的剧目,因人物的身份、性格不同,恋爱的方式,状态也各不相同,即表现为不同的生活形式。比如《拾玉镯》,表现的是一个少女第一次遇到有人向她表露爱情时的心态,戏是通过孙玉姣掩掩藏藏地拾起傅朋故意丢下的玉镯,欲还又舍不得,后被刘媒婆看到,欲盖弥彰等一系列动作表现出来的。与拾镯相串插还有轰鸡、做针线等细节,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的生活形式才把这个农家少女初恋的情感表现得那样细腻,这种纯真美好的情感使观众得到观赏的愉悦。
《游园惊梦》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家闺秀,受到封建礼教的严密束缚,她连坐在家门前做针线、喂鸡的自由也没有,她对爱情的向往被压在心底。一朝到春天的花园里赏花,对爱情的要求便被诱发出来,但又只能在梦中追寻。
再如《烤火》,一对青年被强迫成婚,关进洞房,少女碧莲看到倪俊是一位至诚君子,想向他托付终身,倪俊却理智地觉得不能与碧莲相爱。这样一种关系是怎样表现的呢?聪明的剧作者把他们安排在山寨上的寒夜,山大王给了他们一盆火,于是两个青年通过让火、争火等动作表达了各自的心思和情感,大胆的进攻和谨慎的防守,全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非常引人入胜。
戏曲现代戏更是以“生活气息浓厚”见长。所谓的生活气息浓厚,即是指这些作品表现了丰富多彩的新的生活形式。早期的现代戏,如《白毛女》、《血泪仇》等把新旧社会做了强烈的对比,黄世仁的逼债,杨白劳的喝卤水,喜儿被迫卖身还债,黄母在佛堂打骂喜儿等生活形式,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有些戏表现了劳动群众笑着与自己的昨天告别,比如马健翎创作、延安民众剧团演出的《大家喜欢》,表现一个二流子从被迫劳动到自觉的改造过程(当年是黄俊耀扮演),他拿镐头刨地,横拿竖拿都不带劲。去年看陕西戏曲研究院青年演员演出,仅这一个拿镐刨地的动作,就以其传神的“象”,引起观众阵阵的笑声。新中国建立初期,有一批表现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现代戏,《罗汉钱》里的燕燕偷偷给心上人一枚罗汉钱,《小二黑结婚》中小芹借洗衣到河边等小二黑等等,是那时男女青年谈恋爱的特定形式,而包办婚姻、媒婆说媒、订婚要看命相、大姑娘配小女婿等落后现象、也成为真实的、富有喜剧效果的生活形式。
50年代中期以后,剧作家艺术家则从沸腾的劳动和建设中汲取戏剧素材,在豫剧《朝阳沟》中,拴保教银环锄地,“那个前腿要弓,后腿要蹬”,以及栓保妈与银环妈这样两位性格不同的亲家在一起拉家常,“亲家母,你坐下”,也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唱段。
新时期以来,戏曲现代戏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有的戏通过普通的生活形式揭示了人物美好的心灵和深厚的情感。如豫剧《能人百不成》中,白世成的奶奶把他从小带大,一心只盼孙子生活幸福,听说孙子已有对象,要送彩礼,她在灯下取出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包,细数多年来一分一角积攒起来的钱,这一数钱的动作,引起观众热烈鼓掌,因为它表现了老奶奶多么深的情!京剧《圣洁的心灵》中孔繁森在灯红酒绿的大饭店外边的小摊上吃拉面,以及离家时他哥哥送他钱,让他做“清官”,都是普通的生活情节,但它都因表现了人的美好的心灵和真挚的关系而具有动人的力量。
有些戏在有特色的生活形式中揭示了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些戏具有浓郁的韵味。比如采茶戏《榨油坊风情》,榨油的劳动号子伴随着人们生活的节奏,结婚仪式上的“撞酒歌”更把人们情感的冲突推向高潮。彩调剧《哪嗬伊呼嗨》中彩调艺人与自己的“玩艺儿”生死不离,艺术与人生浑然一体。吉剧《关东雪》里的人们生活在大风大雪的环境中,在冰下刨鱼招待客人、因雪大压塌房屋、畜圈等情节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而云南花灯戏《金银花竹篱笆》展现的却是云南农村的风情。一道竹篱笆隔开两家,因观念和劳动方式的不同,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差异,于是又引起了思想狭隘的“壳壳虫”对全婶、银花一家的嫉妒和怨恨。这种邻里关系又是通过种花、雇工、说亲等一系列生活情节表现出来的,一股鲜花一样芬芳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二、生活形式是进行舞台创造的基础
但是戏曲艺术确实与话剧、影视艺术有显著不同。话剧、影视重再现,戏曲重表现,或者说是在表现中再现。在几种社会功能中,戏曲除重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外,也更强调要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因此它更强调要在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舞台创造,而不能原样照搬生活形式,在这一方面,前辈艺术家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且形成了一套带普遍性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戏曲的程式。程式既然是前辈艺术家创作经验的积淀,那就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戏曲的舞台创造中,是不能轻易抛弃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前人的创造是流不是源,只能做为今人进行创造的借鉴,而不能代替今人的创造。
在建国以来戏曲舞台艺术的创造中,大致可分两种路子。一种主要是各地方剧种,创作者重视从生活中撷取素材(生活形式),按照戏曲艺术的规律加以改造、夸张、美化,使之成为生动、新鲜的舞台表现形式。比如骑自行车这一动作,是传统戏曲中所没有的。1958年,导演张建军在现代戏《张四快》中,借鉴马鞭代马的原理,用车把代自行车,创造了骑自行车的身段舞蹈。新时期以来,骑自行车舞蹈有很大发展。在豫剧《风流女人》中,导演用双人舞不仅真实地表现了信贷社王主任骑自行车带杨花走在崎岖山路上的状态,而且传神地表现出两个人一个乘机要挟、一个不失分寸地防守这种复杂的关系和心态。在评剧《黑头和四大名旦》中创造了一场骑自行车的多人舞,把车间主任黑永春与四个调皮的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发展变化富有情趣地表现了出来。
京剧等古老剧种传统比较深厚,形式相对凝固,所以导演和演员在进行舞台创造时,常常先要考虑“可行性”。即运用、改造和重新组合哪些传统的手法可以更好地表现新的生活。导演阿甲和演员李少春等在京剧《白毛女》中就成功地进行了这种创造。然而这一创造之所以成功不仅在于创作者熟悉传统,而且在于他们也熟悉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从塑造新的人物和表现新的生活出发,就能赋予传统表现手段新的生命力。
这两种创造过程:一种是借鉴传统改造美化生活形式,一种是依据生活运用、改造、重新组合传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向。有扎实的生活基础,从不同的方向出发,可以殊途同归。但若生活基础不扎实,创作者不熟悉不掌握丰富的生活形式,完全依靠传统的手段来塑造新人物,势必给人以陈旧感,长此下去,创作的灵感就会枯竭。
随着物质技术的发展,舞台表现手段也日益丰富。比如灯光的作用,已不限于照明,它可以出情感,出节奏,可以给人以美感,从而成为塑造人物、体现思想的重要手段。灯光的灵活运用,改变了舞台的叙述方式,克服了舞台布景的许多障碍,从而也可打破剧作的习惯结构。这一方面的发展方兴未艾,有广阔的前景。但是如同借鉴传统不能代替生活积累一样,运用新的技术手段也不能代替新的生活形式的追寻。如果生活贫乏,新的技术手段也是掩盖不了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文章《舞台是演出生活的场所》(着重点为引者加)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在文中指出当时俄罗斯舞台上存在的一些现象:一些新的成果、发现,新方法、理论、手法都非常短命,未及开花,就调谢了。“为什么所有的新东西都遭到某种有趣的玩具那样的命运?人们一下子扑向新东西,然后大失所望,然后弃置不顾,接着又醉心于另一种更加新的、更加短命的东西。”他指出,“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为形式而形式;缺少内容的形式,不善于创造内容的形式(掩饰空虚的形式)。这是臆造出来的形式。是招贴画,是粗暴地解释那个同样的粗暴倾向的招牌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形式取代了真正诗人的剧作的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译文载《戏剧春秋》1995年第5期)
重复一句,我们现在在形式上的创新还很不够,在这方面还应认真学习,积极探索;但在进行舞台形式创新的探求的同时,切莫忽略生活形式这个基础。一个戏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做深入考察,只看表面现象,认为某个戏的成功在于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于是你上台一百人,我上台二百人,想在这些地方比高低,便本末倒置了。1996年岁末,我看了两台话剧,一台是在北京看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商鞅》,一台是在福州看的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沧海争流——郑成功与施琅的故事》。前者在舞台上呈现了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军马、战车,古朴凝重,气势恢宏;后者仅用了一般的转台和多层平台。但两台戏都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因为它们都以生动的生活形式展示了壮阔的历史画面,揭示了历史人物的心灵。
三、舞台创造——追寻比生活形式更高的形式
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这就使它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强调歌舞的形式之美,一是具有讲故事的叙事性。二者结合起来,就要求它的形式需是有意味的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说明生活形式对于戏曲舞台创造的重要。同时舞台上表现出的生活又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因此舞台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追求比生活形式更高的形式。
所谓更高,一是要比生活更美,二是要比生活更感人。把普通的语言、动作加以音乐、舞蹈化实际上就体现了把生活形式美化并使之更感人的原则。优秀演员的一段唱、一段无声的表演可以引起满场的掌声,可以催人泪下,就是这个缘故。所以说唱做念打是表演的基本功,也是进行舞台创造时首先要下力气的地方。不重视这些基本表演手段,而只注意场面调度之类,是舍本逐末。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视吸收借鉴,努力革新,使唱做等等更美,更感人。
戏曲可以使美的生活形式更美,不美的变成美。比如生活中病残、疯癫、酒醉、死亡等等,都是令人厌弃引不起美感的丑恶现象,但在戏曲舞台上却可以用精彩的表演表现出来。《贵妃醉酒》、《太白醉写》、《宇宙锋》(赵艳容装疯)、《疯僧扫秦》等,都围绕醉、疯演出动人的戏;《盘肠大战》、《挑滑车》等负伤后的表演和壮烈牺牲(“僵尸”)都成为既有观赏性又有感人力量的表演。
有些不宜在舞台上直接表现的场面,如男女的欢会,在戏曲舞台上可以含蓄而又美丽地表现。随着观念的变化,有些过去回避的生活形式,今天也可表现得很好。如女人生孩子,过去认为是污秽,在京剧《洪荒大裂变》等作品中,却以优美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对生命的赞歌。
“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高则诚语)为了增强感人力量,传统戏曲常采用重复的手法以加深印象。传统剧目中以“三”命名的不少,三上轿,三击掌,三盗盒,三滴血,三盖衣,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打白骨精,三打陶三春以及十八相送等等,在重复中把意蕴向深层推进。
比重复更有力的是传神的夸张。最典型的例子是川剧《射雕》中嫂子把花荣和含嫣二人“视线”结在一起,用虚拟的手法把无形的视线当成有形的线,拉之可动,弹之有声,这是把戏曲的特点发挥得最充分的绝妙的创造!它最有力地说明了舞台形式与生活形式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可以有怎样显著的不同。但这只能是经过长期积累的神来之笔,如果随意模仿和搬用,便会失去新鲜感。
舞台表现贵在对生活形式的发现和创造。常见的形式如能赋予新意也就是新的创造。如恋人之间、亲人之间因反目而打耳光在现代戏中已用得太滥,但豫剧《儿大不由爹》中一个耳光却“打”得好。老头对儿子生气,无法发泄,却没来由地给了来劝解的老伴一个耳光,老伴没想到老头会这样(这在他们多年的夫妻生活中也是少有的),她一愣之后还了老头一个耳光,老头更没想到老伴会这样,又一愣,但两个人不是继续发火,略一停顿之后,都感到刚才的行为不对,于是互相去揉对方的脸。这样就把这一对多年相依为命的老夫妻一场特殊矛盾的迸发用特殊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对于戏剧来说,由生活形式到舞台表现,要经过剧本文学的中介。所以二度创造很重要。剧作家写剧本时,心中要有舞台,但他们往往更重视文学性,即使舞台性较强比较适于演出的剧本,要搬上舞台也必须经过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比如湖南花鼓戏《八品官》中“驮妻离婚”是最精彩的一场。队长刘二坚持原则,违反了妻子桂英的“约法三章”,桂英闹着要到公社离婚。路上经过一条河,桂英要刘二背她过去。在这过河的耳鬓厮磨中,两个人回忆起结婚以来种种亲密的情景,于是打消了离婚的念头,这是多么有戏剧性的一场戏。但我看到早期的演出中,刘二真的把桂英背在身上,这样唱做都很吃力,也不能给人美感。后来别人建议,如二人转那样,改为两个人一高一低象征背在身上的舞蹈,表演就方便多了,也更美了。
再如郭启宏的昆剧本《司马相如》中有司马相如三过青云桥的描写。他看到达官贵人颐指气使的样子,也立下必求显贵的决心,在桥上写下“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第二次乘上了高车驷马,于是踌躇满志地涂去了两个“不”字,改成“乘高车驷马过此桥”,但不久又被罢了官,再过此桥,不知题词如何修改才好,索性改成不带任何附加语的“过此桥”。这是一种很有文学意蕴的描写。但在舞台上怎样表现?一次听导演苏民讲,开始他很为如何设计这题词费心,后来青年导演卢昂把第一次题词写在天幕上,后两次改题词只在台词中叙述,并不改舞美设计,这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方法,这样做得到苏民的赞赏。但再想一想,这一情节是否还有动作性更强的表现?能否使这一情节更具喜剧的形式和悲剧的意味?
从认识生活、积累生活、把握生活到表现生活,从一度创造到二度创造,生活形式都是一个关键。希望大家能更重视这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