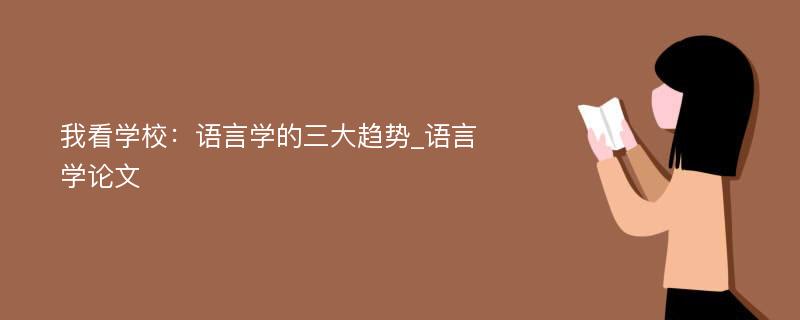
我看流派——语言学中的三大潮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三大论文,流派论文,学中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本文以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为对象讨论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探讨不但在语言学界,甚至在整个学界都很少见,哲学务虚不算。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判断、评价缺乏逻辑标准,(朱晓农 1990a)所以只注重眼前结果。科学的根基是逻辑,所以重推导过程,重程序。方法论就是讲究这个程序,讲究运作程序的逻辑机制。而重结果的后果就是为了向往的结果可以不择程序;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各种取巧心理,结果是没有原则、没有目标、没有程序、没有自信,当然也顾不上普遍性。下文所谈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如有不当处,请方家指正。
2 从追踪历史来源到演绎逻辑关系
19世纪的科学在追踪本原,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都是历史研究。历史主义(注:说“历史主义”是从后世对他们的工作性质的认识来说的。其实,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是“自然主义”,持一种“有机”语言观。在拉斯克、施莱赫尔、缪勒等等眼里语言像自然界的有机物,有生老病死,但没有“历史”,因为他们注重的是个体之间的同一性,而忽略因时间地点造成的个体差异。因此,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历史学。) 假定语言也有生长老死,所以探索语言演变的过程,直至起源。方法无非是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当年胡适回国,口口声声科学的方法就是这两法。没想到在那之前,语言学已经开始转向了。
语言学中的目标转换是从20世纪初索绪尔(注:其实区别出共时和历时语言研究还有更早的,Dittrich在1903年就已经用了synchronie和diachronie这两个词。(转引自钱军1998:108)) 开始的。其实这是当时或稍早时科学和哲学界大转向的一个小插曲。科学上的理性主义转向以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出现为标志。在哲学上,实证主义先驱、法国人康德(Conte)说:“探索那些所谓本因[案指历时原因]和目的因,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绝对不去做的,也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完全不想陈述那些造成各种现象的动因,因为那样只会把困难往后推。”他认为“人类精神如果不钻进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仅限于在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是仍然可以在其中为自己最深入的活动找到取之不尽的养料的”。(详见朱晓农1987—88)看看康德的观点,就可明白为什么当时语言学界讨厌“钻进”语言起源之类“无法解决的问题”、转向“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内进行共时研究背后的大气候了。
但是,只要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时间的演化性,那么就免不了要上溯追踪起源问题。起源的假说哪怕再不合理,理性认识的程序上还是少不了,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起点,一个逻辑起点。那就是为什么牛顿要那个“第一推动”,这跟“唯心”“迷信”不搭界。19世纪对语言起源的种种猜想并不比第一推动更唯心,那只是在当时科学水平上的认识。一旦科学取得进展,现在又有很多新的探讨了。
对于西方人来说,共时还是历时,必须两者择一。共时的问题一旦求助于历史的解释,立刻引出大麻烦,逻辑上开了个口子,就会没完没了地追到时间的尽头,那就跟本原探究没区别了。解决历史问题有过形式化的努力,如半个世纪前赵元任(Chao 1941)对中古音的音位处理,高本汉(Karlgren 1954)不以为然;还有人(如Bynon 1977)试图建立语言演变的结构主义模型和转换生成模型,结果都不了了之。
所以要么历时,要么共时,不能骑墙,不能掩饰矛盾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重要,那也少不了”,不能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无原则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逻辑必须彻底!论证能走到哪儿,全看演绎法能带到哪儿,跟走不走极端无关。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折中的态度都对科学不利,都会把研究引向玄辩特色,都会重复几千年来矛盾辩证糊涂循环的阴阳五行传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不可以,但至少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没有逻辑矛盾。从这逻辑要求来看,玄学就不用去说了,就拿历来受人称道的“务实慎立论”的朴学来说,的确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优点,也作出过巨大成就,但要适应现代科学的需要还须进行诠释:“实”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实,这是唯一坚实的务实基础。而务实要为创新服务,而不是为不作为(“慎立论”是“不立论”或“述而不作”的委婉说法)作借口。记得吕叔湘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强调“务实创新”,意思是“务实为创新服务,创新建于务实之上”。也就是说,“务实”如果阻碍了创新,就不是真正的务实;“创新”如果不建立在务实之上,大概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当时强调“务实”还有其特定背景。那时玄虚的“文化语言学”在一些文化相对后进的地方蔓延。那些年我有幸每过一两个月去吕先生家亲炙教诲,有一次吕先生对我说,那种“学”离“禅”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吕先生的嘱咐是有极强的针对性,也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朱晓农 1988b)如果抽掉语境、片面强调,就不再是吕先生“务实创新”的原意,会起到反作用,会引起打不完的“语录战”。如果要脱离语境一般地谈方法论,可以从科学的两个步骤——随机探索(假设)和逻辑评价(检验)——出发来讨论。(朱晓农 1987)
3 确定逻辑条件和公理化
共时探讨逻辑条件用的是形式化方法(formalization, formalism),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axiomalization)。公理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万物皆数”的观点。(注:毕达哥拉斯的高徒菲洛拉乌(Philolaus)说:“一切能理解的事物,都具有数;因为如果没有数而想像或了解任何事物,那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出现了最早的但至今仍可作为范式的公理化研究: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逻辑学。现代的公理化研究,起点就是几个元素,几条公理。公理可以是元素的定义,(朱晓农 1990)也可以是陆丙甫(2002)所说的“很简单的常识”。音韵学中区别特征的发现或发明是一个追求基本粒子追到尽头虚实转化的典型例子。换句话说,把实物切分到最后,不是像墨子所说的“万世不竭”,物质切到最小竟成了性质。朱晓农二十年前也朝此方向努力,不但探求汉语语音的元素(区别特征),对音系做公理化构筑,(朱晓农 1983)甚至还着手把语言学中最意义的领域(复句和修辞格)加以形式化,甚至公理化。(见朱晓农1989c,1990)
语言学中的形式化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结构派的搭建分类系统,到生成派的营造规则系统,再到自主音段派的构筑公理化系统。戈斯密(Goldsmith 1976)的声调研究是公理化的一个好例:H、M、L是他的元素,像是点、线、面。连接规约(Association Convention)是他的公设或公理,“元音和调素从某根连接线之后自动一一对应”像“两点之间有且仅有一条直线”;“连接线不交叉”更是像平行公理在语言学中的翻版。
形式化有三个标准:自恰性、完备性和简明性。从静止的角度来看,只有第一个逻辑要求“自恰性”(即内部无矛盾)是必要的,第二个实践要求“完备性”(对内周延而对外排他)和第三个美学要求“简明性”(独立公理数,推导过程,所构筑的系统均简明)都不是必不可少的。换一个动态角度来看,自恰性是起点要求,从一开始构筑一个形式化系统就必须具备的。完备性是终点要求,是某项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而简明性则是从起点到终点之间的途中要求。(注: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操作中简明性原则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需引进辅助标准,见后文§4最后一段。另外,起点简明,即独立公理数目少,往往导致过程繁。专家理论上的简单,并不一定实际操作简单。) 在研究过程中,常常有各种竞争性的模型,中国特式的思维(秦人逻辑)是不讲、也没法讲(因为没有亚氏逻辑)方法程序的,他靠的是悟,“取舍之间,一得之愚”,就这么说者满意听者犯晕地解决。形式化工作当然不能如此,要有个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简明为优。
使用形式化方法来研究汉语音韵古已有之并取得辉煌成就,最早是受印度声明学影响创造的韵图。从音位学到现在,更是成果累累。近年来冯胜利(2000)、端木三(Duanmu 2000)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他们都是从某个基本单位(冯胜利的“自然音步”、端木三的“非核心重读”)出发建立起整个理论体系。
4 “解释”的解释
有人在谈到历史来源和本原时用“本因”“目的因”一类词,也有人在谈逻辑条件时会用“原因”。但我们前面只说历史来源和本原,逻辑条件和逻辑端,而不说原因和本因。这是我有意避免的。我要把“原因”留给下面的实质/还原主义,留给物理条件,留给“因果律”(cause-effect)里的那个“因”。
形式化里的A→B(if...then),这个A最好就叫“逻辑条件”,简称“条件”,而不要叫原因。因为A→B是否成立全看假定的初始条件(元素和公设)。初始条件重新设定,逻辑结果也跟着改变。
至于历史来源,最好也不要叫“原因”,他可能是原因,但只有在时空齐一性的条件下得到证明才能算。在历史学范畴内谈“原因”是件危险的事,(朱晓农 1989b)一则我们的学术传统没这习惯,“秦人不懂演绎法”;二则按照信奉胡塞尔现象学的钱钟书(个人通信):“一个简单现象可以有很复杂的原因,很繁多的原因,而且主因未必就是通常认为是重要的事件或因素”;三则有些被认作原因的事件往往只是时间上的巧合,由于历史事件不像物理事件那样可以重复,所以要分清历史事件间的先后关系(sequence)和因果关系(causation)就多了一重困难;四是常会把一些实质上是“缘”的事件误认为“因”,其实“真正的原因叫做因(cause),而一时触发的媒介叫做缘(occasion)”。(潘光旦 1941)
因此,同样是“解释”,历史主义指的是历史来源,形式主义指的是逻辑条件,实质主义指的是广义的物理原因。
历史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用新的“发现的逻辑”的观点,是一种“反溯法”(the method of abduction)。这个术语以前译成“外展法”,后又有译成“溯因法”的,意思是明确了,但“因”这个词要留给cause-effect中的广义的物理原因。而反溯法所溯的可能是时间上的来源,也可能是逻辑论证上的充分条件,还可能是广义的物理原因。所以译得含糊些——反溯法。此外,反溯法是倒推追溯,不像实质主义和形式主义,还要顺推作预言。
形式主义的“解释”是指明逻辑条件。一般认为结构主义是“描写性的”,而后来的生成派和现在的功能/认知派都是讲究“解释”的。但照我看来,谁都在做解释,只是“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我曾讲过“解释”的五个方面:A)指明时间顺序,即找到来源,追到底就是本原;B)指明因果关系,追到底就是本因;C)指明构成成分,追到底就是元素;D)指明所属系统,指出他在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他跟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A)是历史主义的历时解释;B)是实质主义的泛时解释;C)、D)是共时解释,也就是静态共时描写。共时状态中的描写或解释只是相对于不同层次而言,上一层的描写可成为下一层的解释。对D作动态描写,即为:E)指明系统运作时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机制解释。
结构派做的是C)和D)的解释,生成派加进解释E)。因此我把结构派也归入形式派,尽管后来的形式派——生成派——跟结构派打得天翻地覆,那是兄弟阋墙。我的判断标准是:哪些东西能取而代之,哪些东西就一脉相承,那么就是一个派的。生成音系学可以取代结构音位学,非线性音系学可以取代线性音系学——它们都是一派的。但结构语言学取代不了历史语言学,功能/认知语言学也难以取代形式语言学——它们都不是一派的。
形式派音韵学中的“解释”处理,往往有多种选择,这只要看看二十年来五花八门的汉语区别特征矩阵就可以明白了。(吴宗济 1980;叶蜚声、徐通锵 1981;朱晓农 1983;陆致极 1987;钱乃荣 1988,1990;吴宗济、林茂灿 1989;曹剑芬 1990;王理嘉 1991;林焘、王理嘉 1992;罗常培、王均 2002)相比之下,朱晓农(1983)的最可取。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判断标准是:结果最简明,即特征数最少,区别元、辅音一共只用了九对。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明确的程序标准,即帮助确定哪些特征入选,哪些排除的一条充要性标准:少一对不足区分,多一对即成赘冗!前半句是充分性——需要的一定要,体现了解释性。后半句是必要性——不必要的不要,最终体现出简明性。这条充要性标准是判别特征矩阵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国内研究区别特征的文章也不算少,矩阵本身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白用什么方法、什么标准得出的。这样从小处说,理论才有改进的余地;从大处说,科学才有进步的动力。当然,简明原则说说简单,真正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把握。有时音库简单了,规则却繁琐了。(朱晓农 1999,2005a)这是形式主义方法论的固有问题,所以我们是得不到唯一正确答案的。说他是“固有问题”还是轻的,实际上形式主义认识论与作为非自定义系统的语言之间有着天生的矛盾。
5 齐一性和实质/还原主义
语言在时间过程中有演变性、在地域分布上有差异性。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reductionism)的梦想就是想消除这种由时空不同带来的“解释”任意性(这儿的“解释”又是一种意思:特设性假设或自成一家言的特色学问),取得研究对象在时空上的齐一性(uniformity, uniformitarianism)。
还原主义也可以追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圣四”(tetraktys)的观念,圣四代表构成万物的四个元素:水、火、土、气。任何事物都可以“还原”或“简约”为这四种元素的不同组合。我借用“还原主义”这个术语表示的是“语言非自足,语法非自主,语料非自备”的意思。逻辑实证主义最早用还原主义这一概念来表示“高层次”的规律可以用“低层次”的规律来解释。按这种解释,语言学可以还原为心理学,心理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进而还原为化学,最后到物理学。
还原主义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名词,因为一方面乔姆斯基也把语言学“还原”为心理学,进而生物学。当然他本人并不真的想做,而是留给了心理学家。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语言学问题都能还原的。这对任何系统都一样,系统的问题并不能完全还原为成份的问题,原因在于还有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所以,在语言学中探求广义的物理原因的也许该叫做“实质主义”(substantivism),他把还原主义包括在内,但含义更广。“实质主义”一词借自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该学科中也有形式派(formalists)和实质派(substantivists)的对立,后者把经济活动理解为是在维系整个文化秩序。
语言学中的“还原/实质主义”可以说是刚刚出现,那就是实验音韵学、社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这可以从“原因简约”和“时间泛化”两方面来说。
首先说时间泛化。所谓“时间泛化”,在认识论上即是打通历时和共时的隔阂;在方法论上就是“以今释古”,也就是Labov(1975)说的" use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第一代历史语言学和第二代共时语言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时间维度。但在还原主义看来,可以用一个“泛时观”来统一。泛时观把共时变异看成是潜在的音变,而历时音变则是实现了的、固化了的变异。也就是说,把分布上的差异性化成时间上的阶段性。“泛时观”这个概念见于朱晓农(1988a),更一般的即是“时空齐一性”。它之所以能够建立,得力于两方面的进展:类型学(Jakobson 1958;Greenberg 1978)和社会语言学。(Labov 1975,1994)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进行。利用语料库进行类型学研究,可以看出普遍的模式和独特的分布,从而发现问题所在。(刘丹青 2001)把社会语言学引入汉语的研究,十几年前林焘、沈炯已经开始了。(如林焘1985,沈炯1987,林焘、沈炯1995)近年来沈钟伟(1997,2002)的研究更是为社会语言学的一般原理提供了新的定量模型。他的基本观点是音变归根到底是一种可观察的个人/社会现象,其原理和新产品、新概念、甚至流行病的传播相似。
其次,再说“原因简约”。音变的原理、机制并不是独立的、“原生”的。我们的嘴巴喉咙活动服从生理学解剖学,我们的听辨服从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我们的发音传播服从声学、空气动力学。所以,历时音变和共时变异如果有什么“内在”原因的话,一定服从这些一般的原理。音变原理、机制就可因此而“还原”或“简约”为物理、生理、心理问题,他们只是一般原理、普遍机制在历时和共时的音韵学中的表现。
认知语言学本质上是实质/还原主义,用Stjernfelt(1995)的说法是“连续主义”(Continuism)。他把语言能力看成是更一般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仅仅是壮观的认知冰山一角”。(Fauconnier 1999:96)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一般以首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召开(Duisburg, Germany, 1989)和Cognitive Linguistics学刊出版(1990)为标志。在这之前,已经有几部奠基之作问世,如Lakoff & Johnson的Metaphors We Live By(1980), Lakoff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1987),Langacker的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1987)等。按照Croft(1999),类型学和认知语言学都认为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句法成分本身,而是句法成分所栖身的建构,即把不同种类的语言信息组合成形式和功能的复合体的信号单位。语言在发生上迟于智力,所以可以设想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会利用到人类的一般智力。近年来,把类型学的方法(刘丹青2001)和认知机制引入汉语研究(沈家煊1999,陆丙甫1993,张敏1998、2002)取得很大进展。例如沈家煊(1999)用两个认知概念“转喻”(metonymy)和“显著度”(salience)来分析解释无核“的”字短语的构成条件和理解机制。陆丙甫(1993)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必须充分利用并受制于人类短时记忆的限度(七块左右)。这说明语言结构的某些基本制约可以还原为更基本的一般的智力因素。
差不多同时,Ohala主编的《实验音韵学》(Experimental Phonology, 1986)问世,标志着实验语音学正式介入历时音韵学和共时音韵学。在实验音韵学眼里,历时的音韵演变和共时的音韵变异服从的是同样的原理。今天的分布是昨天演变的结果,所以分布如果有什么规律可言,那就一定服从演变的规律;而演变如果有什么规律可寻,那就一定能从共时的类型学上看出来。Ohala(1989,1993)甚至提出了一个语言学中从未有过的、连梦想都嫌奢侈的口号: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音变,都要叫他在实验室里重现。
近年来我在“实验音韵学”中实验,写了几篇文章。朱晓农(2003)从空气动力学原理来解释群母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朱晓农(2004b、2005b)以回复调音器官的初始状态来解释发生在汉语历史上的元音链式高化,以及为什么链式高化总是推链式的。朱晓农(2004a)则借用动物行为学(ethology)里的一个高调理论来统一解释从各类小称调到女国音、“美眉”等形形色色以往难以解释的高调现象。朱晓农(1989a)中,使用数理统计解决了一个自宋代吴棫、郑庠以来的千年难题——如何释读古韵文,并以此来重建当时的韵母系统。这个难题也囊括了有清三百年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孔广森毕生从事的古音学的几乎全部工作。这项工作的前提也是还原主义,即把语言现象还原为一种统计现象。
6 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异同
简单地来说,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相同点是都想寻找解释,都使用演绎法。不过,此解释不同于彼解释。
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区别在于:1)基本假设:语言系统是否自足,语言学是否自主;2)材料来源:通过内省,还是通过类型学/语料库,来获取材料、发现问题;3)物理背景: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包括量子论、突变论等);4)数学工具:数理逻辑还是数理统计;5)基本目标:给出逻辑条件,还是寻求广义的物理的因果解释。
“语言系统是否自足”这个前提是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的分界点。按我的理解,自足系统实际上是个自定义系统,自定义系统中的任何矛盾都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来消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作为公理化系统他的目标是完备性(语言的每个角落和每个角落的语言),离四十多年前的理想更远了,而不是更近了。问题就在于语言难以成为一个自定义系统,其矛盾没法靠重新定义来解决,所以只能靠缩小范围来加深认识。前面说了,形式化工作的最高境界是公理化。形式语言学如果能达到那境界,早就做到了。就像平面几何,一个人做完,两千年来其他人没多少活儿可干。
说语言难以成为一个自定义系统,指的是自然语言不是形式系统,人工语言当然又两样了。我们说话,并没有想遵照形式逻辑去构筑一个形式系统,遵循的是一种我称之为“秦人逻辑”的联想环、类推链。其实,就是想构筑形式系统都不可能,因为在这世界上,古往今来,除了说印欧语的人在希腊和印度分别独立创造出了演绎逻辑,其他民族不要说老百姓日常说话,就是名家辩者再百家争鸣、孟子荀子再雄辩滔滔、知识精英如王阳明再对着竹子苦思冥想,也鸣辩格致不出个形式系统来。(朱晓农1991)
如果要打比方的话,可以说实质主义是外部开源,形式主义是内部挖潜。形式主义安排内部条理,实质主义寻找外在原因。两者在学术目标上互补而不冲突,无论从哪个前提出发,都是要找出内在和外在的分界。
对“语言共性”的认识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定义:实质主义把他看成人类语言中共有的东西(内部定义),形式主义把他定义为人类语言中有而动物通讯系统中无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外部定义)。本来内涵定义就这两个标准:对内有周延性,对外有排他性。实质主义强调前者,形式主义强调后者。但从操作层面看,实质主义的定义更有利于本学科的研究。
我不把所有用形式化方法来处理语料的都叫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可以单留给那些基本假设是“语言自足”、基本目标仅仅是给出逻辑条件的研究模式。具有其他假设和目标的学者因为同样需要处理作为系统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也要使用形式化的方法,但他们不是“形式主义者”。如上文所举的沈钟伟的工作,说明探讨语言的社会因素不是仅凭印象谈杂感,确定语言的社会参数可以做得非常形式化。而社会语言学我们一向认为是和形式语言学从基本假设开始全然不同的派别,因此往往会做成社会语言漫谈。
最后再谈两句材料的“自备性”问题。语音学中有条规矩,研究者本人是最不“理想的发音人”。本人的发音可以用来做些先导性试验,用作发现是允许的,但要想用来证明,据此立论,那就犯了大忌。用技术点的话来说,那是造成系统误差的来源之一。语法学中使用语料库,以及实验和统计的方法来测试句子的可接受性,(如Cowart 1997)也是朝着客观性方向的努力。要做到客观不容易。我在研究中要是看到合乎自己观点哪怕有点怪的例句,常常会越看越合格;看到不合胃口的,越看越不像。我知道自己容易受暗示,也知道自己难免有偏见的,但我没绝望,因为我明白,一旦我认识到这一点就有摆脱暗示偏见影响的希望。
7 接近的现实
优选论的出现,按我的理解,在三方面偏离了形式主义:1)借助于语料库。想当年从Jakobson起,标记论(markedness)就是以语音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的,现在转了个圈又回归到这个基础上。与此相应,确定约束的优先级(ranking of constraints)也就要根据在语言样本中的出现频率。2)不再认为语言是个自足系统,音系学不再是自主的。Kager(1999:5)说大多数音系学家都同意音韵标记植根于语法系统之外的因素。一二十年前Ohala(1990)和Anderson(1981)之间关于“音系学是否自主”的争论至此可以告一段落。Anderson认为音系学完全自主,他跟比如说语音学的关系为零。Ohala认为音系学完全不自主,他跟语音学完全重合。这段争论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外在原因,也就不知道内在“原因”;反之亦然。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从两端使劲,合力推进了语言研究。3)允许了矛盾命题,照Kager(1999:4)的说法,语言是个充满矛盾对抗的系统。解决的办法是为矛盾命题定不同的等级,或运用时有先后,总之不直接对抗。
有了第一个偏离,方法论上就放弃了内省法,至少不再独大。有了第二个偏离,认识论上放弃了原来的“自足”假设。有了第三个偏离,本体论上放弃了语言是自定义的形式系统。总之,优选论的出现使得大家从本体、认识到方法都接近于“三不自”原则了。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准备学位论文时,拼命抓住Lehiste(1970:vi)一句话" A phonologist ignores phonetics at his own peril." 一方面把他当救生圈,另一方面又想证明他的正确性。谁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已经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了。
前面提到对历史问题曾有过短暂的形式化努力。现在又有用优选论来处理语言演变的了,(如McMahon 2000)这是统一历时和共时的努力,与实质主义目标一致。至于共性和个性的问题,还有争议。Kager(1999:1)那本书开宗明义:“语言学理论的主要目标是说明在所有语言都有的基本原理。”其实,Prince和Smolensky(1993)最早的零假设就是所有约束都具有普遍性并普遍出现于所有语言的语法中。但McMahon(2000:10)却认为优选论在“努力解决普遍的音韵模式时,恐怕就难以处理个别语言的特定问题了。”照我看来,这实际上涉及的是个物理观念和数学工具的问题。语言规则用充分条件、绝对蕴涵来表达,总是会有反例,很偶然才会碰到没反例的。(见朱晓农2003)换个基本假设,换个物理观念和数学工具,把共性看成是统计现象,就容易理解多了。那种很偶然的“真正”共性、绝对共性不过是100%或0%,而100%或0%都只是特例而已。
其实,自足性、自主性、自定义系统,作这些个假设只是研究的需要。有了这些假设就能够建立研究范式和推进内部挖潜。在我看来,“各门学科独立出来研究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并不是那个研究对象本身是独立的或者可以独立[或自足]的”。(朱晓农1987—88)就像我研究修辞格,可以把他公理化,(朱晓农1990)但我一点不认为修辞现象本身是个公理化系统,所以,我是不信有谁真的把自然语言本身看成是个自足的形式化系统。
8 三大潮流:代总结
语言学两百年来有三大潮流: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如果给这三股大潮各选一位代表,那么,历史主义可以选Grimm做代表,形式主义可以选Goldsmith做代表,实质主义可以选Ohala做代表。用“时间观”作为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主义是“历时观”,形式主义是“共时观”,实质主义是“泛时观”。
以上所论,别看这个主义那个派,根本上都一样:寻找解释,依靠演绎,信奉同一律。就这演绎逻辑同一律一条,咱们还有不少是信奉同构律的。(朱晓农1990a)好在情况在改观,沈家煊先生在庆祝《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的大会(南昌,2002)上说,他支持寻求语言现象背后的解释,让人振奋。像现代中国所有的科学学科一样,语言学是一项引进的事业。像一切引进的研究有分布差异事物的学科一样,语言学在移植过程中需要调整。就像赵元任所说,要先学到一个合格的地步,再加上中国特殊的贡献。
本文上下两百年,纵横三大派。其实语言学各流各派的精神是相同的,根本上都是一样的“科学主义”、“逻辑主义”,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推动了理性认识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