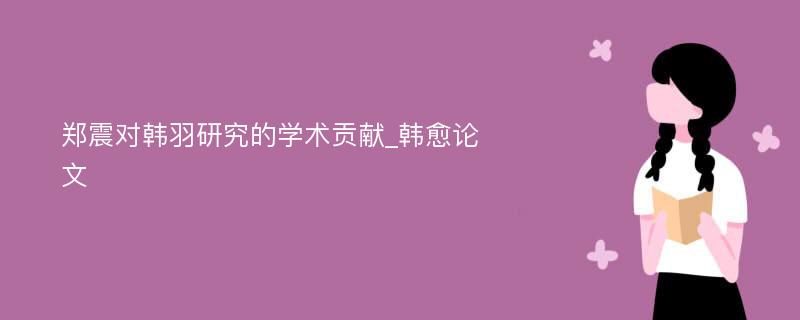
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愈论文,贡献论文,学术论文,郑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韩愈”条谓:“研究著作,王鸣盛《蛾术篇》、郑珍《巢经巢文集》、俞樾《俞楼杂纂》诸书的有关条目或文章,具有学术价值。”韩愈诗文集,自其弟子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宋人辑编《外集》后,至南宋庆元年间魏怀忠(仲举)编刻《昌黎先生文集》和《外集》,已集录五百家注(以下简称魏本)。其中举凡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谱注》、方崧卿《举正》、朱熹《考异》,都是洋洋大观者。自是以后,研究成果,代有人出。有清一代,顾嗣立(侠君)《集注》、方世举(扶南)《笺注》、以及朱彝尊(竹坨)、何焯(义门)《批韩诗》,影响亦甚为昭著。郑珍身处僻壤穷疆,际遇坎坷,终老乡间。其书版刻已少,加以地域环境限制,流传更难广泛。致使其学术上的真知卓见,长期湮没沉埋,鲜为人知。基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对郑珍的称许,虽只一句,却极有份量,应当引起重视。有意思的是,这一句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郑珍”条目,撰写者都是同一人,真有高山流水,知音其希之慨。本文拟就这惜言如金的一句评价为纲,将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试作发掘申论。郑珍的研究,并非有专文专著,宏制巨作,而是以“跋语”和“书后”的形式表现。《巢经巢文集》卷5有“跋韩诗”短文二十篇,卷6有《书韩集与大颠三书后》一篇。这些读书笔记,虽为残丛小语,但已涉及到韩愈思想,交游和韩诗旨意,系年等诸多方面。有的可说已澄清千年疑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归结为四点,逐一论述。
一、正本清源,排谤去诬
韩愈一生,其升沉起落,都与释老有密切关系。他尊崇儒学,力主儒、墨、法并世兼用,对愚民蠹财的佛老,排斥不遗余力,因而诬名毁誉之辞不绝。据《唐文纪事》卷82,较为可信的赵德所编《昌黎文录》,并无《与大颠书》三篇。该文最早出现,乃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刻石于潮阳灵山禅院。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因“其以《系辞》为《大传》,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与己意合为由,认为“宜为退之言”。苏轼已知其伪,其《杂说》云:“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尔后洪兴祖录其文,朱熹虽认为“有不成文理处”,却仍以“旧本亡佚,僧徒所记不真,致有脱误”搪塞,将三篇归入韩集,实已别有用心。郑珍说:“是洪氏者必欲以此三书为真韩氏作也,必欲实韩氏之崇信佛教也。得此书以实韩子为崇信佛教,而韩子之人品学问乃始大裂。此朱子之心也。噫!朱子之心亦私而隘哉!”一针见血指其居心不良。郑珍考辩有三点:一为语言文字和文风,韩愈文章,即使短篇书简,都文从字顺,富于文采,极有气势。此书非但无气势可言,且文辞鄙俚,语言不通,更兼逻辑混乱;二为韩愈贬官前所任为刑部侍郎,遇赦后晚年才任吏部侍郎,不应在贬期自署此职衔,韩愈本人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做,显系作伪者依托;三为以韩愈上《谏佛骨表》贬官潮州刺吏的行程日期推算,与该书所署日期不合。郑珍指斥朱熹“自私”、“狭隘”、本于何焯《批韩诗》:“(朱子)必欲反复文致三书为出于韩,亦可见朱子用心之隘而私矣。”(《义门读书记》)袁枚《答是仲明书》(见《小仓山房尺牍》)则揭了朱的底。对于儒家道统地位,“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只此一座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据其位?”朱熹为了争这个位子,不惜相信伪作,往韩愈身上泼污。苏、何、袁诸子虽为之不平,却不能细析其伪,据理力争。实事求是者,岂非郑珍否?今天学术界已不信三书,郑珍之辩,应是起着相当作用的。
韩愈因诗遭误解被损毁名誉的,为数不少。贞元十年(794),传闻孝廉谢寰之女谢自然信道而白日升天(事详《大平广记》卷66引《集仙录》),朝野哄动。郡守李坚表奏,赐诏褒谕。时年26岁的韩愈写了《谢自然诗》,力辩其诳惑荒谬。时人及后世不细审诗意,反讥韩信其实而同流合污。刘商《谢自然却还故居诗》云:“仙侣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云随。不知辞罢虚皇日,更向人间住几时”已含讥意。杨慎《升庵诗话》更借刘诗发挥:“谢自然女仙,白日飞升,当时盛传其事自长安。韩昌黎作《谢自然诗》记其迹甚著,盖亦得于传闻也。盖谢氏为妖道士所惑,以幻术贸迁他所而淫之,久而厌之,又返旧居。观商诗中‘仙侣招邀’,意在言外,惜乎昌黎不闻也。”自是以后,对韩诗的看法便多歧见,朱彝尊甚而说“率尔漫写,不见作手”。韩愈对世之求仙者,一直抱着“吾宁屈曲在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记梦》)的态度,更认为对佛老须断然“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顾嗣立说:“公排斥佛老,是生平得力处。此篇全以议论为诗,词严义正,明目张胆,《原道》、《佛骨表》之亚也。”郑珍则更进一步申论:“刘(《四部备要》本误作陈)商有《谢自然却还故居》诗,此女信得道者耶?然以公所言观之,其去而复还,仍是为魑鬼狐狸所弄,特彼不肯自承耳。否则复还者,即木怪狐妖所为,岂真自然哉!”此似针对杨慎说反诘,对顾说补充。话虽简略,却切中要害,即韩愈本意,乃视仙道犹鬼道也。
韩愈《示儿》诗,据《苕溪渔隐丛话》卷16,苏轼曾谓“所示皆利禄事”,且引杜甫《示宗武》诗,谓“所示皆圣贤事”,认为杜以圣贤劝勉儿子读书,韩则以利禄引诱儿子读书。此说如果成立,韩、杜人品高下,不辩自明。朱熹更指责韩愈《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之言,已不复存在,“本心何如哉”!邓肃《跋陈子翁书邵尧夫诫子文》,也说“韩愈氏《示儿》古风,用玉带金鱼之说以激之,爱子之情由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矣”。后世虽有朱彝尊、何焯等人回护,终觉乏力。郑珍力排众议,说:“东坡论此诗所示皆利禄事,浅视诗旨也。读‘开门’一段,是所指为利禄者。深玩之,诗言身为卿相,持国钧轴,而与同官往来,止以酒食相邀逐,博槊相娱乐,皆行尸走肉耳。其所讲之唐虞,亦止口中仁义,即公所云‘周行俊异,未见皮毛’者也。‘酒食’联下接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郑重作一指点,语似眼热,齿实冷极。重言其官职,正轻哂其所为,所谓赞扬盛于怒骂也。不然,上言‘无非卿大夫’是矣,又著此二语,津津不置,不重复无谓耶?观‘又问’四句,言过从讲道者,唯有张(籍)、樊(宗师),则自两人而外,皆无一可与言者。愈见上文所云,并非艳于利禄,夸诱符(韩子名符)郎也。坡公特末细思耳。”韩愈教子之意,《颜氏家训》等早已有之。后世程学恂《韩诗臆说》认为韩诗可与杜诗《七歌》“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参见。又认为韩平生过从交往之人,唯有张、樊相得,若以富贵利禄期待子弟,则无须专提二人,因此“东坡语亦不得执煞看”,乃承袭郑珍之说。韩诗皮里阳秋,反语妙用之手法,经郑珍揭示,始见明豁,诗旨自然贯通无滞。
《示儿》诗旨既明,韩愈另一首教子诗《符读书城南》便易为理解。黄庭坚曾认为此诗劝奖之功,与孔子同归正论。魏本引宋人陆唐老却短之云:“退之《佛骨》一疏,议论奋激,曾不以去就祸福回其操;《原道》一书,累千百言,攘斥异端,退之所学所行,亦无愧矣。唯《符读书城南》一诗,乃微见其有戾于向之所得者,切切然饵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此岂故韩愈哉!”后人虽有申辩,终不如郑珍剀切:“读书通古今,行身戒不义,学行并进,文质相宜。达则富贵若固有,穷亦名誉不去身。为圣为贤,止是如此。论古今通理,有‘潭潭府中趋’之俗子,必无‘鞭背生虫蛆’之哲人。子孙苟贤,藏身有求,即不为卿相,亦免人奴人仆。必欲饿不任声,寒而见肘,是其时命所极,决非父母之心。若伏猎侍郎,弄獐宰相,固韩公所不屑计较,于符岂有虑焉。如唐老者,吾知其教子孙作木石耳!”《巢经巢诗》前集卷7《次昌黎〈符读书城南〉韵示同儿》诗,以“唯其勤读书,道德塞太虚”,勉励其子郑知同,取意正与韩合。是知郑珍身体力行,并非空谈虚妄之言。李光地《榕村诗选》所谓“此诗勉符诗书,后则由文章而归之于穷经观史,修饬行义也”,及程学恂云“看他说公说相,到底都归在行义上,是岂以富贵利达饵其子者乎”!均与郑珍意同。
二、考定交游,知人论世
韩愈和贾岛的交游,古籍传闻记载虽多,但欠落实。如贾岛因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句推敲末定,误撞韩愈马头事,《刘公嘉话》、《又玄集》、《鉴戒录》所记皆同。自苏轼云“世俗无知者所托”后,洪兴祖、樊汝霖皆辩其乌有。《唐摭言》又言贾岛因索句唐突京北尹刘栖楚被执,《新唐书》信以为真,采入本传。郑珍认为皆是谬谈。理由是:一、贾、韩交往,据贾《携新文见张籍韩愈途中成》诗,知贾由幽都见韩前,先至长安谒张籍,故诗题是先张后韩,诗尚作于见张前。见张在元和五年冬,明春始赴洛与韩相见,故韩愈《送无本师(贾岛法名无本)归范阳》诗有“始见洛阳春,桃枝缀红糁”句,并非因误撞结识。二、《新唐书》本传所谓禁僧不出,贾作诗自伤,亦不足信。是年秋韩任职方,贾随之进京,及十一月贾归范阳,始有韩《送无本师归范阳》诗赠。其后至长庆四年,韩告病城南庄,贾复来相见,有《黄子陂上韩吏部》诗,云“石楼云一别,二十二三春”。从元和七年(812)到长庆四年(824)韩去世,约十三年(此可校正贾诗当作“一十二三春”)间,贾都不时陪侍。韩、贾交游,全过程如郑珍所考。钟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以下简称钱本)录郑珍跋语全文系于诗后,其价值可见。另外,郑珍对贾岛与刘栖楚、孟郊之间的交往,辩析甚详,均可补正旧说,足资参考。
韩愈《崔十六少府摄事伊阳以诗及书见投》诗,自东雅堂本注《赠崔评事》诗谓“立之初摄伊阳尉”,后世遂误认其与崔立之为同一人,方扶南不悟其非,又据以谓立之摄伊阳在为评事后,并于《西城员外丞》诗后详列崔立之履历,谓“评事谪官摄伊阳尉”。郑珍认为某氏一误,方氏再误,三人成虎,迷谬已甚,不可不正。《跋语》说,韩愈有赠崔立之诗多首,皆称崔二十六,不称崔十六。行第称谓不同,其为两人已明。诗中有“三年国子师”句,知为元和三年(808)作。韩19岁到京师,乃贞元二年(786)。其四年,立之登第;八年,韩登第。则知韩、崔交好,当在贞元之初。而此诗前半所叙,乃韩于元和二年分司居东都,与崔十六赁屋连墙,始相认识,明是新交事情,此距与崔立之相交,已逾二十年。二崔之事经郑珍辩白,至此方明。钱本采人郑说,足具慧眼。
三、补正旧说,阐明诗旨
韩诗《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朱熹云“此诗多不晓,当阙”。刘攽(贡父)《中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皆以“韩讥其勉力为诗,不如不作”解诗。陈沆《诗比兴笺》虽有此章乃进之于道”之说,惜语意不明。按皇甫湜字持正,唐代文学家,元和进士。师事韩愈且思想倾向接近。韩逝后,曾撰《韩文公墓铭》。郑珍从两人师生关系考虑,认为该诗“大意谓人生百年内,当留心于大者远者。孔、颜事业,终身为之不尽,区区园池中景物,自然不及关怀。皇甫之《园池》诗,何异掎摭(拾取)粪壤?用心既误,藏否更不必论也”。因此,韩愈写此诗,“盖勉之及时进业,无复流连光景,费无益之心事耳”。郑珍还进一步指出,刘、叶所说皇甫不能作诗,诗不传世,皆为臆谈。“持正诗今存三篇,《题浯溪石》、《石佛谷》、《出世篇》,何尝非诗人吐属?特全集失传耳”(三诗见《全唐诗》)。钱本附录郑说,以备资证。
韩愈《人日城南登高》诗“圣朝身不废,佳节古所用”句,注家都付阙如。郑珍云:“古用人日登高,注家未详,于何徵之?曰:晋桓温参军张望有《正月七日登高》诗,李充有《人日登安仁峰铭》。《寿阳记》:‘宋王正月七日登仙楼会君臣,父老集城下,皆令饮一爵。北齐阳休之有《人日登高侍宴》诗,乔偘亦有《人日登高》诗。《景龙文馆记》:‘中宗景龙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辉阁登高遇雪,令学士赋诗,李文等六人皆有作。’是知人日登高,自晋至唐,皆为故事,故公诗云然。”博闻强识,郑珍学力,可见一斑。
韩诗《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三首,其二有“配地行新祭,因山托故封。凤飞终不返,剑化会相从”句,魏本引王安石语,以为“此非君臣所宜,言近于黩”,指斥韩诗欠严肃庄重。其实韩诗是暗用《晋书·张华传》的一个典故:“雷焕得丰城双剑,送一与华,留一自佩。曰:‘灵异之物,终当化去。’华得剑,宝爱之,曰:‘天生神物,终当合矣。’”张华死后,其佩剑与另一剑入水化龙而去。大行皇太后指顺宗庄宪皇后王氏,宪宗生母。帝后本是“灵异之物”,所以“终当化去”。他们又是“天生神物”,又“终当合矣”。剑器在中国古代,自来有龙形隐幻变化的传说,以之喻帝、后龙凤之姿,无不得当处。郑珍认为:“后与顺宗同葬丰陵,故诗云‘因故托山封’,‘凤飞终不返’句,即承‘故封’。接下‘剑化会相从’句,言今日祔葬得礼。王介甫不了诗意,讥剑化为黩,失旨之深”。朱彝尊谓此诗“圆和有态,正得诗人风韵”,已看出了韩诗比兴圆转,生动有致的特点。若与郑说相参证,则诗旨更添显豁。
韩诗《咏灯花同侯十一》“黄里排金粟”句,诸家均不得确解,盖因不明“黄”为何物。郑珍据《文选》注“石中黄子,黄石子也,宫额用之”,并以梁简文帝《美女篇》“约黄能效月”,李商隐“低眉遮黄子”诗句为证,考黄乃石名,妇女以之饰额。韩诗以“钗”对“黄”,此物连类,拟状肖形,的是正对。“黄里排金粟”句,郑珍谓“灯之火光内黄外赤,花在其中,恰是‘黄里排金粟’;钗以比灯芯,花在其首,确是‘钗头缀玉虫’,于此见公体物之精”。若无郑珍的观察体会,韩诗之精妙,后人仍难领悟。
韩愈《陆浑山火》诗,诗题各本不一。然以皇甫湜原诗韵相和,并无歧义。此亦可补充前郑珍所谓皇甫能诗说。诗中“女丁妇壬传世婚”句,洪兴祖、朱熹、朱翌《猗觉寮杂记》等皆不知所谓。方崧卿改为“女丁夫壬”或“夫丁妇壬”,虽削足适履,终难契合。郑珍考证萧吉《五行大义论·五行相杂》引《五行书》为韩诗所本,认为这是用夫妻亲缘关系喻自然界的阴阳调和。亲缘关系、夫妻关系顺,则阴阳调和,否则逆反。陆浑山火起,亦是阴阳失调所致,非人力所能制止,只能因势利导,此即诗中“时行当反慎藏蹲”之意。《谷神妙气诀》所谓“夫五行更为夫妻者何?皆有威制”,亦是此理。治水治火如此,治理国家亦然,韩愈盖针对朝政权幸势炽,炎官趋附而言。韩诗用阴阳五行说立意,郑珍以阴阳五行说解诗,可谓相得益彰。
另外,郑珍对韩诗《寄卢仝》“立召贼曹呼五伯”中“五伯”的含义,徵事数典,考之极详,足可补正旧说。原文甚明,兹不赘述。
四,辩析诗意,厘定系年
韩诗自方世举始有编年。然间多模棱不清至舛误者,郑珍厘定8首,皆确凿不移。
韩愈《叉鱼招张功曹》诗,方氏据《祭河南张员外文》“避风太湖,七日鹿角。钩登大鲇,怒颊豕豞”,《祭郴州李使君文》“投叉鱼之短韵”句意,断为韩愈“俟新命于郴州作”。韩愈贞元十九年(803)贬为阳山令,过郴州,始与李氏结识,而据权德舆《李伯康墓志》,永贞元年(805)十月李已卒于任所。明年顺宗即位,韩愈遇赦;秋天宪宗即位,韩愈量移江陵府法曹参军。所谓“避风太湖”,“钩登大鲇”之事,皆在李氏病故之后。因“叉鱼春岸阔”,时令已在春天;“脍成思我友,欢乐忆吾僚”,“友僚”皆指李氏,“思忆”明指李氏已亡故。故郑珍说:“余以为公祭张员外所谓太湖即洞庭湖,故叙七日避风,在住观南岳之后,非叉鱼地也。叉鱼在郴州城外西湖,今皆为田,余曾亲往其处。方氏殆误。”郑珍所谓“亲游”,指道光六年(1826)赴京会试不中,入程恩泽幕游郴州时。《巢经巢诗》前集卷1有《游北湖怀昌黎公。湖在郴州北郭外,周广可四十里,今皆为稻田矣。去年,程春海先生嘱刺史惠安曾钰,于道侧蓄一池,祠昌黎于其上》诗,云:“湖地四边今叱犊,昔年中夜此叉鱼”,已作实地考察。叉鱼之事发生在与李氏初结识之时,《叉鱼》之诗则作于李氏故后赴江陵途中。这样既合叉鱼时令,又合诗题中张署“功曹”官职(之前张为郴州临武令)。此诗系年,当编在顺宗永贞元年之后,《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诗前。钱本系于贞元二十一年,却谓“然是春张尚为县令,功曹之称,或系后来所题,或原作张十一,而为编者所加”,郑珍之辨,实可补正此游疑不决之辞。若再与其后《跋韩诗合江亭首》语同参,则此诗系年,当无别虑。
韩诗《和席八十二韵》首,方氏注谓“此诗未定为何年所作,然以落句观之,盖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遥和之诗也”。各家之说,亦未见肯綮。郑珍据诗中“纶猷谋猷盛”,“傍砌看红药”句,判定席八时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据“倚玉难藏拙,吹竽久混真”,知韩与席同知制诰。末韵云身老无所用,理合退休,与席久混,唯有自惭。“江海未近身”句,指未还江海之身。对朝廷来说,江海、江湖,山林都是一个意思,并非定在大江大海。郑珍最后说:“此诗应编在《人日登高》后,扶高误解末句,遂多生穿凿。编年既误,明白之诗反晦矣!”钱本编年时,引用了郑珍跋语,且将该诗系于元和十一年(816),列于《人日登高》诗后,显系完全采纳了郑珍意见。
韩诗《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方氏编在《岳阳楼别窦司值》诗后,郑珍以为当系于《潭州泊船呈诸公》诗前,即作于自衡州至潭州途中。理由是:“诗云‘清水清且急’,则在湘江也;云‘凉风日修修’,则八九月也;云‘胡为前归路,旅泊尚夷犹’,观岳之后,泊潭之前,中间必以故稽留一二十日。此诗之作,即在其时。宪宗之立,(王)伾、(王叔)文之贬,在八月;京使至湘中,当在九月。此时公已闻诏,则诗作于九月无疑。盖阻风鹿角,地在潭州下流二百里,时已是十月,与凉风句不合;若过岳阳,已是大江,不得云湘水也。”郑珍因有过实地考察,措词才如此明晰果断。钱本谓“郑以此为观岳阳后迫潭前作,其说是也”,并据以编年。
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方氏谓为长庆四年(824),即韩为吏部侍郎辞世前病中作。郑珍认为“误矣!此诗决非作于长庆四年”。原因是,这年中秋后韩病转重,至十二月卒。其间张籍常来省视,都迫于公事,不能久留。而且韩既病重,岂能与人在风雪中纵谈数日?其门人辈又怎能如平时随意谈论?“余细审之,当是贞元十四年(789)孟冬,公在汴州时作”。当时张初见韩,韩为考官,张得首荐。以后张常到韩所,连朝累夕谈论。是知此诗皆实叙非谈谐求胜于门人。韩卒时,张学问人品,已几乎和韩并驾,世号“韩张”久矣,不能说仍“处闾里”。另外,“晓鼓朝”指董晋之衙,非韩朝;“将归乃徐谓”,是担潮时连日宿韩处,不能以归家疑之。郑珍的分析,鞭辟入理,将诗意条析得至为明白,无丝毫窒碍。既为考订系年提供了可信的依据,也是研究韩张早期交往经历的有力参证。
韩诗《贺张十八秘书得裴司空马》,李汉编在《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诗前,本不误。方氏改编在其后,并谓“籍此时已为水部员外郎,前题称之;此称秘书,或仍其旧,或传写误”。方说因无他证,不免主观臆测。张籍有谢裴度(时为河东节度使进检校司空)寄马诗,裴度亦有诗回酬。当时李绛、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贾和韩愈都有诗相贺,足见张籍得人心处。元和十五年(820)冬,张尚为国子助教秘书,未为国子博士,至长庆二年(822)后才迁水部员外郎。郑珍引白居易《香山集》卷19《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诗为证,韩、白此时皆称张为秘书。“方氏称易旧次,自取葛藤,不知何由知得马时定为水部员外也”。钱本采郑珍说,系此诗为元和十五年,应是信而有徵。
韩愈《谴疟鬼》诗,韩醇《韩诗全解》谓因皇甫湜、程异诸人作。方扶南则认定为宰相李逢吉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作,且引《郾城联句》“天殃鬼行疟”为此诗缘起,系年于其后,即元和十二年(817)。郑珍以韩诗《纳凉绝句》“疟渴秋更数”为证,谓为纪实之什,即永贞元年(805),韩愈遇赦由郴州至潭州病疟时有感而作。郑珍说:“公贬阳山,在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渡湖经岭,皆极寒之时。二十年在阳山,又无缘至湖岭。唯二十一年由阳山俟命于郴,则越岭有热石之行。又由郴下潭州,自衡以下皆湖地,其时又正当夏秋,夏痟秋疟,即叙在渡炎湖,行热石之下,又与此乘秋作寒热合。知公偶尔病疟,作此消遣。其曰江水清,曰《九歌》、曰清波,白石、芙蓉旗,并就眼前景附合楚《骚》,以为娱戏,非凭空拟撰也。”此诗宗旨,郑珍说:“要之名门子孙,不修操行,以忝厥祖父者,比比皆是。公自嬉骂疟鬼,而使不肖子读之,自知汗背,正即有关世道也,何必定指斥某子耶?”钱本谓“郑说得之”,并依之编年。
韩愈《和李相公摄事南郊览物兴怀》、《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陈诚》两诗,方氏认为“必非韩作。大抵二相属和,不得已而假手代之。李汉不审,漫以编录耳。公以末暮之年,倦于笔墨,遂未加推敲耳。论道而贬三代,昌黎为人何至此?此诗之所以必赝也”。王鸣盛虽觉得方氏“未见确的”,但亦无辨证。王元启则游疑于两可之间不能决断。李逢吉依靠宦官势力,在宪宗、穆宗朝两次为相,排挤守正官员,无一事近仁。其妒害裴度,阴阻计蔡州吴元济,与韩翕政见相左,本为路人;杜元颖乃唐初大臣杜如晦五世孙,穆宗时拜相,为得志新贵。方氏从回护韩愈的感情虚及,若诗为韩作,则见其同流合污,违心献媚,有碍名节。
对前诗,郑珍说:“余以理揆之,原无可议。凡和人诗,必就彼题,装入己意,大抵赞人者多,或寓规于赞,体例自是如此。公和李作,题是摄事南郊,览物兴怀。逢吉原诗,必见倦于枢务,思息山林之意。即此一念,视世之颠瞑富贵,恬不知止者,讵不远甚?”郑珍进而分析说,既是和诗,不可能直接指斥对方为小人,促其引退,而是委婉其辞,劝其尽职诚劳,以仁心待民,以静养待国,不要妄起事端。诗意在劝其改恶行善。“逢吉嫉功妒能,妨贤树党,实不仁不静,不能吐握者。公诗力砭其病而浑无痕迹。如方氏意,则此诗若出公手,必痛加斥詈乃合。然则‘浊水污泥清路尘’、‘应许闲官寄病身’之言,何自贬损乃尔耶”?近人蒋抱玄《评注韩昌黎诗集》谓“此诗富有规讽,读之意味深厚”,可谓深得郑珍之心。
对于后一首,王元启说:“谓禹、稷之功不及玄元之道,此言似非公所宜出。”似未领悟诗意。郑珍解释说:“‘在功诚可尚’二语,言禹、稷之功可尚如此,而姬家、夏家于尊崇之道未极光华,不若我唐之追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也。道非道德之谓,于道上承姬家、夏家,言夏、周两朝之于道,于字不属禹、稷。题是朝享太清宫,自宜就事论事,何暇以禹、稷、老子比较高下乎?”至于代笔之事,郑珍说:“方氏误解词意,遂疑非公作。不知苟属代笔,不出张(籍)、李(翱)之徒。论道而贬三代,即张、李决不道。明明诗语,乃如此读之,可叹也。”钱本认定两诗为韩作,系于长庆三年(823),且附郑说于后。
郑珍跋韩诗文诸篇,非一时所成。《巢经巢文》卷5《跋韩诗谢自然首》题下编者注,谓“大约在辛酉以前,总录于此,依韩集编次”。辛酉为咸丰十一年(1861),距郑珍辞世仅三年。这之前一年,太平军白号军朱明月部进逼遵义,郑珍携家口避乱经娄山关到桐梓,赁居于魁岩杨家河畔。郑珍《题移写韩诗批本》云:“避乱桐梓魁岩下,近谷雨,犹寒不可出。因以三日力,称录于方扶南笺本上。”题中所谓“批本”,指有未彝尊,何焯两家“批韩诗”的穆阿彰于道光十八年(1838)重刊顾嗣立集注本。在移录时,郑珍写了上述跋语。
实际上,郑珍对韩愈的研究,自青少年时代便开始了。他曾倾注心力逐首批注韩诗,原稿本未刊,现珍藏于遵义市图书馆。对这段经历。郑珍自述说:“余年十五六始见国初顾侠君《韩诗补注》,酷嗜之,抄而熟读焉。而聚宋之五百家注,朱子《考异》,吕、程、洪、方四家年谱(吕大防《韩吏部文公年谱》、程俱《韩文公历官记》、洪兴祖《韩子年谱》、方菘卿《韩文年表》)。洎明凌稚隆所刊宋廖莹中世采堂韩集,以及朱竹坨、何义门朱墨批本,方扶南之笺本,莫不取而参稽之,互证之,几无一字一句不用心钩索者,至今垂三十年矣。”(《柴翁说》)郑珍晚年号“柴翁”,其由来亦缘于韩愈。韩诗《南溪始泛》有“山农惊见之,随我观不休;匪唯儿童辈,或有杖白头”句,张籍《祭退之》将之概括为“柴翁携儿童,聚观于道旁”。“柴翁”即山农之老者,取号“柴翁”,寄寓瞻仰韩愈之意。《巢经巢诗》中有不少诗题与韩愈有关,不少作品如钱仲联先生说,“与昌黎神貌俱合”(《梦苕庵诗话》)。这都说明郑珍与韩愈感情上有极深厚的联系,韩愈在郑珍一生学术和创作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郑珍作为晚清宋诗派的领袖人物,与他“终模韩以规杜”(郑知同《行状》)密不可分。探讨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可以促进韩学研究,在考察郑珍诗学师承渊源和创作风格上,同样具有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