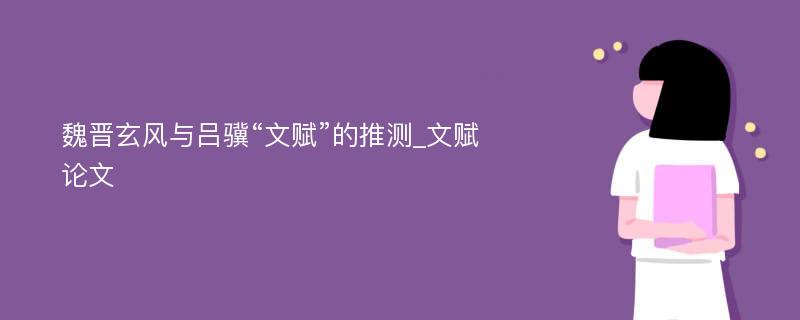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魏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机(261-303)所作《文赋》,辞丽论精,向为历代文人推崇。然《文赋》之成就不仅在于它首先提出了“缘情”和“应感”等重要的文艺理论观点,而且通篇还充满了思辨性。这后一点正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陆机所处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而其时儒学不振玄风盛行的思想潮流对陆机及《文赋》写作更是影响巨大。如果说,《文赋》对情感和灵感的重视是因为其作者是处在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话,那么,《文赋》的思辨性则显然是玄学思考方式对作者影响的结果。
一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无常”,中国社会在东汉末进入了一个长期动荡时期。其时,兵燹频仍,群雄驰鹜,以致“皇纲辐裂”。(陆机《答贾谧》)豪族庄园经济的兴起和黄巾起义的冲击使整个社会基础发生了大变动,也必然使社会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当时,儒术独尊的地位已无法维持,“通人恶烦,羞学章句”①渐成风气。及至魏晋之际,先因曹氏父子以王公之显却“三世立贱”而破坏了传统的儒家道德标准,继之各种学说异端蠡起日兴。于是从正始起,“儒道兼综”的玄学便大行于天下了。陆机生于斯时,风气习染在所难免。他的诗赋创作既表现了重名教建功立德的儒家思想,又流露了尚自然任情性的老庄观念。这对他文学观点的自觉成熟是十分有利的;而他承家学重《易》之阴阳之道则对他接受玄学的思辨性特征更为有利。自汉朝设五经博士,诸学子便各严守家法,不入异门。陆机自幼受教于家学,其叔祖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注易释玄,皆传于世”。②故机也“自幼服膺儒术,非礼不动”,且循家教精心研习易学。此时江左学风保守,而且陆绩所传之《易》偏重象数之学,但陆机却独喜扬雄之仿《易》作《太玄》。扬雄少时师从治《易》、《老》著名的严君平,③后模仿《易》、《老》作《太玄》五千言。子云《太玄赋》云:“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又《法言·问道》中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陆绩对扬雄兼收儒道独创《太玄》十分赞赏,他说过:“雄受气纯和,韬真含道,建立玄经,与圣人同趣,虽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过”。④陆绩如此美誉扬雄不会不影响陆机,而陆机受家学之教也确实习读过《太玄》并体会甚深。他在诗文中曾多次引《易》录《玄》,如《辨亡论·下》云:“〈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玄〉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赠潘尼》中则有:“道之所混,孰后孰先?及子虽殊,同升太玄。”
正是因为陆机在吴中时就已研习过《易》、《老》、《玄》等著作,所以他的思想观点实际上已有摆脱儒学正统的倾向,因此他入晋后能很快地接受玄学观念尤其是王弼等人的观点。王弼虽然晚扬雄近二百年,但两人的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他们既认为孔圣高于聃周,又崇尚虚无和天道自然。王弼援老人儒注《易》,偏重于哲理论辩,从“有、无”这对概念的辨析入手,重新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与扬雄所著《太玄》实有不少相通之处。如王弼说:“圣人体无……老子是有者也。”⑤万物以自然为性”。⑥而扬雄则认为:“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⑦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⑧作为更晚一辈的陆机,既处礼崩乐坏之时,又受家学渊源熏陶,接受王弼等人的玄学思维方式及观点是顺理成章的。《水经注》、《异苑》等载有的一则异闻——陆机过江人洛途中,夜宿客栈遇王弼显形,交谈玄理后机心服膺。──这也许是后代文人想以这种虚构来说明陆机人洛后受玄风影响的事实而己。陆机入洛后诗文中三玄色采日益浓厚,这在《文赋》中也可见到,如“伫中区以玄览”,“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等等。
玄学重抽象的论辩与推理,常将儒、道两家作为对应的观念体系进行辨名析理的论说。当时,言意之辨曾一度喧嚣于文坛,成为玄学论争的一大内容。在言不尽意,言能尽意,得意忘言三说争讼纷纭之际,陆机也以《文赋》直接参与了这场论战,并在文论史上作出了发煌启后的建树。陆机自己说《文赋》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这一主旨贯穿了《文赋》的始终。从作文之由一感于物,一本于学(“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人论,逐层阐发了作文之构思所要解决的意与物、意与文(辞)的关系,以形象化的比拟曲尽其妙地阐发了“作文利害之所由”,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言不尽意与言能尽意的辩证关系。而在解说言意关系时,他借鉴了王弼等人论著中的思辨式论说方法,即建立许多对应统一的概念作为思辨论述的出发点,通过一系列辩证的分析对比,一层层地揭示天道自然的本质规律。王弼、郭象、裴頠、欧阳建等人均从有无、动静,体用,名教自然等对应观念的辨名入手来分析万物之理,论述现象界和宇宙本源之间的关系。如王弼从有无入手,提出,“道者‘无’之称也”,“凡有皆始于无”、无乃万物之本,故名教(有)出于自然(无)。陆机作为儒道兼备的名士,对《易》之阴阳对立又转化的思想精髓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很容易从玄学的思辨方式中汲取长处。在《文赋》中,陆机运用了颇多的对应物事来象征或比喻一系列对应的文学观念,在对比辩析中充分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见解。由于他充分发挥了赋体语言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论述就更显精辟和形象了。如《文赋》中的芳春与劲秋,天渊与下泉,竭情与率意,以至象“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等等对仗工整的句子比比皆是。这种论述不同于汉代经学的烦琐说教,而是充满了思想的灵气与逻辑的力量。这种思辨性在陆机以前的文论中是极少见的,而《文赋》的这种形式特征和体系性直接启发了“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的写作。陆机在《策问秀才纪瞻》中曾提到过自己思辨式论述的来由:“夫五行迭代,阴职相须,二仪所以陶育,四时所以化生,〈易〉称在天成象,在地为形,形象之作,相须之道也”,故“思闻辨之,以释不同之理。”这显然与玄学将老庄之说与阴阳象数之术相结合论辩特点相一致。
二
陆机受玄风影响而善用思辨之法来辨析言意关系还与他弃名教尚自然的思想转变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他不再重视唯实的经学思维方式,他才得以充分展示了了形而上的思辨才能,并从自身体验中逐渐形成了“诗缘情”的观点。目睹了国家灭亡的陆机在思想转变的情感体验过程中是十分痛苦的。陆机身为吴国大司马陆抗之后,从小又受过儒学教育,他的纲常名教经世治国的思想是比较深厚的。这从他在《文赋》末尾提到诗歌的教化作用就可看出。但是,吴都被破后陆机虽退隐山野“颐情志于典坟”十年有余,最后还是入洛仕晋并历任显宦。国亡而事二主是为不忠;家仇不报祖业不守是为不孝。再加上陆机入洛后屡遭谗言,不能得到晋帝的信任与重用,所以他经国安邦之志逐渐被亡国去家之悲愤消融掉了。在洛阳时,他与以贾谧为首的一帮显贵子弟交游甚密,且名列“二十四友”之中。晋时重门阀出身,机为吴之重臣后代,又文名卓著,故附庸风雅的显贵子弟们常邀他饮酒论诗,谈玄说理。他身羁浮华,不能象张季鹰那样退隐吴中安享鲈鱼脍,但又无法抹掉亡国之痛,故心境矛盾愤懑,时常悲从中来。如《赴洛二首》中:“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思归赋》中:“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方思之殷,愤而成篇。”《赠弟士龙诗其九》中:“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抚膺涕泣,血泪彷徨。”这些伤时悼逝之作是陆机痛苦心境的自然流露,也是个性和情感的强烈表现。他事实上并没有遵循教化的信条,甚至也超出了单纯的“诗可以怨”的范围,而是在称情任情中恣意抒发自然天性。这种情感转变在他人洛后的诗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使他坚定了“诗缘情”的文艺观念。如他在与诗友名士的交往中,常常摆脱礼义名教的束缚,饮美酒,服纨素作秉烛游。这种生活逐渐使他的情性旷达起来,并形成了简傲放诞的诗风。他在《顺东西门行》中写道:“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弹哀筝,取乐今日尽欢情。”在《饮酒乐》中有:“饮酒须饮多,人生能几何?百年须受乐,莫压管弦歌。”
创作倾向的变化势必对理论发展产生影响,而魏晋之际的诗歌风格转变当然会动摇传统的诗教观念。当诗歌从政治交往讽劝应制的小道转变为表现个人天性的大业时,这就意味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也就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独立与进步。魏晋诗风中张扬个性情感的时代潮流创造了“诗缘情”的理论,而陆机恰好是时代所造就的这个理论的创始人。在《陆机集》中,“缘情”一词的提法除了《文赋》外,另有两处:元康六年冬,机37岁时所作《思归赋》中:“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又机于40岁时作《叹逝赋》中有:“乐颓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故陆机《文赋》成年在四十岁左右是有道理的。此时的陆机不仅接受了玄学重形而上思辨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接受了玄风影响下人们崇尚自我的情感方式。这种情感方式突出了自然天性,不受董仲舒“以纲纪化之”⑨说教的约束。如郭象曰:“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阮籍有“情寄八荒之表”的抒发。潘岳则以“情洞悲苦”诉怨。从陆机及许多同代人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诗赋所缘之情中既有君子不屑的思妇儿女之情,又有违反“后妃之德”的大恸大喜的激情。可以说,陆机提出“缘情”说,不仅标志了文学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确立,而且标志了文学理论的成熟和文学观念的进步。并逐渐形成了中国诗歌理论的民族特征。
三
在创作心理的认识上,《文赋》对艺术想象和构思的问题作了思辨式的论述。陆机一方面从老庄思想中汲取了神思想象的内省观点,另一方面又从儒家重现实的观念中接受了应物斯感的外察之功。由于他以辩证的观点客观地描述了灵感活动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因此使人们对创作心理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不再迷惑于灵感的神秘了。陆机认为,灵感来时,人的想象可以“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这与老庄的“涤除玄览”,“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是共通的。而他在诗句中说:“感物百忧生,缠绵自相寻。”(《赠尚书郎顾彦先》)“观尺景以伤悲,抚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则明确地表现了自己应物斯感的体验。他在《文赋》中对灵感的这种内省与物感相统一的描述,以及对灵感的突发性(“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和创造性(“思纷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等的描述都比较切合于当代文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
《文赋》以其体系特征显示了玄学思辨对作者理论思考方式的巨大影响。刘勰认为《文赋》“巧而碎乱,鲜观衢路”,钟荣认为《文赋》“通而无贬,不显优劣”等均有以已度人之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赋》实在可说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初创的诗学通论,在文体结构上有开宗立派之功。所以章学诚指出:“刘彦和本陆机之说,而昌论〈文心〉。”
《文赋》的思辨性实为魏晋玄风影响所致,而魏晋时思想开放的环境也促成了陆机在情感和灵感等文艺理论问题上的建树。隋唐以降,儒学复立为正统,至宋明理学,儒学更僵化为教条。《文赋》所开创的有体系、思辨式文论写作不振,感悟式的诗话与点评却大兴。这是因为,思辨论述需要对立观点为参照,建构体系需要新的观点为基石,然封建时代思想专制,道学独行,唯经至上,故何来思辨?更遑论建构理论体系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文赋》的开创作用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注释:
①《文心雕龙·论说》。
②《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③《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④《全三国文·吴》陆绩《述玄》。
⑤《魏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⑥《老子注·五章》。
⑦《太玄·玄图》。
⑧《太玄·玄莹》。
⑨《白虎通·三纲六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