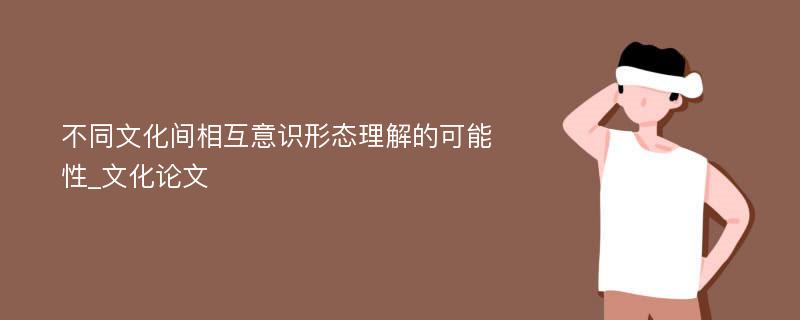
异文化之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可能性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7)05-0002-008
一、自己和他者
我的专业是佛教史,特别是日本佛教史和中日佛教关系。在研究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中国和日本两国学者的议论相互错位的情况。在异文化之间进行思想讨论的时候,会有哪些问题呢?本文将力求以葛兆光的论文作为线索,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考察,然后通过对佛教思想的相关例证的分析,对此做进一步的探究。
葛兆光在他的论文《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①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丸山真男等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做了批判性的检讨。然后将“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作为“他山之石”,试图使其为建构“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发挥作用。思想史,甚至文化研究之中是否应该意识本地文化和异地文化,或意识自己和他者的区别是研究方法上非常重大的问题。当然,真理是普遍的,不依研究者的观点为转移也是可以成立的。从这个立场出发,无论由谁进行研究,真理终究是真理。无论是本地文化的研究,或是异地文化的研究,都与真理本身毫无关系。
对此,葛氏采取了应该自觉地区别本地文化和异地文化,或者自己和他者来进行研究的立场,我赞同他的立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20世纪出现了量子物理学,阐明了如果像迄今为止那样无视研究者存在的话,真理是不可能成立的。况且在人类文化的研究中,并不会存在完全客观的真理,离开研究主体的研究也是无法成立的。脱离了自我认识就无法进行对他者的认识,脱离了对他者的认识也无法进行自我认识。如果想研究本地文化,就会同时牵涉到如何看异地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研究异地文化之际,譬如说日本的中国研究,或者中国的日本研究如果不能各自对本地文化的立场有一个认识,也就无法进行。
此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不同,还有时代也应该予以考虑。人生存在空间和时间之中,所以无法摆脱时间上的时代性的制约。我们生存在21世纪最初的十年之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技术在西方高速发展,并作为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扩展,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亚洲是它的受害者,在这之中最快吸收西方文化而成功发展了近代化的日本则站到了侵略者的立场上,而与受到侵略的中国和韩国持有了相互对立的历史。只有立足于以往历史,今天的亚洲研究才可能成立,而如果无视它,则历史研究无法成立。
这样看来,如果要想在世界公民的公共空间之中建立真理的话,虽然看上去建立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真理,实际上是以西方近代的哲学—科学作为前提,并且带着可能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的危险。爱德华·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②就是这个问题。相反,如果要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其本身就会以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形式——又陷入逆向东方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果避开西方的话,那就无法谈论近代。亚洲主义正是这种逆向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是被虚构的近代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那种亚洲主义也是从本地文化所看到的亚洲,而与从中国看到的亚洲主义和从日本看到的亚洲主义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个问题上,葛氏显示了卓越的洞察力。③
由此可见,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与置身于现代的自文化—他文化、自己—他者的认识有着深切的相互关联。在这种场合里重要的问题是:那种研究态度是否会导致因为把自文化和他文化相互对立而陷于狭隘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本地文化中心主义。与此相对立的可以说是:那种自他的区别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国家”、“文化”等在实体上并不是确定不移的东西,从什么立场出发进行研究是与现在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以及我们从哪里出发建构什么样的主体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因此,应该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有必要通过明确地意识他文化和他者,在尊重他文化的同时,来重新审视自己应有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葛氏通过将日本的日本思想研究作为“他山之石”予以尊重和参考,以此作为反省自我思想的线索的方法,是极为恰当的。
用什么方法把什么样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东西而予以接受,与其说是由宿命所决定的,不如说是通过自己对被置身其中的环境的选择而形成的。在那里也建立了编织一个“故事”的自己的立场。那未必意味着是让自己单纯地同某个立场同一化。譬如雅克·德里达虽然置身于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出身的犹太人这样一个边境性的立场,但同时在法国使用法语进行活动,承担了批判性继承西欧哲学传统的工作。像这种置身于边境线上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欧美不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日本的韩国人的思想至今尚未完全确立,但是今后可以有所期待。在今天,并不认为日本是单一的一个,而是承认有“几个日本”的想法日益扩大。赤坂宪雄提出了“东北学”,将日本的东北地方作为自己的据点,试图向“单一的日本”这种想法发起挑战。④就中国而言,是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中心进行观察,还是以包含少数民族多种文化的中国来观察中国文化,其看法会大不相同吧。
这样看来,“日本”的立场或“中国”的立场,绝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也不应该把近代民族国家予以绝对化。但是,如果要想思考经历了近代期的现代问题的话,毫无疑问,无法摆脱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关联的民族主义问题。暂且不说将来是否会以什么方式使现在的国家消亡,在目前的阶段,以现有的国家框架里形成起来的文化为中心进行考察,也许是迫不得已的。
二、研究者之间认识的错位——围绕“本觉思想”的理解
上述部分抽象地讨论了一些文化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想从作为本人专业的佛教史的领域列举一些具体的例证。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于2004年11月所召开的第一届中日佛学讨论会上,以“本觉思想”作为了讨论的议题。⑤“本觉思想”无论在今天中国或在日本的佛教研究者中间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那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为活跃的讨论。所谓“本觉”,出现在《大乘起信论》这本书里,是我们众生的自身之中所具有的觉悟的本性。现在已经很明确的是,在印度的文献里并没有这个词。在印度的文献里,开启觉悟的可能性被称为“如来藏”或“佛性”。“佛性”的概念在中国的佛教里也受到重视。“本觉”是对“如来藏”或“佛性”等概念的发展,其特征就是强调觉悟的本来性。不知道自身内部具有觉悟的本性的状态是“不觉”,从不觉向本觉修行的过程被称为“始觉”。
“本觉”特别在中国的华严宗里受到重视,并作为核心概念而被使用。中国的华严宗从唐朝中期以后,强调人心的绝对性,并提出世界来自于那个心的展开。为了明确地说明那种心的绝对性,而经常使用“本觉”这个词。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在称呼“本觉思想”的时候,大多是将其看作是从《大乘起信论》展开的华严的思想。顺便说一下,这种把心看作世界的根源性原理的华严的思想,以后对儒教的根源性的探究予以很大的影响,对宋学的“理”和“太极”等观念的形成也予以了影响。因此,中国的研究者关注华严的“心”和“本觉”的概念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日本所使用的“本觉思想”这个词具有稍微不同的意思。本来“本觉”这个词自古以来就有,但是“本觉思想”这个词是日本近代研究者开始使用的一个新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是由田村芳朗经常使用而使之普及的。⑥但是,由于田村芳朗的影响力而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的“本觉思想”这个词,原来起源于《大乘起信论》,与中国华严所重视的“本觉”的问题并非没有关系,但是其意思有一些不同。这就是将原来在佛教里被否定的世俗的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现象世界的总体原封不动地予以绝对的肯定,并进一步认为无须进行修行的思想动向。基于这种思想,那么地狱作为地狱本身是完全的,所以没有必要脱离地狱。不仅仅是动物,即使草木按照其本来的姿态也是完全的,并显示出成佛的姿态。这种思想是在日本中世的天台宗里特别发展起来的,因此,从比较限定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可以说是“天台本觉思想”。但是,不仅仅是天台宗,其他的宗派里也能看到,所以也就不限定为“天台”,而直接称为“本觉思想”。⑦
这粗看上去似乎与起源于《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的概念没有关系,但是为什么被称为“本觉思想”呢?日本中世的天台宗,站在“本觉门”和“始觉门”两个立场。这固然起源于《大乘起信论》的“本觉”和“始觉”,但是其用法与原来稍微有些不同。所谓“本觉门”就是无须进行修行,承认人和世界的原来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绝对的立场,而与此相对,“始觉门”是立足于承认有必要进行修行的立场。在日本的天台宗里认为“本觉门”比“始觉门”居于更高的位置。这个“本觉门”的思想在进入近代被重新评价的时候,称为“本觉思想”。因此,“本觉思想”的最为极端的形态就是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任何人为的改变,只要放任自然就可以了。
这种“本觉思想”和中国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很相似。但是,“无为自然”必须经历脱离人为这个过程,与此相反,“本觉思想”并不需要这个过程。在中国最为近似的思想形态可以举出被称为“无事禅”的禅的动向。“无事禅”将马祖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推至极端,将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看作是觉悟,认为坐禅修行也没有必要。但是,“无事禅”是彻头彻尾的禅的主体的实践的方式,与此相对,日本的“本觉思想”的特征是:并不限定于人的实践,甚至地狱和草木等人类以外的存在也包含其中。
为什么这种“本觉思想”会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呢?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佛教,也对中世日本文化全体产生了影响。中世的日本文化发现了就自然的原来状态进行欣赏的理想。譬如,我们看到美丽的花绽放会感到喜悦。但是,花会立刻凋谢。一旦凋谢就不会成为观赏的对象。但是,在中世的日本思想和文学里,会在花的绽放、然后凋谢的无常的时间过程中去发现它的美。这种影响遍及能、茶道、花道等的美学之中。这种美学的想法是与“本觉思想”同一性质的,认为这是“本觉思想”的影响所导致,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常常有人会指出:这种美学思想不仅仅是中世,也是直到现代的日本文化的特征。
当然,轻易地说“日本文化的特征”是存在危险的,对此我们还会在后面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日本学者所关注的“本觉思想”和中国学者所关注的“本觉思想”有一些不同。为了方便,我将以日本的“本觉思想”为核心的、将现状视为绝对的形态的“本觉思想”称为“本觉思想A”,与此相对,将“本觉”的原理视为绝对的形态的“本觉思想”称为“本觉思想B”。⑧也可以说日本的“本觉思想”是以A为中心,中国的“本觉思想”则是以B为中心。实际上,在日本的“本觉思想”中也夹杂着很多“本觉思想B”的要素,二者密切相连,所以问题很复杂,但是就大体的倾向而言,是可以这么认为的。因此,在日本提及“本觉思想”的时候,通常在头脑里会浮现“本觉思想A”,而在中国提及“本觉思想”的时候,头脑里会浮现“本觉思想B”。在进行相互讨论的时候,在自己头脑里的“本觉思想”未必是同一个东西,如果那样的话,讨论的时候会发生相互错位的情况。对此有必要予以注意。
但是,日本的“本觉思想”的问题在日本学者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兴起的“批判佛教”运动是以批判“本觉思想”作为其中心课题。“批判佛教”是以袴谷宪昭和松本四郎两位学者为中心发起的,而且在美国的学界也引起热烈讨论,相关论文编成一本英文的论文集,于是这个问题国际化了。那本论文集也被翻译成中文。⑨在那本论文集中有我执笔的一篇论文。“批判佛教”一方面批判日本的“本觉思想”陷于无须修行的现状肯定,而且不仅如此,同时也把印度以来的“佛性”和“如来藏”思想作为与原来佛教的无我论相背离的实在论的想法予以了严厉的批判。因此,作为其对象的范围既包含了“本觉思想A”,也包含了“本觉思想B”,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地方。但是,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个问题成为范围广泛的、国际性的问题。⑩
这是出自日本而引起问题讨论国际化的一个实例。诚如上述所讨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也显现出来对“本觉思想”的理解不同等等——相互的问题意识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问题的国际化也使得我们可以从更新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围绕是否承认作为“本觉思想”的根基的《大乘起信论》及其核心的“如来藏”的观念,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也曾引起很大的论争,对今日中国内地、台湾佛教界也有巨大影响。“批判佛教”并不了解这些情况而重新提出相同的问题,尽管双方存在文化的差异,但可以认为是延续、继承了同一个问题。这样看来,这个问题作为东亚佛教近代化这样一个大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1)有的时候原来在某一个文化里被认为是特殊的那种现象,随着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会被发现:它与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应该欢迎既能够对相互理解的错位予以细心地关注,同时又具有广阔的国际性视野的研究态度。
三、古代的论争的举例——“非情成佛”和“草木成佛”
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问题意识的错位,决不是新的东西,从文化交流开始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举例来考察一下9世纪在天台宗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议论。(12)天台宗在8世纪末由最澄传入日本。最澄在中国从道邃和行满那里学习了天台。当时,天台宗在六祖湛然所领导的复兴以后,再次走向衰退的时期,关于最澄的这两位老师也很少为人所知。在日本,刚刚开始学习天台宗的教义,如果对教义的理解有不明确的地方,便会向中国的天台宗的学者发出寻求解答的信件。这种问答的记录被称为《唐决》而留存下来。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日本方面在考虑什么问题,而中国方面对此又提出了什么观点。在其中有很多天台学中的细小问题,但是也包含着即使在今天也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无情(非情)成佛”的问题。在佛教中,将持有心的存在称为“有情”,并承认其有成佛的可能性。有情是轮回的,具有变化的可能性。动物属于有情,因此有佛性,可以成佛。但是,不持有心的植物或矿物(无情、非情)则没有成佛的可能性。植物或矿物的世界与人也许会因轮回而转生的动物界是根本不同的领域。正由于这个原因,本来有情以外的成佛就不会成其问题。
但是,在中国“非情成佛”也开始议论起来。其中有几种议论的方法,譬如如果依据佛教的唯心说,因为外部世界是心的创作,所以这个心如果成佛,那么由佛创造的世界也与佛一体化。因此,虽然也说“非情成佛”,但是主体是有情的,而非情的成佛则依附于前者而成立。
在《唐决》中,日本方面以此作为问题——“非情成佛”究竟是什么?——向中国方面寻求解答。此时,日本方面是以非情是否也可以发心、修行而成佛来作为其问题的。从佛教的理论来看,这是奇怪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天台宗未必能够予以充分的理解。所谓“有情”是有心的,所以有可能朝着“觉悟”而发心,以求成佛。但是,即使说植物发心、修行而成佛,具体而言是些怎样的事情,实际上不容易理解。因此,根据佛教的常识来判断,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面对这些问题的中国的天台僧侣就是这样回答的。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个回答,日本方面并不认同。日本的安然写了《斟定草木成佛私记》这本书,对中国方面的回答进行了批判。安然并不是很有名的人物,但他是9世纪后半叶日本天台宗的僧侣,也是撰写了大量著作的大学者。他当时希望留学唐朝,但是因为日本的遣唐使停止而无法实现其留学的梦想。于是,他在日本对尽可能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研究,建立了以密教为中心的独自的思想,对以后的日本佛教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也是对佛教日本化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思想家。
安然的《斟定草木成佛私记》继承了《唐决》里日本方面的疑问,对中国方面的解答进行了批判。明确地主张:一草一木也可以各自发心、修行、成佛。按照安然的说法,“有情”的动物与“非情”的植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有情”可以发心、修行、成佛的话,草木也应该可以发心、修行、成佛。那么,所谓草木的发心、修行、成佛,具体而言是些什么呢?安然的著作在进入议论的时候中断了下来,没有能够最后完成,因此他的解答并没有显现出来。安然在他的其他著作里曾经试图从密教的立场予以解答,却未必成功。
但是,日本方面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试图坚持一草一木也可以发心、修行、成佛的说法,不能接受中国方面的解答。而中国方面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问题也觉得无法理解,因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冷淡的处理。恐怕从中国方面看来,日本方面的问题是属于对佛教的基础理论都不理解的那种层次上的问题,所以很难认为是一个可以进行真正讨论的问题吧。
那么,为什么日本方面要坚持、固执这种可以称为奇怪的立场呢?非常明确的理由很难知道,但是如果进行推测的话,可能是在日本将动物和植物予以区别对待的想法比较弱吧。《日本书记》中,在由天上的诸神确定秩序之前的日本的状态,被认为是“复有草木咸能言语”。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泛灵论,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物都受到同样的对待。草木,也就是植物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从安然明确地提倡“草木成佛”这件事中可以得到了解,但这与中国的“无情成佛”、“非情成佛”是不同的。“非情”包含着矿物等无机物。因此,作为“非情”的代表,并不是草木,而是有时被举例为“墙壁瓦砾”之类。在日本,“草木国土”的熟语广为人知,除了“草木”以外,其他也有包含在“国土”之中,但即使如此,也是自始至终地由“草木”来作为代表。
在安然那里无法解决的“草木成佛”的问题,在12世纪才开始得到解决。根据那个时代里写成的、作者不明的《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里的说法,草木的“生”、“住”、“异”、“灭”(即出生、存留、变化、灭亡)的姿态,也就是草木的发芽、成长、衰弱、枯萎等用发心、修行、菩提、涅槃予以表现。即:草木并不进行任何特别的佛道修行,自然原生的状态就是草木的成佛。在《三十四个事书》里则认为:草木甚至没有必要成佛,就按草木的原本的形态就可以。这种自然观对中世的能等艺术,以及茶道、花道等,即所谓“日本式”的文化的形成赋予了相当大的影响。(13)
实际上这种想法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日本式的“本觉思想A”。在那里重视自然原生状态,而对于人为的活动则多予以否定的评价。虽然近似老庄思想,但是老庄则认为:作为人的主体的存在方式,有必要有一个否定人为的活动;而“本觉思想A”则认为:放弃一切努力的草木的存在方式才是理想的状态。丸山真男追溯日本的思想,举出贯穿其中而不变的“古层”或“执拗的低音”就是有一个“成为”的想法。(14)“成为”与“作为”或“创造”相反,就是不做任何人为的努力、放任现状的态度。
丸山尝试发现基于有责任性的个人的主体性而建造的社会所具有的近代社会的特征,在他的成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5)里揭示了在前近代的日本也存在人为的创造社会的想法。但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一个谁都不承担责任而放任现状的无责任体制。丸山试图通过否定那种无责任体制,来寻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新的出路,但是丸山的努力并未成功。在丸山晚年,他似乎放弃了那种希望,他认识到通过发现日本思想的“古层”里“成为”的想法,来使日本思想转轨到“作为”的想法是困难的,并因此陷于悲观之中。
四、关于思想的结构
用简单扼要的言辞说明一个文化的特征,并以此与其他文化比较,这在文化理解上比较方便。将日本文化和思想赋予“成为”的特征,将“本觉思想A”视为“日本式”的思想,在一般通俗的场合里会受到欢迎,而且它也并不是完全错误的。日本18世纪天才的思想家富永仲基曾经进行过印度、中国、日本的文化比较,认为:印度人喜欢“幻”,中国人喜欢“文”,日本人喜欢“绞”(《出定后语》,1745年)。“幻”是指神通力那种超现实的事物,“文”是指文词装饰那种繁杂的事物。与这些相对的“绞”比较难于理解,是指性急难耐的状态。富永所勾勒的这些特征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些概观式的特征很难有更多的讨论的空间,在学术上最多不过是具有一种参考的价值。
这样的将文化和民族的全体内涵赋予某些特征,具有导致文化和民族性决定论的危险。譬如皇帝制度是直至清朝为止的中国的传统,对此谁都无法否认。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皇帝制度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因为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彻底崩溃了。这样的话,包含制度的文化是变动不居的,断定式地判定其特征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中完全不会改变、而且在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是并不存在的。本来,一个民族和文化本身的范围会根据时代而改变。就中国而言,不仅仅是汉民族,也因少数民族的如何关联,其文化的性质会大相径庭。日本文化的场合,本来几乎都是从大陆获得,就民族而言,也是混血的,并不会存在那种单一而且不变的所谓“日本民族”。
那么,如何具体地考察思想史和文化史呢?那就不是考察全体的概括性的特征,而是有必要去理解在各个时代里各种思想如何相互关联的内在结构,以及动态地观察其如何变化。譬如就中国的皇帝制度具有革命思想,而日本天皇制度则是由一个家族继承,经常被指出是二者的区别之处。这件事就概括性的特征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仅仅对此进行指出的话,则对讨论的进展并无帮助。应该说明它们在具体的历史中是如何地展开和变化的。
以其他为例的话,譬如我们来尝试考察一下各种宗教和思想的潮流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在中国,儒、佛、道被称为三教,在日本,儒、佛、神道被称为三教,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涉被认为是大问题。在中国由道教所占据的位置,在日本是由神道所占据。道教原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老庄思想,但是作为系统的宗教则是受到佛教的巨大影响而形成起来的。日本的神道是土著的神灵信仰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体系化的,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类似的。
但是,道教和神道的历史地位未必完全相等。在日本,“神佛习合”的传统很长,佛教和神道相互之间密切交涉而形成一个体系。神道和佛教作为不同宗教而确立起来,是到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的时候,因为政府命令进行“神佛分离”而开始的。从漫长的传统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新近的事情。而且即使已经分离,到现在也并非区分非常严格。即使在现代,日本人也去神道的神社和佛教的寺院拜神、拜佛。而且二者分担着不同的职能。与人的出生相关的事情,则参拜神社。譬如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或者祈福儿童成长等时候。新年也到神社参拜。与此相对的是,佛教的寺院则更多处理与死有关的事情。葬礼和死后的法要大多在寺院举行,在神道的神社举行的则很少见。这种分工体制在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的关系上是看不到的。
三教之中,儒教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和日本也是不同的。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儒教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普及,它既是政治理念、伦理准则的同时,也和生活礼仪密切关联,拥有一套礼的体系。与此相对的是,在日本虽然儒教是武士阶层的政治哲学、伦理体系,但未必包含日常生活的礼仪。特别是在德川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叶),根据幕府的命令葬礼必须用佛教的仪式举行,而儒教仪式的葬礼则受到禁止。由于没有日常的礼仪,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儒教会急速的衰落。虽然孔子屡屡受到批判,即使在今天也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教则由新儒家进行着复兴。与此相对,日本则难以考虑在现代复兴儒教。
近代思想与佛教的关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课题,它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在中国和日本吸收西方的新哲学的时候,都为了对其进行理解,而在传统思想中寻求有关线索。于是,佛教受到了关注。在中国,19世纪中叶出现了杨文会,开始了佛教复兴,此后,康有为、章太炎等寻求变革的思想家们也对佛教予以关注。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初期,佛教势力开始衰弱,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推动了“佛教再发现”。近代是日本与中国的佛教交流非常频繁的时期。直至近代为止,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比较多的时期,到了近代,则是中国向日本学习,并接受其影响比较多的时期。(16)但是,与日本的知识人逐渐加深禅和念佛等实践佛教的关注相比较,中国的知识人则较为喜好唯识,更多关注哲学的讨论。
这样,中国和日本都是三教相互关联,但是,中国方面的儒、佛、道的关系与日本方面的儒、佛、神道的关系,大相径庭的地方很多。从上述的例子中可以了解到,在异文化的思想、宗教作用的比较过程中,如果限定某些特定的概念或思想则可能无法看清全貌,而且容易引起误解。
我在上面就异文化之间如何相互理解各自的思想,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使双方发生误解,以中国和日本的佛教的事例为中心,进行了粗浅的考察。佛教无论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日本而言,都是外来思想,就这一点而言,作为比较的材料是非常合适的。从上述几个事例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与日本,粗看似乎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似的思想和现象,但是详细地予以观察,二者之间存在不少的差异。这种差异虽然看上去很小,但是如果不是明确地理解这种差异的话,也会成为产生很大误解的原因。
理解作为他者的异文化决不是容易的事情。很多情况下容易导致相互误解,有时也会造成国民感情的纠葛,甚至相互敌对的结果也并不少见。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不应该轻易地认为可以立刻理解异文化,而应该经常意识到这是一个理解上有很多困难的他者,在考察思想的背景的同时,认识思想的差异和不同。只有把他者作为他者进行认识,反而会开启准确理解他者的大门。
*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张翔副教授翻译。
注释:
①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3期,《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4年8月)。这篇论文另收入葛氏的著作《西潮又东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听说前者只是一个缩写,而以后者为详。2005年1月,我邀请葛兆光在东京大学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那时,围绕葛氏的该论文,以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为首的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也参加了讨论。为了这次学术会议,以《复印报刊资料》所收的葛氏论文作为底本翻译成日语(翻译者:池丽梅、张欣、王芳),这个翻译,以及包含我对此的看法的论文“思想和思想史”收入末木文美士编《日中近代哲学的佛教》(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2005年3月)。在做了进一步的修订以后,预定在《思想》(岩波书店)2007年9月号刊登。
②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1978.中文版《东方学》(王字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
③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收于《西潮又东风》)。
④赤坂以东北艺术工科大学东北文化研究中心为据点,1999年开始发行季刊杂志《东北学》,兴起了以东北地方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日本的中外日报社联合举办了自1985年至2003年共10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日佛学会议”续其后,预定由中国人民大学自2004年开始,隔年主办一次。2006年举办的第2届会议以“佛教的本土化”作为主题,我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参与了会议。
⑥参见田村芳郎等编《天台本觉论》,岩波书店,1975年。
⑦关于日本的本觉思想,请参见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思想史论考》(大藏出版,1993年)、《镰仓佛教形成论》(法藏馆,1998年)等。
⑧关于“本觉思想”A和B的区别,在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的发表论文《本觉思想的定义和类型》、拙文《本觉思想与密教》(《系列丛书密教》4,春秋社,2000年)有所论述。
⑨参见J.Hubbard&P.Swanson(ed.)Pruning the Bodhi Tree,Hawaii,1997.中文版《修剪菩提树:“批判佛教”的风暴》(龚隽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⑩在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上,“批判佛教”的主要倡导者松本史朗不但参加了,而且与中国方面的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1)作为最新的成果,唐忠毛的《佛教本觉思想论争的现代性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从这个观点出发,讨论了“批判佛教”的本觉思想批判的问题。但是,唐也没有区别本觉思想的A与B。
(12)以下部分,也请参见末木文美士《平安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春秋社,1995年)。
(13)参见拙文《能与本觉思想》(收于《解体的言语与世界》,岩波书店1998年)。
(14)参见丸山真男《历史意识的古层》(收于《忠诚与叛逆》,筑摩书房,1992年)。
(15)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中文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
(16)参见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收于《西潮又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