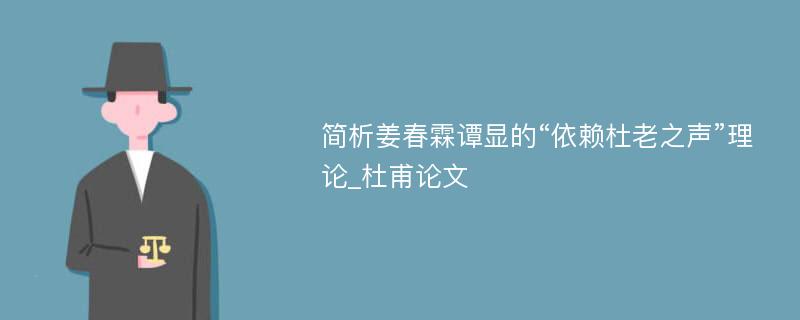
谭献关于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说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春论文,倚声家杜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3)06-0096-05
一、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说并非空穴来风
谭献《复堂词话》评骘《水云楼词》有一段精彩的话: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
谭氏从“正变”、“家数”的角度观照文学本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确为探本之论。文学正变发源于政教得失。什么是“变”呢?《诗大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质言之,“变”即乱世之音,“清商变徵之声”。《论语·阳货》云:“诗可以怨。”从“变风变雅”的怨刺传统看《水云楼词》的伤离悼乱,确实“流别甚正,家数颇大”,堪称风雅之苗裔。谭氏把《水云楼词》放在“咸丰兵事”的特定时空中去审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他把蒋词的成就归于天意,似带有唯心、神秘的色彩,但“咸丰兵事”毕竟是近代历史的真实存在,它影响并生成了那个时代士子的群体心态。而蒋春霖的文学生态与杜甫有惊人的相似,在诗学精神上亦同归一脉,前后相承,所以称他为“倚声家杜老”,并非凿空之论。《水云楼词》声誉之隆,莫过此评。谭氏之说一出,海内翕然从之,几乎一锤定音,时贤或后人纷纷祖述。各家肯定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主要是着眼于《水云楼词》真实反映了晚清末世这个干戈纷扰、陵谷变迁的时代文人普遍的迷惘心绪,具有“词史”的价值。很显然,谭献诸人的鉴赏判断带有正统士大夫的倾向。但他们较贴近作品本体,对《水云楼词》的艺术特质,颇具真赏。然而,不容回避的是,蒋春霖在词中流露出对太平天国革命强烈的怨毒之情。这种敌对情绪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晚清士林群体心态的折光。谭献诸人对蒋春霖政治立场的认同或模糊,无疑有着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是一种落后的世界观,理应引起必要的批判。
然而,我们一旦纯粹用阶级观点分析《水云楼词》,就会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持彻底否定态度,认为《水云楼词》“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完全是封建糟粕,应该坚决抛弃的。”[1]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则一口咬定“蒋词无法和杜诗比美”,主要因为蒋春霖“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抱着敌视的态度,并把农民军诬之为‘贼’。”[2]周梦庄、谢孝萍皆谓“鹿潭不能配享草堂”,因为“杜甫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诗圣’的形象,这一切比蒋鹿潭高大得多。”[3]这类否定蒋春霖“倚声家杜老”的观点,一味从词人的政治立场出发,极少艺术上的品鉴,失之偏宕。此说背离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堕入了庸俗社会批评的泥淖。
至于新时期出版的几种文学史,如袁行霈、章培恒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等,对蒋春霖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作了淡化处理。书中对《水云楼词》的抒情艺术,有了较深的把握,但对“倚声家杜老”一说始终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缺乏专题的探讨。针对《水云楼词》评价的误区,严迪昌先生中肯地指出:“蒋氏词为特定时空之产物,可以褒亦可以贬,唯求公允客观耳。回避不可,抹杀尤不可,是乃绝非唯物史观之治学态度也。”[4]遗憾的是,严先生的《清词史》对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这一词学命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倚声家杜老”说或许存在着谭献艺术上的偏嗜,但他特别强调《水云楼词》乃“清商变徵之声”,“咸丰兵事,天挺此才”,联系安史之乱,玉成少陵,那么这一说法确非空穴来风。诚然,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不可挑战性。他的影响正如清人叶燮《原诗·内篇》所云:“杜甫诗,包源流,综正变。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他的诗既“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5]集前代诗学之大成,又“伐山导源,为百世师”,[6]启后人门径之无限。这样的“诗圣”,后人无不景仰,谁敢跟他并肩呢?但是谭献是颇有些反叛精神的,他在《复堂词录序》中说:“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他重视读者的感悟,这一审美思想已经包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因子。谭氏正是本着“何必不然”的审美心理,提出蒋春霖“倚声家杜老”这一词学命题。我认为只有破除心理定势和审美成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美学的眼光去看待杜诗蒋词,才会“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7]
二、蒋春霖与杜甫天赋性情、文学生态的相似性和诗学精神的传承性
《水云楼词》能冥契杜诗,最主要的是蒋春霖的天赋、性情、遭际与杜甫相似。蒋春霖少年颖悟,据金武祥《蒋君春霖传》记载:“(春霖)幼随荆门公(指春霖父蒋尊典,官荆门知州)任所,久涉郢汉,得江山骚赋之气为多。……尝登黄鹤楼赋诗,老宿敛手,一时有乳虎之目。”杜甫亦是早慧的诗人,《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蒋春霖不媚于俗,与世为忤。《东淘杂诗》云:“渐懒折腰步,犹能抱膝吟。艰虞尝傲骨,齑米损文心。”杜甫高风跨俗,刚肠嫉恶,“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壮游》)春霖有经世之才,“排金门,历元阙,任承明著作无愧。即出肩民社之贵,理棼千剧,有余裕也。顾名不通版,浮沉掾曹,又为世摈弃,将以词人终,遇亦穷矣。”[8]《水云楼词》掺杂着蒋春霖青衫憔悴之悲。词云:“漂零漫惜青衫,算舞散湘皋,都是憔悴。”(《瑶华》)“青衫铅泪似洗,断笳明月里,凉夜吹怨。”(《台城路》)杜甫自比稷契,欲“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十年长安困守,“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同上)。春霖晚年穷困潦倒,到苏州依附友人杜文澜,杜拒绝接纳,他失望而归,“舣舟垂虹亭,一夕而卒”。[9]杜甫暮年漂泊西南天地间,阻水耒阳,舟次方田时,客死于孤舟。两人的结局竟是惊人的相似!杜甫《天末怀李白》诗云:“文章憎命达”,又云:“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委实道尽了异代才人的琐尾流离之悲。杜、蒋都是清醒仁爱的性情中人,才气纵横,而命途乖蹇,又遭逢乱世,发之于诗词,宜有其相似的艺术风格。
蒋春霖早岁为诗,瓣香少陵,得其金针。金武祥在他搜辑的《水云楼词剩稿》序言中说:“余近得其古近体诗剩稿不及百首,恢雄沉厚,亦多可传。……余谓即以诗论,实亦神似少陵。”[10]李肇增推许蒋春霖《东淘杂诗》十六首,“不减少陵秦州之作”。[8]聊举《东淘杂诗》二首以管窥:
大有衣裳会,俄传草木兵。烽烟危隔县,舟楫聚荒城。野哭空皮骨,民穷一死生。明堂谁献颂,犹喜说时清。(其十三)
郁勃祢衡鼓,单寒季子裘。杜门花避俗,因树屋宜秋。笔退怜儿病,尊空与妇谋。莼鲈期远近,愁绝五湖舟。(其十四)
再录杜甫《秦州杂诗》二首以资比勘: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其七)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峰峻,悬车幕井干。风连西极动,月过北庭寒。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其十九)
诗风之沉郁,诗人之忧世伤生,杜、蒋可称波澜莫二。
蒋春霖中年曾焚弃诗稿,对友人云:“吾能诗匪难,特穷老气尽,无以蕲胜于古人之外,作者众矣,吾宁别取径焉。”[9]“别取径”即专力为长短句,将杜诗之“凌云健笔”移入词体。《水云楼词》化用杜诗较多,确能脱胎换骨,与古为新。(注:兹列举《水云楼词》化用杜诗的例子如下:《水兰花慢》:“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从《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及《返照》“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化出。《木兰花慢》:“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从《秋兴》(四)“鱼龙寂寞秋江冷”化出。《虞美人》:“银潢何日销兵气,剑指寒星碎。遥凭南斗望京华,忘却满身清露在天涯。”从《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及《秋兴》(二)“每依南斗望京华”化出。《忆旧游》:“酒态添花活,任翩翩燕子,偷啄红巾。”从《丽人行》“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化出。《一萼红》:“漫惆怅、天寒袖薄,唤玉笛、吹怨入空林。”从《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化出。《庆春宫》:“却月疏帘,玉臂清辉。”从《月夜》“清辉玉臂寒”化出。《满庭芳》:“空江上,沉沉戍鼓,落日大旗孤。”从《后出塞》“落日照大旗”化出。《淡黄柳》:“写遍残山剩水,都是春风杜鹃血。”从《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化出。)只此一端,即可看出蒋春霖善学杜诗,将其深厚之旨隐括入词,浑成妥帖,又具飞动之美。
杜甫作诗惨淡经营,刻意不渝,追求“毫发无遗憾”(《敬赠郑谏议十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蒋春霖倚声,情况皆同老杜。春霖工于炼字,往往一字传神,警动异常。如:
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木兰花慢》)
步前汀未晚,舟小蹙波行。(《一萼红》)
点波细雨,乍泥住归人,便迟春信。(《扫花
懵腾梦在寒潮里,浪啮船唇语。(《探春讯》)
细竹通凉,疏苔媚雨。(《琐窗寒》)
“圆”、“蹙”、“泥”、“啮”、“媚”,不独体会入微,壮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音节浏亮,新隽有味。《水云楼词》炼意清畅而不甜俗,精健而不生涩。如:
绕船三月落花多,是千点泪痕红聚。(《西子妆》)
长亭燕子,偏不许春光别南浦。听歌声、唱到将离,悄衔花瓣飞去。(《尉迟杯》)
待攀取垂杨寄远,怕杨花比客更飘零。(《甘州》)
像这样的好句,《水云楼词》中不一而足。蒋春霖的刻意烹炼,体现了对杜诗浑厚、灵动之美的追求。
《水云楼词》在韵律上亦力追杜甫的诗美境界。杜甫说“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十九曹长》)。杜诗在韵律上的精严老到,堪称律诗之圭臬。蒋词持律甚细,可摩少陵之垒。何咏《〈水云楼词〉序》云:“鹿潭所作,于九宫七始八十四调,不差累黍。而能天机开阖,云情偕畅。别具工自成馨逸。视夫胶柱聆音,引绳约尺,目论一孔,计穷三变者,不啻水观海而泥忆云矣。”姚燮谓《水云楼词》“绳尺之中,自有天籁。羽宫所在,能移我情。”[11]守定四声,而不以音律害意,臻于自然高妙之境界,有清一代,实为罕见,蒋春霖《水云楼词》此其一。
蒋春霖对杜诗艺术的汲取,不仅在文字、句法、韵律等形式技巧上,更主要的是在《水云楼词》中溶入了“沉郁顿挫”的风格。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清人词略》中论及《水云楼词》时,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词中有鹿谭,可谓止境。谭仲修虽尊庄中白,陈亦峰亦崇扬之,究其所诣,尚不足与鹿谭相抗也。词有律有文,律不细非词,文不工亦非词。有律有文矣,而不从沉郁顿挫上着力,或以一二聪明语见长,如《忆云词》类,尤非绝尘之技也。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与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楼为冠,亦无愧色焉。
吴氏不满足于词体“有律有文”的形式美感,而将“沉郁顿挫”的杜诗风格作为倚声的“绝尘之技”,正是洞见了《水云楼词》中潜在的杜诗影响。吴氏推尊《水云楼词》为清词之冠,也恰恰是从“沉郁顿挫”着眼的。
蒋春霖尝谓:“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与异否也。”[8]他将诗词置于同等的地位,追求“风雅之旨”。这一词学品格与谭献说的《水云楼词》“流别甚正,家数颇大”正可相视莫逆。而“情至韵会”的审美理想与“沉郁顿挫”又是息息相通的。“沉郁”是就“情”而言的,“顿挫”是就“韵”而言的。周振甫先生《诗词例话》在谈到“沉郁”的风格时说:“沉郁这种风格,需要有深厚的内容,激越的感情,内容不深厚,就浅露,感情不激越,就和缓,那就不能构成沉郁的风格。”《水云楼词》得杜诗真髓,即体现在“从沉郁顿挫上着力”。蒋春霖生当清季,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加之英俊沉下僚,郁郁不得志,登山临水,伤离悼乱,将深沉激越的情感寓于抑扬抗坠的旋律节奏中,得到了曲尽其致的传达。如《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
泊秦淮雨霁,又灯火、送归船。正树拥云昏,星垂野阔,暝色浮天。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梦醒谁歌楚些,泠泠霜激哀弦。婵娟。不语对愁眠,往事恨难捐。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
此词感时伤事,表达了深沉的忧国之情。词中“往事恨难捐”之“往事”当指鸦片战争时期,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四日英军攻陷南京事。“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这三句实写英人军舰在长江上肆无忌惮地航行,清军武备废弛,无法阻挡。“鱼龙”隐指腐朽的官僚老爷,他们高枕无忧,哪管侵略者的横行。词人悲叹时局,惟有将一掬伤心之泪,“付与秋烟”。谭献《箧中词》(五)评此词曰:“子山、子美,把臂入林。”此评深得词人之词心。庾信羁留西魏、北周而怀梁朝,杜甫位卑而一饭未尝忘君,爱国情怀,春霖堪与二公“把臂入林”,而无愧色。从艺术上看,此词境界苍凉阔大,既激越,又低沉,当得起“沉郁顿挫”之誉。其他像《扬州慢》(野幕巢乌)、《淡黄柳》(寒枝病叶)、《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凄凉犯》(短檐铁马)、《甘州》(悔年时刻意学伤春)、《水龙吟》(一年似梦光阴)等,皆能接武杜诗,得其沉郁顿挫之妙谛。从诗学角度看,谭献称蒋春霖为“倚声家杜老”,不愧大匠手眼。
三、杜诗与蒋词的人道精神、阶级意识并无异辙
“诗史”与“词史”都具有史料价值,但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体,绝不是史事的简单排比,而是创作主体以其诗人的敏感,去形象地描绘历史画卷,表现时代精神,并将个人的心态、情感的体验融会在历史的整体观照之中。杜诗与蒋词都蕴涵着社会脉搏的深层律动。
先说杜诗。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在那万方多难的时代,他和人民共度流亡的生活,艰难备尝。他深入底层生活,并投身朝廷实际斗争,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等一系列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这些诗篇洋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可谓具一代之兴亡,与风雅相表里。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明人陈献章说得好:“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12]诚然,杜诗既是十分独特的自我表现,又为时代和人民发出了呼声。他说出了人民心坎上的话。如: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
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又呈吴郎》)
然而杜甫又是反对农民起义的。杜诗《甘林》云:“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什么是“远奋飞”呢?就是远走高飞,铤而走险,造反起义。所谓“死王命”也就是顺从王命,绝不反抗。《喜雨》诗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诗句下自注云:“时闻浙右多盗贼。”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要清洗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是什么人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即袁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再如《夔府书怀》:“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杜甫的诗意就是强盗厉害,虽是绿林小盗,也不能轻忽。对于“苍生”,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防患于未然。可见杜甫的阶级意识多么强烈!忠君即是爱国,儒家文化意识的深沉积淀决定了杜甫不可能偏离封建轨道。虽然命运多舛,但一旦农民起义的风暴袭来时,他依然会坚决反对的。
再说蒋词。蒋春霖处于咸同乱世,自咸丰元年(1851)就任淮南盐官至同治七年(1868)卒于吴江垂虹桥舟中,这十七年的时间一直漂泊在扬州、东台、泰州、盐城的水网地带,身经兵燹离乱之苦,一腔黍离之悲,尽付之倚声。《水云楼词》描写战乱,笔力主要聚焦于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的怒潮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所至之处如摧枯拉朽,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大多数知识分子出于儒家正统观念对这场以基督教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抱有本能的阶级敌视和文化抵触,加之革命的巨大破坏性带来的灾难降落到他们的头上,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怨毒与诅咒。《水云楼词》正是这一群体心态的折光。蒋春霖在词前小序中径称太平军为“贼”,如:
癸丑十一月二时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扬州慢》小序)
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陷贼中数月。(《虞美人》小序)
词中多以“磷火”、“阴磷”“鬼火”、“秋磷”影射太平军。如:
秦淮。几星磷火,错惊疑,灯影旧楼台。(《木兰花慢》)
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灭。(《台城路》)
十里深芜阴磷碧,哭青山、谁唤春魂语。(《金缕曲》)
月黑流萤何处?西风黯、鬼火星星。(《扬州慢》)
惊飙乱起,满地青枫,弥望秋磷。(《庆春宫》)
从“鬼火阴磷”这个阴森恐怖的意象当中,我们不难发现蒋春霖对太平军露骨的仇恨。他在东台任富安场盐大使时,“恤灶利,课团丁御侮”,[13]积极准备对抗太平军。他把战争的疮痍完全推到太平军的头上,认为太平军肇乱,致使生民板荡,而不从清王朝统治的根本颓败找原因。
但是蒋春霖的思想又绝非“反对太平天国革命”所能牢笼,他的《水云楼词》涵茹着深广的人道精神。诚如唐圭璋先生《蒋鹿潭评传》所指出的那样:“他对于家园的飘摇,人民流离所失的景象,也都有一种诚挚而伤痛的叙述。……一种风尘沦落之感,和无国、无家的情绪,都写得深透无匹,而一腔温柔忠爱的心迹,竟与屈灵均、杜少陵如出一辙。”这个评价实在并无虚美之处。《水云楼词》是晚清动荡社会的产物,作品所反映的战争乱离的场景、文人的迷惘心绪是极为真实的。近人郑骞《成府谈词》云:“词人写乱离情况者,鹿潭为古今第一,虽白石亦无其清厉。”可谓知言。《水云楼词》写乱离之景,不只是个体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表达了人民对和平,对正常生活的向往,同样说出了人民心坎上的话。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杜诗蒋词所着力描写的都是他们生存的那个年代。两部作品在人民性、阶级性、艺术性方面都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在词艺上,蒋春霖的《水云楼词》能师法老杜,得其金针,将沉郁顿挫的风格融入词心,无愧于“倚声家杜老”这个称号;在仁爱之心上,《水云楼词》抒发了民胞物与之怀和爱国主义精神,亦能与老杜把臂入林。但二者在胸襟、气度、力度、眼界以及影响方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杜诗追求“掣鲸碧海”的雄浑之美,虽多伤乱话语,却无悲观厌世的倾向,“其才则海涵地负,其力则排山倒海”,[14]具有“向上一路”的美学品格。而从《水云楼词》的情调看,蒋春霖未脱才人窠臼,穷老气尽,情思郁而不化,给人沉重的压抑感和幻灭感。此外,从诗词的功能看,诗的叙事性强,造语醒豁,更适于描写现实,所以较容易为读者接受。杜诗的巨大影响,与此不无关系。而词乃是一种狭深的抒情文体,行文注重含蓄吞吐,潜气内转,象征隐喻的色彩极浓。蒋春霖服膺常州词派“言内言外”,“比兴寄托”的创作取向,《水云楼词》中多用比兴,不落言笔、诸多意蕴待拟想而填补,因而也不易为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些都是蒋春霖无法取得与杜甫并肩的地位,终究不足配享草堂的原因。
收稿日期:2003-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