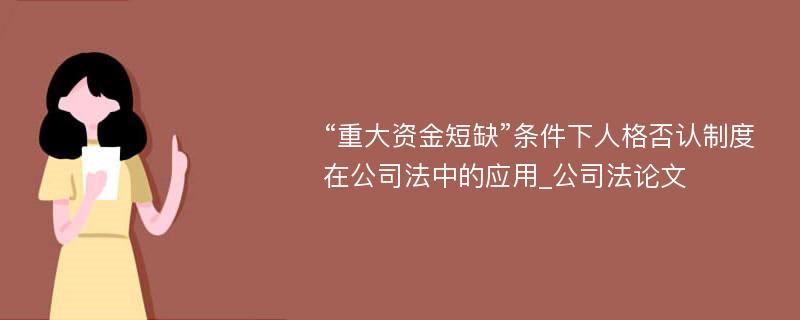
“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司法论文,人格论文,资本论文,制度论文,情形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15/j.cnki.fxpl.2015.03.019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公司资本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促进商业发展和鼓励创业的现实需求下,降低甚至是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发展趋势。在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上,立法者的天平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中更加倾向于追求效率、在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博弈中更加倾向于保护股东。2013年12月28日,我国《公司法》也应潮流而动,对资本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同时,对发起设立的公司采取了完全自由的认缴制。 由于法律总是在寻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当公司资本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选择了效率后,如何保障交易安全,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随即成为《公司法》适用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有力措施之一,将真正从“法条跃入实践”。尤其是,没有了最低资本的限制和实缴制的要求后,基于“资本显著不足”的原因适用法人否认制度,以此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将会陡然上升。然而,产生于判例法的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引进时间尚短,司法适用的裁判标准还不明确,在资本制度改革后,如何正确判断“资本显著不足”,从而通过法人格否认制度衡平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通过对境内外以“资本显著不足”为原因的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该制度的适用需要准确把握如下几个核心要素:“资本”如何界定?“资本显著不足”如何判断?“资本显著不足”的具体适用情形和条件有哪些?“资本显著不足”时的民事责任又该如何承担? 一、“资本”的内涵: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抑或净资产? 对“资本”内涵的准确界定是正确适用“资本显著不足”引发的法人格否认的基本前提。如何认定“资本”,司法实务界与学界有不同看法。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是以公司的注册资本来确定“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的“资本”额。对此,学界有不同认识。尤其是在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在认缴制下,注册资本额不必然等于实缴资本额,为此,有学者就认为,判断“资本显著不足”时的“资本”应以“实收资本”为标准,即公司的实收资本与所经营的事业相比是否明显不足。①换言之,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源于股东实际资本与营业规模不相称时,可以认定为股东滥用了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②而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资本制度虽为认缴制,但仍属于法定资本制的范畴,只是可以分期缴纳,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的缴纳方式。在分期缴纳制下,判断资本显著不足的标准仍然应当以注册资本作为判断标准。③另有学者则认为,应当根据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公司“资本”额,一般情况下“资本”是指注册资本;但是当公司设立时股东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实的情况,“资本”则应指公司的实收资本;当股东在有效成立公司之后抽逃出资、转移资产逃避合同义务时,“资本”则应指抽逃后的净资产。④可见,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并未形成共识。 那么,究竟应以何种标准认定“资本”?通过对域外案例的考察以及制度设计本意的探寻,我们可以发现,“注册资本”标准值得采纳。 首先,从法律角度看,“资本”一词在公司法的语境中一般即指注册资本。尽管,目前学界及司法实务界批评“注册资本”不过是公司成立时登记的一个抽象的数额,并不代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真正的净资产,但无可否认的是,公司注册资本体现了股东的出资信用,代表着股东对公司经营所需承担的责任。如果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则表明公司股东利用公司人格经营其事业的诚意欠缺。这种利用较少资本计划经营大事业者或者高风险事业者,目的就在于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降低,并通过公司形式将其外化给公司债权人。这显然有失公平。在美国司法实践看来,充足的资本是承认公司独立人格,赋予股东有限责任的基本条件。法律允许为了特定目的设立一个公司来避免个人责任,⑤但是这个权力并非没有限制。“如果一个公司被组织起来并进行运营,但是无足够与其可能须承担的责任相适应的资本,致使公司很可能没有足够的资产来清偿债务,那么允许股东们通过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公司来逃避个人责任是不公平的。”“如果试图设立一个公司,但却没有提供与其可能会需要向公司债权人所承担的经济责任相适应的足够的资本,那么股东们也不应当逃避公司的债务。这已经成为了一项公共政策,就是股东应该诚信地投入与公司未来的责任风险相适应的资本。如果同公司将要从事的业务和可能导致的损失相比,公司的资本是严重不足的,那么这将构成拒绝承认其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特权的一个基础。”⑥因此,股东应当根据业务风险,诚实地投入“适度充足的”(reasonably adequate)、“无负担的”(unencumbered)资本,来应对潜在负债。⑦在德国学者看来,对债权人而言,原始资本是一种担保金额,必须至少有一次真实地缴付过它,且只要公司财务没有超过原始资金,就不可以向股东进行支付(第30条第1款,原始资本的交付和维持原则)。⑧我国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法律人格要素之一,而在此意义上的财产首先指的便是公司资本。公司以资本作为其对外独立承担责任的最低担保,与债权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往往是导致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⑨ 其次,“资本”应当不只包括实缴资本,而且应包括认缴后还未届缴纳期限的待缴资本。我国2005年的《公司法》修改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分期缴纳的资本制度。在该制度下,发起设立的公司(一人公司除外)注册资本一次性发行完毕,但可以分期缴纳。该制度设置的初衷在于“避免公司设立初期经营活动尚未充分展开导致的资本闲置和浪费现象,并避免奉行实缴资本、资本确定原则下繁琐的公司资本增加程序”。⑩待缴资本的性质,可以被界定为是公司的债权,在会计上可将其归入公司资产中的“应收账款”科目。因为从出资者投资入股,成为股东的行为过程来看,出资者认缴出资或认购股份的行为构成允诺,并以此作为其取得股权或股份的对价。这种对价理应属于公司资产,但因其还未届履行期,因此,可将其视为远期债权。此外,股东认缴资本构成了对社会公众和广大潜在债权人的承诺,虽然在公司成立之时不必缴纳,但迟早要缴。这一义务并不因履行期未至而解除。倘若公司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偿债程序,认缴资本的股东必须在其承诺的认缴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美国,公司法理论将股东这种已认缴而未实缴的责任,称为其法定债务,可以由公司债权人直接向股东请求。(11)在我国,《企业破产法》第35条也体现了该思想,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可见,将未届缴纳期限的出资视为公司对股东享有的未届履行期的债权有其合理性。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条之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可知,股东应缴而未缴的出资额应构成公司责任财产的基础。尽管股东之间对于出资期限有约定,且该约定为公司章程所认可,但这种约定仅为章程的自治性约定,体现了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而公司以其全部财产为限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是法律规定,属于外部关系。有关认缴出资时间的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外部债权人。综上,既然股东已经通过公司章程和商事登记向债权人明示了自己的注册资本,那么,全体股东就应以认缴的资本对债权人承担责任,即使股东认缴资本的出资期限未至,若公司已经出现无法清偿债权人债权的情形,股东认缴的出资也负有加速到期义务,以满足债权人的利益诉求。可见,仅以实收资本作为判断资本显著不足的依据不符合立法原意。 最后,以净资产来界定“资本”属于误读。净资产体现了公司的偿债能力,其可以作为判断公司是否能够偿还债务,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受到“严重侵害”,进而决定是否需要否认公司人格来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指标之一,但其本身并非“资本显著不足”下“资本”的确定值。换言之,用净资产来确定公司对债权人的偿债能力是能否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条件,但并非确定“资本显著不足”时的“资本”额。因为“资本显著不足”反对的是股东没有向公司进行相应投资,滥用有限责任,利用公司的“壳”恶意将公司经营中的潜在风险转移给债权人的行为,针对的是股东的出资责任。而公司净资产的概念并不具备这种法律意义。 二、“显著不足”的认定: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融合 在公司法中,有限责任是出资人和公司其他利害相关人之间就风险分配达成的一项格式化契约。“透过有限责任,出资人与所有固定清偿主体、潜在的公司行为受害人、客户等均达成了关于风险分担的契约。”(12)在该契约下,有限责任使得出资人在承受责任方面有了一个上限,但出资人必须对公司进行真实出资,并放弃对该部分出资的直接控制权,使其处于风险状态。这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这是出资人获得有限责任的对价,其不能将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到他人身上;其二,如果股东不进行真实出资,则可能会进行非理性的风险投资。(13)而资本显著不足便是出资人对有限责任初始契约的偏离,法人格否认的目的即在于纠正这种偏离状态。 (一)实践中对“显著不足”的误解 对于“显著不足”的理解,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有不同看法。早在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了《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其中规定,没有投资或者投资达不到法定最低资本限额的公司,可以否认其法人人格,使股东承担无限责任。(14)当时,尽管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正式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但该批复实际上隐现着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身影。2005年《公司法》修改,法人格否认制度正式引入,但最高院的上述批复依旧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适用“资本显著不足”时的基本判断标准。通过对北大法宝案例库的搜索,可发现截至2015年1月,在我国司法审判中以“资本显著不足”为搜索词可获得的案例与裁判文书共有37个。其中,以公司资本低于法定最低资本限额为由,且被法院判决人格否认的案件共有3起。 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这种认定方法,理论界普遍持反对意见。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出资低于法定最低资本说明公司在设立时根本就没有满足法人的成立要件,其后果应是对公司人格的彻底否定,而非特定情形出现时的法人格否认。因此,在最高院的批复作出后不久,学者们就纷纷指出“资本显著不足”“决非是指公司资本与公司法上对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要求相比,达不到法定最低标准时的情况”;(15)“以股东出资是否到达法定最低资本作为否定法人格的做法,忽视了公司经营对财产的实际需求,没有考虑股东的主观意图,且一刀切的做法容易引发不公平”;(16)“公司资产是否充足不仅取决于公司资产的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公司所营事业的性质。”(17)可见,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资本显著不足”与公司法定最低资本额并无必然关系,即使公司资本达到了法定最低资本要求,且资本真实,但较之公司所营事业的需要明显不足时,仍构成公司资本不足。在2013年《公司法》修改后,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外,公司资本法定最低限额已不复存在,司法实践中惯用的标准已彻底失去了存在基础,此时,司法审判必须摆脱对僵化的具体数字的依赖,寻求新的判断依据。 (二)“显著不足”的认定标准 目前,对“资本显著不足”的理解,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基本趋同,即“相对于可预期的经营规模和可预见的潜在责任,资本的规模是否合理”。(18)如果“股东根本没有根据企业经营原则投入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必要的资金”(19)或者“如果公司资本与公司业务和损失的风险相比是虚幻的(illusory)或微不足道的(trifling),则否认法人格就是有基础的。”(20) 需说明的是,对于“显著不足”的这种认定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判断,因为投资者没有义务对于经营失败的公司再负补充投资义务。若采用这种方式,“以结果反推资本充足与否,那么每一个陷入资不抵债境地的公司都可以被认为是资本显著不足”,(21)而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同时,在衡量资本充足与否时,虽应以股东投资时合理的(reasonable)、可预见的(foreseeable)经营风险和潜在债务为标准,但并非要求资本足以覆盖或能够清偿潜在债务。否则,公司在经营中,从债权人处借款融资的简单行为就可能构成资本显著不足。因而,对于有学者所主张的“以资本额是否足以清偿公司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所可能发生的债务为资本充足衡量标准”,(22)值得商榷。因为“衡量资本是否充足的目的,应当是判断股东是否有充足的资本对经营失败的风险承担‘公正的’份额,换言之,是否有充足的资本激励控股股东作出合理的经营决策”,(23)而不是要求股东的出资必须能够完全偿付公司负债,或者说要求股东投资成为公司债务履行的全部保证,否则有限责任制度的意义就丧失殆尽。因此,如果股东基于正常、合理的推测,认为以现有的认缴出资为基础,经过合理经营,公司能够有经营收入与潜在负债相匹配,那么就应当认定公司资本充足;相反,若一个公司在设立时并无足够资产,却被用来从事高风险活动,且股东应当能够预测到该活动的潜在风险,并能够预测到其难以被支付,但仍为之,则应属于“资本显著不足”。 (三)“显著不足”的判断方法 “资本显著不足”之所以会出现适用难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其不仅涉及事实判断,而且涉及价值判断。正如托马斯·莱塞尔等在《德国资合公司法》中所写到的:“如果用企业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可靠地确定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股本数额,大概就没有人会怀疑,应该根据这一资本数额在法律上给债权人提供保护。因此,主要的困难还在于客观事实的理解和证明。”的确,不得不承认,公司资本充足与否是一个经济要求,而非法律要求。(24)在美国公司法中,这被认为是一个事实(factual)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公司而言,什么是足够的资本并非是立法机构所能够决定的”。(25)而纵观各国立法,迄今也尚未有国家能够以成文法形式规定“显著”的具体标准。 除立法机关外,司法机关对此问题同样显得“力不从心”。而这或许正是“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法人格否认制度难以被适用的根本原因。然与立法机关不同的是,司法作为维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必须寻找出相对合理的判断路径,以便公平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对此,判例法国家的检测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对比测试法。即将被告的公司与其所在同行业、同地区、同规模的公司资本水平进行比较,以此判断公司资本是否充实,其中参考的主要数据有流动比例、速动比例、资产负债率等。该方法的优点在于,排除了对公司的事后追溯,具有标准性和相对客观性;但其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选出合适的对比者并不容易,二是,即使选出合适的对比者,法院在对比前必须首先确定对比者的资本水平本身充足,而这就需要将对比者的资产情况与另外一个对比公司先行比较,如此反复。这样一来,法院可能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对比当中。(26)为避免这种困境,在美国,法院会依托于市场上具有公信力的资信评估机构,以便确定一个客观的资本平均水平作为对比测试标准,例如,邓白氏国际信息咨询公司、穆迪投资手册、标准普尔公司记录等等。(27) 其次,专家证言。法人格否认的案件审判通常包含了复杂的事实问题,资本充足性的判断尤其如此。尽管法院在判决时可以参照一些量化的同行业、同规模、同类公司的平均财务指标,但事实上,在不同公司、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商业环境下,这些指标差异很大。因此,就需要更为专业的个案分析。由于法官并非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或职业经理人,被告的公司从事特定商业领域的专业活动所需资金是否充足,法院往往需要专家协助其作出判断。这些专家主要是经验丰富的金融分析师,如注册会计师、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等。如果一个熟练的金融分析师认为,根据公司资本情况判断,公司资本不足以支撑该公司在该时点某一项业务的规模和性质,则可定性为公司资本不足。在美国,有学者将其称为“熟练的金融分析师”标准,(28)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Laya v.Erin Homes,Inc.案中,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特别承认了在资本充足性问题上专家证言的必要性;在In Re Mobile Steel Co.v.Diamond案中,第五上诉巡回法院也承认,金融分析师对于判断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Collet案件中,Missouri州上诉法院就依据专家证言,认定被告的公司资本远远低于行业水平,进而否认了公司人格。 三、“资本显著不足”的适用情形与条件 (一)适用时点的确定 目前,我国学界对“资本显著不足”应何时适用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衡量公司资本是否充足的时间应以公司设立之时为准,通常在公司设立时,就要求衡量其是否根据经营性质及其风险程度进行了合理投资。(29)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公司设立时已经有足额资本,且符合《公司法》规定,也符合公司经营规模的经济要求,只是最后在经营与竞争中,因经营不善或其他原因而导致资本减少时,不能认定为是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但是如果是因支配股东的不法行为而发生了公司资本不足的事实,则应当作为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但不能以公司设立时资本显著不足为理由否定其法人格。(30)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有观点就认为资本显著不足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公司设立之时,股东在公司有效成立之后抽逃出资,在公司存续期间,转移资产以逃避合同义务等,同样是对有限责任的滥用,有必要以抽逃后的净资产作为判断基础,就此考虑公司法人格的适用可能性。(31)有学者在考察美国的制度后,对上述观点予以认可,主张资本不足包括:在公司设立时股东初始投资不足甚至为零;在公司运行中股东抽走所有或几乎所有收入或利润;在公司运行中没有根据需要追加投资等。(32) 由上述观点可知,学者们对于公司设立时适用“资本显著不足”并无疑义。诚如Clark等公司法专家所言,资本显著不足之所以成为公司人格否认的首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因资本显著不足而推定的股东对公司人格的滥用。在公司设立初期,股东对公司经营可能碰到的风险和债务有充分估计的机会和能力,但其仍然选择投入与其不相称的资本或者虚假出资、不实出资,那么就应对公司人格进行否认,要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3)在Kinney Shoe Corp.v.Polan案中,法官就以资本显著不足为主要原因否认了被告的公司人格,其经典论述便是“股东的责任应当以其在公司中的投资为限,但被告并未投入任何资本。这个公司仅仅是一个壳——透明的壳。当公司没有任何资产时,公司法不为其所有者提供保护;没有投入,没有产出,也就没有保护(nothing in,nothing out,no protection)”。(34)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经营过程中的公司是否可以运用“资本显著不足”来否认公司人格?由于“资本显著不足”是对股东偏离出资义务的纠正,而在实践中,股东完全可能在公司设立时进行必要的出资,待公司成立后,再将资本转移或撤回,实际上同样可以造成股东出资的严重不足,达到将经营风险转移给无辜债权人的效果,因此,资本是否充足的判断时点应当包括公司设立之后。在美国,丰富的案例实践表明,因资本不足揭开公司面纱的比例为73.3%,而这里的资本不足不仅包括公司开办之初的资本不足情形,也包括公司在运营后转变为资本不足的情形。(35)可见,“资本显著不足”不仅适用于公司设立之时,在公司整个运作过程中,股东都有义务提供与公司经营相匹配的充足资本,且这是一项伴随公司经营事业存在的持续性义务。(36)在英国,学者同样认可股东提供资本的持续性义务,即“公司资本是确定公司净资产最小价值的刚性尺码,这个最小的净资产价值必须在公司成立之初形成并在经营过程中尽可能地得以资本维护。”(37)在德国,“资本显著不足”也适用到了公司设立后的经营过程中。有学者就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和增资之下的资本缴付规定,是为了确保股东按照章程确立的原始资本金额真实缴付公司财产。作为补充,法律保护原始资本金额范围内的公司财产,以免公司将其分配给股东。”(38)在直索制度中,“毁灭生存”情形的适用也是该持续性义务的体现。德国联邦法院对“毁灭生存”的解释是,股东对于公司债务的责任限制有其前提,即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相互区分,如果股东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措施抽取公司财产,“决定性地”损害了公司履行其债务的能力,从而事实上毁灭了其生存基础的话,那么就应拒绝股东享受法定的责任限制待遇。(39)在“不来梅佛尔康”案中,法官对“毁灭生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即“保护附属的有限责任公司,使其不受其一人股东的侵吞……主要必须维持公司的基本资本,同时必须保证公司的生存不受危险”。(40)可见,“毁灭生存”的理论基础就是为了保证公司资本在经营过程中的持续充足(当然正常经营的损失或失败除外)。 除抽逃出资外,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经营范围的扩大也可能造成“资本显著不足”。在公司业务发生变化,面临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作为判断依据,无异于鼓励股东先成立经营风险小的公司,然后再修改公司章程,扩大经营范围,通过小投资进行高风险经营,利用有限责任实现“以小博大”的目的,同时将风险不当转移给债权人。这显然违背法律的公平性。在德国学者看来,“资本缴付规定涉及新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新的业务份额,也就是公司设立或增资。但是,如果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先为了储备的目的而被设立(公司壳设立或储备设立),在事后又为了一个经济活动而被激活起来,则也要相应地适用资本缴付规定。使用‘旧的’外壳,即事后将一个已经停止业务活动的有限公司投入于一个新的活动,也要作为经济上的新设而受到资本缴付规定的规范。”(41)可见,当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时,若变更后的经营活动风险高于变更前,则应以变更时点为标准,考察股东对公司的投资与该经营活动将产生的潜在负债相比是否“显著不足”。 (二)适用前提的判断 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要求股东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股东的滥用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因而,无论是基于哪种情形的法人格否认,都应具有该结果要件。然而,如同“显著”的表述具有主观性一样,“严重”的表述同样没有明确标准。如何认定对公司债权人的损害达到了“严重”程度,这是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达到“严重”程度,就不能随意将公司债务责任追溯至股东。《公司法》引入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根本上并非是要否认有限责任,而是要在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有限责任原则之间确立一个平衡点。 通常情况下,债务的受损情况是权衡“严重”的最重要因素。而债权人受损情况是可以量化的,公司不能偿还的债务就是一个确定的数额。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数额为标准来认定“严重”,是以未能履行的债务超过一定金额为标准,还是以未能履行的债务超过一定比例为标准?若以一定金额为标准,会有失合理。因为债权人的情况各有不同,未偿还债务对每个债权人的意义也因人而异,难以通过数额来认定多少债务未偿还对债务人是“严重”,多少又是“轻微”。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法人格否认案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司法审判中,法院是否否认公司人格与债权人的受损数额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其中,在公司人格被否认的案件中,最低的损害金额是11860元,最高的是1674万元;而在公司人格未被否认的案件中,最低的损害金额是58032元,最高的是1100万元。(42)而若以一定比例为标准,也会有失公平。如上述数据所显示,每个案件中债权人受损害的基数相差极大,如设置一个相同的比例,那么,可能会出现虽未达到规定比例但受损基数大,实际损失大的债权人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而虽达到规定比例但受损基数小,实际损失相对小的债权人却能得到法律保护的不公平现象。可见,无论是规定一个数额还是规定一个比例,都不尽合理。由于债权人之所以要求否认公司人格,其本意就在于,公司已无清偿能力,不要求有过错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债权就无法实现,因此,一旦股东滥用了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使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就可以认定构成“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结果。(43) 当然,为平衡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在计算债权人的损失时,应当以直接损失为主要依据,对于间接损失应审慎计入。此外,如果公司不能偿还债务只是暂时的,尽管债务数额较大,但通过一段时期的经营或者采取资产注入等措施可以很快克服困难,就无须进行公司人格否认;如果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事实已持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公司财产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甚至已经达到“资不抵债”的地步,就可以做出已经“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判断。总之,应以公司的长期而非短期偿债能力作为判断公司是否能够清偿债权人债权的基本标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公司净资产可能不足以支付债权人的债权,但是,如果有替代性措施(例如保险金赔偿)来偿还债权人,那么应将替代性措施考虑在内。换言之,如果公司的净资产加上为赔偿用户、消费者等债权人的潜在损失而购买的责任保险,可以足够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则不应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 (三)自愿之债与法定之债的区分设计 债权依据形成原因可分为自愿之债与法定之债。基于二者形成的机理不同,在以“资本显著不足”否认公司法人格时,除前述的“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结果要件外,其他的适用条件和要求却不尽相同。 就自愿之债而言,其适用条件相对严格。有观点甚至认为,由于债权人与一个公司签订协议时,负有调查义务,且法律假定债权人熟悉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其与该公司签订协议的基础是经其调查、了解后的公司资本状况,而非股东的个人信用,因此,不得以注册资本投入不足作为法人格否认原则适用的因素。(44)该观点尽管过于绝对,但其论证过程具有合理性。在自愿交易过程中,债权人确实有时间和机会去寻找、选择、调查公司的资信。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在与公司交易时,若明知公司的注册资本很低,有可能到期无法偿还债权,但仍选择与该公司交易,则表明其原意承受该风险。此种情形下,债权人以债权面临严重损害为由,请求法院否认公司人格,很难得到法院支持。这也是合同法中“买方当心”风险分配原则的具体体现。 但是,“资本显著不足”引发的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否完全不能适用于自愿之债?非也。若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时,股东对债权人进行了欺诈,则很可能导致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因为此时欺诈因素的介入,使得债权人“自愿”承担风险之情形不复存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件Dewitt Truck Brokers v.W.Ray Flenning Fruit Co.案可以说这点。该案中,被告Flemming是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也是公司运营的唯一控制者和受益者。该公司实际上没有任何真实的资金,资本不足的情况非常明显。该公司长期以来拖欠原告的运输费。被告向原告作出保证,如果公司不能偿付该费用,将由被告个人偿付。后来,公司无法偿付,原告起诉,要求揭开公司面纱,由被告个人偿付债务。本案的审判法官认为,对于Flemming而言,其保证的目的明显是提高自己的个人好处,因为公司继续运营下去的唯一受益者是其本人,此时,其作出的保证诱导了债权人向其公司继续提供运输服务,并对其赊款,该事实构成了揭开公司面纱的足够的原因。(45)可见,在意定之债中,如果债权人是因为受到股东的欺诈才与该“资本显著不足”的公司交易,则应当认定公司股东滥用了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恶意侵害债权人利益。总之,在自愿交易中,单纯的“资本显著不足”因素通常并不构成法人格否认,只有在欺诈或者其他权利滥用的情况下,法院才会适用该制度。(46) 实践中,这种欺诈往往表现为积极行为,尤其是“虚假陈述”,正是因为这种虚假陈述误导了债权人,使之与公司发生交易或者业务往来。(47)有学者甚至认为,只要法院发现有虚假陈述的事实存在,就几乎一定会判决否认公司人格。(48)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消极的“不披露”行为,是否能够认为是欺诈?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财务情况若仅仅是保持沉默,则不应承担责任;(49)而有观点则认为,公司股东对公司财务信息负有披露义务,如果其没有向债权人披露公司财务的危机状态,则属于欺诈。(50)对该问题的理解,实际上要追溯到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意。该制度旨在纠正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的违法行为,而不是要免除债权人的应然注意义务。作为理性经济人,债权人在与相对人交易时,应对其资信尤其是财务信息进行询问、调查、分析,进而判断其履约能力;且根据波斯纳的观点,自愿债权人在与商事公司进行交易时通常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51)从而使其能够方便的获取相关资讯信息。此时,如果债权人因疏忽或各种原因而没有积极调查公司资信,则属于自己责任,应自担风险。因此,公司股东不应负有主动的信息披露义务,其“沉默”并不构成欺诈。 就法定之债而言,其适用条件则相对宽松。在非自愿交易的情况下,不存在自愿或合意的因素,如果承认资本不充足的公司独立存在,实际上无异于将风险和损失转嫁给了无辜者。譬如,在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因公司的侵权行为而遭受到财产或者人身损失,其所受到的伤害总是被动的,他不能像公司的合同相对人那样基于对公司状况的了解而决定是否与公司交易。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法院更有理由在侵权案件中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52)或者说,在侵权案件中,缺乏充足的资本成为法人格否认制度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甚至可以单独适用。(53)Minton v.Cavaney案即体现了该思想。Seminole公司经营了一个公共游泳池,原告的女儿溺水而亡,原告要求Cavaney(Seminole公司的董事、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发现Seminole公司没有任何实际资产,游泳池是租来的并且因为无法支付租金已被收回。基于此,法院认为Cavaney并没有提供足够资本的意图,因而根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判定Cavaney承担赔偿责任。(54)该判决说明,公司设立时股东应当有义务根据公司事业的经营性质和风险程度衡量其投资是否合理。否则,法定之债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基于“资本显著不足”而请求否认公司人格,要求股东对其承担责任。如果说要寻求该种情形下的“滥用”因素,那就是,公司股东应当意识到自己所投资公司的经营事业的风险性,(55)而其却无视这种风险,未对公司进行任何投资或只进行了明显不足的投资,那么,显然是意欲将这种风险转移给无辜的受害人。 四、“资本显著不足”情形下的民事责任承担 依据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原理,股东滥用了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侵害了债权人利益,给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那么,应与公司一起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然而,该规定只是一种原则性阐述。在实践中,应根据具体情形细化相关规定: (一)自愿之债与法定之债的不同追究机制 在自愿之债情形下,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时,因公司股东对债权人进行了欺诈,诱导其与公司进行交易,造成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此时,债权人的风险并非自己判断错误造成,而是因为受到了欺诈才产生,因此,应由实施了欺诈行为的股东与公司一起对债权人负连带赔偿责任。对于其他未实施欺诈行为的股东而言,则无需负责,仅承担有限责任。 在法定之债情形下,如上文所言,有“滥用”恶意的股东实际上是公司的所有股东,包括设立时的股东,也包括增资时新加入的股东。因为此种情形下,“资本显著不足”是导致法定债权人权益严重受损的基本诱因,而此诱因是因为全体股东应当知道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包括设立时的数额或增资后的数额)明显低于所经营项目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却无视这种风险,甚至意欲将该风险转移给法定债权人,因此,各股东应当对此种情形下的公司债权人负连带责任。当然,股东在对外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后,可向其他股东基于风险损失约定或投资比例进行追偿。 实践中,法院可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投资人在公司人格被否认之前,已经转移股份,那么是否还属于适格的被告?对该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否则,在法人格否认之讼提起之时拥有公司股份的人,以及在诉讼进行中应承担责任的人,很可能在判决作出之前,通过简单的股份转移来逃脱责任,因此,要求其承担责任具有合理性。而对于转让后的受让人而言,因法人格否认的立法政策是侧重于债权人保护,因此,其可以被要求首先承担责任,继而再向转让人追偿相应损失。 (二)资本填补责任与法人格否认责任的对接 在公司设立或者增资过程中,股东有可能会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股东有可能会抽逃出资。这些行为显然是对公司资本的侵害,很可能造成“资本显著不足”。从法律性质上分析,股东的上述行为属于对公司财产权的侵害,属侵权行为,应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该责任以股东未出资本息范围为限或以股东抽逃资本额的本息范围为限,属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由于该责任属于股东对公司负有的责任,相对于债权人而言,仍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责任,并不直接关涉债权人利益,因而,即使法律规定债权人可以在特定情形下就股东虚假出资或不实出资行为、抽逃出资行为直接向责任股东行使请求权,但这实际上是债权人在“代位”行使公司对股东的权利,只是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一项技术性安排,权利的“代位”本质并未改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股东的虚假出资、不实出资、抽逃出资很有可能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进而严重影响债权人利益。一旦其满足了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有责任的股东需同公司直接对债权人负连带责任。那么,这种内部的有限责任是如何向外部的无限责任转化的?这里就存在一个制度间的对接问题。德国学者将其描述为“内部责任转变为外部责任”的过程,即“设立中的公司的股东责任是针对公司的,但在例外情形下,对股东的直接追究仍还是不可欠缺的,即结果上就是穿透。”(56)从具体适用来看,这种衔接应当理解为:如果股东对公司补足出资或返还出资后(即注册资本真正投资到位),能够足以清偿债权人的债权,则无需进行法人格否认;而如果注册资本真实到位后,仍然属于“显著不足”的状态,则说明在公司设立之时或拓展高风险业务之时,股东即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明显意图,如在此情况下公司无法清偿债权,则可加重对出资瑕疵股东、或抽逃出资股东的违法行为成本,否定公司人格,要求有过错的股东承担无限责任。 不得不承认,起源于判例法国家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希望得到准确适用绝非易事。法官应在何时、何种情形下否定公司的法人格,让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责任,确实是一个难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即使在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也证明,“法庭在‘撩开公司面纱’时缺乏一贯的政策,所适用的具体标准相对混乱,有关法律推理也笼罩在一片隐喻当中。”(57)具体到“资本显著不足”这一情形,更是如此。其适用除了考虑公司自身的注册资本外,还需判断公司所营事业的潜在负债以及注册资本与潜在负债相比是否“显著不足”。而这对法官来说的确困难,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官并非商人,同时,法官也不能做事后诸葛亮,以结果来判断行为当时的合理性。然而,尽管如此,该制度的价值仍不可否认。尤其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在取消法定最低资本制、发起设立的公司实行完全自由的认缴制的情形下,如何在股东的有限责任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需要法官的智慧。 注释: ①参见诸红军主编:《公司诉讼原理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参见吴日焕:《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理论困惑与实践思考》,第三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会议论文,2014年5月11日,北京。 ②参见宁金成:《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与债权人保护》,第三届公司法司法适用高端论坛会议论文,2014年5月11日,北京。 ③参见周友苏:《新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④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74-75页。 ⑤See Bartle v,Home Owner Co-op.,309 N.Y.103,106,127 N.E.2d.pp.832-833. ⑥H.W.Ballantine,on Corporations(Rev.Ed.1946) §129,pp.302-303. ⑦See Briggs Transp.Co.,Inc.v.Starr Sales Co.,Inc.,262 N.W.2d 805,Iowa 1978. ⑧参见[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著,《德国公司法》,殷盛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 ⑨参见范健、王建文:《公司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⑩赵旭东等:《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11)参见刘俊海:《公司法修改二三言》,载《品茗》第10期。 (12)张曙光、杨如彦:《揭穿公司面纱的经济学原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03年8月11日-12日,丽江。 (13)Franklin A.Gevurtz,Piercing:An Attempt to Lift The Veil of Confusion Surrounding The Doctrine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76 Or.L.Rev.853(1997). (14)《关于企业开办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3.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15)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 (16)葛伟军:《论最低资本与揭开公司面纱——兼谈对法复[1994]4号、法释[2001]8号及法释[2011]3号文件的理解》,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17)石少侠:《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18)苗壮:《美国公司法制度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19)[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页。 (20)前注⑥,H.W.Ballantine书。 (21)Douglas G.Smith,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In Regulated Industries,2008 B.Y.U.L.Rev.1165. (22)赖英照:《关系企业法律问题及立法草案之研究》,载《公司法论文集》,台湾地区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编印1988年版,第128页。 (23)前注(13),Franklin A.Gevurtz文。 (24)参见张勇健、金剑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研究》,载张穹主编:《新公司法修订研究报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5)前注(13),Franklin A.Gevurtz文。 (26)See Thomas K.Cheng,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Doctrine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80 Miss.L.J.497(2010). (27)See Mark A.Olthoff,Beyond The Form——Should The Corporate Veil Be Pierced?,64 UMKC L.Rev.311(1995) (28)See In re Mobile Steel Co.,563F.2d692,703(5th Cir.1977). (29)参见前注(24),张勇健、金剑锋文。 (30)参见前注①,诸红军书,第246页;参见沈贵明:《论公司资本登记制改革的配套措施跟进》,载《法学》2014年第4期。 (31)参见前注④,朱慈蕴书,第75页。 (32)参见前注(18),苗壮书,第40页。 (33)参见前注④,朱慈蕴书,第76页。 (34)See Kinney Shoe Corp.v.Polan,939 F.2d 209,C.A.4(W.Va.),1991. (35)See Robert B.Thompson,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An Empirical Study,Cornell Law Review,Vol.76,PP.1044-1045. (36)See Harvey Gelb,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The Undercapitalization Factor,59 Chi.-Kent L.Rev.1 (37)L.C.B.Gower's Principle of modern Company Law,4th ed.,London,1979,p.216. (38)前注⑧,[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书,第358页。 (39)王锴:《论公司股东的直索责任》,载《学术论坛》2012年第5期。 (40)前注(19),[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书,第490页。 (41)前注⑧,[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书,第362页。 (42)参见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43)参见前注(17),石少侠文。 (44)参见薄守省主编:《美国公司法判例译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注释①。 (45)See Dewitt Truck Brokers v.W.Ray Flenning Fruit Co.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Fourth Circuit,1976,540F.2d.681. (46)See Robert.W.Hamilton,Corporations(4[th] ed.),West Group,p.180. (47)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48)See Cases and Materials on Japanese and U.S.Business Corporation Law,Volume 1,Temporary Edition,1993.,p.3-21. (49)See Moore & Moore Drilling Co.v.White,345 S.W.2d 550(Tex.Civ.App.-Dallas 1961,writ ref'd n.r.e.).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应当调查正与其进行交易的公司的财务状况。该原则同样适用于小的合同债权人,因交易的规模或者商业的竞争本质,其并不会对其客户进行仔细调查。 (50)参见前注(13),Franklin A.Gevurtz文。 (51)See R.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92,4th ed.,pp.391. (52)参见前注(46),Robert.W.Hamilton书,p.178. (53)参见前注(47),施天涛书,第35页。 (54)See Minton v.Cavaney,56 Cal.2d 576,364 P.2d 473,CAL.1961. (55)例如Minton v.Cavaney案中,公司作为游泳设施提供者,应当考虑到可能会有游泳者溺水的情形出现,进而可能会出现赔偿责任。 (56)前注⑧,[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书,第390页。 (57)蒋大兴:《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Ⅱ》,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标签:公司法论文; 股东出资论文; 公司人格否认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法人股东论文; 债务承担论文; 注册资本论文; 股东论文; 有限责任论文; 投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