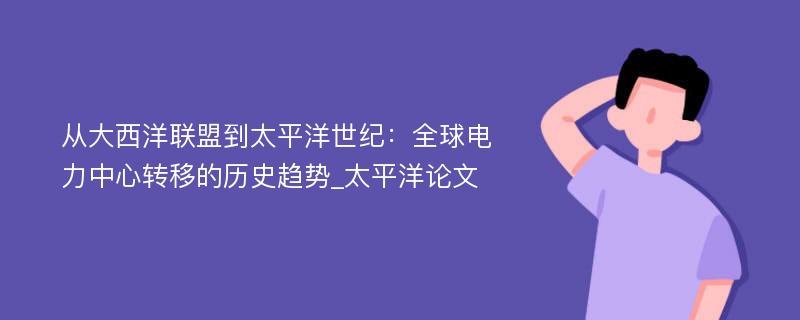
从大西洋同盟到太平洋世纪——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历史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西洋论文,太平洋论文,重心论文,同盟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尚难判断世界将如何变化,所能知道的是我们将处于“变化多于传承”的转型之中。①在经历了2011年的西亚北非冲突、欧债危机和英美国内社会抗议活动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正在发生的全球变局,这就是大西洋同盟的裂变与太平洋世纪的凸显。然而,这还是一个关于权力转移的故事的开端。我们还无法知道它的确切轨迹和具体情节。但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就像保罗·肯尼迪所说的那样,世界正“跨越新的分水岭”。②
欧元区的欧洲
欧洲的辉煌应该从1500年算起。从那时起,欧洲国家利用“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美洲白银资本,③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获得了比亚洲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财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全球体系。④在400年间,支配世界的主导权像接力棒那样,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的手中传递,欧洲成了控制世界的枢纽地区。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原本是欧洲殖民地的美国后来居上。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使美国成为欧洲大国均势的最终平衡者和债权人,⑤欧美间形成了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战后建立起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欧美共同支配世界的大西洋轴心的开端,而美国获得了在欧洲主导下的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席位。那时的欧美,既是主要伙伴,也是主要对手。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重操故伎再次“远征欧陆”,运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未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能力,建立了美苏共治世界的雅尔塔体系,成了欧洲的保护伞和救济人。⑦表面看起来,全球力量重心依然在大西洋,只是美国成为了大西洋轴心的真正核心。
在美强欧弱的格局下,美国不断利用强大的美元体系侵蚀欧洲国家的利益,这引起了戴高乐等欧洲政治家各种方式的抗争。⑧1971年8月,在欧洲美元持续兑换黄金的压力下,尼克松单方面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面对欧洲人的质疑,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说出了最能体现美元霸权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⑨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欧洲有赖于美国的保护,不可能去解决美欧间的货币利益问题。但美国“货币帝国主义”⑩的做派,却播下了欧洲决心要摆脱美元体系控制的种子。(11)同样重要的是,从“舒曼计划”开始的欧洲产业和经济基础一体化在稳步推进,(12)而这打下了欧元的根基。
冷战结束后,维系大西洋同盟的共识与目标纽带渐趋松懈,欧洲国家谋求摆脱美国主导的活动却日趋活跃。有过领导全球经验的欧洲人知道,分散的欧洲在与美国和其他大经济体的竞争中断无获胜的可能。因此,欧洲在政治上组建欧盟、在经济上推出欧元、在军事上尝试独立的欧洲防务,力图通过欧洲国家“抱团”的方式,形成在全球格局中够分量的力量板块。随着欧元问世、欧盟扩张,美欧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越来越低,全球治理的分歧越来越多,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力明显减弱,欧美出现渐行渐远之势。卡根曾抱怨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认为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13)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美国经济和美国模式遭受重创,而这却为解决欧元区制度中的缺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欧元区核心国家决定推进“危机边缘”政策——利用危机造成的强大压力迫使欧洲国家让渡财政主权。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多次提出,欧洲必须要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要建立财政联盟。2011年12月,欧洲峰会提出制订欧洲国家间新的财政协议,获得了17个欧元区国家和除英国以外的其他欧盟国家的首肯。看来法德采取的“危机整合”战略已经奏效,就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议会上所说的那样,如果在几个月前有人说欧洲会在2011年底前建立一个欧洲财政联盟,会被当作疯子,(14)而现在欧元区已走上“通向财政联盟的不可逆转的轨道”。(15)这不仅是欧洲度过当前危机的需要,也是推广“莱茵模式”,为将来的“欧罗巴合众国”铺平道路。不甘心被法德主导、又担心利益被欧陆国家侵蚀的英国,再次选择了“孤立”于欧洲的立场。而欧陆国家在法国式激情和德国人精细的配合下,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踏上了新台阶。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大西洋同盟的瓦解,蒙代尔等人就提出了“欧美元”的设想。(16)但问题在于,美国会接受一个欧洲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布鲁塞尔—华盛顿体系吗?对美国来说,一个保有弱欧元的弱欧洲才符合其全球利益。然而,在危机中更加“抱团”的欧洲已不再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附庸了。对欧洲人来说,构建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保持影响力的“欧洲合众国”,“让欧洲站起来”,是一个值得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17)在全球金融化的时代,货币金融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要形态。维持并发展欧元区是欧洲最优先也是最关切的政治目标,而奥巴马政府一次次否定欧洲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意见,美国的评估机构对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降级威胁,都使得美元体系越来越成为欧元区摆脱危机、重获发展的障碍。欧元体系与美元体系的竞争,正在成为撕裂跨大西洋轴心的主要矛盾。在交织着地缘政治和币缘政治的复杂博弈中,美国在欧洲一步步被边缘化了。今天的欧洲正在成为“欧洲人的欧洲”,更准确地说是“欧元区的欧洲”。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经济体,欧元区的欧洲自然会生成与其经济地位相应的政治意识以及与美国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
回顾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冷战后大西洋同盟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导致欧美难以相向而行的更深层原因,是大西洋同盟指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政治制度设计,以及美欧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是大西洋轴心瓦解的制度性根源。人们已经发现并将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近百年的大西洋同盟在制度缺陷和危机的锯切下,已经被割裂在大洋两岸,美欧两个车轮在各自轨道上分道扬镳。
非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被欧洲边缘化和被排斥的美国不愿意“调头回家”成为“美洲的美国”,只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部分背景。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在其《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原因有清晰的表述。在她看来,亚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并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太地区的人口几乎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拥有很多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有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她提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18)看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已经作出了未来全球政治和经济将决定于亚太的判断,而正是作出这一判断所依托的现实与趋势,成为吸引美国“重返亚洲”的另一重要战略背景。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应该是发端于1898年。那一年的5月31日,美国兼并了夏威夷;两个月后的7月31日,美国开始准备占领菲律宾。(19)指挥了这两大事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回忆道,我们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坚持占领菲律宾群岛,这使美国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20)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夫伯指出,麦金莱总统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是占有少量的土地用以实现征服世界市场的目标,同时占领为确保征服的实现所必需的战略要点”。(21)一个拥有广袤土地和资源而人口相对稀少、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显然更渴求市场而不是土地。坚持“门户开放”的原则,以市场为目标的要点控制——这是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亚太战略。所谓“门户开放”,就是要求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同等地位,这体现了这位强国俱乐部的迟到者参与瓜分的强烈愿望;而以要点控制市场则体现了美式霸权目标明、成本低、效益大的特点。其后由美日主导的华盛顿体系和美苏共治的雅尔塔体系,实质上都是与强国一道瓜分亚太利益。然而,历史进程无法设计,瓜分也会导致冲突与战争。对日战争、对苏冷战、朝战、越战等,都是美国试图以战争“大棒”主导亚太局势。除了对日作战是对日本过度扩张的反击外,其他发生在亚洲地区与美国相关的战争均具有“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与错误对象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特征。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清道夫,也是历史的魔术师——这些战争的副产品是,亚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复兴,以及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诞生。鉴于越战的教训,美国在十几年时间里避开亚太的是是非非,专心对付苏联和进行新经济试验。直到苏东集团瓦解、“9·11事件”爆发,美国的战略重点都放在欧洲和中东。
对亚太地区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是对冲基金对美元圈边缘地带一次劫掠引发的危机,由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盟国家渡过了可能的灭顶之灾。这使东亚国家萌生了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在当年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确定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两年后的1999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10+1)的建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在美国沉浸于科索沃和“反恐战争”的10年中,东亚地区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整合。从东盟—中国“10+1”发展为东盟—中、日、韩的“10+3”,形成了涵盖20亿人口、14.5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数万亿美元贸易量的东亚合作带。从2010年1月开始,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开始运行,双方93%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并尝试在货币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中日韩三国也在积极磋商自贸区和货币合作。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促使日本政治家萌生了“脱美入亚”的念头,韩国也向美提出减少驻韩美军和交出作战指挥权的要求。东亚合作带从经济开始向政治和安全领域扩展,出现了类似欧元区的前兆,让美国产生了可能会再被亚太地区边缘化的担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制造业占全球的一半,是全球制造产业链的龙头老大。但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向金融化方向快速转变,金融活动中与实业有关的比例越来越低。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后,美国制造业转移和金融创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如今美国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2%,而金融服务业却超过25%,美国企业收入中金融服务所占的比例超过40%,美国经济的真正支柱已经是以金融为主的服务类产业了。长期以来,亚太地区的贸易、外汇储备主要使用美元,其中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70%,而在亚太外汇储备中,有70%为美元资产。不难判断,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环太平洋地区是围绕美元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生产的“美元湖”。对已经多年处于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中的美国来说,维持全球金融货币收益这道底线,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这才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战略的真正出发点。美国经略亚太的重要目标是为了维护“太平洋美元湖”的稳定,而这是美国与欧元体系争夺全球金融利益的根基。至于是打压中国还是与中国合作,关键要看中国对美元霸权的态度,以及中国发展是危及还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霸权。
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美国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赫然出现一个大国对手,而是债台高筑、基础设施破损和经济不景气这三重打击。”(22)在支撑美国霸权的金融、科技和军事三大支柱和其他诸多优势中,除了军事力量还是美国实力水桶的优势长板之外,其他的桶板已优势不再或濒临崩塌。处于国力下降和国内党派政治困局中的美国,已经无力再推出亚洲版“马歇尔计划”来吸引亚太国家,所能做的只是依靠军事力量、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综合运用,通过加剧朝鲜半岛紧张、操弄“南海争端”,制造亚太地区可控的紧张,打安全牌以凸显美国军事力量的价值。同时,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凌驾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上,意图通过采取“操控危机+主导议题”的两手策略,争夺并掌握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逝者如斯。奥巴马要面对的亚太地区与麦金莱时期、杜鲁门时期、尼克松时期甚至与小布什时期的亚太地区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同样变化的还有美国的国力与国势。历来强调大西洋身份的美国,开始向太平洋地区倾斜,这在全球力量重心开始向亚太转移的时候完全可以理解。只是在美国国力上升、国势如虹的20世纪,美国尚且需要与他国分享亚太地区的权力和利益;而在亚太地区龙虎并起、蓬勃兴旺的21世纪,希拉里国务卿竟提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虽重在造势却实在不合时宜。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太平洋世纪,一定不是美国一家独占的太平洋世纪。
亚太的未来:共创与分享
回望百年,在上一个太平洋世纪中,前半部分是亚太地区国家摆脱西方各色殖民统治的50年;从万隆会议开始,亚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声音,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而直到最近10年,东亚地区才开启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面合作的进程。与破碎化的欧洲不同,由于拥有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主体板块,亚洲有能力创造并长期传承文明成果,使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列强和其后的美苏都无法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23)亚太国家数千年的共存史,形成了大国仁而小国智的国际政治文化,共同的反帝反殖经历和文化多元、意识形态色彩淡薄、儒家文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文明包容共存的传统,有利于亚太国家形成区域共识,创造和睦相处、合作发展的政治意愿和制度框架。这一切使亚太地区能够在全球化时代迅速构建起与欧洲、北美体量相当甚至更大的贸易区,甚至有可能建立统一的货币区,以防止西方金融资本的洗劫。
在美国重返亚太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事务,在近期都难免会受到冲击。但从长远看,亚太形势并不悲观。因为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多种文明和发展模式长期共存、竞争发展,已经建立并还在尝试建立多种有竞争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的组织框架。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12个亚太国家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比一般贸易合作更进了一步。据日本学者推算,正在酝酿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可达到0.74%,超过了美国推出的TPP的0.54%。一份新西兰的报告指出,如果TPP成为地缘政治游戏,并不能保证经济上更依赖中国的国家一定会支持美国。(24)其实,重返亚洲的美国受到自身实力底线和亚太国家态度的双重限制,其战略空间就在制造麻烦和防止危机失控之间,要利用制造麻烦来牟利,前提是要防止爆发全面和重大的危机,尤其是大国间的危机。从把南海议题控制在“航行权”、白宫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台湾地区选举关键时公布赴美免签证暗助马英九等实际行动分析,美国亚太战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持可控的紧张,这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因为如果与区域国家特别是与主要大国全面交恶,就会引发亚太区域大动荡和大冲突,结果将导致中国或东盟及亚太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加快与美国“脱钩”,美国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就丧失区域主导权,这既违背了美国的利益也超出了其能力。希拉里提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是资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国际政治新版本。希氏漫天要价,还须就地还钱。美国亚太战略落在实处,无非是通过“操弄危机”与“制造议题”来实现其主导亚太地区的目标。
看清楚了世界力量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就知道美国大张旗鼓地“重返”,实质上是要掩饰其实力下降,是无可奈何的收缩和调整,甚至有想整合亚太与欧洲再竞高下,以延长其全球霸权的权谋。所以,从建构与整合统一亚太板块的意义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并不一定是破坏稳定和发展的负面因素,亦可以扮演一种建设力量和平衡砝码。但前提是,美国政府和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要克制赢者通吃的贪婪。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是倾向于对亚太利益的独占,这是美国战略的致命缺陷。太平洋地区不会永远是“美元湖”——美国必须学会适应这一点。
作为亚洲大陆的主体板块,中国应该发挥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和带动亚太地区长期发展的作用,应以长远眼光去确认中国在亚太的地位,进而确定中国的亚太战略。必须明确,我们反对“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并不是要去构建所谓“中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国亚太战略的目标是建设可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板块并肩鼎立的亚太区域。欧洲的历史已经证实,在全球化时代,分散板块很难维护自身的利益。东亚整合符合亚太地区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亚太战略应该是“共创与分享”,即共创发展、共同治理、共享成果。这是与中国推进全球多极化战略相呼应的区域战略。这意味着亚太的未来是一个不排他的、开放的未来,亚太的未来不属于特定的国家,却属于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体亚太人民。亚太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建设和治理,也应该共享成果。为达此目标,中国要做更多的实际工作,如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建设联系,推进跨国公路、铁路和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建设改变经济地理,形成打破国界的区域产业链、利益链,建构能够维持稳定发展的货币体系,重塑亚太地缘和币缘政治格局。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一点,特别是“重返亚太”的美国还希望通过给未来的太平洋世纪冠名,把美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面对美国为主导亚太地区采取的竞争性战略,中国应采取避实就虚、陆海均衡的策略。以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改善地缘战略态势的关键与底线,通过调整国家经济重心过度沿海化的偏差,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海上通道的依赖,避免被迫与海外强国在远海争锋的局面;同时积极开发西部,向亚欧大陆的内陆方向发展,在亚欧大陆内部寻找新的资源通道和合作伙伴,实现陆海均衡——在亚欧大陆内部经济一体化与太平洋区域一体化之间保持总体平衡。在殖民地时代,陆海两栖的中国常有腹背受敌之危;而今天的中国,在地缘版块和产业链上却存在着左右逢源的机缘。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已呈现出复杂的大三角关系——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大陆另侧的欧洲,都有可能成为对手或伙伴,抑或对手加伙伴。最近,中美俄联手反制欧洲收取航空碳税说明,在当代,合纵连横的古老智慧仍未过时。
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源于不同的目标,也就是一国独占利益,还是多国共享成果?最终实现哪个目标,不是凭人们的意愿,而是基于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黏实力综合博弈的结果。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其实可以接受分享利益的结果,只是希望它的份额大些、再大些,这也就限定了“重返”可能带来的冲击强度。“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国可以气定神闲地应对。历史往往走合力线。最终的结局,将可能既不是独占,也不是更趋平等的共享,而可能是根据各国实力与态势的分享。
无论如何,亚太的未来将属于亚太人民。新的太平洋世纪,容不得任何国家对区域利益的独占。共创、共治、共享才是亚太地区发展的大道。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全球力量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对亚太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注释:
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②Paul Kennedy,"Crossing a Watershed,Unawares",New York Times,October 25,2011.
③[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④[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第30页。
⑤[美]迈克尔·赫德森著,祈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2页。
⑥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⑦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40-41页。
⑧[美]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⑨[英]戴维·马什著,向宋祚等译:《欧元的故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⑩[美]迈克尔·赫德森著,祈飞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第346页。
(11)[英]戴维·马什著,向宋祚等译:《欧元的故事》,第69页。
(12)[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祎、陈志瑞译:《欧洲一体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3)[美]罗伯特·卡根著,肖蓉、魏红霞译:《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4)“萨科齐提出欧元区‘重建’计划”,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1-12/03/content_11530804.htm.(上网时间:2011年12月28日)
(15)“德国总理:欧元区已走上通往财政联盟的不可逆转轨道”,http://www.licai18.com/article/ArticleDetail.jsp?docId=1228223.(上网时间:2011年12月29日)
(16)“诺奖大师畅想‘欧美元’”,http://www.chinanews.com/fortune/2011/09-30/3364534.shtml.(上网时间:2012年1月6日)
(17)[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祎、陈志瑞译:《欧洲一体化史》,第142页。
(18)Hillary Rodham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pp.57-58.
(19)[美]孔润华主编,周桂银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20)[美]孔润华主编,周桂银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第461页。
(21)[美]孔润华主编,周桂银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卷,第437页。
(22)Stephen M.Walt,"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25,2011.
(23)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55页。
(24)“亚太安全不应仅归结为中美竞争”,http://www.xoyue.com/viewnews-25929.html.(上网时间:2011年12月28日)
标签:太平洋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同盟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亚太实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