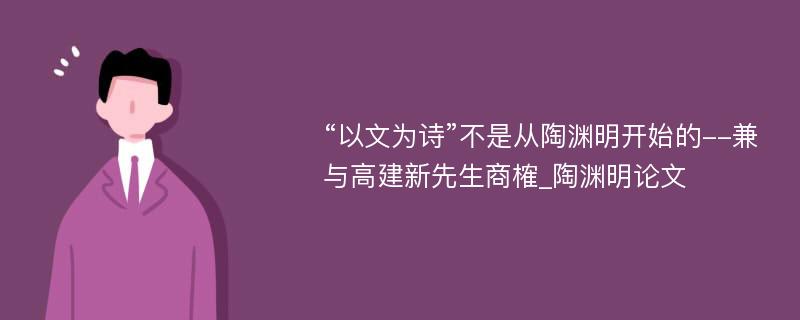
“以文为诗”不始于陶渊明——兼与高建新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以文论文,高建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2年11期转载了高建新先生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社)2002年4期的《“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一文,读后颇有所获,但又觉得此问题尚有商量的余地,故不揣浅陋,作此拙文,以就教于高先生和其他方家。
一、在谈论“以文为诗”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诗与文的地位升降问题。我们早就习惯了诗与文对举的表达方式,但诗与文的地位是不同的,而且彼此的地位还有升降变化。近读王小舒先生《从情欲出发体悟人生》一文,颇喜其这么一段话:“文学发展到宋代,不同体裁间的分工和位置已经基本划定,这是一个由上而下的阶梯式格局,文最高,因为文是‘明道’的,诗次之,它是‘言志’的,除了‘美刺’之外,还有抒发情性的功能,所以又被称为‘文之余’,此二者合在一起,组成正统文学的全部。北宋中叶的文学革命运动,恰是在这两个领域展开的。①所谈诗文的地位是宋代及其以后的情况。那么,宋代以前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诗的地位高于文的地位。先秦五经之中,《诗经》的文学性最强。到了汉代,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诗对文的冲击。汉代骚体赋也好,大赋、小赋也好,都带有很浓的“诗化”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看到了诗歌对历史散文的巨大影响。就连皇帝的诏书,也打上了诗歌的痕迹。如汉武帝元鼎五年十一月《郊祠泰畤诏》:“联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以祈丰年。冀州脽壤,乃显文鼎,获荐于庙,渥洼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克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泰一,修天文祥。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咸登,饬躬斋戒,丁酉,拜况于郊。”②不但两次引用《诗》句,而且以四言行文,当是受《诗经》影响所致。至于南北朝之后形成的骈文、骈赋乃至律赋,则与诗歌的区别越来越小,有的就已经是诗歌了。
从宋以前诗重于文到宋以后的文重于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这一变化的远源是:六朝以还,诗歌朝着“言情”和“绮靡”的道路发展,逐渐丧失了“言志”的功能,其社会作用也就逐渐下降。而其近因则是:唐代的古文家大力提倡古文而轻视诗歌。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粱肃、柳冕等都有重文轻诗的倾向。元结虽写有不少诗,却全是古体,他企图恢复六朝以前的诗歌特点。韩愈诗歌成就很高,也以古体诗为主,喜欢以文为诗。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古文家大力提倡散文的宗经、载道和济世之功,使其成为一种最具现实意义的文学体裁。相形之下,诗歌的地位也就降低了,古文家们之所以要以文为诗,可能是为了避免诗歌的功能和地位进一步沦落,使其也能起到“文之余”的作用。
陶渊明生活在各种文体都普遍“诗化”了的时代,但诗歌本身却出现了反动,这就是玄言诗的出现。以孙绰、许洵为代表的玄言诗人,运用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形式,大谈玄理,钟嵘《诗品》评其“语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保存到现在的玄言诗已经很少了,但由现存的作品推测,其在章法、句法等方面具有高先生所说的“以文为诗”的特点,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可是,老子的《道德经》千古共仰,为什么受其影响形成的玄言诗却不为后世所容呢?笔者认为,当各种文体普遍追求诗化的时候,玄言诗却主动地去接受“文”的特点,这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在当时却无疑是一股逆流。而缺少形象和感情的“陌生化”更增加了读者的拒斥心理。可是大家也不要忘了,不管玄言诗有多少不足之处,陶渊明诗却是从玄言诗脱颖而出的。在陶渊明的时代,玄言诗中已滋生出山水诗。陶渊明几乎不写山水诗,但从玄言诗到田园诗跟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其路径是相似的,只是指向不同罢了。脱胎于玄言诗的田园诗和山水诗同样具有浓重的玄学理趣。谢灵运山水诗的“三段论”也好,谢朓诗景事情交融也好,都反映了这个特点。比谢灵运还要年长的陶渊明当然也不可能摆脱说理,他的伟大和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基本上用饱含生活情趣的哲理代替了抽象的玄理,并且和田园风景、农家生活及作家的喜悦之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肯定不想象他之前的玄言诗人一样去把诗写得像“文”,他要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即努力摆脱玄言诗中所包涵的“文”的成份,让诗歌的特点重新回到诗歌中来。以恢复诗歌应有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至于他的诗中还存在着一些黄先生所说的散文特点,这实在是从玄言诗中所带来的,是陶渊明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排除的残余部分。黄先生发现了陶诗的这些成份,就认为陶是在意地“以文为诗”,恐怕有违陶渊明当年的良苦用心。
二、“以文为诗”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前人论述颇多。钱钟书先生在谈到王安石时说:“荆公五七古善用语助,有以文为诗、浑灏古茂之致,此秘尤得昌黎之传。”③“昌黎荟萃诸家句法之长,元白五古亦能用虚字,而无昌黎之神通大力,充类至尽,穷态极妍。”④许可先生这样说:
说韩愈“以文为诗”,在一定范围内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韩念以古文大家而写诗,以文为诗,原是很为自然的事情,而且看来他恐怕还是有意识地在做这样的试验。不过律诗与骈文关系密切,与古文关系疏远,要以古文而为律诗,几乎不可能。韩愈不大爱写律诗,他的律绝诸作确乎也很难说有多少以文为诗的表现。与古文关系密切的是古诗。韩愈多写古诗,而他写古诗有时确实运用过古文的句法与章法,而且以议论入诗,这些可说就是“以文为诗”。虽然这并非韩愈自我作古,但到韩愈却有所发展,以致成为韩愈古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以文为诗是韩诗创新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方面,同时也是韩诗最受攻击的一点,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⑤
罗联添先生《论韩愈古文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韩愈以文为诗的方式大致有以下数端:句式散文化,不用对偶句,使用大量虚词;以文章气脉入诗,布局构思有文章脉络;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以议论入诗;诗多赋体;诗兼散文体裁。⑥
综合以上诸家观点,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以文为诗主要是指以古文的特点去写诗。具体地说,就是以唐代古文家所开创的散文入诗。由于韩愈是唐代最大的散文家,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又很重,所以人们常常把“以文为诗”的创始之功归于他。其实,比韩早几十年的散文家元结的诗,散文化程度要比韩诗重得多。笔者曾作有《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一文,专门探讨这一问题。⑦钱钟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说:“唐人则元次山参古文风格,语助无不可用,尤善使‘焉’字、‘而’字。”⑧从元结、韩愈又可上推到杜甫。《后山诗话》引用黄庭坚的话说:“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⑨所谓“杜以诗为文”,是说杜由于不善于作文,就以诗来承担了各种文体的功能。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五古凡例》说杜甫的诗:“若《上韦左丞》,书体也;《留花门》,论体也;《北征》,赋体也;《送从弟亚》,序体也;《铁堂》、《青阳峡》以下诸诗,记体也;《遭田父泥饮》,颂体也;《义鹘》、《病柏》,说体也;《织成缛段》,箴体也;《八哀》,碑状体也;《送王砅》,纪传体也;可谓牢笼众有,挥斥百家。⑩这虽然与元结、韩愈的以文为诗有所不同,但对元、韩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接受了黄庭坚关于杜甫是“以诗为文”而不是“以文为诗”的论断,则“以文为诗”的时间上限就可以确定下来了。这样看来,说“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在时间确定上还嫌太早。
第二,以文为诗是在古体诗中进行的。唐代,近体诗兴起并繁荣起来,但“以文为诗”的“诗”却始终局限于古体诗,而很少侵入近体诗的领地。这样,当作者去“以文为诗”时,就存在着一个把古体诗与近体诗相区分和相对照的问题。杜甫律诗极精,“以诗为文”却限于古体诗;元结不屑作近体,其所有的古体诗都是散文化的;韩愈多作古体,以文为诗就在这块领地上进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皆兼擅近体和古体,以文为诗也主要是在古体诗中进行的。陶渊明生活在一个没有产生近体诗的时代,因此所作全是“古体”。假如我们说他“以文为诗”,他的诗歌却没有近体诗这一可供比较的对象来突出其“真正的诗”的特点,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第三,以文为诗不仅是指“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11]还包括以议论为诗和以赋为诗。或者仅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以赋为诗”之所以被看作是“以文为诗”的一个分支,可能因为赋与古文的关系本来就一直比较密切。如汉代大赋又被称为散体大赋,原因即在于此。在此笔者想补充的是,由于形式不可能独立,它必须与内容统一在一起。以文为诗在内容上最突出表现是让诗去承担了“载道”的功能。这也应该是以文为诗的一个方面。甚至可以这么说,“以文为诗”实际上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
即使我们按照高先生的说法,承认陶渊明是“以文为诗”,也很难得出其始于陶渊明的结论。就以用虚子来说吧。钱钟书先生说:“诗用虚字,刘彦和《文心雕龙》第三十四《章句》篇结语已略论之。盖周秦之诗骚,汉魏以来之杂体歌行,如杨恽《拊缶歌》、魏武帝诸乐府、蔡文姬《悲愤诗》、《孔雀东南飞》、沈隐侯《八景咏》,或四言、或五言记事长篇,或七言,或长短句,皆往往使语助以添迆逦之概。[12]所举除沈约外,皆早于陶渊明。如从章法、句法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使按照高先生的标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曹操是“以文为诗”的结论。而如果继续往前推,则又可发现屈原的《九章》原来早就是“以文为诗”了。如果一个概念的使用,泛化到这种程度,那它到底还有多少意义,可就很难说了。
三、其实,说陶渊明“以文为诗”并非从高先生开始。诚如高先生所说,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已说:“唐以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13]高先生之论点殆起于此。高文的新意还在于,不仅认为陶是第一个以文为诗的人,而且认为:“散文化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的使用,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给陶诗带来一种自由流畅、朴实明净、天然入妙之美。”“‘以文为诗’的运用,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贴近人心,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它与陶渊明的为人及朴素自然的诗歌风格协调一致,妙合无间。”[14]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商量的余地。如上文所说,玄言诗即是诗的“文化”,用高文的观点,即应该是“以文为诗”。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假如他又去“以文为诗”,这明明是走别人的老路,怎么会令人“耳目一新”呢?再者,即使我们承认陶渊明的那种做法是“以文为诗”,它就真的会带来高文所说的那些好处吗?笔者以为不见得。韩愈的“以文为诗”是公认的,我们就读一下钱仲联先生对韩诗的评价吧:
对韩诗的评价,自北宋以来,就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尤其在“以文为诗”这一问题上,贬之者认为,韩愈的诗是押韵之文,于诗无所解,褒之者推尊韩愈为大家,与李杜可鼎足而三,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两派的分歧极大。他们批评韩诗,有切中弊病的一面;赞扬韩诗,也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但都把问题说得绝对化了。韩愈的“以文为诗”,其部分作品具有流畅平易的特点,与六朝以来浮艳萎靡的诗文形成鲜明的对照,也确实扩大了诗歌领域。但这种古文式的语言,当然有它的缺陷:其一、有些诗篇几成押韵之文,特别是那些古文中常用的虚词,出现在诗中,几乎不像诗句;其次有些诗长篇议论,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显然不符合写诗规律,缺乏诗趣;其三,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作诗,铺排堆砌,晦涩呆钝,加上诘屈聱牙的僻词怪字,饾饤满纸,这就是损伤了诗的真美和感染力。这些联句,在险韵窄韵上逞奇斗巧,几近文字游戏。韩愈以文为诗的得失,大致如此。[15]
虽然钱先生所说的“以文为诗”比高文的涵盖面要大得多,但其所指出的韩诗的三个缺陷,在陶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只是陶诗较好地把握住了“度”,因此其负面影响尚不明显。可是,要说陶诗具有那些优点,是因为他“以文为诗”,恕笔者不敢相信。“散文化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的使用”,都是纯形式上的东西,怎么会有如此奇妙的作用呢?玄言诗写得像文,却“酷不入情”。不少真正的散文也未必能做到“亲切、平和、贴近人心”。笔者甚至这样设想,假如陶渊明有意识地排除这些散文的因素,而多加进一些诗的因素,说不定他的诗会更加具有“自由流畅、朴实明净、天然之妙之美”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文为诗”跟唐宋时期中国诗与文地位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背景有关,又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陶渊明诗从玄言诗来,他是在努力恢复“诗”的特点,是“以诗为诗”,而不是“以文为诗”,当然更不是“以文为诗”的开创者。其诗歌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也不宜归结为所谓“以文为诗”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10-14
标签:陶渊明论文; 韩愈论文; 诗歌论文; 玄言诗论文; 以文为诗论文; 古文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散文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