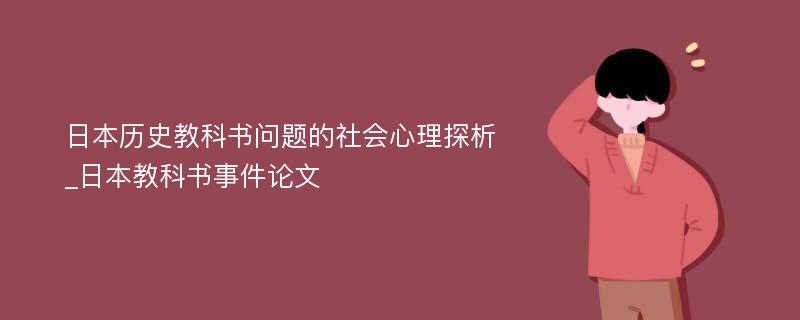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日本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审定通过了由一部分右翼学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国家史实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做一次修订,都要引起一场国际范围的争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顾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总是强词狡辩,利用各种机会来否定过去侵略中、韩等国家的史实,翻历史的定案。在这历史教科书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一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东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骠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不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三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い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社会,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