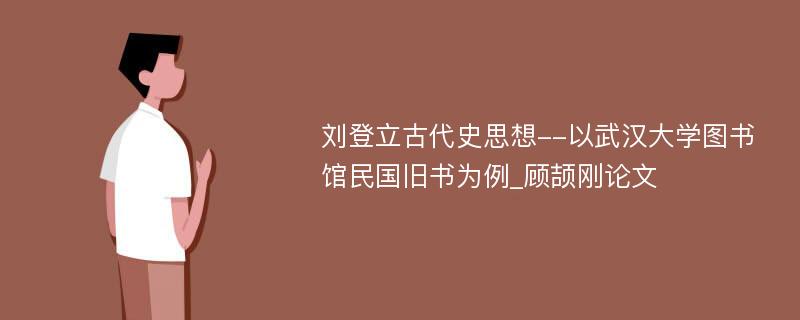
刘掞藜的古史思想——以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民国老讲义为蓝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蓝本论文,讲义论文,民国论文,武汉大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的刘掞藜先生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民国十二年(1923),顾颉刚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刘掞藜率先撰文商榷,刘掞藜等人的批评意见使得顾颉刚不能“停歇于浮浅的想象”,而不得不“愈进愈深”,终于构筑出“古史辨”的学术体系①。因刘先生英年早逝,刘掞藜的名字如今几乎被人遗忘,人们也只能在《古史辨》的附录中才能看到刘先生关于古史的零散论述。所幸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仍藏有刘先生在武汉大学授课的讲义——《中国上古史略》,本文欲以此讲义为蓝本,对刘掞藜先生的古史思想作一简要评述。
一、古史辨运动中的刘掞藜
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在胡适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考辨中国古史问题。1926年,顾颉刚把1923年以来的古史论文及与学界相互切磋的信函、文章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标志着他的古史思想体系已初步形成。顾颉刚在为该书所作的《自序》及晚年的自述中均坦言,作为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他的成果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他的研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多少有点始料未及:
哪里想到,这半封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②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使清乾嘉以来抨击伪书的传统复苏起来,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史坛上的古史辩运动。不可否认,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工作给当时的学术界乃至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顾颉刚的古史思想体系也正是在与当时学界的论辩和交流中逐步成熟、完善的。但是,一种有创新意义的学术体系的形成,仅靠学术观点的惊世骇俗以及辩论中的相互指责是不够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90年前的这场运动时,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辩运动中,到底哪些商榷和争论对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完善和学术体系的形成有切实的建设性作用?
如顾颉刚自己所总结,当时的学界对其疑古言论有誉有毁,而“毁”的声势可能更大于“誉”。对疑古运动批评最严厉、被顾颉刚称为“说我着了魔”的,当是章太炎先生③。经学大师章太炎在古史辨运动的酝酿阶段就批评疑古思潮,称“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④。此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疑古运动的批判,甚至在演讲中公开斥责“疑古之史学”为“魔道”⑤。章太炎对于古史辨采取敌视的态度,主要原因可能缘自他是一位民族感极强的民主革命家,对日本史学界率先进行的怀疑中国古史的相关研究的政治目的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惕。他反复提醒国人:“信谬作真,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不亦大可哀乎?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深望国人能矫正之也。”⑥
可见,章太炎对疑古的批评主要基于政治因素和民族情感,将怀疑古史上升到毁史、亡国、抹杀民族文化的高度。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章太炎先生的这种态度也无可厚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章太炎的严厉批评与胡适等人的“盛誉”性质是相同的,胡适等人对古史辨的无条件称赞与支持,其实主要也是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等需要出发的。
更多的旧学人和旧史家对顾颉刚的古史之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以柳诒征为例,他撰文说:“比有某君谓古无夏禹其人……叩其所据,则以《说文》释禹为虫而不指为夏代先王”,柳氏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对“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法”的基本知识不熟悉,“第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尠不为通人所笑矣”,“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⑦!在经学风气尚盛的民国初年,这种近乎蔑视和讥讽的态度,大体是知识界的一种普遍心理。
民国年间学界的状况,“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⑧,一些有资历、有成就的学界巨擘有时针锋相对,相互发难,恰如古史辨中的章太炎、胡适、柳诒征等人。而一些有学术追求的后学们与这些史学前辈或学界巨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有实力的学者对疑古派观点的商榷其实是有所顾忌、若隐若现的。例如,今天公认为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先生从未公开指责过疑古运动及古史辨,但是他一直主张伪史书中亦有真史料,并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经学在资料等方面的特殊性,指出:“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⑨这些言论,其实隐含了对古史辨的批评。王国维也没有直接批评顾颉刚,但他在清华园中大讲“古史新证”和“二重证据法”,也有借“地下之新材料”及“纸上之材料”纠正人们过分疑古之风的用意。他说:“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⑩
因此,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辨”言论,虽然在学界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但其影响主要在于舆论,就公开的成果和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恰如论者所评价的那样:“在学界仍产生极大波澜,但并未出现有力的反驳。”(11)
正因为如此,刘掞藜批评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在古史辨运动中显得十分突出。相比于其他人过于激烈或过于隐讳的态度,刘掞藜偏向于从学术求真的角度评论疑古辨伪的得失,而且采用了直截了当的正面交锋方式。刘掞藜与顾颉刚的正面交锋并不偶然,在那个时代,他们同属于年青学人,刘出生于1899年,比顾尚幼五六岁。胡适、顾颉刚发起疑古运动时,刘掞藜刚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时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史地部,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征学习。当顾颉刚在北京大学与钱玄同论古书时,刘掞藜在国立东南大学史地研究部工作。可以说,他们在年龄、辈份上旗鼓相当。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基本上被视为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两个主阵地,而胡适和柳诒征则分别是两大史学阵营中的两大导师。因此,刘掞藜与顾颉刚的论争与交流,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大学术阵营的学术论争与交流,也是20世纪20年代多层面复杂史学动态中的一个侧影。
因“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提出和确立,顾颉刚成为古史辨成果的汇集者和收获者。但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认真审读刘、顾两人之间商榷与回应的文本时,不难看出,在学术求真的层面,刘掞藜一直掌握着这场论争的主动权。如顾颉刚《自序》所言,顾氏很早就有疑古辨伪的打算,但由于“向来只知道翻书”,没有“按着篇次”系统地阅读诸经(12),因此,他的灵感多来自于视野所及的部分史料。而刘掞藜早年苦读诸经,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后,才师从史学大师柳诒征,“由经入史”(13)。扎实的经学基础,使得刘掞藜面对以经证史的问题时,能迅速地利用富裕的经学储备,依据实证史学的原则来检验相关命题的是非。1923年2月,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文章发表不久,刘掞藜的商榷文章便于同年5月刊出,文中旁征博引,直指顾颉刚史料和论证的缺失。顾颉刚不得不在“答书”中解释:“不幸豫计中的许多篇‘某书中的古史’还没有做,而总括大意的《与玄同先生书》先已登出,以至证据不充,无以满两位先生之意,甚以为愧。”(14)针对刘掞藜等人的责难,顾颉刚特制定了一个“想一部书一部书的做去”的读书计划和在《读书杂志》上分期发表的回应计划。顾颉刚的回应计划尚未完成一半,刘掞藜便有《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一文回应。面对因各种客观原因“没法做专门研究”的顾颉刚所作的疑古计划,刘掞藜表示“这很足使我们欲早日一睹为快的心陷于渴望的情境”,“先生有很好的证据和说法时,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将这篇大话一笔勾销”(15)。因回应不能如期完成,顾颉刚先是发表启事,称“刘先生《再质》一文,只得等我这文发表完了之后再行回答,望鉴原”(16)!后来又在《自序》中解释说:“因为在家养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个月的生计负担已压迫我回复馆职了,一篇答复的长文只作成了一半。”(17)
总观两人的论争,刘氏多着眼于史料和论证过程,而顾氏多谈“我对于古史的态度问题”;刘氏擅长于就具体问题用充分的史料予以澄清,而顾氏擅长于用宏大的史观去“建立一个假设”;刘氏的回应总是非常及时,而顾氏则不断地制订“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刘氏身体不如顾氏,但只字不提客观原因,顾氏经常强调“养病”、“生计”、“祖母去世”等客观原因。不言而喻,在顾、刘两人的论争中,刘掞藜一直掌握着学术上的主动权。
总之,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运动其实造就了两名年轻人:顾颉刚以其勇于怀疑的精神和反传统的史观一举成名,而刘掞藜则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求真务实的学风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正如其弟子在回顾其生平时所言:
(民国)十二年,吴县顾颉刚君揭其怀疑古史之说于《读书杂志》,先生以其引据多舛,疏解尤不衷于理也,乃再作长函以辟之。源源本本,殚见洽闻……由是海内学者,无不知有先生。(18)
二、刘掞藜对顾颉刚古史思想的促进
在《古史辨》的《自序》中,顾颉刚也“建立了一个假设”:“要是我发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后,没有刘楚贤先生(刘掞藜字楚贤)等把我痛驳,我也不会定了周密的计划而预备作毕生的研究”(19)。这句话真实反映了刘掞藜在顾颉刚古史思想完善过程中的作用。研读两人论争的文本,可知,刘掞藜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力辩难了顾颉刚,迫使顾氏不得不进一步“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从而逐步走向成熟。
其一,依孤证立论和凭臆想理解史料。史学研究最重证据,且孤证不立。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依据粗读《诗》、《书》的印象,提出一些大胆的设想。对此,刘掞藜往往信手列举一连串的反证予以批驳。兹举一例:
顾颉刚读到《诗经·商颂·长发》篇“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的句子,认为“这诗的意思是说商的国家是上帝所立的。……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商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顾颉刚又引用《小旻》篇中“旻天疾威,敷于下土”之句,认为这里“下土”是对上天而言,进一步说明西周中叶以前,人们对于禹的观念是一个神。
对此,刘掞藜先举出《鲁颂·閟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奄有下土”及《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的句子,问曰:
如果以“禹敷下土方”说为“上帝叫禹下来布土……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然则后稷也是上帝叫他下来奄有下土,武王也是上帝叫他下来为下土之法了,他们也是神,不是人么?
果如顾“禹敷下土方”说为“上帝叫禹下来布土”,则“帝立子生商”更明明白白说是上帝置子而生契,若以为禹是神,不是人,则契更是神不是人了。
那末,我们将《诗经》展开来读,神还多呢!
刘掞藜又举出了《商颂·玄鸟》、《大雅·文王有声》、《大雅·韩奕》、《小雅·信南山》、《商颂·殷武》的众多例证,连声追问:“这诗对于禹的观念也是一个神吗”?职是之故,顾颉刚在以后的回复中决定“把‘下土’与‘降’的两词搁起”,重新寻找证据来说明“禹是一个神”(20)。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两篇中,类似这种用大量例证反驳顾氏孤证的例子俯拾即是。
其二,滥引《说文解字》,望文生义。顾颉刚根据《说文解字》对“禹”的解释,认为禹“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并进一步猜想:“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21)
如前,这样的解释,已被柳诒征讥为不懂古文字学的基本知识。刘掞藜也称顾颉刚为“说文迷”,并进一步作了批评:
这种《说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的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我骇了以后一想,或者顾君一时忘却古来名字假借之说。不然,我们要问稷为形声字,是五谷之长,何以不认后稷为植物呢?……九鼎上的动物——“禹”流传到后来成了真的人王,何以不说“稷”为九鼎上的植物,流传到后来成了周的祖宗呢?
胡堇人也撰文质疑顾氏的这种解释:“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说文》禹字训虫便以为禹不是人类,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如何叫人信服呢?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得帝舜就是一种植物吗”(22)?
经刘、胡等人的批评,顾颉刚后来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说:“我上一文疑‘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最引起两先生的反对。我对此并不抗辨,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我现在对这个假定的前半还以为不误,对于后半,便承认有修正的必要了。”(23)
在《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中,刘掞藜专门讨论了顾颉刚对“敷”、“甸”等字训解的失误,批评顾颉刚:
将前人把“敷”字解作“分”,解作“赋”,把“甸”字解作“治”的一并抹杀,自己牵强附会,将“敷”字换作“铺”,用之解“禹敷土下方”……将“甸”……解作“列”,说为“排列分布”之意,用之解“维禹甸之”……又凭空说“治水”的“治”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又硬把“丰水东注,维禹之绩”的“绩”字当作“迹”……(24)
刘掞藜指出:“这种主观的意见是我所最不赞成的。我们解释古书上的字,应依古代的解说。若穿凿附会,迁就己意,是朴学者所最忌的”(25)。
其三,先入为主、曲折求证的治史方法。顾颉刚在《古史辨》的《自序》中多次提到自己“推翻伪史的壮志”,表示要比崔述更进一步,彻底“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而且在很早的时候他心中就建立了一个古史“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好是一个反背”的假设。他也多次述及胡适等新文化领袖对其“大胆的假设”的肯定。在晚年的自述中,他强调古史辨工作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是要把封建经典“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26)。由于这些现实使命和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存在,顾氏在他的古史研究中,就难免根据他的假设来解读史料,或者在史料中为他的假设寻找证据。对此,刘掞藜有明白的提示。例如,对顾颉刚在训释《诗经》中上述关键字的种种失误,刘掞藜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是“因为先生早已有‘禹有神性’的主见在脑子里”(27)。
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未及作答,即先亮明自己对古史的态度。为此,在《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中,刘掞藜用专门的篇幅作《关于先生所持古史态度的讨论》,对顾文中有待论证的观点,刘掞藜提醒说:“只是说《尧典》乃因‘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而产生出来,这话尚待先生辨《尧典》的文字登出读后,才敢说赞成或不赞成”。对证据不足的一些观点,刘掞藜也即时纠正顾颉刚的论证方法,并晓之以正确的态度。如顾氏据有限的“似是而非”的史料提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刘掞藜指出“谓古史中多神话,是我承认的。但举这些例来证‘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是不可不辨的”。在逐条批驳其论据后,又告诫顾颉刚:“故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28)!
在答复刘掞藜商榷的过程中,顾颉刚完成了《答刘胡两先生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两文,一方面修正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寻找新的证据,同时,将自己开展“古史辨”的意义定位在“史观”和对待古史的态度方面,并且就“禹是否有天神性”、“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文王是纣臣吗”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较详细的讨论。这些讨论使得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得以确立,这一史观的方法论意义远胜于史学史意义,且逐渐超出古史研究领域,成为一种基本的史观和方法论,并一直影响至今。
三、刘掞藜的古史观
刘掞藜和顾颉刚之间的论争是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的前沿阵地,从双方撰写的论文中虽也能看出刘藜掞对中国古史的基本态度,但毕竟过于零碎。民国十九年(1930),刘掞藜应国立武汉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其间,曾撰《中国上古史略》作为授课的讲义。该讲义目前收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全书约十万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古史观。
刘掞藜编《中国上古史略》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专门论述“太古史料之别择”问题。第二章至第八章将太古至秦代的中国史分为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
太古至尧舜: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
夏代:君位禅让转成世袭
商代:神权政治时代
西周:封建政治完成时代
东周春秋:霸主时代
东周战国:贵族政治转成君主独裁政治时代
秦代:君主专制政体之初立
通读全书,不难体察刘掞藜古史思想的特点。尽管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充当了批判疑古言论的先锋,但透过他对“太史古料之别择”问题的论述,可以明了,刘掞藜并不反对勇于怀疑的精神,他所极力反对的是“疑古过甚”及“疑古不当”。就史料观而言,刘掞藜对上古史的基本态度也是“疑古”的,他说:
我国太古史事,自来绝无一记载稍完备稍真实之史书。其片言片行,一人一事,惟散见于周秦诸经诸子。而诸经诸子又多讬古改制,或不免传说歧异,真伪杂糅。逮乎汉晋,谶纬杂说云兴,增益附会丛出,太古史事益纷乱难理。……史家著述,往往推引远至五帝以前。神话荒唐,殊非事实!(29)
刘掞藜也引用崔述《考信录》“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的论述,表示要继承乾嘉学者敢于怀疑的治学传统。刘掞藜和顾颉刚同是在继承前贤的治学传统,同是在“疑古”,何以两人却走向了论战的对立面?姑且撇开政治因素,刘掞藜精心编写的《中国上古史略》的八个章节启示我们,刘掞藜疑古的目的在于“建设”——构建出一套在史料来源上基本可靠、能向学生及公众讲授的上古史来。而顾颉刚疑古的目的在于“破坏”——推翻现有的古史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30)。作为中央大学史地研究部的一员,刘掞藜显然不能忍受顾颉刚将中国历史“打对折”的行为。但难能可贵的是,刘掞藜对顾颉刚的批驳没有借民族情感或政治批判来做文章,而基本上从一个纯粹学者的立场,从求是、求知的视角出发来摆事实、讲道理。因此,刘掞藜的古史观显得更冷静、更务实。
在刘掞藜看来,上古史事之所以自古以来即让人生疑,其根本的原因是年代久远,记载缺失、鲜少:“盖太古草昧初开,书契初作,民智幼稚,文物疏陋,虽有史事,无能记载,其后进化,文明渐启,史事稍有记载矣,而亦简约”。因而“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状况,也是历代文人史家早已认识到的现象:“夫孔、左、杨、屈诸子生当春秋战国,去古未远,而已或叹古初之事莫纪,或断唐虞以前史迹弗载,或置黄炎以上之事不道。矧周秦以后,遭秦燔灭史籍之余,而妄言上世,侈谈其事迹,岂非荒诞而不可信哉”(31)可见,刘掞藜的观点很明确:疑古固然重要,但疑古有当疑者,有不当疑者。对于古圣先贤亦无能为力的上古史事,若无地下出土的新证,今人与其纠结于有限的文献,不如采取存而不论、暂时存疑的态度,不然,“各执一说,聚讼纷如,穿凿支离,臆为曲合。究之孰是孰非,无能决定;纵欲深知研诘,而虚无荒渺,徒劳无功;即能曲为别说,终不能得识者之致信。吾人如此,宜弃绝而弗道”(32)。此为不当疑者。
但对于上文提到的讬古改制、传说歧异、真伪杂糅、谶纬杂说、附会丛出的内容,刘掞藜采取了毫不犹豫的怀疑态度,此为所当疑者:
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讬古改制,始铺陈上古人物史事,于是有所谓“五帝”……不宁惟是,且忽增“三皇”之说。……逮秦始皇议帝号,李斯等竟进“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最贵之言。其后桓谭《新论》遂为“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之荒古政治史说。是故有识之士,心常疑之,或斥其诬。
更可笑者,复有所谓中国首治君主盘古之说……诸如此类,不可胜举,而蚩蚩流俗,往往称道之。(33)
刘掞藜的“存而不论”及其所疑和所不疑基本代表了传统史学派“疑古而不疑经”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经”之所以可不疑,是因为“经”正是千百年来人们“疑古”的结晶,“经”之所之被称为“经”,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正由于在与无数谶纬杂说的比较中显示出优势,“经”才被人尊奉。就经书的产生过程和目的来看,一般而言,“经”是为了传信史而教化人民,而不是为了制造谎言而欺世。就史料的选择和利用而言,经书一般比较严谨。因而,“经”自然应该成为当世学者做古史研究时的首选资料。刘掞藜本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严谨奉行者,例如,他遍览群书,发现“我国古代诸书,皆言尧舜有禅让之事。特异说纷纷”,为此,他共列出有关禅让的八种异说,感慨“以上八说,其孰是耶?其孰非耶?其皆想象或‘讬古改制’之言耶?殊莫能明”。经过慎重的比较与选择,终决定“今姑以《虞书》、《孟子》及《史记》为据”(34)。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刘掞藜在构建其上古史框架时,选择立论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对史料选择和利用的严谨与否。《中国上古史略》所依据的史料及参考书,并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五经”或“十三经”,但凡史料运用比较严谨者,刘掞藜会有选择地采用。例如,对尧、舜以前的“太古史”,他宣称:
今余之叙中国太古史迹,惟以《易》、《礼》、《诗》、《书》、《史记》、《韩非子》等取材比较严谨者为据。班固《白虎通义》等论上世社会进化而至于有政治文化之状况,极与今日社会学家所言者相符,殊多可采,故亦引焉。……至如《补三皇本纪》、《帝王世纪》、《拾遗记》及谶纬诸书所言虽详博,但悉属神话杂说,怪诞不经,毫无信史价值,不足闻问。(35)
依据刘掞藜关于古史的上述观点,自然可以将其归入比较“守旧”的传统史家的行列。但他并不是那种拒绝新事物,对世界潮流及国际学术动态充耳不闻的传统主义者。相反,他对当时的东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例如,在论及上古“社会进化与政治文化萌芽”时,刘掞藜特意谈到“后世所命之古人象征名”的问题,他强调指出:
惟吾人须知:所谓庖牲氏、神农氏者,特表社会进化中发明畜牧、发明农业者之象征,非实指一定之某人,或某一人自名庖牲氏、神农氏者。故有历史眼光者,类能知之。(36)
事实上,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各个章节基本按照进化论的史观安排,向读者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无家族、无制度的简单初民社会向“创制渐多与政治萌芽”、“政治组织之渐备”直至君主专制政体确立的复杂社会演变的过程。书中对“宗法社会”的形成、土地兼并与阶级的兴起、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制演变等等方面,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极为相近的精彩论述。这些都表明,刘掞藜对新史观并非拒斥,他固守中国的史学传统,又积极吸收新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并把他接纳到的新知识、新观点纳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系当中去。
注释: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页。
②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③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颉刚回忆说:当时“多数人骂我,少数人赞成我。许多人照着传统的想法,说我着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庙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第18页。
④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0页。
⑤章太炎1935年3月15日在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作《历史之重要》的演讲,在演讲结束时说:“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参见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⑥章太炎《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载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⑦柳诒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载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17~222页。
⑧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第13页。
⑨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
⑩王国维:《古史新证》,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11)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2页。
(12)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13)陶元珍:《亡师新化刘掞藜先生事略》,载《国风》第7卷第1期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第44~45页。
(14)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7页。
(15)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1页、186页。
(16)顾颉刚:《启事三则》,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
(17)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18)陶元珍:《亡师新化刘掞藜先生事略》,载《国风》第7卷第1期民国二十四年九月,第45页。
(19)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0页。
(20)刘掞藜对顾颉刚的商榷详见《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等文,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2~186页。
(2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3页。
(22)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23)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8~120页。
(24)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5)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6)顾颉刚:《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及《自序》,参见《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43、52、80等页。
(27)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6页。
(28)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载《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3~161页。
(29)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1页。
(30)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3页。
(31)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1~2页。
(32)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3页。
(33)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1~2页。
(34)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10~11页。
(35)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1~2页。
(36)刘掞藜:《中国上古史略》,国立武汉大学印(确切时间不详),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