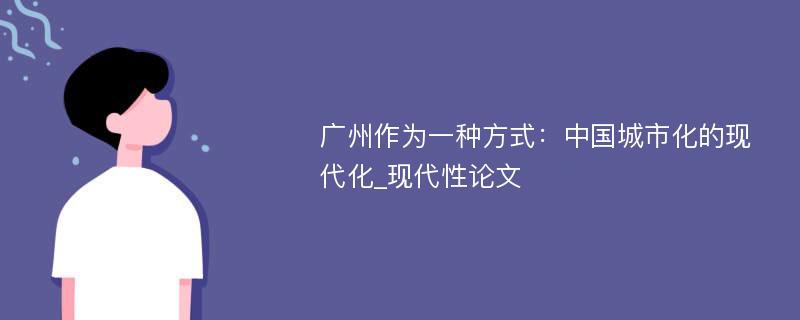
作为方法的广州——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北上广”的位置图绘:现代中心与本土边缘
近年来,伴随高房价、蚁居族等现象,“逃离北上广”这个颇具噱头色彩的口号应运而生。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员百姓,都在纷纷热议。2010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三卷本的“逃离北上广”图书系列,分别为《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州太竞争》。尽管有着炒作之嫌,但从刺眼的标题上,还是可以捕捉到这个华丽时代背后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焦虑、困惑与纠结。所谓“逃离北上广”,是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中的年轻人,由于房价居高不下和生活压力日增,试图以退出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方式,重新选择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但是,仅仅过了一年,“逃回北上广”这个更富戏剧性意味的口号又被大众媒体铺天盖地地抛到了社会面前。①从逃离到逃回,归去来兮之间,夹杂着无名大众的希望与失望、退避与不舍、理想与现实的重重矛盾。其实,在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北上广”作为大都市典型代表所蕴含的中国城市化的现代性问题。
不妨来看,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剧烈变化,最重要的表征便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将自己对现代性的理想和抱负都寄托在了GDP高速增长的衡量标杆上,举国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则更是这一梦想实现的核心载体。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②按城乡人口比重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比率,1949年为10.64%,1976年为17.44%,1978年为17.92%,2011年为51.3%。显然,1949-1976年的中国城市化比率仅增长了不到7%。1978-2011年的33年间,城市化比率却增加了33.38%,并于2011年历史性地突破了50%的界线,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时期,而这一成就又主要来自经典城市现代性的推动。经典城市现代性,在现象层面,是指全国各个城市的面积不断增量,写字楼、立交桥纷纷拔地而起,现代化居民区、豪华别墅群、主题公园、机场等各类建筑竞相纷呈,城际高铁、高速公路、市内轨道交通迅猛发展。在理论层面,则体现为中国当代城市建设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吸收,尤其是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法国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两位人物的思想,前者的“田园城市”③和后者的“明日之城”,④对中国城市化改造和发展的影响尤为重大。它们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美好构想:仿佛只要拆毁了旧城市,就真能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更新更美的图画。“明日”“田园”,似乎应了中国人的那句老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论怎样,至少“看上去很美”。于是,神州大地,处处平地拔起高楼,片片树木化为草皮,各地高调营造花园城市、宜居城市,甚至争建国际化大都市。无数道路挖了又填,无数房屋拆了又建,无数树木倒下,无数广场兴起,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三十年间的中国俨然如一片大工地,以致在海外学者眼里,“拆啦”(China谐音)成了当代“中国”的代名词。⑤但经典城市现代性及其“拆啦”的方式果真带给所有人一个现实美好的大都市吗?
无论数据多么重要,无论景观如何美观,城市化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仍在于人与城市的关系。按照文明史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城市是一个巨型的容器。⑥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是,这个容器越来越大,越来越光鲜了,但是它对于居住其中的人而言,究竟是栖息眷恋的家园,还是难以忍受的牢笼,或许就难一概而论了。也许,那些归去来兮的人们,正是在追求家园理想与忍受牢笼现实之间试图去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但无论怎样,大都市之于放弃者们或追求者们而言,肯定意味着更多的一些东西。就社会大众的想象而言,“北上广”是一种当代中国大都市及其所象征生活方式的标志。这一称谓所指涉的意涵其实远远超过了日常中的房价、工作和前途,隐匿其中的核心焦虑仍是全民族百年来的集体政治无意识,即被称为“现代性”的那个梦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上海、广州同为中国社会寄托现代性梦想的容器,它们之间却又存在着交织了传统与现实的某种微妙差异。从文化心理来看,北京是数百年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则是近代以来迅猛兴起的经济中心;至于广州,虽然一直是中国进行海内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但很少自认为是什么中心。相对于北京、上海那种“双城记”的抗衡与较劲,广州的确一直自甘边缘。从地理位置来看,由北京、上海到广州,的确可以由点到线,画出一条中国东部一线城市的黄金连线。但就历史地位而言,广州的城市影响力却在近百年来落在了京沪两地的后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借助改革前沿的地理和政策优势,广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以其经济和文化影响全国,形成了短暂的“三足鼎立”⑦局面。但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广东再一次被上海赶超。同时要注意,其实广州总是隐匿在广东的背后,哪怕是所谓“三足鼎立”时期,其实也只是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广东与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的抗衡。回到作为一座城市的广州,并无与之抗衡的姿态。显然,在“北上广”的同质化能指的背后,有着一种异质化现实的差异。北京、上海代表了中国大都市的“现代中心型”实践取向,而广州则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本土边缘型”实践经验。
二 城中村与村中城:广州的城市异象
相较北京的帝都气象、上海的十里洋场,广州实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省会城市而已。在一轮轮“明日田园”的城市拆建过程中,尽管广州也如北京、上海一般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时代的现代性滚滚洪流中,但时至今日,北京、上海已然有国际大都市的气度,而广州却依旧残留了某种非城非乡的独特面貌。一方面,广州的现代城市建设,如同全国各大城市一般,也规划了新的城区中心,如1990年代以来的天河区,新世纪以来的CBD珠江新城,并营建了一大批景观地标建筑,如广州图书馆新馆、广东博物馆新馆、广州大剧院、国际金融中心IFC、花城广场、海心沙公园、广州塔,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内部那些无处不在的村落,乍看上去像块块陈旧的补丁,扎眼地夹杂在众多现代建筑、花园广场、城市地标的中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如果从北京出发,历游上海、杭州、厦门,一路往南抵达广州,你会顿生道路逼窄、空间密集的强烈反差感受。无论是飞机抵穗,还是火车达粤,进入市区的过程中,一幢幢现代建筑、一条条城市公路夹杂着一片片由马赛克瓷砖拼贴修饰的村落景观不断映入眼帘。广州绝对不是你所能预想的那种整齐利落的大都市,如果你有过经典现代性城市体验的话。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广州的名声曾让人爱恨纠缠而复杂难言,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前沿,但同时也是在全国出了名的脏乱差城市,加之本地发达的媒体系统对各类社会案件如凶杀、仇杀、情杀等的频繁报道,更使得人们对这座城市烙上了光怪陆离的印象。笔者2008年底第一次赴羊城前夕,一位曾在珠三角地区生活过的友人告知,如果从来没有到过广州,一定要多加小心。当她听说我将抵达广州站时,更是执意要请广州的朋友来接站,因为据说广州站附近陷阱众多,随时可能遇到小偷、骗子、飞车党。由此,广州这座城市留给大众的社会印象可窥一斑。其实,自2008年以来,广州的公共治安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得力于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努力和第16届亚运会的申办,广州站所在的流花地区实行了无死角的全方位电子监控,并开通“越秀区政府流花地区旅客服务中心”,为抵穗旅客提供放心咨询服务。到2010年上半年,广州火车站广场实现了116天刑事案件零发纪录。⑧尽管广州的实际治安有了好转,但城市留给人们的刻板印象却并未彻底改观。今天的广州,尽管不再是个罪恶之城,但仍然是个让人难以由衷钦羡的“美好城市”。至今民间仍流传着对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城市风貌的一种经典评价:“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农村又像城市,城市又像农村。”或许问题并不完全在广州本身,而恰恰在我们如何界定“美好城市”?“美好城市”,是不是简单等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
按照香港学者马杰伟的说法,包含了广州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涵盖粤港澳三地)的城市化进程呈现的是一种“压缩式现代性”。⑨据称,这一理论表述源自文化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的“后都会”(post-metropolis)概念。所谓后都会,是指老工业城市中心的重构,它经由交通网络与领近城市及卫星城镇连接而成为某种超级城阵。后都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大都会不同,大都会是绝对的城市中心主义,离市中心越远城市化程度就越低,而后都会则是散播的城市中心主义,它在城市化网络的不同节点上散布着多个中心。马杰伟指出,大都会对应于第一现代性,它立足于福特式生产、线性发展、工具理性,而后都会则对应于第二现代性,它立足于后福特式生产、非线性发展、跨国工作。在这一现代性问题视野下,马杰伟提出,大珠三角正处于转向后都会的进程中,其城市化进程所显示出的灵敏性和混杂性要比西方同类的形态更富活力和地方色彩。“压缩式现代性”,正是指大珠三角地区特殊的社会构成,即“结合了前现代农业精神、工业生产模式、大都会消费形式和后现代的混杂展示”。⑩无疑,这一切都与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巨大历史社会实践密切相关。所有根源便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启动和加速,在飞速展开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又来不及对农业文明形态进行现代式“祛魅”,大量村落及其文化形态得以夹杂在城市化区域遗存下来,便造就了大珠三角地区这种城不像城、乡不似乡的独特城市化景观。
压缩式现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大珠三角的区域城市化进程与现状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但是,一旦聚焦到广州这一具体城市的内部,其文化生态环境可能会呈现更有意思的一面,而侧重于时空维度解释的压缩式现代性有可能获得更深一层的阐释空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广州那更为细致的肌理纹路之中,才能洞悉隐藏于城中之村与村中之城背后的完整生态结构。
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认为:“从本质上来说,城市本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11)在林奇的眼里,一座城市是具有某种可读性的,可读性并不等于美观性,它是指能够使人容易认知城市的各部分并方便形成一个凝聚形态的特性。基于可读性,林奇提出了“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这一观念,它具有某种深刻的人文学内涵:“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事实上,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12)显然,“城市意象”的评价标准并非是外表观赏性的“美”,而是内在关系性的“好”。
林奇对于城市的这种充满温情感、敬畏感乃至人性感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何谓美好城市有着非凡意义。因此,为了避免在字面上将“美好”片面等同于“美丽”,也为了避免在理论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田园城市”“明日城市”这类经典城市现代性的观念,更为了避免在经验上将“城市意象”简单等同于以经典城市现代性观念而营造出的高楼大厦、广场外滩、花园绿地,我们毋宁将之作些许调整,以“城市异象”来指称广州的独特城市景观及其所包蕴的某种独特方法论意味。任何一个初到广州的人,其实很容易迅速而清晰地将它与北京的广场意象、上海的外滩意象区分开来,其“异”所在正是它那“城”与“村”的杂糅景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主张:“最简单的、表面的东西也就是最高级的东西。”(13)城中村与村中城所表征的广州异象,也许不仅是这座城市的表面,而且是其所包含的现代性问题的本质。
三 生态城市现代性:“村际群落”的地方性知识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城中村”的说法,但是严格来看,却只有广州的“城中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学者高小康指出:“其他大多数城市的所谓‘城中村’其实是在城市规划尚未涉及的城市边缘地带,被称为‘城乡结合部’更妥帖。而广州的城中村却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城中村’——它们大多数的确是插在已经建设起来的繁华市区中的一个个村落孤岛。”(14)由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城中村”模式:第一种是普遍的城中村,普遍性并不等同于典型性,尽管它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地理位置上却多为城市化改造或建设规划未曾关照到的城市边缘地带,其实更妥帖的称谓是“城边村”;第二种是典型的城中村,典型性也不等于普遍性,它主要就是指广州城中村,地理位置上多为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村际群落。这里,与高小康的界定略微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广州的城中村并非“村落孤岛”(village island)而是“村际群落”(village community),隐匿其后的是尚未获得深入认识的一种地方性经验及其知识。
认真比较一下普遍性城中村和典型性城中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差异。
首先,在布局关系上,前者是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带的一些散点,构不成线、面联系,更谈不上与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断裂和依附两种简单关系。后者的城与村关系既不是断裂绝缘,也并非简单依附,它们具有某种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曾举“鸭兔”图画的奇妙效果,(15)既可视为乡土村落嵌入了由商贸中心、现代公路所构成的城市领土,也可视为城市中心为乡土村落、传统河涌(河涌是指遍布珠三角地区的河水分支、岔流)所团团包围。
其次,在历史经验上,前者是经典城市现代性进程尚未波及的剩余区域,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界定,它的前途终究将变为高档楼盘、花园广场和新一轮的城市地标建筑。而后者则是名副其实的村,有着自己独特的村落历史传承感,这种传承感不仅体现为实体建筑与场所,而且体现为一种民风习俗的村落精神而存在,它复杂地包含了经典城市现代性所无法理解的地方性经验。
最后,在生态结构上,前者隶属于经典城市现代性的建设,远离唯一的城市中心,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死角,要么凋敝落后,要么奄奄一息只待拆迁。后者则处于大珠三角的这种压缩式现代性的区域结构之中,并不远离某一绝对城市中心,有的甚至直接处于新的城市中心位置,虽然它们有着藏污纳垢的负面现状,但也有着走马观花者若不置身其中便难以觉察的生态活力。
这里,不妨以广州城区内最富代表性的城中村猎德村为例来研究。猎德村,是广州市天河区属下的行政村,位于现在的广州城区新中心珠江新城的南部,村地域范围东接东圃镇石东村,西邻冼村,南濒珠江,北至黄埔大道。据《天河区志》记载,该村建于宋朝,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截止到2007年,共有户籍人口7000多人,3300多户,还有1万多外来暂住人口。传统的猎德村,珠江分支猎德涌从村中流过,将村庄分为东、西村,河两岸景色秀美,村内保留着大量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石板街、古河涌,具有岭南水乡特色。沿河涌岸边分布有约十座岭南风格的清代祠堂、家庙和家塾,甚至村内每条老巷的名字,譬如崇惠里、德仁里、抗日里,都沾染着浓浓的历史传统情韵。(16)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岭南文化村落的典型代表,它一直保存了包括“扒龙舟”在内的诸多民风习俗活动。每到农历五月初一,总是要以村里的氏族为单位联络起来,然后同全广州的其他村落进行扒龙舟的竞赛。据介绍,扒龙舟、舞醒狮、唱粤曲都是猎德村延续上百年传统的风俗,而猎德村最著名的“花龙”(即船身有彩绘的龙舟,其他地方的龙舟则或是红龙,或是黑龙)和“游龙探亲”更是广州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17)这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好留存,正是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城中村的最重要特色。每到年节,各村之间都会组织适时的风俗活动,在珠江大小河涌里,在村落古老巷道里,或扒龙舟,或舞醒狮。可以说,正是城中村的存在,为岭南文化的保留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并非我们今天在诸多旅游城市所能看到的那种仿民俗或伪民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岭南民间文化的活态保存。
当然,在历史文化传承之外,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城中村,确实也存在藏污纳垢的一面。由于广东地处开放前沿,流动人员数量巨大,而城中村的那些“握手楼”以其低廉房价满足了众多底层人群的需求,于是飞车党、背包党、企街女等无不寄身于城中村。但这个问题需要更为辩证地看待,不能因负面的存在而漠视了在更大范围内的城中村的文化生态意义。
实际上,城中村在城市中心的存在,为更多的正常弱势群体提供了一片可以寄居的屋檐。就广州而言,可以举出许多这种结构性生态共生的例子。比如,海珠区的康乐村毗邻广州国际轻纺城,天河区的石牌村毗邻天河电脑城,前者是国内最重要的纺织品集散批发中心,后者则是广州最大的数码产品市场。在这里工作的数量庞大的打工仔,其食宿问题都可在附近城中村获得相当低廉而合理的解决,同时又减少了中心与郊区的通勤人数。而在北京,就连租住并不便宜的地下室都有随时被清扫出门的可能,广州城中村所表征的独特之处还不明显吗?一般常言,广州是个大市场,此言不虚。但严格来看,广州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贸交易城市,如果缺少了这些嵌入城市中心地带的村际群落,恐怕会要大大增加其人力和交易成本。相较负面状况,城中村所起的这种经济生态效应一直被简单忽视了。更重要的是,城中村的存在还展现了一种包容底层民众甚至弱势群体的城市文化价值取向。广州城中村不是离心化的,不是在经典城市现代性进程下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剩余物,而是一直位于广州城的各个贸易商圈周围和城市中心地带,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着隐性的补给和支持。
美国学者理查德·瑞吉斯特(Richard Register)曾描绘过理想中的“生态城市”,它包含有“就近居住”“紧凑规划”“生态多样性”等规划原则,以高密度、功能互补的方式来规划城市。瑞吉斯特认为,“生态性”的核心意义就是“功能共生”。(18)鉴于此,我们认为,广州的城与村,正体现为一种杂糅了经济文化诸多意味的生态式现代性,而并非简单时空意义的压缩式现代性。压缩式现代性,终究隶属于一种发展的、进步的时空观,它并未承载更为复杂的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生态式现代性,不仅区别于片面强调“旧貌换新颜”的“拆啦”式经典城市现代性,也没有止步于一种播撒形态的多中心城市规划想象,它的意义在于,跳脱受启蒙理性主义支配的客观物化态度,将城市视为城市境况,多元人群生存其中,它包容着他们的感情与记忆、困顿与期待。
生态城市现代性的现实载体正是村际群落。如前所述,“村际群落”,不同于“村落孤岛”,原因在于:首先,村落与村落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猎德村、康乐村、石牌村这些广州本土村落个案,在民俗文化上充分展示着村与村之间依然保持着数百年来的交往与友谊,那些扒龙舟、舞醒狮的绝不是拿工资或劳务报酬的临时演员,而是本土本村的村民,到今天仍不乏“80后”乃至“90后”的后生仔。其次,村落与城市之间也是相辅相生的。一方面,城市经济为村落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和外来人口,在耕地几乎被城市征用的现代性境况中,依靠商业租赁或住房租赁,村落的经济仍能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村落的存在也为城市提供了一道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景,本土本乡的古老村俗为现代城市商业中心增添了并非刻意而为的文化多样性。除此之外,村落还为现代城市起到了降低人力成本、减少通勤人流等作用,减少了诸多现代城市的通病。
四 认同重塑与美好城市:多元现代的“今日之城”
2007年,猎德村,这座珠江边的典型性城中村还是遭遇到了城市改造这一现代化的必然命运。但是,这是一场不同于国内普遍“拆啦”模式的“非典型”改造。其实,从1996年开始,猎德村的土地就陆续被征,用于建设广州新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自2007年10月始,猎德村更是全面开启了旧村整体改造规划。对于国内普遍性的城边村而言,人们关心的无非是在城市改造中为自己要个高的补偿款,大多数城改的关键问题都在于经济利益。但是,猎德村的改造,关键问题却不在于补偿款的多少。当时社会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保存猎德村的古老岭南风情原貌,如何在改造的同时还能传承扒龙舟、舞醒狮、唱粤曲这些毫无经济效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血脉。
猎德村的改造并非一味拆迁,而是注重保护村民利益,保护和延续历史文脉。2007年,广州市政府对猎德村改造提出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猎德村的改造主体是村民,原则上市、区两级财政不投入,通过拍卖复建安置剩余用地筹资改造旧村,确保改造工作收支平衡,确保村民住宅复建和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二是拍卖剩余用地,在扣除必要的运作成本和必须上缴国家、省的有关税费后,将土地出让金等土地收益全额返还给村,用于城中村改造。(19)改造方案将原猎德村内具有历史与人文价值的宗祠,规划于新建的猎德大桥东侧,在邻涌边及池塘边集中复建,结合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功能延续猎德的建筑文化和宗祠文化。对于其他不作集中迁建的古建筑,结合区内园林绿化进行统一设计,同时按民俗传统在北边设置池塘,以保证延续猎德传统龙舟文化。(20)2010年,猎德村改造完成,可以说,这次改造较为完善地保存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原村民在改造完成后原址回迁入住复建现代化楼房。虽然村民的居住条件有了变化,但四周保留或复建的猎德宗祠区、猎德牌坊、龙母庙、岭南水乡民居依然向经过的人们展示着一个村庄的久远历史。至今,猎德村民们仍然居住在这块乡土上,每逢端午、新春依然扒龙舟、舞醒狮。甚至入住复建安置区时,村集体还主持摆起了808桌的露天宴席,款待入伙新居的村民们。(21)“吃饭”所表征的是一个最重要问题:古老村落群体认同的保留与延续。
这种村落性、宗族性的群体认同感,正是广州本土的地方性经验所不同于北京、上海的独特之处。广东地处岭南,其本土族群基本可分为广府群体、潮汕群体和客家群体三大文化族群。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宗族认同意识。这种渊源有自己的传统认同,至今仍然保留在岭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即便在城市,也遗留在了城中村的文化血脉内。如果按照普遍现代性观点来看,这似乎有点“旧风俗”的嫌疑。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个尚未完全“祛魅”的世界。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传统身份认同的存在未免没有给我们提供别样理解城市现代性问题的契机。
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指出,西方“原生的”现代性文化方案造成了三种重大变化:强调人的能动性以及人在时间之流中的位置观念,赋予人对于自主创造未来一种新的想象;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使之丧失了以往的合法性;给予人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去质疑一切未曾“祛魅”的事物或现象。(22)同时,这种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还具有同质化和霸权化的性质,妄图随现代性在全球扩张而得到普遍应验。但事实却是,现代性的确蔓延到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却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制度模式。社会和社会之间,文明和文明之间,有同也有异,此即为“多元现代性”。(23)
其实,经典城市现代性正是这一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的附属品。它主张城市的功能分化,区隔作为工作场所的城市中心与休息场所的花园新城,甚至极端厌恶老城市,主张推倒重来。只要回顾广州的地方性经验,我们就会发现经典城市现代性正是近代以降西方普遍主义和文化霸权的产物。它的根本症结在于,没有考虑到城市是“人”的城市,人本身更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的生成体,只有依托具体而多元的文化土壤才能更好地生活。因此,一座城市的“美好”,并非“田园城市”“明日城市”的乌托邦蓝图,而更应该是充分具有历史包容性、文化包容性、阶层包容性的系统生态筹划。再深入一层来看,美好城市的根本要义,并不在于整齐利落、现代豪华,它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人们对于城市本身的认同感,感觉到自己命运与城市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央商务区的周围,居然能保留下整整一个村落及其生活方式,这是比仅仅维护古建筑更有意义的启示。
按照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看法,“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24)它的三大动力是“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它们共同瓦解了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将人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然后再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进行“再联结”。就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是社会关系总和”来看,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传统社会关系的打破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但是,新型社会关系一直存在深刻的危机。在传统社会中,人的身份意识体现为对祖先、宗族等共同体的传统归属感。进入现代社会,一切的传统归属感被无情地“祛魅”,被专业分工乃至跨地区、跨国界的工作流动消磨殆尽。在这种过程中,人开始产生了“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以自我的反思性来为自我赋义。就此而言,现代性规划可以理解为自我认同取代了传统认同,自我认同塑造出了一个貌似自主有力的现代主体。但远离传统归属的另一面,却是现代人普遍的焦虑心理,以及时而涌出的“个人无意义感”。(25)焦虑的根本在于,仅仅拥有自我其实根本无法支撑起全部的人生意义,否则“死亡就意味着失去唯一属于你的东西”。(26)失去了传统归属,个人的生存便为孤独焦虑和永恒死亡所威胁。
本文伊始所提及的“逃离北上广”与“逃回北上广”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其实正是这一现代性症候的中国版呈现。归去来兮的群体,绝大部分都并非“北上广”的土著居民,更多的是打工一族、奋斗一族。这些群体怀揣着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美好梦想,从乡土社会抽离出来进入大城市,基于现实压力与认同迷惘,徘徊不已,盘旋来去。这种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和不舍,又无不和承载它们的容器——城市——这个母体密切相关。虽然,以猎德村为代表的广州本土城改案例,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后传统社会中乡土村落与现代城市的生态共建问题,但是如何在更为广大的非本土流动性人群与一个古老城市之间建立新的归属感、认同感,是包括广州在内的中国城市现代性改造所面临的更迫切的问题。
作为方法的广州,留给了我们一种现实主义而非现代主义的观念启示: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座“今日之城”,而非“明日田园”。
注释:
①于德清:《年轻人为什么又逃回“北上广”》,《新京报》,2011年7月17日;北岸:《年轻人为何“逃回北上广”?》,《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贺兰:《逃回北上广:无处安放的青春》,《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
②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2月12日发布,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③[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00。
④[法]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李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⑤鲁晓鹏:《文化·镜像·诗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49页。
⑥[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16页。
⑦杨东平:《城市季风》,新星出版社,2006,第365~371页。
⑧林劲松、涂峰:《广州火车站十年治乱》,《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27日。
⑨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⑩马杰伟:《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第5页。
(11)[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第3~4页。
(1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第3页。
(1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8页。
(14)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文化的包容性》,《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5)[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第270页。
(16)樊克宁、邓琼:《未来猎德村,岭南民居还是高楼大厦?》,《羊城晚报》,2006年8月22日。
(17)李立志:《猎德村:最后的扒龙舟》,《广州日报》,2007年6月20日。
(18)[美]理查德·瑞吉斯特:《生态城市》,王如松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10页。
(19)谭希莹、孔小云:《猎德村“头啖汤”成功饮》,《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27日。
(20)广州规划在线,http://www.upo.gov.cn/pages/zt/ghl/gh10years/lswhmc/case/2010/5216.shtml。
(21)刘显仁、黎亮:《广州获整体改造城中村摆808围酒席招待村民》,《广州日报》,2010年11月22日。
(22)[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39页。
(23)[美]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第5页。
(2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2页。
(25)[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6页。
(2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45页。
